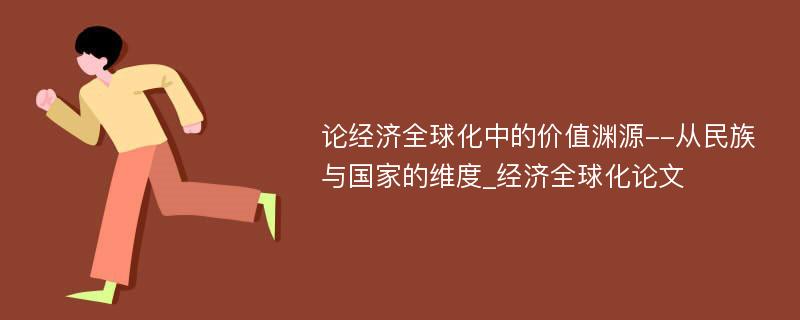
论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来自民族-国家维度的诘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原点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民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价值原点”一词所标识的是在民族-国家维度,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原初价值立场与基点。这样,本文就是从价值论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活动本体的价值关怀。“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诘辨,不过,它主要不是针对经济全球化本身的价值合理性——这作为一个基本前提存在——而是针对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的合理性诘辨: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应当是什么?依据何在?
“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是典型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当今正在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正在对人类经济活动乃至整个人类存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世界交往、普遍联系不再是某种抽象的学理,正在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经济地球村的出现,每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每一个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这个地球村的一员,相互依存。这意味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在这个世界市场中,资本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意味着一种经济交往制度的全球性扩展,一种新的世界交往关系及其秩序的形成。那么,这种新的经济交往制度的全球性扩展、新的世界交往关系与秩序的形成,对于现有世界交往格局、尤其是对于晚发民族-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说肇始于几个世纪以前的经济全球化的萌动是与殖民地扩张如影随形的,那么,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经济全球化,是否还会带有某种特殊的没有殖民地的殖民地之可能?
经济全球化表明在世界市场形成基础之上,新的世界经济分工及其秩序的出现。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对于晚发民族-国家享受人类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分工发展所带来的福祉,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它是否仅仅带来福音,而不会同时带来某种忧虑不安?晚发民族-国家一般均是经过漫长艰苦卓绝斗争,在近几十年中才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刚刚开始获得自己某种脆弱的自由,这种刚刚开始生长的自由个性,会不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湮没?
其二,中国加入WTO指日可待。顺应世界普遍交往大趋势,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融入世界交往中,其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领域。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融入世界交往之中,有没有一种价值基点?
其三,在人文价值精神层面,世界正涌动着一股普世主义或普世伦理思潮——我称之为普世情结。这种普世情结是对人类当代多元对立、相对主义盛行的孤离化、离散化倾向的反思。希望多元基础之上的一元价值,既使人类能够寻得某种共同的精神家园,又使人类在行为实践层面有所规导与约束,当然是极富意义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普世主义或普世伦理如何得以确立?如果说我们对于人类存在、对于世界市场、对于经济合理化亦负有一种责任,那么,这种责任是何?应当如何恰当地把握这种责任?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交往”理论,试图揭示一种新的人类存在范式。但是“商谈”、“交互主体”的具体规定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普世主义或普世伦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与“商谈”、“交互主体”的关系又怎样?我们在全球化经济活动关系中能透视到什么样的当今人类可能生活图式?
二、西方中心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既往历史
经济全球化本身给人们带来这样一个感觉:似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价值的立足点应当是全球的,而不是某个民族-国家的;既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活动,那么,就应当放弃特殊的民族-国家立场,而确立起普遍的世界主义立场。这种感觉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既然是全球化的经济过程,那么,确实应当具有某种全球化的价值指向,否则,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然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全球化的经济新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全球化的经济新秩序是各民族-国家经济交往活动的结果,还是一种预设?如果说是一种预设,又是谁在预设?是否所有民族-国家都平等地参与了这种预设?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经济全球化缘于资本扩张之全球化流动的内在冲动,它是一个以世界某一区域为中心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上溯至16世纪初的世界地理大发现,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及其全世界发展。当初,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为了向外寻求资源、廉价劳动力与市场,通过武力扩张、建立殖民地的方式,推进了经济全球化。此时的经济全球化与殖民地化或殖民地掠夺是同等意义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这一实质内容,及其西方民族-国家的价值原点属性。他们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是在资产阶级的这种扩张过程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这些论述,深刻说明了经济全球化既往历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这一价值内容及其历史事实。
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是市场经济自发冲动基础之上的自觉活动。首先推进这个进程的是那些最先进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向外扩张,试图抹平民族-国家间界域,建立资本全球性普遍流动的新秩序:即,经济全球化、建立新经济秩序的过程,是以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为主体、为其自身利益建立起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不仅是经济扩张,还有政治扩张与文化价值扩张。在这个过程中,晚发民族-国家起初以被动的方式被强行纳入这个经济全球化轨道,不得不接受这种经济新秩序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但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趋势,已被越来越多的晚发民族-国家自觉认识,并自觉融入;而随着晚发民族-国家的自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及其具体内容会与以往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晚发民族-国家以被动的方式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某种不平等位置的状况。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民族-国家居于强权主导地位,并由于其自身所处的主导地位独立特行地先行创制了一系列世界性经济交往规则,并利用强权优势将这种交往规则推广至全世界的所有民族-国家,作为具有可公度性的普遍游戏法则;另一些民族-国家则由于其晚发特点——其中又以被殖民地化以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为首要特征——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接受那些既有的世界经济交往规则。因而,这些民族-国家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极不平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不平等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世界经济交往规则的他在性,即这些规则首先是由那些先发民族-国家制订,并且至少在初始阶段主要反映与代表了那些先发民族-国家的利益;其二,经济实力本身的巨大差别,先发民族-国家通过殖民地化,以血与火的方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率先实现现代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秩序;而晚发民族-国家则由于以被殖民地化为代表的诸多因素影响,实现现代工业化、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秩序,仍是一个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晚发民族-国家如果抛弃历史的因素,不考虑殖民地运动所造成的历史事实与自身的特殊境况,放弃自己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原点,天真地将既有经济全球化秩序奉为圭臬,很可能使自己在21世纪处于一种没有殖民地化的新殖民地状态之中。
既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是由先发民族-国家制订的,晚发民族-国家在进入经济全球化时,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反对霸权话语,争取平等参与世界新经济秩序规则的制订,改变既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多元世界的共在共生理念之下,构建起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包括晚发民族-国家利益在内的全球新经济秩序,而这离开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自身价值本体地位,则是不可想象的。
三、“商谈伦理”:困境与出路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新秩序,内在地要求有一种超越狭隘民族-国家视域、关照全人类的普世主义精神。没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精神,经济全球化及其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真正建立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普世主义精神既是人类在当代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如经济、生态、环境、人口、战争与和平、新技术运用等一系列问题的前提,亦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公民的内在精神规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普世主义精神何以确立?
哈贝马斯针对现代性中的多元性及其统一性问题,提出了“商谈”、“交往”的“商谈伦理”思想,主张通过对话、沟通,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及秩序。在抽象学理上,“商谈伦理”表达了一种主体间关系。虽然主体间关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自身主体,但是主体间关系却是以独立主体及其利益存在、以及对这种独立主体存在及其利益的自觉意识为前提。在此基础之上,自我主体在理性的指导之下,通过实践理性能力,逐渐构建起一个我们的共同生活世界,达于我们-主体这样一个主体间关系境地。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实质上所秉承的仍然是契约论方法,只不过较之传统契约论更为理智,少了那种自然性的原初特征而已。但是所谓“商谈”、“交往”过程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成员相互间在实践中的契约过程,用哈耶克的语言表达,就是“理性累进”性过程,其优点是最有利于在抽象角度揭示存在者间平等的自由权利。然而,契约论方法本身亦预设着契约方价值立场的自身本体性:自身的存在及以自身为出发点,因为舍此则契约活动就无法进行。只要是契约论方法,就必不可免地坚持自身本体的价值立场。
“商谈”必须在一种历史的眼光中来认识。在历史的维度中,民族-国家间“商谈”并达成经济全球化新秩序;但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有其特定的背景:既有的“商谈”对话规则,各民族-国家的特定历史与现实状况,及在既有民族-国家间关系中的利益格局,等等。正是这些背景,决定了最终“商谈”结果。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前述,一方面,这些对话规则是由西方发达民族-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而制订的,它们凭借经济全球化中的统一活动规则之理由,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市场经济活动规则表达的话语形式本身就是霸权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民族-国家在既有市场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且凭借其已经形成的政治、经济力量,通过跨国公司对经济全球化过程本身施加影响乃至控制。因而,这种似乎平等的“商谈”,在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一组数字可以佐证。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尽管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金融市场等方面受到限制所产生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则表明,贫富国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人均收入的差距由1960年的30倍拉大至现在的74倍。占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它们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额的68%,全球电话总数的74%。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以一种“先位优势”的方式居于中心地位。这至少表明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并不是民族-国家间的平等,亦不是民族—国家自身本体价值取向的消解;相反,民族-国家的自身本体价值特质以一种极为赤裸裸的方式存在着。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扩大。民族-国家间的“商谈”一开始就是以实力、以不平等为基本特征的。
这种不平等的“商谈”,令人想起斯密所谓自由经济的自身本体价值特质。自身本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仍然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着。哪一个民族-国家若放弃价值的自身本体性,这个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仅会受到来自本民族内部人民的强烈反对,亦会在世界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斯密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揭示的下述思想具有真理性: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主体价值基点的自身本体性就是必然的。那些以经济全球化中应遵守市场经济交往规则而否定价值自身本体性者,不是理论上的幼稚,就是实践上的别有用心。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商谈”,是在坚持价值的自身本体基础之上的交流、对话、沟通、协作、竞争、互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斗争,并以实力为基础。
对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商谈”的这种理解,并不否定应当确立起某种普世精神,并不否定每一个民族-国家对于人类应当承负的责任;相反,恰当的普世精神的确立是世界交往、经济全球化活动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问题的关键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普世精神的合理理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普世精神、人类责任,在民族-国家层次上最基本的就是经济交往活动中的人本价值取向,自主主权,民族-国家间平等,权利义务间平等,相互间平等,等等。离开了这些最核心内容,普世精神很可能成为霸权主义意识形态。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跨国公司,对整个世界交往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冲击着人类近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疆域,乃至使民族-国家有衰落之危机。在这个背景下,再在民族-国家维度提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自身本体是否恰当?跨国公司给人类世界交往活动、既有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以及既有民族-国家主权等问题均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新课题,甚至跨国公司与自己母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但是,不可将跨国公司神化,更不可因为跨国公司的出现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而轻率地否定民族-国家伦理实体或独立主权利益之地位。
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深刻揭示的那样:“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从某些方面看,与其说它代表着均势学说的延续,毋宁说它企图把美国宪法条款推及全球”;虽然联合国对于维护国际安全无济于事,但人们对于联合国的关切“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基于对单个国家主权的深切许诺”,“它推进了而不是削弱了民族-国家作为当代普遍的政治形式的首要地位”。(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8页)虽然吉登斯直接说的是民族-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但其所论对于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亦同样适用。更何况对于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问题如果不从国际政治、民族-国家间关系角度认识,总是浅薄的。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新世界经济秩序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一方面各民族-国家应当具备平等主权的理念,在一种平等权利基础之上“商谈”,构建起新秩序框架;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这个“商谈”又总是居于自身民族-国家独立、主权与利益基础之上,且又总是以一定的实力为依据。经济交往活动中的普世主义精神,不是超人类力量所设定与强加的,而是人类所有民族-国家平等参与所形成的、真正代表所有民族-国家利益的伦理关系的结晶。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中价值原点的真实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