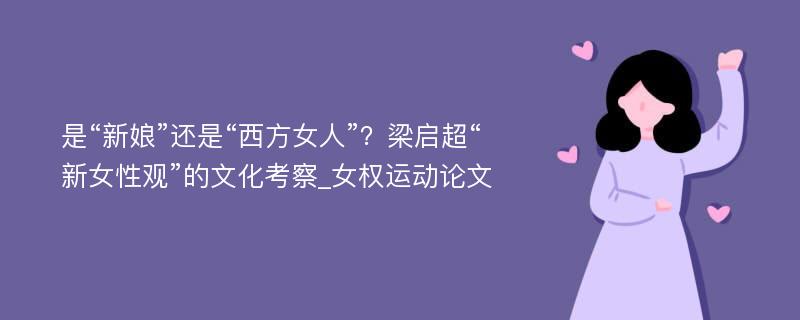
是“新妇”还是“西妇”?——梁启超“新妇观”的文化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妇论文,文化论文,西妇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4)01-0032-06
一、现代“西妇观”对维新派“新妇观”的批评
近十几年来,一些关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专著和文章,在分析到梁启超及维新派的妇女观时,大都采用这样的理论批评范式:一方面承认梁启超等人“反缠足、兴女学、倡女权”的新妇观,是对数千年封建意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撼;另一方面却认为,维新派把妇女解放局限在培养“贤妻良母”的狭小圈子里,与近代以来女权运动所提倡的女性独立人格大相径庭,(注:这类文章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有兴趣者不妨信手找几篇相关论文来看,大体都没有超出这个调子。随便举两例:“这种贤妻良母的女学观仍然未能给女子以独立的人格,而把女子限制在为妻为母的地位,但较‘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是一大进步。”(参见霍占雄《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清末最初出诸男性本位、由男性宣传家来提倡和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忽略了女子本身的参与权利和志向兴趣,有‘越俎代庖’之嫌,因此以男性宣传意识为定位的妇女运动,不能够称得上是全面完善的妇女运动。”(参见陈三井主编《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第72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甚至有学者因此而断言,这种由男子提倡的妇女运动,本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因为“女权运动,必须是妇女自觉自发地去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P198-199)我们把这种看似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观的当代妇女理论批评范式,称为现代“西妇观”,它实际上是把西方近代女权运动当作中国妇女运动的标准,把原本一体的维新派“新妇观”割裂成传统的部分及现代的部分,在肯定了维新派妇女运动“历史意义”的同时,却又抨击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主要由男子倡导”,“仅有少量妇女参加”;“重义务,轻权利”;“把解放妇女的目的,划定在‘相夫教子’的狭小圈子里”,“与男女平权的主张相悖”[2](P105-111)等等。认定维新派的妇女观,是在落后的中国传统两性文化与先进的西方近代女权理论之间做痛苦挣扎,而又难逃传统文化束缚,因而与“现代妇女运动”相去甚远。这种现代“西妇观”极具代表性,而且非常有影响力,实际上,它不仅仅反映在对维新派妇女观的批评这一点上,而是广泛渗透到对中国近代以来妇女观和妇女史的众多评说中。(注:比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妇女观的评述,认定了“子君”式的悲剧源于新文化运动同仁在妇女理论建构上的“缺失”,亦即先天不足的对西方“权利意识”、“独立意识”、“自我意识”的缺失;新文化运动中“女性主体成长中的空白,显露了不仅是女性自身,而且也是整个现代史上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参见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绪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是彻底改弦更张,依样画葫芦地照搬西方?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地固守传统?抑或在两者间创出一条立足文化传统而又力争与时俱进的“中庸之道”?如果说,“西妇观”的实质是全盘西化或西体中用的话,粱启超的“新妇观”则属于“中庸之道”——既非照搬西方,亦非固守传统,而是在传统的“阴阳和合”框架下,要求中国妇女与中国男子一同与时俱进,像男人一样开眼看世界,像男人一样提高自己的“智识能力”,并通过“智识能力”的提高,自立于社会,不仅能够做到“自养而不待养于他人”(《变法通议·论女学》),还要以提高了的“智识能力”教育好下一代,为培养新国民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从而最大限度地开掘和发挥妇女的主观能动性,以应对这纷纭复杂、变化多端的动荡社会。(注:现代“西妇观”把梁启超的“智识能力”说局限在西式的“教育”理念之下,仅仅把它看作梁启超等人“反缠足”、“兴女学”、“倡女权”的三大妇女解放思想中“兴女学”的一个小小内容,甚至认为他们为了现实的需要,重视的是对妇女的“教化”,而没有对妇女的“权利”给予应有的重视。这实在是舍本逐末,窄化了梁启超的本意。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理念从来是“以人为本”、“全方位”的,梁启超之所以把提高女子的“智识能力”放在“竞业”、“参政”之上,就在于他的“教育”理念打着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先得把做人条件预备充实,才能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人权与女权》)。)也就是说,它并不存在“西妇观”派学者所以为的那种“对立”与“二分”,相反,他们的中国妇女观最大的理论贡献及其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中的最大功绩,恰恰就在于他们对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努力整合之上。
我们认为,粱启超和维新派的“新妇观”,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国情、力图推动中国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本土化妇女观;而近现代的“西妇观”,实则是忽视中国文化传统和脱离中国国情,将西方文化传统当成“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来“折磨”中国妇女运动的西化妇女观。
二、梁启超“新妇观”的历史文化追踪
梁启超及维新派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与异质文化冲击,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不但重视妇女在挽救民族危亡过程中的作用,视“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3](P469),而且还比照西方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经济独立,倡导男女平权的现状,曾经形成一个共识:即把中国妇女看作呆在家里,坐享其成的“分利者”,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者,并认为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中国就会永远地贫弱下去。用严复的话来说,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囿于家内,恃男子以为养;迁流既极,男子亦不能自养,而又仰给于他人。“展转无穷,相煦以沫,盖皆分利之人也……国弱民贫,实阶于是。”[3](P468)粱启超则根据西方国家经济学理论:“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指出中国社会贫弱的原因就在于:“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维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虽说造成中国这种“一人养数人”的局面,“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业为最初之起点”(《变法通议·论女学》)。而要想使中国妇女成为“有职业”,“能自养”的社会一员,就必须让她们放小脚,出家门,进学堂,增广见闻,拥有“求学”、“谋职”、“婚姻”的自主权,甚至政治上的男女平权。概括地说,就是废缠足,兴女学,倡女权。维新派的这一“妇女解放”思路,也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典型思路,从“辛亥”到“五四”再到新中国,可谓大同小异,一脉相承。
但维新派的思想观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事的演变和思想的升华,严复、粱启超等维新派精英人物的新文化观,程度不同地扬弃全盘西化观,朝着本土化方向迈进,其妇女观也就从全盘西化的“西妇观”转向本土化的“新妇观”,即将废缠足,兴女学,倡女权这些妇女解放主张仅限于政治层面,而社会和文化层面则着重强调男女“阴阳和合”传统的与时俱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梁启超完整而清晰的“新妇观”。例如,他强调:“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4]不难看出,粱氏“新妇观”所强调的已非法权上的男女平等,而是“智识能力”和“痛切的自觉”上的“同等地位”,说白了,就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女人要像男子一样,增长顺应时代变化的“智识能力”;同时,还要像男子一样,具有“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自觉意识。这就意味着:只要妇女能够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即或仍是“分利者”的身份,同样也可以阴阳和合地与时俱进。否则,“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把梁启超的这一“新妇观”放到他个人的思想变化历程及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史中去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不仅是梁启超“新民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中国两性文化传统面对异质文化冲击所做出的积极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回应。
首先,从政治层面上看,粱启超的“新妇观”顺应了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大政治需要。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华民族要想不沦为殖民地,只能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奋起抗争。居四百兆中国人之半数的中国妇女,自然不能被排除在“保国保种”的大业之外。这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它不同于近代西方“女权运动”,“女权运动”是在资产阶级人权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向女性群体自然延伸的产物,而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的逼迫下应时而生的。当西方社会发展到“由妇女自觉自发地,去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的“女权运动”之时;中国社会发生的则是“由妇女自觉自发地,去与男子一道争取与世界各国平等的权利”的“妇女运动”,而这一切也都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发展的必然。粱启超的“新妇观”无疑是顺应了中国政治这一需求,它指明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方向——“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居四百兆中国人之半数的中国妇女,不仅要有“强国保种”的“痛切的自觉”,还要自觉地培养自己适应时代需要的“强国保种”的“智识能力”。纵观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尽管不同时期的妇女运动发展理论大都是由“少数男子”提出的,但总体上看,他们大都成为了近代中国妇女的自觉意识和自发行动,也就是说,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进程中,大体上不存在“男子提倡”与“女权运动”之间的对立,这是由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兴起的历史、政治大背景所决定的。
其次,从社会层面上看,粱启超的“新妇观”同样吻合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需求。如果说昔日“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的小农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的话,那么,粱启超“女子须有在智识能力上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的痛切自觉”,则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下近代中国转型社会的产物。它不仅架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相夫教子”与近代西方文化“男女平权”之间的桥梁;而且打通了传统“贤妻良母”与近代“保国保种”之间的隔阂,使妇女的权利与义务从“家内”直接与“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接轨,从而赋予中国妇女以真正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女性人格”与“男女平权”,(注:凡是能够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妇女权利与义务构成的文化内涵的人,便不难理解梁启超这种“新妇观”的文化内涵(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下面对梁启超“新妇观”的文化层面分析)。)这既是近代中国转型社会的要求,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需要。因此,从这一点上看,便是梁启超及维新派提出了“贤妻良母”论,也不是“把解放妇女的目的,划定在‘相夫教子’的狭小圈子里”,而是赋予了传统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以丰富的中国近代文化内涵,也自然融入了西方近代文化“男女平权”的最人本的因素——使妇女在智识能力上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其中不仅根本不存在什么男/女、“男子提倡”/“女权运动”、“义务”“权利”、“贤妻良母”/“独立人格”、“相夫教子”/“男女平权”的分歧与对立,相反,特别强调的恰恰是中国男女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在“强国强种”上的和谐统一与步调一致,这是由近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所决定的——在那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国家危在旦夕、社会动荡不安、全体中国人都必须为基本的生存权利而奋斗的岁月中,既不存在西方式的“争女权”的条件,也不存在所谓“为了女性的权利”而发动的“女权运动”的可能。试想在那个时候把西方的女权运动硬搬到中国来,首先挑起中国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内部性别战争,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堪设想的事。果若是,倒真可能应了张之洞的担忧:“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5](P1)
再次,从文化层面上看,梁启超的“新妇观”继承了中国“阴阳和合”的文化传统,契合了中国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发展规律。西方文明是以个体为本位的、建立在货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商业文明、讲求的是“天人两分”前提下的个体“自由”与个体“联合”;中国文化则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华文明则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血缘群体共有制基础之上的农耕文明,讲求的是“天人合一”原则下的“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这一根本区别,是由于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不同决定了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关于东西方文化特色的分析与总结,请参阅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的相关内容,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就东西方的两性关系而言,西方的两性关系自然也是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在西方的男子靠航海贸易、海上掠夺和海外殖民迅速积累起大量财产和财富、并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城邦国家之时,西方的女子没有也不可能夫唱妇随地直接参与,因此,在由之而形成的个体私有制度中,她们不但不可能或极难成为财产或财富的共有者,而且自身也不得不沦为男子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当男子凭借财权和政权以及相应的话语权,耀武扬威地成为“不在家的男人”时,他们的妻子却成了名副其实的“主要的家庭女仆”,并“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6](P71),从而导致“妇女的家庭世界与男人的公共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隔离”。[5]这种男人=社会,女人=家庭的“男/女对立并行”的两性关系发展到近代,当男人们凭借世界范围的殖民掠夺而使西方社会空前繁荣之时,娜拉们的视野也随之开阔,终于意识到“男人的公共世界”也应该有她们的位置,她们不仅要求进入社会,像男人一样成为社会的一员;同时,也发出“我要用自己的脑子好好想一想,是社会(男人)正确还是我正确”的“颠覆”呼声。起初,为了从“男人的私人附属物”的身份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立于社会的独立女性,女权运动只是在“走出家庭”的旗帜下,追求成为独立的职业女性,并将男女平权当成女权运动的目标。随着西方妇女的逐步职业化,尽管她们实际需要的不过是“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镑”,但职业女性的女权运动却由于她们的视野的扩展与社会活动能力的增长而逐步升级,她们不仅向男人权力宣战,而且还力图掀起一场两性间全方位的战争。由于生存与温饱已然不成问题,西方的女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西方妇女们实现和发展自我的一种安身立命的个人事业,以致与男子争权成了她们唯一的目标或职责,其他的责任与义务似乎都与她们无涉,甚至连婚姻与家庭,她们也都可以弃如敝屣。
中国的两性关系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阴阳和合”基础之上的。(注:关于中国两性关系“阴阳和合”文化特色的论述,请参阅汪兵《阴阳和合——论中国妇女社会性别角色及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6期。)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不仅生发了中国独具特色的血缘群体共有制,而且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家国同构”的拟血缘国家及其拟血缘群体共有观念。(注:关于中国血缘、拟血缘群体共有制以及家族本位、家国同构群体共有观的研究,请参阅汪兵《共——中国人的公私观》,《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汪兵,汪丹:《土地·血缘·共有观》,《历史教学》,2003年第4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男人不仅不是西方式的“不在家的男人”,而且堪称是世界上少有的“为家族生存而奋斗”的男人。对于广大中国妇女而言,男人为家族生存与发展所从事的“主外”事业越大,就越需要“主内”的女人们的配合与合作。从表面上看,中国两性文化固然是“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不仅“治国、平天下”成了男人们的专利,而且“牝鸡司晨,惟家是索”,凡关乎养家糊口、整肃门庭、对外交往、光宗耀祖的“齐家”大事,也难容她们置喙插手,她们似乎完全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但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女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阴阳和合的一个整体,只有女人秉承古训,尽职尽责地主好“内”,男人才能心无旁顾地去修齐治平,所谓家和万事兴。也就是说,中国女子的“主内”,同样是国泰民安的千秋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尤其是传统的大家族,更是矛盾重重,错综复杂,要真正做到“主内”,谈何容易?因此,如何学习和躬行“主内”,便成为中国女人从“弄瓦之喜”就开始了的毕生事业。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并非主张妇女愚钝便是德(例如《红楼梦》中的那位邢夫人,便是才德皆乏的反面人物),而是主张妇女无须具备男子治国平天下之才,却必须具备“主内”之才。而“主内”之才的最高标准就在于德——凝聚家庭或家族之德(《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尽管是巾帼不让须眉,却由于乏德而终于难以肩“主内”之大任)。
而且,中国妇女们的“主中馈”、“相夫教子”绝不等于囿于家务琐事,而是“夫唱妇随”地“水涨船高”——“夫”的事业有多大,她们“相”与“教”的职责范围便有多大。比如皇后,她不仅要承欢君王,教养太子,处理好与三宫六院、宦官婢子及至宫外朝臣的各种关系,还要爱民如子,母仪天下,成为全国母亲们的典范及君王“江山社稷大家业”的“贤内助”。如果皇上先逝,她们还得在三纲五常的框架下,以母后的身份承继帝业,以垂帘听政或母仪天下的方式,相子教孙,承继帝业,只不过照例是在幕后罢了。等而下之的便是《红楼梦》中的老祖宗贾母或平民百姓家中的“婆”。也就是说,她们不仅是社会劳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连她们的道德规范、行为举止,也都成了关乎家国存亡的大事。正所谓“家道正而天下定”,家与国的千秋大业,都只能在男女双方齐心协力下方能实现。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家事、国事之间往往失去了明确的边界,更不可能存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严格界限。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形式下,实际存在着一种中国式的、动态的男女平等,即男女双方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平等。或者说,是一种男女双方皆自觉牺牲“人格独立”,阴阳和合共同维系或兴旺家庭或家族的平等。这是中国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始终在生存和温饱线上挣扎,而极少有发展空间的家庭或家族来说,唯其如此,才可能维持生存,争取温饱。即或是在改革开放了的今天,真正富起来的毕竟还是“少数人”,其他尚处在温饱线上或线下挣扎的“多数人”,大抵还是不得不实行这种中国式的平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正是靠了这种中国式的男女平等,使中国的文化与历史独一无二地一以贯之传承了数千年之久。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当近代中国转型社会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的知识分子都那么重视妇女的作用;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新文化运动,从没有把妇女排斥在外。明乎此,也就更加理解,为什么“少数男子提倡”的“妇女运动”居然会得到广大中国妇女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响应,她们不仅没有计较近代以来的一次又一次“妇女运动”是由男人还是女人来提倡的——在她们看来,只要为了家国的兴盛,谁来提倡都是一个样。即或是由妇女提倡,也绝不意味着会与男人作对,向男人要求妇女自身的权力(除非这种权力是和当时的社会、时代主题相一致的);相反,在“男主女从”两性文化传统的作用下,中国妇女更加适应这种“由少数男子提倡”的“妇女运动”——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阴的随动”,(注:钱穆先生在《阴与阳》一文中,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和合”关系,指出:“《易经》以乾坤两卦代表阴阳。乾德为健,坤德为顺,健是动,顺也不就是静,其实顺还是动,只是健属主动,顺属随动。何以不说被动而云随动,因被动是甲物被乙物推动,随动是甲物随顺乙物而自动。主动和随动一样是自动,只是一先一后之间有分别。至于被动则并非自动,只是他动而已。”参见《湖上闲思录》,第16~1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它不是“被动”而是“自动”的,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她们为家国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也就自然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关于这一点,从中国传统社会中“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婆权”获得上,反映得最明显。(注:俗话说“多年媳妇熬成婆”,代表古代中国妇女最高权力层次的“婆权”不是靠与男人的对立与抗争,更不是靠挑战、颠覆男权而获得的,而是靠“熬”——像煲老汤一样煲得的。一个“熬”字,代表着传统两性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久见人心,百忍见功力,以柔克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赋权”之路,在这条路上,权力与义务从来都是“拎不清”、“道不明”的。相关研究请参阅汪兵,林杰《中国古代的婆权》,《山西师大学报》,2003第1期。)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粱启超所提倡的“新妇观”,为什么不仅与其“新民观”浑然一体,是其“新民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更代表着中国两性文化传统面对异质文化冲击所做出的积极的回应——当中国“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观念被打破,中国男女不得不面对工业与商业文明所带来的必然的城市化、社会化转型局面时,以“天下兴亡,匹夫(妇)有责”的文化自觉意识来整合男女权力的分化;以“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来提升妇女在社会上与男子并肩奋斗的信心与实力,以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实现新的两性关系再谐调,而不是使两性关系走向对立与分化,竞争与内乱,这不仅仅是一时的政治救亡的需要,更是中国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中国两性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综上所述,粱启超的“新妇观”,无论从当时的政治救亡意义、社会转型意义,还是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看,都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为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而提出的。它所谓的“新妇”绝不是以“西妇”为标准,而是代表着中国“阴阳和合”两性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发展方向。
三、关于“新妇观”的现代反思
粱启超及维新派的“新妇观”也确实有其时代或历史的局限性,它主要表现在没有对东西方妇女“主体权利”的不同文化内涵作深入的辨析,实际上是借西方的“个体权利意识”来强化中国男女个体“天下兴亡,匹夫(妇)有责”的责任心,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群体生存权”而奋斗,自然也就淡化甚至忽视了对西方个体本位的“主体权利”的深入研究与定位。如果说这在当年全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与自主而奋斗的年代是“势在必行”的话,那么,当中国人民已经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走上自强自主之路,而中国妇女也取得了妇女半边天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之后,这样的“新妇观”理所当然地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但它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怎样地“俱进”也绝不能“进”成“西妇观”。
“西妇观”当然也有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例如强调对于“个体权利”及“性别差异”的尊重,开展对于女性生理——心理经验,包括性行为、妊娠与成为母亲及女人一生周期性的研究,重视妇女特殊需求的制度性建设等等。毋庸讳言,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确不如西方社会,要想补上这一课,我们也确实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仅仅是“借鉴”或“补课”,而不是伐毛洗髓、脱胎换骨。正如我们吃鸡是为了果腹和营养,而绝非“连毛带骨一起吃,然后自己变成鸡”。而现代“西妇观”所走过的“理性探索”之路,却总给人一种必欲“变成鸡”的感觉。例如,它往往将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史”看成是一片空白,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们统统视为被父权制“压迫”、“奴役”的“文明的残片”、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交战中的败北者”,以及生活在“历史地平线之下”、“黑暗、隐秘、喑哑的世界”、“古代历史的盲点”之中的“无形象”、“无意识”的群体。(注:参见前引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绪论”及“结语”部分。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引自该书。)好像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都由父权制的父家长们一手遮天、全包全揽下了,中国妇女除了充当生育和维护男权统治的牺牲品外,不知有“自己”的存在;同样,当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终于有了“少数男性”提出“男女平权”问题,而且从戊戌维新到新中国建立,经过中国男女半个多世纪的并肩奋斗,中国妇女终于取得了包括“同工同酬”在内的“男女平等”社会地位之后,如此巨大的变化,只因为其间忽视了对于女性个体权利及性别意识的研究与尊重,便被一笔勾销,中国妇女再度落入“男女平等(实际上还是现代男权意识)神话陷阱”,再度沦为“在一个解放、翻身的神话中,既完全丧失了自己,又完全丧失了寻找自己的理由和权力”的“无形象”、“无意识”的一群。好可怜的中国妇女,只要她一天不确立所谓的“主体意识”、“性别自觉”,无论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她都是一个“空洞能指”。这不是伐毛洗髓、脱胎换骨还是什么?
现代“西妇观”既不是今天才形成的,也不是中国妇女的“自觉自发”意识。它同“新妇观”一样是东西方文化撞击的产物,但却从属于近代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
钱穆先生有一个观点:中国人“开始觉悟到要从头调整他的全部文化机构,来应付这一个几千年历史上从未遇到的大变局,那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自西元一八四二鸦片战争,直到现在一百年内,中国人便在此情况下挣扎奋斗。我们若看清这三百年来(注:“三百年来”钱穆先生解释为:“嘉庆、道光以下,正当西方十九世纪开始时期……那时的中国人,内部尚未能摆脱满清部族政权之羁勒,外面又要招架西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压迫与侵略。”)中国人之处境,与其内心情绪之激扰与不安定,则在此时期内,中国人之不能好好接纳西方文化而加以消化,是不足深怪的。”[8](P209)更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多民族融合的大国而言,古老厚重的、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本来就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在广袤的中华大地,经历几千年兼并与融合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近代以降,面对前所未有的异质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会形成怎样的新的文化传统,谁说了也不算,仍然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排异与吸收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一切有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讨论,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即便是背离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思潮,也本不算什么“文化的歧路”,是“不足深怪”的。
但是,钱穆先生当年为我们敲响的警钟,也许对于今天包括“西妇观”在内的一切“西化思想”都有警示作用。他说:“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所谓民族争存,度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9](P168)换言之,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若全盘西化,则中华民族也就不复存在。“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在,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些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9](P144)
那么,中国妇女运动的主旨,就不再是“解放”,而是“改进”。而“改进”的方向则应该是:
实事求是地借鉴“西妇观”,
与时俱进地发展“新妇观”。
收稿日期:2003-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