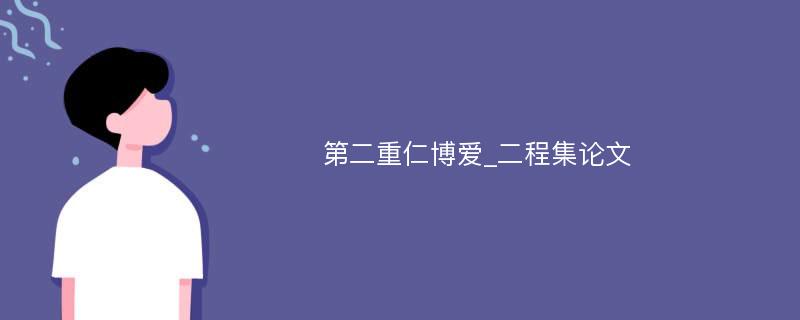
二程论仁与博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爱论文,二程论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15)02-0073-07 在理学史上,大致与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同时,关联仁与博爱的另一知名命题,是程颢所说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①。如果说,从张载“民胞物与”走出来的是“大家”说,程颢仁学开出的则是“大我”说,即与张载“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的“小我”不同。但是,“大我”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接着“大家”往下讲的,所以程颢极为称赞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②所谓“意极完备”,是说从天地浑然之气到人物共循之性,整体都贯穿着仁爱的情感和与此相呼应的道德生命,是即所谓仁之体也。 一、“一体”之仁与仁、爱之间 仁之体是与仁之方相对而言的,二者共同支撑着仁的一体论说,“大我”观也正是由此而建立起来。程颢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③ 医书上说手足痿痹为不仁,程颢以为这最恰当地揭示了仁的相状。《黄帝内经》专有《痿论》、《痹论》篇,其中便多言及“不仁”,意谓荣卫之气不通,肌肤肢体麻木的状态④。所以手足不仁,便是气不相贯而人对其肢体无知觉,好像已不属于我所有。可以说,从曾子启手足以来,儒家认为人应当爱其肢体以全孝道,孟子亦有“兼所爱”之说。但由于手足痿痹,人不能知觉其身体,生命有机体在事实上招致破坏,爱意也就无从畅达。由此,仁在程颢之生发,首先便是基于身体发肤完备基础上的生命的自觉。有此自觉,即“有诸己”和“与己相干”,才可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在这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是总体,但只讲到“一体”、“总体”显然不够,因为它离不开言说此总体的主体,即“己”或“我”。己者,我也,所以《粹言》的相关表述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尽!不能有诸己,则其与天地万物,岂特相去千万而已哉?”⑤从“认得为己”到“知其皆我”,越发具有更强的孟子之“万物皆备于我”的色彩,因为只有在确立“我”之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天地万物的“一体”才是可能的。 就是说,“一体”或总体作为观念性的实在,是需要人——这里是“我”去体贴出来的。所谓体贴,不是逻辑的推演,而是直接的感悟。自先秦以来,已经具有“心之所同然”意义的“通天下一气”,已经预设了物我同一的存在论的基石,“仁”也就可以通过“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呈现自己的总体样态。在此样态中,不只是“我”,任一个体都具有说“莫非己也”的品格和资质。有此本体论的基础,仁民爱物也就不必都由亲亲来推出,反而是无物不是亲亲,无人不在爱物。因为天地万物“莫非己也”,已成为“我”自身的构成部分。 如此“大我”的形成,依赖的固然是生命各部分之间的血脉、气息或生气的流通——如同《内经》中已表述的那样,但又不限于我之气血自身的流通,而是我与气化生成的不同人物相互感通。如此的生气感通,体现为“我”对天地万物的关爱。我关爱天地万物,实乃对自身的关爱,故没有不能达到的。发于我身的博爱情感,也就具有主客、内外交相合的意义。贯穿其中的基本点,就是“身”的概念。“全身”不只是四肢百体,而且是身心如一。程颢说: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以为仁之方也。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⑥ “至仁”是仁的最高境界,但这最高境界不过是对“天地为一身”之“大我”存在状态的心理体验。在此一体验中,“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呈现的是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在而不可分离的蕴含。天地万形的“一体”落实为四肢百体的“一身”,并在“属己”或“在我”的前提下得以成立。所以程颢总是要以“己”或“一身”来论仁,因为从“属己”、“在我”来论仁,可以凭借气血流通而生意畅达的物质手段。如果手足麻痹,四肢百体不能“属己”,不能“在我”,即在“我”的观念中它们已不在场,不参与人的知觉活动,生意无法遂适,仁的“一体”性也就从根本上被破坏。 至于孔子示子贡以为仁之方的“能近取譬”,《论语》是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去讲的,以使人能够切近体验和亲身实践,不致因为“博施济众”的宏愿无法实现而使仁流于空谈。不过,程颢此处论仁,与孔门师徒已有所不同:“能近取譬”重在切近实践,手足之爱则重在自身体感;但二者也相关,因手足疾痛之体感就发生于人自身,是最近的取譬。若残缺了对一肢一体的关爱,生命不再是一个整体,自然就不能叫仁了。而“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则又进了一步,说明即便在疾痛与知、一气贯通的情景下,人仍然有不仁者,这里可以联想到宰予当年不知感恩,不愿为逝去的父母服丧三年作为回报,故被孔子斥之为“不仁”的事例。 可以说,手足风顽是客观病痛导致的气血中断而不仁,忍心无恩则是行为主体有意阻断气息流贯导致的不仁,前者只发生于“一身”之内,后者则存在于天地万形之间。“一身”是四肢百体的整体,“一体”则是天地万形的整体,由此来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心就不再是“欲立”、“欲达”的个体主观设想,而是一般性的“立人”、“达人”的现实结果。而所以能从“己”欲立一方的条件推出立“人”一方的结果,正在于一体之仁本来是由己及人流淌开去的。这或许也有助于说明,虽然站在存在的角度或人己同气的立场,仁爱不必再是亲亲、仁民、爱物的逐步推广,但从方便或效用的角度看,爱亲敬长模式作为“能近取譬”的现实,更容易让人理解随我心之仁意流淌而体验到天地人物一体的博爱情感的真切。 博爱作为真实的情感流露和仁德播撒的过程,突出的是实爱而非虚情,孕育和培养的是人真实的品性。在父子、兄弟、民物间的亲疏不等和普遍之爱之间,值得关注的不是差等与无差等的矛盾,而是一体之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如何与环境相适应而恰当表现。那么,博爱心理的生成和付诸实践,就成为一定环境条件下确定生起的结果,也具有必然的性质。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⑦,个别就是一般。但从另一面看,仁或博爱既然取决于气血流通或恻隐之心的生发扩充,如果因意识的缘故阻断了这一过程,那“一体”也就随之断裂,博爱也就不可能了。对此,张载称之为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程颢则叫做忍心无恩之自弃。这说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作为整体的仁体,又是在其实施或作用之中才能生存的。虽说有体才有用,但用在最终的意义上决定着体的实现和完成。 可以说,程颢虽然刻意拈出了“仁之体”的概念,但这仁体不论作为实体还是境界,均需要落实到日用常行之中。就作用一方看,可以孔门师徒的“泛爱众”、“博施济众”和孟子的“仁民爱物”等为代表。由此来看“博施济众”之爱,一方面是崇高的境界,另一方面则是“圣”之概念所必然蕴含的功用的要求。所谓“‘博施济众’,云‘必也圣乎’者,非谓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济众’者乃功用也”⑧。仁与“博施济众”都是指爱的普施,都彰显了万物一体的境界,这是同一的层面;但区别在观仁在得其体——仁爱的本心,观“博施济众”则在其功用,即爱人在物质层面的落实。二者之间,“博施济众亦仁也,爱人亦仁也。‘尧舜其犹病诸’者,犹难之也。博则广而无极,众则多而无穷,圣人必欲使天下无一人之恶,无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诸’。‘修己以安百姓’,亦犹是也”⑨。仁是一般的范畴,“兼上下大小而言之”⑩,所以爱人是仁。若能落实到天下无一人一物不被其爱、不得其所,便是博施济众,但这在物质财富匮乏的古代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无极”、“无穷”本来就不具有现实的意义。“修己”可以使德性纯熟、境界高尚,但却不能转化出现实的物质财富,所以“病诸”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当年韩愈阐扬的“博爱之谓仁”的命题及其所涉及的爱与仁的关系: 问仁。曰:“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11) 圣人言仁处不少,以“恻隐”言仁便是其一。恻隐之心的发动,依据孟子性善的机制,有普遍而不可阻遏的必然之势,而仁性便是此必然之势能够发生的根源。由此来区分性情和分别仁爱,恻隐固为爱,但却属情,乃仁性之发端,故不能径以爱为仁。在圣贤诸多的“言仁”话语中,韩愈“博爱之谓仁”的命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韩愈之时,以博爱释仁反映了儒家向佛老的慈悲怜悯争地盘的目的,其作用应当充分估计。程颐这里以为不妥,就在仁和爱的关系是本性与其情感表现的关系,故通称的“仁爱”实乃从统一面说性情,或曰性生情也。由于性体必然生发为情用,即仁者固博爱,但博爱作为已发,作为情用一方,本不能等同未发的本性或仁体,所以博爱又不能尽仁。 但是,仁毕竟主要是通过爱来表现的。孔门弟子有子说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程颐解作孝悌是仁之一事,为践行仁德所必需。然孝悌本身不仅是德行,更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所谓“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2)仁不等于爱,但又主于爱,孝悌之爱父兄,恻隐之爱他人,作为仁之发用又真实地展现着仁体。同理,“博爱之谓仁”的命题以情感发用去揭示仁德,程颐对此也是给予肯定的。其称韩愈“博爱之谓仁”一段“此言却好”,以为“只如《原道》一篇极好。退之每有一两处,直是搏(博)得亲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博也”(13)。那么,肯定韩愈此语好,是从“博”的角度而言,点明了仁所具备也本来表现为博爱的情感,固自是亲切。但韩愈博却不精,不知道情爱与本性的差别,所以又受到了二程的批评。 就此而言,仁主于爱又不能径以博爱为仁,关键就在如何恰当看待这种相依又不等同的关系。例如在张栻编次的《粹言》中,有学生问:“爱何以非仁?”其师的回答是:“爱出于情,仁则性也。仁者无偏照,是必爱之。”(14)性情之分是二程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点,仁性作为本体,是不应该与发用的情感混为一谈的。但在同时,仁本身体现为爱意的生发,突出的是普遍之爱的规定,德性是嵌入在其中的。二程要对仁与爱作出区分,在于意识到传统博爱观仅以情感说仁爱的不足。仁既是情感也是德性。因为情感的生发,一是基于自然亲情的推延,亲疏厚薄不能避免;二是与个体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状态相关,爱的发现不能持守中道,或过或不及,譬如父母对子女的溺爱或偏爱就是如此。换句话说,爱可以出于私情,但仁却必须是大公,爱与仁也就不能等同。仁性爱情的构架,实际也是从公私的层面对仁与爱再作区分,故强调的是仁者无偏照。如若不然,人有私意干扰,爱心的抒发便不能顺畅,所以情感又需要德性的方向调节。 二、仁者廓然大公 德性的意义,在以仁性之公道的价值调节情感,使爱能出于公心。就是说,私意与仁是不相应的。比方:“‘回也三月不违仁’,如何?曰:‘不违处,只是无纤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15)在程颐,孔子对颜回德行修养的称赞,已经被引入到公私问题上来考量。颜子之心能谐和于仁,根本点即在大公无私。由此来看“如何是仁”,程颐的回答便是:“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16)回答很简洁,但问题并未解决,关键在“思量”得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由于公与博爱在定义域上相通,突出的都是普遍而无差别的方面,而仁显然还有差别的蕴含,所以简单地以公解仁,并不能得到二程的认可。参看《外书》的记述: 谢收问学于伊川,答曰:“学之大无如仁。汝谓仁是如何?”谢久之无入处,一日再问曰:“爱人是仁否?”伊川曰:“爱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谢收去,先生(尹焞)曰:“某谓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谓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恶人。”伊川曰:“善涵养。”(17) 谢收与尹焞实际上同在思考“仁是如何”的问题。从程颐的回答和引发看,仁是顶层的概念和最高的境界,爱人无疑是其内涵,但爱人又只是仁的发端,不等于仁的全部。发端者,即凡爱人便进入到仁,但此爱若能普遍播撒而又公正无私时,应当便是仁意的完全展现,可能尹焞也因此而感悟出“公”之一言。但程颐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因“公”字本身存在再解释的问题,尹焞思虑“公”的结果是“能好人,能恶人”,意味能以同一的道德尺度公平地对待他人。可是,程颐给出的“善涵养”的评价却颇模糊,不知其对事还是对人。对事,则“能好人,能恶人”的境界需要善涵养才能达到;对人,则是认可尹焞之“公”意,而称赞其善涵养。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能出以公心好人恶人应当是公的内涵,善的价值尺度实际已镶嵌于其中。从善的尺度和人与人之间相亲爱的仁的基本蕴含出发,能好人恶人也就是当爱就爱,当不爱就不爱,公平地对人和对己。如果联系到就近取譬的立人达人模式,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恶而恶人。用二程自己的话:“尝谓孔子之语仁以教人者,唯此为尽,要之不出于公也。”(18)孔子的立人达人之教法最为完备,“公”在这里体现的是公平之爱,故己立则立人,己达则达人,作为恕道,也就是所谓黄金法则。 但恕道体现公平之爱,只是引入或落实仁的方式,不直接是仁本身。所谓“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因其恻隐之心,知其有仁”(19)。恕道的发动,建立在恻隐之心的基础之上,恻隐的普遍必然之爱在推己及人的实践中得到落实,仁性也从而得以体验。所以又要注意这些关联范畴之间的差别。程颐故称: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20) 这一段话,涉及仁、公、恕、爱等多方面的关系,体用的架构实际上存在于其中。笼统说,仁无偏照,公、恕、爱都是仁;但细分之,“公”所体现的,是爱的公平和普遍性质,是仁之体即性理的一方。公之性理在推己及人的实践中展现出来而人又能真正体验,这便是体用合一之仁。换句话说,仁就是凡事出以公平之心,物我兼照而无私爱偏重。在此前提下,推己及人或恕道就是仁之理的实施方式,博爱则是仁体流行的实际效用。由于在实践中,体用各方实际上都贯穿着公的精神,所以要认识仁道,关键就看如何理会这一“公”字。 可以说,“仁者公也”(21)是二程的一般主张。此“仁者”就名言说,可以有二义:一是指实体,即作为仁之体或仁之道的性理;二是指仁人——尽仁之人,仁人要秉持的,是无偏照的关爱情怀。“仁者”二义在圣人情怀、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意义上又是一个整体。但就“学者”而言,情况却有所差别,因后者存在着主客关系问题。仁体作为对象和实体,是与“学者”这一主体相呼应的。“学者”需要识仁,“认得(仁)为己”需要以学者的境界和涵养为前提。站在学者的立场,“人”与“仁”的主客之间,“人”需要识仁、识理的“穷索”才可能以己合彼,由有对进达无对,由具体作用进达公天下之理。程颢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22) 程颢强调识仁,可以从多方面的意义去阐释,就性理一方说,重在提供公天下的普遍之爱所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即如果体验到仁体的存在本身是一个浑然总成,是融摄仁义礼智信的全体,是基于道德内涵完满无缺基础上的人物一体,爱的普遍实施就有必然的意义。在此意义上,首先要知道仁是超越了人己、人物隔阂的包容性的普遍必然存在,识仁的实质就是识其“同体”,其工夫表现为先识后存。此理此道的存在既以“无对”为表征,“大”(天)也就不足以名之。 同时,既然在存在的意义上我(仁者)与天地同体,天地之用自然就是我之用——同用。孟子当年的“万物皆备于我”是基于性天一致的前提,毋庸说也是一种同体说——天人同一本体,“反身而诚”即是体验到这一本体,也即程颢论证仁的本体性存在的现身说法。可以说,“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是从作用层面来证实和体现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体同贯而不是二物有对,于我是最大的快乐,于物则是爱的普施,公天下的理念在哲学上得到了论证。其具体的表现,便是“备言此(仁)体”的张载的《订顽》(《西铭》)。 即在程颢,张载同性同气的“民胞物与”之爱也是一种“(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说。因为它以爱意消解了现实中严峻的上下等级关系,父子君臣的樊篱被一体相连的气性所取代。同气同性而有“同体”,造就的正是彼与己的和合为一,人之爱物成为发自本心的意愿。存此“同体”之意,必然生发的是以诚敬之心爱人,仁是在其流淌即爱的普施之中实现“同体”的。相应地,既然谓之“同体”,则你我公私之隔阂自消,“大我”实质上便转义为无我。程颢在给张载的信中说: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23) 在这里,无我或者无心,贯穿的是一种以天地万物本来的存在为归依的深度和合感,兼有本体与境界的双重蕴涵。所谓无心、无情,并非是说主体没有任何的心思和情感,而是突出了心普万物、情顺万物所彰显的无私或无我的境界。这是天地、圣人的常态,也是君子之学的目的。包括等级尊卑在内的窒碍已不见踪影,我心廓然坦荡地关切众生,因而也就能与任何外物融洽地交流,和谐共生。 程颢此答书在历史上以《定性书》闻名,其基本点在强调性无内外,故他“同体”说的本体论依据实际在其“同性”说。“性无内外”也就是通天下一性,与张载的“性者万物之一源”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程颢认为张载的“定性”说有性物二分之嫌,张载的确也有要求去气之蔽塞的问题。但如果从存在而不是修养来看,张载本来也是主张性气(物)一体的,从而才能尽道尽性而博爱天下。 依据其性无内外的性物一体观,必然导出的就是心不应分彼此,万物应得到同样的关爱。不过,从方向上说,廓然而大公是心向外扩,物来而顺应是心向内收,外扩是爱他人,内收则被人爱。仍用程氏之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24)最普通的士人,如果心中充满的是爱物的情怀,对他人必定能有所救助。爱物和济人本来都是博爱的具体表现,但这里以假言判断的形式出现,说明程颢是将对于人物的物质救济建立在“存心”关爱的心理基础之上的。结合到“无心”、“无情”之说,就不是真的无心、无情,而是以关爱万物之心为心而没有自己的私心,即具备廓然而大公的心理素养。相应地,物来而顺应,也就可以理解为因我爱人而引致出的人我相爱的博爱氛围。 的确,以存心爱物来彰显的程颢的博爱,并不只停留于理论的呼唤,而是已施诸于亲身的实践,博爱体现为基层官府的施政行为和责任意识。《宋史》记载说,程颢任晋城县令,“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25) 如果说,在《礼记·礼运》景仰“大同”和张载发“民胞物与”宏愿时,博爱或许还只是心灵的期许,但这在程颢治下的晋城,一定程度上已是可以感知的现实。程颢本传,《宋史》载之于《道学传》,而按编撰者的意图,《道学传》是为推崇道学而“示隆”,故一县之治能如此完美,博爱实践能如此不留遗憾,可能其中有溢美的成分,但从中大致还是能感受到在北宋中期,包括二程、张载等一大批思想家在内,对博爱情怀的普遍呼吁、认同和实践。故《宋史》本传称程颢“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弟子吕大临在程颢去世后撰写的《哀词》中亦称赞其师是“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26),真切地展示了程颢存心于爱物的廓然大公的胸怀和严于律己的责任,也可以说是“大我”观在施政方面的具体体现。而所谓“力役相助,患难相恤”等等,则充分展示了博爱的互惠性质。当爱人者又被人爱时,他会产生发于心理满足基础上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博爱的实施。 ①②③程颢:《遗书》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④《黄帝内经·素问·痹论》:“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王冰注:“不仁者,皮顽不知有无也。” ⑤二程:《粹言》卷一《论道篇》,《二程集》,第1179页。 ⑥二程:《遗书》卷四,《二程集》,第74页。《宋元学案·明道学案》认为是程颢语。 ⑦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页。 ⑧程颢:《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5页。 ⑨⑩程颐:《外书》卷六,《二程集》,第382—383,382页。 (11)(12)程颐:《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2,183页。 (13)程颐:《遗书》卷十九,《二程集》,第262页。 (14)二程:《粹言》卷一《论道篇》,《二程集》,第1180页。 (15)(16)程颐:《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284,285页。 (17)祁宽:《尹和靖语》,《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33页。 (18)二程:《遗书》卷九,《二程集》,第105页。 (19)(20)程颐:《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68,153页。 (21)二程:《遗书》卷九,《二程集》,第105页。 (22)程颢:《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6—17页。 (23)程颢:《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二程集》,第460页。 (24)程颢:《近思录》卷十,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另:二程《粹言》卷二记载本条为:“一介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亦必有所济。”见《二程集》,第1266页。 (25)《宋史·道学一·程颢传》。 (26)吕大临:《哀词》,《遗书》附录,《二程集》,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