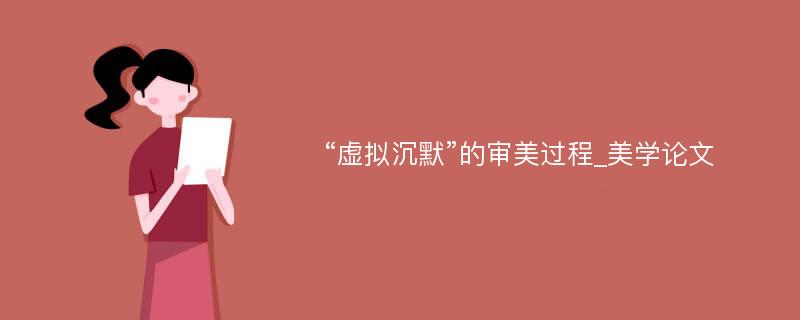
“虚静”的美学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历程论文,虚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虚静”一语,最初见于周厉王时代的《大克鼎》铭文:“冲上厥心,虚静于猷”,指的是宗教仪式中一种用以摆脱现实欲念,便于敬天崇祖的谦冲、和穆、虔敬、静寂的心态。先秦哲学领域里的虚静则更超越于宗教心境之上,具有新的理论内涵。在先秦哲学领域,对“虚静”论述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老庄。老庄哲学以“道”为基本概念,在他们看来,“道”是自在自为、先天地而存在的宇宙本体,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质,具有时空上的广延性和无限性,概念上的抽象性和多义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形无影,难以定义。而“虚静”则是“道”的本体存在的一种形态,即“道冲”(冲即虚空)。“道”的这种特性决定它不可能被致道之人以普通的感知方式所认知,所以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老子·十六章》)王弼注云:“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非动作,卒复归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道德经注》)即是说,道的本体特征是静,动仅是外在表现,因此致道之人只有虚静其心,个体汇入大化之中,犹如百川入海一般,才能与“道”周始,得到“至美至乐”的享受。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把“虚”、“静”合为一词,《庄子·天道》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并提出“心斋”、“坐忘”。《庄子·大宗师》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心斋”和“坐忘”,是庄子关于“虚静”的核心观点,前者侧重于去知,排除感官与外物的接触和感知,否定“心”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思维;后者侧重于离形,不仅否定人的认识活动,还排除人的生理欲望,这样去知、离形就能达到与天道一样的虚和静。另外,庄子还有一些有关技艺神化的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佝偻承蜩”,反映了同源同感、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过,在以人心之虚静体悟天道之虚静的过程中,老庄否定了具体的“视听”作用,认为人只有抛弃了一切具体的、局部的、主观的“所见”、“所闻”、“所知”,才能获得对事物全面的、真正客观的认识。
在先秦哲学领域,除老庄外,宋尹、荀韩也讲求虚静。宋妍、尹文认为,“天之道虚,地之道静”(《庄子》),为了认识天地之道,心灵就必须“虚一而静”。关于“虚”,他们说:“夫心有敬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庄子》);关于“一”,他们说:“专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若近”(《庄子》);关于“静”,他们说:“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庄子》)。荀子杂合老庄及宋尹的思想,进一步重申“虚壹而静”,并对“虚”、“壹”、“静”作了详细而具体的阐释,《荀子·解蔽》云:“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但他又认为“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谓受令”(《荀子·解蔽》),这就容易把心的活动说成不受物质条件、客观环境的制约,将人的认识引向偏重于追求心的“大清明”,有浓厚的唯理论色彩。韩非则走得更远,“思虑静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韩非子》),主张把以静制动的辩证法用入实际人生,理性色彩显得更为浓厚。
不难看出,宋尹、荀韩的“虚静”思想,在承认人的认识活动必须以人心之虚静为前提的基础上,突出了理性和思维的作用,突出了认识的全面性和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但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宋尹、荀韩的虚静说由于过分的理性化反而不如老庄的虚静说更能适合于审美和艺术。诚如上文所述,老庄以人心之虚静体悟天道之虚静的认识论有神秘直观的性质,但是,对审美和艺术来说,则又明显蕴含着极有价值的思想。从美学的角度看,老庄认为对“道”的认识必须排除一切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这一点完全符合审美的特征,因为人类的审美活动的确具有超功利的一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老庄特别是庄子提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应该凝神专注于特定认识对象,从而达到对“道”的深观远照。因此,后世艺术和美学中的虚静说便更多地受老庄而不是宋尹、荀韩的影响,而老庄的虚静论也从美学、文艺心理学方面给后世的文艺家和美学家以极大的启示。
2.魏晋六朝时,世态动荡纷乱,风习险恶污浊。王弼、何晏等正始名士伏膺老庄,希冀在政治角逐中以静制动,保身避祸。嵇康放浪山水,陶渊明归稳田园,以素朴虚静之心追求精神快乐和人格解放。士族名流广占田园林蔽,湖泊水泽,在他们眼里,这些自然物既是生活资料,又构成审美对象。正缘于此,老庄和佛学才蔚为兴盛,成为时人信奉的生活哲学,虚静说也滋蔓开来,逐渐进入了审美领域。
最早将“虚静”自觉地运用于文学创作研究的是陆机。陆机身处魏晋易代之际,目睹各种动乱变迁,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道家深观物化、玄览静怀的思想,使他对人世和自然持虚静超然的态度,这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和实践。《文赋》云:“伫中区以玄览”、“馨澄思以凝虚”等就是强调作家在艺术构思过程中必须保持一种虚静凝神的心理状态,其《辩亡论》、《演连珠》、《叹逝赋》等作品就是这种虚静审美心态的产物。在他看来,虚静是深观物化、与道周始的心灵的距离化,是从事审美创作的主体框架。
陆机的这种思想在南朝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南朝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应物,澄怀味象。”“澄怀”即虚静其怀,就是使情怀高洁,不为物欲所累;“味象”即品嚼、把玩、体会宇宙万物的形象之美。以“味”作为一种美感体验而运用于文艺在晋宋齐梁较为普遍,但在画论上则肇始于宗炳。宗炳把视觉味觉化,强调了绘画艺术在美感心理体验上的持久性。在宗炳的时代,其一,尚未完全摆脱魏晋玄学中“言、象、意”的认知模式;其二,以自然山水为对象的审美观照极为重视外在形象,追求“形似”之风颇炽。但在宗炳眼里,“象”已不是现实的自然山水的外在形象,而是艺术家处于虚静状态中进行审美观照时所显现于目前或脑海中的审美意象。因此,“澄怀味象”实质上是指艺术欣赏时应当具备的一种审美心胸与精神状态。诚然,宗炳的“澄怀味象”仅局限于自然山水,但它强调“味象”,即审美观照中的美感体验,触及了审美心理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具有一定的美学理论价值。刘勰的《文心雕龙》,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陆机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不仅指出审美主体内心的虚寂澄明是艺术构思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文心雕龙》),而且详尽论述了“虚静”与创作情感、创作想象的关系。在刘勰看来,“虚静”就不是艺术创作前“唤起想象的事前准备,作为一个起点”(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而是伴随创作情感、创作想象贯穿于艺术创作始终。刘勰的上述思想,和先秦哲学领域特别是老庄的“虚静”说一脉相承,并深受当时玄学、佛学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新领域的理论,这些思想特别是陆机、刘勰的文学创作虚静论,既不是对前人学说的简单因袭,也不是对时人理论的复制移用,而是极富开创性。具体表现有二:
其一,陆机、刘勰的“虚静”说注重知识才学。陆机提出创作前要“颐情志于典坟”(《文赋》),创作中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文赋》)刘勰强调创作构思有待于“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文赋》),在“神思”过程中,是“志气统其关键”,“辞令管其枢机”(《文赋》)。由此可见,知识才学是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不过,这些知识才学必须沉淀到“虚静”的审美心态之中,通过“虚静”这个中介而发挥出来,使知识才华融化在想象与情感的和谐运动之中。
其二,陆机、刘勰的“虚静”说暗含科学道理。一般来说,动而趋静,静而趋动,一静一动,自我调节,维护大脑的健康运转。作家创作时摈除纷乱,澄观一心,而后才能腾踔万象,情致渐进,意象天成。这是一个由静入动的过程。由此可见,陆机、刘勰的“虚静”说实质上就是一种由静入动、以虚生实的创作论,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艺术辩证法。
魏晋六朝的“虚静”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是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的。它把先秦时尚处于哲学领域的“虚静”说与审美和艺术理论融为一体,创建了精深严密的理论体系。自此开始,“虚静”作为创作者和欣赏者在审美活动中应该具有的一种虚空澄明的审美心态,便几成共识。六朝之后,虽然不少文艺家、美学家在论述构思或文艺欣赏活动时,都对“虚静”说作了补充和发挥,但大多数都是沿承陆机、宗炳、刘勰“虚空澄明”的审美心态理论。直到王国维集意境理论之大成,提出“境界”说,才始有突破。
3.王国维认为:“词的境界最高。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把它分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两类。“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由于动之静时得之。”首次将虚静与境界同时并提,拓宽了中国古代美学中“虚静”的理论视野,使“虚静”发展成为一种“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
“以我观物”的“我”指审美主体,“物”指审美客体。当主体进入审美活动时,其内心实际上已经分化为两个“我”,一个是充满激情、欲望的现实的“我”,王国维称之为“欲之我”。这个“我”不是审美观照者,这不是把客体视为审美的观照物,而是把客体当作情感宣泄和移易的对象。另一个是超功利的“虚静”的“我”,王国维称之为“知之我”。这个“我”才是审美观照者,只有它才把客体当作审美观照物。在这种情况下,因两个“我”同时并存,主体观照客体,便带有自己强烈的感情、意志,从而使客体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失去了其自在自为的本色,而染上了“我”的色彩。“有我之境,由于动之静时得之。”这外“动”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斗争,而是主体自身“欲之我”与“知之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运动的结果,则是渐趋于静:“欲之我”在审美对象的吸引下,逐步向“知之我”转化,将激情转移、发散掉,获得精神解脱,从而消除两个“我”之间的矛盾,使审美主体的整个心灵暂时达到舒适平静。与此同时,“知之我”则把沉浸在激情、欲望之中的“欲之我”与客观外物一起作为审美对象,并在两者的相互制约中凝聚成既矛盾又统一的境界——既要“观物”,又要“观我”。因此,“有我之境”实质上就是一个由“欲之我”向“知之我”,由非虚静向虚静逐渐转化的艺术境界。
“以物观物”的前一个“物”指审美主体,后一个“物”指审美客体。当主体内心摒弃“欲之我”,唯有“知之我”,完全处于忘怀一切的虚静状态时,在审美观照中观照者与观照物已失去界限,因而也就“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了。“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这个“静”,诚如宗白华所说:“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时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物,万物如在镜中,光照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的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所得。”由于“心无挂碍”、“一点觉心”,所以心与物之间毫无矛盾,它们的契合也就成了自然天成。主体的内心本来就是虚静的,审美观照则是在无矛盾的状态中不知不觉进行的,交融的结果又是物我完全契合的静态平衡。所以王国维所言“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决非真是以“物”去观,而是“艺术心灵宇宙意象‘两境相入’互摄互映”,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
总之,王国维的境界理论以虚静为主要特征,“有我之境”由非虚静向虚静转化,“无我之境”静始静终,物我两忘。既丰富了境界的美学内涵,又开拓了虚静的理论视野,两者相融相汇,使“物我两忘”成为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倍加推崇的艺术至境。
先秦以降,“虚静”在哲学领域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大学》具体明确了“静观”对于“格物”的必要性;道教为了交接神明,特重“斋戒”;魏晋玄学以“静”为本“动”为末,“无”为体“有”为用,强调以无统有,以静制动;佛学把以明镜之心去静静地参悟证入看成达于佛性的根本途径,强调以无物之心观色空之相;佛家宗派禅宗,无论南顿北渐,都强调宁静的心灵参悟;宋明理学更将虚静推向极致,它借佛道的个体修炼和宇宙论、认识论建构自己的伦理哲学,通过寂然不动的“主静”、“无欲”达到与天的“感而融通”,再通过人的思致而返归“纯然至善”。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是影响一切精神文明的思想背景。中国古代美学、文艺心理学领域的“虚静”论,正是在中国哲学“虚静”论的影响、启发下,在对审美活动的分析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自身规定性——既是一种虚空澄明的审美心态,又是一种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前者以后者为旨归,后者以前者为起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风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收稿日期:1999-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