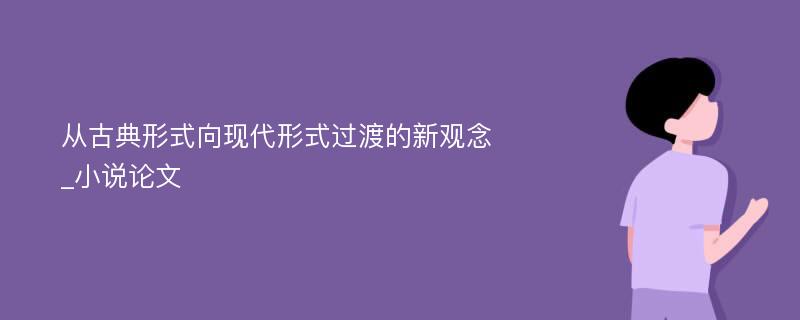
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小说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观念论文,古典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小说自萌芽状态,中经志怪、传奇、话本,到清朝后期已跌入低谷。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给中国小说注入了兴奋剂,使近代小说呈现出了与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的色彩。而且这些与传统小说若干迥然不同的色彩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程度地“传染”了“五四”文学,表现出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某些特点。
一、从“小道”到“大道”
从汉代至戊戌变法之前,小说在儒家的心目中始终是“小道”,并不为“正统”的儒家所称道。大雅君子虽于饭后茶余也可能读读小说,但绝不动笔写小说,而且将写小说视为贱劣行径,如胡应麟一方面赞叹《水浒传》作者的笔墨,一方面又慨息“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深为施耐庵将精力耗费在小说写作上而惋惜;程晋芳为好友吴敬梓将才华埋没于撰写小说而叹息不已:“《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黄小配还作文论述了“二十年以前文坛”以撰小说为辱的历史事实与社会根源。可见,无论是读小说的,还是写小说的,戊戌变法之前都认为小说是“小道”。
清末民初以前曾经有人为提高小说的地位而呐喊。最明显的是海上蠡勺居士的努力。他于1872年写有一篇汉译英国小说《昕夕闲谈》的《小叙》,蠡勺居士拿小说和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国史古鉴之记载作了比较,认为这些东西满纸说教,一般人听着听着就打瞌睡,而小说嘻笑怒骂,人们注目视之,倾耳听之,都觉得津津有味,所以它“感人也必易”,“入人也必深”,将小说列入“小道”是不合理的。蠡勺居士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比起前人来,在对小说的地位的认识上进了一大步。但他的这些意见并未得到世人的重视。原因很简单:条件不成熟,当时的社会环境还不需要他这些理论。小说在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仍然是“小道”。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铁甲战舰把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推入深渊。有着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救国救民的方略。开始他们是学习西洋造枪制炮,但这并未挡住八国联军的侵略。在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屡屡挨打遭败的同时,有识之士纷纷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对西方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特别是小说创作加以关注。“小说救国”的口号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赞同。
小说从“小道”转为“大道”还得力于政治家兼小说理论家、作家梁启超的呐喊。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利用他在维新变法前后所赢得的政治声誉,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带有煽动性地鼓吹小说对改良群治、开通民智的重大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的新小说论得到了广泛响应,陶祜曾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里声称:“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邱炜萲在《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中说:“文化日进,思潮日高,群知小说之效果捷于演说报章,不视为遣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美民德之要素……此其所以绝有价值也。”于是,在梁启超的鼓动下,小说的地位得到迅速提高,正如老棣(黄小配)在《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所说:“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而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
除了社会环境的需要和政治家兼文学家的呼唤,小说从“小道”升至“大道”还得力于翻译小说的启示。1890年至1919年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又一翻译高潮。在这次翻译高潮中,大量外国小说的输入使中国读者了解到:小说在欧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文学类型,有些有成就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上占据专章论述,地位不下于我国的唐宋八大家。楚卿于1903年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他说:“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伦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与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连自己的朋友都看不上眼的施耐庵在异域竟有如此高的地位,在我国被人视为小道的《水浒传》、《西厢记》在异国受到殊誉,这不得不令中国读者“骇”后而思。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论述小说的社会作用时,也是以域外小说为比照物的。康有为说“泰西尤隆小说学哉”;梁启超说“小说为国民之魂”,在异域,“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诠为之一变”。这些话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于是,小说适应形势的需要,借助于政治家的影响力,以西洋小说为参照物,于19、20世纪之交从“小道”神速地转变为“大道”。
借助于政治家的推动,通过“为政治服务”,使始终徘徊于文学殿堂之外的小说争得进入殿堂的门票,迅速地改变了小说界死气沉沉的现状。应该说,梁启超是有功劳的。但是借助政治提高小说的身份,而不是以小说自身应有价值显示其地位,这就像一位自身缺乏造血能力必须通过输血来维持生命的人一样,当然不会有健康的肌体。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开口便见喉咙”的作品很快就失却了读者,“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淹没了“小说界革命”者的呐喊。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值得记取。
二、从教诲劝戒到描摹人生百相
用不奇即怪或亦奇亦怪的故事使读者(听众)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接受教诲劝戒,其教诲劝戒的内容主要是包括封建道德的人之常理,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主题。小说以“人之常理”教诲劝戒于人,常此以往,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势必蹈入重复与类似的泥坑。集志怪与传奇之大成的《太平广记钞》以及集中国话本小说之精粹的“三言”、“两拍”之所以给人千篇一律、重复类同的感觉。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以教诲与劝戒为己任的小说并没有错,而且将来它仍旧是小说内容的一个分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它还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小说内容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缺陷是主题的狭隘,它只能是小说的一部分,而不能成为小说的全部。中国传统小说的弊端就在于将部分当作全体。这就束缚了中国小说的行进步伐。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不以教诲与劝戒为己任而是以揭示人的复杂情感世界为主的《金瓶梅》、《红楼梦》,但在问世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因受传统小说观念的强大斥力而未受到世人重视。
《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西方小说的陆续引进,使中国传统小说的教诲、劝戒观念受到震动。大小仲马、狄更斯、嚣俄、欧文等人的作品成为中国读者喜爱的读物,其感人肺腑的情节、深沉的人生意蕴成为中国小说作家仿效的楷模。从此,中国小说发生重大变化:从教诲劝戒而转向描摹社会人生的广阔图画。这一转变,堪称中国小说的近代革命和“五四”现代小说的先声。因为与以教诲劝戒为主题的传统小说相比,描绘人生百相的小说必须在取材、结构等许多方面作相应的调整乃至变革。
以教诲与劝戒为目的的传统小说,所取的素材基本上是死的,它不需要作家一定去体验生活,即使凭想象编造一个故事,只要能达到教诲与劝戒的目的,也就百事大吉了。在志怪、传奇、话本里,我们很少看到描写人生图画的生动笔墨,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传统小说观念的陈腐。而以社会人生百相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却要求作家必须有生活,否则他的描写就会失真。尽管清末民初的大部分小说作家由于出身经历的限制还很难驾驭其作品,而且作品所暴露的缺点与问题也恰恰说明了新型小说对作家必须具备生活体验的要求,但是众多作家的众多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小说从教诲劝戒向描绘人生的转移,尽管这种转移还仅仅是开始。
清末民初的小说作品,数量极为可观,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清末民初的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图景。在描绘社会人生的风貌方面,崛起于20世纪初的短篇小说胜于当时的长篇。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有数千之多,只是由于大部分未结集至今仍尘封于历史的一角而为人所忽视。就我们现在能见到的部分作品来看,它们犹如一个个特写镜头,记录了时代的风云。从王钟麒的《学究教育谈》我们看到了维新派所号召的新学与实践中的新学之间的距离之大。从吴趼人的《查功课》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镇压同盟会所采取的卑鄙手段。从饮椒的《地方自治》我们可以看到“预备立宪”的骗人把戏。从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和包柚斧的《善良烟鼠》我们可以看到鸦片对中国人民毒害的真实情景。从叶圣陶的《穷愁》、《贫女泪》和罗韦士的《卖花女》、《采桑女》以及恽铁樵的《工人小史》,我们可以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工农的悲惨生活。
总之,清末民初的小说作家,其笔锋所及,从皇宫帝王将相,到县衙文武官员,以及洋奴、买办、商人、财主、妓女、市民、文人学士、华侨、兵弁、革命者种种形象,官场、商场、战场、贫民窟等等各个角落,都作了较为生动的描绘,展现了各个阶级、阶层的动态。那种以教诲与劝戒为宗旨而编造小说的情形渐渐失去了市场。但是,清末民初的小说作家大部分出身微贱,既与上层统治阶段隔着一堵屏障,又与下层工农相当隔膜,他们的作品所描写的又恰恰是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工农。暴露统治阶级丑态的谴责小说有概念化、新闻化倾向,描写工农血泪生活的短篇小说有干瘪瘦弱之嫌,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三、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专为下等社会写照”
清末民初,狄更斯、大小仲马、嚣俄等作家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生活的小说,打开了中国小说家的视野,特别是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为中国小说作家提供了以下层劳动者为描写对象的范本,使“专为下等社会写照”(林纾语)成为当时思想比较进步的一批作家所自觉追求的目标,而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类的题材渐渐受到冷落。
作品的思想内容之所以从“上”向“下”滑动,首先与作家的构成成分发生了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小说的作者的身份虽然不甚整齐,但大致说来却以出身显贵者为主。白话小说的作者出身比较复杂,有的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如曹雪芹,有的头戴桂冠,如凌濛初,但大多是不得志的失意文人。他们之中除林纾、梁启超、曾朴、丘菽园等寥寥几位出身举人外,其余多为布衣:李伯元屡试不第,只好到上海靠办小报谋生;吴趼人从中落的官僚家庭走出,20多岁就辗转于上海、山东、日本,最后不得不卖文为生,病死于上海;刘鹗虽稍好一点,曾因治河有功官至知府,但因曾从俄军处贱价购买太仓粮转卖给居民,后来被劾私售仓粟谪徙新疆而死。从整体上来看,清末民初的小说作家,在出身门第及帽翎的等级上,比起前代来明显地呈下滑趋势。
文学作品是作者的思想感情、社会经历的曲折而形象的再现。统治阶级的座上客所熟悉的是帝王将相的生活,所热衷的是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他们的作品也就不可能离开这些题目。于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下层劳动人民只有在个别话本里有几笔少得极为可怜的描写。这正如鲁迅先生的《南腔北调集·〈总退却〉序》里所说:“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小说的结局也多半是封王挂印或大团圆的美满下场。若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作家与统治阶级和下层劳动者之间分别划两条线,他们与下层劳动者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更接近于下层劳动者。他们的作品较多地描写下层社会,抒发下层劳动者的思想感情也就在情理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与西方民主思想的碰撞,是中国小说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重要契机。同情弱小者、怜悯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描写劳动人民对社会的贡献与他们应该得到的之间的悬殊,从而对他们的不幸命运予以同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积极主题。它既可以视作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也可以视作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人道主义精神的闪烁。这种精神只会因历史的前进而更加明亮,却不会被历史泯灭。当历史车轮转到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西方民主思想通过种种途径传入我国,特别是翻译小说中下层劳动者备受磨难的情节,更激起了富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小说作家的同情心。它无异于电火花,将中西作家所共有的同情下层社会的思想牢牢地对接起来。
中国小说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专为下等社会写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成分加重,二是以劳动人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增多。
在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对立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宝座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攻击下愈显摇摇欲坠之势,其腐败性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时期的谴责小说以辛辣的讽刺,嘲弄了统治阶级的无耻、腐朽,揭露了他们色厉内荏的肮脏灵魂。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阶级成为小说中讽刺的对象。小说创作的这种倾向,在以前的作品中还极少出现。以前的小说或出自官办的史家之手,或出自富贵的秀才文人,其作品要么歌颂帝王将相的业德才略,要么描写公子小姐的缠绵情思,表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向,下层劳动者的爱憎只有在个别思想进步的小说作家的作品里才偶有流露。
如果说表现下层劳动者的爱憎之情主要体现在以吴趼人、李伯元、刘鹗、曾朴等为代表的谴责小说里,那么以下层劳动者的具体生活为描写对象则表现在清末民初后期崛起的短篇小说里。可以看到,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所描写的下层人物是十分广泛的,其中有工人、农民、渔民、士兵、华工、学生、村姑、商人、妓女、厨役等。作品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描绘了他们艰难的人生。周瘦鹃的《檐下》写一位衣衫褴褛的修路工人和为他送午饭的妻子,在红墙大宅的屋檐下,相敬相爱,相濡以沫,而百页窗内的富家夫妇却争风吃醋,闹得沸反盈天,作品指出劳动人民的朴实无华的情操要比有钱有势的富人的狭隘卑鄙的心怀高尚得多。恽铁樵的《工人小史》的主人公是上海南市某厂工人,作品描写了他辛苦挣扎却难得温饱的一生。髯的《农家血》描绘的是地地道道的农家血泪:农民钱大哥在颗粒未收的岁月仍被逼照例交租,被关进大牢死于非命,其妻悬梁,女儿投河。无愁的《渔家苦》吐的是渔民的一腔苦水。企翁的《欧战声中苦力界》描写了欧洲战争爆发,在“洋行也关门了,海船也停驶了,土货又不能出口,洋货又不能进来”的情势下,上海靠出卖苦力的一群人难熬的日月。短篇小说中的另一类,不是以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为主,而是以提示下层人的美好心灵为己任。如俞天愤的《卖菜儿》歌颂了一位以叫卖青菜为生的十几岁的孩子的高尚品德;罗韦士的《采桑女》所写的虽然也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但主人翁已由农家姑娘和穷书生代替了传统小说中的公子小姐,作品歌颂了他们清彻见底的纯真爱情。周瘦鹃的《为国牺牲》歌颂了一位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国对日宣战之后,他毅然告别妻子,奔赴战场,最后以身堵炮眼,壮烈牺牲。
四、从传统笔法到中西合璧
中国传统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由于目的是向听众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所以在结构上都呈链条式:人物情节一环扣一环绝不散架,各个人物都有所交待。从结构上来看,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物情节多少不同、起伏的波浪大小有别。一个短篇可以扩写成长篇,反之亦然。由于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巨大张力,清末民初时期的长篇小说还难于完全摆脱这种链条结构模式,但局部已在西洋小说的影响下作了一定的变革:章回体的对偶式回目、开头结尾的套语为自由得体的方式代替;链条所串连的环扣不再那么紧密,其周围吸附上若干与主链条有关的部件……这是由于长篇小说是一个大的工程,西洋小说的影响力一时还难于打破它数千年形成的结构模式。
西洋小说影响下的短篇小说却得到较大改变。浓缩了的长篇式的链条结构已经渐渐失去市场,横断面的结构方式,即以类似于特写镜头,截取人生或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片断来表现人的性格和社会现实的方式渐渐为作家所青睐。这样的短篇小说是富于现代意识的短篇小说,是真正的短篇小说,它绝不能随作家的意志而任意放大,“虽云短制,颇同长篇”(鲁迅语)的情况不会存在。例如陈景韩的《路毙》截取的只是在“隆冬腊月天里倒于城厢之内,十字街之路侧”的一老汉这个镜头;吴趼人的《查功课》也只写了督署到某学堂查功课那一刻所发生的事情;徐卓呆的《入场券》只写了“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入场时所发生的一件小事;徐卓呆的另一短篇《买路钱》是某大显贵罢官归故里时在半路上的奇遇……它们都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由于作品只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场面,作品的故事性、情节性明显淡化,给读者以更多思考想像的余地。情节的淡化和非情节因素的加强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个表现方面,其变革意义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才显露出来。
在描写手法上,西洋小说给中国传统小说带来的新东西,一是心理描写,二是景物描写。
中国传统小说并不乏精彩的心理描写,但由于“说话”这一形式的特定要求,不得不以人物的言语行动折射之,不便从正面直书,否则就会令听众打瞌睡。西洋小说却惯用细腻入微的笔触直书人物的心理活动,大段的心理自白俯拾皆是。清末民初期间中国的小说作家所以能够接受西洋小说的这种技法,一是由于这时中国小说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说”到“写”的过渡,使学习这一技法有了可能性;二是由于这种技法恰恰是中国传统小说所缺少的,学习这种技法很有必要。周瘦鹃的《真假爱情》里郑亮在情敌、朋友落水呼救时的矛盾、吴趼人的《恨海》里棣华与伯和在逃难途中同宿一床时的羞怯与激动、刘鹗的《老残游记》里妓女翠环在得到老残要将她救出火坑时的时而欣喜时而忧心忡忡的复杂心情……都是借鉴学习西洋小说中心理描写的范例。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用第一人称手法着意描绘方外之人的难言之恫,随时随地自我剖白,将其视作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抒情心理小说的先躯都不为过。
中国传统小说,诸如志怪、传奇、话本里,极少景物描写,只有在《红楼梦》等极少数作品中才能找到几笔。在西洋小说里,景物描写大致是用来烘衬时代背景、映照人物的心理活动的。而烘衬时代背景和映照人物心理,在中国传统小说里一般不采用、也不适合采用景物描写这种方式,因为中国传统小说重情节,景物描写这一非情节因素势必受到排斥。西洋小说大量译进之后,其中的景物描写受到我国部分小说作家的青睐,也试着在自己的作品中试验使用。《玉梨魂》开篇的梨园描写以及《老残游记》里关于大明湖、千佛山的景色描写都是十分成功的例子。
五、从文言到白话
清末民初以前小说的语言,距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尚有一段距离。文言小说自不必说,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以及“三言”、“两拍”也并非是用纯正的白话写成的。它们之中,有的是夹杂了不少文言的白话,有的是宋元时代的白话,有的是酸秀才的白话。这种语言实际上还有相当浓重的书面语色彩,并非口头日用语,尤其算不上清末民初老百姓的口语,清末民初的小说作家开始自觉地疏远文言而追求一种朴实无华的白话。虽然用极为通俗的白话写成的小说还是凤毛麟角,有的只是用方言土语,有的是用浅易的文言,有的则尽量削弱秀才气而用半文半白的语言……但追求接近日常口语的风气开始形成。例如连梦青的《邻女语》、黄世仲的《宦海升沉录》、符霖的《禽海石》的语言已经接近老百姓的口语,酸秀才气味十分淡薄,识字不多的老百姓已经能读懂。四大谴责小说中虽然也有个别生僻字,但白话成分已占优势,至于短篇小说《查功课》、《入场券》以及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言情小说已经是相当标准的白话文了。
清末民初的小说语言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其原因、动力是多方面的。它首先是适应改良群治、启发民智的政治需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发动群众以使提高他们的觉悟。维新派人士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开通民智;要开通民智,必须人人通晓文字,读得懂有相当大的社会作用的小说。而传统的小说言文分离,显然有碍于“人人通晓文字”,从而使开通民智落空。所以,维新派人士极力推广白话文,提倡用浅近的白话写小说以启发民智,达到发动群众,国家强盛的目的。维新派人士发动的白话文运动促进了中国小说语言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
西洋小说的译进是中国小说语言从文言向白话转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林纾用文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只是在各阶层知识分子中流传,读者并不太多。一般老百姓还读不懂他的文言小说。直到用白话译成的《黑奴吁天录》问世之后,识字不多的老百姓也成为读者才使翻译家认识到白话文的长处,以白话译西洋小说蔚为风气。以老百姓读得懂为目的的西洋小说译本的大量问世,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文白相间的语言格局,渐渐形成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白话文。例如周桂笙、陈冷血、包天笑等人的译文和创作小说都是使用这种白话文写成的。如果没有西洋小说的译进,也就没有以白话译西洋小说这种风气,所以我们认为西洋小说的译进是中国小说从文言向白话转变的动力之一。
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的发现是中国小说从文言向白话转变的巨大动力。20世纪初叶,上海、天津、北京等工业大城市的崛起,产生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市民队伍。这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识字不多,但紧张的劳作之余有寻求娱乐消遣的要求。这时,梁启超及其麾下的“开口便见喉咙”的政治小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失去市场。市民迫切需要一种轻松的文学样式供他们工余茶后消磨时光。于是在这种情势下,小说的另一种功能——娱乐与消遣——被小说作家重新发现。社会需求刺激了生产,以市民读者群为对象的白话小说很快就风靡文坛。
但是,清末民初20余年间,虽然白话小说的市场越来越广阔,文言小说仍旧有一定势力。这是因为当时的小说作家大都是读过旧学的人。他们有的既用文言也用白话写作,有的则先用文言写就再“译”成白话,这就难免在白话中夹杂上些文言,即使以白话为目标也难于收到预期的效果。另外,当时的小说作家大都是江浙人,他们对“官话”虽然听得懂,但并不十分熟悉,所以他们极力模仿“官话”所写的白话小说,距“读其文者,如见其人,如聆其语,不知此时为看小说,几疑身入其中”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再说语言是内容的载体,小说语言真正做到明白如话,首先要求小说作者是具备平民思想的人,因为只有平民作者才最熟悉平民的语言。在清末民初,绝大多数小说作家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中国小说的语言从文言向白话过渡的完成还有待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