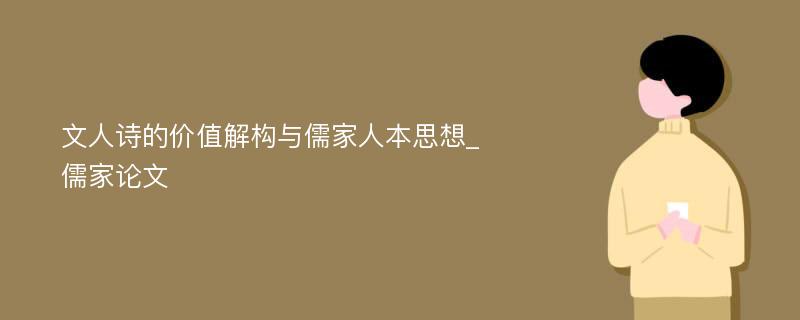
文人诗词的价值解构与儒家人本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文人论文,人本论文,诗词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古代诗歌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结构中一直以亚文化的方式执行其伦理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古典文人诗词从社会审美的层面反映了以儒家人本思想为主流的文化建构的源流。文人诗词借助美神意识和酒神精神,表现了审美理想与人性价值在政治媚俗中的纠缠与迷离,这虽然代表了类似民粹主义的人本价值取向,但并不具备反主流规范的内在要求。中国文人文学的功能始终趋向伦理秩序的整合,因而难以形成近代意义的文学精神。
关键词 文人诗词 儒家文化 社会审美 价值形态 雅颂 美神 酒神 人本主义
从周秦的《诗经》起,古代诗歌就一直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结构中以亚文化的方式执行其伦理功能。汉唐以来的文人诗词,则是从社会审美的层面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渊源。由于中国文人所特有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主要来自儒家入世的的人本思想,诗词不仅作为历代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立德立言的基本形式,也是藉以安身立命、寄托理想的精神支柱。在一定意义上,摈除文人与官僚一体化的官方文学因素,文人诗词中一些最具解读力的传世作品,主要来自那些仕途坎陷或政治失意的文人学者。他们托物比兴、隐逸孤怀的审美意境与省思人生、褒贬世俗的文学主题,通过诗词的延宕与流变,为弘扬儒家的使命精神和人格精神,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文人文学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形态。
《诗经》所衍化的雅颂精神,象征了儒家传统的社会审美理想。因而,作为儒家雅颂与个人际遇相互契合的文人诗词,借助美神意识和酒神精神的感发,反映了审美价值与人性价值在政治媚俗中的纠缠与迷离。文人诗词的不同价值归途,不仅烘托了历代文人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徜徉的忧患意识,而且昭示了传统理性结构中不断嬗递的质疑精神。但是,古典诗词中由贵族文学所演变的文化精英主义气质,虽然代表了类似民粹主义的人本倾向,却并不具备反主流规范的内在要求。文学的功能也不再注重人性价值的思辨与建树,而是始终趋向伦理秩序的整合。儒家知识分子在切割现实的文学整形中,虽然有时在意识形态上是质疑的,但在道德上却是始终合致的。因此,文人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亚文化形态,与近代欧洲出现的个人主义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别。用古典诗词来诠释“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治的儒家”,并赋予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思考,显然可以从深层结构理解中国的文学精神。
1
中国的古代诗歌,从文艺美学的层面反映了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文化发展的渊源。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作为文学艺术的古代诗歌,不仅是个人抒发情志的文体著述形式,而且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濡化方式。从孔子删赞《诗经》开始,诗歌就被规范到儒家传统的价值结构中,以亚文化的方式执行其伦理功能。由于孔子“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意识滥觞,儒家种种人伦的义务和社会的责任从此便落在文人学者的肩上。源于农业文明的文化秩序与社会建制的营造意识,则诱发了文人建德立说的愿望和好大喜功的心态。所以,凡是以儒家思想入世的文人,无论自觉不自觉,其文学道路都要钻进政治理想主义的圈子。汉唐以来的文人诗词,既是文人藉以安身立命,寄托情志的精神支柱,又是求取功禄,立德立言的主要形式。文学与政治的不解之缘,使诗词艺术的价值整合最终将达成教义与文体的统一。无论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那些最具可读性的传世作品,都充溢了审美理想与圣贤人格的揄扬,其辞章言情喻理,藻饰文采,目的都是为了观照社会和劝尉人生。
古代诗词文学的延宕与流变,勾勒了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自汉代开始,举荐文学、贤良的条件,不惟精通经学,还要熟习辞赋,两者相得益彰,方能致仕。唐宋以来,诗词艺术达到顶峰,究其原因,一是科举取士,文人皆以韵文和散文获取功名;二是历朝统治者都宏奖诗词,优待士人,诗词势必成为受宠的、儒雅的文学形式。官方的主流文学则是将北方崇尚经学的文学与南方注重诗歌的文学,合一炉而冶之,诗歌的审美价值与社会的伦理规范因此得到整合。同时,诗词作为先秦礼乐文化的承续,又有新的发展。在形式上,儒家礼乐的建制与诗词艺术的程式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诗词的创制首先要精通礼仪和音律,方能制谱填词,使雅乐颂曲不断翻新。在内容上,诗词的取材超越了六朝时的宫体范围,不惟公子王侯,才郎佳丽,而且村夫野老,妇孺樵牧,和尚道士等,都可以纳入诗词意象。随着儒家政治文化的复兴,文人诗词也愈来愈繁荣,这标志着传统社会以诗歌方式揭示政治伦理价值和个人存在价值的内在联系。
中国古代多数文人所特有的道德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主要来自儒家入世的人本思想,所以“致君尧舜”、“济世拯民”的人生思想,体现为政治价值与人生价值的统一。孔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诲,使中国文人在对生命本真的的追求中,始终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建功立业,辅弼王权,实现兼济天下;要么诗词立言,穷而后工,以求独善其身。由于大多数的文人学者都是仕途坎坷,不仅不能官达位显,而且即使入仕,也常常被排斥于朝政之外,在中国的社会系统中,因为没有相应的机制容纳文人群体的分化与组合,文学道路便作为失意文人寻求审美自足与道德自觉的唯一精神领地。诗词托物比兴、隐逸孤怀的审美意境与省思人生、褒贬世俗的文学主题,一方面融入了文人的个人情操与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也凝结了儒家关注伦常之道的使命意识和精英意识,从而构成传统诗词的主要价值形态,包括文人的思维定势、心理结构、审美习惯以及政治理想等。因此,文人诗词在排除了官方文学的因素之后,相对注重社会现实与人生际遇的感受。文人的审美观照,也多从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的题材中获得共识。这是文人诗词的显著特征。
一般说来,文人诗词的审美取向,一是抒发人生的恋情心理,二是咏怀现世的忧患意识,这主要来自个人际遇的不同体验。抒发恋情心理的诗词,主要表现伤春悲秋,离情别怨的内容,具有婉约美的特征,像欧阳修的“更被春风送惆怅,落花飞絮两翩翩”,秦观的“伤情处,高楼望断,灯火已黄昏”等等,深切抒发了人生对岁月流失、繁华无常的无奈与感叹。咏怀忧患意识的诗词,主要表现个人身世、家国前途的内容,具有悲壮美的特征,像李煜的“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陈亮的“正销魂又是,疏星淡月,子规声断”等等,强烈寄托了家国不幸、世事纷纭的的感慨和愁怀。文人诗词中婉约、悲壮的审美旨趣,是以情韵交合的方式来展现的,因此,诗词的道德理序与语象艺术的转换,常常唤起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和现实责任感。所以文人诗词中的怀古和咏史的题材颇多,像“愿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就将求取封侯与人生价值的困惑,融入悠长的历史沉思,因而蕴藉着丰厚的人本主义精神。文人诗词也注重暴露现实矛盾的社会主题,像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就以税赋、灾役、兵乱、离愁为题材,贯注了无限的哀思与同情,表现了文人诗词审美悲壮的精神。《诗大序》这样说:“故止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可见,诗词作为与儒家社会审美理想有关的文学形式,最终衍化为政治秩序与人伦秩序的象征,并一直规范着文人的价值取向。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倾向鼓励“自得其乐”,并且将整个文化建基于自足的圣贤人格与王道理想之上,但诗词文学的价值结构,则是鲜明地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对理想秩序的殷切与执迷。文人诗词或以人本主义的审美理想来抚慰自我,或以精英主义的参与意识来批驳现实,这种由迷离和纠缠所形成的文人入世致用的精神,必然投向更为广阔的群体范围或虚空世界,才能实现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最终结合。
古代诗歌艺术,原本属于传统礼乐文化的范畴。儒家关于“雅颂”的称谓,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先秦礼乐制度的总结,因为“雅”是朝廷盛典用的礼乐,“颂”是宗庙祭祀用的礼乐,均属于社会的约束性质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二是雅颂作为“诗三百篇”的主要内容,代表了孔子对诗歌美学意境和道德价值的最高评价,并延伸为儒家社会审美理想与伦理政治的完美概括。因此,“雅颂”精神不仅是与“风俗”诗歌相对应的美学概念,也是与“世俗”政治相对应的哲学思想,具有儒家文化的深刻蕴涵。由于儒家首先关心的是治世之道,所以起初并不注重发掘诗歌净化道德的美学价值,认为风俗化的诗歌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后世儒家也认为美感只能煽动人们的欲望,华艳足以冶荡人们的心灵,所以一直有“辞赋小道,壮夫不为”的说教。到了汉代,辞赋文学被文人普遍接受,并逐渐纳入儒家正统文化的体系。班固曾说:“赋者,古诗之流变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若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两都赋序》)这里,班固深刻表达了古代诗歌的伦理使命,就是确认辞赋作为由雅颂所扮演的文化权力结构的亚文化方式。由此说明,文人诗词唯有借助雅颂精神,才得以实现儒家价值观与审美观的不断嬗递。
2
儒家意识形态作为审美观和道德观的表征,是用来支持或改变既存现制的思想,因而具有支配性的文化哲学意义。所以,文学的价值形态并不仅仅表现为情感体验或审美旨趣的潜意识,它最终要将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与意识形态的理性系统结合起来,加以重新组构。文人诗歌因此侧重政治理想主义的价值选择,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把谪贬时弊、褒扬人事作为体现使命意识和人格精神的象征。雅颂在文人诗词中吊诡地运作,不仅能激发出对美好事物和生命本真的眷恋情怀,而且也能将文学省思机制中隐藏的理想成分,迎合某些乌托邦的因素,这样,文人诗词将政治理想的豪壮与艺术审美的委婉揉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秩序化和主流化的架构,改变纯艺术形式不代表他人、也不向社会承诺的姿态,并不断加强那些意识形态化的质素。
文人诗词普遍存在的艺术倾向,就是将儒家的雅颂嬗递演变为美神的召唤和启迪。美神形象在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因为在世界范围的神话体系或文学形式中,女性美神都是作为人类希望与祥和的象征。美神除了独具的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之外,又体现了人们追求人生与社会最佳选择的文化心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与之相似的“后妃之德”的概念,这虽是一种从属地位的美神形象,不同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性格,但仍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式的美神意识,是以善为前提的,其美感与美质的产生,都是来自秩序与和谐。从《诗经》开始,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描写,就被纳入儒家理想政治的价值体系。孔子曾依照道德理想主义的原则来删选诗歌,编定《诗经》,开创了以美色来喻比德政的先声。这样,儒家将德政、仁道的审美理想寓于男女情爱之题材,反映了先儒对美德、美俗、美政的执着,以及以其学说作为“后妃之德”来辅政佐世的愿望。由儒家思想演绎的美神精神,在传统的文人诗词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君子遇美人的题材,强烈寄托了文人欲寻觅知遇、展示自我的价值意识,体现了完美人格与理想美政的最佳结合。由于女性美神在表现人生的男女情爱和社会的政治际遇之间,具有某种同构的关系,因而在作为文人精英意识和存在价值的理性超越时,可以使人生与社会的最敏感主题——爱情与政治的双重理性——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上得到深层的契合。
雅颂精神向美神意识的嬗递,使文人诗词的审美特质因此蕴藉了朦胧的乌托邦精神和桃花园情结。在楚辞中,屈原率先对美人芳草予以高雅而深挚的颂扬,将孤傲深沉的美学意蕴与纯厚坚实的哲学内涵,化作对世间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以后,像宋玉的辞赋作品,借写美人幽思怀春,来暗示君王要纳贤取士,以美人操守坚贞的品德,来自喻人格的尊严与美政的向往。曹植也善用美人比兴,他多以美人失恋来寄托感士不遇的孤独,用春梦幽合来喻比人与人衷情不能相通的苦闷,反映了个体价值意识在群己关系中欲求解脱和慰藉的愁怀。在历代的文人诗词中,美神意境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沿习。像李白的“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苏轼的“望美人兮天一方”,以及辛弃疾的“暮云飞,佳人何处?数尽归鸦”,等等,都是寄寓情志于空渺之中的美神。这些虚幻境界的神女仙姬,飘飘忽忽,时隐时现,她们都不是诗人专诚的情爱对象,而是借以实现社会审美理想和自身存在价值的化身,其中深刻的意蕴在于:用完美的女神形象来启迪和召唤文人入世;用高洁的人格精神来喻比和感怀生命本真;男女情感的交融则是为了憧憬崇高的道义与和谐的美政。美神精神对诗词意境的渲染,使意识形态的美感能指最终嬗化为一种文化秩序的建构。
文人诗词中的美神意识,隐藏着儒家在现世中谋求人与神相互沟通的强烈愿望,这可以视为一种灵魂的自我救赎方式。美人形象在古典诗词中频频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和社会政治原因,因为传统社会中男女情爱的悲剧比比皆是,文人的政治压抑感又普遍存在,所以,女性美神所具有的独特艺术美感和富于表现理想的非凡效果,深切表达了对现实的超越和未来的憧憬,它一方面通过形象美来展现文人的使命意识和价值意识,另一方面又透过意境美来反照社会现制的污浊与丑恶。深层的涵义则是文人带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追寻失落之中的人生目标。男女情爱在本质上所具有的人格再造和人性向善的内蕴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深邃。用女性的美感来反衬现实的丑陋,是文人诗词的惯用手法,它既隐含了文人自负才情而无知遇的苦恼,又表达了对那些以谄媚邀宠得势的庸官佞臣的不满。所以,李白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抱负,杜甫有“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的感叹,韩愈有“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的风骨。当政治参与的入世精神彻底失落以后,他们便只能从虚空的女神寄托中得到最深沉的抚慰。
文人诗词除了塑造出那些令人意动神迷的美人佳丽来寄寓理想之外,也刻画了一批表现离情别恨、相思愁怀的哀女怨妇来抒发身世的不幸。这里,从政治理想的破灭,到忧患意识的膨胀,再到隐逸情结的感发,表达了女神意识的跌落,从而鲜明地烙上文人心态随时势迁变的印记。在哀怨女性的寄托中,常常借助环境的烘托,如风雨落花、缺月残云之类的景物描绘,以及情怀感伤、哀痛幽思的细致刻画,使文人苍凉凄婉的心境更加强烈挚真。如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沂孙的“双蛾不拂青鸾冷,任花阴寂寞”,等等,就将一种深沉的哀怨融入诗词的审美意境。表现女性哀怨的作品繁多,是因为以美人姿色凋零、心灰意冷来感伤年华易逝和青春渐老,反映的却是传统社会中普遍的文人心态。它有些类似西方文学中临水自照的“水仙子”情结,是一种感伤个人际遇不幸的自恋型心态。由于文人的入世主义精神主要源于儒家思想的疏导,建功立业、敬德保民便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终极目标。当女神意识的跌落同个人际遇的不幸联系在一起时,女性哀怨所示的自恋情结,便会演变成失意文人的最深重的悲哀。审美理想的转移,渐渐消解了渴望朝廷知遇或才情不得施展的忧郁,隐逸心态也深化为人生存在价值的反思和回归。
女神精神蕴含的审美理想以及对生命本真的反照,体现了古代文人欲以理性的方式质疑传统价值的思维定势。由于文人诗词很难完全脱离历史真实和文化存续所创造的想象世界,儒家雅颂所衍化出来的女神意识,其伦理骨架一般并不具备颠覆性或破坏性的因素,但透过女性哀怨的审美寄托,则可以看到个人生命所承受的重压。文人普遍感到的崩坍使他们逐渐疏远了自由浪漫的章法,而采取较为严整的形式,来节制情感的泛滥,其人文精神的延伸,又似乎隐藏了某种质疑性或异见性。这种由文化精英意识造成的道德悖论,决定了古代文人在伦理意识和价值观念方面,与国家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结构的分合。当一种类似玄理禅思的内心体证,将尘缘的丑恶或缺陷用美丽的语言和动人的情感加以乔妆打扮,并且假定一切丑陋均不存在时,文人诗词的审美理想就偏离了雅颂的价值规范。
3
历史上,道德价值体系从分崩走向重建,再由坚挺倒向疲软的周而复始,决定了儒家文化在秩序建构中的地位。政治的羁绊使文人只能依照秩序的观念来启动他们的文学本能。当社会普遍弥漫的失落感和孤寂感被玄理精神或禅宗悟辩所统摄时,一种游离于儒学之外的文学倾向,便是以佛老的崇尚自然本真之性来解构儒家的学说。因为文人的整体意识在经历了社会分裂与重建专制所造成的精神空虚之后,已经能够超越现实的迍邅。一些文人以登临山水、琴棋书画为真趣,将隐逸心态与诗酒情趣融为一体,试图摆脱传统价值的困扰。这种看似不流于世俗,实际却未脱离媚俗的文学准则,在外部力量和内存情感压力下,又构造了文人诗词的另一个范本。这里,已经看不到由雅颂精神嬗变的女神形象,取而代之的,却是由媚俗特质所濡化的酒神精神的弥漫。
作为与雅颂精神相对应的文艺美学的价值形式,“媚俗”现象代表了文人诗词企盼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理想。先秦时期的人文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将媚俗排斥于《诗经》之外的。《论语》中曾有王孙贾以世俗之言感化孔子,欲使孔子求昵之的记述,但孔子不以然,却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论语·八佾》),表示儒家宁肯阿附国家最高执政,也不讨好有权势的官僚。孟子也是鄙视“媚世”的,他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将草民愚昧与谄媚权贵加以比照,反衬了儒家政治的崇高。孔孟不肯流于世俗权势的精英意识和人格精神,确为儒学凭添了许多浩然正气。这对后世的文人意识显然具有深刻的影响,文学雅颂的审美现想也得以传承。但是,文学作为一种最终流俗化的文本形式,毕竟不能代替教义层次的空泛说教,同时,诗歌艺术也不可能面对社会难题,谋求解决之道。这样,在文人诗词的价值体系中,除去绮丽浮华的艳体诗、宫阁词而另辟蹊径之外,最终还是要认同诗歌艺术的风俗化。雅颂精神作为《诗经》演绎的道德观与审美观的最佳结合,是以礼乐文化的道德体验和真实人性作为基础的,因而必然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的美质,并由此涵化了美神意识,包容了文人的使命精神和人格精神。然而,当文人的整体意识变得虚空之后,艺术形式也作为审美理想的唯一来源时,文学价值便会嬗递为“媚俗”。这样,文人诗词在取悦世俗的艺术氛围中,又营造了酒神式的文学审美形式。
酒神精神作为原始文明的象征,也是缘于中国乐感文化,与古代诗歌同出一脉。由于文人以饮酒为乐事,诗歌与饮酒的结缘,使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特异古风。诗酒意境作为一种文化心态的渲染,适应了文人寻求慰藉,摆脱孤寂的审美心理,在文人诗词的创意中层出不穷,并被赋予不同的艺术内涵。所以,杜甫有“白日放歌须纵酒”的豪迈,李白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悲放。酒所造就的一时间的形神相分的欣快幻觉与诗所要求的对普通情性的超越融合到一起,就在这种诗酒合一中,令文人感受到某种与文化有关的兴奋。酒虽然不能改变文人的情志,却能够通过暂时的快感来增强某种心态,将朦胧混沌与明察洞鉴混而为一,同时又兼容了隐逸情结与非理性状态。这似乎表明,文人诗酒意境折射出对浮世人生的依恋与执着,并不是为了寻觅理想的仙境。事实上,中国式的酒神精神是作为与文化秩序相联系的心理结构和价值形态,蕴含了伦理约束与人性规范的内在要求。与西方酒神文明不同的是,中国的酒神意识并不是用来谋求人与神的沟通,或致力于自我灵魂的救赎,而是转过来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隔膜和差忤。尽管等级是森严的,礼法是刻板的,但只要循规蹈矩,人们毕竟可以相安无事地以诗酒作乐,从而将传统的礼乐文化演变成一种媚俗式的欢娱。
酒神精神被纳入某种文化范式,创造各种艺术意境,其实是与酒本身的特点有关。汉代的《说文解字》,就从传统文化的层面,诠解了酒所具有的“就人性之善恶”、“造人生之吉凶”的内在涵义。如果说,经过历代文人的发掘,酒的功用在于体证人与人的关系,或省思人的自我存在价值,那么,透过酒神意识的阐发,却可以促使人们摆脱种种情感的桎梏而能赢得自由的心态,体现生命意义的本真。酒神精神适应了各式各样的文人心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风貌,曹操对酒当歌,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感慨,来抒发军事失利后的苦闷;陶潜诗酒田园,有“何以谓我情,浊酒且自陶”的郁欢,以排遣官场失意后的烦恼;苏轼把酒问天,触发了历史与人生的沉重感,也唯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遗恨。不容置否,人性和情感的张扬是从个体存在价值的确认开始的,文人正是在肯定自身需要和合理存在的基础上,寻找人本思想价值的归途。但是,用一种昏沉沉的酒神心态来伸张人性,是失意文人遁入艺术王国的无奈发泄,而传统的价值结构则是不能容忍激情恍惚者的质疑精神。所以,在本质上,中国的酒神意识是鼓励人们流于世俗,它所要求的是一种对现世的绝对认同精神。酒神意识排斥人们兴奋之后的醒世精神,这可以视作是对文人忧患意识和精英意识的销蚀,这样,诗词艺术的媚俗特质将最终排除价值结构中的质疑性和异见性。
在中国文化中,人生价值的置换与社会制度的存续,主要来自对现世的依恋。儒家入世的人本思想也加强了这种趋势。当轻松而媚俗的文学审美精神,将人世的哀伤、慰藉和留连都用酒神心态加以淡泊和忘却之后,现实丑恶与审美理想之间的痕迹便得到弥合。而文人的醒世精神是无法与现实相颉抗的。酒神精神作为文学的媚俗,是对屈原式的“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忧患意识的嘲讽和戏谑,由此形成了缧绁世代的文人顽世心态。酒神的意识形态媚俗,是将自身与世人都捆绑起来,用肤浅的美感和快感慢慢地消解理性或现实中的矛盾冲突。因此,酒神精神对文人诗词艺术的浸润,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女神意识所形成的影响。酒神将传统的末落资源与未来的理性资源都搅合在一起,经过狂热的纷乱之后的再次整合,它所延伸出来的工具化或功利化的理性,就会朝向秩序化和主流化的方向演变。
中国文人虽然醉心诗酒的意境,但又不能摆脱现实中处境的尴尬,因为酒神的媚俗一旦被识破,也就变得像人类其他弱点一样可怜。历代的文人中,多是苏轼所说的那样:“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他道出的是中国文人对价值形态的终极关怀。现实中文人的贫寒,使自身的存在价值发生严重的倾斜,人性的理想精神也变得更加脆弱,从而戳破了传统价值和审美理想所编织的神话。历史上,像陶潜的乞食,孟郊的号寒,贾岛的啼饥,以及杜甫的悲秋等等,都是作为不合理社会的缩影,凝结了古代文人“诗穷而后工”的深刻涵意。文人诗词中,除了少数作为官方文学颂德称圣的点缀之外,多数处境贫寒的文人创意,一如破壁残垣边的秋虫呢喃一般,哀音纵一再高扬,音力却越来越弱,沉重的生存忧患意识已经无法平衡安贫的心境。但是,诗词文学的流俗,又必然借助华艳与冶荡,为脂粉气和市井气平添几分高雅和妩媚,然而,这恰恰是文人的悲哀和社会的悲哀。
4
诗词艺术的语象化,通过切割现实的整形力量或毁形力量,将意识形态对原初的压抑,以及现世与来生的错忤,频频展现给世人,因而具有解构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功能。由于儒家人本思想对文人文学的浸润,诗词的审美理想常常倾向关注现世的伦常秩序,所以,政治清明时,文人便争相“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社会黑暗时,则援引“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这种写实主义,一般不含有对民众悲难处境和社会黑暗的追根溯源。它只是早期人本意识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心理认同,它最终寄托的希望是喻告统治者要依照儒家的仁道精神来体恤百姓,关注民生。文人诗词将一种秩序化的内在要求,用来伸张理想,取悦世俗,抚慰受难者的心灵,努力完成一个整体的结构方式,并始终标举自己的伦理精神。情与理,心与志的艺术化整合,将每个伦理主题都与传统的价值结构联系起来。文人诗词的道德逻辑与价值规范,作为儒家追求以道德转化政治的社会审美精神,既是表现性的,又是功能性的,所以需要特别强调道德的作用,以便迎合封建社会中一以贯之的伦理纲常传统。这有时是顺应的,有时又是异见的。当某些作品用表现审美理想的美神精神或酒神精神向社会统治的“天理”挑战时,虽然在政治上是质疑的,但道德上却是始终合致的。
在古代文人的整体意识中,托物比兴、隐逸孤怀的审美意境同省思人生、褒贬社会的道德主题常常是交缠在一起的。曹魏时,杨修就认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子,风雅无别耳。”(《答临淄侯笺》)魏晋六朝的艳辞之风,一味追求“嘲风弄月,流连光景”,似乎也包含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隋唐以来的诗歌复古运动,则排斥了这种“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隋书·李谔传》)的文学淫靡之势。由此可见,文人诗词的不同价值取向,显示了传统理性结构中审美观与道德观不断疏离又不断弥合的轨迹。象征道德审美的“雅颂”与追求存在价值的“媚俗”在诗词艺术中的浮沉,强化了儒家文人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徜徉的自恋情结。诗词艺术的哲学流变,不论是以道释儒,还是援儒入佛,其玄理与禅思的感发,只能沿着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识,来构建自己的文学殿堂。因此,由美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所嬗变的外化世界,作为儒释道的哲学整合,是将意识形态的美感或快感涵化为一种恒久的文学审美精神。这样,由于传统的审美理想有了内在的自足,因此确信世界与人的和谐是绝对的,用这种信念来看待现制与理想之间的紧张,其审美价值便会由此延伸到宗法关系、人伦秩序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绝对认同。无论文学艺术的形式怎样转换,都难以超越价值所规范的情感范畴,因而,文人诗词从总体看无法从传统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解脱出来。
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种传统主义的理性价值形态。它是以整体的伦理架构作为个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准则,个人价值只有充当这个总体架构的工具,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是一个包括人及其社会在内的庞大等级体系。在这个传统理性的框架内,文人诗词所表现的救世主义思想,尽管对现存社会的弊端和潜在危险,每每加以揭露与警告,但在整体上并不具备反主流规范的内在要求。这种以伦理的真善美作为基石的文学理念,要求文人们对客观外界的反映不要违背现存的审美规范。这种一元化的文学反映论,并不注重表现人性价值与世界本真的差距,人们由于个性被纳入模式而愈加趋于依赖和自我贫乏。因此,艺术表现主义的光环只是用来美化社会秩序。文人济世拯民的良方妙策,要么是借助美神精神的启迪,使人们在深沉古朴的现实秩序中达到平衡与安宁;要么是借助酒神精神的陶冶,使人们在清香淡雅的梦幻世界中得到解脱和净化。文人诗词的启蒙性和召唤性虽然颂扬了人的存在精神,却无法帮助人们脱离苦难。由于个人缺乏逃避媚俗的空间,文人自身也难以从美学困惑中实现自我救赎。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思想激励了人本主义的理性精神。这里,理性是作为与对神的敬畏和对权威的崇拜相对立的综合价值系统,它的道德内涵和审美内涵,是与自由、正义、人性的概念相联系的,并由此引申了民主精神、平等意识与人权要求。欧洲传统主义的贵族文学向个人主义文学的演变,是将个体生命的寓言转换为社会化的大众寓言,因而与民粹主义的精英文学不同。它虽然无法满足人类追求富裕与人道相统一的社会审美理想,却把谄媚权贵的人性扭曲与膜拜金钱的欲望膨胀等同起来,用象征人文主义价值的文学理性来加以消除。它虽然不能医治人类内心精神的贫乏和道德感的失落,但培育了选择与调节人类行为的能力,其人性价值与存在价值的确立,就不再依赖少数先知先觉的个人的呼吁,而是要社会普遍认同。因此,近代理性所标榜的文学精神,能启迪和召唤人的独立思考与理智判断的能力。这样,欧洲文学英杰所体现的美神意识和酒神精神,并不仅仅满足将一种乌托邦的理想用于现存秩序的批判,他们最终要建立人道的权威与秩序,并依此来作为人们追求最大幸福的道德基础。
作为儒家乐感文化的文人诗词,通过中国式的美神意识和酒神精神的阐发,反映了审美理想与人性价值在政治媚俗中的纠缠与迷离。中国文人文学一贯标榜关心民间疾苦,虽然具备了类似民粹主义的人本倾向,但作为由儒家文化所演变的精英主义文学气质,却无法超越传统所营造的理想世界,去寻觅迷失了的人性价值。文人诗词由于不能抵御政治媚俗,在强调教化的美感或乐感达成审美自足的功能时,其整体效果便是削弱了自身与大众的省思能力和批判精神。文人诗词在对来世的憧憬与对现世的朦胧认识中,自我标榜超凡脱俗的自恋意识又常常作为人本价值的归途,因而难以形成近代意义的文学精神。虽然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文人诗词可以透析出“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治”的儒家精神,但都是作为对“文化权力”的执迷,来发挥精英文学的亚文化功能。但文学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单纯的伦理功能的载体,因为文学一旦变成儒学的形象化而扮演了教父的角色,诗词艺术的基本精神也就枯竭了。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酒神精神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文化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诗经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人性论文; 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