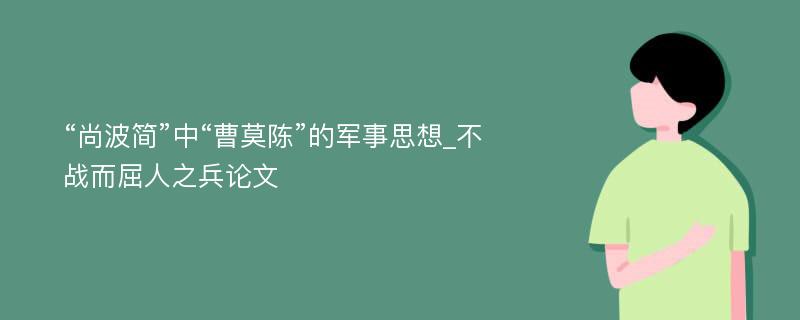
上博简《曹沫之陈》的军事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军事论文,上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简介: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225;E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2-0021-12 《曹沫之陈》是上博简第4册中最长也最引人注目的一篇,①记载的是春秋前期鲁庄公与曹沫(即曹刿)的问对。②目前学界对《曹沫之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竹简的编联和简字的释读及其性质的讨论上。虽然很多学者多以其为佚失已久的古兵书,③但对其军事思想却没有专门讨论过。《曹沫之陈》成书早于《孙子》《吴子》等经典兵书,其军事思想既朴素又弥足珍贵,本文试对其军事思想作深入探讨和研究,以期还原春秋前期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新面貌”,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提供新材料和新视角。 一、“有克政而亡克阵”——政治对战争的制约 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④史官往往将目光的焦点集中在政治与战争这两个方面。《曹沫之陈》简文对于政治与战争的认识与其他典籍中所载正统史家的认识是一致的,皆是强调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对于这一点,《曹沫之陈》的作者凝练为“有克政而亡克阵”。 《曹沫之陈》简文载鲁庄公接受曹沫“修政而善于民”的建议后,他“不昼寝,不饮酒,不听乐。居不重席,食不二味”(简10-11),这完全是明君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典型作为。一年以后,庄公再次垂询曹沫,问:“吾欲与齐战,问陈(阵)奚如?守边城奚如?”(简13)⑤因庄公之语有“问陈(阵)”的字样,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本篇篇题“曹沫之陈”,从而将本竹书视为论兵之作。但是简文所载曹沫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来回答庄公,他不仅没有论述相应的“阵法”“兵法”,而是得出了“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阵”的结论。这一结论引人深思。为了方便探讨,我们将相关简文摘引如下: 臣闻之:有固谋而亡固城(简13),有克政而亡克阵。三代之阵皆存,或以克,或以亡。(简14) 在这一段简文里,曹沫引用“臣闻之”阐述了自己对于战争与政治的认识。这种说明问题的方式与《国语》是一样的,⑥所反映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曹沫在论述中提及的“三代之阵”,是指夏商周三代战争理念。本段简文中“克”训为“胜”,“克政”即足以胜人之政,“克阵”即足以胜人之阵。在曹沫看来,固守不破的城池(“固城”)不如固定的谋略(“固谋”),一定取胜的布阵打仗的办法(“克阵”)不如一定取胜的为政之法(“克政”)。“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阵”,可谓精确到位,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曹沫之陈》作者治国理念的高度概括。在对“政”(政治)与“阵”(战争)的关系问题上看到了根本问题所在,那就是政治对于战争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 在这一段简文中,曹沫先以“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阵”回答庄公“问阵”与“守边城”的问题,随后指出小邦处在大邦之间据守边境的谋略。点明“坚甲利兵”固然重要,但是“必有战心以守”才是上策。转而提出“三和(为和于邦、为和于豫、为和于阵)”的重要性,庄公进而询问“为和于邦”“为和于豫”“为和于阵”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属于政治教化的范畴。至此,《曹沫之陈》作者的观点已经非常清楚,关于政治与战争,他更看重的是政治,并尽量引导国君回到修政这个主题上来。 《曹沫之陈》简文所载关于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的讨论,是在曹沫与鲁庄公对话中渐次展开的。在讨论“三教”的问题之后,鲁庄公询问曹沫关于各种“出师之忌”“复战之道”,曹沫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又成功地将庄公的关注点引回到政治问题上。曹沫提出“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从而使庄公进一步思考“为亲”“为和”“为义”的问题。曹沫遂适时地提出“先王之道”,庄公进而询问三代之得失,曹沫以“古亦有大道焉,必恭俭以得之,而骄泰以失之”作答。意思是说,古代也有治国理政的规律存在,而这些道理必定要靠恭敬简朴的态度才能够得到,若采取骄奢傲慢的态度就会失去获得这些道理的机会。因此可以说,《曹沫之陈》的作者关心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立足于政治讨论战争,希望君主修明政治,和睦亲族,教化民众,融德政于兵事中,这也是春秋时期受传统礼乐文化影响的政治家的共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曹沫在回答鲁庄公“问阵”之时,曾说“三代之陈皆存,或以克,或以亡”(简14)。虽然“三代之陈皆存”这种说法让人振奋,但在曹沫看来,三代之阵并不是作战之“正道”,有的用它取得了胜利,有的用它却灭亡了自己国家,所以真正应该关注的还是三代之政。而关于三代之政,禹、汤、桀、纣时代就是“正(恭俭以得之)”“反(骄泰以失之)”两方面的样板。简文的主体思想更加明了。它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曹沫将“教民”上升到“先王之至道”上来,更是彰显了《曹沫之陈》的思想特色。 在战争中,比武力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的政治。春秋中期晋楚鄢陵之战前夕,楚贤臣申叔时指出:“德、刑、详(祥)、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⑦申叔时将德行(“德”)、刑法(“刑”)、敬顺(“祥”)、道义(“义”)等看做战争的根本和战争胜利的原因。著名的齐、楚召陵之盟前夕,齐桓公向楚使臣屈完炫耀兵力,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当即驳斥道:“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⑧在屈完看来,诸侯国之间应当以“德”相待,而不是武力威胁,这样才会令人心服口服。 中国古代的兵家对于政治与战争胜负的紧密关系,看的也很清楚。所谓“战胜于外,福生于内,胜福相应,犹合符节”,⑨他们已经认识到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统治者政治上的成功,所以孙子等军事权谋家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策略,都认识到国富兵强的重要性,都重视对将领谋略的运用、智慧的开发,将治军与治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到了战国时期,先秦的兵家大多吸收法家的思想,支持国家的改革,希望通过变法改革,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而且还将法治的观念贯穿到治军中,依法治军,严明军纪。“车不发轫,甲不出橐,而威服天下”,⑩这虽然是他们的美好理想,但反映出他们对政治与战争的取舍态度明显不同。 古代兵家十分关注战略战术。他们承认政治是战争的首要因素,但同时认为战争是决不能放弃的手段。他们对战争的取胜之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司马法·严位》认为,“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11)再如《孙子兵法·计》篇指出,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在出兵之前要认真核算敌我双方的情况,“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义、天时、地利、将领、法规,这5项内容,将帅一定要了然于胸,必有胜算的可能,然后才能出兵。在5项当中,将“道”列为第一位,“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12)即民众与国君同心同德,国君的行为符合道义的要求,这是对一国政治总的要求。将帅在出兵前要反复的思考:“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13)通过这些“知胜负矣”。《尉缭子·兵谈》说:“兵胜于朝廷,胜于丧纪,胜于土功,胜于市井。橐甲而胜,主胜也;阵而胜,将胜也;战(而)胜,臣胜也。”(14)孙子将“主孰有道”列为“七计”之首,又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用兵的上策;《尉缭子》认为“兵胜于朝廷”,他们如此强调治道,都是认识到了政治对军事的重要而深层的影响。但《孙子》《尉缭子》等关注的是战争,最终的落脚点在战争胜负之上,而《曹沫之陈》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战争,而是政治,最终的落脚点在国君的修德修政之上。所以说,《曹沫之陈》是政治家言兵,而非兵家言战。《曹沫之陈》简文虽然涉及“论兵”的内容较多,但是其“论兵”是为“论政”服务的。他倡导德政、重视民本,处处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认识到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 二、“夫阵者,三教之末”——政治教化是战争胜利的前提 《曹沫之陈》的作者在强调政治对战争制约作用的同时,又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思想,即政治教化是战争胜利的前提。曹沫指出鲁国作为小邦,处在大邦之间据守边境的谋略,提出“三和(为和于邦、为和于豫、为和于阵)”的重要性,并得出“夫阵者,三教之末”的结论,颇为耐人寻味。我们先来讨论曹沫所讲的“三教”的意蕴。相关简文如下: 臣之闻之:不和(简18)于邦,不可以出豫。不和于豫,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战。是故夫阵者,三教之(简19)末。君必不已,则由其本虖?(简20) 关于“三教”的理解,学者意见不一。李零先生的原释文认为:“三教”即“和于邦”(国家内部和谐)、“和于豫”(率军出发时军队内部和谐)、“和于阵”(布阵时军队和谐)之教,并指出“三教”为本,阵法为末。陈剑先生认为简文“三教”可仿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五教法》之五教而称为“处邦之教”“处豫(舍)之教”“处阵之教”。(15)高佑仁先生指出简文已经明言“阵”为“三教”之“末”,则“三教”不可能是“本”,因为本、末乃两个不同的概念,若以“三教”为本,而“末”又为“本”之一,这种讲法说不通。他认为“和于邦”“和于豫”“和于阵”等三者乃“三教”的内涵,而“为和于邦”才是三教之“本”,“为和于阵”则是三教之“末”。(16) 其实,以“三教”为本,阵法为末,其中“阵法为末”并非是说“三教”中的“和于阵”,而是指具体的阵法、作战方法。当然,从下文看,曹沫劝谏庄公“君必不已,则由其本虖?”庄公紧接着问:“为和于邦如之何?”可知“为和于邦”乃是三教之“本”,从而推出“为和于阵”应该是三教之“末”。(17)在《曹沫之陈》的作者看来,“和于邦”“和于豫”“和于阵”三教是层层向前推进的关系,而“和于邦”才是确保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国君应该抓根本,立足于修政修德。 简文所谓“夫阵者,三教之末”,既是对于战争的恰当定位,也是对政治教化的高度肯定,体现了《曹沫之陈》作者的“仁本”思想。“教”字在《曹沫之陈》简文中共出现有四次:一是“三教(为和于邦、为和于豫、为和于阵)”;二是庄公所说的“既成教”;三是“用都教于邦于民”;四是“鬼神惚恍,非所以教民”。其中“既成教”,陈剑先生认为“教”皆为正式作战之前之“教”。(18)高佑仁先生认为“成教”应该读作“承教”,为接受教诲、教令之义。(19)联系到此简的上下文内容,此处的“既成教”意思是指将帅已经完成了对于下级将领的告诫教诲,下面该正式出师了。所以此处的“成教”是指出师前的训诫,而不是广义上的政治教化。其余三处的“教”皆为政治教化万民之义。不仅如此,《曹沫之陈》简文中还有大量的论政治教化的内容,如“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可以说,《曹沫之陈》“教”的含义很广泛,其重点却不在于军事训练,而在于政治教化。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兵家不同。中国古代的兵家也重视对士卒的教化,如《吴子》提倡“用兵之法,教戒为先”,(20)主张对士卒“教之以礼,励之以义”,(21)但这种“教”主要是指培养士卒的荣辱观念,激发士卒的斗志,加强平时的军事训练。“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22)采用这种教战方法提高士卒的战斗力。《尉缭子》亦有类似的训练方法:“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会之于三军。”(23)《六韬》亦是如此:“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24)中国古代的兵家重视对士卒的教化是为了“以治为胜”,(25)而《曹沫之陈》推崇的教化不仅是指对士卒的教化,更多的是指对广大民众的教化,对于战争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仁义之战阶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曹沫之陈》的作者指出“亲率胜。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简33),这本来是强调将帅在统率军队时要亲近士卒,教化士卒,但是在庄公垂问“为亲如何”“为和如何”“为义如何”之时,曹沫的回答明显又回归到了政治教化方面。如,曹沫回答“为亲如何”时说:“君毋惮自劳,以观上下之情伪。匹夫寡妇之狱讼,君必身听之。有知不足,亡所不中,则民亲之。”(简34-35)回答“为和如何”时说:“毋嬖于便嬖,毋长于父兄。赏均听中,则民和之。”(简35-36)回答“为义如何”时说:“申功上贤,能治百人,使长百人;能治三军,使帅。”(简36)这些都是《曹沫之陈》的作者对于国君为政的要求,与《国语·鲁语》上的曹刿所论相似。《曹沫之陈》的作者在论述战争问题时,都能回归到以政治为本源的探讨上面来,他寄希望于政治,关注的始终是政治教化。 在探讨作战之道时,重视政治教化的功能,这是《曹沫之陈》的作者非常明显的思想倾向,也是其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不仅如此,作者在“教”与“战”中还极其重视“和”的理念的运用,在三教中强调一个“和”字。在解释“善守者奚如”时,提出“其食足以食之,其兵足以利之,其城固足以扞之(26),上下和且辑”(简15-16)。在论述“毋冒以陷,必过前功”时,指出“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简33)“和”的理念可谓是贯穿简文始终。“和于邦”,这是出兵的前提;“和于豫”,这是布阵的前提;“和于阵”,这是开战的前提;“上下和且辑”,这是弱小国家保全自己的法宝。“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这本来是将帅统率军队的原则,但曹沫在具体阐释“为亲”“为和”“为义”的内容时将其扩大成对广大民众的政治教化。《曹沫之陈》的作者将“和”的理念扩展到君臣之间、君民之间、官兵之间、士卒之间,认为这种“和”不仅是国家繁荣兴盛的标志,还是在战争中能够获胜的前提。这也是春秋时期比较常见的一种认识。如,《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楚、郧蒲骚之役前,楚大夫斗廉满怀信心地说:“师克在和,不在众。”也就是说军队取胜不在于军队的数量,而在于军队是否团结一致,已经认识到军队团结与否和军队战斗力的联系。当然,春秋时期“用众”的思想也很突出,如,《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大夫子重云:“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左传》成公二年亦载君子语:“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师克在和”与“用众”并不矛盾,只是不同的战略,“用众”虽然强调以军队数量取胜,但也需“和”,“用众”的根本在于“惠恤其民”,这样才能赢得民心,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左传》“用众”的思想也是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在战争中的运用,《司马法》甚至说“古者戍兵三年不典,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27) 政治教化的目的在于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和谐一致。《曹沫之陈》篇谓“不和于邦,不可以出豫;不和于豫,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战”(简18-19),其着眼点都落实在“和”。这一观念对于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不仅儒家强调“和为贵”,(28)而且后来许多军事家也都注目于此。例如,《吴子》就相当重视“和”的理念在治国治军中的运用。其首篇《图国》篇载吴起初见魏文侯,劝谏魏文侯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其中提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与《曹沫之陈》简文的“修政而善于民”意思是一样的,而其“四不和”与《曹沫之陈》简文“三不和”如出一辙。二者突出的皆是一个“和”字,强调的都是修德修政的重要性。有学者据此指出今本《吴子》是有着十分可靠的来源的,(29)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入魏前,“尝学于曾子(即曾申,曾参之子)”,亦曾“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国的兵学传统可能对其有一定的影响。《曹沫之陈》在战国时期还曾流传到楚国,它的军事思想对于作为改革家、军事家的吴起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 三、“战有显道,勿兵以克”——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自古以来备受人们赞赏,被视为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精髓,对后世的战略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早在《孙子兵法》出现之前,《曹沫之陈》简文就已有此战略思想的萌芽,即“战有显道,勿兵以克”理念。 《曹沫之陈》简文载曹沫在向鲁庄公解释“夫阵者,三教之末”的观点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战有显道,勿兵以克”,颇值得我们深入剖析。相关简文如下: 庄公曰:“勿兵以克奚如?”答曰:“人之兵(简38)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人使士,我使夫大夫。人使夫大夫,我使将军。人(简39)使将军,我君身进。此战之显道。”(简40) “勿兵以克”,原释文以为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孟蓬生先生从之,训“勿”为“无”,认为“无兵以克”,是说没有(不依靠)军队而取得胜利,亦即不战而屈人之兵。(30)高佑仁先生认为“勿”有表示禁止或劝阻之义,义同于“别”“莫”。简文“勿兵以克”犹言“莫以士兵克敌”之义。(31)陈斯鹏先生以为“勿兵以克”于义难通,本简中的“勿”字与传抄古文中的“刀”旁相似,故字似可释“刀”。(32)然而,在楚简文字中,“刀”与“勿”本不易相混,而且将“刀兵以克”作为“战之显道”的思想与《曹沫之陈》的军事思想整体上不符。所以笔者认为,高佑仁先生对“勿”的本义的理解应该较为妥当,“勿”的本义就是“不要……”,但是简文此处的“兵”不当指士兵,也不当指兵器,而应当指战斗、战争。简文意指如果执行了以上的办法(即“人之兵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那么就是没有开始战斗,即已稳操胜券。 “勿兵以克”意即不战而胜,这固然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相一致,但其中也有些许区别,值得我们仔细体味。“不战而屈人之兵”见于《孙子·谋攻》篇,原文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百战百胜,算不上好中最好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得上好中最好的。《尉缭子·兵谈》篇亦载:“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并且指出“兵胜于朝廷,胜于丧纪,胜于土功,胜于市井。”意思是说军事上的胜利实际取决于朝廷的政治改革,取决于百姓的安定生活,取决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取决于贸易的繁荣兴旺。孙子将“主孰有道”列为“七计”之首,又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用兵的上策;《尉缭子》认为“兵胜于朝廷”,都是认识到了政治对军事的重要而深层的影响。这些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未开战之前,要在国内进行充分的准备,正如《管子·七法》篇所说:“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这是计定于庙堂之上,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做法。然而《曹沫之陈》的“勿兵以克”则是战前的具体准备,主要包括两点内容:一是要做到坚甲利兵,武器精良;二是要保证领兵将帅的权威,一定要胜过对应的敌军将领。这些认识显然没有后来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全面翔实,但却显示了其战略思想的素朴之貌。这也正是因为这一思想所出时代较早的缘故。 曹沫主张“勿兵以克”,前一句“人之兵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这是强调兵器、甲胄要优于敌方。军备器械精良,这本是打胜仗的硬性条件,属于军事常识。但是后一句“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这是强调统帅的出身,要求所任命与派遣的将帅的身份地位要明显高于对方一个级别。将帅,特别是主帅,他的行为直接关系着战争的结局,所谓“凡战,三军一人胜”,(33)就是强调主帅在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曹沫之陈》将这种以统帅的身份地位压人、胜人的策略作为“战之显道”,则是非常罕见的。虽然一直到战国时期,统帅的尊卑对战争依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却很少再强调君主的亲力亲为。《曹沫之陈》所反映的正是春秋时期的情况。而且“人使将军,我君身进”,它的意蕴也并非要求国君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而是强调君主自身的权威。在曹沫看来,国君身份尊贵,其作为统帅的影响力是无人能及的,所以国君最好能作为统帅直接将兵。“三军出,君自率”,君主亲自率军出战,才能保证军队的和谐。“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此战之显道”。这种逐步向前推进的逻辑关系,强调了国君独一无二的影响,是对国君权威的充分肯定。春秋时人谓:“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34)国君统“神”与“民”两者,其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于此可见。《国语·鲁语》上篇载鲁大夫里革对鲁成公说:“夫君人者,其威大矣。”晋大夫阳毕亦谓:“图在明训,明训在威权,威权在君。”阳毕认为“威权在君”,国君要威、德并用,则“民心皆可蓄”。(35)这些重视国君的“威望”“威权”的思想与《曹沫之陈》是一致的。《曹沫之陈》简文格外重视国君尊贵的身份以及其作为统帅的影响力,这是和春秋前期鲁国的国情相符合的。春秋前期,鲁君的权力较大,鲁国公室受世家大族的牵制不明显。此外,鲁秉周礼,其时鲁国的政治相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国君贵重的身份及无与伦比的地位,不仅为本国人尊崇,也为其他国家的人所尊崇。例如《左传》载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晋军新军的将领卻至在战场上见到楚王,便不顾战场之拼杀搏斗“免胄而趋风”,意即跳下战车,脱去头盔而快步疾走,以此对楚王表示尊敬。并且“三肃使者而退”,对楚使恭敬地拜谢三次后退走。与此同时,晋军下军的将领韩厥也以“不可以再辱国君”为由放弃了对郑成公的追击。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贤大夫子产甚至以“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为“国之大节”,(36)可见国君的威权之重,作为统帅三军的最佳人选当然就是国君了。所以《曹沫之陈》的作者将“人使夫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作为“战之显道,勿兵以克”的重要内容。 四、“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重视“贵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时期行师论兵,大都认识到了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了战争与民众的密切联系。《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正是春秋时期关于战争的主流认识。由于春秋时期宗族兵依然是军队的骨干、战争的主力,所以《曹沫之陈》的作者重视君主的权威之外,还格外强调宗法贵族在统领军队方面的天生的优越性,并且将君主与贵族视为一体,这一思想贯穿于曹沫与庄公问对的始终,突出的表现是曹沫回答庄公“为和于豫”的做法时,两处提到“贵人”,一处提到“公孙公子”,相关简文如下: 三军出,君自率(简22),必约邦之贵人及邦之奇士,御卒使兵,毋复前(简29)常。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后则见亡,进(简24下)必有二将军。无将军必有数嬖大夫,无嬖大夫必有数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凡有司率长,(简25)……期会之不难,所以为和于豫。(简23下)(37) 这段简文强调了国君亲为统帅以及贵族统军的重要性。三军出征,国君亲自统率军队一定要约请国内的“贵人”以及“邦之奇士”,让他们指挥士卒。所谓“奇士”盖指有奇特谋略或奇特技艺之人。相传秦孝公曾经下令国中,招募人才,谓“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周初重臣吕尚是一位“多兵权与奇计”的杰出人物。秦末陈平曾经批评项羽“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38)可见陈平把自己看作“奇士”。对于这些出谋划策的“奇士”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曾总结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39)《曹沫之陈》所提到的“奇士”,当即这类人才。 除了“奇士”之外,《曹沫之陈》似乎更为重视“贵人”。认为凡是“贵人”位列前行,则可奋士气而取胜。如果他们居后,则容易溃亡。并且进一步说,军队前进一定要有“二将军”指挥,没有将军的时候,一定要有“数嬖大夫”来指挥,没有嬖大夫一定要有“大官之师”“公孙公子”来指挥。所有的职官都要由出身高贵的官长率领,军队按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也就没有什么难做到的了,这样就能做到“为和于豫”。在这里,“豫”,读若“预”,是一种预备状态,此时军队已经出发但是尚未布阵。我们可以看到,“为和于豫”最关键的是国君与“贵人”的统帅与凝聚作用。那么应该怎么理解“贵人”呢? “贵人”,原解释为身份高的人,笔者认为并不是很准确。商和西周时期,贵族与民众俱可称“人”,唯身份低贱者称“小人”,但并没有相对应的“贵人”之称。春秋时期方有“贵人”之称,至战国时“贵人”的称呼多了起来。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出身于贵族之人称为“贵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象。先秦典籍中的“贵人”是指身份高贵之人,亦往往指与国君有血亲关系的贵臣。如《韩非子·扬权》:“毋贵人而逼焉”,“贵人”,王先慎注为“贵臣”。(40)《吕氏春秋·贵卒》:“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贵人”,高诱注:“贵人,贵臣也。”(41)《礼记·内则》:“贵人则为衣服。”孙希旦集解:“贵人,卿大夫也。”(42)再联系到春秋时期鲁国的社会结构,其贵卿皆是出自公族,所以笔者认为《曹沫之陈》简文中的“贵人”应该是指与国君有血亲关系的贵臣。强调“贵人”的作用,固然是适应周代宗法制社会结构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有强调军队指挥员权威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增强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使军队上下行动统一,听从指挥,从而保证战争取得胜利。 关于“为和于豫”的做法,曹沫先总说“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后则见亡”,然后解释说“进必有二将军。无将军必有数嬖大夫,无嬖大夫必有数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将军”“嬖大夫”“大官之师”与“公孙公子”,这是层层向下的关系,其中“公孙公子”似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依周代礼制,“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43)公子、公孙是公族中地位最为显赫者。所以简文此处的意蕴可能是指国君出征,所任命的将领皆为出身高贵的人,他们以贵人的身份兼有官职,或者为“将军”,或者为“嬖大夫”“大官之师”。而“公孙公子”则仅有高贵的出身,没有具体的官职。即使没有官职,但他们“公孙公子”的身份具有天然的权威,可以凝聚军心,他们亲自带兵就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不仅如此,简文载曹沫在解释“为和于阵”时,再次提到了“公孙公子”的重要性,相关简文如下: 车间容伍,伍间容兵,贵(简24上)位、厚食,思为前行。三行之后,茍见端兵,什(简30)伍之间必有公孙公子,是谓军纪(简26)。(44) 以战车进攻,疏而不合,就会有空间为敌军所乘,所以“车间容伍,伍间容兵”,编组严密整齐。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车兵为辅,而且骑兵大量出现,《吴子·治兵》篇中论及驯养军马的方法,并强调驯养好战马就能“横行天下”,这说明骑兵已经成为重要的作战兵种。而《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依然是春秋时期的作战情况,车战依然是主要的作战方式。进攻的方式首先要求有整齐的编制,上下之位严整,错落有致,步调一致,这很符合古军礼的要求。“车间容伍,伍间容兵”,这是布阵的编组要求,这种编组排列能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作用。这与春秋前期郑国的鱼丽之阵异曲同工:“先偏后伍,伍承弥缝”,(45)兵车一对分为二偏,每偏为二十五乘车,以步卒五人为伍,在车后,弥补偏间的缝隙。《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车阵战,这也正是春秋时期典型的作战方式。这一点是《曹沫之陈》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有力内证之一。 简文指出“什伍之间必有公孙公子,是谓军纪”,如此强调“公孙公子”在军纪方面的重要性,这是后世兵书所没有的。伍、什是军队最小的编制单位,相当于一个战斗小组,公孙公子遍布什伍之间,这就是军纪。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军纪”明显不同。因此疑简文此处“纪”字,非指“纪律”,而是作“纲纪”“纲要”“总要”讲。(46)简文以公孙、公子为军之纲纪,强调以贵族血统维系军心的重要性。此外,《吴子·料敌》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军命”即军之命脉,与简文此处的“军纪”意思是一样的。《吴子》以“虎贲之士”为三军的命脉,《曹沫之陈》则以“公孙公子”为三军的纲纪,所反映的时代观念明显不同,亦表明《曹沫之陈》成书之早,反映其社会结构仍然是重视血缘关系的典型的宗法社会。春秋时期,贵族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这在《左传》中屡见不鲜。如,《左传》载,庄公十年,公子偃与鲁庄公联手取得了鲁宋乘丘之役的胜利。成公二年,鲁、卫等诸侯国从晋伐齐,而楚令尹子重起师救齐,“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蔡景公与许灵公两君都没有成年,但要担任车左、车右,所以勉强为他俩行加冠礼。在这场战役中,楚国看重的是蔡景公与许灵公两君的身份地位,而非其自身的作战能力。再如,昭公二十三年,吴楚争夺州来,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分析当时的局势说:“(楚)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楚帅的地位低,没有大的威信,这就注定了楚军是一定要打败仗的。 另外,我们要看到,当时“贵人”“公孙公子”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还因为他们所率领的是以家族、宗族为单位的军队,这也体现了春秋时期军队的特色。到了战国时期,军队兵员大量来自征兵,少数常备的精锐部队则来自募兵,《吴子·图国》篇提出“简募良材”,并主张“选而别之,爱而贵之”,视其为军中之精锐。正是说明了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兵役制度的不同之处。 《曹沫之陈》简文两处出现“贵人”,两处出现“公孙公子”,是很引人注目的。强调带兵打仗时“贵人”“公孙公子”的重要性,并将“公孙公子”视为军之纲纪、命脉,这是《曹沫之陈》的特色之一。可以说,《曹沫之陈》与《孙子》等皆强调“以气势取胜”,以《孙子》为首的兵书更多的是强调以“势”胜人,而这种“势”是指战术中的“奇正”之术,但是《曹沫之陈》强调的是具有高贵血统地位的“贵人”的气势。就任用将领方面,《曹沫之陈》强调“将”的高贵血统,注意的是“贵人”“公孙公子”的作用。这是春秋中前期才有的理念。后世的兵书如《吴孙子》《齐孙子》《吴子》等强调的是选将,重视所选将领的个人素质。成书于春秋后期的《吴孙子》对于“将”的要求是具有“智、信、仁、勇、严”(47)等素质,而非具有贵族血统。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齐孙子》亦是如此。其《将义》篇云:“将者不可以不义”,“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将者不可以无德”,“将者不可以不信”,“将者不可以不智胜”,强调将领必须要有义、仁、德、信、智。《六韬·选将》以“八征”作为选拔将领的标准。《吴子》也尤其重视选拔“良将”,但它所说的“良将”和是否出身贵族毫无关系,而是指将领的威严、品德、仁爱、胆略,只有具备这几种素质的将领才足以统帅军队。可以说,后世兵书论选拔将领,都注重的是将领的才能,无所谓尊卑,反而是最忌讳“贵人”的特权。《曹沫之陈》格外强调贵族、血缘的重要性。这一点与《吴孙子》《齐孙子》《吴子》等不同,表明它们成书时的社会结构不同,也表明《曹沫之陈》问世的年代较早。 《曹沫之陈》简文强调国君的权威与重视权贵人物的影响力是一致的,这是《曹沫之陈》的特色之一。《左传》所载庄公十年曹刿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主动觐见庄公,并运用“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军事思想,使长勺之战成为中国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曹刿所说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似乎与《曹沫之陈》中的曹沫重视“贵人”的思想不一样。其实不然,曹刿(曹沫)所生活的春秋前期,是新旧两种思想交替的时代,出身下层的精英人物不断涌现,但是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的依然还是出身高贵的贵卿重臣,典籍所载的曹刿虽然认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主动要求参战,但他是作为庄公的车右参战的,在长勺之战中,统率军队的是鲁庄公。所以传世典籍中的记载与简文的记载并不矛盾,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总体上讲,《曹沫之陈》所反映的是春秋时期政治家言“兵”,而非兵家言“战”,其对政治与战争的论述,已经涉及中国古代军事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后世所重视的一些军事政治学的理论,如政治决定军事,军事是政治的手段,政治贯穿于军事的全过程等等,在《曹沫之陈》简文里都有质朴的表述。《曹沫之陈》早于《孙子》《尉缭子》等经典兵书而提出了内涵不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这是该书独特而宝贵之处。《曹沫之陈》还格外重视宗法贵族的领军特权,其战略指导思想依然是遵循礼法的“正规作战”的方法谋略,并没有形成“兵以诈立”的思想。李零先生曾经指出:“宋襄公以后,中国的兵法,以《孙子兵法》为代表,都是讲‘兵不厌诈’。”(48)虽然,宋襄公以前的兵法并非全都不讲诈术,但是宋楚泓之战之后,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这种符合古军礼的战法从此就被彻底摒弃了。而《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宋襄公以前中国古老的“兵法”思想。 注释: ①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图版见其书第91-156页,释文考释见其书第241-285页。此篇简文的整理者是李零先生。本文所引《曹沫之陈》简文皆出自此书。 ②曹沫(或者曹刿)是春秋前期鲁庄公的重要谋臣。曹沫与曹刿虽然是一人异名,但典籍中所称曹刿与曹沫还是有区别的。曹沫是以“执匕首劫齐桓公”而出名的刺客,而曹刿是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争理论出名的军事家。李零先生说“曹沫(曹刿)既当过刺客,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家。”(《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读书》2004年第9期。)笔者认为典籍记载的差异是曹沫(曹刿)“形象”与“史实”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转变的结果。参见拙作《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以“曹刿—曹沫”为考察对象》(《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③见李零先生《曹沫之陈》释文说明,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第241页;田旭东:《失传已久的鲁兵书——〈曹沫之陈〉》,《华学》第8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55-160页。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61页。 ⑤春秋前期的鲁国虽然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能够与齐国相抗衡,但是在军事上一般以防御为主,典型的例子就是《左传》记载的鲁庄公之父鲁桓公对“疆吏”的一段话。桓公十七年,齐人入侵鲁国的疆域,疆吏来告。鲁桓公说:“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疆埸之事,慎守其一”,意思是说边境上的事,原则上只要守住自己这一边的边境就可以了。春秋时期,诸侯纷争不已,齐强鲁弱的局面逐渐形成,鲁国一贯的战略就是守土的防御战略。当然,在守住疆土的前提下,也要“备其不虞”,要时刻警惕,积极准备。一旦疆土受侵,就要“事至而战”,坚决打击来犯之敌。鲁桓公的积极防御之策不失为春秋时期中小国家保全自身的正确策略。 ⑥《曹沫之陈》全篇有9处“臣闻之”,可以说曹沫的重要的言论都是以“臣闻之”的形式阐发的。而《国语》所载当时的卿大夫也是经常以“臣闻之”的形式阐发重要观点,据统计,《国语》共有23处“臣闻之”,其中《鲁语》有3处。 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80-881页。 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92-293页。 ⑨徐勇:《尉缭子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⑩徐勇:《尉缭子浅说》,第53页。 (11)田旭东:《司马法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12)此句简本作“民弗诡也”,十一家本作“而不畏危”,参见《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页。 (13)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8页。 (14)徐勇:《尉缭子浅说》,第53页。 (15)陈剑:《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稿)》,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1.htm,2005年2月12日。 (16)高佑仁:《〈曹沫之陈〉“君必不已则由其本乎”释读》,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3.htm,2005年9月19日。 (17)关于简文“三教”,除了就简文本身来讨论以外,似亦可从简文之外来考虑。春秋时期的卓识之士往往从夏商周三代治术之别来议论三代政治得失,如《礼记·表记》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汉代纬书《元命包》由此而发挥,说道:“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变。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荡,故救荡莫若忠。如此循环,周则复始,穷则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卷54,《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42页。)这里所说的“三教”实指夏代的“忠”之教、商代的“敬”之教、周代的“文”之教。简文“阵”,意犹战争。战争是忠、敬、文三教之后不能奏效时方采取的手段,故简文称其“三教之末”。古代文献中屡有“五教”之说,指父子兄弟间的伦理关系,简文此处所说的“三教”与其有较大距离。三教之说不见于春秋时代的文献,《元命包》的三教说尚不知其来源,故附记于此,以俟来日。 (18)陈剑:《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稿)》,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1.htm,2005年2月12日。 (19)高佑仁:《〈曹沫之阵〉校读九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gaoyouren004.htm,2005年11月13日。 (20)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80页。 (21)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第58页。 (22)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第80页。 (23)徐勇:《尉缭子浅说》,第138页。 (24)孔德骐:《六韬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25)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第79页。 (26)简文“其食足以食之,其兵足以利之,其城固足以扞之”,与《论语·颜渊》篇所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内容很相似。《曹沫之陈》的简文是回答“善守者悉如”的问题,《论语·颜渊》的内容是回答“问政”的问题,突出的是“民信”的重要性,《曹沫之陈》没有这一点,只是指出守城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下一句“上下和且辑”才是强调上下齐心,团结一致。 (27)田旭东:《司马法浅说》,第48页。 (28)《论语·学而》,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页。 (29)单育辰:《从战国简〈曹沫之陈〉再谈今本〈吴子〉〈慎子〉的真伪》,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09,2006年8月30日。 (30)孟蓬生:《上博竹书(四)间诂》,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2005/mengpengsheng001.htm,2005年2月15日。 (31)高佑仁:《〈曹沫之阵〉校读九则》,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2005/gaoyouren004.htm,2005年11月13日。 (32)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 (33)田旭东:《司马法浅说》,第77页。 (3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16页。 (35)《国语·晋语八》,《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48页。 (3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212页。 (37)相关简的编联参见拙作《上博简〈曹沫之陈〉疏证与研究》,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82-84页。 (38)分别见于《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02、1478、2054页。 (39)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3页。 (4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9页。 (4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476页。 (42)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3页。 (4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61页。 (44)相关简的编联参见拙作《上博简〈曹沫之陈〉疏证与研究》,第76页。 (4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5页。 (46)“纪”做纲纪、纲领、总要讲,古籍中常见,如《老子》第14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文子·微明》:“故随时而不成,无更其刑,顺时而不成,无更其理,时将复起,是谓道纪。” (48)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0页。 (49)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