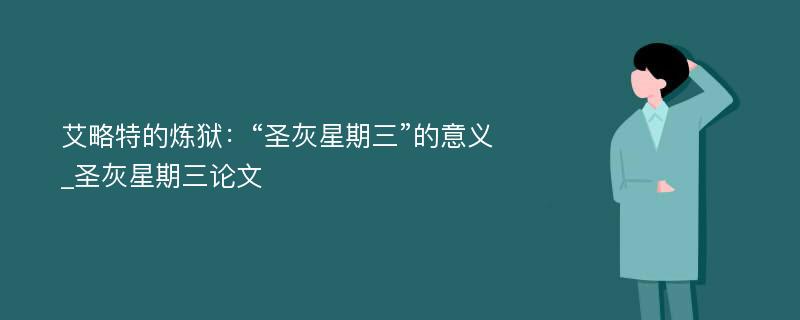
T.S.艾略特的炼狱——《圣灰星期三》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略特论文,炼狱论文,意义论文,星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洛德·布罗姆(Harold Bloom)在论及《圣灰星期三》时说,这首诗是“有关天主教的悖论的一个简单的极其机械的目录,作为念珠游戏它是可以的,但作为想象的意义它就不行了”①。布罗姆的批评是非常尖刻、非常挑剔的,但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说,他与艾略特的关系可能属于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他对艾略特的攻击可以说是“儿子”对“父亲”的叛逆,这与艾略特在《圣林》中反对浪漫主义的实质是相同的②。《圣灰星期三》在艾略特诗歌创作的历程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它是继《荒原》和《空心人》之后的又一大作,它标志着艾略特后期诗歌的开始,它以一种新的声音和新的姿态为艾略特后期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为《四个四重奏》埋下了伏笔。可惜的是在我国,它仍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甚至没有一篇有关这首诗的论文。本文试将对《圣灰星期三》作一个全面的分析,意图不在于填补学术界的空白,而在于刺激学术界的兴趣。
一、“衰老的老鹰”
谈论《圣灰星期三》,大概不能不提及宗教节日“四旬斋”,因为“圣灰星期三”是“四旬斋”的第一天。顾名思义,“四旬斋”就是四十天斋戒,它在“复活节”前,为的是纪念耶稣在野外接受考验、最后战胜魔鬼撒旦。这段时间是基督徒忏悔和斋戒的日子,而以“圣灰星期三”命名的诗歌自然也与诱惑、忏悔,并力求更彻底地转向上帝等主题有关。诗歌一开始,艾略特就以一种追悔莫及的姿态出现,把自己看作一个罪人,一个尝尽人间酸甜苦辣而又对一切都感到绝望的人。在《圣灰星期三》的创作期间,艾略特曾写信给P.E.莫尔(Paul Elmer More)说道:在人间幸福和人与人的关系中,他所看到的是虚无。“只有基督教才使我接受了人生,否则它将是令人作呕的”③。对他来说,荣誉、权力、能力、爱情、快乐和人间的一切物质享受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尘世的诱惑而已。他像一个过来人,似乎已经看破红尘,无心追逐物质利益和人间的荣耀。
但是,1930年的艾略特是否是一个看破红尘,对人间欲望感到彻底失望的人呢?《圣灰星期三》的创作始于1927年,这一年艾略特正式接受英国国教会的洗礼而成为基督徒。虽然英国是基督教新教国家,但英国国教在众多的教义上与天主教相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洗礼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它洗去了过去的罪孽,也洗去了他头脑里的邪念,从此他以全新的面貌成为“天国”的一员。不管这是否真实,其督徒普遍认为洗礼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标志着旧生活的“死亡”;而正是这种“死亡”才使他得以进入一种更崇高的生活,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死进新生”。
历史上不乏名人面对弃旧从新而忏悔的事例。但丁在《神曲》中因自己重新见到比阿特丽丝时产生了动物般的感情而感到惭愧而落泪;圣奥古斯丁也在《忏悔录》中对自己在青年时代的不纯洁的感情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感到追悔莫及。到更近一点的约翰·多恩,这种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惭的作法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一种惯例。在《神圣的十四行诗》中,多恩痛苦地感到“黑色的罪恶”已经将他的自我推进了无尽的黑夜:“啊,火焰/欲望和嫉妒之火曾经燃烧/并使它更丑恶;让这些火焰熄灭/而让火一样的激情,哦上帝,你的和天堂的/在我心中燃烧,在燃烧中治愈”④。可以说在《圣灰星期三》中艾略特承袭了这样一个传统:他的忏悔是没有足够的生活基础的,是一种惯例性的渲泄。换句话说,他的“追悔莫及”看上去有点小题大作、自我作贱。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经抱怨道,“我有点厌倦听到四十多岁的艾略特把自己描写为一只衰老的鹰并问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去展翅飞翔”⑤。也就是说艾略特的忏悔看上去不完全是真诚的(sincere),而仅仅是例行成规(routine)。
然而,对于全诗的感情发展来说,忏悔却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虽然诗中并没有虔诚的基督徒那种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的情景,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过去的悔恨,充满了谦卑(humility),表达出他对“已经做过,但又不能重做的事情”的追悔莫及。“我不希望转身”来自中世纪意大利诗人吉多·卡瓦坎第(Guido Cavalcanti)的《叙事诗:写于在萨兰闸期间流放》,它充分表明了艾略特对人间社会的失望和从这个世界“隐退”并不再回首人间的决心。同时,诗人也深感自己与卡瓦坎第同是“流放”之人,被挡在“天国”之外。所以,他祈求上帝对他仁慈,祈求上帝不要过重罚落,也祈求上帝指引正道,以使他寻规蹈矩。“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吧,现在和我们死亡的时刻”。
至此,诗人已将自己“罪恶”的一生化为一堆白骨,并愿将它付诸“遗忘”。这象征的、精神的“死亡”可以说是一个仪式,诗人在这里演出他的“死亡”为的是更有力地表明他与过去的决裂。三只白豹的作用与但丁的《神曲》里的三只猛兽相同,它们可能指人间的三大淫欲,也可能指尘世、淫欲和魔鬼。诗人在过去的生活中,由于没有精神的指引而误入淫欲的沙漠,被罪恶之兽啃食成骷髅。然而他很高兴成为一堆白骨,因为这样他就彻底告别了感官的生活。《圣灰星期三》的这种情绪的低沉可以说也不是艾略特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是基督徒“精神历程”(spiritual progres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忏悔所造成的“绝望”往往是基督徒进入梦幻、达到“极乐”的前奏,这些在中世纪神秘哲学中有充分的阐述。
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的艾略特对圣人的生活和业迹有特殊的兴趣,所读的著作包括圣十字约翰(St.John ofthe Cross)的《灵魂的黑夜》、无名氏的《无知的云》和诺瑞奇的朱丽安(Juliana of Norwich)的作品。他还写下了《圣那喀索斯之死》和《圣塞巴斯蒂安的情歌》等有关圣人的诗歌⑥。圣人的著作常常是写他们如何通过一系列心理训练,达到“彻悟”的境界,他们进入这种境界时所获得的“极乐”就是对他们多年修行的报答。《圣灰星期三》遵循了这种精神历程的模式,在感情发展上是落于俗套的,在语言上也大量借助了《圣经》和《祷告书》的内容,布罗姆对它的批评在这种意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是,这首诗的意义并不在于“老瓶装新酒”,而在于将传统运用于现代生活,使一个受难的灵魂在传统中找到它自身的意义。忏悔和低沉并非此诗的目的,对于刚刚成为基督徒的艾略特来说,它们只是他转向上帝的第一步。
二、“崇高的梦幻”
《圣灰星期三》由六首短诗组成,前三首发表于1927至1929年间的不同杂志,并有各自的题目。后三首写成于1930年,也各自有题目,组合起来才被取名为《圣灰星期三》。C.K.斯泰德(C.K.Stead)认为,这组诗歌与《荒原》一样本是没有整体构架的。它的价值在于一些零散的闪闪发光的诗段,而总体构想是后加的,也是不重要的⑦。如果斯泰德对《荒原》的分析是精辟的,那么他在这里就显得有点牵强附会。因为这组诗在系列中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们各自独立能够表达的意义。如果总体构架是后加的,那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相反,这个总体构架的设计是对这些独立的诗歌的再创造和重新组织。可以说,这个系列是在各个部分的基础上的提高。
《圣灰星期三》的中心思想集中表现在灵魂的“攀登”和诗人在那“暮色的王国”与一位女士的相会。这听起来仿佛是一组爱情诗的题材,若换一位作家,我们一定会得到一组柔情烂漫的爱情诗。的确,艾略特在诗中不仅称这位倩女为“女士”(Lady),而且称她既有“美丽”又有“美德”,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艾略特所欣赏的两位爱情诗人。中世纪意大利的阿诺特·丹尼尔(Arnaut Daniel)写道:“你的优雅,哦,我心中的女士,/在我的心灵里撒满了金色的光辉”。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在《致羞怯的情人》中也写道:“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这羞怯,女士,就不算罪过”。艾略特的女士也是一位值得爱慕的对象,她不但优雅,而且“漫步在紫罗兰与紫罗兰之间”,“使喷泉有力,使泉水清新”。她是一组爱情诗的当之无愧的主人公。
然而,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法来理解《圣灰星期三》,那么我们就错了。艾略特曾经说,《圣灰星期三》是“将但丁的《新生》运用于现代生活的结果”⑧。也就是说,在这组诗中艾略特采用了但丁那部诗集的模式。但丁的《新生》的确是一组爱情诗,它们表达了诗人对女友比阿特丽丝的爱慕。但它们又不全是爱情诗,因为女主角已经去世。在记忆中向但丁走来的比阿特丽丝已经不再是他曾经见到的比阿特丽丝,她的形象笼罩着一个光环,她已经变为一位天使。或者说在记忆中,她的意义改变了,她不单是一个世俗的情人,而且是通过神灵的媒介。在一篇几乎与《圣灰星期三》同时发表的论文《但丁》中,艾略特写道,《新生》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神曲》的理解,“至少我们能够开始懂得但丁是如何将一种古老的激情的再生熟练地表现于一种新的感情、新的情景之中,而正是这种新的感情、新的情景包括、扩大了那古老的激情,并给予它意义”⑨。
但丁在九岁时第一次见到比阿特丽丝,后来一直热恋她并视她为理想的形象。比阿特丽丝去世后,但丁仍然对她不能忘怀。在《神曲》中,她被描写为“完美”的化身,在天堂迎接但丁的到来。当但丁看见她时,从前那些爱慕又涌上心头,那“古老的激情”又重新萌发在心中。但是,他立即感到这种感情的罪恶,并忏悔自己的过失。但丁与比阿特丽丝的关系是微妙的,它介于爱情和虔诚之间。用艾略特的话来说,但丁的感情逐渐从“活着的比阿特丽丝转移到死去的比阿特丽丝,然后上升到对圣母的崇拜”⑩。也就是说,在《新生》中,爱情和虔诚的界限模糊了,二者甚至被重叠起来。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感情升华”。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说道:“当介时(求美的)本能涌现出来选择各自的对象时,如果内心深处仍未得到满足的话……那么,那模糊的早期爱情的名称和记忆就可能延续并成为没有实现的完美的象征……当但丁认识到(比阿特丽丝)对于他的幼稚幻想来说无异于宗教理想对于他的成熟想象时,他就有意识地将它们合二为一,就像所有诗人将综合与具体、普遍与个体结合起来一样”(11)。
不过,“感情升华”的先决条件是这个感情本身,可以说《新生》的妙处就在于感情与升华之间。没有感情就没有升华,相反,如果只有感情没有升华,那感情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但丁的比阿特丽丝既是凡人又是天使:在但丁看来,她似曾相识,又不尽相识;因为似曾相识,所以他立即产生了感情,但这时的她又不完全是从前的她,所以他的感情也应与从前的感情不同。
如果用这个模式来看《圣灰星期三》,我们可能会问(尽管有批评家奉劝人们别这样做)(12)艾略特的“女士”是何人?是否这位“女士”的后面有一个现实的模特儿?到1930年为止,艾略特的生活中出现过几位比较重要的女性,但很难想象其中任何一位可起到比阿特丽丝对但丁所起的作用。尽管艾略特的母亲夏洛特(Charlott Eliot)对他本人的影响极为深刻,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但母子之间的感情岂可与爱情等同?1915年,艾略特在伦敦与维维安·海伍德(Vivien Haigh Wood)结婚,但从各方面资料来看都没有那种浪漫的爱情,我们很难将维维安与“完美”联系在一起。对艾略特影响更深的一位女性叫爱米丽·赫尔(Emily Hale),在婚前,艾略特曾经通过朋友向在美国的爱米丽赠送玫瑰花(18)。但是,艾略特婚后,爱米丽似乎从他的生活中消失,至少到1933年他俩重逢为止,他们的关系没有证据让人们相信她就是他的理想的化身。
纵观艾略特在1930年以前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他作品里的女性多数是堕落的、反面的。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到《荒原》,她们不是禄禄无为,就是水性放荡,她们是现世腐朽生活的象征。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场景中,也有几处令人难忘的爱情戏。在《哭泣的姑娘》中,“我”对她的观察是动情的,感人的,也是充满爱慕的;而另一首诗《在餐馆里》则通过一个无耻的招待讲述了幼年时代情窦初开的动人经历,我们从故事中能体验到那次经历对他灵魂的冲击。最后,在《荒原》中,“我”同风信子姑娘深夜从花园里出来,不知明暗,不明生死,唯独意识到“光明的中心”。这同样是异常激动、异常热切的爱情,恋人已经进入了梦幻前的恍惚状态。这些事例是否折射了艾略特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呢?艾略特是否将他幼年或青年时期的一些经历写进了《圣灰星期三》呢?这些我们很难断定,不过,艾略特在攀登到楼梯顶端的花园时所见到的那位女士同比阿特丽丝一样,也似曾相识,但又不尽相识。她虽清新飘逸,但蒙着面纱诗人又不敢相认。
这是行进在其间的岁月,带走了
长笛的提琴,带回了
一个睡梦和清醒间游移的人。
艾略特的“女士”可以说最初也是一位凡人,然而,经过“行进在其间的岁月”,长笛、提琴和人间欢乐都被带走,在“睡梦和清醒”间重新出现的她已经经历“升华”。现在伴随她的不仅有“玛丽亚的色彩”,而且她被“包裹在白光中,像在剑鞘里,包裹着”。她已经变形为一位天使,她折射圣母玛丽亚,并时时与她重叠而成为一人。
但丁对英国诗歌的影响是深刻的,艾略特只是受他影响的诗人之一。然而但丁的影响在具体不同的英国诗人中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约翰·济慈的《日神的坠落:一个梦幻》不但从但丁那里获得灵感,而且深受艾略特的喜爱:在这首诗里,“有努力争取感性统一的迹象”(14)。它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在梦幻中来到一个巨大的祭坛,他看见台阶顶端有一位蒙面的女士,站在一尊巨大的神像旁。她双眼放射出温和的目光,她神圣的眼帘似乎半闭,不屑瞭视。但是在漠然的灿烂中,她的双眼像柔和的月亮放发光芒,给她看不见的人们以安慰,同时也不知何人在仰望她的尊容(15)。这位女士就是蒙内塔(Moneta),日神的祭师,同时也是诗人得以与日神交流的媒介。她的作用可与但丁的比阿特丽丝和艾略特的“蒙面的女士”相比拟,因为这两位诗人也同样把他们各自的女士看作神的影子或化身。也就是说,他们与神的交流是通过这位“女士”才得以实现的。不同的是济慈的日神已经被世俗化了,宗教的经验在他的诗中只变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平行,或语句上或修辞上的回首”(16)。他的日神不是艾略特所指的“精神上的完善”,而是诗歌的灵感,他的攀登者仅仅是一个诗歌意象的追求者。
到十九世纪的“拉斐尔前派”诗人,但丁的影响就更明显。在D.G.罗塞蒂(D.G.Rossetti)的《神圣的女郎》中,我们发现世俗的恋人与升天后的姑娘仍然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这个情节的安排似乎与《新生》和《神曲》有关,它不仅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的缅怀,而且把一生一死的恋人的结合描绘成一种现实。在天堂的女士虽然得到了神灵的赐福,但她仍然眷恋着人间的感情。虽然她已离开人间,但她对诗人来说仍然是从前的恋人,仍然使他激动万分。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但丁所描写的那种经验的影子,但是,罗塞蒂的“神圣的女郎”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想起“精神上的完美”,她不可能帮助诗人“攀登”精神的高峰,从而达到灵魂的拯救;她也不可能像艾略特的“女士”成为朝圣者的向导。说到底,罗塞蒂这首诗已经脱离了宗教上的意义,而完全成为一首世俗的爱情诗。这就是为什么艾略特说:“罗塞蒂的《神圣的女郎》开始以惊喜然后以反感支持着我对比阿特丽丝的欣赏达数年之久”(17)。这其中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济慈、罗塞蒂和艾略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但丁的影响,他们所描写的经验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那就是通过梦幻中的女士与她的原形的对比,力求改变爱情的意义。艾略特在评论但丁时说,《神曲》“属于我所说的‘崇高的梦幻’(high dream)的世界”,具有圣约翰的《启示录》的光辉。非常遗憾的是,在中世纪曾经是一种平常现象的梦幻现在却被斥为病态。可以说《圣灰星期三》就是艾略特的“崇高的梦幻”,是他力图把但丁的思维方式运用于现代生活的尝试。在以上三位英国诗人中,艾略特与但丁最接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埃兹拉·庞德称艾略特代表了英语中真正的但丁声音。
三、“沙漠里的花园”
1928年,艾略特发表了《给朗斯洛·安德鲁斯》,在论文学的同时,表达了他对几位英国教会的主教的看法,赞扬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一位未署名的评论员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文,称这部论文集为艾略特“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的明显迹象”(18)。对许多评论家来说,1930年发表的《圣灰星期三》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预言。甚至埃德蒙·威尔逊都认为艾略特“在他新的宗教时期所主张的谦卑对他的诗歌有削弱的作用”(19)。但是,当我们读《圣灰星期三》这样一首诗时,我们应该避免自己的信仰的干扰,应该像S.T.柯勒律治所说,“终止我们的不信任”(20)。如果我们抛开了思想意识上的考虑,而单就诗歌的结构和技巧而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首诗有它独有的长处。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从头至尾都存在着两个不同方向的张力(tension)。耶稣和撒旦分别代表了这个张力的两个极端。他们的斗争在诗中形成了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人间与来世的斗争。这些斗争都使读者意识到通向上帝的道路就是灵魂接受考验的过程,而它的成功取决于灵魂能否抵制现世快乐的诱惑。按照这个推理,诗人应该完全离开感官的生活、完全拒绝现世的追求。但是,《圣灰星期三》不但没有完全脱离现世生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现世生活,这就在诗的深层意识里形成了一个矛盾:本来诗人的目的是“隐退”,然而人间的诱惑时时使他心神不定,诗中的大海和沙滩、长笛和音乐、花园和青草都代表了艾略特所眷恋的人间生活。当他竭力从生活走出,超越物质利益的思考时,生活又不时地把他拉回来,人间的得失、权力、金钱,荣耀和地位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也就是说,诗人从离开现实生活出发,“不希望再转身”,但是,当他向着精神目标攀登时,他却一步几回头。F.O.麦息生(F.O.Matthiessen)甚至认为在诗歌的后半部分“对感官生活的欲望”又有了“出人意料的复苏”(21):第一部分的“衰老的鹰”变成了第六部分“不折的翅膀”,翱翔蓝天。
艾略特说,“怀疑的魔鬼与信仰的精神是不可分割的”(22)。这在第五部分的有关“道”(the word)的议论中有充分的表现。这个大写的“词”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与道教中的“道”相同。根据《圣经·约翰福音》记载,在世界出现之前“道”就已经存在,这就是所谓“太初有道”(23)。后来“道”被变为肉体,这才有了耶稣基督。耶稣之所以称为“道”,是因为他是通向上帝的道路,连接两个世界的纽带。另外,如果这个大写的“词”是上帝的金口玉言,那么耶稣就是这个金口玉言的传媒和化身,他代表了上帝的意旨,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道”。但“道”的存在也同样依附于罪恶的存在,由于整个世界都在反对“道”,所以他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基督教才有坚持它的必要性。“哦我的臣民,我到底对你们做什么了”——传说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它表现了耶稣对人们拒绝他感到极端的不理解。然而,正是这对矛盾,这种张力,才使他的存在产生意义。休·肯纳(Hugh Kenner)评论说,“张力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感性和信仰的精神之间——上帝的创造和上帝之间——的反向拉力应该被保持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和不可缺少的多义性,而不应该把它的一方降至人间,另一方抬上天堂以加‘调和’”。(24)
迷失的心灵坚强起来欢庆
逝去的丁香和逝去的海潮
软弱的灵魂复活过来叛逆
只为弯曲的金条和逝去的大海气味
之所以坚强起来的心灵被描述为“迷失的”,复活过来的灵魂被说成是“软弱的”,是因为此诗的目的是决不回首人间。正如E.E.邓肯·琼斯(E.E.Duncan Jones)指出,“《圣灰星期三》是理性的声音”(25),感性的出现是不由自主的,是理性所未能完全压制的。大海代表了艾略特童年的一段幸福的时光,孩提时他常随家人在马萨诸塞州的安角度假,对海水、沙滩、贝壳、水藻和飞翔的海鸟都有深厚的感情。“遗忘”是困难的,理智的抉择常常被感情推翻,快乐的诱惑又占了上风。这样反反复复演示出一幅灵与肉的斗争画面,而这个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沙漠里的花园”这个意象中。
当诗人从“忏悔”进入“崇高的梦幻”、然后又重新回到他的“放逐状态”时,他在梦幻中所看到的那个“花园”就消失了,引导他进入那个“花园”的女士也不复存在。在这个神秘的经历当中,这位女士起到了耶稣的桥梁作用,连接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她的消失使灵魂又回到了“沙漠”,“在得与失之间动摇”,受着尘世欲望的煎熬。虽然“我不希望希望这些”,但是“白帆仍向大海飞翔”,心灵仍然飞翔在欲望的天空。换句话说,“这是生死之间的紧张时刻/三个梦幻在蓝色岩石间交会的/静谧之处”。全诗以祈祷结束,这次祈祷不是为求得神灵的赐福和保佑,而是祈求神灵的指引:“教我们关心又不关心/教我们静静地坐着/让我别分离”。全诗的主题可以说是“我们的平安在他的意志里”,而全诗的形式可以说是一首颂歌:“让我的心声传达于你”。
《圣灰星期三》在艾略特发展历程上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一个转折。艾略特前期的诗歌多集中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写现代生活的穷极无聊;《小老头》追溯历史写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荒原》写现代社会的颓废和渴求复兴的愿望;《空心人》写现代人的精神贫乏和碌碌无为。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就是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对生活的悲观失望。用艾略特的话来说,它们是对生活发泄的一个小小的“牢骚”(26)。
在前期的诗歌里,艾略特经常使用的比喻是“地狱”。诗中的“角色”往往被置于地狱一样的环境中发泄他的“内心独白”。《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引用了但丁的《地狱篇》作为引语:“如果我认为我的回答是给予一个将回到人间的人,那么这地狱之火将不再燃烧”。《荒原》在描写现代人的精神“死亡”时,又引用了但丁的《地狱篇》。主人公凝视着一片通过伦敦桥的上班族,深沉地感叹到:“我没想到死亡夺去了这么多人的生命”。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艾略特对他所生活的世界有着非常特殊的看法。
如果艾略特前期的诗歌多写阴暗面的话,他后期的诗歌将转写正面和光明面。《圣灰星期三》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虽然它仍然含有对现实的批判,但作者不再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来抒发不满,而是站在宗教立场上来贬低物质世界,夸大精神生活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当艾略特竭力抛弃现实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他的诗中反而显得更美丽、更有吸引力。象但丁在《神曲》里一样,后期的艾略特已经走出了地狱,正通过炼狱向天堂攀登。
《圣灰星期三》可以说开始了艾略特的炼狱阶段。他这时的痛苦不再是悲观失望所引起,他的痛苦来自对自身的净化。在评论但丁的《炼狱篇》时,艾略特写道,“在炼狱里,灵魂受苦,并且情愿受苦,因为这正是为了涤罪”(27)。在《圣灰星期三》和《四个四重奏》中,灵魂都受着各种折磨和煎熬,但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意识的敏锐度,从而感觉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四个四重奏》把煎熬化为等待,把人间同天堂对立起来,把时间同永恒对立起来,诗人所等待的正是“时间与永恒的交会”。艾略特用西方哲学和神学的概念来思考他所亲身经历的“彻悟”,试图通过传统的“自我净化”和“沉思”来重复那瞬间里体验到的“极乐”。而这些在《圣灰星期三》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预示。
注释:
①哈洛德·布罗姆:《塔上的敲钟人:浪漫主义传统研究》,芝加哥,1971,第200页。
②参见格里高利·杰(Gregory Jay):《T.S.艾略特与文学史诗学》,(巴坦路依,1983)有关布罗姆的部分。
③艾略特:致P.E.莫尔书信,1928年忏悔日。
④约翰·多恩:《神圣十四行诗》第五首,第10-14行。
⑤埃德蒙·威尔逊:《阿克梭的城堡》,格拉斯哥,1959,第109页。
⑥在《力士斯温尼》中,艾略特引用了圣十字约翰:“灵魂不可能达到与圣灵的结合,除非它与现世的一切爱决裂”。这句话对《圣灰星期三》具有点题的意义。在《四个四重奏》中,艾略特又引用了《无知的云》和诺瑞奇的朱丽安的作品,这表明了他对这些作家的兴趣。
⑦参见C.K.斯泰德:《新诗学:从叶芝到艾略特》,哈蒙支华斯,1969,第170页。
⑧艾略特:致P.E.莫尔书信,1930年6月2日。
⑨艾略特:《论文选集》,伦敦,1980,第262页。
⑩艾略特:《论文选集》,伦敦,1980,第275页。
(11)乔治·桑塔亚纳:《诗歌与宗教》,引自F.R.利维斯:《英国诗歌的新方向》,哈蒙支华斯,1967,第106页。
(12)利维斯:《英国诗歌的新方向》,第102页。
(13)彼德·阿克洛依德:《T.S.艾略特》,伦敦,1985,第63页。
(14)艾略特:《论文选集》,第288页。
(15)参见约翰·济兹:《日神的坠落:一个梦幻》第一章,第265-271行。
(16)M.H.亚伯伦思:《英国浪漫诗人:现代论文》,纽约,1960,第48页。
(17)艾略特:《论文选集》,第262页。
(18) 艾略特:《论文选集》第368页。
(19)埃德蒙·威尔逊:“评论”,贝麦克·格兰特:《T.S.艾略特:批评传统》伦敦,1982,第259页。
(20)S.T.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文学生涯》第二章,第6行。
(21)F.O.麦息生:《T.S.艾略特的成就:诗歌本质论》,纽约,1956,第121页。
(22)艾略特:《论文选集》,第411页。
(23)《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24)休·肯纳:《隐形的诗人》,伦敦,1979,第227页。
(25)E.E.邓肯·琼斯:“论《圣灰星期三》”,见B.拉坚:《T.S.艾略特:众人评说》,伦敦,1947,第37页。
(26)这句的具体出处不详,但为西奥多·斯宾塞(Theodore Spencer)所引。见艾略特遗孀瓦勒丽·艾略特(Valerie Eliot):《荒原:原稿的复印和誊写》,伦敦,1979第1页。
(27)艾略特:《论文选集》,第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