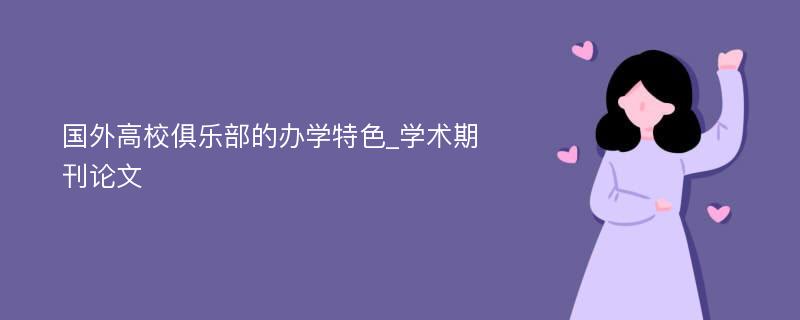
海外大学社经营特色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社论文,之道论文,特色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转企改制的深入,几年来大学出版社这一群体在生产力、竞争力、创造力上的成长有目共睹。背靠高校资源的基础上,如何制定自身的发展规划、释放出版能量,创建新型的运营机制和运作模式,使出版社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已经成为了众多业内同仁的共识。尽管大学社陆续完成形式上的转企改制,但来自业界内外的挑战仍不可回避:一方面区域性的集团化限制了大学出版社的生长,许多大学出版社的辐射面狭小、影响力有限,只是在其所在地“单打独斗”,较难凭借自身的产品闯入外省市市场。一些出版集团的组建,也加剧了地方教育出版社和众多大学出版社的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当前大学出版社主攻的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其市场本身仍存在一定缺陷,譬如教材教辅的无序、学术评审的失范等,都不利于身处其间的大学出版社的良性发展。而大学出版社正在尝试进入的大众领域,却又存在重复出版、恶性竞争的顽疾,其对大众市场的出版规律把握远没有想像中的如意。认清这样的现状刻不容缓,国内的大学出版社或许应该先从“认识自己”开始——转企改制以后,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在哪里、方向在哪边,什么样的发展策略更适合自己,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更具备潜力?既要明确大学出版社的家底与实力,也要厘清自己的思路和需求。正确的市场定位与出版定位,方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学界经常会讨论“我们的大学与国外的大学差距到底有多大?”。反观业界,国内的大学出版社之中,就出版质量与学术影响两个方面而言,能够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名社并肩的还寥寥无几,这也着实反映出国内的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影响力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的大学出版社可以向国外的大学出版社借鉴与学习什么?”这或许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此次特地总结归纳了一些海外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特点和布局策略,希望可以给更多的读者带来启发和思考。
特色1 “非盈利机构”定位服务学界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创立于186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办于1878年,芝加哥大学创办于189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建立于1913等等,许多美国的大学出版社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也让许多业内同仁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百年老店”竟然一直如此“与世无争”、“默默无闻”,甚至许多还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是因为美国大学出版社整体来讲都属于小型出版机构,像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约200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约300种,耶鲁大学出版社每年约出版400种图书,这在美国大学出版社中已经属于相当有规模的数字了。更多的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新书不过百种,甚至十几种。因此,我们也不难想见,为什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那些大学出版社的展位面积是那样的局促,归根结底还是品种稀少的缘故。
不同于当前国内的大学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定位,美国的大学出版社被其政府定位为“非营利机构”。美国大学出版社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基金会的资助、政府机构(主要是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采购和私人捐赠(多半是针对某单本图书的捐赠),另一部分才是市场销售收入。因此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大多数都是亏损经营,亏损面在90%左右;赢利的出版社也多在某个年份赢利。然而,美国的大学对自家办的出版社却都有亏损补贴政策,以确保出版社能够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保证学术出版的顺利开展。这一点尤为值得我们学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创办者丹尼尔·科伊特·基尔曼提到“于大学而言,推进知识发展并且将知识不仅在那些可以每天聆听讲座的人中间传播——而且在更大更宽范围的人们中间传播,这是它最高尚的职责之一”。这一大学出版宗旨向来为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所重视。毋庸置疑,国内的大学出版也遵循了这一理念,特别是大学出版社占据我国学术出版绝对地位的事实有目共睹。只是国内的大学出版社在肩负学术职责以外,还承担了对市场与利润的诉求,这种鲜明的特色使得我们的大学出版社面临更大的压力与挑战。
倡导学术和谋求效益——鱼和熊掌如何兼得?在遭遇了北美学术出版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在近几年进行了转型,从一个只出版学术著作的出版社转变为参与到职业人士读物出版商的行列,并且在成功盈利之后,以盈利的资金来继续维持学术图书的出版需要。此外,随着商业出版公司逐步放弃一些不赚钱的图书出版,不少大学出版社又发现了新的图书出版选题,如一些地方文化、经济或历史类图书。近些年来,又掀起对世界研究的出版热,如索马里问题、墨西哥问题、伊拉克问题和朝鲜问题。美国大学出版社归纳起来,是强调大学出版社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出版社与学术的关系,以及大学出版社在大学社区里的地位,这些举措无疑都会反作用促进大学出版社与自身背后高校的发展。
反观国内,这是业界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并非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或许国内的高校应当效仿美国的大学,积极协力学术出版工作,譬如每年专门规划出一部分经费用于学术出版,或者适当减免大学出版社上缴的利润所得,缓解经济压力。大学出版社还可以积极推进社会上的组织机构创办学术出版基金,以满足当前的学术出版需求。
当然,大学出版社自身也可以主动在校园内外筹款,推进学术出版建设。像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就进行各种款项筹集,美国人文学科基金会更是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资助方式,譬如大学出版社自己每筹集到4美元,它就配套提供1美元资助。有些大学出版社就动员整个大学筹集,以建立一定量的基金,从而成功地获得了不少的美国人文学科基金会资助。显然这些做法对于国内的大学出版社来讲还非常新鲜,而如何谋求“倡导学术”和“谋求效益”共生共存恐怕还有许多路要走。
特色2 高校资源协力选题评审
许多海外大学出版社都在依托学校资源的基础上,借助学校和董事会、监事会力量,在破解行业困局、谋求特色发展的同时,明确长远的发展目标。从策划、审稿到经营业务的部署,均给予适当的指导,在盘活高校可利用资源上颇为值得国内大学出版社的借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大多数美国大学出版社不同,它的所有权不属于普林斯顿大学,大学也不给出版社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出版社从成立至今都是由私人拥有和控制。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直和普林斯顿大学保持密切关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从大学教师中指派人员组成出版社的5人编辑委员会,对出版社要出版的书稿负有生杀大权,而出版社的15位董事会成员中有9位必须与普林斯顿大学有关系。在出版流程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专职编辑负责组稿约稿,接着将书稿先交由非出版社或普林斯顿大学的专家审查,然后才交由该社的编辑委员会讨论通过。历经一番严格的评审之后,通过后的书稿再进入常规的出版流程。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成员由加州大学的教职人员、社外出版界专家和社会活动家组成。董事会主要负责出版社的财政收支管理,譬如筹款活动和分配来自慈善捐款投资收入的出版经费。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由20名大学教职人员组成,代表加州大学全部9个校区,该委员会负责审定出版社的所有出版项目;斯坦福大学的教师中有不少人也受大学委派或出版社邀请参加出版社的编辑委员会、担任顾问、丛书编辑或同行评审。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还配合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采取相关举措,譬如出版一系列本来无法获得出版的、高度专业化但通过了同行评审的研究成果以及主要外语语种的重要文献的翻译版本,形成与大学的学术互动。
大学监管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內容与出版流程,这一现象屡见不鲜。相似的还有牛津大学出版社,它受一个大学委员会控制,其执行主席由大学副校长兼任,委员均是从牛津大学教职员当中委任。委员会负责确立出版方向、制订政策,任命管理人员。除了学校放假期间,委员会每两周召开一次例会,对编辑部上报的选题进行审核。任何计划出版的新书必须先提交委员会审批,其对出版的内容和质量则有相应的规定。有时还需要作者提交相关的图书提案,并邀请作者本身亲身参加选题会议。一旦提案通过,组稿编辑代表出版社与作者签订合同,两者共同工作,直到书稿完成。此外,个别委员需要与出版社的编辑保持紧密联系,就其学术专长提供必要的协助。编辑再与作者讨论意见,并作适当修改。如是这般,方才定稿。邀请牛津大学的专家作为评审,正是其重要的出版政策,也是牛津的学术出版可以享有盛誉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也很值得国内的大学出版社的借鉴学习。
特色3 学科优势转化出版优势
高校的学科优势转化为出版优势是海外大学出版社的另一特色。以耶鲁大学为例,它共有13个专业学院,特别是众多一流的人文科学系和人文科学研究计划享誉国际。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领域因而也集中在人文学科,主要出版领域如中世纪及文艺复兴研究、美国历史、英国历史、西欧现代史、艺术、建筑、教育学、法律、文学、哲学、政治学、宗教、犹太问题研究、斯拉夫研究等,其中有名的系列图书包括《耶鲁圣经》(The Anchor Yale Bible Series)、《注释版莎士比亚》”(The Annotated Shakespeare)、《反思西方传统》(Rethinking the Western Tradition)、《乔纳森·爱德华兹著作》(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Series)、《耶鲁版塞缪尔·约翰逊著作》(The Yal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耶鲁戏剧》(Yale Drama Series)、《耶鲁青年诗人》(Yale Series of Younger Poets)。
像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然及工程科学在世界上享有极佳的声誉,其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也同样优秀。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重点图书系列也多围绕于此,其中有不少著作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智能系统(Computer Science and Intelligent Systems),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博弈论与建模(Game Theory & Modeling),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在内都是其部署出版的重点领域或系列,与麻省理工学院本身的优秀学科相辅相成。
哈佛商学院出版社是哈佛大学旗下两家出版社之一。哈佛商学院以培养企业人才而著称,可谓是企业家的西点军校。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在转变学科优势为出版优势上自然也不例外。《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是自1922年起,由哈佛商学院集结专家、教授,一直致力于创造和传播最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并针对管理事务的研究而出版的专业杂志。目前《哈佛商业评论》在全球有250 000本的发行量、11个版本的授权。而且,哈佛大学商学院大量“商业实例”为哈佛教学改革和创新,即案例教学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源优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能够不断地向全球读者提供不断更新的哈佛案例,进而确立了在案例出版领域的领导地位。
除了围绕学科优势的出版之外,还有许多的特色出版。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Birds and Natural History系列,出版了百余种鸟类学、昆虫学和自然史相关的著作,纽约大学出版社的Library of Arabic Literature系列,专攻阿拉伯文学。还有密歇根大学出版社,该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从1961年起就以其古代和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著称,出版专题因此也涵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像Film Guides for Students of Chinese、Michigan Abstrac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Michigan Classics in Chinese Studies、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等系列都属于这种情况。
特色4 紧随数字创新出版前沿
海外的大学出版社,尽管历史悠久,但绝不固步自封,它们中的很多人都走在数字出版创新领域的前沿。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早在1990年,就制作出电子版的《简明哥伦比亚百科全书》(The Concise Columbia Encyclopedia)。此后,又相继推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在线”(Columb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格兰杰诗歌在线”(The Columbia Granger's World of Poetry Online)、“哥伦比亚世界地名索引”(The Columbia Gazetteer of the World)等。
剑桥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为每本图书建立了电子档案,从绝版书目中选出重点图书做成电子书,使得6000多种绝版图书获得重生。它从爱尔兰数字软件公司Atomic Assets手中收购了国际学习框架(Global Grid for Learning),它是最早被图书馆、教育工作者和博物馆使用的数字教育在线交流平台。之前,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拥有名为“Cambridge Books Online”的电子书数据库,提供按主题分类的电子书,并在其基础上,开发了面向图书馆用户推出数字内容资源平台“大学出版在线”(University Publishing Online)。此外,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构建起了复杂精妙的数字控制平台,像作者资料数据库、作者合同数据库、市场销售预测数据库、电子内容数据库、库存管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和销售跟踪系统等197种信息管理系统。据了解,近些年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数字业务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传统业务,至少有20%以上的收入是来自于数字出版。
不仅仅是固有的数字出版,在传统的出版优势上,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样在积极推进数字化的工作。在出版业务重新洗牌之后,剑桥的学术、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和学校教材三者的战略部署里面,ELT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的专业出版业务也有了数字出版的鼎力支持。譬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就专门设有Cambridge English的专业网站,里面还区分为Teacher zones和Student zones等板块,以便服务不同的教师和学生群体。为整合所有资源,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所有英语语言教学及教育出版的活动都统一在Cambridge Learning这一品牌下进行。利用现有在英语语言教学和教育出版领域的巨大资源,辅以Cambridge-Hitachi开发的电子产品。
“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作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项目,其中包含了许多大部头词典和参考书,例如“牛津英语词典在线”(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牛津艺术在线”(Oxford Art Online)、“牛津民族传记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牛津参考书架”(Oxford Reference Shelf)、“牛津健康计划”(Oxford Health Plans)等,并在去年成功上线“牛津经典著作在线”(Oxford Scholarly Editions Online),为广大师生的科研、教学提供可靠的第一手参考资源,提供各种在线工具以全新方式审视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仅是构建数字出版平台,牛津大学出版社还与Google Scholar、Google Books进行项目合作,为自身的产品提供预览和下载的服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也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合作开发了一个全文电子期刊服务系统——“缪斯项目”(Project MUSE),提供超过120个出版社的500余种期刊,并且每年都在不断增加新刊,其收录期刊的学科重点主要围绕于文学、历史、地域研究、政治和政策研究、电影戏剧和表演艺术等。此外,哈佛商学院出版社还推出了哈佛网络课程(elearning Harvard Business for Educators)这一集视频、音频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网络学习工具。
特色5 学术期刊经营夯实根基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研究论文的主要载体,其在海外大学出版社群体中已经拥有了成熟的评审、出版机制。学术期刊的质量又直接反映了其身后的出版机构、学术机构的治学能力与治学态度。
在19世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就先后拥有了数学教授James Joseph Sylvester、化学教授雷姆森Ira Remsen、语言学教授Basil Lannau Gildersleeve创办的数学、化学和语言学学术期刊,早期学术期刊阵营的建设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在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营根基。此外像Leviathan:A Journal of Melville Studies、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Theatre Journal、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作为当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著名刊物,也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科建设赢得了声望。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刊物也有近50种,涉及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教育学、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等多种学科。创刊于1895年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是社会学领域的最早的一本学术刊物。到了2004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旗下的所有刊物都可以提供在线阅读。
剑桥大学出版社以专业权威的自然科学和国际领先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而闻名世界。同时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众多世界知名的学会保持着合作关系。譬如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hysiological Society、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Protein Society等学术组织。
在自然科学方面,剑桥大学出版社拥有学术期刊105种,其中63%被SCI收录,其中以数学、环境与保护生物学、农业、神经学与心理学见长。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和Journal of Navigation是所在学科排名第一的期刊,此外Laser and Particle Beams、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和Quarterly Reviews of Biophysics也都是所在学科的翘楚;在人文社会学方面,剑桥大学出版社拥有学术期刊133种,其中27%的期刊被SCI或SSCI收录,其中以地域研究、历史、政治学和语言学见长。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China Quarterly是所在学科排名第一的期刊,此外English Today、Journal of Linguistics等都是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期刊。
相较于此,国内的大学出版社在学术期刊的建设上还有着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在使用量化标准的机制上还有诸多不完善,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成果影响因子评估机制,为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此外,数字化学术期刊现在还是一张白纸,如果能以此为基点,对结构布局以及整个体系、分布、运作、传播进行顶层设计,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期刊改革也能看到希望所在。
标签:学术期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