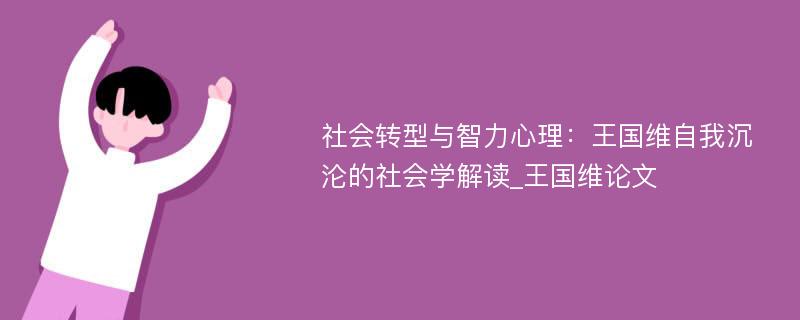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心态——对王国维自沉的一种社会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心态论文,王国维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09)03-0077-06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社会观念变迁的速度是知识分子心态的风向标。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国学大师王国维(字静安)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重大损失。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地位,关于他的死因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各家对王国维自沉之谜见仁见智,争议较大。[1](P1-2,87-178)在民国初年这个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社会文化界,掀起了阵阵波澜。本文试图通过对王国维之死的一种社会学解读,窥见清末民初社会观念急剧变迁时期处于文化震惊中知识分子的一种复杂心态。
一、安身立命之基的内在冲突:对学术与政治双重关切的两难
王国维一生视学术为生命,他的学术观念非常先进,一度对学术充满信心。“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2](P25-27)作为学者,王国维博学慎思,学风严谨,功力深厚,广泛涉猎诸多学科领域,开启了治学理念与治学方法的现代性枢纽,在哲学、文学、史学等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他通晓英、日、德语等外语,最初致力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研究兼及美学和教育学,成为把叔本华、尼采等学说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在文学领域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开创了中国传统戏曲研究之先河;他创立了“二重证据”、“语言比较”和“诗文证史”的方法,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把我国传统的史学考据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他中年以后的主要成果《观堂集林》和《观堂别集》,涉及古文字、古器物、古音韵、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等学科,为其史学领域实证性研究之集大成。[3]从哲学到文学到上古文字器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或治学方法的转换,其背后是王国维苦痛的心灵和曲折的心路历程。对于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陈寅恪曾这样高度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4](P219-220)遗憾的是,就在王国维的学术建树正当其时、如日中天之际,他的生命之歌戛然而止,“使假其年,则所诣未必即止于此,是亦世界学术上之不幸也已”。[5](P4-50)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作为学者,王国维主张学术与政治分开,非常重视学术本身的价值,反对学术文化之外的任何功利,不遗余力地追求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然则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解者也。”“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为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6](P1822-1829)无疑,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王国维追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旅程布满了荆棘,他对现代学术理念的探求常彷徨于歧路。他沉浸着现代意识的苦痛展现于“古典”的写作之中,使得正走向末路的传统“残余”形式留下了一些充满奇特张力的文本。[7]正如陈寅恪在所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P218)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思想复杂的人物,他向来重学术、轻政治,在他心目中,做学问家要强于做政治家,“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9](P1848-1850)然而,学术总又避不开政治,并常常相互缠结在一起。在中国传统社会,通常视学术为政治的附属物,认为学术理所当然应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服务,否则就没有价值。[10]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也向为读书人所关注,视学术为国之生命和己之生命,是读书人的共同心声。学术关乎国家存亡,学人报国救国,首先离不开学术,因为学术乃是国民精神与民族生命所寄托的动力源泉,这正是学人参与政治的最初起点。[11]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让王国维无法独善其身。由于他重大学术成就和讷言少语的性格,人们很容易将他看成是一个纯粹醉心学术研究、并不关心政治的人。其实不然,试读一读他给别人的信,就可以发现,他对国际国内的政治极为关注,且绝不置身度外,总是将自己摆进去,十分热衷。王国维早年很关心时事,戊戌变法时,他的思想倾向于变法一边,变法失败后,海宁士大夫舆论责怪变法的主持者康、梁,王国维甚不以为然;1901-1905年,王国维悉心研究西洋哲学,对政治转而淡漠,他不想步趋康、谭借哲学为置身政界的阶梯;[1](P6-7,67-68)1916年曾供职清廷学部,至辛亥东渡日本,约四年半;1923年,以蒙古升允荐入清宫,任职南书房行走,为清逊帝溥仪师,食五品俸,至1924年冯玉祥逼宫止,约一年半。这样,晚年的王国维又被不自觉地卷入到政治的漩涡之中,并对政治时事表现出真切的关注。
西方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一直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是二元的,学术上追求真理,政治上充当“社会的良心”。王国维在政治上虽然谈不上充当“社会良心”,他的政治观和伦理观都有着极为浓厚的士大夫意识,但是他对文学和学术的态度,却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式的,即以追求真理、探索人生为目的。[12](P274)在清末民初激烈变化时局的影响下,急功近利的文化心理使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很好地把握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王国维先进的治学思想与保守的政治倾向,使其在定位自己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时,常常发生对学术与政治双重关切的两难,从而陷入不安的心境之中。他对传统文化的衰微现状感到忧心忡忡,对西学西政之说影响中国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在他心目中,传统的君主制是祖先留下的一种恰到好处的统治形式,要胜过走极端的西方立宪、共和制。“窃自辛亥以后,人民涂炭,邦域分崩,救民之望非皇上莫属。”[13](P416)毋庸讳言,王国维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正如其女王东明所言,“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他那执著念旧的个性,并受罗(振玉)氏保皇思想的影响,与宣统帝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故对清室怀念,自在情理之中……一位讲信义的学者,总比朝三暮四之徒可爱又可敬得多。”[14]王国维对学术与政治的二元观照与内在龃龉,导致他的内心承受了剧烈的痛苦。其自沉悲剧的发生,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人生境遇悲凉的凄美。从根本上说,王国维的死,是对清朝复辟失败的绝望与对民国社会秩序的忧惧,是学术和政治碰撞的必然恶果。[15]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言:“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1](P7)
二、价值体系的断裂与张力:对中西新旧文化普遍调适的牴牾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是在外患日亟与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五四精神的洗礼,使文化的中西新旧之争,成为困扰传统知识分子的焦点论题。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融会、整合,实际上远远地超出学术的范围,广泛地深入到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各个方面。而所谓“新旧之争”,也主要表现为中西之争。王国维率先破除了限制学术发展的中西新旧的畛域,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提出“学无中西、无新旧”的主张,自觉地引进、吸收外来学术思想,从哲学的高度冷静地剖析中西两种文化,以一种开放的博大心胸容纳古今中外一切真知与思想方法,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华夷之防”,融会古今新旧,兼采诸家之长[10],企图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建构超越中西文化之上的民族文化理论。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王国维反对言学者有中西之争,主张中西互补,两者兼顾,相互促进。“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16](P6-9)西方文化以科学和民主为特征,有强烈的理性色彩;中国传统文化以宗法伦理为特征,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西方文化面前,中国文化也有其自身优势。1920年,王国维在给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说:“世界新潮流倾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柝,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17](P311)
与此同时,王国维主张调适新旧文化,维持民族生存之根,延续民族文化生命。王国维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历史上一切学说,一切制度、风俗,都有其所以存在与变化的理由。“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其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16](P6-9)研究历史,就是要“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18](P2-3)在具体研究中,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19](P1927-1928)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特别是中国传统学术缺乏对研究对象作规范化实证研究,以及内在规则较为模糊笼统,王国维也提出了批评。[20]王国维认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地位”,原因在于中国人缺少“思辨”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太过于“实际”、“通俗”、“具体”,而不擅长“抽象”、不精于“分析”。[21](P449)借助西风东渐的契机,西学成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支点和利刃。王国维是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大学者,兼采中西新旧文化之优长。他对国学有深厚的根基,继承了传统经史考据学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等精华,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在中国文化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同时,他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中吸收了近代西方学术中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对西方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
法国评论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在其名著《知识分子之背叛》中认为,知识分子存在于一种普遍性的空间,既不受限于民族的疆界,也不受限于族裔的认同。而实际上,民族或其他种类的社群(如欧洲、非洲、西方、亚洲)具有共同的语言和一整套暗示及共有的特色、偏见、固定的思考习惯,我们似乎无从逃脱民族或社群在我们周围所设定的边界和藩篱。[22](P28、31-32)不论王国维多么喜欢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在他身上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传统文化深厚土壤的熏陶下,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因子已内化、渗透到他潜在的心理意识层,形成了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深度规训,对他的日常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内心世界里传统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心态变异缓慢,对传统文化有浓烈的依恋情绪,造成了他一种保守拒变的自缚式心理定势。再者,王国维的文化人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不仅有新旧、中西的矛盾,还有体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意识与方法、学问与处世等各种层面的悖立或冲突。而在所有的冲突背后,是文化与文化人格的冲突。他的“可爱”与“可信”、“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中西文化在其内心发生冲突的结果。面对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的冲突和社会秩序的失范,以及社会出路的迷茫,王国维表现出无限的忧思。在中西新旧文化交汇与碰撞的情境下,王国维面临两难的选择:既要因应时代,又要因循传统;既要因应世界潮流,又要顾及中国社会。然而,他企图对中西新旧文化普遍调适的努力陷于困境,难以很好地完成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介文人,王国维性格内向、深沉,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情结,使他感觉自身从文化中心滑入边缘化地位,这种文化震惊使其内心极度苦闷、彷徨,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中无法自拔,最终陷于绝望,献祭给多灾多难的民族文化。他对死亡的选择,既是对其文化人格的自我塑造,又是其文化人格之悲剧性冲突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文化的悲剧。[23][24]
三、意义寻求与向死而生:个人精神操守与群体心理归属的歧路
经典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25](P4)在探究自杀产生的社会因素时,迪尔凯姆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环境及带有某种共性的社会思潮和道德标准。[25](译序,P1-2)可见,自杀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产物。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存在论不是把死理解为命运之神从外面割断了生命之线,而是理解为“向终结存在”(Sein zum Ende)。因为死本身也属于此在(Dasein)之在。[26](P287)这样,死亡便获得了一种存在的意义。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将人形容为“大自然中的一枝芦苇”。任何人都无法预料自己在何时何地会以何种方式死去,然而,恰恰就是在这种“与死共舞”、向亡逼近的有限的时空中,去追求无限的可能(设想、理想、幻想、……),这,就是生活的意义。[27]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一种生命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死亡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个体的文化存在方式。那种足以击毁人并能造成自杀行为的外在压力,首先是人的精神仰仗。但这种个体抑或群体的自杀,并非由于他(们)信仰的蚀解,而恰恰是“信仰”坚挺的反证。正如老舍一再郑重宣布的:“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28]
通常说来,所有社会集体、或者某一人类群体,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一个超然于个体心灵的心灵,就是说,拥有某种“集体灵魂”,或者某种“团队精神”。[29](P6)个人精神操守的坚持,往往是标志知识分子自身存在、建构其群体心理归属的表征。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制倾倒摧毁了儒学长期依赖的制度基础,政治信仰失重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意义与价值危机,在新的国家权威信仰系统尚未确立之前,人们思想处于混乱、迷失状态,复辟与复古成为革命后的重要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30]与此同时,日常生活的内容和本质都在转型过程中,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统一的世界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强烈的时空抽离感使知识分子对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疑虑,对自我身份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实现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的渐进式蜕变,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汇合与分流。王国维集封建儒家学说、老庄哲学、佛学、叔本华与尼采等思想于一身,养成了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与刚性的心理结构,心理保护膜与承受力都很脆弱。王国维的性格,具有三点最重要的特色: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禀赋所造成的在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执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31](P1-18)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的混乱局面,使王国维不能单纯保持超然之理想与地位,而陷入一种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而不能自拔。个人与群体之间双重理性与双重信念的冲突,自始至终存在于王国维的人生选择与精神交锋中。他在坚持自己精神操守的同时,却无法建构其心灵外化的群体心理归属。冷酷的现实境遇,无情地碾碎了其持守终身的纯粹、圆满的价值根基与坚定执守,而个人精神操守的失落与迷茫,又导致群体归属感剥离与精神上的空灵。自我认同的冲突与含混,同文化性、宗教性、古典道德义理及现代个体生存等内涵一起,构成王国维自杀的内涵与意义的多重性与含混性。[32]王国维内心的痛苦是收敛式的,其自沉悲剧的发生,是个人精神操守与群体心理归属步入歧路的产物。
总之,王国维的死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经济上的穷困,使他难以负荷多子女家庭的生活重担;社交上的屈辱,使他忍受不了罗振玉的欺侮和逼迫;政治上的保守,使他对革命感到恐惶;信仰上的悲观主义,使他对人生深感痛苦,以至绝望。[33]当然,王国维的自杀,非单纯出于他个人的原因,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传统道德、传统气节观以及传统社会理想)是重要的根源。[34]挚友之绝、丧子之痛、贫病交加、悲观思想,以及社会环境等等,都是其复杂心态的致物和自沉的诱因。从社会学角度看,作为一个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王国维无法解决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群体的多重矛盾,安身立命之基发生内在冲突,价值体系呈现断裂与张力,自我认同的恃仗虚化,精神操守的归依幻灭,实践“场域”缺失,思维“惯习”迷路。而其执著的人生追问造成这位转型期知识分子独抱一己之理想,向死而生的意义寻求导致了他最后选择生命的迫降。王国维作为物理意义的生命虽早已消殒,但其独立自由的精神犹存。哲人逝矣,然碑碣犹存。[35]最后,笔者以王国维之女王先明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36]
标签:王国维论文; 政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社会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信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