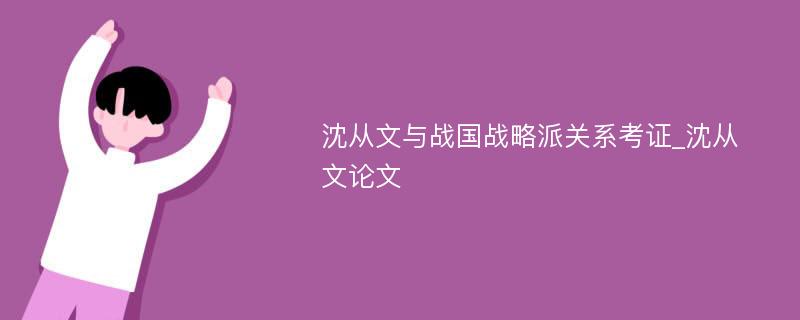
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关系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策论文,关系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1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2)03-0041-08
一
1940年4月,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同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铨、历史系教授雷海宗等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在昆明出版,沈从文被列为26位特约执笔人之一。编者在第2期《本刊启事》中声明:“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k)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由此形成了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战国策派”: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倡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以拯危救亡;从文化形态史学观角度出发,认定世界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在反思文化传统的同时,提倡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最终完成中国文化的改造。
作为一个流派的“战国策派”存续时间并不长,但由于他们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独特的学术理念,甫一开始,即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更由于政治态度方面的歧异,遭到了革命阵营的严厉批判:“‘战国’派的言论的实质,是一派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为虎作伥与谋反的谬论。”①“‘战国’派的‘天才’论,‘英雄’论,‘战国’派的‘恐怖’,‘狂欢’与‘虔恪’的艺术观,是尼采反对人类的平等的贵族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所以‘战国’派和德意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尊尼采为他们的祖师,为他们‘时代的先觉’,决不是偶然的。”②无独有偶,在茅盾所做的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中,也特意指出“十年中间我们曾和各种各样的反动文艺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在基本上打败了敌人。我们曾经驳斥了‘抗战无关论’,曾经对当时大吹大擂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艺政策’从各种角度上加以抨击,使之体无完肤,我们曾经集中火力打击那公然鼓吹法西斯的‘战国策派’,我们又经常揭露市侩主义的本质以及其他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谬论。”③在今天看来,这种“批判”,已经明显地超出了正常学术讨论的范畴。
多少年后,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对当时的情形有过这样的回忆:“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同志,个个都把唯心主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一碰头就是谈冯友兰、贺麟,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新文章。这个情况,所有的同志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雷海宗主编的刊物《战国策》,对我党态度不友好,《群众》主编章汉夫著文批判《战国策》,点了雷海宗的名,孙晓邮主编的一家经济刊物,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话,许涤新同理论界同志对此进行了批判。”④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战国策派”被贴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写入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各种教科书。不幸的是,这一流派的主要成员都留在了大陆,不得不背上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
作为《战国策》的编者、作者,沈从文也深深地卷入了这一理论漩涡之中。但与陈铨、林同济、雷海宗这些“战国策派”主要成员不同的是,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非常复杂,对于沈从文是不是“战国策派”的成员,作家本人及学界都讳莫如深。但这又始终是沈从文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它不但对理解沈从文的创作有着重要作用,也与沈从文解放后的命运密切相关。有很多人认为,沈从文1949年后饱受冷落,即与这段经历有关。夏衍在与李辉的对话中曾经这样说过: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没有沈从文,这个事情很奇怪吧。沈从文很有名气,为什么连代表都不是?当时我没有参加。大会是7月召开,上海5月刚解放,接管工作非常忙,我留在上海。后来文代会之后我到北京,有人同我谈到沈从文的问题。我问周扬,怎么沈从文没有参加文代会。周扬表情很奇怪,说:“说来话长,不谈不谈。”后来我辗转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沈从文在1943年或1944年的时候,给当时的《战国策》杂志写过文章,陈铨主编的,他写过《野玫瑰》。陈铨他们公开拥护希特勒的。这个时候,沈从文在那上面写文章,主要讲三K主义,这个你可以查出来。聂绀弩的杂文集,宋云彬、秦似的文章有批判他的。为《战国策》写文章,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写文章,因为我和他不熟,我不晓得,没看他的东西。
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但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⑤。施蜇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一文中也认为: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⑥。
其实,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印象,关键问题还是对“战国策派”的评价。正是由于这一流派长期被人们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很多人才避之唯恐不及。沈从文自己就曾经多次否认自己与这一派别的关联:20世纪50年代,在一份传记材料中写道:“曾和联大同事钱端升、陈岱孙等编过一周刊,又同林同济等编过一半月刊。广西方面刊物找对象骂人,总以为有个什么《战国策》派,其实全不相合。我不再写文章,问题也极简单,即到我明白刊物有一点政团意味或官僚关系时,我搁笔了。”⑦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在和金介甫对话时,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⑧。可能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态度,在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热潮当中,很多研究者在“战国策派”问题上大多采信了作家自己的这种说法。如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说,“由于沈从文当时与陈铨、林同济同在西南联大,并在《战国策》上发表过文章,有人便散布沈从文是‘战国策派’的谣言。”⑨吴立昌也认为,“沈从文仍然抱定文学应超越政治的宗旨,再加之林同济、陈铨都是朋友熟人,所以,他照样在《战国策》先后发表了八篇论文和随笔,尽管它们大多谈的是文学或自己的思想感受,没有直接议论政治,更没有同刊物编者产生理论上的共鸣,但仍然因此而被一些人误戴上‘战国策’派的帽子达数十年之久”⑩。在诸多研究者中,王保生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最为明确:“说沈从文是‘战国策’派,或者说沈从文与林同济合办《战国策》,都是不正确的。”(11)可以说,出于在政治上为沈从文“辩诬”的目的,很多研究者都否认沈从文是“战国策派”成员。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温儒敏、丁晓萍编辑的“战国策派”论著集《时代之波》(12)没有收入沈从文的相关文章;同样,江沛的专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13)也没有将沈从文的文化思想纳入研究的视野。
一时之间,沈从文不是“战国策派”似乎成为1980年后研究界的“共识”。但是,沈从文到底是不是“战国策派”?这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它最起码牵涉到以下几个层面:
事实层面:即沈从文与《战国策》杂志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真如有论者所说的仅是一名普通的作者?还是沈从文本身就是主持其事的编者之一?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思想层面: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思想观念是否有内在关联?不错,他确实围绕“英雄崇拜”问题写过一篇与陈铨争鸣的文章,但仅从这一点,是否能够排除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在思想上的相通?
创作层面:沈从文所创作的大量小说中,有没有隐含着与“战国策派”相关的质素?这也是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属于某个派别的重要因素。
我们还是从不同层面对这一问题详加讨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在《战国策》创办之初,沈从文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他是把《战国策》当作自己办的一个刊物,还是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普通作者?这个问题对我们辨别一个以刊物为中心而形成的社团或流派的成员至关重要。
二
沈从文到底有没有编辑过《战国策》半月刊?这并不是一个难弄清的问题。实际上,在《战国策》半月刊创办之初,沈从文自己曾在书信中多次谈及此事,明确表示正在和朋友合办一份刊物。1940年2月26日,《战国策》还在筹备当中,沈从文在写给沈云麓的信中说:“我杂事过多,近又同朋友办一杂志,每月必有一万字文章缴卷,一年要万多印刷费,经费不困难,只是邮运极不便利,分配刊物到各处,恐不大方便。”(14)信中所说的杂志,即是《战国策》。1941年2月3日,在写给施蛰存的信中则说:“刊物纯文学办不了,曾与林同济办一《战国策》,已到十五期,还不十分坏,希望重建一观念。因纸张太贵(将近三百元一令),印得不甚多,不够分配,因此老友也不赠送。”(15)这两封信都是写于《战国策》杂志筹备及办刊期间,因而所述事实应该不至有差。但上述事实也只能证明沈从文参与了《战国策》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至于沈从文到底是一般参与还是其重要成员,这还要从其他方面来考察。
从现有的材料看,沈从文与《战国策》的关系,恐不似沈从文所说“到我明白刊物有一点政团意味或官僚关系时,我搁笔了”(16)那么简单,这需要从“战国策派”存在的时间来作出判断。“战国策派”是因刊物而命名的流派,因而,它的存续时间需要用刊物的出版与停刊来印证;而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则需要看他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数量及持续的时间。1940年4月1日,《战国策》半月刊创刊,这也标志着“战国策派”的诞生;1941年7月20日,刊物出版至第17期后停刊;1941年12月3日,重庆《大公报》出版了《战国》副刊第1期,1942年7月1日,《战国》副刊停刊;1941年,上海曾经出版过几期《战国策》月刊,基本上都是《战国策》半月刊文章的汇编,可以与《战国策》半月刊看作一个刊物。虽然陈铨后来又主编过《民族文学》这样的与“战国策派”有一些联系的刊物,但严格讲来,“战国策派”的存续时间在1940年至1942年这三年之间。在此期间,沈从文先后在《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战国》上发表了《烛虚》(二篇)、《白话文问题》、《续废邮存底》、《读英雄崇拜》、《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小说作者和读者》、《谈家庭》、《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等9篇作品,第一篇《烛虚》刊发在《战国策》半月刊的创刊号上,最后一篇《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则是发表在1942年2月11日的《大公报·战国》副刊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应该说是“战国策派”中一个比较活跃的作者,很难说是“到我明白刊物有一点政团意味或官僚关系时,我搁笔了”。此外,1941年在上海出版的《战国策》月刊的撰稿人名单中,沈从文依然列名在林同济、陈铨之后,排名第三。同时,1940年11月20日,沈从文还出席了《战国策》半月刊为著名记者范长江举办的晚餐会,出席这次晚餐会的林同济、陈铨、雷海宗、洪思齐、何永佶等均是“战国策派”的核心成员(17)。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国策派”存在期间,沈从文与这一团体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因而,从事实层面来看,沈从文确实是“战国策派”中的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成员。
然而,判断一位作家是不是某一流派成员,不仅要看其是否参与了这一流派的各种活动,更要看其思想理念层面是否与流派的主张相契合,因此在讨论沈从文与“战国策派”思想渊源的诸多论文中,往往以沈从文与陈铨曾围绕“英雄崇拜”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为据,否定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思想关联(18)。的确,在“英雄崇拜”及对“五四运动”的看法问题上,沈从文与陈铨的见解确实有很大不同。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总体语境下,陈铨倡导“英雄崇拜”,在他看来,“人类的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而“英雄是群众意志的代表,也是唤醒群众意志的先知”,“没有他们,宇宙间万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而由于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官僚化”和“经过二十年反对英雄崇拜的近代教育”,最终造成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无人格,无信仰,虚伪矫诈,阿谀逢迎的风气”。在陈铨看来,“怎么样改变教育方针,怎么样打破中国士大夫阶级腐化的风气,怎么样发扬中国民族潜在的精神,怎样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这就是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19)而沈从文认为,“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迷信崇拜。”(20)
实际上,陈铨和沈从文对“五四”运动的看法的分歧更大。在陈铨看来,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使个人自由得到了无限伸张,致使个人主义变态发达,“对一切的传统都要打倒,对于任何的英雄,都不佩服。他们相信的,崇拜的只有自己。在这一种空气之下,社会一切都陷于极端的紊乱。”“所以五四运动的功绩,是打破中国旧式的传统,五四的流弊,就是更进一步使中国士大夫阶级,更加腐败。”(21)与陈铨相反,沈从文对“五四”的评价甚高,“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我们若能保留了这份天真和勇敢精神,再加上这二十年来社会变动文运得失所获的经验,记着‘学术自由’的意义,凡执笔有所写作的朋友,写作的动力,都能从市侩的商品与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脱出,各抱宏愿和坚信,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来表示这个民族对于明日光明的向往。”(22)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认为陈铨对“五四”的意见“与事实不大以相合”,认为陈铨所列举的诸种问题,“系与‘党政’有关,与五四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却不相干!”(23)这是沈从文对五四运动的基本判断。正因为如此,还是在40年代,沈从文就在一封信中特意强调了自己和陈铨的不同:“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铨先生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先生写了篇‘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时的技巧,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你若有机会翻《战国策》也就会明白,不至于同意杂感家胡扯了。”(24)无独有偶,陈铨对两人的分歧也曾经有过明确说明:“我在《战国策》第四期,发表《论英雄崇拜》一文以后,引起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批评。沈从文先生,甚至于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来详细反对。沈先生的诚恳,很令人感动,沈先生文章里所指摘的小节地方,我也可以在某种条件下赞同接受,但是重要的,乃是这个问题后边,隐藏着欧洲数千年另外一派思想界的潮流,决不是几千字的文章,所能说清楚的。沈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思想最主要的问题,还没有抓住,而且对于欧洲英美传统派而外的思想实在是太隔膜了。”(25)
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将沈从文与陈铨在“英雄崇拜”和“五四”问题上的分歧作为判别沈从文不是“战国策派”的依据。因为“战国策派”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其成员的思想观点,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一点他们自己有着明确的认识。在战国策派成员特意为范长江举办的晚餐会上,当雷海宗、林同济与范长江讨论“历史分期”、“战国时代”、“历史哲学”等问题时,“沈从文教授、洪思齐教授、何永佶教授皆发表声明,关于这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有一致的意见,林、雷两先生刚才这些看法,只是他们个人的思想,不是《战国策》全体一致的立场。”他们再三强调,“我们大家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写文章也没有事先讨论过,编辑不过是收收稿子,并无一定不变的编辑方针。”(26)由于“战国策派”成员本来就分属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不同的学科,专业背景、思想趣味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单纯从“异”的角度还不足以考量某人是不是“战国策派”成员,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们是否有“同”的一面,而这“同”的一面,又是否是这一流派的主要理论诉求。
三
从总体角度看,“战国策派”在“文化形态史学”、“英雄崇拜”诸问题之外,还有着其他的更为重要的理论诉求。而在这些方面,沈从文和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一场决战,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各党派力量摒弃前嫌,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将领便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27)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称,“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28)正是在这一整体语境下,1939年3月,国民政府成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主持其事,先后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国民公约》等法规。“国民精神总动员”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为共同目标,最终完成“救国之道德”、“建国之信仰”及“精神之改造”,这一切被看作是“抗战制胜之主要条件,亦救国建国之最新武器”(29)。随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运动作出了积极响应,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30)为此,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举行精神总动员宣誓,“以空前热烈和团结之精神,虔诚拥护精神总动员之纲领,及国民公约。”(31)毛泽东则在会上发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明确表示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32)。在1939年至1943年间,《新华日报》对这一运动均作了积极反应。也正是在这一情形下,“战国策派”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作出了积极响应,林同济曾经这样解释“战国策”的内涵:“如果浅一点解释,《战国策》即《抗战建国方略》。如果再进一步解释,战即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策即意志集中、力量集中。”(33)林同济虽然没有提及正在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但他的解释完全照搬了这一运动的“共同目标”。也就是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并不是“战国策派”同仁创造出来的一个口号,而是沿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所提出的口号。像中国共产党宣布对这一运动“积极拥护”一样,“战国策派”的这一选择,并不是拥护“独裁”、宣扬“英雄崇拜”,它只是民族战争条件下有良知的国人的共同意愿。沈从文虽然没有直接回应过“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主张,但统观沈从文的战时言论,就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对这种对国家的态度是赞赏的。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明自己的观点:“近十多年在各种刊物上最常见的是‘民族精神’字样。今年又为‘精神动员’。就常理说,所要准备动员的‘精神’,应当就是先前一时谈及的那个‘民族精神’。”(34)“现在如果有什么人,还想凭借武力来推翻当前政府,我们就不会坐视国家统一的破裂,甘心重新陷入割据混乱的局面,为维持安定和统一,对于内战我们必会极力想法避免。到无可避免时,也要想方设法直接间接来制止它,消灭它。至于战争若系完全对外,对方又是一个凶狠横蛮的民族,五十年来处心积虑,用尽各种鬼蜮伎俩,豪夺巧取,侵略我领土,削弱我民族生存能力,想慢慢毁灭我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我们因图自卫自存而战,这战争,当然人人有分!”(35)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湘西歌者的沈从文几乎放弃了此前的民族立场,他真心地希望家乡人能够摒弃前嫌,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为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芸庐纪事》、《动静》等小说,在这两篇以自己的兄弟为原型的小说中,充分展示了从普通国民到职业军人对待民族战争的一致态度,这就是“杀敌报国”。这是一个把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沈从文。
除在“国家—民族”感情上与“战国策派”的相通之外,在对文化传统的认知和疗救之道上,沈从文与他们有着更多的相似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沈从文就开始关注中国人性格中的“阉寺性”问题。在他看来,在文明的进程中,中国人染受了过多的“文明病”,变得“虚伪”、“乖巧”,办起事来畏首畏尾,生命的野性丧失殆尽,这在小说《八骏图》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作者甚至借《如蕤》主人公的口发出慨叹:“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再发生了。”抗战开始以后,由于国势的颓败和军事失利,沈从文的这种感受更加真切了:
街上人多如蛆,杂声嚣闹。尤以带女性的男子话语到处可闻,很觉得古怪,心想: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人既雄身而雌声,因此国事与家事便常相混淆,不可分别。……“外戚”“宦官”虽已成为历史上名词,事实上我们三千年的历史一面固可夸耀,一面也就不知不觉支配到这个民族,困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如今有多少人作事,不是因“亲戚”面子得来!有多少从政者,不是用一个阉宦风格,取悦逢迎,巩固他的大小地位!(36)
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37)。
面对这种局面,沈从文忧心如焚:“我们应当承认,直到如今为止,后方有许多事都近于消极应付,不是积极进行的。即有关国防设计各重要事业,负责任肯作事的固然不少,怕作事,懒作事,不会作事因而误事的,也到处可见。公务员之不讲效率,对生命无目的,无理想,更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38)而这种现状产生的原因无他,依然是阉人性格从中作怪。应该说,这是沈从文经过长期的观察、体验和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
无独有偶,“战国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也集中在生命力的缺失上。雷海宗就曾直接将国力的衰微归因于中国文化中的“无兵”:“兵的问题,牵动整个的社会;兵制与家族制度又是不能分开的。”而“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一个民族或个人,既是软弱无能以至无力自卫,当然不会有直爽痛快的性格。”而这一切皆是因为两千年来畸形发展的文德结果。他认为“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39)在这方面,林同济说的更直白:“我们分析中国过去传统的思想与文化的气质,感觉得其中有个大缺憾,就是我们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中,太缺乏了军人的影响,军人的贡献。”“任何健康有为的国家,它的思想与文化都必带有军人的成分,武德的成分。反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一般思想与文化是太缺乏了军人的色彩与武德的因素,其国必弱,其民族必不免萎微不振。”“‘怕’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充满了‘怕’。我们做一桩事,往往不是因为此事之该做,乃是因为不做便遭人言。我们不做一桩事,也往往不是因为事之不该做,乃是因为一做出去,又怕有人说话。我们一动一静一举一止的动机,都是个怕字——怕人言,怕闯祸,怕不得上司的垂青,怕不博乡党的称誉。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怕’!我们晓不得人生乐趣正在放胆做去。看得到,做得到。管他三七廿一,管他青蝇之营营,宵小之指摘,我且凭我的良知,做将过去。怕什么呢?原来中国的怕的人生观,怕死的哲学与中国孝的学说的某部分发生大关系。‘孝子不登高不临深’的一套,意也许是欲求一种矜持的态度,但终不免是鼓励那‘可怜虫’的战战兢兢的丑样子。我们说,孝子(此处疑脱一“不”字——引者注)登高,西方人专门喜欢爬高。我们说,父母在不远游。西方人专门喜欢探行危险百出的地方。”(40)他在一篇书评中曾经这样分析中国的文化传统:“人类的问题,就在如何使‘自我’得充分的发展与运用,以防避‘阿物’、‘超我’与环境任一者之畸形的发展与过度的肆威。中国传统伦理下的社会,如果用福罗特的名词来形容,可说是建立于‘超我’淫威之上。崇拜先王,敬从长老,率由旧章,遵守习惯——何一而不显出‘超我’的威风!在此四面紧包的‘超我’势力下,‘阿物’摧残已极,而个人的迈进力,个人的生机热情,也当然消磨殆尽。五四以来的种种解放运动,一方面可说是减杀‘超我’的权威,一方面也是要促进‘阿物’的发滥发洩。‘阿物’的发洩是一种极含爆发性,极含离心力的现象,——它是冲散的,不是团结的;它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然而在‘世纪的末造’,不破坏那能建设?有‘超我’万能的当年,就不得不有‘阿物’冲荡的今日。”(41)显而易见,林同济虽然讨论的角度与雷海宗略有不同,但他们的结论却相差无几:中国文化缺乏对生命力量的足够尊重,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虽然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学人的思考路径有些差异,沈从文偏重于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战国策派”学人多从学理层面上展开讨论,但这是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环境不同使然,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人的性格作出相似的判断。
无论是沈从文所说的“阉寺性”,还是“战国策派”学人所说的“超我”的淫威和“武德”的匮乏,它所导致的都是人的生命力的缺失。正因为如此,他们开出的救赎之方也是相似的。30年代开始,沈从文之所以着力于营造湘西世界,写下了《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小说名篇,原因就在于这里没有那么多“文明世界”的束缚,有的是“乡下人”的蛮性冲动。他曾经说过,“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42)因为“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43)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沈从文将这种对生命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看来,“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44)“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需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45)他甚至希望用“意志”来取代中国人所信仰的“命运”,把“生命力”的激发——勇敢与健康看作是延续“国家—民族”存亡的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成为沈从文长期坚守的一个信念。
“战国策派”学人则受到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的启悟,将意志和生命力的发扬看作是关乎民族命运的关键所在:“一个民族不了解,甚至于曲解误解‘力’字的意义,终必要走人堕萎自戕的路程;一个文化把‘力’字顽固地看作仇物,看做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间没有‘无力’之生;无力便是死。诅力咒力的思想,危险就在这里。诅力咒力即是诅咒生命,诅咒人生。”(46)而在陈铨看来,“力量是一切的中心,它破坏一切,建设一切。天才是社会上的领袖,他推动一切,创造一切。然而天才的本身,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力量。”(47)因此,林同济提倡“战士式的人生观”,陈铨提倡“英雄崇拜”,原因无它,他们在战士、英雄身上看到了“生命力”的激荡。也正是因为如此,林同济才把“恐怖”、“狂欢”、“虔恪”看作是艺术的三道母题,因为他在中国艺术家的笔下看到了太多的促人安眠的山水、花鸟,而我们我所需要的是暴风雪中的挣扎;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的生命力渐趋枯涩,而我们需要的却是生命的狂欢。因此,他们将生命力量的贯注看作是构成一切伟大文学的要件:“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就是能够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文学。文学不是好玩的东西,文学家应当有‘崇高的严肃’。末世文学家,根本想逃避人生,他们著作的流行,只能摧毁民族生命的力量……盛世的文人,气魄雄厚,力量充足,他们喜欢寻求壮美的对象。”(48)因此,在崇拜生命力量这一点上,沈从文与林同济、陈铨的诉求别无二致。
综上所述,尽管在文化形态史观、英雄史观以及对五四运动的评价诸问题上,“战国策派”学人与沈从文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但在抗战时期“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姿态、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改造传统文化的思路方面,他们的许多看法与沈从文多年来的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之处。因此,无论从事实层面,还是在思想、创作的相通性层面,将沈从文列为战国策派的一员,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至于对“战国策派”的评价问题,我们将专文予以讨论,我们相信,随着思想观念和“政治—历史”理念的进步与开放,“战国策派”应该得到更为公正的评价。
注释:
①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群众》,第7卷第1期。
②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群众》,第7卷第7期。
③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6—57页。
④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2—123页。
⑤李辉:《与夏衍谈周扬》,《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242页。
⑥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长河不尽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⑦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本文所引沈从文文章,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沈从文全集》,特此说明。
⑧“后来又有人指责沈协助编辑昆明的一份杂志《战国策》,指责它是宣传法西斯的刊物。沈坚决否认编辑过该刊,说他是编辑的确也没有任何证明。”参见金介甫:《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82页。同时参见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155页。
⑨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63—64页。
⑩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42页。
(11)王保生:《沈从文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12)温儒敏、丁晓萍:《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13)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81页。
(15)沈从文:《致施蛰存》,《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90页。
(16)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89页。
(17)范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湖南《开明日报》1941年1月9日;后收入《云南文史资料》第21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63—65页。
(19)(21)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
(20)(23)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5期。
(22)沈从文:《“五四”二十一年》,《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33、135页。
(24)沈从文:《给一个军人》,《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27页。
(25)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战国策》,第6期。
(26)范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云南文史资料》第21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202页。
(27)毛泽东等:《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解放》,第1卷第10期。
(28)《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29)《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新华日报》,1939年3月12日。
(3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群众》,第3卷第1期。
(31)《延安各界群众大会响应精神总动员通电》,《群众》,第2卷第24—25期合刊。
(32)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群众》,第3卷第3期。
(33)范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
(34)沈从文:《一种态度》,《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26页。
(35)沈从文:《给青年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21页。
(36)沈从文:《长庚》,《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6页。
(37)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3页。
(38)沈从文:《变变作风》,《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59页。
(39)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18、217,69页。
(40)林同济:《抗战军人与中国新文化》,《东方杂志》,第35卷第14号。
(41)林同济:《福罗特与马克斯Freud and Marx,a Dialectical Study》,《政治经济学报》,第5卷第3期。“福罗特”今译“弗洛伊德”,“阿物”今译“本我”。
(42)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7页。
(43)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24页。
(44)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3页。
(45)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66页。
(46)林同济:《力!》,《战国策》,第3期。
(47)陈铨:《狂飙时代的席勒》,《战国策》,第14期。
(48)陈铨:《盛世文学与末世文学》,《文学批评的新动向》,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4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