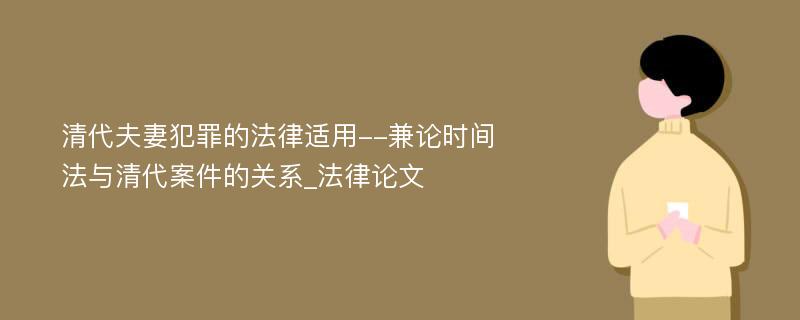
清代夫妻相犯的法律适用——兼论《大清律例》有治罪明文时律与例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例论文,明文论文,清代论文,大清论文,夫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1)06-0038-09
清代的夫妻相犯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在夫妻之间,并被《大清律例》所惩处的互相侵害行为。根据清律的表达方式,它包括夫对妻的卖休、典雇、抑勒妻与人通奸、有妻更娶、杀妻等侵害行为,妻对夫的背夫逃亡、和诱、逼迫夫自缢身死、告夫、杀夫等侵害行为。这类行为严重侵犯了清代社会中的伦理纲常、贞节观念乃至家族秩序,因此,《大清律例》对夫妻相犯规定了轻重不等的刑罚措施并予以制裁。清代的基本法律形式是律和例,律,指大清律,例,则是指条例。清王朝建立后,曾于顺治四年(1647年)、雍正三年(1725年)和乾隆五年(1740年)分别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例》三部正式的成文法典。最后的定本律为436条,附条例1049条。①自乾隆五年定本以后,至清王朝解体,律文基本不再有增损②,而例顺应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变化,至同治年间已增至1892条。③
虽然对于《大清律例》法律文本自身真实可靠性的考证十分必要,正如田涛、郑秦指出:“研究清律,切忌随意援引条例,因为对于所论的课题,这一条例,可能已是删除了的,也可能是尚未纂修的。因此,引证清律,特别是条例,一定要考其颁行年代,才能确认其法律效力和价值。”[1]点校说明对法律文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就文本而论文本的阶段。要了解一个法律文本对一段历史时期的影响,必须看它在实际操作运行的状况。“因为任何一项法律颁布后,即使它在条文上再完美无瑕,但如果没人去执行遵守,或者不被多数人所认可接受,那它很可能成为空文。而一个法律文本的实际效力从文本内容上是无论如何也发现不出来的。”[2正如郑秦所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力求作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考察,不能就制度论制度,就律例条文论律例,那样,清朝的法制无疑就是‘完美无缺’的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不但要看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更要看是如何实行的,既要找到清廷官方的表述又要找到其与社会法律生活的实际差别,努力描述出客观实际的情况”[3]自序。
因此,在《大清律例》有治罪明文时,分析清代夫妻相犯案件的法律适用,有助于考察《大清律例》对社会的实际控制情况、分析“习惯”、“情理”与《大清律例》的关系,探讨司法实践与官方和民间的表述之间的可能背离。据笔者的考察,律例有治罪明文时,夫妻相犯案件基本上严格援引律条,少数引用条例,即以律为主,以例为辅,个别情况下,以例改律、以例废律、以新例破旧例等。
一、律为主导、例为补充
何勤华教授指出:“在清代,律是基础,例是补充,一般情况下,某个案子呈送到审判官面前时,他首先适用的是律,只有在律文明显落后于形势发展或没有律文可适用时,才会适用例。那种认为例的地位高于律,在律例并存的情况下首先适用例的观点,与清代的审判实践并不相符。”[4]夫妻相犯案件的法律适用恰好印证了该观点。
(一)律为主导
律为主导,即指律文被严格适用,这在清代夫妻相犯案件中尤为突出。从刑部的这些案例汇编来看,承审官在定罪量刑时首先出现的用语往往是“查律载……”、“又律载……”、“依……律,拟……”、“自应按律问拟”等。以下仅举两个较特殊的案子加以说明:
如“妻妾失序”律条,虽一直在“本夫并未承祧两房与后娶之妻有犯”的案件中被得以严格适用,但却在“独子承祧两房,两房各为娶妻,本夫与后娶之妻有犯”的适用中经过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不过,该律条最终得以被严格适用。《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妻妾失序”律条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虽然律条规定后娶之妻应离异归宗,但是若后娶之妻与并未承祧两房夫及夫之亲属互犯杀伤时,仍要以服制科罪,因为“推原律意,有妻更娶即应离异,此礼经所谓无二嫡之义也。第此等乡愚易犯于例禁,固干断离,而其以礼为婚,于名分则为已定,与苟合买休等项不应有夫妻名分者不同。亦与以妻为妾,尊卑失序,律应更正者有别。如与其夫及夫之亲属互犯杀伤,素有尊卑服制者,仍科以服制之罪,此于严例禁之中仍寓定名分之意本有成例可循”[5]1458。由此可见,本夫并未承祧两房,后娶之妻律应离异,因此二者有犯,仍依夫妻服制拟断,但是,该“妻妾失序”律条却在“独子承祧两房,两房各为娶妻,本夫与后娶之妻有犯”的适用中经过一番周折,这主要涉及后娶之妻的地位问题。最初嘉庆十九年礼部“余万全丁忧案”将后娶之妻雷氏比照妾论,而刑部在较长时间内断案皆援引礼部成案,认为:“至承祧两房之人,愚民多误以为两房所娶皆属嫡妻,故将女许配,议礼先正名分不便,使嫡庶混淆,而王法本乎人情,原毋庸断令离异,有犯应以妾论,情法俱得平。”[5]1460且在道光三年说帖中也这么认为:“查有妻更娶,与其夫及夫之亲属有犯,仍按服制拟断之例,系指其夫并未承祧两房,后娶之妻律应离异者而言。若承祧两房,各为娶妻,冀图生孙续嗣,是愚民罔知嫡庶之礼,与有妻更娶不同。止宜别先后而正名分,未便律以离异之条。”[5]1459一直到咸丰元年,直隶司的王廷庸一案中,刑部才最终做出了不同于礼部的解释:“礼部议覆河南学政余万全丁忧请示案内,以礼无二嫡,将后娶之妻作为妾论,系专指夫之子女为后娶之妻持服而言。至于后娶之妻与夫之亲属有犯,倘竟作妾论,则案关人命,罪名轻重悬殊,办理转多窒碍。自应比依‘有妻更娶’之律,有犯仍按服制拟断。”此案最终依律条判决,并纠正了先前援引成案而不遵循律文的错误,维护了律文的权威性、连续性和重要性。
若一旦条例的表述与律文稍有不符,刑部则依律文判决,将不妥条例删除,或另拟新例以适用律文。如“山阳县民妇倪顾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缢身死一案”,江苏巡抚吴坛将倪顾氏依例拟绞监候。刑部在驳议中,阐述了律与例对于该类案件惩处的不一致之处,即律文规定“妻殴夫至笃疾者绞决”,而条例只规定“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比依‘妻殴夫至笃疾律拟绞’”,而没有明确规定“绞决”,这样就为各问刑衙门拟断绞监候留下了余地,以致适用时非常容易牵混。因此,刑部认为江苏巡抚将倪顾氏拟绞监候,与律不符。倪顾氏应依妻逼迫夫致死者,比依“殴夫至笃疾绞决”律拟绞立决。皇帝同意刑部的意见,并且颁布谕令授权刑部将“引用牵混,殊未妥协”之例文“另行妥议,改正通行”[6]355。刑部秉承谕旨,除了通行各省督抚之外,为避免援引错误,还将与律文不完全相符的原例文删去,另立了“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拟绞立决”专条以与律文相适应。
《大清律例·刑律·断罪引律令》律条明确规定:“凡(官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大清律例·名例律下》“断罪无正条”之条例还规定:“若律例本有正条,承审官任意删减,以致情罪不符及故意出入人罪,不行引用正条,比照别条以致可轻可重者,该堂官查出,即将承审之司员指名题参,书吏严拿究审,各按本律治罪。其应会三法司拟断者,若刑部引例不确,许院寺自行查明律例改正。倘院寺驳改犹未允协,三法司堂官会同妥议,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疏忽,别经发觉,将院寺官员一并交部议处。”因此,各级承审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会反复推敲案情,审慎地援引最为“允协”的律文。否则将会被追究责任。如乾隆四十四年,山东司“夏津县李化为殴逼李殷氏、赵梅氏等投身死一案”,刑部认为,所有错拟罪名的承审各官,应交送吏部照例办理,在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奉旨:“依议。其错拟罪名之承审各官著交部察议。钦此。”[6]353再如“山阳县民妇倪顾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缢身死一案”的上谕中,皇帝对审理此案失于宽纵的官员进行了追究:“此案系吴坛审拟具题,吴坛在刑部司员任内办理案件最为谙练,不应援引失当。若此使其尚在,必将伊交部严加议处。至臬司为刑名总汇,塔琦亦由刑部出邑司员简放,审拟此案,失于宽纵,殊属非是。塔琦著传旨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谕知之。钦此。”[6]356
(二)例为补充
关于例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的诏令,以及皇帝对臣下奏议等文件做出的批示(上谕);二是从刑部就具体案件所做的并经皇帝批准的判决中抽象出来的原则。[4]没有律文可引时或律文规定有不足时,承审官一般以条例为准。如“查例载……”、“又例载……”、“依例……,拟……”、“自应按例问拟”、“自应照例拟罪”等也是承审官在定罪量刑时的基本用语。例为补充主要表现为补律之不备、对律做扩张解释及补充律意等。
1.补律之未备
如律条规定本夫奸所登时杀死奸夫、奸妇,勿论。律条还规定本夫只杀死奸夫,亦勿论。但是,本夫只杀死奸妇,应否勿论,律条却无明文规定,因此就有“杀死奸妇,奸夫脱逃之例”以补律之未备。即《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条例规定:“如本夫奸所获奸,登时将奸妇杀死,奸夫当时脱逃,后被拿获到官,审明奸情是实,奸夫供认不讳者,将奸夫拟绞监候,本夫杖八十。若奸所获奸,非登时将奸妇杀死,奸夫到官供认不讳,确有实据者,将奸夫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本夫杖一百。其非奸所获奸,或闻奸数日将奸妇杀死,奸夫到官供认不讳,确有实据者,将本夫照已就拘执而擅杀律拟徒。奸夫杖一百、徒三年。”即“杀死奸夫”条条例将本夫杀死奸妇,奸夫供认不讳的情形分为三种:奸所获奸,登时杀死奸妇;奸所获奸,非登时杀死奸妇;非奸所获奸或闻奸数日杀死奸妇等,承审官吏在断案时,如遇上述律无规定而例有补充的情形,自然会照例拟断。
再如童养媳“早在宋代业经出现,以后浸淫发展,到清代已相当普遍”[7]251。清代童养婚姻的普遍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为制止溺婴、补救日后婚娶困难所作的努力。[7]6童养媳的最大好处,一是生女有人抚养,二是遣嫁婚礼简约,均是为了减少经济开支。童养媳制度对减少溺女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不少地方志的记载均可证明这一点,可以说童养媳制度是一种社会发明,是古代中国生育行为自我调节的一种机制。[8]315-316然而律条却没有任何有关童养媳的内容,徐忠明教授曾指出:“把《大清律例》翻检一过,居然没有提到童养媳的内容。……作为一种在社会上相当普遍的婚姻实践,清代法律竟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不是咄咄怪事吗?”[9]256他还引用王跃生教授的观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条件下,婚姻的缔结不是一种政府参与的事务,而完全是民间行为。一般来讲,只要未婚男女有人主婚,就可视为合法婚姻。从清代法律来看,除了对指腹割衫为亲者加以禁止外,童养婚行为政府不加干预。”[10]145因此,徐教授认为正是由于“政府不加干预”,因而法律对童养媳制度没有相应的规定。
其实,由于清代童养的普遍性,《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条例已经“舍礼从俗”,补充了律条之不备。该条例规定:“凡童养未婚之妻,与人通奸,本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并有服亲属捉奸,杀死奸夫奸妇者,均照已婚妻例问拟。”此条是嘉庆六年,安徽按察使恩长条奏,未婚妻本夫之父母、伯叔、兄弟有服亲属捉奸,杀死奸夫,请定条例一折,奏准定例。《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条例还规定:“至童养未婚妻因奸谋杀本夫,应悉照谋杀亲夫各本律拟断。”④薛允升认为:“童养妻系送至夫家,尚未完婚者。童养之名不见于古,民间贫乏之家安于简陋,遂至相习成风,到处皆然,舍礼从俗,盖亦不得已之意也。”[11]卷三十二然而,对于这些条例,薛允升还认为,“未免过重,以未婚究与已婚不同也”[11]卷三十二。如嘉庆二十二年,“直督咨:魏九杀死与伊童养未婚妻高氏通奸之缌麻服侄高风光。查高风光出继高姓,例应归宗。魏九系高风光缌麻服叔,因见高风光与童养未婚妻高氏通奸,前往捉拿,致被挣脱,并不鸣官究治,辄将高风光擅行杀死”[12]145一案,律文并无对该案惩处专条,因此,刑部的审断完全是遵照了条例的规定。
2.对律做扩张解释
《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律条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该律条赋予夫对犯奸之妻与奸夫生命的予夺权利,可谓是夫权扩张的一个极致。不过清代统治者也考虑到这种权利的存在可能会引起夫对妻与奸夫的滥杀,因此特别强调“奸所”、“登时”。
如嘉庆六年,刑部议准,纂定例文对“登时”与“非登时”进一步做出区分:“凡本夫及有服亲属杀奸之案,如奸所获奸,忿激,即时殴毙者,以登时论。若非奸所而捕殴致毙,及虽在奸所,而非即时殴毙,或捆殴致毙者,俱以非登时论。”⑤
然而,律例依然没有对“奸所”、“登时”做出明确的界定。“奸所”固然比较容易理解,但在具体案件中,其含义也较为宽泛;而“登时”本身就含义模糊,在司法实践中更会产生较大的争议。这与清代统治者既赋予捉奸人杀奸之权,又不想开滥杀之风有必然的联系。
笔者在整理刑科档案时发现,刑部为惩淫恶,对“登时”、“奸所”的解释多是扩张律文中“登时”、“奸所”的含义,并得到皇帝的批准,可以说是“从而创立了一项判例法规则,事实上完成了一项新的立法。”[4]下面简举数例以示之:
乾隆六十年“貊应瑞因妻张氏与王幅通奸杀死奸妇一案”,刑部对于“奸所”的扩大解释为:“是同坐既属恋奸,巷道即属奸所。律载‘非奸所’一条,非谓行奸必有定所,亦不必两人正在行奸之时。巷道之内,奸夫奸妇同坐一处,不可不谓之奸所;则经本夫撞获,当即忿激将奸妇殴毙,即不可谓非登时。”[6]669
嘉庆二十二年说帖,河南巡抚请求刑部“请将登时非登时界限详晰核明指示,俾得有所遵循”,刑部在咨覆中对“登时”与“非登时”之区别作了部分澄清,认为殴跌倒地致死不同于捆殴致死:“详绎杀奸例文,载有即时非即时字样,是杀奸之案总以是否奸所临时忿激致毙,并殴打时有无间断以为登时非登时之别,至倒地后殴伤致死以非登时论之语。另见捕殴贼犯例内盖事主因贼犯偷窃,登时追捕,其未经倒地之前尚虑其抵拒,故捕殴致死,既已离盗所亦拟城旦。若已被殴跌倒地,不难拘执送官,辄复叠殴致死,既无忿激可言,故即照擅杀律拟绞。而杀奸例内仅有捆殴致毙以非登时论之语,并无倒地后殴伤致死即以非登时论之文,诚以妇女与人通奸,捉奸者羞恶难遏之情有不容自己之势,其殴跌倒地例不与捆殴并论者,例文俱有深意,不能与捕贼之案一例而论也……总之杀奸之案情节百变,全在司谳者详绎例内即时非即时字样,悉心核拟,不得以忿激即时殴毙之案牵引捆殴致毙之例,尤不得以杀死奸夫之案牵引追捕窃贼倒地叠殴之例比附拟断,致开畸轻畸重之渐,所有该抚咨请分晰登时非登时界限之处,应毋庸议。”[5]911
嘉庆五年集案,刑部认为:“查杀奸例内所称奸所之与非奸所,总以本夫是否当场撞见奸情为断,登时之与非登时总以本夫有无过后转念为凭,奸所非独行奸之所,如本夫亲见奸夫奸妇同屋嬉笑,究问奸情是实,或奸夫乘间脱逃,或奸妇哀求免杀,或他人从旁解劝,事暂寝息,过后转念而杀之者,此杀非登时而不能谓非获在奸所也,登时亦非独行奸之时,如本夫外出,经祖父母、父母亲属窥见奸情,向本夫告知,究问属实,忿不可遏,并无过后转念,仓猝直前追捕奸夫,或至途中或至其家内杀之者,此获非奸所而不能谓杀非登时也。”[5]901
嘉庆十七年说帖,“登时系指获奸之时,忿起于触目之余,杀激于刺心之怒,自应原情勿论。若业经捆缚则事已稍缓须臾,并非出于仓猝,故例内指明捆殴致毙以非登时论”[5]894-895。
道光五年说帖,“至例内何者为即时,总以殴打时有无间断为断,如无间断虽倒地叠殴致毙,应以登时论,若有间断,虽非倒地叠殴,亦不得为登时”[5]907。
此外,本夫“登时获奸奸妇逃出揪回杀死”,以登时论、捉奸之人“拐所杀奸与奸所杀奸同”、“妻被奸拐本夫追捕将妻殴死”,与奸所登时无异、本夫“究出因奸怀孕即同奸所获奸”、本夫“杀奸殴未间断即属登时”、本夫“追赶奸夫无及回家杀死奸妇”,因本夫并未稍缓须臾,即没有间断,就属奸所获奸,登时而杀。[5]894、914、916、885、913、882-883
3.言明律意
如《大清律例·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律条规定:“抑勒妻妾及乞养女与人通奸者,本夫、义父各杖一百,奸夫杖八十,妇女不坐,并离异归宗。”然而律条并没有明确对“夫逼妻卖奸后,又故杀妻”的惩处。乾隆四十一年,奉天司“张二即张丕林扎伤伊妻徐氏身死一案”,皇帝认为,刑部核拟张二即张丕林扎死伊妻徐氏一案,将张二照“夫故杀妻”律拟以绞候,并不妥当。刑部奉旨后认为:“请嗣后凡以妻卖奸之夫故杀妻者以凡论,其非本夫起意卖奸者仍悉依律例办理,庶廉耻足励而情法得平矣。”[6]401此后拟定了新条例,即《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条例所规定的:“若本夫抑勒卖奸故杀妻者,以凡论。”该条例补充了“纵容妻妾犯奸”律条虽未明言但却内含之意,因为“纵容妻妾犯奸”律条规定逼妻与人通奸,奸妇不坐,但要离异归宗。那么,本夫杀死律应离异之妇,就应按照凡人杀伤惩处,新条例的规定属于罪罚较允当。
再如《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出妻”律条规定:“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辄自)改嫁者,绞(监候)。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该律条规定了夫对“背夫逃亡”之妻的嫁卖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妻从夫而居的义务。律条既然规定妻“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则“本夫逃亡三年不还”,妻或可别行改嫁,则是其律意之所含。因此,“出妻”条条例体察律意,对该律条做出了合乎人情的补充:“期约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因为“本夫逃亡不回,其妻无所依倚。夫之生死不知,归期无望,必令终守,则非人情所堪,许令改嫁,则非法令所宜,特于此微示其意曰‘三年之内’,则三年之外不同矣”[13]287-288。
二、以例改律、以例废律
《大清律例》本身是一个多层面的混合体。一般来讲,它的436条律比较道德化、理想化,而它在清末的将近2000条的例则比较实际。[14]重版代序苏亦工教授认为:“明清律因大量承袭《唐律》,其中的有些条文,特别是有关婚姻、家庭、继承等条文仍僵化地坚守儒家礼教的信条,与明清社会的实际情形不免有些脱节,明清朝廷为因应这些变化不得不在正律之外制定许多条例予以适当的变通。当这些条例与律文的规定相冲突时,明清官方采取的适用原则是‘断罪依新颁律’⑥,此条明文载在律典,由来已久。”[15]287
乾隆五年以后,由于清政府几乎不再对律文进行修改、补充,律文无法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适时作出调整,有时确实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条例则可以更好地解决律的制定者所未能预料到的特殊事情。因此,以例改律、以例废律的情况在夫妻相犯的刑科案件中还是偶有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承审官吏更加注重顺应情理与习惯。
(一)以例改律
如,《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律条规定:“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监候)。”本夫被杀,实由本妇与人通奸所致,因此,奸妇虽不知情,律亦拟绞,不可谓处罚不严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出现奸妇虽不知情,但其当时喊救与事后即行首告,将奸夫指拿到官,属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如果仍将其照律拟绞,从情理上就说不通了。因此,乾隆四十二年,遵照雍正三年原奉谕旨,恭纂条例,修改了律条规定之不妥:“凡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而当时喊救与事后即行首告,将奸夫指拿到官,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仍照本律拟断。该督抚于疏内声明,法司核拟时夹签请旨。”因为“如当时喊救,事后首告,得准夹签减流,原其尚不忘旧也”[5]838。且“以此等当时喊救,指拿奸夫之妇人,若仍照律拟绞,恐将来有犯转致畏罪不肯出首,是以谕令夹签声明,量予减等”[5]839。
再如,《大清律例·名例律上》“犯罪存留养亲”律条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笃、废)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养)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军犯准此)。”该律条规定了死罪犯存留养亲同时要具备的三个条件。由于清代统治者鼓励妇女夫亡后守贞,为对孀妇从一而终给予特殊优待,嘉庆六年,《大清律例·名例律上》“犯罪存留养亲”条条例规定:“……核其情节,秋审时应入可矜者,如有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及孀妇独子,伊母守节二十年者,或到案时非例应留养之人,迨成招时,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兄弟、子侄死亡者,该督抚查取各结声明,具题法司随案核覆,声请留养。”该条例部分修改了律条的规定,其一,条例规定了守节二十年的孀妇之子可“存留养亲”;再者,条例的孀妇守节二十年,独子留养时,勿论其老疾与否的规定,突破了律条规定罪犯之亲只有老疾方可留养的局限。
(二)以例废律
如,《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尊卑为婚”律条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虽无尊卑之分,尚有缌麻之服。)杖八十。并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此仍明律,顺治三年修改并添小注,乾隆五年删定。该律条从制订颁布之时起,就未能有效地执行,法律上的禁忌只是具文,因为民间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在许多地方是正常习惯。最终,清代统治者不得不屈从于习惯,明定条例:“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⑦《集解》曰:“凡条例大都严于律文,此条独揆乎情法,姑开一面,亦王道本乎人情也。”薛允升也认为:“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较同母异父姊妹为婚罪名虽轻,而一系有服,一系无服,亦有差等。律系均禁为婚,例则不禁此而禁彼。明洪武十七年,帝从翰林侍诏朱善言,其中表相婚已弛禁矣。特未纂为专条,仍不免人言人殊,迨雍正年间,有听从民便之例,议论始归画一矣。”[11]卷十一条例之所以能屈从于习惯,从而废律,是因为“清代习惯与法律的关系比较和谐,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冲突和对立,或者习惯法与制定法之间的二元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清代习惯与国家法律的背后都是传统儒家伦理精神,二者在维持和谐统一的社会现状、控制社会上也是一致的”[16]195。
此外,从“同姓为婚”与“居丧嫁娶”的案件中,我们可看出条例顺应习惯与人情而废律的情形。《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同姓为婚”律条规定:“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此仍明律,其律目律文小注,均顺治三年添入,乾隆五年删改。但民间并没有能够严格遵行,常出现同姓为婚之事。《清律例汇辑便览》注云:“同姓者重在同宗,如非同宗,当援情定罪,不必拘文。”所说可代表一般人对同姓为婚律的态度。[17]101瞿同祖认为:“自从姓氏失去原来的意义,同姓并不一定是同血统的标志时,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就失去原义,逐渐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法律上仍旧保留这种规定,实际上已与社会脱节,渐成具文。从《刑案汇览》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妻与夫同姓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法律所采取的不干涉主义。法律自法律,人民自人民的情形。没有一个个案是单纯为同姓不婚而涉讼的,即因其他案件而被发现,问官对此也不加追问,并不强其离异。”[17]99如直隶各县习惯,“向有同姓结婚之事,案牍中如李李氏,刘刘氏等,数见不鲜。查同姓为婚,律所不许,但此种习惯行之既久,已为社会上普遍之惯例。然皆以不同宗为限制条件。大概此种习惯,不仅直隶一省为然,即长江以北省份,亦多如是也”[18]759。
再如,《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居丧嫁娶”律条规定:“凡(男女)居父母及(妻妾居)夫丧而身自(主婚)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父母)丧(而)娶妾,妻(居夫丧,)女(居父母丧而)嫁人为妾者,各减二等。”在现实生活之中,“诚以僻壤愚民不能尽谙例禁其居丧嫁娶各条,往往违律者甚多,固不能因乡愚易犯而遽废违律之成规,亦不得因有违律婚娶之轻罪,而转置夫妇名分于不问。要在谳狱者体会谕旨,随案斟酌,核其情节轻重分别拟断”[5]449。刑部说帖云:“盖律设大法而例本人情,居丧嫁娶虽律有明禁,而乡曲小民昧于礼法,违律而为婚姻者亦往往而有。若必令照律离异,转致妇女之名节因此而失,故例称揆于法制似为太重,或于名分不甚有碍,听各衙门临时斟酌,于曲顺人情之中仍不失礼法之意。凡承办此等案件,原可不拘律文断令完聚。若夫妻本不和谐,则此等违律为婚既有离异之条,自无强令完聚之理。”[5]251
基于“同姓为婚”律条与“居丧嫁娶”律条对社会的失调,《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嫁娶违律主婚媒人罪”条条例做出规定:“凡嫁娶违律,应行离异者,与其夫及夫之亲属有犯……若止系同姓及尊卑,良贱为婚,或居丧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将妻嫁卖,娶者果不知情,实系明媒正娶者,虽律应离异,有犯,仍按服制定例。”此条是嘉庆十三年四川总督勒保题“彭韦氏殴伤彭世德身死”一案,议准定例。一方面,律文不承认“同姓为婚”与“居丧嫁娶”等的效力,另一方面,条例又不肯否认基于这种婚姻而有的亲属关系,以名分为重。该条例所注意到的与其说是“同姓为婚”与“居丧嫁娶”等的法律效力问题,不如说是杀伤罪发生以后的名分问题,该例的适用实际上是“以例废律”。如道光时周四居丧娶周氏一案,刑部的说帖只是重视居丧嫁娶可以断令完聚,对于同姓为婚根本不曾过问。[5]251再如“永顺县详报潘文科与彭氏通奸,谋死本夫彭金贵一案”,刑部对彭金贵娶同姓之彭氏没有过问,只是将彭氏依“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律拟凌迟处死,奸夫潘文科依“奸夫同谋杀死亲夫,系奸夫起意者,斩”例拟斩立决。[6]238
三、以新例破旧例
如,乾隆五十六年,“河抚题:陈张氏与王杰通奸被拐,致伊父张起羞忿自尽,将陈张氏依妇女与人通奸,父母并未纵容,一经见闻,杀奸不遂,因而羞忿自尽例拟绞监候一案”,陈张氏与王杰通奸,致使其父张起羞忿自尽,河南巡抚因陈张氏是已嫁之女,照例问拟绞监候,刑部亦照拟核覆。乾隆皇帝则认为,河南巡抚与刑部的拟断虽然属于照例办理,但陈张氏却不能因其出嫁而被从宽惩处,应拟绞立决,理由如下:
但张起之死由于伊女陈张氏与人通奸所致,与子孙因奸因盗致祖父母父母忧忿自尽者情罪相同,自应一律问拟绞决。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轻重尚可,若一关父母之生死,则不可如寻常罪犯照出嫁降服之例稍从轻减也。且明刑所以弼教,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区别,设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岂可免其凌迟,概从宽典耶,嗣后妇女通奸致父母羞忿自尽者,无论已嫁在室之女俱着问拟绞立决,交刑部纂入例册。所有陈张氏一犯即照此办理。[5]1219
刑部奉旨纂例,即《大清律例·刑律·人命》“威逼人致死”条条例所规定的:“妇女与人通奸,致并未纵容之父母一经见闻,杀奸不遂,羞忿自尽者,无论出嫁、在室,俱拟绞立决。”因此,皇帝的谕旨上升为新例,废止了旧例的适用效力。
再如,乾隆四十三年,刑部议覆云南巡抚裴宗锡题“文山县客民申张保即申忠义殴死高应美情事败露,以致伊父申茂盛、伊母胡氏先后服毒身死一案”(下文称“申张保案”)。申茂盛娶妻胡氏,所生三子。长子申张保另在他地耕种,居住相距十里。高应美打算回原籍,将店顶给别人,但因账未收清,寄住在申茂盛家,与胡氏不避嫌疑,屡为申茂盛撞见,二人因此反目。申张保劝过几次,申茂盛皆隐忍不说,但郁结成疾。申张保再次去看视时,申茂盛才将情由偷偷告知。申张保欲接其母同住,就先回去收拾。其后,胡氏被夫责逐,就至其子申张保家居住。申张保携棍往山挑柴,路遇高应美欲往其家,申张保用言阻止,高应美嗔其不应,互相詈骂。高应美拾石向掷,申张保闪过,顺用所带挑柴木棍还殴,致伤高应美囟门倒地。高应美又顺手摸取石块,申张保恐其起身殴打,又用棍头向戳,致伤高应美肾囊殒命。事发之后,申茂盛、胡氏忿激羞愧,先后服毒身死。
云南巡抚认为:申张保杀死奸夫高应美,罪应论死,且因奸情败露,以致伊父母一人先后服毒自尽,较之父母一人自尽者情罪尤重,将申张保拟绞立决。刑部核覆同意。但是,乾隆皇帝却认为“实未允协”、“未得事理之平”:
将申张保问拟绞决固系按律议罪,而揆其情节,实未允协。凡子犯罪致令父母自尽拟以立决者,原为其子违犯教令及身犯不端之事,致累其亲忿恨自戕,此等孽种断不可复留于人世,例意显然……是此案衅由伊母胡氏与高应美有奸,淫恶欺凌,实为为子者所宜恨。且申张保始而劝解其父,继复接母同居,并无不合。迨后奸夫欲往其家,明系图奸其母,此而再不心生忿恨,任听其母与人苟且,则竟无复廉耻之心,且将置其父于何地乎?是申张保之殴死高应美实出于义愤,殊堪矜悯。而申茂盛、胡氏之死由于奸情败露,忿愧轻生,并非申张保贻累。若变予以立决,未得事理之平。但非于奸所杀死奸夫自不能免罪,拟以绞候亦足矣。此本著交九卿,会同该部另行妥酌定例具奏。嗣后遇有此等案情,即照新例办理。[6]266
刑部遵照上谕,拟定新例,即《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条例规定:“凡母犯奸淫,其子实系激于义忿,非奸所登时将奸夫杀死,父母因奸情败露忿愧自尽者,即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绞监候本例问拟,不得概拟立决。”对于“申张保案”,按照原有条例,子孙罪犯应死及谋故杀人事情败露,致使其祖父母、父母自尽者,应拟以绞立决,因此,云南巡抚照例将申张保拟绞立决,刑部也同意了该抚拟断。但是乾隆皇帝的谕旨却突破了旧例的适用,并成为新例。
由上述两例,我们也可看出两点:首先,一般情况下,皇帝的意见都能得到刑部的重视和执行,创设新例废弃旧例,主要是皇帝意志所定。这种以新例修改旧例的判例,“实际上是通过颁布新例开创了一项新的判例法原则,有时还会从这种以新例破旧例中诞生一系列新的条例”[4]。其次,还能看出例的优势所在。但与此相联系的是,“例的存在又常引起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和困难。一方面,例通常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的事项,越此一步,即失去适用意义;但另一方面,例一旦被收入法典,它也会像律一样具有某种稳定性,结果有时例在其针对性已经丧失之后还保留在法典之中”[19]47。如《清史稿·志一百十七·刑法一》称:“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至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的确,如“申张保案”后拟定的新例,以后再没有得到适用,难怪薛允升会说:“此条专为杀死奸夫后,父母忿愧自尽而设。第云非奸所登时照例拟绞,不得加至立决,则奸所登时之案,自可无庸拟绞也,与诉讼门条例参看……然究系绝无仅有之件。”[11]卷三十二
此外,虽然皇帝的意见都能得到刑部的重视和执行,但案件通过地方到中央层层的审转,已经让皇帝改变原审的法律意见的情况减到最低的程度,而且刑科题本又是经过精心制作高度格式化的公文,其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往往能与法律意见构成切合的因果关系,以及面对数量庞大的刑科题本,皇帝完全不可能事必躬亲地逐案审核,与刑部官员一较长短。因此,在一般性的夫妻相犯刑案中,若非是确实事出有因,或出现足以推翻原案情的新事证,或出于敦清伦理风气、情法得以允协的需要,皇帝通常相当尊重刑部官员的意见。正如郑秦认为:“作为封建社会末期专制权力极端强化的清代,皇权对于司法的作用,又有其独特之处:概括起来说,就是清代大多数皇帝始终牢固地把国家最高司法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保证亲自行使,但又大体上能使其权力的行使‘符合’法定的程序。”[3]73皇帝还常常提醒各级司法官吏体察其维护法律尊严、保证执法公正的良苦用心。在“申张保案”中,乾隆皇帝批示:“朕综理庶狱,无论案情钜细,悉为反复权衡,折中至当。如其子自作罪恶,致亲忿激轻生,则当立正典刑,以申明刑弼教之义。若似此案之杀奸因雪耻而成,亲死非波累所致,则不宜即予缳首,致乖明慎用刑之文。内外问刑衙门并当深体朕意,慎重听谳,并将此通谕知之。钦此。”[6]266
注释:
①关于学术界对顺治律的颁布时间及雍正律的颁行时间的争议,详见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②郑秦先生通过研究,(即“顺治三年律考——律例的继续和变化”、“康熙现行则例考——律例之外的条例”、“雍正三年律考——律文规整和集解”、“乾隆五年律考——律例定型与运行中的条例”)发现,《大清律例》的律文即使在乾隆五年以后,也还是有一些细微变化的,并不能绝对地看待“万世成宪,不再更易”的说法。参见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③“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而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清史稿·志一百十七·刑法一》)。
④该条是道光二十三年,安徽巡抚程雷採奏宋忠因奸谋杀未婚夫查六寿身死二案,附请定例。(参见[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十二,“杀死奸夫-35”,光绪三十一年京师刊本)
⑤薛允升认为:“此例虽系明立界限,究竟不甚妥协”及“此处非登时一层,似应删去。”([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十二,“杀死奸夫-17”,光绪三十一年京师刊本)
⑥当律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一致时,《大清律例·名例律下》“断罪依新颁律”律条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已前者,并依新律拟断。(如事犯在未经定例之先,仍依律及已行之例拟断。其定例内有限以年月者,俱以限定年月为断。若例应轻者,照新例遵行。)”
⑦《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尊卑为婚”条条例,雍正八年定例,乾隆五十三年修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