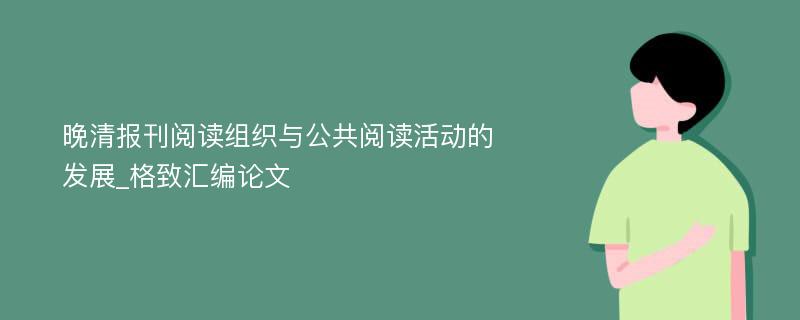
晚清阅报组织与公共读报活动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2-0132-12 与私人读报活动的个体体验不同,晚清时期,个体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公共空间”的阅读活动,则展示了公共阅读的社会价值。宽泛意义上的阅报组织从现代报刊产生之初就已经出现,比如早期的报馆就具有公共阅读的某些功能。后来一些书馆、书院、学堂、学会、官衙创设书报阅览室,使公共阅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清末阅报社的发展,则为更多的读者提供了读报的机会,推动了公共阅报的大众化,以达到广见闻、开民智、树新风的目的。阅报社的广泛开设,与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有关,也与地方社会各种势力的价值取向及文化话语权有关。从组织建设与组织传播的角度看,创设面向大众的阅报社,需要资金、人力、场地等基本条件,从而涉及权力控制、资本筹措、阅读空间、社会价值等方面的问题,而读者在公共场所的读报活动,则具有丰富的社会意涵和文化价值。 一、甲午之前阅报场所发展与公共读报方式的演进 这里所探讨的报刊“公共阅读”,主要从报刊传阅的角度上考虑,一般而言,报刊如果置于公共场所,被不同的读者所阅读,就具有公共阅读的性质。从这个层面看,鸦片战争之前,梁发在广东科举考试之际所散发的宗教书刊,对于参加科考的士子而言,就具备公共阅读的某些特点。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之际,下令收集并翻译粤澳出版的报刊,由于需要聘用相关人员进行新闻加工,也由此具有“一报多读”的特点。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号虽然仅印刷了600份,但是,由于在广州的外国人向中国人大量散发,所以后来又加印了300份。据《中国丛报》调查,甚少有华人出资订购,但辗转获得,阅读之后,多如称道。①一些读者免费获得的刊物,就有可能被其他读者推荐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阅读。但是,从总体上看,鸦片战争之前,集体性的读报活动还非常少见。 早期的报馆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报刊,使一些报人兼具读者的身份,有机会读到多种新式报刊。如墨海书馆于1843年成立后,便成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翻译和出版中心,它广泛收集各类西方书报,尤其是加强与至沪轮船的联系,获取西方报刊的大量新闻。《六合丛谈》的“泰西近事述略”,便是翻译的西方新闻汇编,其第二期的新闻中就声称“火轮驿船以林至沪,驰递泰西诸札”。②而麦都思虽然在香港创办《遐迩贯珍》,但他长期定居在上海,因此,墨海书馆便成为这份刊物在上海的发行中心。其时,王韬、李善兰等“秉笔华士”都在墨海书馆任职,有机会阅读《遐迩贯珍》,而其他香港报刊也通过墨海书馆在上海发行,这在王韬的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由于麦都思、慕维廉、韦烈亚力等多名传教士大力译介西学和编撰书报,在馆内工作的华人助手便有机会阅读来自西方和香港的书报,而郭嵩焘偶尔造访墨海书馆,便能够获赠《遐迩贯珍》,说明墨海书馆的确藏有不少当时出版的中文报刊。在1850年代,尽管传教士报刊在内地的发行并不理想,但是,墨海书馆却凭借其获取海外新闻和传播文化的优势地位,将现代报刊作为“公共读物”置于馆内,至少让华人助手有机会阅读新式报刊。从这个层面上看,王韬等人的读报活动,体现了“公共阅读”的某些特征,他们是借工作之便接触到各类报刊,尽管墨海书馆可能没有书报借阅的条例,但它体现了新式书刊组织化传播的某些特征。 1860年代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步推行,“新闻纸”便成为洋务派人物了解西方社会的重要窗口。在一些洋务派代表人物的衙门中,订阅报刊便成为一项公共事务。曾国藩、刘坤一、李鸿章等地方大员,注重了解国外时局,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国际资讯。这就为中外报刊进入官方机构提供了条件。如薛福成自1865年进入曾国藩幕府后,通过阅读“外国新闻纸”,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日本废藩府、日本内战、明治维新、朝鲜内乱、美国南北内战、布法战争等国际新闻,通过阅读《香港新报》等中文报刊,了解国际贸易状况。正是由于薛福成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为他以后成为驻外使节创造了条件。而在1872年前的4年,薛福成一直在两江总督衙门担任幕僚,他所看到的中外报刊,应为总督衙门所订阅。除了薛福成之外,其他官员和幕僚也有机会看到一些报刊。与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也在曾国藩幕府看到了大量报刊。同治丁卯年(1867)十一月二十一日,吴汝纶在日记中记载:“是日见新闻纸,谓法国与布国(普鲁士)战,是西洋各国有不和之征,中国之利也。”③吴汝纶关注的布法战争,延续了几年,同治十年(1871),薛福成在日记中也多次记载了布法战争的进展,如二月二十五日记道:“新闻纸电报云:布、法议和,日耳曼军皆退出巴黎斯城,布相亦已回国矣。”④由此可见,两人都是在两江总督衙门通过看报纸了解国际时政,而两人对西学的了解与平时的广泛阅读有着直接关系。两江总督衙门所订购的书报,对于曾国藩的幕僚们而言,具有“公共读物”的性质,这是当时幕府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洋务派较为开明的表现。 与衙门内报刊局限于一定层次的少数读者不同,随着商业报刊在街头的出现,一些娱乐休闲场所为了招徕生意,也开始订阅报刊。1870年,上海福仙园茶馆所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本茶馆有字林洋行本地新闻纸给茶客看视。凡贵客来本馆饮茶者,轮流请看,可也。”⑤这则刊登于《上海新报》第一版的广告,所指的“新闻纸”就是当时由字林洋行所创办的《上海新报》。然而,在此之前,以《上海新报》每期不到1000份的发行量,要大量供应给各处茶楼,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1870年代之前,有机会在公共场所阅读“新闻纸”的读者是较为少见的。 在1870年代,随着《申报》等商业性报刊的发展,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报刊进入公共场所的机会大增,尤其是《申报》在城内重要商铺设置代售点,方便了普通民众购阅。早期《申报》标榜其读者群体以“市肆之人”为多,并声称:“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⑥早期《申报》对店铺的看重,是由于当时邮政不发达,报纸传递不广,而店铺是人群聚集之所,置一张报纸于其中,顾客便有可能“随意观看”。由于报纸提供了一般人难以知晓的新闻,而店铺为顾客营造了一种“场域”,通过读报或者听讲新闻,顾客可以获得许多重要新闻和商业信息,也可以参与到“公共的闲话”讨论之中。因此,对于许多店铺而言,放置一份《申报》,则意味着营造了一种文化景观,报纸不仅供顾客围观,还成为一种资讯的象征,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传教士将学校作为报刊传播的重要场所。中国本土教会书院的发展有近70年的历史,从1858年至1900年,是教会书院的兴盛期。⑦教会书院是传教士从事基督教教育、介绍和传播西学的中心,为新式报刊的组织化传播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1875年,福建厦门的外国传教士与商人在创建博闻书院时,就注重报刊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购备《万国公报》、中国《京报》、《中西闻见录》、上海《申报》、香港日报及各处新报,并买译成华文泰西格致各学书籍。存于院内”。开辟了供社会各界免费阅读的图书室。并对阅读书报作了具体规定: 凡来看书之士,须各安心静坐观阅,不得言语喧哗,以及谈说闲话,倘如不知自爱者,面斥莫怪。本书院内所有各书各报,欲看之人,俱请来院阅看。无论何人,一概不准借出。倘有无耻之辈,私自窃取出门,一经发觉,定照窃律究治。本书院各书各报,各有一定处所安设,凡来看书看报之人,须在原处观看,不可参差翻乱,以及东走西观,漫无定向。如此处安设之书及报,不得携至彼处安放,观毕仍归原处,以免紊乱难查。⑧ 上述条规,具有现代图书室阅读条例的基本内涵,与之前设于报馆或官衙的报刊不同,博闻书院的图书室面向社会开放,虽然限于“仕宦绅商”,却表明当地读书人只要办理借阅手续,便可免费阅读。因此,博闻书院可以视为现代图书馆的雏形,其基本功能在20多年后的阅书报社中大体得到延续。 1876年,傅兰雅在格致书院创办《格致汇编》,使报刊出版与学校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傅兰雅在《格致汇编》的创刊号上告知读者:“凡欲定买《格致汇编》,或有疑问之事者,祈寄信至上海格致书院内《格致汇编》馆可也。”⑨格致书院集教学、研究、出版为一体,使学生能够广泛阅读新近出版的各种西学书报,这显然有别于传统书院以“经典”为中心的阅读范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以格致书院为代表的教会书院,将现代传媒引入教学空间,使学生有机会通过公共阅读的方式获得西学知识,这是教会书院对现代报刊阅读的一大贡献。而本土书院生徒有机会读报,一般认为是《时务报》创办后,由于地方官员颁令订阅才有可能。 在1870年代,尽管统治者对新式报刊整体上持排斥态度,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开明官员对现代报刊的态度有了极大的改变。早在《申报》创办之初,当时的总理衙门就有订阅,郭嵩焘在出使英法之前,于光绪二年(1876)二月二十九日,“上兵部及总理衙门,并致吊库仁龛之弟,见《申报》。”通过读报,他得知“黎召民去岁议设立伦敦洋行,已经定议”。⑩郭嵩焘当时能够在总理衙门看到《申报》,说明它是一种置于官厅的公共读物,有兴趣的官员是可以免费阅读的。而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张荫桓、李经方等驻外使节,在使馆内经常收阅从上海寄来的《申报》,说明当时的使馆已经将《申报》作为了解国内动态所必备的读物,驻外使节至少都有数名随从,尤其是充任翻译和文案的随员,需要代拟文稿,阅读《申报》应成为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早期的《申报》能够引起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当朝显贵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地方督抚衙门是有可能订阅的。而他们读报后对某些新闻的评论与反应,也表明某些高级官员注重报刊舆论对他们名节的影响。这些督抚们所阅读的报纸,是可以在他们的下属和幕僚中传阅的。而衙门中的读报活动,也具有“公共阅读”的某些特征。 1880年代之后,新兴的商业性报刊都比较注重在公共场所设置代售处,如1887年,《广报》在广州城内的唯一派报处就设在“双门底圣教书楼”(11)。1892年,《中西日报》在广州城内设立6个“派报挂号处”,包括“本城黄黎巷福昌书信馆、同兴街万泰打饷店、杉木栏逢源席店、马鞍街美南鞋店、双门底圣教书楼、西门口永盛号”。(12)圣教书楼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设,是当时广州新学和新式报刊传播的中心。根据冯自由对圣教书楼的记载:“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类,皆尽量寄售,实为广州惟一之新学书店。”(13)这几种报纸将主要的发行点设立于传播新学的圣教书楼,在报刊阅读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与之前《申报》等商业性报刊主要以店铺为代销点不同,广州圣教书楼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书报销售中心,由于与传教士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受到特别的关照。作为输入新学的重要窗口,圣教书楼无疑成为开明士绅的向往之所。《广报》、《中西日报》乃至《万国公报》等报刊在此销售,就是凭借其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受到读者的关注。从这个层面看,报刊发行从店铺走向书楼,在文化空间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以前在店铺发行,报刊以启发“市肆之人”为荣,以下层人读报为销售口号,但从“精读”的角度看,下层民众识字不多,对报纸的理解非常有限。一旦报纸“走”向书楼这一新的文化空间,就成为读书人关注的精神产品,其对读书人的直接影响就更为明显。因此,到书楼读报与买报则具有明显的公共文化消费的特质。 二、维新前后的阅报组织与读报活动 维新时期,全国各地学会将创办报刊作为其重要的工作内容,许多学会附设报刊,以鼓吹新政,提高学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湖南的南学会以讲学、集会、研讨、阅读为重要内容,甫一创设,就对公共阅读问题十分关注。《南学会申订章程》明确规定:本学会所藏书籍,准人领取阅书凭单,入内浏览……自本月十五日起,愿阅报者,照单领凭择观。(14)其时,南学会订有26种报刊,共计89份,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全国发行的主要报刊。南学会根据报刊的性质决定所订报刊的数量,如维新报刊《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报》等各备10份,《申报》、《沪报》等商业性报纸则仅备1份。由此可见,南学会所开辟的阅览室,将中文报刊作为公共读物提供给公众阅读,这与单个读者的私人阅读有着很大差异。读者来到南学会的阅览室,需要办理借阅手续方可入内,并需要遵守阅读规则,由于有许多读者“在场”,读报纸就具有共同的场域感,读者在读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公共阅读的诸多好处,如读者通过阅读不同种类的报纸,对各报的内容与形态有着直观的比较和借鉴,读者的思想与观念随着报纸的“流动”而不断变化。对于平时难有机会接触报纸的读者而言,阅览室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而那些经常来阅览室读报的读者,每次读报又成为一种仪式,读报纸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和文化信仰,报纸的“公共展示”为阅读的集体化、规范化、仪式化创造了条件。 维新前后,面向民众开放的公共阅报社开始出现。阅报社是进行报刊阅读推广的重要组织,其创办的初衷源于普通民众没有读报的习惯,又无力或不愿购买报刊,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经常阅读报纸,创办阅报社便是有识之士的一项公益性活动。创办阅报社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进行社会启蒙,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何在近代中文报刊发展了数十年之后,才有阅报社的称谓。而教会书院购置书报供给公众阅读,为何未能进入阅报社的研究视野。从阅报社产生的机理看,它与报刊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北京较早创立的日新阅报社在周年纪念时,撰文指出:“去年(1905)的今天,本社开办,在那时候,没想到准能立成。阅报处本是一个新花样,庚子以前,谁也没听说过。”(15)尽管这是从北京的情况谈到阅报社的状况,但是庚子以前很少有阅报社的设立,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因此,李孝悌认为,阅报社的建立成为一种风气,大概是1904年以后的事情。(16)这段时期白话报刊发展较快,一般认为是阅报社进一步将白话报刊引入下层社会。 但是,仅仅将白话报刊与阅报社视为因果关系可能有失偏颇。在维新时期出现的各种学会,也曾订阅报刊供会员阅览。如湖南的南学会所订购的26种报刊,除了《启蒙报》之外,其他报刊并非白话报刊。而维新时期,一些新式学校和书院已设有阅报室。如1898年,鲁迅在矿路学堂读书时,学堂已设立了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17)。与鲁迅一样有阅读新式报刊经历的学生,在维新时期并非个案。如钱均夫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于1900年与同学组织励志社,并设立书报阅览室。“各同学将自阅之书报、杂志,如旧的《时务报》等,新的《清议报》(后改为《新民丛报》)等,《译书汇编》及有关传播知识之书籍,置诸书架,各同学可于课后来借阅。”(18)浙江求是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湖北两湖书院当时都订有《时务报》等新式报刊,这些书院学生读报的机会便大大增加。当然,维新时期各学堂、书院所开设的阅报室,很少面向社会开放,其公共阅读的功能尚不明显。但也有热心公益者创办面向公众的阅报会,如南京东牌楼某报房,“创设阅报会,购办沪上各报,无不应有尽有,以备有志维新者得就近取阅”(19)。另外,维新时期地方官衙订阅了报刊,一些官员能够有机会读报,但这些报刊仍然不面向民众开放。因此,许多“阅报处”并不具有广泛的公共性与免费阅读的功能。维新之后,一些新成立的学会,往往会订阅报刊,促进会员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如1904年成立的沪学会,就将“补习科育、普及教学、阅览书报、运动游息、招待客员”(20)作为其主要功能。显然,此类学会所附设的书报室,为公共阅读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公共阅读的历史看,早期的报馆订报具有明显的行业性和排他性,读者仅限于报馆同人。后来的官衙订报,其读者也主要是衙门内的官员和幕僚。之后的一些商业店铺代理售报,虽然为读者的集体阅读提供了条件,但并非免费阅读。一些书院、学堂所订阅的报刊,也不面向社会开放。厦门博闻书院面向读书人开放,可以说是近代公共阅读的一个重要起点,可惜之后的教会书院并未广泛设立类似的机构。而维新时期的学会办报,虽然也注意到报刊的轮流阅读问题,但少数阅报室也仅对会员开放。进入20世纪后,随着各类阅报社的创办,不限制身份的公共阅读才真正兴起。 三、20世纪初官办阅报社与读报活动的推广 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报刊成为传播新政的重要媒介,上至中枢大臣下至地方官绅,对于报纸的作用与价值都有着新的认知。利用政治资源推广报刊阅读,成为官方创办阅报社的主要动力和目的。清末的阅报社有官办和民办之分,李斯颐统计清末的220家阅报社讲报所创办者身份中,官员(含政府机构)占35.5%,士绅(含青年会、学生会、商会等民间社团)占57.39%,市民占7.1%。(21)这一些统计还不太完整,但是总体上反映出清末阅报社的性质。虽然从总数上看,官办的阅报社数量要少于民办,但是,官办的阅报社大多集中在城市繁华地带,其规模与影响力往往较大。而民办的阅报社,虽然源自民间人士的捐助,但其创办则需要通过官方的审批,且对具体营运有着一定的制度约束。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民办阅报社难以持续发展。因此,阅报社作为公共阅读组织的存在,应该看作清末新政在施行过程中的新现象。 尽管维新之后清廷加强了对报刊的管控,但是在《苏报》案之后,随着各类报刊的不断增多,尤其是留学生报刊和革命报刊的发展,清廷对报刊言论防不胜防。统治者认为一些以革命排满言论而著称的报刊,“致阅者惑于革命、自由之谬说”(22)。而报刊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逐步为统治者所关注。如一向仇视报刊的慈禧太后,也开始关注报刊新闻,“命李大总管订购各报,并饬姚宝生于每日恭请平安脉后,即于驾前诵读各报”(23)。军机处也设立阅报处,“派军机章京四员,逐日轮流阅看各种报纸,凡有关本处事宜以及有关国计民生者,皆随时择出,呈堂阅看”(24)。北京工艺局“在局司事各员自行捐资,广购报纸,设立阅报处”(25)。所谓上规下随,最高统治者和中枢大臣注重阅报,地方大员自然不敢怠慢。对于各地创建阅报社,地方大员一方面具有批准监督之责,另一方面又可凸显自身政绩,只要新设的阅报社遵守官方的规定,地方官员不仅乐观其成,还利用各种机会加以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出现的大量官办阅报社,以州县一级官员为主要创办力量,其中县令所占比重最高。一般而言,当时的省会城市一般都有报纸出版,其他报刊发行量也相对较高。省一级官员深知“劝民阅报”对于通晓时务的重要性,并从行政上加以推动,“直省各大宪札饬各府厅州县晓谕绅商士庶,观阅报章,其培植人才之意至切”(26)。但在全省政务中,读报纸毕竟不是最急于要解决的大事。对于督抚大员而言,捐立阅报社尚需要考虑时效和实际运作问题,对他们的政绩难有直接的影响。但州县官员在具体执政的过程中,就直接面临民众“见闻不广、智识不开”的问题。许多穷乡僻壤尚不知报纸为何物,“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将何以鼓舞其精神,激发其志气”。(27)倡导读报活动,不仅有利于开发民智、改变民风、推广新政,也有助于地方官凸显政绩、树立亲民形象、获得政治资源。加之他们与地方士绅接触的机会较多,对创设阅报社的公益活动自然加以支持。如河北霸州知府认为“欲通今者,莫若阅报”,与当地士绅商量,“于州署大堂左侧设立阅报处一所,拟定章程,购储各报,每日令人进处阅看”(28)。郑孝胥在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期间,创办学社,并订阅《外交报》、《大陆报》、《国粹报》、《东方杂志》、《万国公报》、《中外日报》等各种报刊,“每报到,用纸大书‘本社寄到某报第几号’,粘于门外以晓众,十日内不得借出学社”(29)。这个学社兼具阅报社的功能,且对报纸借阅有严格的时限规定,主要考虑到报纸阅读的时效性和读者的阅读需求。但是,清末由府州一级长官所创办的阅报社数量不多,相比而言,在以知县为主体的官员主导下,清末县一级阅报社得到了快速发展,是官办阅报社的主流,其背后蕴含的政治逻辑耐人寻味。 知县创设阅报社,一般都以“养廉银”作为资金来源。如山东诸城县令在禀告设立阅报社时,就声称“房屋之租价,管理之人之薪工,以及购备各报之资……皆由卑职捐廉自备”(30)。河北元氏县县令鉴于本县风气不开,“特于城内南街筹设阅报处一所,捐廉购备各种新闻报章,专供众览”(31)。河北井陉县令在拟办阅报社中承诺,“社内器具以及一切茶水夫役工食,皆由知县担认,筹款给发”(32)。山东高邑县令在县城毕公祠设立阅报处,各报由他“按期选购”(33)。河南忻城县令租借“闲废官厅,略加修葺”,并捐养廉银,“设阅报社一处,将各种报章纵人观览,不取分文”(34)。浙江桐乡县令徐汉澄,“采办各种报章,在学宫后创一阅报社”(35)。这些有关地方县令捐资创办阅报社的报道,成为当时官方新闻的一大亮点,这不仅在舆论上为这些县令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地方官重视阅报社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各地知县纷纷设立阅报社,是地方社会的一件大事。由于有地方大员的鼎力支持,阅报社作为新的公共阅读场所,成为一些读书人新的文化消费空间。作为地方官员推动的文化工程,阅报社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阅读需要,还具有“文化坐标”价值,在辨别政风民风方面也有特殊的意义。1904年至1907年间,正值预备立宪与地方自治之际,地方官员将创建阅报社作为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也视之为地方政绩工程向上级官员呈文汇报,以捐养廉银展现自身热衷公共事业的形象,从而对上可以获得一定的政治加分,对下可以获得亲民的美誉,目的是“使学者诚能大者识政,小者识艺,四民皆有振奋自强之心”(36)。而当时各类报刊尤其是官报对这些捐资设阅报社事迹的报道,进一步提高了这些官员的知名度,并在官场形成了“从众效应”。 从当时的县级官办阅报社的报道情况看,此类官办阅报社主要集中在京津、山东、河北、河南、吉林等省,南方省份的报道相对较少。初步统计,长江以北的阅报社占全国总数的80%以上,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地则鲜见官办阅报社的报道。从报刊分布的角度看,由于维新之后的数年,南方报刊发展较快,尤其是两湖、广东与江浙地区的地方报刊数量较多,县一级的报刊发行市场已初步建立,一些乡镇邮局亦可订阅报刊。从彰显政绩的角度看,南方地方官员捐建阅报社的效果可能不太明显。而北方报刊发展整体水平较低,从北方各县阅报社所订报刊的种类看,京津出版的各类官报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北洋官报》出版之后,各官办阅报社争相订阅,官办阅报社所订其他官报的比例也较高。如山东高邑县令在县城毕公祠设立阅报处,订购的报刊有《北洋官报》、《北洋法政报》、《商务报》、《政治官报》、《学报》、《农话报》、《学部官报》、《法政官话报》、《警务白话报》、《农务报》、《顺天时报》、《天津日日新闻》。(37)山东利津县令设立阅报处,购备各地及农学、商务各报,陈设厅内,任人观览,以开风气。(38)河北万全县成立的官办阅报所,订《北洋官报》、《天津日日新闻》、《京话日报》诸报及《教育杂志》数份。(39)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官办阅报社很少订阅南方地区出版的报刊,尤其是《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大报,在北方的官办阅报社难得一见,至于当时在各类学堂流行的留学生报刊,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等,官办阅报社更是不太可能触犯禁令而订阅。1905年之后的革命性报刊,则是官方严厉禁止订阅的读物,显然不可能在官办甚至民办阅报社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北方各县县令倡建阅报社,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一方面他们要忠实执行新政的具体措施,通过阅报社进行政策导向,起到“上情下达”的作用,从而为地方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通过“选择性阅报”,把当时的“异端邪说”排斥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外,尤其是让普通民众减少接触“革命排满”思想的机会,从而维持满清政府的切身利益。如四川江安县教谕傅廷玺、合江县教谕傅崇榘在禀告总督岑春煊开设阅报公所时,特别表明“将奇邪淫诐之报,并不许阅,以免坏风俗而丧人心”(40)。其“正人心,避邪说”的目的十分明确。尤其在1905年前后,清政府发动“预备立宪”运动,地方官员积极响应,通过发动民众阅报,“使民间先具政治思想,然后及于自治,以为他日宪政成立之基础”(41)。之后的一些阅报社以“祛旧染而启新知,化成见而不致阻力于宪政前途”(42)为目的。显然,地方官员的政治导向非常明确,将劝民读报与推行新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四、民办阅报社与读报风气的延展 与官员比较注重政治目的不同,地方士绅设立阅报社的自治意识和文化服务意识要强烈得多,体现了“绅权”在基层社会的延伸。民间力量参与创办阅报社,与官方的导向不无关系,尽管士绅商民创办阅报社大多是自发的,但如果没有地方官支持,就很难得到制度保障,尤其是要拿到省级提学司的批文,需要地方官专文上报。而民间阅报社的创办也与地方官的政绩有关,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民间阅报社推广读报、开通风气与宣扬新法,进而为地方官施政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如江苏丹阳书报社以“增进一群之知识,完全全权之人格”(43)为宗旨,体现了士绅对群体利益的高度关注。因此,各地地方官在上报阅报社时,都对民间创办阅报社大加赞赏,以期与士绅形成合力,共同维持地方社会的利益。如四川江北厅上报阅报社的禀文,就受到总督的褒扬,认为“筹划周详,实心任事,查阅训词,亦甚质朴中肯”。并要求当地官员“督饬绅董等认真办理,以期教育普及”。(44)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对丰润县民间捐建阅报所予以奖励,并批文确认:“该县教员郑赞清嗣母刘氏捐制钱五百吊,应准给予‘名垂彤管’匾额一方,并给予其子郑赞清六品功牌一张。捐钱二百吊之刘伏生等二名,准给予六品功牌二张。”(45)官方对捐建阅报社的民间人士进行奖励,有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尤其是督抚对辖区阅报社的态度,对民间人士创设阅报社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促使州县地方官员将之视为辖区的重要新政措施,从各方面加以扶持和引导。 1904年之后,各地民间阅报社蔚起,新办的阅报社大多宣布“免费阅报”,并以“开通风气”为宗旨,以此吸引民众的关注。以北京为例,1906年6月27日,《大公报》调查阅报社共有26处,(46)而到了1907年,各类阅报社的总数累计达到45所。(47)其中大多数为民办阅报社,这些阅报处的设立者包括退休官员、商人、医生、教师等不同职业者。其他地区的民办阅报社,有一人独立出资者,有集合同志捐资者。如天津沈家庄的张文治联合本村佟春泉等五人,各捐资购办各种日报,并就张文治自有房屋腾空,安置桌椅,为阖村人民阅报之所。(48)福建福州黄某捐资创一阅报社。湖北咸宁某君购就书报多种,设立阅报处一所。四川锦竹陈象山、彭温如诸君汇合同志,设立益闻阅报公所。(49)山东曲阜近经东洋留学生陈宪镕氏函商在籍圣裔孔广修氏,创设阅报馆于该处。(50)山东威海华商松江沈君、江宁朱君、登州柳君等创设阅报社一所,名曰威海阅报社。江西南昌汪仲潜、方仲藻诸君发起于樟树下地方,创设普爱阅报社。(51)广东东莞“有志士多人组织一阅报社于石龙”。(52)福州阅报社由于“社中志士实力讲求,”“诚足为开智之先声,广闻之要旨矣”。(53)以上所举的这些阅报社,分布于全国各地,清末数年,创办阅报社已成为民间社会的风气所向。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阅报社由“志士”创办,志士应该是没有士绅身份,而思想、作为先进的平民。(54)这说明阅报社的作用与价值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认知。从总体上看,民间力量捐资创设阅报社是为了“开通风气,增进文明,使人增长知识,通晓时务”,(55)可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多一阅报人,即多一晓事人开通风气,断以此举为要着,且又简便易行,所以亟亟兴办”(56)。社会各界创设阅报社的热情,由于得到了官方的鼓励与回应,与清末十年废科举、改书院、办学堂、废旧俗、树新风等举措融为一体,成为趋新之士关注的重要公益领域。 应该看到,民办阅报社对报刊性质和宗旨也较为关注。如《北京阅报社规则》就指出:应择忠君爱国、合群保种、知耻自强之报为主义。此外如怪诞不经、驳杂不纯诸报,一概不备。(57)在符合“宗旨纯正”的原则下,民办阅报社在订阅报刊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如民办的北京西城阅报社所备各报,在京出版的有《中华报》、《京话日报》等类,在外埠出版的有《汉报》、《外交报》等类。(58)民办的北京公益阅报社订有“《大公》、《北京》、《中华》、《直隶》各报纸多份”。(59)北京的《华字汇报》设立阅报处,“得旬报日报四十余种,始犹以为少也”(60)。1907年,吉林的一家新开阅报社,“将各报订购二十余种”(61)。天津沈家庄的乡村阅报社,也订有“《民兴报》、《北方日报》、《时闻报》、《天津白话报》、《中外实报》各一份”(62)。这表明阅报社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订阅到当时出版的各类报刊,而从报刊的类型看,并非是白话报刊占主导,各地阅报社一般都比较注重订阅地方报刊和有影响的大报,一些阅报社还广泛订阅商业性、行业性、消遣性报刊。阅报社订阅不同类型的报刊,说明其服务对象并非是完全针对下层社会,而是考虑到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但是,检看当时阅报社的报刊名录,没有革命性报刊出现。因此,在阅报社这一公共空间,阅读的自由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对于具体的阅报社管理,在地域上可能会有所区别。 20世纪初期,除了大量的阅报社之外,一些酒楼茶楼妓院与娱乐场所也购置报刊,供客人空闲时观览。1900年,钱均夫与同学集资订阅《杭州白话报》20份,分送给庆春门外坿郭之茶坊酒肆。(63)显然,这些求是书院的学生热心于推广白话报,希望普通民众有机会接触新式传媒。当然,更多的酒楼茶馆则将购置新式报刊作为营销策略。如天津满春楼西餐馆就在广告中称:“且有各种报纸,随意观览。”(64)而茶馆是普通民众的消遣场所,一些有识之士观察到茶馆在传阅报刊方面的优势,遂订阅报刊,供众阅读。如北京德胜门外大关的回民杨某,“在自己的茶馆里,添设阅报处”(65)。天津启明阅报社设于东马路一品茶楼左,“于晚间兼教授贫苦人等识字”(66)。四川仁寿县乡绅屈玉辉在老君场四义茶社组织阅报公社,“购备各种报章,任人浏览”(67)。 由于阅报社与学校阅览室在服务对象与功能上的差异,阅报社的创办者面对的是一个区域的潜在读者,其辐射力和影响力一般大于学校阅览室。阅报社对地方文化与社会风尚的导向作用也日趋明显。如江苏陆师学堂毕业生赵百先,回到老家镇江大港后,在家祠内创设学堂,并设立阅报所,“计储日报旬报十三种”,为了便于远道而来的读者阅读,他规定“可留餐宿”,“并在阅报楼下设茶馆,所有旧报,凡来茶客必一一给阅,不另索资”。对于茶馆阅后的旧报,“又复汇集一处,贱价以沽,乡人咸争购之”。受到阅报风气的影响,“大港人士之来郡城者,皆具有新知识,非复从前气象矣”。(68)又如《中国白话报》有一篇对安徽庐州的调查认为,庐州一府四县一州,庐县的人要开通一些。究其原因,“听说一位姓庐的绅士,在他们县里很尽了点开通的义务,办那些开学堂、阅报社的事,所以,有这点文明的效验”(69)。在调查者看来,开学堂、办阅报社是社会开通的重要原因,社会贤达对地方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整体上看,清末阅报社的数量并不多,且许多边远地区并没有创设。但它作为一种新型阅读组织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却是值得关注的。 五、阅报社规章与公共阅读的制度化 对于阅报社的创设者而言,他们从服务民众、开发民智、传播文明的角度出发,力求为社会作贡献。如江苏丹阳书报社以“开通内地风气,提倡民族精神”(70)为宗旨。但创设者深知,如果不能在制度上进行管理与约束,良好的愿望就会化为泡影。阅报社为读者服务固然是中心任务,但是由于大部分阅报社是免费服务的,读者与阅报社之间并没有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创设者如何筹措资本、管理场所、维护秩序,都需要进行详细的筹划与制定细致的章程。而在阅报社的整个运转过程中,这些规章起到了约束和保障作用。读者进入阅报社,就意味着进入了公共阅读空间,这就需要读者在满足自我阅读需要时,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因此,阅读规则是确保阅读秩序和阅读效果的重要基础。许多阅报社都从爱护公物、有序借阅、保持安静等方面对读者在阅报社的言行进行了具体规定。如1902年设立的成都开智阅报公社,在章程中就特别强调了借阅制度: 第十三条,新到之报,每期所取,以一册为限,连旧报不得逾四册,日报未订成册之前,只许在社披阅,不得携出。 第十四条,本社报章概不能圈点批抹,如有所见,只可黏条达意。 第十五条,取报逾期不还者,由干事派人走取,脚力钱由本人自给(城内一角、外二角) 第十六条,社友临时有要事,不能亲身到社取报章还报,务托妥人持票到社,如阻于风雨,自当格外通融,于晴朗日开社交还,否则,照逾期办理。 第十七条,凡取报遗失者,照全部价赔偿,污损者,照价赔偿所污损之册,违者罚停取报。(71) 显然,成都这家较早设立的阅报社,具有对外借阅的功能。章程的重点是确保报纸得到有效保护并能尽量发挥流通作用。由于这家阅报社是集资创办,“入股者每年每股出洋二元,作为购报之费”。只有入会的社员才有资格外借报刊。而清末一些阅报社对读者的行为规范有严格要求。如北京较早成立的西城阅报社要求读者看完报纸后,“一定要送回取报处放好”。并要求读者遵守如下规定: (一)阅报时不能够随便叫唤,高声喧笑。(二)各种的报不能借出去看。(三)报内常常有精细的图画,阅报的人不能把他砍下拿去。(四)阅报的人虽然自己有什么见解,不能够在报纸上动笔批写。(五)除阅报外,不能够在这里闲坐闲谈。(六)屋里头有吐痰的器具,阅报的人不能够随便乱吐。(72) 这几条禁止性的规定,从现代阅读文明的角度,要求读者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尤其是要求读者不高声喧哗和不随地吐痰的做法,对当时国人的不良习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在1905年的北京,民众在公共场所吐痰已习以为常,但是西城阅报社作为传播现代文明的新型组织,却在阅报社安放痰盂,要求读者讲究卫生,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举措。此后的一些阅报社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一些阅报社针对读者的特点,增设了较为人性化的设施,如河北深泽县阅报室“另设一桌,以备饮茶吸烟之用”(73)。其目的是为了不影响其他读者认真读报,尽可能地营造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福州西城阅书报所在章程中提出:“本社力量稍充,当添购图书仪器,以供实验。”(74)阅报社提供“仪器”的意图,表明创立者希望读者能够进行科学实验,从而提高科学认知水平。江西某阅报社附近,由黄君荪潭,在百花洲内开办之三育善会阅报留餐处(75)。设立“阅报留餐处”,一方面说明阅报社的读者不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此类餐馆为读者服务的理念,使阅报社的附加功能进一步延伸。 除了部分个人独资设立的阅报社外,一些合资设立的阅报社往往需要“协同管理”,尤其是一些采取“社员制”和“会员制”的阅报社,往往存在着出资与权益的问题。因此,此类阅报社往往在章程中强调社员的团结,如成都开智阅报社就要求社员做到以下几点: 一、当存自重之念,养成廉耻之心。二、当起亲爱之情,养成共同之趣。三、当兴辞让之风,养成静肃之气。四、当求卫生之要,养成清洁之习,除鄙吝之私。五、铲隔阂之弊,开意气之偏,涤龌龊之秽;平等平权,务蹈大道,以收乐群之效。(76) 这几点要求,主要从道德层面对社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达到“克己”而“合群”的目的。作为立足于地方社会的公共组织,阅报社试图将服务民众与自身建设结合起来,提高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阅报社对自身的约束被认为是制定规章的重要前提。如北京地区的阅报社在联合推出规则时,首先就指出:“凡我同志,既以劝人为己任,各宜认明公理,脚踏实地做事,方与立阅报社、讲报社之宗旨相合。倘假托文明,沽名钓誉或藉此别有取意,则恐一人累及同社,一社污点累及全体。先事预防,不可不慎。”以“同志”之称告诫参与者,既要表明志同道合之意,又要告诫参与者要洁身自好以维护组织的荣誉,善于“克己”,“既为阅报社之同人,自当以身作则,始可为社会之矜式”。在清末各种学会、社团、公会等团体纷纷设立的背景下,阅报社注重对组织者和管理者严格约束,旨在加强内部协调与沟通,以期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和影响。而北京地区由于阅报社较多,各阅报社虽未成立联合组织,但订立了共同遵守的规则,并规定了对外交涉和处理措施:“如有局外人故意寻隙无理取闹者,当执守文明,以和平之法过之。不可稍涉,操切激烈。如不能情恕理遣者,则约集各阅报社公评,以定曲直。”(77)这表明阅报社同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对于较为复杂的事务有着协同处理的约定,以便提高阅报社的行业声望和管理水平。 清末的一些阅报社不仅对民众免费开放,还根据时局的需要展开学术研究与公共讨论,进而从思想层面上扩大其社会影响。1906年,18岁的王云五在上海益智书室任教时,组织了一个振群学社,并任社长。租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屋,楼上购藏书报,或由各人以自有图书储存,备他人公余阅读,并相聚论学。社员们“讨论一般社会问题,旁及国家大局。或谈天说地,放言无忌;或专题讨论,集思广益”。(78)又如成都开智阅报社对“讲学”非常重视,规定“每月上弦下弦取报之日为讲学之日期”。这里的“讲学”,不同于“讲报”,具有学术研究与交流的意图。 阅报社的制度建设,为其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奠定了基础,也为读者的“制度化阅读”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阅报社创造了公共阅读的新形态,加之阅报社所订购的报刊往往数量较多,读者可以在公共空间“博览”群报。阅报社一般设立于城镇繁华地带,人群流动性较大,有利于其广纳读者,从而促进了报刊阅读的大众化。在清末社会,尽管随着邮递网络的扩张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县一级发行市场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下层社会民众购阅报刊的比例仍然有限,即便是北京这样的大都会,在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之前,下层社会对报纸普遍茫然无知,也就是在1904年之后,随着北京各街道逐渐设立阅报社,读报风气才逐步形成。 让民众有机会接触报刊,是推动报刊大众化的重要前提。除了私人订报之外,报刊在公共场所的呈现,对读者的公共阅读有着深刻影响。早期的报刊“公共性”主要通过报馆订阅的方式得以体现,一些报刊编辑通过博览报刊摘录新闻,从而兼具公共场所的读者和编者的身份。但是,报馆所订购的报刊并不面向公众开放,其阅读面较为狭窄,既便是维新之后各级官府、书院与学校订购的报刊,也仅在其内部流通与阅读。阅报社就是为了解决民众无力购报和无法阅报的困难而设,早在1875年,博闻书院创设的阅览室就面向厦门士绅开放,这说明传教士就已经注意到报刊的公共服务功能,而维新时期一些学会所创设的阅报室,却很难对普通民众开放。真正具有“任人阅览”功能的阅报社,是在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地方官员对创设阅报社的支持与鼓励,既有迎合新政、凸显政绩、获取权力资本的需要,也有热心公益推动文化普及的心愿。尽管官办阅报社的比例不高,但它却起着舆论导向与价值引领的作用,尤其是对政治动向与报刊宗旨的规定,使阅报社必须在官方的监控下运行。社会各界人士热衷于创设阅报社,一方面受到地方官的鼓励与嘉奖,具有彰显个人价值和服务民众的双重意蕴;另一方面也开创了新式报刊免费进入民间社会的新途径,对开民智、树新风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阅报社体现了权力、资本与文化的融合,在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合力推动下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清末各地设立的白话报刊试图掀起下层社会的阅读革命和文化启蒙,但是,从整体上看,白话报刊尽管通俗易懂,却面临着不识字者不能和不愿阅读的困境。而阅报社讲报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报刊文化”的下移,尤其是县一级阅报与讲报所在承接下层社会阅读方面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然而,在乡村社会,阅报社讲报所的数量毕竟有限,“公共阅读”在许多偏远地区仍然难得一见,“劝民读报”活动在实际运作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教育不广,智识难开。尽管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报刊大众化的价值与意义,但是读者总量的偏低从根本上制约了报刊公共阅读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清末的报刊大众化与启蒙运动,仅依靠阅报组织的推动,尚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 ①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王海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②《泰西近事汇编》,《六合丛谈》第2号,咸丰丁巳(1857年)二月一日。 ③吴汝纶:《吴汝纶全集》4,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373页。 ④薛福成:《薛福成日记》上,蔡少卿整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⑤《福仙园茶馆告白》,《上海新报》1870年5月9日。 ⑥《论本报销数》,《申报》1877年2月10日。 ⑦邓洪波:《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⑧《厦门泰西各国仕商创建博闻书院启事》,载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31、2032页。 ⑨傅兰雅:《发行〈格致汇编〉启事》,《格致汇编》1876年第1卷。 ⑩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页。 (11)《广报》1887年11月16日。 (12)《中西日报》1892年6月18日。 (13)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页。 (14)《南学会申订章程》,《湘报》第75号,1898年6月1日。 (15)《日新阅报社期年纪念演说》,《京话日报》1906年7月5日。 (16)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17)周树人:《鲁迅自传》,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29页。 (18)钱均夫:《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载刘萍、李学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1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94页。 (19)《设会阅报》,《申报》1898年9月26日。 (20)《沪学会章程(甲辰七月)》,《警钟日报》1904年8月27日。 (21)李斯颐:《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2)《力遏奇邪》,《申报》1903年3月19日。 (23)《慈宫注意报纸》,《通学报》1908年第98册,“报界拾遗”。 (24)《军机阅报处》,《通学报》1908年第98册,“报界拾遗”。 (25)《工艺局设立阅报图书所》,《申报》1905年7月10日。 (26)《大通厘金兼保甲总办许苓西太守劝商民阅报以益智慧录》,《湖南通俗演说报》1903年第7期。 (27)《山东诸城县朱大令设阅报馆禀》,《东浙杂志》1904年第1期。 (28)《霸州详设阅报处并定期宣讲抄录章程请立案禀》,《教育杂志》1905年第13期。 (29)中国国家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2,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95页。 (30)《山东诸城县朱大令设阅报馆禀》,《东浙杂志》1904年第1期。 (31)《元氏县创设阅报所并章程禀》,《教育杂志》1905年第14期,1905年10月13日。 (32)《井陉县禀设立阅报社情形酌拟规则呈请示遵文并批》,《北洋官报》2747册。 (33)《高邑县禀在毕公祠设立阅报处文》,《教育杂志》第19期,1905年11月。 (34)《新城县禀捐廉创设阅报社宣讲所情形文并批》,《北洋官报》2722册。 (35)《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1905年12月21日。 (36)《山东巡抚周劝选阅报章以扩见闻示谕》,《政艺通报》1903年5月11日。 (37)《高邑县禀在毕公祠设立阅报处文》,《教育杂志》第19期,1905年11月。 (38)《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2年第9期,1905年10月23日。 (39)《万全县设立宣讲阅报所禀并批》,《教育杂志》第21期,1906年1月。 (40)《力遏奇邪》,《申报》1903年3月19日。 (41)《高邑县禀在毕公祠设立阅报处文》,《教育杂志》第19期,1905年11月。 (42)《吴桥县详设立阅报兼宣讲所并批文》,《北洋官报》2965册。 (43)《丹阳书报社缘起》,《警钟日报》1904年8月23日。 (44)《江北厅禀筹设阅报所一案》,《四川教育官报》第4册,1909年5月。 (45)《直隶提学司详郑赞清嗣母刘氏等捐建宣讲阅报所请予奖励文并批》,《四川学报》1907年5月。 (46)《京师阅报社调查表》,《大公报》1906年6月27日。 (47)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0-405页。 (48)《天津县详沈家庄职绅张文治等捐立阅报社文并批》,《北洋官报》2868册。 (49)《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3年第5期,1906年6月16日。 (50)《孔子故里设阅报馆》,《鹭江报》1904年10月23日。 (51)《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4年第9期,1907年10月31日。 (52)《阅报社成立之可喜》,《东莞旬报》1908年7月3日。 (53)《福州阅报社》,《鹭江报》1904年9月14日。 (54)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55)《深泽县阅报室简章》,《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1月14日。 (56)《北京日新阅报处创办章程》,《教育杂志》,1905年6月17日。 (57)《北京阅报社规则》,《大公报》1906年2月10日。 (58)《北京西城阅报处创办章程》,《直隶白话报》1905年第10期,1905年6月17日。 (59)《纪公益阅报社》,《大公报》1905年8月9日。 (60)李洵:《〈华字汇报〉缘起》,《大公报》1905年6月3日。 (61)《阅报社开办有期》,《吉林白话报》1907年11月5日。 (62)《天津县详沈家庄职绅张文治等捐立阅报社文并批》,《北洋官报》2868册。 (63)钱均夫:《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载刘萍、李学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1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94页。 (64)《满春楼广告》,《中外实报》1909年5月1日。 (65)《老回友很有热心》,《京话日报》1906年8月12日。 (66)《又一阅报社》,《大公报》1905年7月15日。 (67)《仁寿阅报社之组织》,《广益丛报》1910年8月4日。 (68)《兴学阅报》,《大公报》1903年9月8日,附张。 (69)《庐州书市情形》,《中国白话报》1904年10月23日。 (70)《丹阳书报社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8月24日。 (71)《成都开智阅报公社章程》,《大公报》1902年10月17日,附张。 (72)《北京西城阅报处创办章程》,《直隶白话报》1905年第10期,1905年6月17日。 (73)《深泽县阅报室简章》,《直隶教育杂志》第21期,1907年1月14日。 (74)《福州西城图书报所总章》,《警钟日报》1904年11月6日。 (75)《阅报留餐处停办》,《警钟日报》1905年1月5日。 (76)《成都开智阅报公社章程》,《大公报》1902年10月17日,附张。 (77)《北京阅报社规则》,《大公报》1906年2月10日。 (78)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4页。标签:格致汇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论文; 时务报论文; 申报论文; 万国公报论文; 北洋官报论文; 上海新报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