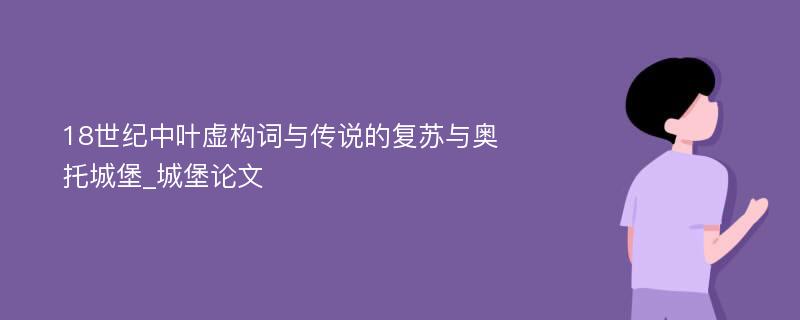
18世纪中期想象话语和传奇的复苏与《奥特兰托城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堡论文,奥特论文,话语论文,传奇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贺拉斯·沃波尔是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名士,他出身显赫,其父是纵横英国政坛多年、曾担任首相一职20余年的罗伯特·沃波尔。贺拉斯热衷收藏,特别是中世纪哥特风的物品,对此的痴迷产生了两个颇具影响力的结果:一是哥特庄园的典范——草莓山——的修建,引来参观者和敬仰者无数;二是小说《奥特兰托城堡》的问世,该作品被认为是哥特小说的开山之作。虽然未像其父那样在政坛大展身手,沃波尔与英国政坛常年保持了联系,其长篇巨幅回忆录被公认为研究18世纪英国政治与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文本之一。《奥特兰托城堡》(下简称《城堡》)自出版以来,赞誉不断。司各特称赞它语言纯净,叙事简洁,人物塑造自然合理,呈现的事件有趣又连贯,悲剧性的结尾令人动容,认为它那“恐惧和怜悯的激情”足以令作者获誉。①此后对这本小说的研究大多延续了把它与哥特小说的传统联系起来的路径,出现了一些较为引人瞩目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如有学者指出它与《帕梅拉》、《克拉丽莎》在主题上的相似性,认为小说的异域风情是建立在对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系列想象性改造上。②也有评论认为,借这部小说沃波尔抨击了18世纪政客滥用中世纪文本谋取政治利益的不道德现象。③本文从《奥特兰托城堡》的两版序言入手,剖析它们看似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下的内在连贯性,这种似非而是的手法暗合作者沃波尔的创作意图,即开创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把被当时主流文学传统排斥在外的超自然素材容纳进小说的疆域之内。本文把沃波尔反复强调的两个核心创作理念——“创造性想象”和“自然真实”——置放在想象话语与传奇复苏的18世纪中期英国文化语境中来讨论,认为《城堡》应和了这种潮流,实现了两者的融合,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看似自然真实的艺术效果与小说的意识形态潜话语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堡》投射了启蒙理性对中世纪的想象,通过拉开读者与故事的时空距离,将其表征为政治和文化上的愚昧黑暗,小说在使读者消费哥特想象的美感之余,达成对哥特因素的观照与遏制。 1757年,沃波尔创办草莓山出版社,出版好友托马斯·格雷等人的诗集和其他一些在他看来具有保留价值的作品。《城堡》完稿后,却未交付自家出版社,而是由伦敦一家出版社于1764年的圣诞前夜出版了五百本。沃波尔对外隐瞒了该书的作者身份。这一版的序言借英译本译者的口吻,对小说的来龙去脉做了交代。译者威廉·马歇尔以严肃诚挚的语气称,作品发现于英国北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古老家族的藏书中,用意大利语写成,1529年在那不勒斯付梓成书。根据描述的事件推算,故事大约设置在1095-1243年之间的某个时间。译者又从作品雅致的语言、作者的狂热以及仆役的姓名等细节,推断它在西班牙语的姓名广为普及之后写成。译者甚至不辞劳苦地对作者的身份进行了揣测:“其时文学盛行,驱散了改革派们憎恶的迷信帝国的肆虐。不无可能,某个狡猾的牧师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写作令大众对他们长期浸染其中的错误与迷信深信不疑。”④显然,这一版的序言效仿了18世纪比较流行的写作策略,即作者隐身,借助某个代言人营造一种“真实的”镜像。然而,不同于笛福、理查森等人的小说,《城堡》与传奇割舍不断的渊源却为这种“真实性”罩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像译者所言,它是一个“奇事、幻像、巫术、梦和其他超自然事件从传奇中大量溢出”的故事,因此,尽管沃波尔的代言人马歇尔有心效仿他人之法营造一种拟真感,叙述也堪称理性和严谨,然而细究下来,不难发现他的结论几乎全部产生于推测,缺少确凿有力的证据或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那种或多或少的在场性。也恰恰是这种似是而非、令人质疑的对“真实”的策略选择折射了沃波尔尝试把这部小说和现实主义路径联系起来的意图,以及他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他试图模拟当时流行的外围叙述策略,为故事披上一层“真实”的外衣;另一方面,故事类别的不同产生的落差又难免令它的真实性被质疑,现实主义小说的拟真效果似乎与这个故事的本性格格不入。 沃波尔对这种窘境有充分的认识,马歇尔并未舍弃对“真”的诉求。他从故事反映的年代入手,指出中世纪的社会状况如此,人们普遍迷信,相信奇事的存在;作者本人即使对此并不赞同,也要履行一个写作者的职责,忠实地记录和反映当时的社会习俗。译者的辩解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它邀请启蒙视野下的读者对未开化的、愚昧的中世纪进行想象,引导他们产生这样的认识,即在另一个时空,故事里的人物可能确实存在,小说的事件虽然有悖常理和自然律,却并不违背文学创作模仿生活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诗歌解释为对人类活动的模仿(mimesis),即再现。16至18世纪,模仿是文学评论(主要是诗歌批评)的关键术语。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发展至18世纪中期,虽然异彩纷呈,主流仍以现实主义为风向标。笛福的作品如此,理查森的亦然,“在此唯一的艺术原则是记录片般的可靠性”。⑤显然,《城堡》的序言对模仿的引入有文学语境的考量。因而,译者在之后的作品评述中,强调人物的言行切合他们各自的身份和场景,行文无浮夸的修辞、离题或不必要的描写,所呈现的事件均与灾难性的结尾有直接关联,等等。总之,“作品人物刻画精彩,基本符合戏剧规则”。也就是说,题材虽然充斥奇异的、背离常规的想象,表现手法却是现实主义的,效果是拟真的。译者还特意突出了作品对读者的情感产生的巨大影响:作者的有力武器是“恐惧”,它和“怜悯”交相辉映,读者被牢牢吸附在“有趣的激情的持续交替之中”(18页),令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情感的观点。一言以蔽之,第一版序言的叙述策略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前置作品“反映社会习俗”的特性和对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的挪用,拉近它与现实主义的真实诉求的距离。这种迂回的、遮蔽的方式隐含了作者把两种当时看来完全不同的文学模式关联起来的愿望,在貌似不可能中隐晦曲折地建构了某种可能性。 《城堡》首版的成功给予沃波尔一个明确阐述创作意图的机会。小说次年再版,在1765年版的序言中,沃波尔开宗明义,将先前的做法归因于对自身能力的不确信和这一尝试的首创性:“它尝试融合两种传奇:古代传奇和现代传奇。前者全然是想象力与不可然性的产物;后者则以成功模拟自然为宗旨。在现代传奇中,杜撰仍然存在,但最重要的幻想资源却因附着于日常生活而被抑制。”(21页)沃波尔所说的古代传奇即通俗意义上的传奇,它主要是关于中世纪骑士的浪漫想象的产物;现代传奇则指那些兴起于18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着力于真实地展现生活,以细腻的描述使读者感到似乎就是日常经验中的事物。前者通常称为传奇,后者是小说。沃波尔指出,如果说现实主义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自然法则禁锢了想象,那么,传奇则完全无视自然法则,人物的言行和情感极不自然,机械如同机器。他试图将两者融合起来,既保留传奇的奇思妙想,又“根据可然律塑造人物;简言之,就是使他们像处于异常处境中的常人那般思考和言行”(21页)。至此,沃波尔已言简意赅地明确了第一版序言隐晦表达的意图,即通过整合古老的传奇和现代小说各自的优势,开创一种新的写作模式,沃波尔称之为“哥特小说”,并在第二版的封面上通过副标题(a gothic story)进行标注。后世的批评家通常从中世纪阴森城堡或修道院的场景因素、离奇骇人的事件以及惊悚的阅读效果等方面来界定哥特小说,而在它的创始者看来,哥特小说首先是基于创作美学的考量。它试图打破传奇与小说之间固有的规约壁垒,给予想象充分的自由,同时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处理人物和事件,力求自然真实的效果。两个版本的序言之间存在共约性和连贯性,暗示第一版通过译者言说的叙述策略不仅仅是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故弄玄虚玩个技法,更蕴含了内容与形式的思考,这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以明晰的语言呈现出来。 在陈述了何为哥特小说之后,沃波尔花了不少篇幅,对小说的人物塑造,特别是小人物(仆役)的粗俗言语、插科打诨进行了申辩。作者明言,“我的原则是自然。”他坚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表达的观点,人物的表现与其身份有直接的联系:“王公贵族们尽可以严肃高贵或多愁善感……仆役们却不适合同等体面的言辞语气。我的卑见是,一方的崇高与另一方的无知形成对比,凸显前者的哀伤。”(22页)申辩延续了“模拟自然”的创作思路,强调人物的塑造要与其身份、地位相符。同时,他还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莎剧的批评(“滑稽诙谐与庄严混杂,令人难以忍受”),重申了其小说创作观的另一个维度,即拒斥所谓“适宜”的僵化规约,高度肯定想象力。他认为伏尔泰式的评价标准禁锢了诗歌,亦步亦趋按照规则完成的作品琐屑乏味,将诗“从想象的宏伟高度降格为幼稚和可鄙的苦干”。序言的最后落脚到哥特小说“开创一种新式传奇”的历史意义上,倡导一套与之匹配的评判标准(25页)。 综上所述,《奥特兰托城堡》的两版序言虽然采用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其内在的思路和意脉是相承的。序言或隐含地、或简明扼要地阐述作者的创作观,即突破文类“适宜”常规的局限,实现小说内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超自然想象的融合。在这一意义上,《城堡》确实如它的作者所言,在特定历史时期开启了一种新的小说创作理念与模式。 沃波尔这种张扬“想象”、将其与“自然真实”融为一体的创作理念不是凭空而来。启蒙运动在18世纪的欧洲发展到顶峰,它崇尚理性,认为理性可以驱散迷信、偏见和野蛮造成的黑暗,使人们以一种较为科学的视角来认识世界。由于理性的外延和内涵是相对于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建构起来,而想象在当时又是与传奇这一中世纪流行的亚文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理性的霸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想象在文学中的地位,传奇凋零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崛起。正如理查德·赫德在《骑士制度与传奇文学》(1762)中所言,伴随17世纪科学发现而崛起的理性主义,造成“想象力这自负的鬼怪”的逃逸,精灵和它们的世界遗失了。⑥然而,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总是蕴含着它的对立面。18世纪以来,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相继出现了打破理性/常识的禁锢、标举想象力和想象文学(即传奇)的声音,至世纪中叶,这些思想和话语日渐浓厚,为沃波尔式哥特小说理念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18世纪关于“想象”的话语要上溯到洛克的经验论。洛克把观念(包括感官数据、记忆以及抽象的概念)视为人脑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媒介物,强调感官、特别是视觉的重要性,认为知识最终来源于感官体验。他用“图画”来隐喻思想,认为简单的观念主要来源于视觉。⑦洛克的观点成为英国文化界探讨“创造性想象”的起点,多位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和批评家参与其中,其中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艾迪生、休谟、赫德、约翰逊等。18世纪早期,艾迪生就在《观察者》中多次撰文论述想象的起源、性质和功能。他赞同洛克观念源于感官体验的观点,认为可见物体引发想象愉悦感,同时人脑可以保留、改变观念或对其进行复合,也就是说能够借助想象(短暂地)超越现实(Spectator 411)。人脑可以自发地联想,产生想象:“特殊的气味或颜色令人联想起偶遇的田野或花园,与之伴随的意象涌现而来。想象插上了翅膀,出乎意料地将我们带往城市或剧院、平原或草地。”(Spectator 417)想象的愉悦弥补了现实生活的不足和匮乏,这种联想的和想象的机制在文学创作中意义重大。艾迪生对作家依靠想象力创作的栩栩如生的奇幻世界尤为赞赏,认为这是最难驾驭的一类写作。想象的创造性能量得到全部发挥,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把读者带入其中(Spectator 419)。在《观察者》第421期中,他提出诗人的非凡想象力“具有上帝创世般的品质”,即作为自然的补充,为上帝的作品增添色彩斑斓的多样性。 艾迪生对想象的大力肯定得到后来者的认同。尽管在外部世界的属性问题上休谟与艾迪生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也给予了想象以崇高的地位。休谟认为,外部世界并非是上帝神性的显示,而是想象作用的结果。想象力将一系列不同的印象(即感官体验、激情和情感)融合为连续的现实的表象,观念来源于印象。休谟还说,在人的天性构成中,想象力和激情都需要通过困境来激发能量,彰显自身:“为聚集力量克服困难,我们强健心灵,使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反之亦然。敌对不仅有助于扩展心灵,而且当心灵充满勇气和气势恢宏时,会主动寻求敌对。”⑧尽管休谟没有直接论述“崇高”,然而在上述引文里,想象力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仅是人脑建构外部世界的基础,其磅礴的意象反映了启蒙时代突破一切障碍的信心与信念。正是在这种想象话语上扬的文化场中,1757年伯克关于崇高的论述得以形成。 在文学批评领域,想象话语的复苏同时表现为传奇的回暖,这股潮流可以回溯至17世纪末。其时,因出版古冰岛诗歌残篇集而名声大噪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对西德尼大加赞扬,称他是用现代语言创作的最伟大的诗人,其诗作《世外桃源》(Arcadia)传承了古诗风韵。⑨至中期,历史上的传奇杰作更是成为批评家们称颂的宠儿,赫德、托马斯·沃顿等人对斯宾塞的《仙后》赞誉有加。在《骑士制度和传奇文学》中,赫德指出,伟大的诗人,如斯宾塞、弥尔顿,均被传奇吸引。他反问:“难道他们是突发奇想、荒唐可笑吗?难道不是哥特传奇中某些元素特别切合天才的观点,切合诗歌的目的?”赫德所说的元素即超自然的、不受现实束缚的、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他对斯宾塞的高度评价正是基于这种想象力,在他看来,由于《仙后》盘活了中世纪传奇,斯宾塞理应在诗人中享有尊崇。⑩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对“天才”与“后天才能”的高下之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想象力的标举。批评家们视莎士比亚为“天纵英才”,正是以其不羁的想象为价值评判的首要标准。如艾迪生认为,莎士比亚有一种“不被艺术规则训导或摧毁”的天然才能,这与后天通过研习获得的才能完全不同(Spectator 419)。 想象话语和传奇批评的升温,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也出现了表现论的呼声。赫德认为,不应以模仿作为评价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诗人拥有自己的世界,与经验相比,持续的想象作用更大。”诗展现的并非是历史或哲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诗性真实”,因而诗人的创造性想象可以游离于自然律之外。(11)在他看来,诗在本质上是表现的,而非模仿的。爱德华·杨在《原创作品猜想》中运用有机体的概念,隐喻天才是自发长成,而非靠模仿而成,(12)这比柯勒律治的观点早了半世纪。另一方面,模仿论亦有强有力的支持者。约翰逊没有全然否定想象力的意义,他认为“想象力这个无法无天的无业游民,不受束缚,对克制表现得不耐烦,它使逻辑学家受挫,混淆边界,打破现实的封闭……每个天才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些革新”(Rambler 125),然而,它缺乏外部世界的扎实根基,因而不足以构成批评的第一要则。他也赞美莎士比亚,却是基于诗人“给读者立起一面忠实反映习俗和生活的镜子”。(13)以约翰逊为代表的主流批评者们坚持的是“忠实反映生活”的文学评判尺度。 有趣的是,尽管在创作理念上表现派和模仿派观念迥异,批评家们都不讳言“自然真实”的重要性。休谟在《论写作的简洁与雅致》中写道,“单单令人惊讶的作品,如果不够自然,不会给人带来持久的愉快。画吐火兽,并非是抄袭或模拟。”(14)也就是说,对文学创作而言,仅有想象或仅仅是模拟都是不够的,只有创造性地运用想象,将其与自然真实感融为一体,才能带给读者好的审美感受。休谟推崇荷马,认为他“摹写真正自然的习俗,无论这一习俗如何粗俗或未开化,总会形成赏心悦目的有趣图景”。(15)重要的不是描写的题材是否超出通常意义的现实的阈限,而是写作者能否完美地驾驭想象,令读者产生仿佛身临其境的拟真效果。这与沃波尔阐述的创作理念在意旨上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尽管在18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场中现实主义主张的模仿占据了主导,然而,反者道之动,对理性思维的霸权的反动和对恪守常规的文学创作模式的叛逆触发了想象话语与传奇在世纪中期的回流。60年代成为英国小说创作的分水岭,“传奇被重新定位成表达想象性经验的文学方式。”(16)“……小说的语境远离了社会现实主义的诉求,仿佛想象的过度发展来源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暂时性过量,人们无法在熟知的、被广为接受的日常生活的点滴描写中找到阅读乐趣。”(17)沃波尔的新式传奇/小说的理念正是产生于这种创作氛围与接受氛围发生变化的转折处,是呈上升趋势的想象话语和传奇与自然真实摹写生活的诉求共同作用与协商的结果。 《城堡》属于想象的文学,它打破自然律的限制,把一个中世纪的想象空间呈现给读者,开启了小说“想象社会学的新阶段”。(18)尽管再版后出现了一些关于第二版序言的批评,认为它破坏了第一版的拟真效果,然而短期内小说被售空,之后又多次重印,印证了它受欢迎的程度。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沃波尔把超自然的事件表现得真实可信。然而,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种自然真实的效果的获得并非完全归结为艺术上的造诣,与小说的意识形态潜话语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迎合了读者对野蛮愚昧的中世纪的心理预期。故事的序言和正文利用叙述者的视角和声音,巧妙地、潜移默化地对阅读进行引导或干预。文本始终存在两个视域:一是故事层面的中世纪人物的视域;二是话语层即叙述者的当下视域,它与读者的视域基本吻合。两者交集,故事里的人物和这个空间发生的一切成为后者审视、评价和回应的景观。这在第一版序言中体现得尤为明确:叙述者马歇尔称,读者将置身于“有趣的激情的持续交替之中”,不由自主产生恐惧和怜悯心。引文呈现了两种视域各自的位置和属性:“有趣的”一词的使用充分拉开启蒙读者与审视对象的距离,把“激情”这一来自异空间的异质物转化为一种可供娱乐、可消费的奇异景观。这样一来,中世纪的故事时空就被作为外来观察者、评判者的启蒙理性宰制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序言预示故事将奉献一道激情的景观,它将受制于理性视域的钳制。在简要交代了奥特兰托城堡之主曼弗雷德之子在婚礼当天被来历不明、从天而降的巨盔活活压死和堡主的失常反应之后,激情与理性二元对立的机制明晰起来。特别是在第一章,文本或是通过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讲述(如“当激情没有蒙蔽理性时,他(曼弗雷德)的美德还会浮现”、“头脑的狂暴”),或是通过人物的对话(“这悲惨的一天让你神智错乱了”),或是通过人物的意识或心理活动(如玛蒂尔达眼中“头脑错乱”的父亲形象、伊莎贝拉的意识折射的曼弗雷德的“狂躁激情”等),建构起一个受权欲蛊惑、利令智昏的君主形象。其他人物也并非能够远离激情这一强烈情感的作用。第四章是继第一章之后“激情”(passion)、“精神错乱”(delirium,disorder)、“理性”(reason)等字眼高频出现的一章。伊莎贝拉之父、维琴察侯爵弗雷德里克垂涎玛蒂尔达的美貌,不顾女儿的幸福,意欲应允曼弗雷德换亲的提议;甚至在神启之后,他也无法摆脱情欲的控制,“深受忏悔和欲望纠结之苦”(100页)。神父杰罗姆与爱子失散多年后重逢,父子相聚的狂喜和对爱子人身安全的忧虑使他丧失了应有的态度和立场,原本义正言辞地指责曼弗雷德休妻再娶的他对后者的谎言沉默不语。在序言里,沃波尔表明小说并非旨在道德教诲,然而,它的叙述手法,特别是高频词汇交叠与汇聚形成的回声场,令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当人物受制于激烈的情感时,理性就远离了,反之亦然。这一潜话语在曼弗雷德之妻海波丽塔的一再恳求中(“让你的灵魂复位,掌控你的理性”)几乎固化下来。也就是说,《城堡》的故事建构在激情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上,受叙述者指引的作者的读者自然而然地把前者与中世纪的黑暗和狂暴政治关联起来,这样一来,异时空的传奇始终落在启蒙理性的钳制之下。远距离的投射使故事的恐怖感转化为美感的同时,也令它的当代读者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与满足感。 在对哥特废墟仿建热的研究中,斯图亚特得出以下结论:通过对哥特废墟这一中世纪的文化符号进行重构,使它成为一道不光彩的历史景观的化身,废墟仿建热实则凸显了18世纪理性主义的胜利。(19)《奥特兰托城堡》也是这样一个文化符号。它产生于世纪中期英国文化界对理性思维的钳制和对现实主义循规蹈矩的不满,应和了想象与传奇回归的潮流,如司各特所言,将哥特从先前“与真正的趣味相左的不良声誉中解救出来”。同时,叙述模式的处理,又在无形之中发挥了引导和干预阅读的作用,促使读者认同启蒙秩序,达成了遏制哥特因素的悖论效果。因而,它对哥特的弘扬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挪用和再想象。18世纪中后期,出现在英国文学、建筑、绘画、园林景观等多个领域里的哥特复兴有异曲同工之效,在这一意义上,《城堡》预示了哥特复兴的实质与走向,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释: ①Walter Scott,"Introduction",The Castle of Otranto(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2004),pp.14-15. ②Clive T.Probyn,English Fiction of the 18th Century:1700-1789(London:Longman,1987),p.171. ③Crystal B.Lake,"Bloody Records:Manuscripts and Politics in The Castle of Otranto",Modern Philology,Vol.110,No.4,2013,pp.489-512. ④Horace Walpole,The Castle of Otranto(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2004) ,p.17.(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⑤Clive T.Probyn,English Fic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1700-1789,p.183. ⑥Richard Hurd,Letters on Chivalry and Romance,ed.H.Trowbridge(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3),p.x. ⑦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ed.Peter H.Nidditch(London:Oxford UP,1975),p.43,p.47. ⑧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ed.L.A.Selby-Bigge(London:Oxford UP,1978),pp.432-444. ⑨William Temple,"Of Heroic Virtue" and "Of Poetry",in Five Miscellaneous Essays,ed.S.H.Monk(Michigan:Ann Harbor UP,1963),p.143,p.188. ⑩Richard Hurd,Letters on Chivalry and Romance,p.iv. (11)Richard Hurd,Letters on Chivalry and Romance,p.xii,p.x. (12)Edward Young,Conjectures on Original Composition,ed.Edith Morley(Manchester:Manchester UP,1918),p.18,p.31. (13)Samuel Johnson,"Preface to Shakespeare's Plays",Samuel Johnson on Shakespeare,ed.H.R.Woudhuysen(London:Harmondsworth,1989),pp.122-123. (14)David Hume,Essays,Moral,Political & Literary(London:Oxford UP,1963),p.197. (15)David Hume,History of England(London:Oxford UP,1826),p.433. (16)Clive T.Probyn,English Fiction of the 18th Century:1700-1789,p.xi. (17)Clive T.Probyn,English Fiction of the 18th Century:1700-1789,pp.186-187. (18)Clive T.Probyn,English Fiction of the 18th Century:1700-1789,p.170. (19)David Stewart,"Political Ruins:Gothic Sham Ruins and the 45",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Vol.55,No.4,December,1996,pp.4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