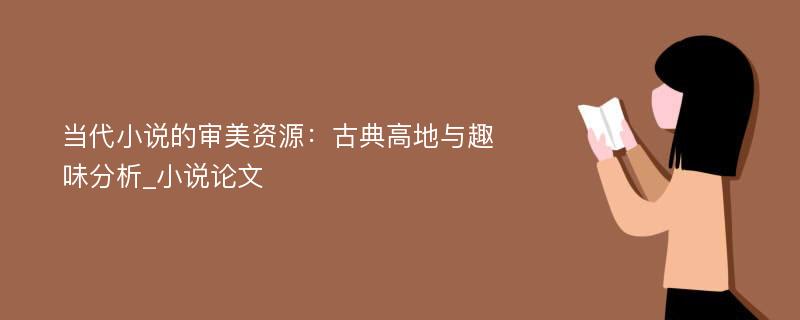
当代小说美学资源:经典高地与趣味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地论文,美学论文,趣味论文,经典论文,当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71(2013)01-0041-05
西方叙事美学理论,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学界曾引起关注和讨论。作为理论舶来品,由于缺乏对应的文本经验引发审美共鸣,对其价值的评价,多停留在对叙事角度或叙事人称等技术性术语的肤浅认识上。
从另一角度看,对于西方的经典小说作品,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由于文化和趣味隔膜,并未表现出探究的热情。由于忽视对西方小说经典作品的研读,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美学资源,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对于西方小说叙事理论哪些地方是生硬的、无助益性的,我们无法提出自己的见解。西方叙事理论中最精彩最深刻最有趣最微妙的理论阐述或批评思路在何处,我们似乎也拿不出像样的阐释方案。第二,对于西方叙事经典文本,往往是作为某种理论方法之案例分析的佐证来使用,而不是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审美经典来欣赏、品味、分析,所以,极难见到中国批评者对西方叙事经典发出自己有见地的批评声音。这是文化隔阂的问题,更是文化惰性导致的。更有可能是,文化惰性与文化偏见,再加上急功近利的时代浮躁病,使得中国文艺理论界对于目前依然不断出版的西方叙事经典,几乎拿不出较有审美洞察力和解读力的文字。这也间接导致国人对于西方小说经典的解读无法从专业学者的著述中受益。第三,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180小说叙事美学自然需要中国思维和中国式洞察。同时,西方叙事理论和西方叙事经典作品,对于当下中国叙事理论和叙事作品的创造,其意义不仅是技巧的研究与借鉴,还是叙事审美内容的充实、更新,以及叙事审美方式的主动碰撞与积极吸收。因此,当代中国叙事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中国传统经典叙事佳作的剖解,而是应该以更大的气象,通过对世界级叙事经典作品的研究,扩展研究的视野,将叙事美学研究定位为对人类叙事文化成果的分析与吸收这一更具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学术研讨之层面上。如此,才可能使得叙事美学的研究在一个“学无中西”、“互相推助”的大格局内获得“上下求索”、“左顾右盼”的有趣并有益的切磋。
当代中国的叙事文学作品滥竽充数者众,网络文学动辄几百万字的所谓的长篇小说以肤浅庸俗的趣味招摇于大众文化市场,所谓的纯文学又多以“文学边缘化”为其创作力的丧失寻找借口,萎靡不振的疲态和了无生气的自我丑化,倘若借此博得同情尚可,对于激发叙事审美的新发现、新创造则无裨益。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批评界以为文学摆脱了政治枷锁就能获得活力,这种活力固然在高压松动后获得一定程度的释放,但对于世界级叙事经典作品缺乏耐心的批判性吸收,如今已经显出后劲乏力的“亚健康”状态。读一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一系列小说和传记,不难发现,今天的世界级的作家是以多大的热情和虚心在充分学习了大师级前辈的经典叙事作品,承继了叙事文学的伟大传统之后,才可能创造出具有东西方文化交融之特点的震撼力作。单就帕慕克最擅长叙述的“忧伤主题”而言,帕慕克的忧伤,在绝望、疼痛感中有柔情似水,在迷失中有坚守和甜蜜,于边缘处有骄傲与恬适。所有这一切,都是处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碰撞中的伊斯坦布尔式的独有的忧伤,是属于帕慕克的忧伤[2]99。这种忧伤既有《纯真博物馆》、《伊斯坦布尔》那样无法承受历史废墟化的身份迷失型忧伤,又有《雪》那样在血腥的现实冲突中充满疼痛感的身份破裂之忧伤,以及《黑书》那样游走在历史和现实迷宫中的身份他者化的忧伤,还有《我的名字叫红》那种因文化身份的剧烈挣扎带有绝望感的忧伤。这种伊斯坦布尔式的“呼愁”之忧伤感,是帕慕克在深刻理解了法国的普鲁斯特、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作品后,作为一位极具反思能力的文化对话型作家,不断提高其对本国的精神文化困境的敏感度,激发思考,强化其对祖国文化痛苦的深思,并获得叙事审美化书写之信心。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帕慕克对福楼拜等西方大师对伊斯坦布尔文化的态度特别在意,他在小说中不断发生着与世界级前辈大师的“潜对话”。同时,作为一位鸟瞰型的作家,他将目光不断投向西方的同时,又坚守着伊斯坦布尔式的谦逊和平静。
帕慕克小说文本的启示还在于,作为一位十分了解西方叙事经典作品的小说家,他对伊斯坦布尔1970年代那种“欠发达状态”中人的生存状态是以一种欣赏而非猎奇观赏的态度展开叙事。帕慕克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符号交织作用下的土耳其文化,从伊斯坦布尔到边陲小镇,能以足够的审美自信,选择了一个感伤而温情的审美视点,刻画着城市或小镇中的各种生灵的欢喜、哀愁、困窘与通达,并将这一切以“情感考古学者”的细腻与谦逊,告诉你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是美好而且值得记忆的。在《纯真博物馆》中,有一位暴发户时不时要到希尔顿酒店喝咖啡,因为只有活动在希尔顿饭店内部,这位暴发户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在欧洲。这是典型的欧洲化想象,如此欧化的伊斯坦布尔人是不会欣赏“欠发达状态”的本土生活之美的。而帕慕克则以“博物馆化”的观念传达这样的信息:匮乏而忧伤的城市里的生活因为某种特殊情感的存在,不但是美的,而且是值得记忆和珍藏的。审美不计较现代化与否,审美在乎的是这种情感的别致性、执拗性和真诚性。这种在西方观念注视下的东方情感,是帕慕克的小说文本中心叙述所在。帕慕克这种东方情感远比任何高扬的文化宣言更具有情感“说服力”——伊斯坦布尔的小市民生活与情感不但是可理解的,而且是细腻、有趣、多情和真诚的。他们和世界上的许多人一样,懂得爱情的美好和尊严;一样珍视爱情每一个阶段的情感记忆;一样会因为失恋而黯然神伤;一样会琢磨自我情感的每一种来源。这样的人们,没有理由不关注,没有理由不倾听,没有理由不施以审美的书写。
帕慕克是面镜子:他鸟瞰着世界,同时,他最懂得贴近本土去欣赏、解读祖国的种种“废墟化”之美,这不是无奈,而是自信和智慧,因为他知道在世界历史格局中如何定位并表达属于祖国的叙事之美。他为祖国而忧伤,又为祖国而感叹,更懂得形塑祖国众生相的诸种。
帕慕克的小说,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昭示我们:世界级的审美叙事资源始终作为一种沉默的宝藏存在着。“文学已死”的论调不是太悲观,就是自欺欺人。叙事经典作品,不仅是作家的对话对象,也是理论家批评家最重要的一种资源。
那么,紧接着话题是,凭什么你会认定某种作品是世界级的经典作品?的确,经典通常是透过文化权力的复杂运作建构出来。认定某种作品是值得进入世界级的叙事作品的行列,首先需要论者说出其可称为经典的理由。就叙事作品而言,成为经典的理由,也并非相对到毫无言说的可能。比如刘再复先生极力推崇《红楼梦》的经典地位。刘再复先生在他的《双典批判》中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批判的依据,恰是他推崇《红楼梦》的理由。可见,即使是公认的经典,依然需要经受如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具备“逆觉”之批判家的反思性评判。刘再复先生以为:“《三国演义》有伟大的智慧,但无伟大的心灵。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历史的洞见,现实的把握,还有未来的预见,其战术智慧可为大矣。可惜三国智慧,包括诸葛亮的智慧,只切入大脑,未切入心灵。由于智慧缺乏伟大心灵的支撑,所以其智慧均是分裂的,常常发生变质,化作权术与计谋。与《三国》相比,《红楼梦》不仅具有伟大的智慧,而且具有伟大的心灵。其主人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智慧是建构诗意生活的想象。”[3]211如果以心灵的诗意性和主题的觉悟性为指针,那么,《红楼梦》的确大大超越了双典。然而,双典在创作英雄个性和江湖生活的刻画上,亦有其叙事的审美价值。按照刘先生的看法,经典的意义,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应该是具有超越性。不过,判定经典还不能单从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寄托和超越性作为单一的标准,因为有的叙事经典显然只关注某一特定的社会层面,比如《水浒传》是对流民为主体的江湖社会的关注,从民间话本世代累积而成的小说经典,是难以为现代社会的读者提供什么超越性的深度思想。但是,《水浒传》对市井社会和草莽情怀的刻画,则可能为读者提供洞照黑暗底层的一种审美镜像。而《三国演义》不仅是对军事斗争的叙事,更对超级英雄的心气与弱点有着入木三分的叙述。这意味着经典的标准不见得是以精神的超越性为惟一的依据,而是多维的。这还意味着,经典的问题单从观念层面上判断会有偏颇,如果“降低要求”从审美的趣味多样性来分析,可能会更具有包容性。
至于分析审美趣味,不能不联系布尔迪厄所言的审美“区隔”:“布尔迪厄把资本的数量与构成方面的差异理论化为两个基本的组织原则,这两个组织原则则把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与社会阶级状况联系在一起。阶级状况方面的这些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相互分化的阶级习性,而这种习性又反过来生产出生活方式的差异。他们把统治阶级的寻求特异性的习性与工人阶级的受必然性制约的习性区分开来。资本总量的差异把那些以可观的经济与文化资本为前提的时间当作稀有的、更加值得追求的实践。具有大量资本的行动者享受着极为可观的自由,使它们免于由物质的匮乏以及谋生的需要所强加的实际的制约与临时性的紧急需要。那些资本匮乏的人发现很难免于谋生的现实要求,这种不同的‘与必需品之间的距离’生产出不同的阶级习性,而后者反过来又产生不同的趣味系统。”[4]189显然,不能将阶级身份与趣味性画等号。经济资本不会那么顺利地转化为文化资本,但经济资本可逐步向文化资本倾斜。从这个角度看,刘再复先生对于《红楼梦》似傻似狂的奇人宝玉的无限向往,是一种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本,以追求精神的超越性为最重要立场的审美旨趣的必然,而尚为“必需品”而奔波的底层者可能会觉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水浒传》更具亲近感。这种文化“区隔”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影响叙事文学经典的价值判定。那么,对于此种审美“区隔”,叙事审美理论的研究者批评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显然,认识到叙事审美世界的博大性和多元性,积极地辨析多元审美趣味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不以单一的叙事审美趣味为圭臬,在勾勒不同的叙事审美趣味的关系图式时,既有鸟瞰的俯视力,亦有无限贴近审美特殊性的细察力,当是文学与文化批评者宜倡导之态度。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审美辨析活动,应多强调理论分析的助益性,让理论的分析成为带着阐述者生命感悟之温度的分析,而不是为了炫耀无体悟性的理论教条。
拓展小说叙事审美的趣味疆界,不是为了趣味而趣味,而是因为趣味的多样性值得我们去解析去体悟去概括各种特殊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辨析小说审美趣味之间的差异性。差异性之辨析,不是没有审美立场的盲目辨析,而是要探讨小说作品给予了人们怎样的思想和情感的开阔度和复杂度,给予人们怎样的想象的自由度和新鲜度,给予人们怎样的叙事美感之精致度和微妙度,给予人们怎样的思想观念之深刻度和超越性。
如果说巴尔扎克对于人的欲望的偏执性有了极其深入的社会性层面的洞察,那么,左拉感兴趣的是这种偏执性背后的生理性原因,而福楼拜以冷漠的反讽对此偏执性作出反浪漫的超然化叙述;如果说托尔斯泰对人的不可遏止的非理性精神层面进行了“心灵辩证法”式的精细剖解,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以拷问式叙事将这种非理性精神层面下人的自我分裂的乖张状态揭示出来——这种对人的严重不信任的质疑式小说直接影响了加缪、纪德、萨特、黑塞的小说创作;如果说亨利·詹姆斯对于人的精神迷思依然以自我深度反思的方式进行自我情感中心化的叙事处理,那么,在普鲁斯特那儿,他已经能够在小说文本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去寻找极微妙极有趣极多样的价值与审美的多重复合的情景中去关照人性的各个向度:从人的瞬间隐蔽动作背后的多重意义,到一个人的一生的戏剧性变化所包含着的审美遐思与价值辨析,普鲁斯特既能从极远的距离打量又能以最贴近细节的方式细察。
伟大作家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小说文本中提供了对人的精神存在的特殊洞察,以及属于这位作家的特殊的感受方式、价值判断与叙述语言。特殊的洞察力,催生出小说审美新的表达样式和审美趣味。托翁最擅长从人物的下意识恍惚状态中去找到人物自己都不太明了的隐秘动机,他的小说开辟了下意识状态的精神疆域,心灵的瞬息万变的感性状态成为托翁捕捉人的生存体验的最肥沃的书写猎场。托翁既能驾驭历史的巨幅画面,又能将巨型情节转化为人的下意识的变化万端的活动之中的小说写法,推崇的是感觉先于意识、变化高于静止的小说美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美学形式无疑是巴赫金所言的“复调式”的“狂欢体”,这种“狂欢体”将有关人与上帝之关系的理念争辩编织入旋风般的场面转换中,从而向读者展示人是如何在迥异的价值观念驱动下与他人争辩着、自我斗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在自我分裂状态下的无休无止的灵魂搏斗极生动地融入种种急遽变化的情节演进中,赋予人的情感变幻脉络以清晰的逻辑性,同时将这种逻辑性放置在严酷审视的状态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灵魂自我审视的小说美学趣味。来自法兰西的普鲁斯特的小说不是审视,而是通过“近视”与“远视”的不断交错变幻,以唯美的心态看待各种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普鲁斯特捕捉各色人等的片段场景、短时感觉、刹那间动作、瞬间表情,这些片段化场景、情境、表情、动作所形成的立体化的符号网络,代替了情节型小说的因果性层级性组织。普鲁斯特的小说,“一道耀眼的闪光”所可能包含的短暂性、永恒性、差异性、相似性、戏剧性、场景性,吸收了传统小说人物中最具表现力的情节能量,引领我们去看那一次次短暂的人生演出,再将各次演出的关系以“远视”的方式加以诗意的升华,勾勒出大跨度命运变迁所内蕴的审美意义。普鲁斯特让我们相信,短暂的相似性叠合,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微妙的意义,绝不亚于层层推进、针线细密的整体感强烈的情节主导型小说。普鲁斯特以他极具幽默感的行文,将人类表情、姿态的文化解读学、比喻学变成了崭新的小说诗学,并革命性地取代情节化的小说诗学。
如此概括具有坐标性意义的小说大师的审美特异性,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即大师与大师之间的审美趣味差异性,并非为差异而差异,而是每一位大师通过他或她独有的叙事艺术开创一个理解世界、描绘存在之新路径。
小说美学的趣味,始终处于彼此互相打量、互相指涉的关系中。哪怕是某种非常鲜明的美学趣味,也可能在不同的理论路径的解读中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敞开。或者说,不同的理论路径,将可能在逼近同一文本之时,显露完全不一样的叙事美学趣味。如对《追忆似水年华》的趣味的解读,热奈特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发现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是一种完全的叙事体,所有的展示都包含在叙事中。不要小看这种发现,因为《追忆似水年华》重新确立了小说的美学原则,小说的散文化议论化的方式不见得都为人接受,热奈特告诉我们普鲁斯特有着极强的展示能力,不过这种展示场面都被“频率化”。虽然过分科学主义的理论做派拘束了热奈特的手脚,但是,不可否认,热奈特对《追忆》中“二度预叙”、“预叙中的倒叙”、“倒叙中的预叙”以及“走向无时性”的分析,具有罕见的分析力[5]52。这种分析力表现在热奈特发现普鲁斯特突破了各种时间界限,并且总结出了普鲁斯特使用了什么样具体的叙事方法:普鲁斯特的小说诗学不是像罗伯·格里耶那样“及物”叙述的小说,而是一种灵活地使用各种心理过程的调度,实现叙事的全面解放。事实上,这种叙事现象,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缪尔就具有类似的观点:“在这部书写往昔的卷帙浩繁的巨著中,普鲁斯特不落俗套,和萨克雷不同;他运用一切手法,随心所欲地忽前忽后打乱时序,他不为故事所牵引,而是以故事背后的内心活动为主导,各种场景好似装入一只变化万千的精雕细镂的魔盒一般,纳入这内心活动。而且也正是这种心理活动使得《追忆似水年华》具有整体性。表面上看来,它是人物小说与戏剧性小说交织而成的集合体;但更本质上它是戏剧性小说罕见的例证,这种戏剧性小说的结尾不是我在外在情节的结尾,而是作者心目中的结尾:一种探索的结果,而不是冲突的结果。《追忆似水年华》中某几部分如果撇开其上下文,就完全可以看作人物小说,但人物小说的写作也可以设想为一个戏剧性情节本身,普鲁斯特就正是将这种戏剧性情节搬入他想象力的另一面及他伟大作品的背景之中展现的。实际上他没有能使他的作品同他自己分开来,使他的作品成为独立的存在而出现;他与作品之间的纽带从没有割断;只是由于那可喜的天才的成就,他能以将这种不幸转化为有利。他不独使我们看到他的想象的成果,同时还有那想象的过程,尤其是那些过程对于他自己的影响,以及他对那些影响的感受。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几本小说,而且是构思小说的意志及创作小说的艰辛。”[6]409缪尔的论述精辟,但是,由于缪尔所使用的“戏剧性小说”等概念拘束了他自己的想法,使得缪尔对《追忆》最精妙的所在仅止于“内心”、“时间”、“探索”层面的论述,而没有看到普鲁斯特的“内心活动”是利用了某种相似性原则让各种奇思妙想贯穿于小说中。缪尔没有说出普鲁斯特所驾驭的内心活动的“逻辑”是什么。热奈特则以“叙事”与“展示”以及时间是在叙事中如何获得逻辑性的奇妙分配来论述普鲁斯特的叙事趣味。缪尔与热奈特相比,缺乏理论的追问力。再有,现代法国思想家德勒兹从修辞性的形象“对等物”更深刻地将普鲁斯特的“记忆”与“时间”逻辑化:“对普鲁斯特的真实来说,修辞上的对等物是一连串的隐喻形象。”[7]81这样,就找到普鲁斯特小说之所以产生如此奇妙的叙事奇观的某一重要原因:修饰之后修饰,想象之后的想象,远距离取譬,相似处推动,纵聚合旋转……所有的这些特点都告诉我们普鲁斯特创造了怎样的叙事隐喻的清溪和洪流。
当代叙事美学的最大的资源是经典文学叙事作品:不要因为“经典了”而无条件崇拜,更不要因为经典的成立是一个各种复杂的意识形态“经典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便轻视经典。再说,不正是文学研究者,在不断地吸纳、淘汰、“更新”着叙事文学经典吗?《悲惨世界》为什么一定比《基度山伯爵》更“正典”?为什么《情感教育》远比《包法利夫人》更具审美震撼性?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新”在哪里?他的明显误区又在哪里?为什么今天人们更有理由读《追忆似水年华》?正是这种种简单但不见得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推动着我们继续探索叙事美学的新趣味。当然,并不是说理论本身就对美学的发现毫无作为,举个例子,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名著《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其中的“根茎理论”、“逃逸线”、“解域线”、“节段化”、“层化”理论,将有可能大大推进《追忆似水年华》的审美趣味的理解[8]。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理论应是一种能够为小说解读带来新鲜审美感觉的理论,而不是仅仅作为某种文本诠释的教条指南。
当代叙事美学资源远未走向枯竭,相反,叙事审美作品的复杂、纠缠、含蓄的审美特性,还有待于通过与当代不同媒介表达的比较分析,获得更深刻和多样的阐释。经典的替换、补充、淘汰、更新是一种常态,而正是这种常态,需要叙事理论研究者对这种“常态”作出理论的回应和引导。
标签:小说论文; 美学论文; 普鲁斯特论文; 帕慕克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小说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红楼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伊斯坦布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