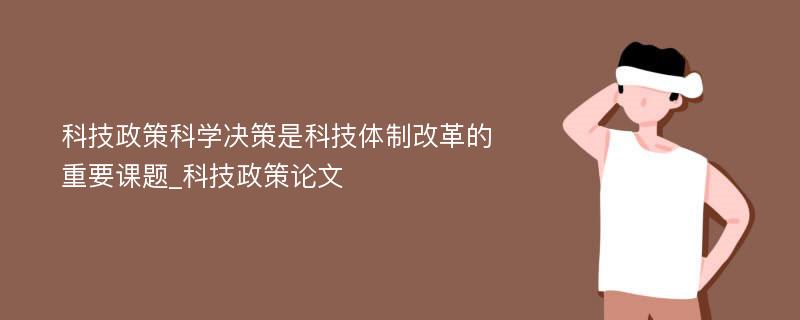
科技政策的决策科学化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论文,一个重要论文,体制改革论文,课题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各国日益关注的政策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一股以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政府制定科技政策依据的潮流(王春法,2003;胡志坚,2000;李正风、曾国屏,1999)。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国家经济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企业,是企业组织生产和创新、获取外部知识的方式。外部知识的主要来源则是别的企业、公共或私有的研究机构、大学和中介组织。因此,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中介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在一国内部的循环流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有助于促进这种科学技术知识的循环流转的方面或者因素都可以划归到国家创新体系之内(OECD,1997;柳卸林,2000)。
自从1996年以来,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开始引起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胡志坚,2000;柳卸林,2000;石定寰,1999)。1997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重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引起了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江泽民对这一报告做出了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传统产业的发展会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机遇。科学院提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从此,国家创新体系成为科技经济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使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增强综合国力、改变世界竞争格局的决定性力量,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日益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发展道路选择,是改变国家命运的战略选择。国家创新体系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我们在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整合社会各主体的创新能力等方面,仍需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
韩国是一个后进奋起赶超先进的典型国家。由于科技发展基础原来比较薄弱,自主开发能力差,因此韩国选择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创新发展道路。韩国采取的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科技发展模式,各级政府鼓励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官、产、学、研协同技术开发行为,提高企业技术研发的水平和效率(涂成林,2005)。任道彬与李显国的《韩国政府创新政策研究:从“划船”到“掌舵”》的研究表明,在个人的创新性低下的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公共组织的特殊文化对于推动创新活动也具有重要作用。尽管韩国政府的整个创新系统具有高度集权特征,决策制定过程却具有参与式特征。在私营部门获取足够能力在企业层面开展研发活动之后,韩国政府就从直接干预的“划船”角色转向间接干预的“掌舵”角色。传统层级制与儒家文化阻碍了东亚人民的创新思考。但是到了21世纪,韩国却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和韩国一样,国民的创新性并不敏锐。韩国的经验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要提高政府部门的清廉度和专业性;二是政府针对技术创新的政策有必要分阶段制定,各国政府应根据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调整政府的角色;三是要充分认识到协作的重要性;四是为实现技术创新,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必不可少。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一方面受国外学者研究的启发,另一方面,在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感到,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区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遂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研讨(孙翠兰,2010)。国外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以实证案例较多,而国内成功的区域创新案例并不多见。国内现有研究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缺乏深层次理论支持,如对区域创新体系如何进化、进化本质等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刘明广、李高扬,2010)。叶林与赵旭铎的论文《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来自英国牛津郡的经验》的研究表明:以美国128号公路地区、硅谷地区以及日本东京地区为代表的传统科技创新城市奉行的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并驾齐驱的科技创新模式,而英国新兴科技创新中心牛津郡的崛起印证了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通过合作关系、非交易相互依赖性、溢出效应与衍生效应四种创新动力机制的构建与发展,牛津郡在市场作用的引领下构建起了一套复杂而行之有效的区域创新系统。牛津郡区域创新体系案例的研究为中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供了不同于128号公路、硅谷与东京的“他山之石”。
随着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科技政策的影响力也日益显著,但是科技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却一直缺乏系统的学科基础,也没有完整的方法体系,这大大制约了科技政策决策的科学化进程(周华东等,2012)。2005年,时任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科技顾问的马堡格(Marburger)不满于已有科技政策研究支撑不力,科技政策制定缺乏事实依据、随意性大,提出并致力于推动科技政策学(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倡议。2006年到2008年,以美国能源部和美国科学基金会牵头的16个联邦科技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一个任务组,研究制定了一份关于美国联邦层面发展科技政策学的路线图(The 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A Federal Research Roadmap)。科技政策学致力于发展科技政策研究的工具和方法,其中定量分析、可视化分析和数据采集所需的工具和方法是主体,如计量经济学、风险建模、选择建模、成本收益、成本效益、系统动力学、网络分析、可视化分析、科学地图绘制、科学计量学、调查、网络抓取、行政数据、数据挖掘;同时,科技政策学也要继续发展一些定性工具和方法,如案例研究、同行/专家评议、德尔菲法、战略/逻辑法等。通过这些工具和方法,以及相关数据的分析和展示平台的搭建,科技政策学提出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和国家战略需求层面关注理解科学与创新、对科学与创新投资、利用科技政策学确定国家优先领域三大主题十个科学问题(程如烟,2012;李晓轩等,2012;刘立,2012)。
科技政策研究首先要揭示科技创新活动的规律。对科学与创新的理解是科技决策者制定政策的基础,是科技政策学研究的微观层面。在这方面,科技政策学主要关注创新的行为基础是什么,如何理解技术的开发、采用和扩散,科学与创新团体如何形成及其演变原因等三个科学问题。
科技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政府资助部门进行合理的分配决策,对科学与创新投资的效益分析是政府进行分配决策的重要依据,是科技政策学研究的中观层面。这方面科技政策学主要关注政府科技投入的价值是什么,科学发现能否被预测,科学发现对于创新产生什么影响,科技投资的效益如何等四个科学问题。
科学投资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其投资决策需要与其他领域的投资决策结合起来考虑。为此,需要发展适当的分析工具,对不同的投资进行详细的相对成本分析和效益分析。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探讨科技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是科技政策学研究的宏观层面。这方面科技政策学主要关注科学对于国家创新和竞争力将产生什么影响,科技工作者的竞争力如何,科技政策中不同政策工具的相对重要性等三个方面的科学问题。
这三大主题与十个科学问题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数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角度研究,共同构成科技政策学。从科技政策学路线图来看,美国政府要通过加强科技政策的方法学,将科技政策研究界定为一门专门的交叉学科,并重在揭示从科技创新到科技政策这个过程的黑箱。总体来看,自2008年科技政策学路线图制定以来,美国科技政策学发展很快,并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已经成为新的科技政策研究的风向标(肖小溪等,2011;周华东等,2012)。
当前,我国正处于迈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如何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已成为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必然涉及众多新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科技决策必须坚持科学化和民主化原则。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现代决策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探索支撑科技决策的好的科技政策的理论与方法。1977年钱学森提出了建立“科学的科学”这一学科的倡议。1986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加强软科学研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报告,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看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后来,万里将讲话稿送给邓小平和陈云审阅。邓小平阅后,一字不改,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也做出批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万里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现在看,虽然我国在科技决策的科学化方面已有了长足的实践与进步,但是,无论是在科学学方面的研究,还是在软科学、管理科学、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涉及的科技政策的研究,仍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的研究主题,与美国传统的模式相似。由此,导致对科技决策的支撑作用有限,科技决策依凭主观经验的色彩依然浓重,决策的科学化还远未实现(刘立,2012;李晓轩等,2012;周华东等,2012)。
科技政策学在美国的兴起,是美国追求科技政策科学化的必然结果。科技政策学的兴起引起了美国科技政策界的震动和改变。中国科技界高度重视科技政策学的发展。2010年,刘延东国务委员在看到科技部中信所的有关介绍后,指示要重视科技政策学的研究。为此,中科院和科技部设立了专门研究课题(刘立,2012;李晓轩等,2012)。
科技政策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单一学科的研究,而是多学科的研究。传统的科技政策研究由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构成。各学科研究自成体系,对科技政策制定虽也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尚不能系统地、完整地回答科技政策的重要问题,从而给予更加有力的支撑(李晓轩、杨国梁、肖小溪,2012;周华东、王海燕、郝君超,2012)。当前,科技政策研究的学者主要活跃于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分支或边缘地带,未能形成界限清晰的科学共同体。现代科技政策学试图构建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通过这一框架将不同学科的研究联接起来。美国科技政策学路线图提出的三大主题与十个科学问题的确是科技政策学研究中带方向性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我国,很多科技政策研究都是课题导向的,往往限于考察和分析实际的具体的政策问题,并被要求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但有些科技政策研究还停留在思辨性的发感慨议论层次(刘立,2012)。美国科技政策学路线图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相比美国而言,或许我们更有必要去建立一套精细化的、基于证据的科技决策系统。相应地,支撑这套系统的科技政策研究也要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向数据平台、分析模型和展示工具等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肖小溪等,2011)。我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迅速成长的大国,应该在国际科技政策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发展科技政策学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亦步亦趋(刘立,2012)。
我们希望中国公共政策学界同仁们能够更加重视科技政策这一未来重要领域的研究,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学人能够加入到科技创新政策领域的研究队伍中来,我们呼吁能够建立起科技政策研究者与科技政策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联合互动的网络,建立不同学科之间、官员与学者之间关于科技政策知识共享与交流的对话机制,从而有效推动我国政府和学界基于国际已有研究基础,结合我国现实需求,通过针对中国国情、实际与实践的科技政策学研究,对当代科技政策学研究能够产生影响和有所贡献,使中国理论与方法成为当代理论的组成部分,并且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