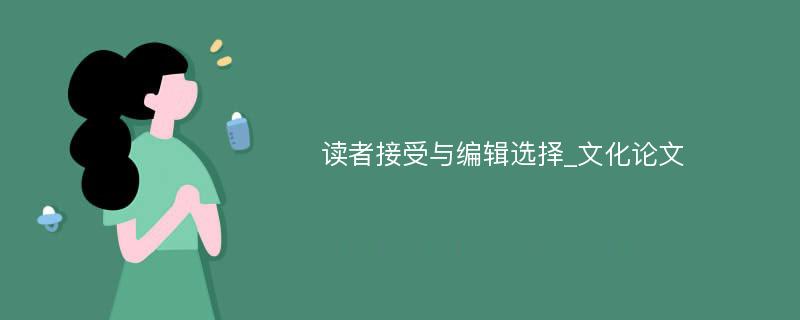
读者接受与编辑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者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类型]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1)04-0151-04
编辑系统研究是整个编辑学建设的基础工程,任何编辑学问题的解决均离不开对编辑系统的深入考察。笔者在《编辑规律探微》一文中,对编辑三元(作者、编者、作者)各自的文化结构及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作了分析,旨在探讨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揭示编辑活动的普通规律。[1]这符合人们对编辑活动认识的传统习惯,但这并不表明在文化传播中三元角色孰轻孰重,也不表明这种序列是永恒不变的。事实上,在市场观念影响下,作者生成文本、编辑传播文本、读者接受文本的次序已悄然发生改变,编者从读者文化需求的角度,策划选题、选择加工文本,已成主流。近年来,“策划编辑”作为一个全新的编辑学名词也已深入人心。编辑三元系统更新重组为“读者-编者-作者”的趋向已日渐明显。这种编辑三元序列的重组趋向已充分说明编辑读者意识的增加。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对读者接受,亦即文本价值的实现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并需从读者接受的角度重新思考编辑的历史责任和文化选择。
一、读者文本接受的过程考察
读者的文本接受过程,从本质上讲,是文本蕴含的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让我们先来看看文本文化价值的实现首先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展开的。庞朴在《文化概念及其他》一文中,曾对文化的结构作了阐释。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物的层次”、“心物结合的层次”和“心的层次”。[2]“物的层次”指“人的主观意识外化为一个物质,它是把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的物,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加以改造使它符合人的需要,这样一个物的东西,脱离人的意识的物的东西”。“心物结合的层次”是说“物化了的物里面的心的部分,就是物当中的人的部分,包含在物当中的人的观念和意识”。作者的作品(自然也包括作者创造的文本)就是一个“心物结合层次”。“心的层次”是指“纯粹的心的部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感情、民族心理等。无论是社会科学的文本还是自然科学的文本,其文化价值的实现首先是通过读者的阅读在读者文化结构的“心的层次”上展开的。当然,社会科学文本与自然科学文本其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又有所不同。哲学社会科学的文本对人的影响侧重在意识形态,尤其是思维方式上,这种影响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的。自然科学文本对人的影响侧重于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但文本的文化价值必然也是首先在读者接受文本,即在阅读过程中实现的,然后再应用于社会生产实践,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因此,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文本的文化价值的确认和接受的过程,文本的文化价值实现的第一层面或首要环节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那么读者是如何接受文本,如何实现文本的文化价值的呢?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和西方接受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读者的文本接受过程。
中国传统文论在接受、评价作品时,向来重视“顾及其人,顾及其文,顾及作品所处的社会时代”,这有助于读者客观认识和评价作品的思想主题。但我们也看到,一部作品即便是一部经典的传世作品,主题的模糊性也客观存在,多重主题的现象不为鲜见。“诗无达诂,文无定评”是相当普通的现象。西方文论中也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一部作品的多重主题并不一定是作者的原始初衷,文本的主题有时会因时因人而异,读者对文本接受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认识。一部《红楼》,“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其个中原委中国传统文论曾一语道破,那就是因为作者“文不逮意”、读者“以意逆志”。但这种感悟式、点评式的评论,未能从理论上对这种复杂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文学文本均具有未定性,都不是能够产生独立意义的存在。文本是一个多层面未完成的“图式结构”或曰“空洞结构”,作者创造的文本留有供读者填充的“解读空间”,读者通过阅读使之具体化。[4](P.449-P.451)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由作者单方面独立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读者和作者共同创造的。这一理论十分重视读者在文本意义创造中的作用,“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作者创造出来的文本没有读者阅读、接受,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结构”的客观存在,文本的意义不能生成,文本的价值也就不能实现。另外,这一理论还对接受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作了阐释。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是由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亦即读者之间“从已读过的作品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对不同文学形式和技巧的掌握程度,以及读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平与欣赏趣味等”[4](P.453)的不同。也许,任何一种理论都是跛足的,都试图在自身单一的理论框架中解释所有的问题,接受美学同样未能摆脱自身的命运。该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70年代在西方学界渐趋衰微。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大量译介接受理论,文艺界曾掀起接受美学的热潮,90年代中期以后,也逐渐淡化。但接受理论对阅读活动的研究和阐释已相当深入,学界也从未否定这一理论的巨大启示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论及西方接受理论对受众接受的阐释主要是针对文学文本而言的,其他文本尤其是自然科学文本其解读空间显然要小一些,但因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解读的差异性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在读者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将接受理论引入编辑学领域,将会给编辑出版工作带来新的启迪。
二、读者文本接受对编辑文化选择的启示
接受美学对“文本—读者”的关系作了细密的研究。接受论者瑙曼指出“社会中介机构”如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学宣传和文学教学等等,在文本生产和个人接受之间的作用。他指出:社会中介机构“代表了社会的、阶级的、集团的意识,指导读者应如何评价作家、作品,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学流派和文学时期、甚至整个文学史,应当阅读或不应当阅读哪些作品以及哪些作家的作品,应当以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标准去衡量作品”。[4](P.453)瑙曼在这里已注意到了社会中介机构对读者阅读接受的制约因素,只是没有进一步地阐释编者对读者文本接受影响。其实编者对读者接受的作用是巨大的。读者之所以能够接受到好的文本,首先得力于编者对文本的确认。一个好的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往往能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但如果不能得到编者的确认,文本就不能被发表,读者也就无法接受文本。从这个意义讲,编辑应该担负着文本选择的“伯乐”角色。编者在文本选择上如果失之偏颇,稍有不慎,就会酿祸成灾,愚昧、落后的文本对读者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法轮功之所以贻害百姓,法轮功的那些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文本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泛滥,甚至能在一些正规出版社“出笼”,不能不说与编辑文本选择失误有关,教训是惨重的。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驱动、管理不善的问题。
考察读者的文本接受过程对编辑工作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着重探讨读者接受对编辑文化选择的启示。
(一)编者对文本的选择
编辑作为联系作者、读者的中介,具有导播和导读的双重文化功能,其中最重要就是选择优秀文本。在新形势下,优秀文本应该是先进文本、原创文本和精品文本。
1、先进文本。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者原创文本经编辑策划、选择、加工、组构形成传播母本。这种文本应该是能够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本,应该是社会先进文化的粒子。因此,从本质上讲,编辑活动中文本的传递,应该是一种先进文化的传播过程;读者阅读、接受文本,也是一种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增殖的过程。文化学认为,文化传播过程中,原有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时,原有文化便会呈现出维模功能。所谓维模(Latency)就是原有文化圈维护自身原有的文化模式。如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模式的维护,有利于优化和完善原有的文化模式,那么这种外来文化就容易被接受。如果外来文化不利于原有模式选择和完善,原有的文化模式就会拒斥外来文化的侵入。那么什么样的外来文化才有利于原有模式的维护和完善呢?文化学也告诉人们,文化具有优势扩散的功能,即先进、优越的文化,易于被愚昧、落后的文化所选取和接受。这与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化学所说的“维模功能”和优势扩散功能,虽指不同的文化圈内的传播和接受的关系,但基本理论同样也适用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文本、读者同样也具有深层的文化结构,文化的维模和优势扩散功能同样也作用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这就是说,先进文本易被读者接受,落后文本易被读者拒斥。编者就应该选择易被读者接受的先进文本,这样才能实现先进文化的有效传播,才能实现文化增殖。如果我们选择的文本是低级庸俗、愚昧落后甚至是反科学、反人类的文本,那么,尽管这些文本有一定的市场,能够迎合某些人的低层次需求,但这类文本在整个文明进程中,在文化传播、文化积累、文化增殖的过程中,就只能是一个负值,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2、原创文本。接受理论认为文本意义的生成和实现有待于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根据自身已有的阅读经验、生活经历去填补文本的“结构空间”。而填充“空间”的前提是文本要能够激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吸引读者。这种文本应当是富有新意、具有创新精神的“召唤性”结构。文本的新意总的来说表现在选题新、观念新、材料新、方法新、体式新、语言新等诸多方面。不同类型的文本其创新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抄袭别人,重复自己,人云亦云的文本肯定是缺乏新意,难以唤起读者的接受欲望的。刘杲先生对理论创新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新,就是独创性,道前人之所未道。新,就是在认识上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深入本质,更加接近真理”。[5]笔者认为,这两点是衡量理论文章尤其是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意义,是否属于原创的标尺,两者缺一不可。仅仅是“道前人之所未道”,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更加符合实际、深入本质、接近真理。杨振宁博士曾说:“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6]任何一门艺术或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寻求创新的过程,也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才富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激发起读者的接受欲望。编者在选择稿件时,应能站在学术前沿,鼓励发表一些富有新见的文本。
3、精品文本。接受美学在充分肯定读者“期待视野”存在的同时,也认为“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延伸的接受链条中才能被读者所发掘出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垂直接受”。精品文本乃至经典文本往往所含信息量大,解读空间大,往往具有较广的读者面,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另外,精品文本往往具有强大生命力,随着时间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精品文本的意义会被读者重新解读,不断生成新的意义,从而使原有文本的意义越来越丰富。一些经典古籍重新被编辑、出版,其目的和意义即在于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文本具有较大的文化增殖潜力。
(二)编者对编辑手段的选择
从引导读者接受的角度看,编辑的文化选择还包括对编辑手段的选择。具体采用何种手段应从引导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视文本的思想性、时效性、可读性而定。
1、编辑技术的选择。包括文本形式(版式、字体、字号、装帧等的选择)和传播媒体(书、报、刊,广、电、网)的选择。编者对文本形式的选择,主要应从吸引读者接受、易于读者接受和引导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考虑。对重点文章采用黑体标题,无疑是提醒读者注意,并暗示读者这是一篇重点文章。政论、社论等思想性强的文章,排列严谨,切忌花哨,也是出于维护文本内容的严肃性考虑的。文艺作品重视形式美感、版式活泼。作者对文本形式的选择应坚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的原则。对传播媒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文本的时效性。一般说来,从图书、期刊、报纸到电视、广播、网络,文本传播的时效性渐强。
2、编辑辅文的选择。所谓编辑辅文是指辅之于文本正文的编者话语。如发刊词、编者按、卷首语、编后语、摘要、关键词以及部分凡例、题解、索引等等。编辑辅文相于文本自身来说处于辅助位置,但对读者接受文本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编辑辅文是最能体现文本的编辑含量的,一篇好的辅文往往言简意赅,笔墨精粹,具点染之功。顺便提及的事,关于编辑辅文的界定、性质、功能、作用、写法等等,编辑学界尚无专人研究,亟待有志者耕耘。
3、组构方式的选择。按什么样的次序组构文本,编者要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习惯和阅读习惯。文本单独成篇,相对独立,也相对完整。但经过编者的精心组构就会产生意外的接受效果,这就是组构学中两者之和大于两者简单相加的1+1>2原理。有些报刊辟有“争鸣”栏目,甚至在同期杂志上相近位置聚合刊登两篇意见相左的文章,其用意就在于让读者充分发挥主观潜能,参与评判是非得失,引导读者最大程度地对文本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收稿日期]2001-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