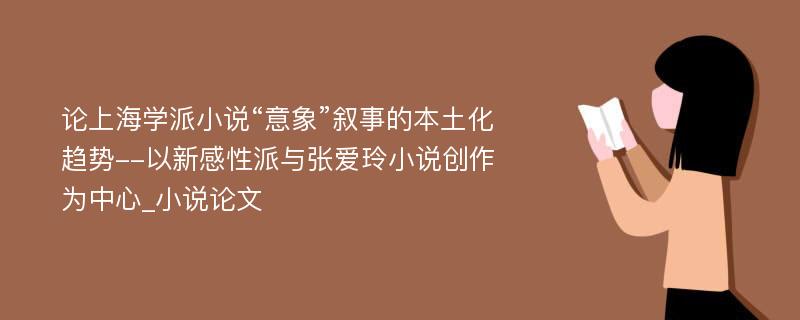
论“影像”化叙事在海派小说中的本土化走向——以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小说论文,本土化论文,以新论文,影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3)04-0130-07
作为新文学的一大支脉,海派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空场域——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学的“民国机制”①为其沟通中外古今的自由创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多元包容的氛围中,1920年代末,海派小说应运而生。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海派是指20年代以张资平、叶灵凤等通俗性爱小说写作为标志的新海派;第二代海派则是指30年代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颇具现代派先锋性的新感觉派;后期海派即是指40年代主要以张爱玲的新市民传奇小说为代表的经典海派。海派小说以自觉的先锋意识和现代技法描摹都市文明,力求艺术上的“变”与“新”,这其中,对电影艺术“影像”叙事手法的借鉴最为光彩夺目。为此,包括严家炎、吴福辉、李欧梵、杨义、张英进、李今以及盘剑等在内的当代海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论及海派与电影这一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总体上看,虽然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家至少“深受三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古典小说、西方的现代小说和新兴的电影艺术”。②然而,研究者们往往对前两种影响颇能认同,而对后一种影响却不太重视。迄今为止,有关文学与电影这两大艺术门类交叉研究的学术成果还远远谈不上丰硕,深入比较海派小说不同时期“影像”化叙事相异性的著述自然甚少,更遑论从本土性视角来研究海派小说中的这一叙事手法,因而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探讨。有鉴于现代“影像”化叙事在20年代早期海派的小说创作中尚不突出显著,故略而不论,在此仅以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为本文论析的中心。
据1930年代一本畅销的城市指南手册——《上海门径》记载,电影这种来自西方的时髦玩艺,“自从流入中国以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并且有艺术上的真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所以智识阶级中人首先欢迎”。③在文学界,尤以海派为最,新感觉派作家和张爱玲本人大都是标准的影迷,甚至还直接参与电影评论、编剧及相关的研究工作,这使他们对电影这种1895年才诞生的最新颖、最生动的艺术形式的成功借鉴成为可能。在文艺实践中,他们往往主动“由文学转向电影”,④并“自觉地把电影叙述方式引向小说”。⑤就“影像”化叙事而言,新感觉派与张爱玲的小说有着颇多共同之处,为了实现文本对象镜头化的审美效果,他们都十分重视对蒙太奇及运动镜头等电影艺术基本技巧的运用,同时,也开始注意到光影、色彩和声音独立的造型、表意作用,有意识地在小说文本中营造一种类似电影假定性的画面感、动态感和立体感。对于海派小说“影像”化叙事的这些共性特征,因前人多有相关论述,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其差异性上。
诚然,新感觉派与张爱玲小说的海派特色均与电影密切相关,然而,二者的“影像”化叙事却是同中有异的。研究者们充分肯定了新感觉派在艺术技巧上的努力创新,认为此派“利用了电影给以他们和人们的‘视觉的教养’,以‘不绝地’‘变换着’的‘流动映像’,织接‘人生的断片’,‘表明故事’而非叙述故事(即蒙太奇艺术),促成了小说文体的又一次‘革命’”,⑥其创作显示了20世纪现代小说艺术实验和发展的一种趋向;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其严重表面化及纯西化的缺陷,指出其创作对电影的借鉴还停留在直接嫁接、完全模仿的初级阶段,难免“于人生隔一层”,“一眼望去,也许觉得这些东西比真的还热闹,还华美,但过细检查一下,便知道原来全是假的”,⑦批评其作品虽能给读者以充分的视觉享受和快感,却无法给读者以更大的心灵震动,也即是说,其小说的“影像”化叙事有太过西化、缺乏生命质感的外化特征。然而如何才能从“外化”进入“内化”、从“西化”走向“中化”呢?40年代的海派代表作家张爱玲最终围绕着“意象”营构这一核心,凭借着对电影中那节奏从容、内蕴丰富的长镜头、慢镜头及旁白的深度发掘实现了这一质的飞跃,就“意象”而言,新感觉派与张爱玲小说的“影像”化叙事的差异性乃是通过意象选择及意象描写来体现的。
首先来看意象选择,由于新感觉派小说从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到表现手法都深受西方文化艺术,尤其是当时最具冲击力的电影文化艺术的影响,其意象往往来自于西方现代艺术世界中常见的充满了肉欲与物质感觉的标志物。在他们作品的意象群中,描写欲望化女体时的蛇、猫、鱼等动物意象频频出现,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在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那位男人的眼中的蓉子姑娘就变成了“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而在其《墨绿衫的小姐》中,醉卧在床上的那位穿墨绿衫的小姐,则由原本的现代淑女瞬间化为“一条墨绿色的大懒蛇”;⑧又如在刘呐鸥的《游戏》中,那些游戏者玩赏的女体呈现出的是“那高耸起来的胸脯,那柔滑的鳗鱼式的下节”。⑨综合来看,此类过于抽象且远离中国现实的动物意象几乎完全放弃了人的主体性及个性发掘,使女体的欲望外化为都市的一种符号,这种带有异域色彩的意象显然主要是受好莱坞电影影响想象西方的产物,暴露出了新感觉派作家在深层体验都市生活上的不足。
此外,其作品中还充斥着代表现代文明的诸如香烟、报纸、洋酒、汽车、舞厅、饭店、影戏院、交易所、夜总会、爵士乐及霓虹灯和广告牌等都市外在的景观意象,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意象常常以密集的意象群出现在文本中,并且主要以频频切换的积累蒙太奇(是指将一系列性质相同或相近的镜头组接在一起,通过视觉的积累效果,造成强调作用的一种表现蒙太奇)及快速连续的摇移镜头来展现都市漫游者的直觉印象。所以,《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那位揣着“臃肿的骆驼牌”香烟的尼采主义者,“嘘嘘吹着沙色的骆驼”,却接连出入于球场、赌场、舞场、酒馆、咖啡馆等追求感官享乐的标志性场所;《上海的狐步舞》中,夜上海的马路上奔跑着“奥斯汀孩车,爱山克水,福特,别克跑车,别克小九,八汽缸,六汽缸……电车当当地驶进布满了大减价的广告旗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去”;《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五色光潮里闪过的都市街景令人目不暇接,“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商,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回旋着,永远回旋着的霓虹灯——忽然霓虹灯固定了:‘皇后夜总会’”。⑩
如上所述,新感觉派作家在意象选择上偏重于都市里最具现代性的标志物,具体描写时又偏于表象化,“刻意用漫游性为途径”,(11)喜欢以蒙太奇特别是积累蒙太奇、“行走”式的运动镜头及主观色调等“影像”化叙事手法来描述自己对上海的那份新感觉,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在动态的视觉冲击中深刻感受对象——新感觉派作家感受最为深刻的现代都市的‘速度’和‘节奏’”,(12)其创作外在形式感过强,难免少了一点厚重,一点深沉,因而总有一种夸张空泛、浮光掠影之感,这恰如那句经典断语:“现代城市文化的动力是提供一系列可变空洞的形式,内容却必然地被淡化抽空了。”(13)
与新感觉派作家不同的是,远离了对都市虚幻的现代性想象的张爱玲,把自己的关注焦点转向了都市内在本真的生命形态,她作品中的摄影机往往在上海普通市民身上及其居住的公寓里弄间驻足流连,细细地品鉴新旧交错的都市生活,“在这个更‘地方化’的世界里,生活的节奏似乎押着‘另一个时间的韵律’”,(14)为此,意象的选择也常常是中西杂糅、推陈出新的。比如《金锁记》中“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滴得太过漫长的酸梅汤意象和“一点,一点”,“缓缓的从云里出来”好似狰狞脸谱的月亮意象;《红玫瑰和白玫瑰》中风吹着就“踏啦踏啦仿佛没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程子……”的落叶意象;(15)《封锁》中“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蠕蠕前移的曲蟮意象,以及“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的摇铃意象;《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那雾里“紫阴阴地远远来了,特别地慢,慢慢过去一辆”的黄包车意象等等。(16)这一个个精雕细刻的意象蕴含着张爱玲对市民世俗生活的深切感悟,体现了其融合中外古今的现代艺术审美取向,“展示了张爱玲和现代性的一种深层暧昧关系,它亦是张爱玲小说的醒目标记”。(17)
值得欣慰的是,张爱玲的意象描写不同于新感觉派一味地模仿与照搬西方的电影技巧,而是结合本土的叙事传统与经验,在“影像”化叙事手法上致力于探索符合国人欣赏节奏与口味的各类长镜头、慢镜头及话本里讲故事似的旁白,旨在突破新感觉派的外化与西化的局限,以“外”写“内”,化“西”为“中”,生动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情感和性格,在意象的构建上,以其外在的异彩纷呈与内在的寓意深远而堪称独步。
张爱玲“影像”化叙事独特的中国魅力,首先展现在其长镜头的运用。长镜头是指“较长时值的镜头画面”,(18)“它是在一个镜头内通过演员调度和镜头运动来完成的,由于保持了现实时空的完整而具有纪实性审美特征”,(19)“景深镜头”与“连续摄影”构成了它的基本内涵。如果说,以短镜头的多种组接为表征的蒙太奇是“一种主观的、表现的艺术”,那么追求真实性、讲究场面调度的长镜头便是一种“客观的写实的艺术”。(20)它不但擅长于逼真地再现客观的现实生活场景,而且在描摹人物内心微妙变化方面更见功力;由于在节奏上比较纡徐舒缓,故而抒情气氛较为浓郁。尽管关于长镜头的纪实理论及美学意义是直到1950年代前后才由法国的电影理论大师安德烈·巴赞系统提出,但作为与蒙太奇同样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它的运用从电影诞生之初就已出现,最早拍摄的电影短片《工厂大门》、《火车到站》、《婴儿喝汤》等大都由固定机位的长镜头来完成,而电影史上如《马戏团》(1928年)、《母狗》(1931年)、《公民凯恩》(1941年)等不少杰作也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并提高着长镜头的艺术表现力。
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那从容含蓄的固定长镜头不但有利于意象的营造及其内涵的发掘,而且颇能充分自然地展现东方的情韵,令人回味深长。如《金锁记》中七巧目送季泽走后的那一段,镜头(中近景)正对着玻璃窗及侧立于窗前的七巧,忠实地记录下眼前的影像:“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来,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眼泪。”“玻璃窗的上角隐隐约约反映出弄堂里一个巡警的缩小的影子,晃着膀子踱过去。一辆黄包车静静在巡警身上辗过。小孩把袍子掖在裤腰里,一路踢着球,奔出玻璃的边缘。绿色的邮差骑着自行车,复印在巡警身上,一溜烟掠过”。(21)在缓慢而悠长的固定长镜头下,景深(就是当焦距对准某一点时,其前后都仍可清晰的范围)内的场面调度扩大了镜头的空间容量,让处于前后景隔着玻璃窗的两种生命形态清晰静谧地交汇在一起,窗外悠然和乐的世界恰好映衬出七巧此刻内心世界那份难于名状的孤寂与痛苦,巧妙的景深结构深化了玻璃(类镜子)意象的视觉化表达,真实细腻地反映着现代都市人的情感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静止的长镜头里,为了尊重戏剧空间的连续性,摄影机视点与观众视点是合二为一的,恒定的镜头画面将前景中七巧的表情动作与后景人物的形态变化与进出场景尽收在内,既真实而又不失其内在的多义性。由此,长镜头“使环境和人物在影片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2)它其实“不尽是写实,而是一种‘显现’”,(23)“显示了它潜在的表意性”。(24)至于那面可将前后景中的人物交错重叠在一起的玻璃镜,则形成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始终在提醒着观众去专注于“同一时空中的‘冲突’”,(25)并“赋予观众以探讨的、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所表现的事件”,(26)体现出了张爱玲以单镜头把握事件整体性的意图。不难推想,倘若没有一点儿处理纵向场面调度(长镜头)的意识,她很难写出如此与蒙太奇大异其趣的精彩段落,让熟悉的镜意象由此延伸出新的意义。
其实,《倾城之恋》中也有用固定长镜头进行的镜意象描写,如白流苏在遭到娘家人的冷嘲热讽之后,默然地独自回屋,扑在穿衣镜前自照(中景,摄影机从流苏身后侧对着镜子):“还好,她还不怎么老。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瓷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颔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走了几步,她走一步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27)为了真切地捕捉住流苏对镜细照及自我表演时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张爱玲选择了利用观众视点的长镜头,从这一更为客观的视点出发,人们在前景中看到的只是流苏真实的背影,在后景中看到的则是其由镜子折射出来的虚幻的正面,在此“镜子的景深起着现实空间背景景深的作用”。(28)一番细细端详之后,那镜中依然美丽的形象俨然给予了白流苏十足的信心与勇气,但重新发现自我的一瞬间恰恰也是失去自我之时,照完镜子后的她,其时已彻底异化为一位“金钱至上主义”者。镜意象模糊了自我与他者、真实与虚幻、过去与现在的界线,恍惚间,早已物是人非。在这个从固定机位拍摄的长镜头里,“景框”式的构图使镜子“产生了华丽深邃的‘透视角度’(perspective)”,(29)“它极力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呈现事先已经存在的、成为剧情组成因素的关系”。(30)在此,作者正是借了这种镜头的内在结构寄寓了“一种暗示性的‘道德批判’”。(31)
在张爱玲小说的意象营造中类似的固定长镜头运用还很多,比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的对镜自照、《花凋》云藩给川嫦打针以及《连环套》霓喜为孩子把尿时等场景中都可见它的身影。此外,颇有意味的是,虽然张爱玲也时常借用运动长镜头,不过那镜头移动的速度与节奏也仿佛糅合了古韵古调始终不疾不徐、悠然自得。至于慢镜头(即电影艺术中延长现实中的时间、延长事物实际运动过程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法),由于创作实践中它有助于抒发情感、引人深思甚至创造意境而成了张氏的一种特色,前文所列举的那些经典意象常常由它完成,镜头里流溢的中国风是如此耐人寻味!既或是旁白,也只需去看看《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和白玫瑰》等作品的开头与尾声那或沧桑或反讽带有传统讲唱文学余韵的旁白叙述就不难体会了,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可见,正是以“意象”的营造为契机,得益于动静自如且深入灵魂的镜像语言,尤其是放慢了节奏后十分适宜在上海的公寓里弄那相对狭小的空间表现市民细微人生的长镜头、慢镜头,以及兼有传统“说话”人格调的旁白,张爱玲才成功地超越了新感觉派,出色地实现了小说“影像”化叙事从“外”到“内”、由“西”向“中”的转化,从而促进了海派小说的视觉性与本土叙事传统及审美情趣的对接与融合,创造了东西文化交融的新境界,也成就了张氏小说永恒的叙事魅力。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尽管电影对新感觉派与张爱玲小说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可是仅就电影的两大主要表现手段——蒙太奇与长镜头的实际运用来看,新感觉派的作家显然比较推崇前者,而张爱玲的骨子里却更加注重后者,二者之间的分野及其不同取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试从二者的具体历史背景、性别气质、尤其是更深的文化层面来予以探讨。
1930年代的前半叶,新感觉派进入全盛期,对于这一流派作家们来说,其时虽不乏战争的阴影,但其居住地——上海由于租界林立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地位无形中暂时拉远了他们与战争的距离,不仅如此,这座由西方现代文明催生正走向畸形繁华的远东第一大都市还为其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作为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都市之子,他们总体上较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限制与束缚,而其男性气质似乎也使他们更乐于做都市的漫游者,尽情地畅游于现代物质文化的河流中,意欲在文学世界里“把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描出来”,(32)因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始终停留在都市本身的现代性上,即便其在本民族文化潜在影响下多少感受到了现代性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依然抵挡不住现代都市的魅惑,在思想文化的取向上,还是不由自主地将西方奉为圭臬。正如穆时英在小说《黑牡丹》中借其笔下人物所吐露的心声:“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33)在他们看来,中国大地上新兴崛起的现代都市及其所代表的“新文明的基本源泉就在于‘动’”,“时间与速度就是现代生活的核心”,(34)而“最能够性格地描写着机械文明底社会的环境的,就是电影”。(35)加之,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日本新感觉派影响的他们,坚信“艺术的内容只存在艺术形式里”,(36)于是理所当然地将自己对现代文明的这种新奇感受在小说里进行一种电影化的实践。然而,大概是出于整体把握都市的急切心理,同时又囿于对电影本性认知上的历史局限(30年代的电影界,不少人都只是把蒙太奇和画面的表现主义当作电影艺术本质),如李今所言,最受该流派青睐并实现其主体感觉外化的“新现实”特点的电影技法,只能是视点自由转换、能够创造节奏、具有强烈主观表意性的蒙太奇。客观地说,这种电影技法或许无助于人们深入到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内在肌理,却颇适宜于抒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37)
相反地,40年代中叶,身陷“孤岛”兼有中西文化背景的张爱玲却坚持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进行小说创作,这不仅因为她出身名门,自小其内心深处就有着极其浓郁的“中国情结”,并且这一情结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一直享有相对独立空间的上海“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来自民族国家的压力”(38)之后,愈发深沉且别具意义,就像她自己所总结的那样:“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即使是在写影评《借银灯》的时候,她脑子里念念不忘的也“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39)于是,本着洋务运动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她对那些既“没有多少是中国东西”,又“对外国爱情故事不经批判的接受”的电影如《万紫千红》及《燕迎春》等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并严正指出:“这种和现实双倍远离的情况引起了不少问题。”(40)同时,女性的特殊气质也使她能够越过纷繁的闹市而更关注家庭以及俗世人生的琐细,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那种着意于闺中“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41)的写实传统情有独钟。在其文艺创作方面,她一贯注重“真实性”,非但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大多‘各有所本’”,(42)往往“和现实人物只有半步之遥”。(43)在《自己的文章》里她坦言:“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并在《我看苏青》中,专门谈到了“写实功夫深浅的问题”。(44)
尽管总体上看,“她较少讨论影片的形式与技巧这些涉及美学上的问题”,(45)不过,据前所述,最合乎其纪实性审美倾向的非长镜头莫属,因为“它能让人明白一切,而不必把世界劈成一堆碎片;它能揭示出隐藏在人和事物之内的含义,而不打乱人和事物所原有的统一性”。(46)甚至它“可以表现某种涵义不断地集中、强化、浓缩,以便从纪实性自然‘升华’为象征性”。(47)由此看来,张爱玲一直为人所称道的“细致”、“成熟”和长镜头的运用是颇有关联的。夏志清先生为此曾惊叹道:“她的小说却是非个人(impersonal)的,自己从没有露过面,但同时小说里每一观察、每一景象,只有她能写得出来,真正表达了她自己感官的反应,自己对人对物累积的世故和智慧。”(48)无独有偶的是,张爱玲在《传奇》中对电影手法的这份独特感悟与运用,恰恰与1948年以一部《小城之春》开启了中国诗化电影先河的费穆不谋而合。费穆曾在回应某位批评者的文章中这样坦率地表露过自己的拍摄理念:“我为了传达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用‘长镜头’和‘慢动作’构造我的戏(无技巧的),做了一个狂妄而大胆的尝试。”(49)两位大家的代表作问世的时间仅有三四年之差,这当然不只是巧合。因为从中国的电影发展史看,自1905年国人自制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起,中国电影人就一直没有停止从内容到形式对这门新兴的现代艺术进行本土化的改造,经过约三十年的摸索与努力,随着孙瑜的《故都春梦》、吴永刚的《神女》、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蔡楚生与郑君里合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一批经典影片的陆续推出,民族电影的创制之路日益宽广。需要指出的是,这其中,战争无意中充当了重要的推手。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后,文艺界的民族文化意识不断高涨,至40年代渐趋高潮,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立场的张爱玲和费穆最终分别在电影艺术本土化过程中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如上所述,新感觉派与张爱玲尽管同属于海派,也会因为历史时段、性别气质以及内在的文化立场的各自偏向而形态各异。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是异质形态文化艺术的强势渗入及本土文化艺术的积极回应。在小说领域,现代“影像”化叙事在三四十年代海派小说中的演变轨迹恰好形象地展示了这一复杂的进程。虽然这一叙事手法,在30年代一味追逐新潮的新感觉派作家手中,由于形式上片面追求都市外在景观的视觉化效果,尚有食洋不化之感,基本上仍然是纯西化的“影像”化叙事,但是到了40年代善于“调和”的海派代表作家张爱玲手中后,这一切已悄然地发生着转变,凭借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对上海普通市民生活深切的感知,特别是对蕴含于长镜头、慢镜头等电影手法里中国元素的探寻,她最终开创了自己亦中亦西的“影像”化叙事手法,建构出具有中国“影像”化叙事格调的现代小说范型,推进了海派小说“影像”化叙事的本土化进程。最难能可贵的是,其本土化是“一种开放的、辩证的、具有世界视野的本土化”,(50)其经典之作,让我们看到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在本土的小说创作中可能达到的深广度与高度。
从三四十年代海派小说“影像”化叙事发展走势来看,最值得关注的是长镜头尤其是固定长镜头及慢镜头等电影手法在本土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殊为遗憾的是,这一方面过去一直为研究者所忽略,本文对此也只是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其价值与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识与发掘。
注释:
①李怡:《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②刘澍:《张爱玲的光影空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③王定九:《上海门径》,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2年,第14页。
④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
⑤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⑥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第160-161页。
⑦沈从文:《论穆时英》,《沈从文全集》第16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3-234页。
⑧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6、205页。
⑨刘呐鸥:《都市风景线》,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⑩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第209、120、55-56页。
(11)张英进:《批评的漫游性:上海现代派的空间实践与视觉追寻》,《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12)盘剑:《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13)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14)李欧梵:《苍凉与世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3页。
(1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05、111、135页。
(16)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1卷,第97、188页。
(17)李欧梵:《苍凉与世故》,第47页。
(18)王光祖:《影视艺术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9页。
(19)冯勤:《论张爱玲小说“影像”化叙事的主要特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20)傅正义:《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2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2卷,第105-106页。
(22)邵牧君:《西方电影史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23)李欧梵:《苍凉与世故》,第10页。
(24)金丹元:《论“长镜头理论”背后的哲学及其当下意义》,《戏剧艺术》2000年第6期。
(25)林年同:《镜游》,香港:素叶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26)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208页。
(27)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2卷,第54页。
(28)爱森斯坦:《蒙太奇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29)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台湾大地出版社,1973年,第132-133页。
(30)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31)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24页。
(32)刘呐鸥:《色情文化·译者题记》,《刘呐鸥小说全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
(33)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第126-127页。
(3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8、109页。
(35)刘呐鸥:《电影形式美的探求》,《万象》1934年第1期。
(36)刘呐鸥:“Ecranesque”,《现代电影》1934年第1卷第2期。
(37)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杂志》1933年第4卷第1期。
(38)金浪:《对视中的陌生人——穆时英与现代文学的“视觉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39)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246、179页。
(40)刘澍:《张爱玲的光影空间》,第44页。
(4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
(42)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25页。
(43)张子静,等:《我的姊姊张爱玲》,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4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3、227页。
(45)刘澍:《张爱玲的光影空间》,第46页。
(46)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47)罗慧生:《纪实性电影美学的基本特征》,《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
(48)夏志清:《〈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序》,见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7页。
(49)费穆:《导演·剧作家——写给杨纪》,上海《大公报》1948年10月9日。
(50)晏杰雄:《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本土化路线》,《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标签:小说论文; 张爱玲文集论文; 张爱玲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蒙太奇手法论文; 文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新感觉派论文; 上海的狐步舞论文; 读书论文; 金锁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