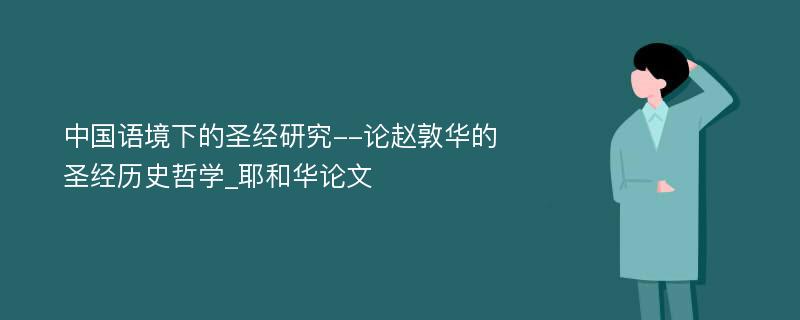
中国语境下的圣经研究——评赵敦华的《圣经历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经论文,语境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总评近年六本圣经研究著作 赵敦华在二十年前出版了那本五十余万字的著作《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早已成为国内基督教研究的经典之作,再版多次,享誉学界,赵敦华因此也被人尊为国内“基督教哲学研究第一人”。二十年后,赵敦华再次奉献给我们学界一部“大书”,这就是近九十万字的《圣经历史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这本巨著再次展现了赵敦华扎实的西方古典学术的功底、基督教思想领域的渊博知识、客观严谨的著述风格,以及在哲学上的真知灼见,堪称是他毕生学术思想的最高成就。《圣经历史哲学》作为《基督教哲学1500年》的前史,从中世纪思想回归圣经哲学,双剑合璧,必将成为国内基督教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 近几年国内基督教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圣经研究的兴起,有人把它叫做“基督教的经学研究”。一方面,它反映了国内的西学研究转向西方经典及其源流的新趋势,在基督教研究中这一趋势体现在圣经研究的转向上,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国内学界在基督教研究领域中日益加深的学术深度。众所周知,旧约研究与新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既有源远流长的古典解经传统,又有圣经批评采用各种现代学术方法的艰深学术研究,一直是基督教研究最核心的领域。国内学界圣经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国内基督教研究逐渐走向接轨西方学界艰深学术研究的趋势。 近十年间出版的基督教圣经研究的诸多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赵敦华的《圣经历史哲学》(2011)还有北京大学东方学系陈贻绎教授的《希伯来语圣经:来自文本和考古的信息》(昆仑出版社,2006)与《希伯来语〈圣经〉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系游斌教授近六十万字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与《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以及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查常平的《新约的世界图景逻辑(第1卷)引论:新约的历史逻辑》(上海三联书店,2011)。 除了这六本研究著作之外,还应该格外提及的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的圣经翻译。众所周知,圣经翻译与评注不仅需要多种西方古典语言的高深知识,而且也需要对圣经有艰深的学术修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两大名校毕业的冯象教授正堪当此任,目前已译出《摩西五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智慧书》(2008)、《新约》(2010)以及《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三联书店,2006)等,公认的优点是文辞典雅,译笔讲究,达到了信达雅的境界;而其缺点也是文辞过于讲究,未能完全贴近他自己所说的圣经文体的“素朴”风格。 上述六本圣经研究著作采用了不同的范式与方法,在对西方学界圣经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的取舍中,能够充分体现出中国语境对基督教学术研究的影响。陈贻绎的旧约研究没有采用基督教旧约神学研究模式,而是采用了希伯来圣经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多学科的现代历史批评范式,以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圣经考古学以及近东历史(苏美尔、巴比伦、亚述、亚兰、埃及、赫梯、腓尼基等)的考古成果、近东神话的文学研究、希伯来语和亚兰语等近东语言的语文研究、犹太教产生的以色列历史背景以及近东各个古文明的历史背景、以及犹太宗教的发展演化的进程,作为诠释希伯来圣经文本的历史语境、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这种范式往往集中于探究与考证旧约圣经的创世神话、大洪水神话、该隐杀兄故事、约瑟故事、出埃及传奇的近东神话与传奇的来源、摩西五经成书的四源说(JEDP)、以色列人的习俗与乌加里特的迦南文学的渊源、以色列人的立约与近东契约的渊源、以色列人的律法与汉漠拉比法典的比较、一神论崇拜的近东宗教史起源、出埃及、士师时期、以色列王国、耶路撒冷被毁、巴比伦之囚、先知运动、祭司派运动等史实。陈贻绎两本著作遵循的范式主要以奥尔布赖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布莱特(John Bright)、阿尔特(Albrecht Alt)、诺特(Martin North)等人的宗教史考古为代表,后来的门登霍尔(George Emery Mendenhall)和戈特瓦尔德(Norman Gottwald)等人又从以色列社会史的视角补充了上述的历史考古的研究方法。陈贻绎的两本希伯来圣经的研究著作客观严谨、编排得当、资料丰富,是“以色列古史辩”范式中的力作。 陈贻绎著作采用的是希伯来圣经的宗教史考古与近东文学文化比较的研究范式,对旧约神学没有太多的兴趣。与他不同,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研究著作在文学分析与历史考证之外,更多了“旧约神学”之维。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将文、史、哲(严格来说是神学)三个维度交织在一起,较为全面地描述与解释了希伯来圣经的文学、历史和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他也吸收了近东考古学、近东文学文化比较以及社会学这三种主流范式的学术成果,但却没有采用这种实证史学的研究范式,而是立足于对旧约神学的整体理解与解释,展示了希伯来经典与以色列信仰群体以及犹太历史传统之间密不可分的动态关系。游斌的著作在方法论上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他所运用的旧约神学方法实际上主要是深受20世纪旧约神学大师冯·拉德(Gerhard von Rad)的“传统传承史”的方法,以及拉德的弟子耶鲁大学的蔡尔斯(Brevard Childs)的“正典批评法”的影响。他从以色列信仰群体的传统传承和希伯来圣经文本的正典形成的过程和最终成型的形式的视角,分析了希伯来圣经作为犹太信仰群体的正典是如何形成并世代传承的。这一解释模式也贯穿与《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之中,从这本书的书名上我们就能看到这种解释模式的基本纲领。此外,在论述西奈与锡安两大传统时,他也深受哈佛神学院的列文森(Jon D.Levenson)的影响。但由于对利科的叙事学、缪伦伯格(James Muilenburg)的旧约修辞学以及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和珀杜(Leo Perdue)等人的“后现代旧约神学”很少涉及,因此他的“正典批评法”并没有在文学和政治的维度上得到充分的拓展和深化。尽管如此,与陈贻绎的著作相比,游斌的著作无疑在方法论上更胜一筹,因为陈贻绎所采用的那种模式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受到了严厉批判,而游斌注重以旧约神学的基本主题、信仰群体的宗教传统、活的律法、崇拜实践以及宗教经典的形成、发展、传承和解释的历史来贯穿和整合个旧约圣经的诠释,则体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旧约神学研究的新范式的学术成就。 同样是从圣经神学而非历史批评的视角出发,查常平在新约研究中试图以救赎史的框架融汇语言、时间、正义和信仰四大范畴,系统地论述新约神学中的历史与逻辑。不过,他试图建构融贯地解释新约历史的圣经神学范式的尝试看起来并不太成功,可能是作者在神学素养以及哲学思考的深度上还有所欠缺。 相比之下,赵敦华的圣经研究对新约历史的解释则更为融贯,解析的程度也更为清晰细腻,饱满丰富。正如这本著作的标题《圣经历史哲学》所示,这是一本关于“圣经历史”的“基督教哲学”,是对圣经历史的哲学解释。然而,圣经文本中的历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承载、经历和见证了上帝与其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以及上帝与普世的人类之间关系的历史,是一部贯穿了旧约和新约的历史跨度的救赎史,是集史实、史观和史评于一身的历史。因此,在解释这部独特的历史的时候,其方法论的原则就既不能同于对待一般的文学文本,也不能同于对待纯粹的历史文本。 在中国的语境去理解和解释西方的经典时,尊重犹太人和基督教传承下来的神圣经典应该是首要的原则。正是基于对“经典中的经典”的敬重甚至是敬畏的态度,赵敦华首先将圣经历史作为救赎史接受下来,并将这一救赎史的解释框架贯穿于旧约和新约的叙事分析之中。但与此同时,他并不认为救赎史与世界历史是截然二分的,救赎的奇迹是完全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无法证明的。相反,他所要做的哲学解释就是要在自然理性的限度之内最大限度地解释所谓启示或神迹的事件仍然是可理解的,作者将其称之为“救赎智慧”,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救赎或奇迹的可理解性”。这一方法论的规划在一个层面上类似于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的神学解释学原则,所不同的是它并不需要像布尔特曼那样将那些看起来是神话的东西还原到生存论的层面,而是要将其尽可能还原到自然科学、上古史和人类学的层面,以充分理解和解释旧约和新约中所记载的通过历史进行救赎的意义。由此,这本书立论的成败与论断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都系于这一解释学原则。 二 《圣经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与圣经历史叙事学 赵敦华的著作不能被归为“圣经神学”,与游斌的著作相比,可以说它的“圣经神学”的色彩在中国的研究语境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淡化。赵敦华将他的著作自我定位为“圣经哲学”,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对圣经历史进行哲学解释的圣经批评与圣经叙事相结合的著作。这本“圣经历史哲学”是关于“圣经历史”的哲学之作,因此,它以首先接受圣经的救赎史观念为前提。而接受圣经的救赎史叙事,就要对发端于霍布斯、斯宾诺莎和莱辛的现代圣经批评进行一个彻底的清算。众所周知,现代圣经批评所预设的一系列前提都是对圣经的救赎史叙事的彻底质疑,它遵循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标准质疑和解构圣经历史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圣经批评是霍布斯、斯宾诺莎和莱辛这些早期现代哲学家的宗教批判的一部分,是科学民主与宗教之间的斗争史的一部分,是现代哲学战胜宗教信仰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其目的也毫不含糊地指向对作为基督教宗教的神圣经典的圣经的解构,最终彻底剥除它作为基督宗教的神圣经典的属性,仅仅将其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经典文学文本无害地保存下来。 然而,去除圣经文本的宗教神圣经典的属性,就不可避免地在最大程度上减损了这一经典文本携带的文化信息,如果像我们现在通行的观念将宗教也视为一种文化传统那样。因此,当我们即使并不是出于对基督教教会的神圣经典的信仰,而是出于对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尊重,而试图尽可能整全地理解圣经旧约与新约的文化信息,这时候现代圣经批评对圣经叙事的摧毁性的态度和方法也不再适用了。 为此,必须要对现代圣经批评的基本原则进行一个反批评。赵敦华将它所预设的那些不言自明的现代哲学前提归纳为十种理论态度:一,否认神迹;二,否认圣经历史的客观现实性;三,怀疑圣经历史见证的客观性;四,否认圣经无谬;五,从宗教进化论的宗教学原理解释圣经文本的发展阶段;六,以文化背景决定论解释圣经的文本和圣经的文化世界;七,以社会决定论解释圣经作者以及圣经的思想观念的起源;八,从宗教先验主体性和信仰生存论解释启示与信仰;九,以后现代主义修辞学或原型批评解释圣经的文本性;十,以语文学索隐圣经文本的寓意或以接受理论强调对圣经文本的当代应用(《圣经历史哲学》上卷,第2—10页)。赵敦华提出要对于现代圣经批评中这些看起来不言自明但却是很成问题的哲学前提“重估其价值”。只有对整个现代圣经批评的局限性有明确的意识,才能找到适宜理解和解释圣经的历史叙事之路。 我们仅举两个小例子。比如,作者批评了威尔豪森的摩西五经成书的 JEDP“四底本说”,并严厉批评了从威尔豪森范式引发出来的那种以近东神话、近东法律和近东历史来解释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的做法(实际上这就是陈贻绎著作所采用的范式),他指出:“这种评判的致命缺点有三:一是以名乱实,没有看到族长崇拜的耶和华和神是同一上帝;二是颠倒因果,没有看到族长的耶和华崇拜是以色列祭司崇拜的原因,而不是后者的结果;三是本末倒置,没有看到族长的耶和华崇拜有其自身起源和发展过程,而不是中东宗教史的分支末流。”(上卷,第112页)再比如,作者在谈到以色列人的“盟约与律法”观念时,严厉批评了以近东的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盟约以及近东各民族的法律习俗来解释以色列人的“盟约与律法”观念及其起源的做法,他指出:“无论什么时代的法律或盟约的文本形式,都不能容纳《申命记》中的叙事,不能取代描写誓约现场的庄严感,没有‘摩西之歌’那样的诗歌文体,更没有耶和华亲临现场的启示(《申命记》31:14—23)。如果把《申命记》这些内容都纳入到宗主权盟约的结构中,难免陷入削足适履的解释困境。”(上卷,第203—204页) 在重估三百年现代圣经批评的价值之后,赵敦华在“导言”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十条解释学原则:一,回归圣经历史作为“救赎史”;二,坚持圣经的救赎史中“神意”的本体论地位以区别世界历史;三,救赎史也有世界历史的客观的可理解性;四,圣经的启示是使人自由的“真理”;五,救赎史是罪与救赎之间的辩证;六,救赎的智慧有其理性之维;七,坚守圣经语言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上可理解性;八,圣经解释应该建立在各种现代科学知识基础之上而不必牺牲理智;九,解释圣经文本应坚守整体论肯定其整体无谬;十,圣经解释也不可避免会有局部上的错误(上卷,第13—34页)。这十条圣经历史的哲学解释的解释学原则,贯穿于作者对旧约和新约的整体性解释之中。 根据这十条解释学原则,作者试图克服三百年现代圣经批评的局限性,拒绝现代圣经批评对圣经叙事不合理的肢解,在最大程度上捍卫了圣经历史叙事的完整性。与此同时,作者又试图在最大程度上捍卫圣经历史叙事的可理解性,避免完全从基督教信仰者的内在护教的视角规避理智诚实的批判。当然,对于那些信仰群体或想要原汁原味地了解犹太—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人来说,为了强化可理解性而频繁援引各种现代科学观念,尤其是现代人类学的观念来解释圣经历史,未免太适应现代人口味而流失太多对那个宗教传统来说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失乐园到底是背叛上帝之罪与罚还是乱伦禁忌问题;而对于大多数持无神论立场的“普通读者”而言,试图以各种现代知识为圣经的救赎史叙事进行辩护性解释,又未免过于回护“宗教立场”。由此可见,欲在救赎史叙事与哲学解释二者之间实现平衡,是一份何其左右为难的解释学的任务。赵敦华的著作在何等程度上完成了这一艰难的任务,在二者的张力之下找到了艰难的平衡,这有待于读者的检验。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对犹太—基督教的救赎史的信仰和观念给出了一份通情达理且合情合理的理解与解释,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中国读者。 可以说,赵敦华给出的充满内在张力的十条解释学原则以及全书所采用的叙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语境下的圣经研究的独特性。尽管作者接受了圣经历史叙事的救赎史的框架,但是这不是基于信仰群体或教会的宗教立场,因此,作者并没有采取“圣经神学”的基本模式。“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的兴起受到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辩证神学革命对19世纪以及整个三个世纪以来的圣经批评及其自然神学和自由神学的前提的彻底批判的激励。就旧约神学而言,正是在这一大转折的前提下才一反从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到衮克尔(Hermann Gunkel)的旧约批评,诞生了20世纪30年代的艾希洛特(Walther Eichrodt)和50年代的冯·拉德两大旧约神学范式,开启了70年代以来由海德堡大学的伦特多尔夫(Rolf Rendtorff)、耶鲁大学的蔡尔斯、哈佛大学的列文森以及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巴尔(James Barr)等人领衔的旧约神学的鼎盛局面。新约神学方面也是如此,巴特对新约神学的决定性影响也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圣经神学”范式是面对三百年来现代圣经批评的一个反运动,是有非常坚定的宗教立场的。赵敦华的著作并没有像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和《圣书与圣民》那样站在上述的圣经神学的立场,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中国这种解释的立场缺乏一个很强的宗教背景,缺乏一个信仰群体和文化传统的支持,相反,它需要面对的是知识界的文化场域以及长久以来深受无神论教育的读者,因此,解释者必须适应接受的受众来确定自己的解释方式。 赵敦华对圣经历史的二阶叙事实际上比较接近于叙事神学(Narrative Theology)模式,在“圣经神学”和纯粹哲学解释(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化学)之间走了一条中道。在哲学上“从解释学到叙事学”的转折是由利科(Paul Ricoeur)完成的,而在神学中从神学解释学到叙事神学的转折是由深受巴特影响的耶鲁大学的弗莱(Hans Frei)、林贝克(George Lindbeck)和豪尔沃思(Stanley Hauerwas)等人完成的。采用叙事神学的模式有助于将“圣经神学”的主题转化为通常可理解的叙事,但又不必将其化简为简单的史实的实证或文学的赏析。根据叙事神学的模式,赵敦华拒斥圣经考古、比较宗教以及社会学还原的历史主义批评,也反对那种将旧约与新约以及将旧约新约各章节“拆分”论述的流行做法,他特别强调圣经从以色列人救赎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事件之间连贯的脉络,并从救赎史叙事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整合旧约和新约历史叙事的框架。它克服了希伯来圣经与基督教旧约、天主教旧约之间的编排次序的出入问题,也克服了希伯来圣经还有次经、伪经、死海古卷、希腊语和亚兰语译本以及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塔木德解经传统,从救赎史叙事的框架强调了希伯来圣经核心部分的结构和次序的稳定性以及基于以色列、耶和华、宗教救赎之上的主题的统一性。至于希伯来圣经或旧约与新约之间的统一性难题(一个是上帝与以色列民族之间应许与救赎的历史,一个是上帝与耶稣基督之间三位一体的救赎事件;一个是上帝一神论,一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一论),作者的救赎史叙事的模式已尽可能克服那种通行的以新约为中心的救赎史模式(无论是库尔曼的救赎史神学,还是潘能伯格的历史神学)或以新约为中心的圣经神学模式,从上帝在世界历史中展开的救赎史(它既包括了旧约的出埃及,也包括了新约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与复活)出发,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两约的连续性。 我们可以举两个小例子来说明作者的叙事策略。比如,在解释旧约中第一篇“智慧文学”《约伯记》时,作者将《约伯记》放在族长时代的背景中,将其视为约伯的耶和华一神论与外族人多神论之间的一场论战(上卷,第128页)。于是,《约伯记》在救赎史的框架中就被定位于从《创世记》到《申命记》这段一神论与多神论论战的阶段以色列人通过与他者的斗争确立自己的一神论信仰之作。作者因此认为,通常将《约伯记》视为“神义论”之作的看法是不得要领的(上卷,第147页),因为耶和华的一神论信仰的确立要先于神义论问题并且是神义论问题的前提。神义论问题并不是《约伯记》的主题,而是现代人的问题关切的投射。再比如,作者遵循古老的传统,将大部分《诗篇》都置于大卫王的叙事这一章,而将智慧文学中的《箴言》都置于所罗门的叙事这一章来加以论述,这也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叙事策略所做的安排。 总而言之,虽然作者处理了如烟海的材料和各家各派的解释,但却都能以自己独特的叙事框架加以剪裁梳理,形成了自己前后一贯的叙事脉络。作者并没有囿于繁琐的语文、历史和神学的考据,也没有受制于那些数不清的学术论点的争议,而是以自己深刻的哲学洞见驾驭丰富的材料,创造了一种将鞭辟入里的哲学分析、精彩纷呈的叙事和渊博的知识融为一体的夹叙夹议的风格,让读者读起来就像是在阅读一本津津有味的故事或一本令人兴致盎然的侦探小说,近九十万字的巨著从头至尾可以一气读完。就此而言,这本书不仅在思想深度和视野的开阔上远远超过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而且也比后者更能展示作者的叙事才华,更具有可读性。 三 以《创世纪》、《申命记》和《以赛亚书》为核心的旧约历史叙事 我们首先来讨论《圣经历史哲学》中以《创世记》、《申命记》和《以赛亚书》为核心的旧约历史叙事,绕过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着重讨论作者的一些创见。 在解释摩西五经时,作者引用《申命记》(7:1—10)中的一段话来总结摩西五经中救赎史的五个阶段:“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第四阶段),……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三阶段)。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第二阶段),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第一阶段)。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第五阶段),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决不迟延。”(上卷,第149—150页)作者运用这一救赎史线索来统领摩西五经的历史叙事,使整个摩西时代的以色列史在一个宏大的救赎史视野中呈现出一个结构完整的叙事。 在摩西五经的救赎史叙事中,作者又通过“立约与律法”的主题,集中阐发了摩西五经中最重要部分《申命记》的深意。作者对《申命记》浓墨重彩的分析特别能体现这本书的叙事风格和思想精髓。作者将解释《申命记》的章节标题写作“誓约新/心/薪传”,其用意在于指出,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或“誓约”乃是以色列人的救赎史观念的基础:“新传”即摩西给以色列人立下的新的律法,其核心都在于“心传”,即“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而它必将被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薪传”下去,即“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上卷,第202页)。 艾希洛特的旧约神学就是以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立约”立论的。但是,冯·拉德就针锋相对地指出,用“立约”这一单一主题很难贯穿整个旧约神学的。实际上,在《申命记》的摩西叙事中我们能够看到誓约、拣选、应许(应许之地)、律法、诫命(十诫)、反偶像崇拜、圣洁以及一神论等等所有这些旧约神学的基本主题都尽在其中了。不仅如此,《申命记》还是“申命派历史”的基础,因为《申命记》乃是救赎史观的第一次表述(上卷,第225页),它也是后来的先知神学的基础,因为摩西也被视为是第一个先知,“摩西是先知传统的开创者”(上卷,第226页)。 不过,作者并不赞同通常的所谓“申命派历史”的说法,即将《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这五经视为“申命派史家”所写的史书。因为前三篇的救赎史是以摩西为中心的关于“应许之地”的历史,而后两篇的救赎史则是以大卫为中心的关于“应许之国”(即以色列王国)的新历史。其中《撒母耳记》中的撒母耳是这一区分的关键之所在,因为撒母耳在祭司制度衰落之际,开创了先知运动与神权政治的新历史(上卷,第260页)。在解释据说是支持“君权神授”学说的最早的神圣经典文本《撒母耳记》时,作者澄清了旧约政治神学中的一个长久以来的根本性谬见,即“君权神授”乃是对君主绝对权力的支持。这是现代人以“民主与专制”这类现代观念强暴地歪曲古代观念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指出,在旧约中,君权神授的意思乃是“强调上帝通过正当性和合法性对君王权力加以制约,乃至于通过先知、祭司、军队和民众的社会合作力量推翻丧失正当性的君王”(上卷,第271页)。作者通过细致地分析撒母耳膏立后来被废的扫罗与后来被兴的大卫的情况指出,旧约中神权政治的正当性是由上帝、先知、祭司、军队和民众五重力量的共同认可构成的,它的复杂构成在政治哲学上要远比现代的单纯法理性的合法性观念更为深刻。由此也可以看出,犹太教的神权政治与基督教教会的神权政治以及罗马帝国的政治神学这三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对《撒母耳记》的分析作为一例,特别能体现作者在哲学上的真知灼见。 从旧约的律法书部分转入先知书部分,即四大先知书和六小先知书,作者首先点出了先知运动的重申“耶和华一神论”与“反偶像崇拜”的主题,其次区分了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先知模式(即“在朝”和“在野”)之不同,再次区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先知的三种类型。作者在论述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先知,如北国的以利亚和阿摩司以及南国的以赛亚和耶利米时,充分阐述了以利亚和以利沙领导的先知运动与亚哈王室偶像崇拜斗争的主题、阿摩司诉求“上帝的公义”的主题、以赛亚重申“耶和华一神论”的主题、“弥赛亚盼望”的新主题以及耶利米作为“受难的仆人”的主题。这些主题塑造了先知神学在苦难中诉求正义的“悲情神学”的风格。 在解释各个先知书时,作者特别突出了“集先知书之大成”的《以赛亚书》在旧约中的突出地位。和前面的《申命记》一样,《以赛亚书》也成为本书论述的一个重点,作者用较大的篇幅进行了细致分析。不过,作者放弃了学术界通常采用的三个以赛亚的区分(即《以赛亚书》1—39章为第一以赛亚,40—55章为第二以赛亚,56—66章为第三以赛亚),这可能多少会招致一些争议。作者的理由是,由于《以赛亚书》具有“过去—现在—将来”这一贯穿旧约全书的基本的救赎史的时间结构,并且先知以赛亚能够立足现在、回顾过去、预言未来,因此,大可不必将《以赛亚书》肢解为三个以赛亚(上卷,第442页)。而通常学界之所以要区分出三个以赛亚,其目的主要是要突出先知神学中的“弥赛亚”的主题以及“受难的仆人”的主题。而这一主题正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救赎史传统的连续性的核心(上卷,第479—480页)。作者最后断言,《以赛亚书》乃是“旧约先知启示的总结和顶峰,又是通向耶稣基督福音的纽带和桥梁”(上卷,第483页)。 四 以四福音书、《罗马书》和《启示录》为核心新约历史叙事 《圣经历史哲学》上卷论述旧约历史,下卷论述新约历史,其中尤以四福音书、《罗马书》和《启示录》为核心。 旧约或希伯来圣经所讲述的是以色列民族的救赎史,而新约所讲述的则是耶稣基督、使徒以及原始基督教会的救赎史,因此,在这两种类型的救赎史之间既存在着连续性,也存在着突变,但肯定不是根本性的断裂。新约的救赎史的核心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与复活的事件,这一事件既是救赎史事件也是世界历史的事件,是救赎史与世界历史的切线。新约救赎史叙事在现代首先遭遇到了历史批评就“历史的耶稣”的真实性的质疑。因此,解释新约历史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辨明“历史的耶稣”是否真实存在、圣经中的“见证”是否真实、以及“历史的耶稣”如何成为“信仰的基督”等问题。 为了回应现代圣经批评的质疑与挑战,作者坚持尊重圣经、以经解经、“回到圣经本身”的原则,用圣经的历史记载的“内证”回答圣经中的“圣灵见证”的真实性问题。显然,圣经作为经典文本的“内证”原则比“圣灵见证”稍微宽松一些。因为对于现代圣经批评来说,所谓的“圣灵见证”是以信仰上帝的启示为前提的。作者对此回应道,“圣灵见证”是门徒逐步认识“耶稣是谁”的亲身经历的结果(《圣经历史哲学》下卷,第14—15页),或者说,门徒对基督的信仰是建立在对“耶稣是谁”的亲身见识的结果。因此,见证具有比单纯的历史客观性和信仰的主观性更复杂的内容。它不能简单还原为历史客观性,但其中却包含有历史客观性。在解释“耶稣复活奇迹”的真实性时,作者就应用了这一“圣灵见证”的圣经内证原则。对耶稣复活的见证,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4)中所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只有在妥当地回应了“历史的耶稣”的批评性质疑之后,才有可能将新约中所见证的历史叙事置于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救赎史叙事的框架之中。作者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救赎史叙事框架下,描述了从对观福音中的耶稣的历史到《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的使徒和原始基督教会的历史,从《约翰福音》被信仰的基督的历史到约翰《启示录》的救赎史。救赎史的历史场景也从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等相继统治的近东地区转移到了希腊化和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叙事的重心也从犹太教的耶和华一神论转向基督教的基督中心论。新约所叙述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救赎史乃是更大的救赎史的一部分,即耶稣基督乃是从前写在圣经上的以及从摩西到众先知所预言的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救赎的实现(下卷,第27—29页)。比如新约开篇的《马太福音》,无论是耶稣谱系的数字结构(三段十四代)还是其他的细节(下卷,第45—47页),都具有救赎史的象征意义,严格遵循着旧约救赎史观的“应许—实现”叙事结构(下卷,第47—48页)。所不同于旧约之处在于,在旧约中所记载的上帝救赎以色列民族的应许和计划在耶稣身上应验和实现了。这是基督教所建立起来的“旧约与新约的连续性”的统绪。尽管这种救赎史观念源自于旧约,但是将其拓展到耶稣基督作为旧约应许的实现的“预表论”,是在新约的四福音书中才达到了无比精致的形式。从此,新约成全甚至是取代了旧约。 再比如《马可福音》,它实际上深深根植于旧约的先知传统。使徒马可将耶稣的生平纳入旧约先知传统的“先知与世界”的二元冲突模式以及“弥赛亚盼望”的叙事模式中。作者指出,对观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三个使徒,不仅代表了追随耶稣的不同信徒群体,代表了来自不同的以色列传统的信仰群体,而且也代表了他们所继承的旧约中的“君王、先知和祭司”三大传统(下卷,第43—44页)。到了加尔文,却将“君王、先知和祭司”作为耶稣基督的三重职司,用基督教的神学教义深深地掩盖了三部对观福音深深扎根于旧约三大传统的事实。赵敦华在《圣经历史哲学》一书中以救赎史的叙事框架建构了犹太人的旧约与基督教的新约之间的连续性,突破了传统基督教神学的“预表论”解释模式的狭隘性,即旧约的应许是新约的基督福音的“预表”,因此新约无比优越于旧约,也克服了这种预表论的危险性,与二战后整个国际学界重新强调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连续性的大趋势合流,对于我们在中国语境中深刻认识西方文明的大传统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 在从福音书转向保罗神学时,作者严厉批判了20世纪新约神学大师布尔特曼的立场,即把《新约》的重心放在保罗和原始基督教会的“宣讲”(kerygma)之上。作者指出,如果没有耶稣本人的宣讲,就没有保罗的宣讲(下卷,第121页)。的确如此,没有耶稣本人的存在以及耶稣宣讲中的神学思想要素,就没有所谓的“保罗神学”。如果没有耶稣本人对犹太救赎史观念的传承、推进与突破,也就没有保罗的再突破。保罗的使徒经历仍是新约救赎史的一部分,决不能因为其富于神学而抬高到高于福音书的地位,以至于成为新约神学的核心。因此,必须将保罗的思想重新放回使徒历史的新约救赎史叙事之中,甚至更有必要将其重新放回到原始基督教信仰群体的犹太教传统之中,就像是杜伦大学的邓恩(James Dunn)、赖特(N.T.Wright)和桑德斯(E.P.Sanders)等人的“保罗新观”(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所作的那样。“保罗新观”和“历史的耶稣第三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强调耶稣和保罗思想所属的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犹太教的复杂传统,而不是其基督教特性。 当然,作者也没有忽视传统新约神学的两大核心文本《约翰福音》和《罗马书》的重要性,对这两个文本有浓墨重彩的分析。在解析保罗神学的代表作《罗马书》时,作者将保罗神学准确地定位于“基督中心论”之上,并指出《罗马书》中的基督中心论是相对于旧约中的《申命记》和《以赛亚书》的“耶和华一神论”的新约神学的核心。作者说:“如果说耶和华一神论是全部《旧约》的本体论、历史观和信仰实践,那么基督中心论就是全部《新约》的本体论、历史观和信仰实践。《罗马书》在神学中的作用犹如科学上的‘范式转换’,‘基督中心论’是圣经启示的‘新范式’,取代‘耶和华一神论’的‘旧范式’。但任何类比都有缺陷,圣经中的新旧交替不是以新废旧,而是用新的启示和行动总结、成全和实现《旧约》中既有的上帝拯救计划。”(下卷,第134页)其实,这段话可以视为这本叙述圣经历史之作的中心思想,即犹太教与基督教在救赎史上的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连续性。 当然,在强调两约的连续性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两约之间的某种断裂。在耶和华一神论向基督中心论转变的语境中,保罗在《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2:16)中以“因信称义”纲领(下卷,第137—140页),与不愿或不能转变信仰基督的犹太人进行论战,为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为后来基督教与犹太教在教理上与宗教上的冲突以及整个欧洲的反犹主义埋下了根子。今天也有人会认为保罗为基督教普世主义奠定了基础,比如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lan Badiou)在《保罗:普世主义的奠基》中就持有这种立场,然而,“保罗新观”派以“恩约守法论”(covenantal normism)反对这种自路德新教以来对保罗的“因信称义”所作的“信仰与律法”二元论的解释模式、对犹太教的“律法主义”(legalism)的定性,以及对救赎的个体化和灵性化而非教会共同体的救赎以及在历史中救赎的取向。 为了解决保罗“因信称义”学说的歧义,赵敦华对《罗马书》中“因信称义”的六层论证(下卷,第150—195页)进行了剥茧抽丝的分析,指出了“称义”本是犹太教的基本观念而非基督教的新义,分析了保罗的“因信称义”只是批驳了那种犹太人以特殊的种族律法作为自己被拣选民族的身份的特权因而抵制耶稣基督作为称义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没有否定一般意义上的犹太的律法,澄清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的救赎史含义,批驳了奥古斯丁以来对保罗神学的“预定论”的解释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根据新约救赎史叙事的统一模式,作者不仅将保罗神学置于使徒的历史叙事之中,而且也将《约翰福音》的作者同样归之于使徒统绪(下卷,第290—291页)。不过,由于使徒约翰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约传统的叙事框架,甚至更多地负面地使用“犹太人”的称呼(下卷,第268—270页),因而有别于对观福音的“前使徒统绪”,是新的使徒统绪的开端。作者特别指出约翰神学中不同于犹太教传统的东西,通常这些因素被视为希腊因素,比如对“真理”、“道”、“光”、“生命”、“真理”等希腊语汇的使用(下卷,第296—300页)。正是从这些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所谓的希腊因素中产生出了“道成肉身”的观念,以及三位一体中的“圣灵”观念,奠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可以说,《约翰福音》是从“历史的耶稣”到“信仰的基督”的核心文本,它既是使徒神学的总汇,又是后来基督教神学的原型。因而,解释《约翰福音》是新约历史叙事的一个重心。 《圣经历史哲学》最后以阐释通常归为约翰所作的《启示录》的救赎史论收束全书,因为《启示录》是救赎史的总结。作者非常重视《启示录》在整个两约的救赎史叙事结构中的地位,这是这本著作显著的特色之一。《启示录》完成了从以色列人的创世观到上帝对以色列的拣选与应许、从弥赛亚盼望到基督徒的末世论和启示录的救赎史体系。与犹太教的启示文学不同的是,新约的《启示录》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它记述的是基督的形象与其他异象之间的斗争关系以及基督教会与其他敌基督势力之间的斗争关系,救赎史集中于“基督与敌基督的斗争史”。 在旧约的政治神学里,以色列人的救赎史主要发生于以色列人与那些征服它的各个近东帝国之间冲突与斗争的历史背景之中,而新约中普世的救赎史主要发生于基督徒与几派犹太人以及基督徒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与斗争的历史背景中。在《启示录》中,与耶路撒冷相对的罗马帝国就是新巴比伦,基督以及基督教会的救赎史就是耶路撒冷与罗马的双城记。可以说,《启示录》开启了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政治神学。然而,当罗马帝国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并在君士坦丁时代被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原始基督教的启示录的政治神学就被终结了。一个新的独立于犹太教的世界性宗教的历史开始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发端,旧约与新约的救赎历史无疑比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及其后的基督教历史更有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文明每当危机动荡的年代,总是要不断地重返旧约和新约的救赎历史而非罗马帝国宗教以寻求自我更新之道的原因。 赵敦华的《圣经历史哲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论述旧约与新约整个圣经历史叙事的哲学著作,这本体大思精的著作包含了丰富的文献知识和深刻的哲学洞见,一反现代圣经古史辩派肢解圣经叙事的做法,以圣经救赎历史叙事的框架全面叙述和解析了圣经所记载的信仰群体的历史世界和思想观念,堪称是近年来国内基督教学术研究最令人赞叹的一个成就。标签:耶和华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圣经论文; 以赛亚书论文; 读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以色列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