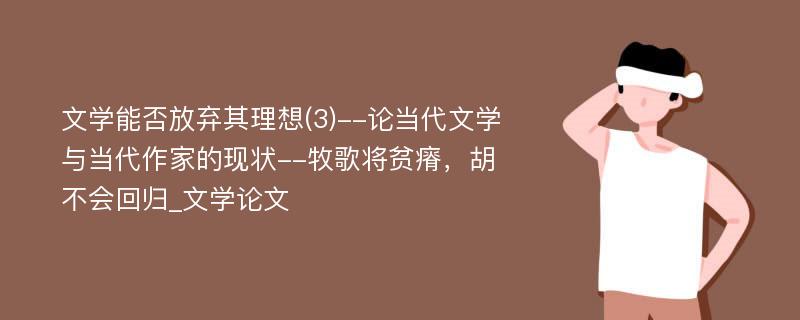
文学可以放弃理想吗(三)——关于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现状的一种讨论——田园将芜兮,胡不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归论文,田园论文,当代论文,现状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九十年代,当新一轮商业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文人下海的呼声便越涨越高,以至海外同人以之为当代中国的一大奇观。然而更值得惊奇的是一批站在岸上的文学中人,他们带着说不清的失落感,渴望着堕落,躲避着崇高,不把自己当“人”。似乎不当“人”便成了不下海之外的选择。这些以玩文学姿态的“码字”者,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宣言中,潇洒走一回。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使文学非文学化的到底是什么力量呢?到底是社会看不起作家呢?还是作家在自轻自贱?这些游戏者仿佛杂耍的艺人,插科打浑之际倒也捞了不少名利。赚一两笔稿费,玩二、三流女人,便觉得他们开始懂得生活了。于是招摇过市,作甚嚣尘上之势,仿佛时代英雄,文坛大腕,以为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了。
然而,这代价却是毁灭性的。不仅文人的声誉彻底丧失,就连所谓引车卖浆者流也羞于与其同伍。难道招摇过市之际就真的那么潇洒?殊不知街中已经贴出了“防火防盗防作家”的标语。越过那些让人生烦、起腻的俏皮话,终难掩饰的是没穿衣服的窘迫。贫嘴耍于一时,利欲逞于一朝,然而明天是不是真的不会来临?假如明天真的来临,还会有什么花招障入眼目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一句素朴的真理,它告诉人们实诚的东西才有可能永存。作为伪装的一切都会被卸下来的。人们在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谁又是始作俑者呢?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堕落了,那么谁是这个堕落运动的急先锋呢?这倒让人想起历史中一个常见的现象:社会的堕落往往是从堕落的文人开始的,或者说,文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一个典型的象征。
我们的社会一点一点地富裕起来,物质前所未有地丰富了。看着日本的电视,穿着巴黎的时装,我们仿佛已经国际化了,进入文明的前沿地带。然而在某一个偶然的黄昏或某一个静寂的夜晚,我们猛然之间会觉出些许的苍凉来,环顾四周我们似乎什么也不缺,唯独缺少的就是我们内心曾经为之激动的理想。理想之光黯淡了,精神之火苍白了。守望着飞动的红尘,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语之感笼罩着我们。我们的人民在向贫困开战中,却面临着新的贫困的阴影。穷得只剩下钱了,说的就是口袋满了、脑袋空了的景象。这时,人们便翘首以待那些精神的战士们,渴望着从他们那里出来清新的精神的风。然而众里寻它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些游戏的知识分子正忙着赶集、忙着快乐,他们一样的两手空空,一样的没有慰藉。于是一种深刻的失望产生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存在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作家在堕落,批评家也在堕落,他们随手拈来西方新而又新的名词,当做可居的奇货,玩得倍热,仿佛手中的鸟儿,节候一到便去放飞,而节候一变便象熊市的股票赶紧脱手。鸟儿飞来飞去,而批评家就是这些玩鸟的人,他们太聪明了,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样的鸟。于是文坛便象乱了方寸的赌场,热闹得很,也空洞得很,除了乌烟瘴气之外,人民看不到他们期待之中的光芒,他们伤心而失望的眼神,便成了我们心中最大的隐痛。那些金色的麦芒,那些金色的牧场到哪里去了,这是一种来自时代深处的呼喊,透过细雨,透过热风,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追问着我们。
就是在这个苍茫的时分,北京大学的一批固守于精神园地的人们发出了重返理想的召唤。他们从边缘的圣地向人民的中心挺进,和他们亲切而热烈地站在一起,共同回答着时代的追问。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景象,在一个世纪的日落和一个世纪的日出之际,理想的光辉重新照耀了我们。谢冕先生在谈及北京大学时,曾经说“这圣地绵延着不熄的火种”,这火种正是难以磨灭的理想精神,这精神不仅属于圣地,也属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不仅属于辉煌的过去,也属于被人们展望和想象的未来。只要这个理想精神还在,我们就会有永远承载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会象海子说的那样“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到了游戏终结的时候了,我们将拒绝漂流,并在理想的精神上找到我们寄居的家园。田园荒芜兮胡不归,让我们一起在精神的田园里朴实而辛勤地劳作吧,该想想我们拿什么馈赠给未来的世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