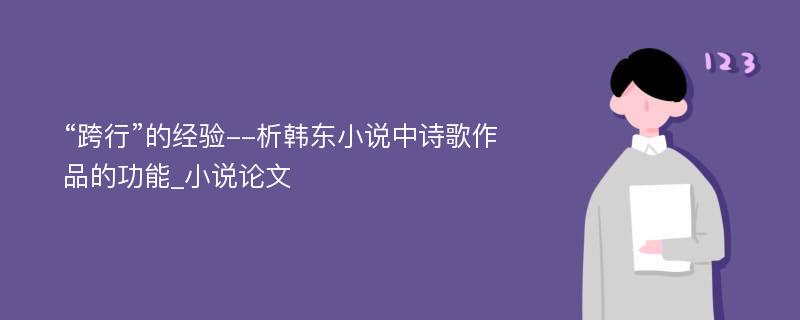
“交叉跑动”的经验——析韩东小说中诗歌作品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经验论文,功能论文,作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同“理论”这个词语本身,对人类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事件中习得经验的梳理是一个 把芜杂、含混的状态加以明晰化、条理化的过程,因此理论家们都很偏爱在比较中实现 对概念的命名,文学研究者也不例外。在谈论小说的叙事功能时,常常和诗歌的抒情特 征并置,再从二者之间的差异出发把小说的特征标举出来。其实,叙事与抒情的区分并 不如很多论者描述的那样显明,文体间的越界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从这 个角度看,作家韩东的小说中频频出现诗歌作品,并不是一次创作的“事故”。有一点 不同的是韩东——在观照韩东的小说创作时绝不能被忽略不计——的诗人身份:作为朦 胧诗的第一个反叛者,韩东是后朦胧诗这个庞大而颇有争议的群体中少数能留下代表作 品的诗人之一。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韩东一开始就是一个颇具理论头脑的人(可能与 他哲学专业背景有关),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不断提出的诗学观点(如八十年代有重大影 响的“诗到语言为止”和近年的“第一次抒情”、《论民间》),还有就是他对自己双 重身份的清醒认识(注:林舟:《清醒的文学梦——韩东访谈录》,《花城》1995年第6 期。)。他的诗歌写作从1982年持续至今,而迟至1989年后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创作。不同意味的两种形式共时性地处理着同一个写作者的人生经验,诗歌(包括他本 人和他人的,笔者认为,对他人诗歌作品的借用,也表征着对他人经验的共鸣和认同, 当然也是韩东本人经验的曲折现形)对小说的大举入侵使得这种处理显得更加复杂,甚 至具有了一种文体学上的野心。下面将把韩东小说中的诗歌作品依存在形态——即引文 与主体文本的分隔与插入——分为卷首语和文中诗两种,并从此处进入问题。
一、卷首语:非叙事性的葫芦格
传统话本小说中有一种显在的或隐性的葫芦格结构,也有人称之为镶嵌式结构。即每 一篇小说实际上有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较为短小,相当于引子,当时语称“入话 ”,第二个故事才是小说正文,是其真正施展叙述变化的地方。后来由于勾栏瓦肆长篇 讲史的需要,最终扬弃了这种套路,以“楔子”或卷首诗词的形式取而代之,杨义先生 曾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为例做过论述(注: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 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6页。)。一般说,葫芦格第一个故事的基本情 节与第二个故事完全一致,以至于有的论者据此断言葫芦格在传统小说中除了“以浓缩 、提纲挈领的方式把小说正文中的主体内涵率先点明”外,“在艺术上毫无价值”(注 :李洁非:《小说学引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杨义先生曾从参 数叙事的意义上出发肯定了葫芦格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使用葫芦格是一种“头回故事赋 予正话故事以附加的故事外意义的策略(注: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4页。)”。韩东小说中常常以卷首语的形式出现自己或 他人的诗歌作品,这一点与葫芦格将一个故事直接放置在主体文本的开头而实际并不构 成主体文本的情节相类。
韩东的短篇小说《农具厂的回忆》(注:韩东:《树杈间的月亮》,作家出版社1995年 版;《我的柏拉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往往被评论家注意的是童年视 角叙述,小说的主题归为对文革的另类记忆。读者的注意力多投注在小说中颇有些紧张 的故事情节上:小培的母亲和张延凤两个女干部去农具厂搞运动,吓死了农具厂很有人 缘的杨厂长,张延凤当时回家给参军的女儿送行,人单势孤的小培母亲处境就显得很是 危险,小培这时偷跑出来代替哥哥陪母亲,于是他就目睹了妈妈与张书记处理农具厂事 件中所谓攻心、检举等近于变态的革命手段,在这里又似乎不经意写了锁匠、张延凤未 出场的女儿等情节。如果把主题锁定在对文革的鞭尸,那结尾处小培关于锁匠的铜锅变 回铜片的梦境就只能是一次想象力的放纵了,无法形成小说的情节板块,锁匠最后拿的 张延凤女儿照片的画面也无从解释。笔者以为如果从卷首引用的《木工》这首诗作为切 入点,可以对小说做出新的阐释。
木工车间里工人们躺在刨花里干活/没有门,没有窗,/也没有墙/只有芦席围起的三面 金色工棚/只有阳光,刨花和木料和/已雕刻成形的各类农具的柄/没有门,没有窗,没 有桌凳和门槛/没有床。是木工取消了木工/刨花掩盖了泥地
这首诗描述的是木工们的一个工作现场。作为居住环境的重要营造者,除了必要的劳 动工具外,这些木工们没有最起码的生活设备。从诗的第二句起,作者都在对整幅画面 进行删除,只是留下动作单一的人、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刨花,而前两者又在专注地产生 着后者,并被后者——这些工作的废料——覆盖,这让读者想到庸常生活对人本身的覆 盖。接下来诗人在诗歌里又用语言对他们进行了的覆盖:整首诗直到结尾才出现木工, 还是被“取消”了的木工。他们好像是被生活愚弄了,动作单一无所欲求。作者反复念 叨的门、窗、桌凳和门槛的缺失并不被木工们注意,甚至他们自得其乐:躺在刨花里干 活。作者也无意于如某些浅薄者那样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拯救,韩东明白这是 无法拯救的,其实这就是惯常的生活图景,每个人都可能受到这样的覆盖。于是,“刨 花掩盖了泥地”,劳动中被弃置不用的部分彻底完成了对他们所站立地面的替换,也是 读者最后看到的唯一一幅画面——被生产出来的刨花数量不断增多,所占用的空间持续 延展、扩大。木工,这个预设(诗的题目)的抒情主人公并没有获得表达的机会。这几乎 就是小说中那个锁匠的象征,作者一直没有交待的他对张延凤女儿变成植物人和张延凤 因此再也没回来一事的态度,“锁匠停下手中的活儿看了小培一眼,接着哼哼哼地从鼻 子里发出一串声音,不知是哭还是笑”。由于结尾的梦,也由于故事视角是一个有机会 窥见全部故事的小孩,可以设想这件事是触动了锁匠感情的,比如一次足以构成故事的 爱情经历或只是一个情感片断(这样一来,张延凤出事后恰巧回家和“适时地生了一场 小病”得以躲过紧张的局面也可以得以印证),可是这场经历或片断被小说中的斗争、 革命气氛掩盖了。锁匠也像诗中的木工那样,组成他全部生活的只是他的劳动和劳动工 具。但是,如果停留在一个若有若无的爱情的推理上,解读也将是剑走偏锋。还应注意 的是,小说中的工人们在照顾他们入厂的杨厂长自杀后,不仅没有轻举妄动,而且还在 那几天特别出活,很耐人寻味。他们仍然深陷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像木工生产刨 花一样领受生活的平庸。小培在用喇叭筒喊上工的口令时——在小培及其家人、到小培 家的下放干部看来这是多么好笑——“他们也不理睬小培。他们的背影就像聋哑人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小培的母亲和张书记,作为农具厂运动的操纵者,他们的革命行为与 无事可干联系在一起:开会、故作高深却极其空洞的发言、表面看负有重大使命实际上 只是向莫须有宣战的谈话、检举、表态、交待等。他们也无法给出一个意义,被生活的 巨大惯性推动,被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刨花”所魅惑、激动和覆盖。甚至还可以从这 首诗看到小说作者对小说写作本身的庸常性:小说一开始的叙述动机(随时可能的复仇) 没有得到爆发的机会,紧张的语言速度也没有影响到故事的走向,只是让所有人虚惊一 场,甚至到了最后韩东竟然好像遗忘了这个故事一样“不负责任”地丢掉了原来情节发 展的可能性,写作的结果只是这些现象的杂陈,没有价值判断,没有任何高潮迭起的蛛 丝马迹。
这样,《木工》这首诗作为一个非叙事性的卷首语同样起到了葫芦格的叙事效用:即 既是对小说主题的复写,又是对故事情节的隐喻。这种情况在韩东的《烟火》、《房间 与风景》等小说中也出现过,不过韩东的这类卷首语还有另外一种,即开头的不是像《 木工》那样的可以和小说文本的故事形成可以找到意指关系的诗,比如《同窗共读》卷 首的诗作《看》:
既看见你/也看见我/但你们二人不能相互看见/中间是一面墙/一棵树/或一阵烟雾/我 在墙的纵面/树的上面/我就是把白雾本身
则是一种超拔的视角,一个居高临下的却并不威严的看顾者,我(诗中的“白雾”)从 未发言,而是看着“一个卑微的怀春少女”在感情成长中的磕磕绊绊。小说《为什么? 》的卷首是于小韦的诗《困顿》的节选:“树/在五点时/倾斜着”在小说中能找到和这 短短三句诗唯一的关联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李冯发现妻子与他人通奸的时间是不到五点时 。回到诗作,一棵倾斜的树很可能不仅在五点是倾斜着的,而是所有的时刻都会是这样 ,但之所以被定格,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时候和诗作者独特的经验相勾连,就像王维诗中 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样,只不过后者作为一种停留在古代诗学体系中的审 美经验被后来的读者分享。对这三句诗的解读至少是对一个经验片断的记忆,但这对《 为什么?》这个小说已经足够,就是这三句诗提供了进入小说人物李冯及其妻子全部故 事的入口。接下来,作者开始冷静地叙述李冯的妻子自杀的全程,就像李冯表现的很自 然地公开这件事一样。可能对旁观者来说,这只是一个猎奇的故事,引起的是好奇心、 窥视欲或某种道德的激愤,可对当事人来说,却是一种猝然而至的创痛,及而李冯意识 到或者说体味到这一点,她的妻子已经以自杀示抗议。这就是小说结尾的李冯家的书房 地面上那个“发白的人形”,这是李冯的个人创痛,是那棵“五点钟”“倾斜的树”, 作者在小说的最后一段警告读者:“你永远不要问为什么”。写作行为构成叙事的一种 可能,作者在阻止读者对故事主人公的窥探的同时,也暗含着对自身的叙事行为及叙事 的可能性的质疑。
二、文中诗:旧布绣新图的意义
在文中引用诗歌类作品,古已有之。浦安迪认为明代四大奇书的一个重要的修辞特征 就是“把诗词韵文插入于故事正文叙述中的写法”(注: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这种修辞方法在元代陈铎那里称为“间叙”:“ 以叙事为经,而纬以他辞,相间成文”(陈铎《文筌》)。从读者接受到的小说文本的视 觉效果来看,不同的阅读习惯使得诗歌的出现影响叙事的进程。如果说韩东小说以诗歌 作为卷首语更多地侧重于干涉叙事形式的话,那么他在文中引用的自己和他人的旧作就 有了拉佛尔格对自己小说集秉持宗旨——“旧布绣新图”的功能(注:蒂费纳·萨莫瓦 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韩东写于1994年的名篇《西安故事》就在文中多次引用丁当、叶芝和韩东本人的作品 。如同韩东所说,他“认为得意的人都是特别乏味的人”,他的人物都是“穷途末路者 ,身份卑微、精神痛苦”,这篇小说的三个人物就是这样:我、何飞和老荒是几个生活 乏味的教师。他们几乎没有像样的业余消遣,几个单身汉的生活单调而邋遢。在描述他 们生活状态时,韩东引用了丁当的诗
……那一年你流落异乡/一头长发满脸凄凉/普通话说得又酸又咸/怕洗衣服穿上了人造 皮革/有时上大街逛逛/两只眼睛饿得滴溜溜乱转/……
下文韩东继续叙述这种生活,起衔接作用的词是“另外”,一下子就把这首诗的作用 揭示出来了:插入叙事之中,用诗歌惯用的通感、双关表达出在小说中需要大篇幅描绘 的内容,并与叙述语言形成互文。相对于小说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诗歌语言的更具凝练 性和思维特征的更富跳跃性的优势得以在小说中施展,从而达到了小说作者的叙述目的 。下文中“我”与刘吉背诵丁当的诗,既有这种意味,又充当了揭穿老荒恋爱谎言的道 具。文中的老荒是一个行事怪异的家伙:他既在近乎疯狂的状态单方面地臆想与刘吉的 爱情故事,又一手用匿名信毁掉了刘吉报考研究生的希望。那个在自己幻想中生离死别 的爱情使得老荒失声痛哭,作者在小说中对此未置一词。在描写这个人物和刘吉道别时 那种单恋不得转而无处发泄的情态时引用了这样的诗句:
然后爬山,在河里游泳/我差点摔死/而你差点淹死/直到最后,跑来了一位绅士脸儿白 净,衣服里裹着爱情/我说好啦好啦/你就跟他去吧/别又哭哭啼啼/就像死了猫咪
这首诗一开始就设置了一种险情,这险情来自可能是游玩,也可以认为是在比喻人在 世间的遨游。我们都运气不佳,差点死掉,这是我们共同的处境。是外人的出现,“衣 服里裹着爱情”可以理解为先前的自然的行为被赋予了某种外来的意义,可是诗的结尾 变成了“我”用不胜其烦的口气劝“你”,显见这种险情的虚假和“你”沉溺其间的矫 情,诗歌一开头设置的悲剧可能性发展为造作的“哭哭啼啼”,并和“死了猫咪”相比 ,一下子具有了反讽的效果,这与整个故事的主题是相合的。韩东不是一个习惯于在小 说里直接发言的作家,这并不能说明他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立场。他的语言有一种直呈原 生态生活经验的效果,引用的诗给人带来了一种回到平庸现象本身的龌龊感,或者说, 在诗歌中可能作为隐喻的语言一旦进入小说就成了抹平多种附加意义的“元语言”。这 篇小说中有两处主题相互关联的引用,一处是“我”送美女刘吉离开时引用丁当的诗“ 一次又一次做一路电车/逼得售票员从姑娘变成妇人”,一处是叶芝的名诗《当你老了 》。前者是对眼见美人迟暮的感慨,美好事物生生从面前消隐却无法挽留;后者是超越 时空和容颜变化的求爱誓言,虽沧海桑田真情矢志不移。这两种非对立,差异却让人为 之喟叹的看法箍着在刘吉那个“以某种受损害的方式葆有了她十二年的美丽”的故事上 。两次引用的效果还会互相抵触,从而消解掉任何一处会产生的终极立场。这样就很容 易理解另一处引用了:“谁限制了你的美丽/谁刻画了灿烂的条纹/谁在经过/仅仅经过 ”。
《我的柏拉图》是韩东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他少见的在文中完整插入诗歌(最 常见的方式是节选)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韩东叙述了“一个痛苦的单恋者”的故事 :陷入婚姻危机的大学教师王舒爱上了自己的学生费嘉,费尽心机终于表白,却被冷漠 地拒绝,在对此事可能会公开的担心中王舒只好离开他任教的学校。文中共引用了三首 韩东自己的诗:《郊区的一所大学》以一种冷静罗列的方式写出了学校对王舒来说是一 个“表面、临时、毫不重要的地方”。可这个“带着它全部的表面性、坚硬和隔膜”的 处所,在费嘉出现后变成了“生活目的的所在”,以至于“返回之路痛苦不堪”。正因 为这与诗歌中所记录的情绪形成极大的反差,使得韩东在处理这个单恋故事时不会把叙 述的重点旁逸至王舒对单位的游离关系上,同时也收到了凸现单恋对王舒的意义之重大 这样一个一石二鸟的效果,无疑,这对接下来写王舒那种犹豫、多疑、琐屑的感情内蕴 打下了一个尖锐的楔子;第二首诗是《孩子们的合唱》,在这首诗里王舒完成了与费嘉 的第一次交流(当然是存在于王舒想象中的),“就像你那样安静地看着我/我猜想你的 声音是实质性的声音”,王舒以一个长者或者说受到别人注视者的眼光打量费嘉,等待 着费嘉的出击。读者在故事中发现,这首诗几乎写出了王舒对可能发生的全部情节的直 觉:没有什么奇迹发生,费嘉继续停留在集体合唱中,和他保持着应该有的距离:“广 场上,孩子们交叉跑动/你必将和他们在一起”。而最终王舒只好采取行动:让黄强打 探费嘉的情况,自己连写两封情书,结果正如诗中所写,费嘉“不为我或者谁的耳朵/ 永远不对着他们小声地唱/这支歌”。也就是说,这首诗已经暗示了王舒行动的不可能 ,甚至即使行动有所结果,如小说结尾处王舒与钟建珊的肉体关系,王舒也无法真正抵 达费嘉。他好像一开始就明白了这只可能是一个停留在理念世界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王舒的所有行动可能只是为了获取“对灵魂曾寓居期间的理念世界的回忆”,也就是 说这是一个人为自己制造记忆的故事;这在最后引用的诗《成长的错误》可以见出,相 对于《孩子们的合唱》,这首诗语速迟缓、涵义晦涩,带着一种专断的宿命口吻。诗的 最后几句:“我走下台阶,记着你的幼稚体态 感到成长是一个错误 其次是时间”, 故事结束了,明知不可而为之使王舒不得不逃离了自己的单位,同时也是对这段故事的 逃离。后两首诗一前一后、一热一冷敷演了出了整个小说透射出的小人物感情受挫只好 寄予冷峻理念的宿命感。
三、意义扩散的意义
葛红兵认为韩东小说的根本特征是“个人化”(注:葛红兵:《障碍与禁忌——论韩东 的小说》,《南方文坛》1996年第6期。)。针对个人化写作,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批评: “沉溺于逼仄的个人趣味”、“迷恋个人小小的悲欢”等,反方也多从个人经验的不可 替代性和对个体的尊重及注视入手进行辩护。这样其实对真正理解个人化写作的意义毫 无助益,最终把问题引向题材或主题的大小之辩,从而离小说诗学体系的构建越来越远 。耿占春先生指出,对小说叙事来说,重要的是对世俗性和日常俗务的关注,而不是割 断这些日常俗务与想象的联系后的日常性。(注: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大学出 版社2002年版,第132-135页。)韩东小说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何种生活经验的选择上 ,而是对之最富有想象力部分的提纯上。诗歌作品对他小说的进入,成了韩东完成这种 提纯的一个有效技巧。正是这些或长或短的词句,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意义生成源,以 不同于叙述的方式扩散于小说之中。
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莉思蒂娃提出了“文本间性”的说法,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 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 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 着其他的文本,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在极端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任何 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罗兰·巴特也说,“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 用已有的言辞”(注:罗兰·巴特.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 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对韩东来说,原有的诗歌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经验记录 和美感生成体,如果只是把韩东这种引用看作是对主体文本不自足的补充或弥合,倒不 如视为对一个自足文本的侵入,使之多义化、零散化,从而在两种经验的分享中获得更 多阐释的可能性。韩东曾说,“诗歌的形式有它自身的界限,和小说相比,它往往不能 与作家整体的混合性状态相适应。”(注:林舟:《清醒的文学梦—韩东访谈录》,《 花城》1995年第6期。)但是,这并不就是说,进入小说的混合境界就不需要诗歌的那种 轻盈的飞翔的美感。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肯定不是明智之举,韩东的处理方式是把诗歌作 为展开小说叙事的一个短促的由头或将含混的小说世界搅得更加含混,换个角度看,这 也是对小说——这种相对诗歌容量更为庞大的文体——审美本质的成就和点亮。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大量的诗歌进入小说,但并没有取消小说的叙事功能,而是被 小说的主体文本所吸收,同时诗歌也将本文向外敞开。关注韩东小说中的诗歌作品,就 是衡量这种敞开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单单从小说形态学的角度来看,韩东小说中的卷首 语和文末诗形成的是两种文体在视觉效果上的交混,这样很自然会使得写作和阅读不再 是通常的线性做法,而呈现出一种“间断性”。对作家来说,在小说中引用诗歌意味着 一个进入故事的便捷方式和对故事的另一种书写手段。对读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 要不断的回读、品味、迟疑、拆解,有时甚至需要唤起更多其他的阅读资源才能解其中 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