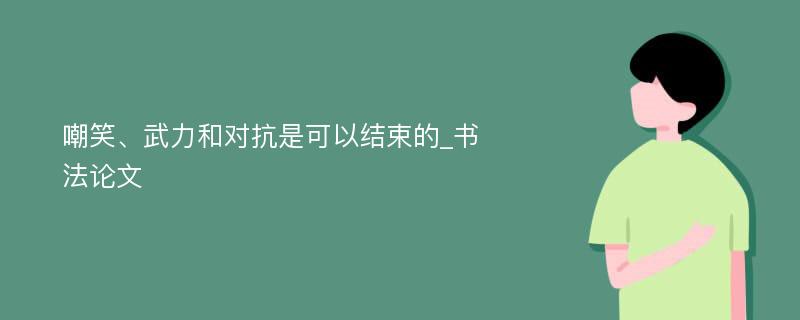
嘲讽、逼问、对立可休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可休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书法”出现后,又经历了“书法主义”、“学院派”,书法界的论争文章可谓“浩浩乎”了。大家的关注点概而言之,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书法如何反映当代文化以及发展可否突破汉字限制等等。对这些关注点的各抒己见,已经使一部分意见达成共识,但并未休止。曾以《析世鉴——天书》成为焦点的徐冰近年又推出“新英文书法”,于是新老问题再度泛起。今年一月,《美术报》载刘宗超先生《新书法论坛·实验汉字》又论及新书法与传统书法的相处,提出:《析世鉴》这样的作品“它仿佛对传统书法的表现方式形成了一种嘲讽和逼问。……仿佛是对传统书法惯性创作模式的嘲讽。传统书法创作模式中几十年如一日地临摹字帖或不厌其烦地复制自我,或毫无创作激情的抄写文字,难道和《析世鉴》的创作模式有根本上的不同吗?”(注:刘宗超《新书法论坛·实验汉字》,《美术报》二○○二年一月。)这种“嘲讽”、“逼问”以及刘先生在另一篇《书法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提到书法中现代派与传统派的“对立”,并非只是刘先生主观的看法,其实是表明了书法界的某种客观情状。而笔者认为嘲讽、逼问与对立实在可以休矣。本文试为一一论之。
关于传统书法创作模式的“老套”
书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线条是抽象的元素,由它所组构的尤其秦代之后的汉字也是抽象结构。所以长期以来书法不容易在其它形式领域找到发展形式的支持,“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形式体系。”(注:邱振中《中国书法技法的分析与训练》,中国美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书家锤炼技法主要靠临摹古代书法杰作也便有其必然性。自古以来,书法又是为民间与官方最崇尚的一门艺术,其地位与诗歌并称,加之文人严谨勤奋的敬业传统,他们纷纷呕尽心血临摹法帖、入其三昧,并在此基础上熔铸自我。临摹愈是功夫深厚,则自我中前人的痕迹往往愈重,风貌也便愈为稳定,某一时期内的创作也许确实呈现出“复制自我”的特点。但我们应同时看到:其一,历史上的书家没有谁一生就一个风貌,大致都在早、中、晚年各呈体格;其二,同一时期的书家彼此面目并未雷同;其三,隋代诸字体已齐备,从此书法史成为个体风格史,各朝代的书风各有不同,每朝代中不同阶段又各具倾向。这些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特征、个体间的差异与个人精神之进程。因此,传统书法大观园里众芳争艳这一事实我们得首先肯定,“嘲讽与逼问”绝不能不基于此事实。
近二十年印刷、复印极大改进,电讯极大便利,书写的实用场合空前萎缩,这种时代语境加之书家日益职业化,书家挥毫之际艺术创作的意识十分明确。而在古代,毛笔是日常书写唯一的工具,书信、撰文、抄经……文人们下笔第一意识乃在记录“文”意,艺术目的归于从属,“书”意成为下意识。飘忽着、流淌着的往往确非激情而是“温情”。可是有什么理由非得褒激情而贬温情?如果刘文所说“激情”指明确而浓烈的书法创作意识之类,则笔者不禁又要问:王羲之无意于佳乃佳的《兰亭序》初稿与书法意识明确的第二稿孰佳?
为什么二十世纪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而中国书法发展依然保持温缓步态?现代人的情感、时代的风貌在书法中得到了多少反映?书法如何完成现代意义的文化转型这个愈益显露的问题,根源依然在于书法的抽象性质。正因为抽象,所以历来书法被认为能够表现时代特征、伦理道德观念、生命体验、性格、学养等极宽泛的方面。传统西方美术以具象为特征,当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时代风云被画家与雕塑家深刻感受之际,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发现抽象的天地广大无边、玄妙而幽深,便以抽象取代具象。这是否就算真实反映了时代尚可争议,但这一形式变革毕竟是感受时代变革之后的巨大步伐却不容否认。然而“与西方艺术‘纯化’过程不一样的是,书法几乎从它产生时起,就已经是高度形式化的艺术”(注: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两千年前的“隶变”更已经从象形意味发展到了抽象,如今还有多少抽象余地可迈?相对于以抽象为主要特征的西洋画,不妨可以说,书法两千年前就已先行“现代化”!到如今其它造型艺术纷然掀起现代化大潮之际,它却因“无所作为”被“嘲讽与逼问”实在是命中已注定的尴尬了。作为嘲讽者与逼问者亦不应对此中原委不予明察。
字与非字,汉字与仿汉字
中国书法乃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但,一些前卫书家受别门类艺术抽象浪潮的感染,力求使书法发展与社会同步,居然将原本抽象的书法形式再推一步,成了非文字、纯抽象的点线挥写。而非字即无所谓书法。为了仍姓“书”,一些书家又紧靠“字界”,推出了一批观念性的实验作品。
反限制、求自由是现代派艺术的共同倾向之一。前卫书家曾一度反感于汉字的束缚、不依照汉字来组构空间,也即从有序走向无序。这种绝对的自由给挥写带来方便之同时更多的却是不便。因为没有文字这一图谱在胸,他们在挥写任何一笔时,下一笔往何处去的可选余地太大,必然会边挥写边构思,行笔中往往迟滞、局促,气息无法畅达。为了得心应手,他们经常费心地预先设计笔线的流程。这恰恰是重新回到有序,何苦呢?另一方面,即便这种非字的作品“视觉冲击力”很强,但欣赏者却只能将此当作一个“幅面”来读,无法方便地找到或者压根就无从找到笔顺,因此欣赏者无法进入“时间”这一第四维,无法进入线流去畅游,搭不着“书脉”,作品的感染力也便大打折扣。书脉实为“意”脉,这类作品作为连结作者与欣赏者审美意念的纽带实在并不称职。
徐冰的《析世鉴——天书》(注:沈伟编《中国当代书法思潮》[C]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二○○一年版。)意在展示某种现代观念,但作品本身实则是自创的楷书图谱。若将颜真卿请来按谱书写,想必也会生动,欣赏者也可以按汉字常规笔顺进入书脉。可是,这只能说这件作品达到了传统书法某些方面的审美高度。因为《天书》只得汉字躯壳而无灵魂(字义),所以,总体审美内涵较之传统书法依然单薄——打破现存字谱不用而创新谱当然也算变革,但以费事为代价、以逊色为结果,焉得称为“发展”?谁将逼问谁呢?
初读到徐冰的新英文书法,让人顿感新奇,会心一笑。多年前笔者曾力劝一位英籍外教创英文书法,然而后来笔者以为并不那么简单。汉字书写升华为书法艺术其实与它的优越条件密切相关:构字因子分笔画、偏旁部首两层,且超出二百个;单字组构式样达五十种以上;笔序与笔画数有可选或变通性;表意的形体中意趣与生命感盎然;方块为变形、行文、章法又提供了很多便利……也许正是认识到了汉字的优越性,徐冰才挖空心思地将抽象的英文字母转化为富于意趣的楷书偏旁部首,并又打破原本单一的字母左右排构、模仿汉字组构式将单词构造成貌似汉字的方块“混血字”。照讲这一来应当在形式上与汉字书法相同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英文书法颇显僵化。首先,改造出的二十六个“偏旁部首”相对于汉字二百多个构字因子数量悬殊,故在字中每一“偏旁部首”重复的概率远远高于汉字;其次,汉字组构方式太多,书写时不得不逐字琢磨套用何式为好,必然影响气息的贯通——新英文书法或别的什么非汉字书法,在没能拿出高于传统书法的作品之前,一切的“嘲讽与逼问”本身就显得可笑。
文意的审美地位
“纯化”与“回归形式本位”的旋风不知是何时刮入中国艺坛的,前卫书家马上意识到:文意既然是非视觉形式本位的,那就剔除吧!“纯化书法”听起来是件好事,实则是“锦上除花”——如果在众多花样的锦绣中偶尔出现那么一两块只见素丝晶亮而无花纹可读的纯化锦面,或许真会令人眼目一新,不妨欢迎它入伍。可是素锦若要“嘲讽和逼问”彩锦,则非众人所能容。
杭州张苍水纪念馆大厅悬着一块大匾,是沙孟海的行书,雄浑劲畅。笔者叹服其势之当下,再留意那三字:“好山色!”脱口而出的一刹内心的审美感受陡然翻了几翻。再一次去考究其视觉之美时,似乎气魄比第一眼更厚了许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均不得不归于作品中视觉审美内容与文意的共振交辉。它们并非简单地累加,而正可谓“一加一大于二”。相反,若请沙老从《天书》中选出三个“字”以同一笔韵书就,其内容可谓纯化与本位了,但品之必觉单薄,原因正在于缺乏虽附属却有独特审美效应的文意之“伴奏”。至于新英文书法勉强算有文意,但破译太费事!更何况它的体式中缺乏汉字的优越?
文意的介入使得书法具有了综合性,类似歌唱中既有音乐旋律又有诗词之美。作品中附属于书法的内容如此之丰,雅涉诗文史哲,入宫庙楼塔、名山大川;俗关婚丧节庆,登百姓门板、苍陌招牌。书法堪称世界上与民族文化结合得最完美、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一门艺术,历数千年而依然广受人们喜爱。而剥离文意就等于割断了它的文化血脉与受众基础。
扫视现代主义绘画的演进,从库尔贝、马奈算起,不难看出“纯化”的趋势。主题非神圣化,主题形象主观化、破碎化乃至消失(抽象),最后达到上世纪中叶“绘画的零度”,走到了“进步”历程的终极点:空白。“在这个阶段,你再怎么画都不‘新’,都不‘震击’”,(注:河清著《现代与后现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一度还超越了绘画,转向行为艺术。现代书法浪潮与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真是何其的相似:对以摹习传统经典为基础的置疑,结字、章法的叛逆,对文字的解构,非文字,假文字……大致也是弱化主题(文意)与突破形象(汉字)两方面。其实走到“非文字”便与抽象画合辙了,只是因为不想失去“书”籍,才又走回来造字罢了。笔者能否“不嘲不逼”地询问:为什么艺术非得纯化不可?为什么在没能找到可行性道路之际也得硬着头皮变,否则就得被嘲讽和逼问?到底是要一幅幅作品中没有了文学内容,只留枯湿、浓淡、疏密、力量与速度或假汉字在宣纸上,人家要看就看、不看拉倒了才算大功告成登上书法更高审美境界、才算跟上了时代呢?还是要以跟上时代为幌子,来催促这门国粹舍此趋彼去与国际接轨、“国”将不国?
当前以传统路子为主、探索实验为辅的必要
正如中国尚有大量票友,京剧及各种地方戏仍有存在必要,传统路子的书法既然至今仍是广大人们仅能接受的类型,也便依然应当留存。发展当然必须,但变化的步伐不宜不顾受众。如果书法主流忽然另类得人们无法接纳,则它就如断了线飞离人们视域的风筝,无论舞姿多么翩跹,于世已毫无意义。
笔者并不讳言书法在反映时代风貌及与当代人的观念、情感对接、同构上的滞后与困惑。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笔者才认为要充分尊重一些实验型的探索作品,甚至有必要增设数年一届的“现代书法展”作园地。即便其中有幼稚与荒谬,亦不宜嘲讽与逼问。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证实了一种路子的不可行也应看作是成绩。徐冰《天书》、《新英文书法》的意义多被认为是“实现了现代观念”,“我是在为这个显得有些无聊的领域(按:指当代艺术)找新的活路,离一个系统远了,也许离真正的艺术的目的就更近了”(注:沈伟编《中国当代书法思潮》[C]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二○○一年版。)。读来仍觉玄乎。可是,这些作品能促使我们去廓清前述那些问题,这个价值倒实在。近些年,一批实验性作品除了作为一种新潮艺术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当代文化精神或给人以视觉美感之外,还为书法界提供了形式的借鉴或激发了某些书家的想像力,也属事实。然而,在没有探索出真正是发展提高、而不只是改变、更不是降格的可行性道路之前,中国书法的主流仍保持传统的路子走下去(并非一成不变!)完全合乎情理,不是心安理得,而是权宜之计!近些年似乎有太多的人在批判书坛的保守,并一再地振臂高呼“改革、前进”,这种论调除了可以助他标榜革命之外,只会弄得书坛更浮躁。书法中精神内涵与形式的调适本来就需要漫长的时间。陆维钊等先生不轻言“创新”就是担忧新未创成而传统的精华又丧失了;笔者以为在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纷纭变幻,而国人又在时髦于“与国际接轨”的当下,中国书坛同时应该听一听“文化民族主义”的呼声、对某些问题尤其有必要及时理清头绪,侧重传统或实验的书家一旦明白了各自的分工与共同的目标,则对立自然化解,嘲讽和逼问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