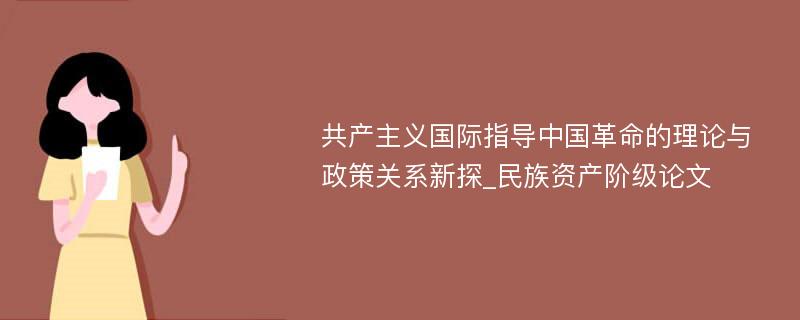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关系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大革命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结论:“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1 〕中共党史界对这个结论已无疑义,但是讲起错误的具体内容来仍然众说纷纭。传统的说法认为,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无论理论还是政策都表现为右倾退让。然而翻阅了历史文献特别是新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二卷之后,深感这种看法难以成立。事实说明,共产国际指导大革命所犯的错误,从政策上看是右倾退让,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体系乃是“左”倾教条主义。
一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最早的设想是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独立开展工人运动,做好“迎接社会革命准备的工作”,要求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2〕。 列宁改变了这个设想,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第一步应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是最广泛的革命动力,与资产阶级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联合。这个革命可以使这些国家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最主要组成部分”〔3〕。
列宁提出的上述理论是正确的,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很快从低潮走向了高潮。但是有些理论问题当时还来不及解决,共产国际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又发生了这样两个方面的错误:
第一,共产国际感觉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两面性的根源及表现。
在共产国际文件中早就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而且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过,这个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支持民族运动”,然而“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4〕。 但是后来共产国际越来越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截然划分为两个阶段。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曾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情况作出如下判断:“如果说,最初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先锋,那么,由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群众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就开始脱离出去”,因此无产阶级只能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5〕。 随着中国国民党内右派的猖狂和资产阶级妥协性的加剧,共产国际开始对中国提出这个问题。1924年12月维经斯基就说,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离革命而远去”〔6〕;1925年4月鲍罗廷进一步说: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不支持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然而当前“是否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可能这个资产阶级觉得帝国主义对它的利益的危害比工人日益增长的阶级斗争的危害要小?”因此“与其说它可能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7〕。 与此同时加伦也说:“由于中国各工业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资产阶级脱离国民革命运动而走向国内反革命阵营,并谋求同外国资本妥协。”〔8〕1925年5月斯大林更加明确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革命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分裂成“革命的部分(小资产阶级)与妥协的部分(大资产阶级)”,这里的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指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斯大林认为,这个阶级“害怕本国的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还要厉害,宁肯与帝国主义者勾结而不愿进行把自己国家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只是目前这部分“还不能与帝国主义联成一气”罢了〔9〕。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便在中国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大暴露和西山会议派出现的形势下,把斯大林的预言看成了现实。此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未就此走向反动,共产国际也没有立即就将民族资产阶级当成反革命阶级,但上述观点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理论化。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第二阶段,虽然工人阶级作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出现在中国舞台上,但是仍然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部分地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第三阶段,运动的基本力量已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会议再次预言此时中国正处于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共产国际认为,1927年4月蒋介石的叛变, 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正式走向反动。同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表明了这个观点, 全会明确地宣布,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阶段〔10〕。
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根源和表现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原因在于照搬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公式,特别是俄国的模式,因而不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11〕。共产国际照搬的正是这个“一般规律”。斯大林还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等同看待,仅仅认为“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是极端软弱的,比1905年时期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软弱”〔12〕。这种观点不懂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具有上述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工农觉悟之后才有的,而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始终同时具有革命和妥协两种性格,这种两面性总的表现是“动摇”〔13〕,而不是从革命走向反动。它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软弱一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甚至有“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14〕,但即使这时它们仍然是动摇的。没有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殊性,单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一般规律,结果必然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反革命阶级将其排挤出革命阵营。
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亦即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认识上也有两方面的错误。
一方面,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提法是模糊的,确切的提法应该是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即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因为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的资本主义要有一个“广大发展”的阶段〔15〕,共产国际的提法恰恰否定了这种发展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搞清楚如何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首先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罗易又补充以“工农苏维埃”〔16〕。1923年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时开始谈及中国革命前途问题,11月26日,在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不能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且应当“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兴起提供可能”,它必须“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17〕。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正式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斯大林在会上还做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认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并且说“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资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18〕。
共产国际主张的建立工农政权也好,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等被剥削阶级或者叫做劳动者的民主专政也好,都把民族资产阶级排斥在政权之外,也都否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明确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实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应该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共产国际的上述观点显然与毛泽东所说相违背,这种观点也是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再现。
综上可见,无论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还是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共产国际理论上的错误都是“左”倾的。当然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只是“左”倾错误,问题在于它是否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同时也出现了陈独秀所提出的那种“二次革命论”,即认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种右倾的理论。但是,遍查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文献,都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应该说,20年代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出现“二次革命论”,反而出现“左”的理论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1905年列宁就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发展为革命转变论,而且很难设想共产国际这期间总的指导思想有“左”的因素,而唯独指导中国革命出现右倾理论。
二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在政策方面犯了右倾错误,已是无须争辩的事实。政策不能不与理论相联系,那么,“左”倾理论是如何转化为右倾政策,右倾政策又是怎样与“左”倾理论相联系的呢?
历史文献说明,上述转化是在国共合作这个特殊条件下发生的,导致这种转化还有一些具体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与“左”的理论不无关系,它们实际上就是“左”的理论与右的政策之间联系的纽带。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对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的阶级属性以及实际力量,作了错误的估计。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估计是不断反复的。最早对国民党阶级属性作出分析的是1921年4月21 日《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报告说国民党“与我们的社会革命党有些相似”〔19〕,就是说它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接着马林经过调查之后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也可以说它是“工人党”。马林是从对国民党成员的阶级成分和国民党政治纲领的分析中作出上述估计的。马林认为,从成员看,国民党中“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者”,党员群众主要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南方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资产阶级是极少数,而且基本上是“侨民”。从政治纲领看,马林认为国民党中的侨民“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国民党政治上提出了三条原则:“反对外国统治;争取民主;争取公民的人的生活”〔20〕。马林虽然也说这三条原则总的还是民族主义的,但对最后一条应解释为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不反对。鲍罗廷的认识比马林前进了一步,指出了国民党纲领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空想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但仍然在强调它不代表哪个阶级,它以整个民族为基础的同时,又说它是“小资产阶级政党”〔21〕。上述估计直到国民党一大前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共产国际本身还是它派驻中国的代表,对国民党的看法总的都没有超出民族主义政党的范畴,又都认为它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什么“工人党”、“工农党”、“小资产阶级的党”、“人民的政党”等等提法,不一而足。
随着对国民党阶级属性过高估计而来的是对它的力量的过高估计。1923年越飞估计国民党“正在成为中国群众性的政党”,孙中山很可能会在近期内实际上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鲍罗廷也说,“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而“在目前和很长时期内”,孙中山是“能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代表”〔22〕。在这样估计的影响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得出如下模糊的结论: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
共产国际在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弱点,认为“国民党已彻底涣散”,因此主张改组国民党。但是共产国际对改组后的国民党估计更高。加拉罕把国民党一大看作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鲍罗廷则说国民党一大开辟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新纪元”。他们认为国民党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以生产国有化为基础,力求在国民革命以后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改组是“整个‘布尔什维克化’进程”〔23〕。
然而事实与上述估计相差甚远。改组后国民党内右派的猖狂,迫使共产国际改变看法,开始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认识到右派是“买办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分子”;中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左派是“广大工农群众”〔24〕。但是随着反对老右派斗争的胜利和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以及所辖军队改编的完成,共产国际对此时的国民党再次作出过高的估计。1926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认为,广东国民政府已是“依靠城乡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顽强反帝斗争的东方革命民主政府的第一个样板”、“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国民革命军已是“彻底的民主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坚决打击封建军阀集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维护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25〕。
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逐渐形成的事实,又给上述认识以当头棒喝。但是共产国际始终把蒋介石视为中派。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国际无视汪精卫已经成为右派的事实,竟将以汪为首的武汉国民党看成“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26〕,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民主政党”〔27〕;将武汉国民政府看成“城乡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政府,“国民党左派的政府”,这个政府虽然实行的“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28〕。
基于对国民党及其所属政权、军队的上述错误估计,共产国际便企图通过国民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维经斯基曾说,国民党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1923年1 月召开的俄共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华的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毕竟不是它们所估计的那种政党,它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不改变自己的估计和企图就只有对国民党实行退让政策。如鲍罗廷所说,如果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内“使右派感到厌烦,我们准备召回他们。在中央机构中没有共产党员我们也可以做好工作”,但是在保持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有组织的、团结的领导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也不应该让步”〔29〕。对国民党实行退让政策,从客观上看就是对资产阶级的退让,这种政策无疑是右倾的。但是主观上这种退让乃是与把国民党看成工农党、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左”的理论相联系的,与夸大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右的理论并没有什么关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理论上“左”的错误,就这样转化成了右倾政策。
导致“左”倾理论转化为右倾政策的另一个因素,是没有真正弄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根源和表现。这个因素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左”的理论与右的政策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更加直接。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把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机械地分为两个阶段。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共产国际便以为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没正式叛变就是革命的,就能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因此共产国际虽然意识到了蒋介石有妥协倾向,甚至有叛变革命的可能,却仍然以“利用”政策代替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如斯大林所说,在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前,共产党应该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斗争是在“广泛利用”这部分力量之后的事〔30〕。布哈林更加明确地说,从阶级性上说蒋介石虽比克伦斯基更坏,但是从战争角度看,蒋介石比克伦斯基还有能利用的地方。因此,“只要他暂时尚未反动尚未变节,只要他能积极的实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31〕。由于有这种指导思想,因而在蒋介石叛变前,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斗争,不肯给蒋介石的反动活动以坚决的打击;蒋介石叛变后,又认为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从而把汪精卫当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继续实行退让政策。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低,是导致共产国际“左”倾理论转化为右倾政策的第三个原因。
应该肯定,从理论上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作用的认识是正确的,它明确地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接触到实际斗争,它便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力量对比,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也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起初,共产国际曾企图经过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工人运动的道路来发展中国革命。那时主要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1923年2 月维经斯基曾说,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形成,必将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因素。但不久他又提出相反的看法,“在中国现时状况下,工人运动还不是能够率领整个民族反帝运动的重大因素”,并且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本身包含着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潜在力量”,这个力量要在“数年以后”才能发挥出来〔32〕。此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估计仍有起伏,但总的趋向是偏低的。共产国际虽然提出了国共党内合作的正确主张,但其根据则包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33〕,因而把在华政策建立在支持国民党上。共产国际一再强调“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甚至认为这个力量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认识不清外,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轻视。
应该说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偏低,本身就是右倾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右倾与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的右倾理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当然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与轻视工人阶级力量本来是矛盾的,为什么共产国际能够把它们集中于一身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在共产国际看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去实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隐约地出现过这种观点,列宁曾以俄国共产党人在前沙皇殖民地土尔克斯坦的工作为例指出,“只要胜利了的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34〕。这种观点此后始终隐约地存在着,鲍罗廷就说过,中国无产阶级弱小,很难领导中国革命。但是,“若拿他与印度无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特别苏联无产阶级共同来看。那末中国无产阶级之必不可免的历史的缺点就百倍的补偿起来了”〔35〕。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先进国家的帮助只能通过本国共产党发挥实际作用,离开本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很难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放弃领导权自然是右倾政策。
在国共合作条件下,由于上述三种因素的存在,“左”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转化成为实际工作中的右倾政策是合乎逻辑的。这种“左”倾理论和右倾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都有影响。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不同,1923年和1926年陈独秀提出的“二次革命论”曾一度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但1924年到1926年,在共产国际正确思想指导下,这种“二次革命论”在不断纠正,共产国际“左”的理论也不断被接受。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最终抛弃了这种“二次革命”论,进一步接受了共产国际“左”的理论,而且立即转化为右倾政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然而大革命一失败,国共合作一破裂,共产国际继续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的“左”倾理论,便自然而然地直接导致“左”倾政策了。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 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9页。
〔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61、363页。
〔6〕同上,第618页。
〔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599~600页。
〔8〕《共产国际、 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661页。
〔9〕《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 113~114、120页。
〔10〕《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32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1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68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4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
〔1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0页。
〔1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2~23、27页。
〔1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336~337页。
〔1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78、268页。
〔19〕《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 —1925),第58页。
〔20〕王淇、杨云若等编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15~17页。
〔21〕《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423页。
〔2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197、369~371页。
〔23〕同上,第307、410、419、452、466、387页。
〔24〕《共产国际、 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660页。
〔2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131、136~137页。
〔26〕《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27〕《罗易赴华使命》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283页。
〔2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324、329页。
〔2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187、576页。
〔30〕分别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78页。
〔31〕《国际评论》(1926—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571页。
〔32〕《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71页。
〔33〕《共产国际、 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36页。
〔3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2页。
〔35〕《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6页。
标签:民族资产阶级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小资产阶级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国民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