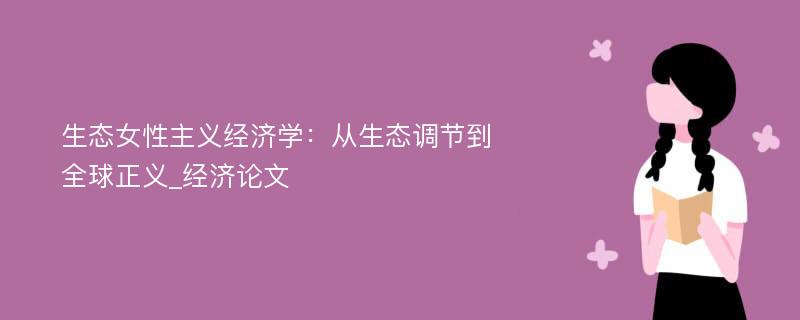
生态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生态适量到全球正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正义论文,经济学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经济学在当前分别致力于全球一体化和地方自治的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中的相关性何在呢?这种交叉学科能够适当回应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和文化多样性的劳工运动的知识基础吗?本文将着重阐述在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再生性劳动概念,用来分析生态工作或“供养性(provisioning)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们都曾是经济的、可持续的和自治的。可以发现,“生态适量”(eco-sufficiency)准则早已被全球大多数劳动者——土著居民、农民和看护工作者——所遵循。但问题是,北方国家的理论家能够与这些“超工业”(meta-industrial)劳动者分享这些智力与政治资源吗?他们能够把新陈代谢价值(metabolic value)的观念提升为经济学中的主流概念吗?
生态女性主义对于生态经济学的价值早已得到著名人士像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or)、拉马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琼·马丁奈兹-阿里尔(Joan Martinez-Alier)、比娜·阿伽瓦尔(Bina Agarwal)和理查德·诺加德(Richard Norgaard)等的认可。阿伽瓦尔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肯定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强调妇女在传统农业和医学中的技能,以及当农民和土著妇女缺乏财产时其社会建构起来的看护性角色如何受到伤害。的确,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穷人的环境主义”。甚至在北方国家,作为其再生性劳动的结果,妇女经历着很多男性并不知晓的贫穷与痛苦。这就是为什么维朗妮卡·本霍尔德特-汤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和玛丽亚·麦斯(Maria Mies)强烈推荐一种倾听来自“下层观点”的方法论:“揭露那些由上层人士创造的幻想,即他们的生活和生活风格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是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的未来榜样……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好生活只对少数人是可能的,而且(享受它)必须要以其他——自然、其他人和妇女儿童——为代价。”①在这方面,通过借助欧洲中心论的眼光来概念化对于男性而言的所谓意义,主流经济学和大多数生态经济学采取的是一种“来自上层的观点”。作为一种可持续性科学的经济学所看到的只是生产主义冰山的一角,人类与自然之间经济转换的大部分甚至没有被提及。
基于此,本文将着重比较由抽象的市场指标主宰的生态经济学和致力于生态完整性的供养性经济模式。当代经济学知识的大量内容正由于过分脱离其总体背景而变得难以理解。更糟糕的是,专业性建议本身已成为一种商品。虽然存在着无数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化学或核排放的政策“措施”,但这些税收和补贴举措、绿色工程和生物道德规范无不都是在修补一种旨在促进个人收益和内在冲突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社会学家已经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自然的分离。皮特·狄更斯(Peter Dickens)把现代“异化意识”视为工业劳动分工难以避免的结果。同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把人类日益退化的生态理解能力解释为城乡之间“物质代谢裂缝”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正在扩大着这种裂缝。无疑,需要技术调节的生活事项越多,人们就会越多地失去我们对与自然有机交换的心理感知。西尔维娅·费德里西(Silvia Federici)用“失忆症”来描述这种知识流失——而环境滥用就是那种内部分裂状态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导致分离的工具理性还没有征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很多地方的人们依然能够理解他们在自然中的物质显现,并知道如何实践生态适量的准则。
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尼古拉斯·乔格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十分认真地信奉人类应该以一种生态健康的方式满足其需求。与凯恩斯主义传统不同,他把一种生物系统意识和热力学原则带入了经济学思考之中。斯蒂芬·邦克(Stephen Bunker)继承了这种观点,并指出:“人类生活的长期延续取决于我们迄今为止尚未意识到的能量转换过程……最初以社会形式发生的开采与生产受制于一个单一的地区性生态系统。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往往需要把开采性活动分散到数量广泛的物种和矿产品中;结果相对较少的物质与能量从这些不同物产形式中开采出来,因而生物链可以相对稳定地再生自身……工业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破坏其所依存的资源基础……因此,自然可以通过社会方式创造出来的观念是一个基于片面思维的离奇幻想。”②
然而,要想充分实现其目标,生态经济学——就像绿色政治理论和环境伦理学一样——也必须借助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与文化研究的概念性工具。尤其是后者,它可以丰富我们寻找增长范式替代方案过程中的视野与想象。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一种性别化的深刻分析或由笔者主张的具体性唯物主义所引入的“生物能量学”。在当前的生态经济学中,“实体性能源”指的是外嵌性(exosomatic)的事实,比如一个产品从生产、运输到消费的生命周期中所投入的燃料数量;而在生态女性主义中,“实体性能源”指的是主体的或内嵌性(endosomatic)的能源流动,比如通过人类劳动、性活动和再生性自然等。很明显,这样一种想法可以导致像多尼拉·米都斯(Donella Meadows)所指称的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意义上的重要创新。
关于自然能量的外部化或“科学主义的”观念与自身形体化的观念之间的区别,可以很容易从下文的“维基百科”(Wikipedia)引述中看出来:“自然资本可以视为在这个星球上对稀缺物质与能量的赠与,除此之外还有复杂的和生物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它直接向人类共同体提供着商品与服务:微观与宏观的气候调节、降雨调节、水循环、水净化、废水吸收、传播花粉、宇宙与太阳辐射保护等。”③在这里,“稀缺”呈现为一种本原意义上持续性的、而不是人为造成的异常,而生命系统被界定为可有效利用的“死物质”或资本,是具有商品化潜能的商品与服务。这里几乎没有主动的人类共同进化的意味,相反,它是“这个星球”(而不是比如妇女的身体)把这个系统作为人类资源而赠与。上述引文忽略了经济学发展中历史形成的性别化、阶级和种族的背景,而没有对日益客观化的资本主义父权制条件下的人类与自然资本术语加以分析。当然,“维基百科”不是一种学术著述,但它的确体现了目前的现实境况。而且,这种外部化倾向还得到了各种量化工具的刺激,尽管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不胜枚举的区域的、时空的和其他的经验性不可比较证据。
另一种典型的简化技术是把经济描述为一个“发动机”。对于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来说,这种机器是由四种可以量度的资本推动的:嵌入的、人类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相互替代。人类满足或生活质量的实现依赖于系统构成要素间的平衡。相应地,科斯坦萨及其同事把智利经济学家曼弗雷德·麦克斯-尼夫(Manfred Max-Neef)的整体主义著述,简约为一组所谓北美生活质量研究的数字:“我们从麦克斯-尼夫的维持生存观点中剥离出一个可称为‘再生产’的新范畴……承认再生产的重要性对于妇女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蕴。”④为什么再生产活动要从维持生存中剥离呢?为什么再生产活动应该被剥离为“妇女的角色”呢?男性也完全可以从实践中学会再生性劳动和生命确证的认识论。比如,农民或采集者的超工业供养活动就展示了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即用自然中不断提高的新陈代谢流动来改进人类需求的满足。
所有这些表明,生态经济学家正在以多种方式打破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而且人为强加的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的分离也在受到挑战。我们只要想想近年来由杰出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所引导的进展,就可以确信这一点。除了经济效率考量,他把“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正义”引入了经济学,并作为其核心指标。除了国民生产总值,他还提出了“真正进步指标”(GPI)。除了热力学定律,他还提醒我们,经济学一词的渊源是生态学,即家庭研究,意味着生态系统就像一个人类大家庭。不同于短视的生产主义,戴利清楚地知道,生物时钟和再生产慢于经济时钟或生产,而且代际间平等原则要求我们用一种更长的时间维度来思考。戴利超越了经济简约主义,支持跨学科研究、三维性方法论和民主的辅助性原则。
但在其他方面,戴利的研究方法背后仍然隐藏着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保守性功能主义遗产,而且这些因素有时会抵消了其更为进步性的意蕴。无处不在的数学模型化就是例证。而且,对于“可持续规模”、“公正分配”和“有效配置”的集中关注,也显然是在迎合绿色经济的幸福意识及其“三重底线”。规模、分配和配置这三个核心指标,在一个特殊系统中运行,而它所设想的边界从未得到经济学家的充分辩护。借用系统理论和控制论类比的抽象语言,这种生态经济学对“经济”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市场自由主义解读“看不见的手”一样。规模、分配和配置在一个官僚工具主义的理性主义框架下进行讨论,而自上而下的管理目标非常类似于一种世俗伪装下的“上帝之眼”。系统分析的主要缺点是,经济功能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来描述,结果造成一种无法区分和无可避免感。这种方法掩盖了权力在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差别,而且弱化了人们承担其相应责任的信念。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戴利把价值界定为一种“心理收益”所暴露出来的唯心主义色彩。不仅如此,相关的讨论往往遵循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好像这些收益对于企业管理人员和土著居民、对于母亲和父亲是一样的。决策参照变量比如“边际收益”对“边际机会成本”也在一个并未社会地界定主体的非历史真空中运行。这种看似中立的方法论漫不经心地把分配与配置模型过滤为一种客观的机制。但事实上,分配与配置是特定主体(往往是白人中产阶级)针对看起来较次要人类群体——即北方国家的目标对象(包括世界各地的女性、南方国家的农民和土著居民)——的生活环境所做出决定的后果。当一种理论分析的社会主体被省略以后,看起来就好像是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和先天的“人性”。
相比之下,跨学科的经济学家也许会以一种更多考虑到阶级、种族和性别差异的方式,来讨论规模、分配和配置。其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谁来决定规模?谁分配给谁?谁被授权来配置?以及为什么?除了上述批评之外,戴利是把“人类资本”和“自然资本”描述为相互关联的生态经济学家中的领导者。通过解构把人类与自然分为两个不同领域的传统的二元主义,这种努力开始将一种从前由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使用的假定转向辩护各种形式的政治主宰。但是,只要其分析框架中的社会学偏见不被改变,生态经济学的超越潜能将只是潜在的。的确,在当前的学术会议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农民和土著社会的专题讨论,甚至会主办一个女性主义论坛。但问题是,这些讨论只能被用来作为“修饰物”以显示一种开明专制中的多元主义吗?这些边缘性派别只能被视为“问题领域”,即分配冲突的例子,或者等待生态经济学的主流来同化吸收的“外部性”吗?
1.作为参照点的再生性劳动
如果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即在创建一种替代性和真正全球性的政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或环境伦理学的过程中,正是那些边缘性群体像家庭劳动者、农民和土著居民能够创造符合21世纪需要的社会正义与可持续性模式,那会怎么样呢?这样一种声称应该在生态经济学话语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它会带来一种远远超越其知识背景的深刻变革吗?母亲或狩猎—采集者被“过分否定性”地建构了吗(“依赖性的”或“偏常的”)?——就像戴利等依据权力的行使所可能解释的那样,妇女只具有“名义上的权力”和“理论上的权力”。古哈和马丁奈兹-阿里尔已经为生态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农民社区中环境政治的卓越评论。约翰·高迪(John Gowdy)(乔格斯库-罗根的学生)则已论证了土著居民供养性活动的合理性。但是,难道只能由很大程度上处在这一学科之外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来阐明一种具体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性和妇女在可持续科学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吗?
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对传统智慧的解构。比如,如果说“稀缺”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那么“无能”就是其统治认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沿着这一逻辑,太多妇女,包括世界穷人中的多数,将会铁定成为男性主义暴力和剥削的牺牲品;而南方国家中的人们将会很快被迫倒在“现代化与进步”的“无情”车轮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成功尺度——比如妇女的个人主义解放和市场参与、农民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面向第一世界的生态旅游——会成为被高度推崇的东西。联合国、世界银行、八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些生态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所谓穷人如何抓住“发展阶梯中的第一梯级”;但这一硬币的另一面是失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圈套,即超工业劳动和维持生计资源的减少。乔治·卡芬特齐斯(George Caffentzis)写道,在发展话语中,“极端贫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一是家庭无法满足其基本需要,二是它们无法挣得每日人均1美元的收入。因此,假定的乞讨者可以凭借每日1美元能够买到的“商品与服务”在美国生活。但是,卡芬特齐斯提醒我们,现实中还存在着实实在在的非货币经济:“的确存在许多这样的乡村,其居民理解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但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却低于每日1美元……在很多非洲村庄中,成年人(在很多地区也包括妇女)能够自由进入那用来维持生计的土地(尽管并没有所有权)。这是一种不能被异化因而并没有交换价值的巨大财富(使用价值)……这对于儿童来说也是一样。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儿童被村庄或扩大的家庭所供养,而他们的实际收入低于每日人均1美元。’’⑤
在联合国的现有发展模式下,公共土地、水、生物多样性、劳动和爱情关系,被从一种生态可持续的和文化自治的自足网络中抽离了出来。依据北方对南方或1对0的逻辑,发展意味着人们必须转换成为“人力资本”,而他们的生活资源转换成为“自然资本”(主要是为了有利于一个国际性少数的企业家阶级及其政府代言人)。多少年来,从非洲、澳洲到南美的无数社区,一直在力图抗拒这种占有以便维持其对地方资源的控制。但问题是,生态经济学家们与他们站在一边吗?或者,这一学科在不自觉地支持这种殖民化并带来了生态欠债或躯体欠债等方面的后果?
如今,在国际上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圈子里充斥着一种对像印度和中国这样国家向北方国家生活标准看齐所带来的消费与排放标准提高的担忧。但未被引起注意的是,比如瑞典政府的一个报告承认,瑞典人在2000年比10年前多吃了40千克的食品,并高于欧洲平均水平30千克。欧盟消耗的食品比亚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有着占消耗世界资源80%以上的生态足迹,却在不停地指责处在边缘地位的世界人口由于它们自己的“新陈代谢裂缝”出口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基于这一背景,关于看护性妇女、小农场主或采集者是熟练的生态经济管理者的主张,也许会被证明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它会威胁到由全球资本家和学术精英所享受的特权。不仅如此,超工业劳动能力的观念是对我们时代的重大智力挑战,因为它涉及到两个看起来相互对立的政治原则:“平等和差异”。无疑,戴利“环境可持续性、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的目标,提炼自现存经济秩序下的平等原则。但问题是,如果这种秩序所依赖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和非正义的,那么这种补救行动是有效的吗?
应用平等与差异原则需要一种在生态经济学跨学科研究中不均衡地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意识。“差异”原则在一个封闭的霸权体系中也许看起来是违反天性的,因为它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环境下无能的“他者”。此外,在应对“其他”概念时,政治生态学家和生态经济学家也许会面对来自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著述中的两个看似冲突的立场。但需要强调的是,关键是看由谁来说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无原则的生产主义左翼的分析,将会支持基于社会产品的公平再分配的工业范式所带来的解放。但站在政治生态学的立场上,上述观点就保护新陈代谢价值而言都难以成立。问题在于:“大多数发展理论家试图把来自工业生产系统的模式扩展到其效果有限的非工业系统中……但交换价值只有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才能创造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生态女性主义坚持认为,再生性劳动和使用价值的生态适量领域对于经济学来说比交换价值生产领域更重要。主张这一观点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包括玛丽亚·米斯、范达娜·希娃(Vandana Shiva)、玛丽·梅洛(Mary Mellor)和艾瑞尔·萨勒等。它是一种基于劳动的立场,而不是基于比如妇女“更接近自然”或“优于男性”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生物学观念。同样,作为一种历史性主题,生态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像“完美的女性”和“高尚的野蛮”那样的唯心主义赞歌,就像辩护性的发展研究者可能指称的那样。我们主张的具体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于人们处置感知人与自然关系的日常经历。同样,它也拒斥所谓富足和后物质主义价值导致了环境意识的自我慰籍式的自由主义论点。
2.具体的唯物主义
具体的唯物主义(an embodied materialism)是指居住地、性、种族、管治、科学和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种难以用计算机加工处理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善于测量他们称之为“生产”的东西,但却很难准确测量“再生产”。然而,如果乔格斯库-罗根的远见得到真正尊重,那么他的“混杂实践者”概念应该扩展到再生性能量循环领域。研究物质流动的生态经济学家承认:“劳动生产的增加只有在同时增加存在于自然物品中的能量开采与转换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然而,这种价值核算所忽略的是再生产性或超工业劳动在协调物质/能源转换和使新陈代谢损失最小化方面的作用。问题是:生态经济学家中谁拥有如此的知识并将其表达出来?显然,它属于一种具有强烈的“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品格的领域,因为“后常规性”的前提是学科的基本假定长期地处在交互审视之下。基于这种思路,米都斯以远超出其同时代人的远见指出,生态经济学需要一个概念性的“参照点”。而笔者认为,再生性的超工业劳动和生态适量的新陈代谢契合(metabolic fit)观念,可以提供这种概念性参照。
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三个范本的现象学解读阐明,超工业供养性活动何以实现生态适量。第一个例子是范达娜·希娃对印度森林居住者的个例分析,这是一种在科学前提下对共同进化与再生性力量的看法。正如她所指出的:“正是在森林与农业的维持生态循环的整体性过程中,妇女的[再]生产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形成与发展。妇女将丰产性从森林转移到田野和动物。她们把动物废弃物转化为庄稼的肥料,并收获作为动物饲料的副产品。妇女劳动与自然劳动之间的伙伴关系,保证了生存的可持续性。”⑥同样,澳大利亚土著人和东南亚狩猎—采集者,在他们审慎的体力劳动中实践着一种“系统性维持”,他们在穿越乡村时养育着可持续性。在这种最为有效的和生态适量的生物区经济中,乡村间的季节性穿越基于如下知识,即如果采取明智的收获方式,每一个栖息地将会得到适时恢复与更新。正如高迪指出的,狩猎—采集者的效率可以从如下事实得到证明,他或她很少使用多于其身体供养所必需的资源中的物质与能量。
另一个例子是城市经济中的超工业劳动,其中德国生态活动家乌拉·特林登(Ulla Terlinden)阐述了家庭再生产中的明智观念。“家务要求妇女[或男性]广泛的知识与能力。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组织。手中的工作必须被整体性地对待……劳动者必须拥有高度的个人综合、创议、直觉和灵活性。”⑦与这种近距离参与相对照的是杂乱的工业劳动分工——来自投资者或装配线指令的冷酷无情和混乱无序。基于父母技能的背景,美国哲学家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谈到了“维持性”劳动,将其作为与良好的生态理性(如果算不上生态管治)相并行原则的具体体现。“维持意味着使风险最小化并调和差异,而不是急剧地凸显它们。[妇女或男性的]维持性活动是适当关注如何保持最低程度的和谐、物质资源和保护儿童安全必需技能的一种方法。它是由世界保护、世界保持、世界修复等需要所诱发的一种态度。”⑧通过使面对物质不确定性时的风险最小化,超工业维持性活动是对适应的一种恰当表述。而且,尽管传统科学遭到事实与价值、空间与时间之间实证主义分离的屏障,一种谨慎的相互联系意识是这种具体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或许有讽刺意味的是,超工业劳动中精确化的经验主义、它内置性的“现实检验”,都远远超过了最严厉的科学证伪标准。
土著居民、母亲和维持生计者的再生性劳动,拥有许多有助于新陈代谢契合的方法论特征:
●消费生态足迹较小,因为使用的是地方性资源并得到供应者的日常性看护。
●规模是小而舒适的和可以控制的,最大程度地回应物质/能源转换并使熵最小化。
●判断由长期的试错过程而做出,因而有可能形成真正具有代际视野的重要评估。
●超工业劳动在本质上是谨慎性的。
●责任链是清晰而且可以问责的——根本不同于导致官僚制经济的少数人决策的专制。
●由于地方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像工业社会那样变得错综复杂,因而仍然有可能采取综合性的难题解决方式。
●在家庭和农场环境中,多维决策是根本性的。
●再生性工作可以更好地协调人类时间与难以预测的、非线性的自然时间。
●这是一种懂得储存与流动差异的经济理性。
●它是一种自治的和赋权的劳动过程,不存在劳动者精神与体力技能之间的分离。
●劳动产品不是异化的,而是可以立即享受或分享的。
●超工业供养性活动是生态适量的,因为它不会通过债务来外部化成本。
上述的其中一些看法与戴利关于经济规模的观点相一致。然而,戴利是从“家庭功能”的视角将经济学和生态学概念化的,因而把“自然提供的生态服务赋予货币价值”,但妇女的劳动仍然没有被重视。同样,在三分之二贫穷世界的背景下,戴利关于三角组合——规模、分配和配置——功能的看法也值得重新审视。在共同拥有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并实施生态适量的供养性实践的社区共同体中,以及在合作性劳动伦理依然胜过极端个人主义“发展”的地方,分配与配置会变得无足轻重或者采取十分不同的形式。马丁奈兹-阿里尔也强调了这一点,用于解释生态经济学在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背景下的起源。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在转变成为政治生态学,一个超工业阶级的概念既是联合性的,也是在政治上包容性的。来自各种社会的妇女和男性在其生命过程的某一阶段上都承担着再生产性劳动——经济的、文化的和生物的。但日益明显的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再生产作为一种经济上被忽视的、未得到价值肯定的和未被货币化的过程,被人们回避了——至少对于大多数男性和在资本主义父权体制中认为暂时成为赢家的部分妇女来说是如此。
3.全球北方国家的能力建设
那些不太了解其学科发展的文化背景的生态经济学家也许会发现,在此提出的批评是有违直觉的。但是,“人类资本”的概念在现实中太容易变成一个缺乏性别立场的观念——就像工人在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中一样。生产主义术语掩盖了妇女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像“超工业劳动”这样的参照工具,家庭看护者所做出的精致的热力学贡献就会被忽略。围绕着森林居住者工作产生的种族盲点,是另一个相关性问题。当劳动者被意识形态地消除其性别或种族特征而“自然化”时,就变成了非人,一种无偿资源,即形体性债务的实例。陈旧的人与自然的二元主义在统治性文化及其学术圈中依然是一个盛行着的神话。
因而,像乔格斯库-罗根那样承认生态经济学必须植根于生态学基质及其物质/能量流动中是一回事,而生态经济学本身如何真正能够做到贯穿一种主体性的生物能量或心理感知则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一个学者自身的阶级、种族或性别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形成什么样的概念或方法。知识总是适应性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种族或性别原因而变得虚弱无力,这些方面就总是会被忽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观察研究所2004年举行的一个大规模全球消费研究未能有效区分消费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很多人已经在实践着生态适量准则时,仍然有许多人坚持说“我们别无选择”。正如尼克·法拉克拉斯(Nick Faraclas)指出的:“选择无处不在。”而卡芬特齐斯进一步强调:“没有任何理由说,那些通过基本需求的非商品化和公共事业的发展而摆脱了贫穷陷阱的人们,将会迫不及待地投靠愿意提供其劳动工资的第一个资本家。”⑨要实现生态适量和全球正义,笔者认为,最有效的“千年目标”就是归还那些以“发展”的名义从人们手中夺取的土地。
生态经济学中对新概念框架的需要可以从朱丽叶·尼尔森(Julie Nelson)关于主流学说中日益强化的自恋趋势的评论中得到证实。这具体体现为一种对现状的先入为主——假定将来与现在不会有太大差别;一种对简单化阐释的偏爱——依赖高度简化的人类行为特征从事过分集合性的分析;一种对学科分野的过分看重——沉湎于理性选择模型的框架而忽视来自其他学科的信息;一种对僵硬性的操守——鼓励对既有模式的信奉却无视它已变得失去效能;一种对现存等级权威的敬畏——维持主流经济学家的形象,他们的论文也是由具有相同的理性选择思维的同事审定的。尼尔森比较了这种封闭系统内的知识创造与“高度可信赖性组织”,在后者中决策权总是给予那些真正具有专长的人,而不管其等级地位如何。尽管如此,生态经济学著述中对“后常规科学”的引用率表明,很多人已经开始审视他们的基本信念的社会建构。他们开始追问:是谁在做这一理论分析?我采取如此一种概括问题方式的立场是什么?我凭什么做出某种理论概括?这种反思可以有助于使经济学对占世界多数的其他声音与价值保持开放态度。然而,尽管“后常规逻辑”看起来接受了一种自由多元主义的立场,但具体性唯物主义并不是相对主义者,而是坚守有助于保护物质代谢价值的一切,即生态学的底线。
正如全球性资本主义开始表明的,人们不得不质问:什么是“价值”的价值?而且,当一种经济建立在否定人类在其中的生命存在基础上时,人们就会明白它是如何自相矛盾的。同样,交换价值以及部分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也将呈现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概念,只是通过少数强权个体的行动主观构建的。真正的“底线”是生态整体性——由物质代谢所体现的复杂过程。在作为先行者的小国厄瓜多尔,这一新概念正在被融入它的宪法,新宪法将通过赋予自然以司法权来消解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与自然对立的二元主义。正如其宪法第一条强调指出的:“自然,作为人类的栖息与繁衍之所,拥有存在、延续、维持和再生其重要的循环周期、结构、功能和进化过程的权利……每一个个体、种族、社区或民族将有权在公共机构前要求承认其自然权利。”⑩这种法律创举为进一步认可新陈代谢价值开辟了道路,并进而逐渐体现到社区管治和经济思考中。
在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看护提供者、小农场主和“原初居民”的“另类”经历被呈现为“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它被置于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政府和联合国机构的可持续科学话语之外。在达沃斯,全球资本主义领导人的世界经济论坛仍在施展着这种花招。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现在受到了先后在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孟买、内罗毕等地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的压力与推动。此外,资本主义父权制全球化下的失利者已经走上从科恰班巴(Cochabamba)到布达佩斯的街头,并主办会议与网站来抗议世界贸易组织和八国集团的政策。这一历史转折点始于1999年西雅图的种族代表会议(People's Caucus)——由美国和加拿大的土著居民环境网络、美国第七代基金和其他组织举办,并向世界宣布:“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提供主导性经济模式和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的可靠替代。我们的可持续生活风格与文化、传统知识、进化中宇宙、精神、集体价值、互惠、对母亲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在我们探求一个平等、正义和可持续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转型社会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11)
正在发生的国际资本的崩溃将各种选择性社会运动推向历史的前台。为了支持这些实践活动家的创举,政治生态学家、绿色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女性主义者和其他有爱心的人,应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生态可持续性,保护物种、性别和代际之间的物质/能源相互依赖性;二是社会—经济正义,保护新陈代谢价值和对共同生活基础的主权;三是文化自治,保护“差异”和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一个社会变得越复杂、技术上越发达,上述目标将越难以协调。但是,一个处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边缘的、自治的再生产劳动阶级,却能熟练地演示给我们如何实现这种综合。在很多后殖民主义环境中,超工业模式仍得以较完整保留;而北方国家的妇女与男性正在创造生物区域性网络、精神性农业公社、地方性社区花园和有机农场等中的替代性经济。当生态经济学家反思戴利的“环境可持续性、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模型时,很多人也许已感到有理由用“文化自治”来替代他的效率概念。因为,当国际经济制度本身是内部自相矛盾的时候,“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目前正是相关学者和全球正义活动家坐下来深入研讨的恰当时机,并且都要求教于那些真正拥有生态适量感知的人们。但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小心一个陷阱,正如澳大利亚土著活动家利拉·沃森(Lilla Watson)强调指出的:“如果你只想来帮助我们,那么你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但如果你是因为你的解放离不开我们而来,那么请让我们一起努力。”(12)
(本文是作者2009年主编的《生态适量与全球正义:妇女论政治生态学》一书的第十六章,经作者授权发表。)
注释:
①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 and Maria Mies,The Subsistence Perspective(London:Zed Books,1999),p.93.
②Stephen Bunker,"Natural Values and the Physical Inevitability of Uneven Development under Capitalism",in Alf Hornborg,J.R.McNiel and Joan Martinez-Alier(eds.),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Lanham,M D:Altamira,2007),p.251,pp.254-5.
③Wikipedia,"Ecological Economics",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Online availableat http://www.wikipedia.com.
④Robert Costanza et al.,"Quality of Life: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Human Needs,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Ecological Economics 61/2(2006),p.271.
⑤⑨George Caffentzis,"Dr.Jeffrey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A Political Review'",The Commoner,10(2005).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ommoner.org.uk.
⑥Vandana Shiva,Staying Alive:Women,Ecology and Development(London :Zed Books,1989),p.45.
⑦Ulla Terlinden,"Women in the Ecology Movement",in E.Altbach et al.,(eds.),German Feminism(Albany:SUNY Press,1984),p.320.
⑧Sara Ruddick,Maternal Thinking: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Boston:Beacon,1989),p.75.
⑩"Ecuador:Nature Has Rights",Green Left Weekly,10 September 2008.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climateandcapitalism.com.
(11)Tebtebba Foundation,Indigenous People's Seattle Declaration on the Third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WTO(Seattle:8 December 1999).
(12)利拉·沃森经常引用的这段话最早是在1985年的内罗毕联合国妇女大会上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