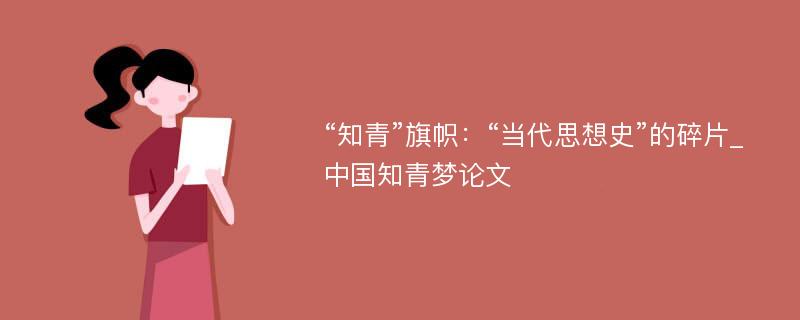
“知青族”的旗帜——“当代思想史”片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片断论文,旗帜论文,思想史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笛卡尔认为,为了达到真理,一个人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把他以前所抱的种种看法通通抛弃,重新取得一套有系统的知识。
——卢梭:《爱弥儿》
这是一个历史的课题:知青文化对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的巨变具有怎样的意义?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场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因此高涨。“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几百万红卫兵变成了青年农民。许多人在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时候是那样的虔诚……还有的知青以为他们像当年的革命家一样,到农村去撒播造反的火种,‘组织起千千万万的工农大军’。很少有知青能够想到,他们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历史已经证明:“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洪流,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既然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和就业问题,又不可能让千百万红卫兵成为无业游民,采用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就成为当时惟一可供选择的方案。”〔1 〕就这样,纯洁的乌托邦梦想与无情的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撞。这种冲撞导演了无数的悲剧与喜剧,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效应——从1978年至1979年间的“知青大返城”到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群”的崛起直至九十年代初“知青文化热”的兴盛……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座桥梁:从忠诚的“红卫兵”到叛逆的思想者的桥梁。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面旗帜:从狂热到绝望再走向希望的旗帜,当代人精神流浪的旗帜。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个标本:极左思潮由盛而衰、思想潮流由一元到多元、价值观念从一极走向多极的一个标本。
而知青文学又是知青文化的绝妙结晶。因此,通过知青文学洞悉知青文化的丰富与芜杂,便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从狂热到绝望
狂热与绝望,是人生情感的两极。但“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却使一代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狂热走向了绝望,从愚忠走向了叛逆。
知青作家邓贤在长篇纪实《中国知青梦》中记录了一代知青从狂热走向绝望的苦难历程。其中关于“北京五十五”的描述就很具有典型意味:他们早在1966年初冬就带着“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考察了西双版纳,并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968年2 月奔赴云南边疆(早于毛泽东发布动员令整整十个月)。但没过几个月,这些热血青年就消沉了: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逼使他们正视严酷的真理——仅凭着理想是不行的。冷酷的现实比火热的理想更强大。不久,他们就先后悄悄地离开了云南。
“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卜大华也于1968年去陕北插队。他后来回忆说:“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我从那虚幻的天上落下来了。……我找生产队长,提出治穷要靠机械化,山区要发展林业,不是靠什么‘大批促大干’。这是我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后得出的结论。”〔2 〕——贫穷的现实击退了狂热;贫穷的现实催生了理性之思。从这层意义上说:贫穷的土壤也是思想解放萌芽的基础。
贫困的现实不仅击毁了狂热的梦想,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存。1972年,知青家长李庆霖冒死上书毛泽东,倾诉知青的苦难——“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不仅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这便是知青的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使广大知青不得不直面生存的艰难,不得不品味生命的苍凉。尽管毛泽东读过李庆霖的信后指示“统筹解决”,但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历史条件下,知青的贫困生存状态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除去贫困的威胁,还有知青与农民间的鸿沟在知青心中产生的幻灭感。《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回忆道:下乡不久,知青就感到当地农民并不欢迎他们。1969年夏(正值“九大”开过,“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失望的情绪在知青中弥漫开来。这种情绪构成了《南京知青之歌》的主旋律:“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颖。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这旋律竟很快唱遍大江南北,又神奇地被莫斯科广播电台传向了世界。“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思考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3〕。感伤、 叹息这些似乎早已被革命风暴埋葬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就这样悄悄回到了知青的心中;强烈的失落感、“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局外人”、“零余者”心态就这样成为现代荒谬感、绝望感的先声(尽管知青们当时不可能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历史证明:“世纪末心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产生。
甚至不仅仅是不欢迎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正是封建特权对人性的恣意蹂躏给了知青致命的一击,使他们中不少人或自暴自弃、在疯狂报复的变态心理驱使下走上反社会的绝路,在打架斗殴、偷盗抢劫中宣泄疯狂;或悲观绝望,千方百计走上逃亡之路——从装病到自残,从走后门到出卖灵魂与肉体……在没有民主与法制的黑暗中,知青运动很快分崩离析。由各奔前程的私逃到1978年西双版纳十一万知青的大请愿、大罢工、大逃亡,并进而引发了全国知青大返城,使知青运动终于在1979年打上了休止符。
此外,“文化大革命”风云的变幻莫测也触发了一代人的“信仰危机”——荒唐的政治骗局毁灭了一部分人,也成就了另一部分人。看破荒唐以后,知青们开始以叛逆者的姿态或嘲弄、或批判极左思潮——有的以篡改“革命歌曲”为乐事,直至变“革命歌曲”为下流小调(这方面,知青作家乔瑜的小说《孽障们的歌》堪称典范。这种变“神圣”为“调侃”的心态,实开“王朔热”的先河);有的敢于质疑当时的金科玉律,大发异端之论。《中国知青梦》中就记载了后来的知青返城运动领袖凌卫民的异端思想——还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他就在大会发言中口若悬河地论证了“英雄创造历史”和“人民创造历史”都是真理,这在当时显然是大逆不道的。而凌卫民当时也肯定不会料到:在新时期史学界拨乱反正的思潮中,历史学家们也会围绕“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展开激烈的论争〔4〕……
这样,由于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的重负,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知青文化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谱写出了文化转型的新篇章。尽管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极左思潮的一统天下,但“知青文学”却开拓了精神的处女地……
“知青文学”的先锋
“知青文学”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八十年代文学的奇迹。整整一代知青作家在“伤痕文学”的暴风骤雨中崛起于文坛。大江东去浪淘沙,文学新潮此起彼伏,文坛上也有了“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说法。但“知青文学”却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不断产生优秀之作,几度掀起“知青文学热”,堪称奇迹。张承志、梁晓声、郑义、孔捷生、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陈村、王小鹰、张抗抗、史铁生、陶正、叶辛、马原、张炜、矫健、陆天明、陆星儿、晓剑、卢新华、李晓、柯云路、李锐、老鬼(马波)、邓贤、朱晓平、乔瑜、郭小东……他们是两千万知青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在当代文坛建起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知青文学”。
但不应该忘记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真实地记录下知青苦难的“地下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从书中披露的史料来看,“林彪事件”以后,“返城风”悄悄刮了起来。动乱的年代耗尽了人们的心力,知青们渴望宁静的生活。一批纯净、奇丽的“童话诗”应运而生——“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我——想——你”(《梦之岛》);“当然, 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那时我们沉沉睡去”(《无题》)。这些知青写下的“童话诗”与八十年代风靡大陆的台湾校园歌曲、席慕容的诗歌在精神上何其相似!
这是滤去了狂热的纯净与唯美。
还有驱逐了狂热的冷漠与迷惘——例如根子(岳重)的诗《三月与末日》:“……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淀/既然他,没有智慧/没有骄傲/更没有一颗骄傲的心/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这种现代主义的诗,这种混合着冷漠、迷惘、忧伤情绪的诗在知青中相当流行。由芒克(姜世伟)、根子和多多(栗世征)为骨干的“白洋淀诗派”因此成为“朦胧诗”的先锋。芒克、多多到了八九十年代仍然继续写作,证明着“地下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某种精神血缘联系。
赵振开(艾姗、北岛)的小说《波动》、王某某的小说《一年》都弥漫着冷漠与迷惘的寒雾。《波动》中的肖凌饱经磨难,理想幻灭以后,无比悲凉地感叹:“咱们这代人的梦太苦了,也太久了,总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会发现准有另一场恶梦在等着你。”“哼,伟大的二十世纪,疯狂、混乱、毫无理性的世纪,没有信仰的世纪……”《一年》中也有一句话:“知青是大地的流浪者”——这些,都是知青走向绝望的血泪结晶。但《波动》、《一年》的叙事笔调又富于伤感色彩,所以,也与麻木、冷酷的境地相去甚远。在绝望中还真情不灭,是许多“知青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特色。
《波动》、《一年》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也是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的序曲。
批判现实主义是良知不灭的证明,从狂热中猛回头,思想者化痛苦为愤怒、为感伤。
此外,还可以从“知青文学”中找到“痞子文学”的源头。神圣感幻灭以后,有的人痛不欲生,也有的人开始调侃神圣。这种调侃集中体现在篡改革命歌曲上。例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原是一首豪迈的进行曲,经知青中的调皮鬼一改,就变成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迎面走来一群姑娘,有的瘦得像猴子,有的胖得像猪一样……”〔5 〕这当然是一种被苦难扭曲的畸形“创作”,也昭示了一种不健康的性心理,但无论如何,它开了八十年代末王朔“痞子文学”的先河。(笔者当年下乡时,也听见过知青传唱《红色娘子军连连歌》、《金日成将军之歌》的篡改版,调侃取乐。)换个角度看:在一个动辄得咎的年代,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知青改写“革命歌曲”也算得上是胆大包天了——在潜移默化中,这种调侃的心态无疑消解了神圣也消解了紧张。
还应该提到知青中的通俗文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就记述了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知青说书艺人的脱颖而出。北京知青章海善于说书,从古典话本《武松》、《儿女英雄传》到当代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还有手抄本《林强海侠》。1975年,他在北京读到香港新武侠小说《碧血剑》、《陆小凤》,很快便在知青中传讲开来……由此可见,在“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横行的年代,知青却走向了通俗文学。不难想象,在那样的岁月中,通俗文学给了苦难中的知青以怎样的精神食粮。而当我们联系到八十年代中期台港通俗文学在大陆的风行,我们也会发现:知青文学中也早就萌发了通俗文学的嫩芽。通俗文学在知青中的流行也于无形中消解了“帮派文艺”的影响。
以上,便是“文化大革命”中知青“地下文学”的多元景观。它们在黑暗的年代里开出了一片片精神的处女地,成为在精神荒原中点燃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唯美主义乃至世俗主义多盏灯火的火种。它们的流行昭示了多元文化魂归神州的原始图景,昭示了人类文化传统不会泯灭的伟大定律。另一方面,它们又是那个年代里公开出版的另一种“知青文学”(长篇小说《征途》、《铁旋风》、长诗《理想之歌》)的对立面。另一种“知青文学”因为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写阶级斗争,塑造知青英雄,至今似乎已为历史所遗忘,但是,其中回响着的理想主义豪情到了八十年代又获得了新生……
因此,得出下面的结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知青地下文学”中,已经孕育了“文化大革命”后思想解放、文学自由的种子。知青文化,也因此而成为当代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标本。
八十年代“知青文学”的壮丽图景
1976年,“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结束。与此相应的,是思想界、文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与反思。于是,有了“伤痕文学”,有了“反思文学”……
“伤痕文学”是苦难记忆的写照,是愤怒岩浆的喷发——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村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卢勇祥的《黑玫瑰》……都是血泪的控诉,又都富于浓郁的感伤色彩。极左思潮葬送了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从恶梦中醒来,却不知该从何处讨回公道!
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衰落了。但知青的控诉却不可能划上句号。1982年,马原发表《海边也是一个世界》,梁晓声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前者压抑、低沉,后者慷慨、悲凉,却都是知青的悲歌。此后,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都一再写到了知青的牺牲(马原在那部小说中写道:“我们这伙人里专门出冤死的鬼魂”……);老鬼的《血色黄昏》于1987年问世后,也取得了轰动效应。这部“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记述了作者在内蒙八年的知青生活,作品展示了知青的非人生活(“如果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话,那么知识青年就是臭老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社会地位比那些老知识分子更低一等。”)——挨整、服苦役、受歧视,因此而发愤赎罪,又因此而自虐(以衣衫破烂为美、写血书以申诉);因此而看破了同路人的势利与可怜,也因此而变得粗鄙、无耻、麻木、冷酷。《血色黄昏》因此也成为“知青文学”中最震撼人心的力作之一,其中对于人性扭曲过程的记录,对心灵变态过程的分析,具有极高的心理分析价值。而其中关于知青异端思想的记录,也是宝贵的思想史料(1968年,就有了“江青成了慈禧太后”的议论;1974年,就有了“社会上跟老师说的完全不一样,你要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寸步难行”,所以,“我自己就是一种信仰”的议论,有了“什么形势大好……工资低得要命,冤假错案成千上万……这政策确实有问题”的愤激之言)。
直至1992年,还有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为知青的牺牲与奋斗作证;直到1993年,还有李锐的《黑白》为知青模范的自杀谱写了一曲挽歌……
控诉与批判的主题一直在延续,意味着知青心中的伤痕永难愈合!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知青作家的控诉与批判并不只指向极左暴政。《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和《上下都很平坦》就无情地展示了知青屈服于淫威的怯懦;《血色黄昏》就感伤地暴露了知青中的可怜虫人性异化的灵魂——为了自我保护而出卖朋友、巴结上司(“为了一个大学名额,一项好差事,一句表扬话,人们互相争夺,不惜打得头破血流。……为什么年轻人都变成这样?为什么?万恶之源在哪里?”是正义者的迷惘。“没有怕就没有生命……严格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叛徒的一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人性就是如此脆弱。”是苟活者的哲学)……而《今夜有暴风雪》中不也有对知青在绝望中释放罪恶能,放火、抢劫、杀人的描写吗?
知青心中的伤痕是极左暴政刻下的,同时,又何尝不是人性恶的证明?
这样,控诉就与叹息联在了一起,批判也与自审联在了一起。痛定思痛,知青作家敢于以抉心自食的勇气反思历史的沉痛教训,进而在当代青年运动史、当代思想史上刻下这一代人的人生哲思。
这样,便有了个性的复归——狂热幻灭以后,猛然发现自己已一无所有,于是就重返自我的小世界:徐乃健的小说《杨泊的“污染”》就记录了知青从“伊加利亚”生活方式转向生存竞争的人生轨迹,面对招工、招生的有限名额,知青们不约而同地接受了“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相信:“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把某种东西变成商品,进行交换”。“时代把我们推到了这么个原始、低级的竞争状态中,粥少僧多,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亲近的人我也不让!”这儿,已经有了八十年代商品化大潮竞争喧嚣的先声。这儿的个性,充满悲凉的意味。另一方面,王安忆的小说《69届初中生》也描述了个性复归的心路历程,却并没有剑拔弩张的焦灼——雯雯在生存的挤压下从理想主义走向实用主义,凡事都要问一句“这有什么用?”“有用的她才做,没有用的,她则不做。”这是世俗的哲学,但王安忆却写出了世俗中可贵的真诚:雯雯是实用主义者,但决不损人。她的想法是:“没法子,我们都是小人物……只能努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我们很自私,可是,我们生活得很认真。”注意,正是这“认真”二字在消解了幻灭感的同时也消解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冷酷。在一片悲凉之雾中还能认真地做人,实在难能可贵。雯雯这样的人生哲学在当代青年中相当普遍地流行着,这种哲学在“信仰危机”的惶惑中维系了心灵的平衡。(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披露:1972年,史铁生就与友人一起讨论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6〕;1980年, 在《中国青年》组织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中,也出现了“合理为己”、在“不损人”的前提下“合理为己”的主张〔7〕; 《棋王》的作者阿城也在谈及自己的知青生活时谈道:“那一段生活毕竟使我开始老老实实地面对人生,在中国诚实地生活。”〔8〕)
从“斗私批修”到“生存竞争”或“合理为己”——是一条重要的思想史线索。它显示了知青中多数人从天真走向务实的心路历程。
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从“改造世界”到“理解世界”。
韩少功的《回声》为“改造世界”的狂热唱了一曲挽歌:路大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青年毛泽东的榜样,下乡来搞革命,可他全心全意依靠的贫下中农要么是根满那样的“阿Q的子孙”, 要么是反对“破私立公”、骂他为“神经”的种田人,他耗尽心力,最后却是铩羽而归——路大为的失败很有代表性。晓剑、严亭亭的《世界》也凝聚了“红卫兵领袖”吴大路在边疆的反思:“他现在已经完全不相信自己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巨大的精神危机迫使他发出这样的心声:“啊,还奢谈什么解放别人,还是先救救自己吧!”重新开始奋斗,但不再是以救世的姿态,而是以探索者的姿态……孔捷生的《大林莽》也通过一个大林莽断送了狂热探路者的悲剧故事感悟人生的真谛:“人类妄想成为大自然的上帝已很久了。问题是,人不仅绝非奴隶,也不是上帝。”“据说,‘人定胜天’这古训,并非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意思。何况,我们有另一句涵义更深邃的古训——‘天人合一’。”〔9 〕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也是神秘的大自然埋葬了知青的狂热梦想的一曲挽歌吗?理想是可贵的。青春的热情是可贵的。想乘长风破万里浪,可是,“你没有舵,没有彼岸,甚至……没有大海”。(《世界》)二十世纪就这样埋葬了一代人的英雄梦。这究竟是一代人的悲哀,还是时代的荒诞呢?!
承认救世之梦的不合时宜,走回到“天人合一”、“理解世界”的传统中来,与世界达成一种妥协,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无奈的宿命。
然而,这也还不是一切。为什么承认了失败,知青作家们还要为知青逝去的青春唱一曲曲真诚的赞歌?为什么知青作家能在一次次风云变幻、人心沉沦的时刻把理想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
例如张承志。他从1978年发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起,就一直写着理想主义的篇章:《绿夜》、《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直至《心灵史》。知青运动失败了,但张承志高傲地拒绝诉苦。他深深地怀念在社会底层坚忍生存、默默奉献的人民,深深怀念青春的激情与理想。他知道“为人民”的口号已不时髦,但他仍然奉之为圭臬;他知道理想主义是一朵“错开的花”,但他坚信“我虽孤独一人但只有我获得了拯救。”(《错开的花》)——他证明了民本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不会消亡,以他那一部部为人传诵的壮美之作,在悲凉的世纪末,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始终狂热地为人民、为理想、为知青而歌唱,而他的狂热也在许多青年中激起了热烈的回响。如此说来,谁又能断言:狂热已不再能拨动时代的心弦?
再如梁晓声。一面以《雪城》、《年轮》继续谱写着知青的感伤之歌、壮美之歌;一面以《浮城》、《泯灭》、 《龙年一九八八》、 《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敲响了世纪末的警世之钟:世纪末的重重忧患令人焦灼。所以他说:“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正是这种“为人民”的立场使他能写出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力作,奏响了正义感、使命感的时代强音。
又如韩少功。1985年他举起“寻根”的旗帜,为的是在浮躁的时世里“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汲取精华,注进现实生活,光大发扬,给当代人来个扶阳补气,益精固本”〔10〕。他为重新发扬楚魂的光荣呼风唤雨,不也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吗?(梁晓声针砭时弊,是社会使命感;韩少功光大传统,是文化使命感。)1986年,在浮躁的喧哗中,韩少功重申人格的意义、知识分子素质的意义,他说:“一种伟大的艺术必定是一种伟大的人格的表现”。“人格就是作家独到的精神境界”。“真正伟大的人格就是既看透了一切又充满着博爱,原谅一切宽容一切去爱、去同情一切。”〔11〕这一番议论,是对文坛上矫情作派、争权夺利习气的批判。1994年,他又在《世界》一文中深刻反思了文化的命运,批判当代文坛的鄙俗化、市井腔,呼唤中国文化的再生奇迹,呼唤“真理的声音,一种高远澄明嘹亮的精神”重放光芒〔12〕。
还有史铁生。这位在1972年就走向了“合理的利己主义”的思想者也在1986年以后走向了爱的宗教。《我与地坛》多么宁静,多么深沉——淡然地接受厄运,承当苦难,需要怎样豁达的襟怀!《随笔十三》多么睿智、多么深刻:“宗教一向是在人力的绝境上诞生。我相信困苦的永在,所以才要宗教”。“知人之艰难但不退而为物,知神之伟大却不梦想成仙,让爱燃烧可别烧伤了别人,也无须让恨熄灭,惟望其走向理解和宽容;善,其实仅指完善自我,但自我永无完善。”〔13〕这便是史铁生的信仰:博大而不偏狭,虔诚却不狂热。
张承志一直是理想主义的旗手。
梁晓声一直是批判现实的斗士。
韩少功一直是文化传统的守护神。
史铁生也一直是宗教精神的播火者。
——他们的个性不同,选择不同,却都富于使命感,都富于理想主义气质。世俗化的思潮愈是汹涌,他们的精英品格愈是夺目。由此可见:知青作家,是世纪末人文精神的传人。他们的业绩表明:在告别了乌托邦之梦,世人纷纷走向务实的年代里,理想主义的火炬并未熄灭。新的理想,建立在古老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又是当年的知青激情在焚毁了极左毒素后的涅槃。当《我与地坛》、《心灵史》、《夜行者梦语》等书在九十年代初的一片沉寂中掀动了人文精神复兴的大潮时,我们便不难发现:“新理想”的崛起竟是以知青作家的作品为主要标志的。
也就是说:“知青文学”已成为世纪末人文精神复兴的典型象征。
而最世俗的哲学与最圣洁的精神都共处于知青文化中这一现象,还能昭示怎样的文化之谜呢?
是的,知青文化是驳杂的:世俗与理想、粗鄙与圣洁、绝望与调侃、放纵与牺牲……知青文化中都有。《中国知青梦》中的知青群像中,既有悲壮的牺牲者、深刻的思想者,也有走私和性解放的尝试者;《血色黄昏》中的老鬼,粗鲁又真诚,坚忍也脆弱;《棋王》中的王一生,散淡又认真,贫贱也柔韧……都是驳杂的证明。
让我们再看看每一次文学潮中的弄潮儿:“伤痕文学”中的卢新华(《伤痕》)、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反思文学”中的韩少功(《回声》)、孔捷生(《大林莽》)……“改革题材文学”中的柯云路(《新星》)……“寻根文学”中的韩少功(《爸爸爸》)、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阿城(《棋王》)、郑义(《老井》)……“新潮文学”中的马原(《错误》)、王安忆(《小鲍庄》)……“性文学”中的王安忆(《小城之恋》)、铁凝(《麦秸垛》)……“新写实”中的刘恒(《伏羲伏羲》)……哪一次文学热潮中没有知青作家弄潮的身影?这一现象是驳杂品格的又一个证明吧:因为经历过风云变幻,所以练就了顽强的生命力、适应力;既能谱写怀旧的篇章,又能迎接新潮的挑战;既怀有古老的理想,又富有现代意识(韩少功、王安忆、李杭育、张承志等人都既是“寻根派”,又是“新潮作家”;张承志、史铁生等人的理想既古老灼热,又充满了现代的悲凉意味)……
所以,“知青文学”常常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年轮》,叶辛的《蹉跎岁月》、《孽债》一拍成电视剧,便家喻户晓。道理很简单:“知青文学”中那浓郁的感伤情调永远为大众所钟爱,也能为精英所理解。当新生代以出奇的冷漠创造出《活着》、《红粉》那样的艺术品时,知青作家却以《年轮》、《孽债》重温了永恒的感伤。
是的,感伤,古典意味极浓的感伤,也许是知青一代人最本质的情感特征。理想的受挫、青春的苦闷、生存的艰难、命运的严酷……这一切在苏童、余华、格非、吕新这些新生代作家的笔下,都冷漠无比。现代主义的荒谬感、绝望感是他们世界观的基础。而知青作家呢?他们中不少人也接受了现代主义的荒谬感、绝望感,陈村的《一天》、《象》,王安忆的《小城之恋》,铁凝的《对面》,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马原的《虚构》、《西海的无帆船》……也都堪称寒气逼人之作。可一当他们回首知青岁月,一当他们描写知青生活,笔调就大不一样、境界也大不相同了——陈村的《给儿子》、《蓝旗》,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韩少功的《回声》,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错误》……都浸透了缅怀青春、感叹命运的感伤之情。由此可见知青作家对自己青春激情的怀恋,可见知青情结的圣洁。
以这样的眼光看去,我们也不难发现,“知青文学”中的感伤之作源源不绝: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孔捷生的《那过去了的……》、《南方的岸》,陆天明的《啊、野麻花》、《桑那高地的太阳》、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桑塬》,李锐的《北京有个金太阳》、《黑白》,梁晓声的《雪城》、《年轮》……这些写实之作从艺术手法上看去,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但是,知青文化的苍凉背景、知青情结的感伤情调,却使这些平实之作具有了感天动地的巨大魅力。这些作品能在文坛上激起热烈的反响,能在人心中拨动真诚的心弦,正是时代需要感伤、需要古老的人道主义情感的证明;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道主义是“知青文学”的主旋律。
都说这是一个风云多变的时代。时间的飞速发展似乎已把古老的一切都抛入了忘川。可是,请看看“知青文学”吧:它是古老的良知永不泯灭的证明;是人类离不开古典情怀的证明;是这一代人忘不了“文化大革命”、忘不了苦难,忘不了民众的证明。
“知青文学”就这样成为一面旗帜——一面世纪末风雨中人文精神岿然不动的旗帜。
结语
人间永有真情在,可是,时光无情。
知青一代已经人到中年。他们可以在一次次的“知青文化热”中唱出“青春无悔”的悲歌,但他们总有一天会老去……
会有那么一天,“知青文学”、“知青文化”成为历史学家、思想史家研究的话题。后来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会怎样评价这一代人的功过是非呢?
早在1984年,张承志就在《北方的河》开篇中写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
1988年,知青作家王安忆也在与学者陈思和的对话中谈道:“我们不如老三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受到的教育已经足以帮助他们树立自己的理想了。……可69届没有理想。”“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但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陈思和也指出:“这一代人实际上是相当平庸地过来了”,“69届一代人很难有浪漫气”。“知青作家始终没有像西方现代青年厌恶战争那样去厌恶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对它的反动本质给以充分揭露,实在是使人失望的。”〔14〕
到了1994年,知青作家张抗抗也谈及了知青的致命伤:“老三届人,也许恰恰是被假马克思主义毒害最深的一代。知识的贫乏再加思想的僵化——这或许是老三届人真正的悲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由于教育和经历的原因,他们在本质上,同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她最后的话是:“我可是走不出老三届了。”〔15〕
——上述议论是知青作家的自审。这种自审意识虽然已体现在《回声》、《大林莽》、《中国知青梦》等作品中了,但再过一段时间,这种自审会超越感伤的情调深化为无情的批判吗?(换个角度看:如果“知青文学”失去了伤感的品格,它的魅力是不是也减色不少?)
不管怎么说,上述议论为研究知青文化、为“知青文学”向纵深挺进提供了新的思路。日后,也许会有客观、公正、辩证的历史结论作出——那当然不是这一代人的事了。只是,我常常想:如果那时还有“知青文学”,如果那时的“知青文学”会无比冷峻地批判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那也一定会失去这一代人的“知青文学”的魅力吧!
而“知青文学”作为多元文化的象征,作为古典浪漫主义的延续,作为历史记忆的证明,对于新世纪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也一定会是新世纪人研究二十世纪末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话题。一定。
1995.4.28~30.急就于华中师大
注释:
〔1〕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第120、 173页,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2〕黄际昌、张平力:《第三次抉择》, 见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5)第95—9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3〕任毅:《一首知青歌,九年铁窗味》,《海南纪实》1989 年第7期。
〔4 〕黎澍先生就指出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苏联的提法,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见丁守和等《黎澍学术思想述略》,《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5〕冯水木、冯至诚:《长歌当哭》,《龙门阵》1988年第1期。
〔6〕《“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86页, 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7〕雪华:《为合理的道德观说几句话》,《中国青年》1980 年第9期。
〔8〕《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
〔9〕《林莽和人》,《中篇小说选刊》1985年第2期。
〔10〕《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1〕林伟平:《文学与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12〕《花城》1994年第6期。
〔13〕《收获》1992年第6期。
〔14〕《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 年第3期。
〔15〕《同“老外”谈老三届》,《海上文坛》1994年第2期。
标签:中国知青梦论文; 文学论文;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世界论文; 波动论文; 棋王论文; 年轮论文; 血色黄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