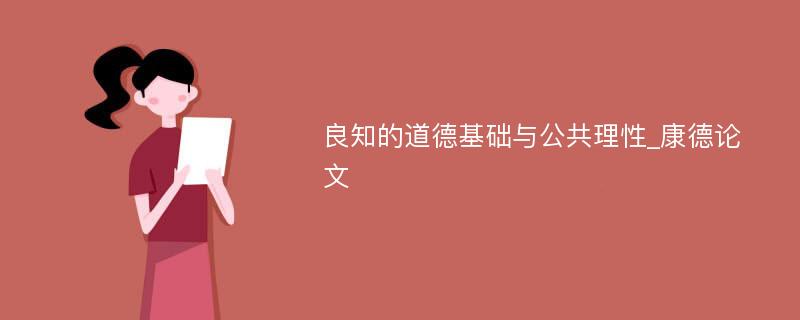
良知与公共理性的道德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知论文,理性论文,道德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罗尔斯公共理性概念及康德人类合作的相互关系证明
(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在提出公共理性概念的时候是意有所指的,针对的是由各种可能的完备性学说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人为的分裂和敌对,因此他把公共理性限定为或者强调为一种超越了各种私人关系和社群关系的公民关系:作为自由平等公民的理性是有关公共的理性、主体关怀是有关公共善、公共性由公共推理表现出来的这样三个方面。①其核心是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一个公民的合作体系,这个体系的前提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和合作。这是关于公共理性的前提问题,没有公民的平等也就没有自由的合作,而如果没有相互间的义务关系的设定,社会中的合作体系其实是无从谈起的。虽然在罗尔斯那里没有直接强调这一点,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前提确定下来,但是这个前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其实也是需要加以论证的,这是公共理性的第一个要点或者叫前提证明。这是我这里要讨论的公共理性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将公共理性确定为公民之间的关系结构,因此,罗尔斯在其中特别强调了“相互性”(reciprocity)②,这是他在《万民法》中关于公共理性的一个核心概念。他突出这一点是为了确定个体之间交往的感性原则:即人们的日常交往是建立在一种互相平等和感性接触交往的基础之上的,即人们的日常交往是一种利益碰撞关系,这个利益性交往的原则就是“相互性”。这是我们这里要探讨的关于公共理性的第二个问题。
“相互性”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秉行的一个潜意识中的基本原则:等利害交换。③香港大学慈继伟教授曾将“相互性”作为“正义”的秉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正义的一个属性是关于正义的各种规范性的内容,这是可变的,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所不同。正义还有另一个属性:就是这个“等利害原则”,慈继伟认为这是正义的“结构性特征”④或形式性特征。他又将这种结构性的正义特性称作是狭义的或抽象的“正义秉性”,⑤也就是说,正义的严格的秉性就是个体交往的等利害原则。在罗尔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公民交往不是建立在相同的或不同的宗教或其他价值观之下的交往,正因为各种完备性学说各不同,因此,公民之交往基础是“相互性”,公共理性的政治架构是为这种“相互性”服务的,公共推理也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但是,我们考察“相互性”作为人们的行为原则其实更是一个心理原则或者叫公平原则,是一种对等的心理和行为预期,它的根基是人的良知,我们必须深入到人心性的深处才能更加完整地把握相互性概念的道德心理基础和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心理前提。因此,我把平等合作关系和“相互性”作为公共理性的两个支点性原则。
在现代社会体系中,人们的合作是基于公民之间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所确定的,但是对它的论证并非易事。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主要是近代自然法的契约论的证明方式,即人的感性的博弈活动导致彼此权利的让渡形成公共权力,并同时将个人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起来。后来,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受到康德很大影响,其人性假设依旧是经济学的“理性人”设定,因为在功利主义兴盛的背景下这种人性设定成为了一种基本的共识,只能通过这种论证才能重新复活一种新的契约论证明,因此,罗尔斯借助“无知之幕”的假设对此进行了重新的演绎。这样,对于人类合作之论证主要都是基于人性的消极假设进行的,其实,还有一个不大为人们所关注的从人性的德性层面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论证,而它主要是康德曾经给出的证明方式。同时,就人际关系的“相互性”要求康德也曾经给出过他自己的证明。
(二)康德人类合作关系的义务论和“相互性”的证明
康德所建构的人的自由和平等是建立在人的道德意志的基础上的,这个道德意志或自由意志是人之为人、人是目的的根据,这是一种积极的论证形态。但是同时,康德又认识到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是基于感性和道德理性的双重复合生活样态,彼此是基于感性与感性或欲望与欲望或利益与利益之间的碰撞,因此康德说:“由于我们是人类,具有一种受感觉官能影响的意志活动,结果这种意志的活动可能与纯粹意志不一致,甚至经常与它冲突,这些法则表现为强制的命令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因此,这类法则是绝对或无条件的命令。”⑥这些命令既包括伦理法则也包括法律法则。康德在这里仍然是从绝对命令的角度来建立他的法则的,这个绝对命令一个是基于人的自由意志即道德意志本身的,同时也有对感性欲望的反思的结果,他又把这种命令称作是“义务”,义务落实到个体头上就成为他的“责任”,不论它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自由成为任何与责任不相矛盾的行动,法律或道德人格化就构成了一个主体的法律的活动的自由,“道德人格不是别的,它是受道德的法则约束的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自由”⑦。确立人的义务观念,在康德,权利观念也就形成了,他认为,“权利概念作为把责任加于其他人的一种根据,则是后来从这种命令发展而来的”⑧。即我的义务与责任构成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共同体成员的相对于我的权利,而这是先验规定于每个人的义务,所以,每个人的权利也应运而生。相互之间的义务关系同时构成了相互之间的权利关系,即我的义务是对方的权利,反之亦然。⑨这是康德与启蒙运动中的契约论者之最大不同,当然这也不否定康德对法律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契约关系的肯定,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人的自由法则,人因为区别于自然约束的自由的自我约束而构成义务,由义务而形成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它只涉及人的行为而不考虑行为的动机,但是,它也遵循自由的道德原则,当然这个原则不再是个人的绝对的自由,而变成相对的相互性的自由。⑩
康德以个人的自由意志确定人的平等,这个平等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而是现实意义上的平等,这个现实平等的表示就是:所有意志的并存。所有意志并存就是说明:每一个意志即每一个个人都是平等的,这个平等是从人的自由推论出来的,而人的平等则要求个人之间不能存在支配关系,即所有意志的并存。以此为基础,康德提出了力的平衡原则。所谓力的平衡就是所有意志平等,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就是等利害关系,人的感性交往其实相当于一种“角力”,康德把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权利关系看成是一个平衡作用的物理法则:“权力的法则可以说是权力概念的典型结构,也就是根据作用与反作用平衡的物理法则,对物体自由活动的可能性进行类比研究,然后用一种纯粹先验的直觉来说明它。”(11)“权力科学的目的在于决定每一个人,取得像数学那样准确的他自己的那一份。”(12)相互间的自由实际成为相互间的强制,这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或者互为前提。康德等于同时论证人际基于道德的义务性和基于感性的“相互性”,而这两个原则其实都可以在儒家那里找到良知的道德根据。
二、儒家良知观念中“伤生若己”的义务论元素
(一)“伤生若己”的根芽
人与人之间彼此承担着相互对应的义务,这在儒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似乎又是难以证明或明述的。因为第一,儒家往往是在情感层面的论证,一般不将之加以形式化的论说;第二,这种论说又是停留在个人情感上的,要么是一种良知情感的苗头,要么就是良知情感充其极的“全体”,因此,存在着表述上的跳跃,的确不那么容易梳理,但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这在儒家的良知学中又是非常明确的。
关于良知,孟子论证以恻隐之心为核心,阳明之良知学说则以是非之心为鹄的。冯友兰先生认为,恻隐之心又为孟子良知学的根本,他说:“孟轲所谓‘恻隐之心’,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忍人之心’,孟轲认为,这是仁的苗头。在孟轲思想中,‘四端’不是平行的,‘四德’也不是平行的。‘恻隐之心’是‘四端’之首,也是‘四端’的根本;‘仁’是‘四德’之首,也是‘四德’的根本。”(13)所以,从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我们可以看到孟子良知学的出发点。徐复观先生认为,孟子是从人的不忍心中发现了个体道德意识之不依赖于人的躯体的独立性和直接性。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14)
孟子以“不忍”昭示出一种人心的状况:恻隐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宁,包括失望、难过、不接受等即“不忍”,它同时包含着对该对象怜悯、同情、慈善以及愿意其状态改变好转向上的愿望,因之,它是心的一种状态,而孟子将它标举为第一性的道德状态,所以徐复观先生指出:“人的道德意识,出现得很早。但在自己心的活动中找道德的根据,恐怕到了孟子才有此自觉。”(15)而且,以往的问题在于,人们通常从人的感官官能的欲求角度来看人心,说人有种种欲望如食色等等,一般都通常的说成是人心有这种种欲望,而孟子开始将此独立开来,即“孟子却把心的活动,从以耳目口鼻的欲望为主的活动中摆脱开,如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例,而发现心的直接而独立的活动,却含有四端之善”(16)。这里需要申述的是:孟子所展开的不是关于人性中有没有“恶”,而是指出人心中有与生俱来的“善”。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恻隐的对象其身体或生命正处于一种严重低于当时社会状况或面临重大危险或威胁的时刻。如果被同情者处于和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相当的境况,他人的同情或类似情感则不会发生,孟子所举出的例子是人的生命状态面临危险的境况。另外,还有对“动物生命”的同情等,如果单纯对于后者来说,这是所有高等生命都不同程度上存有的“心理结构状态”或“生理结构状态”,因此它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些都是人们基于对象的相对的弱势状态而发;对于人类良知情感来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对于社会的不平等等情况所产生的“恻隐”或“不忍”,人类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容忍”呢?那就是平等状态下。一般认为,“正义感”产生于“是非观念”即孟子的“是非之心”(17)。但是我们要说,如果没有恻隐、不忍之“仁”就没有是非分辨之“智”,其实前者是后者根据,这个根据当然不是学理上的而是从人的生命上来的,它们同源而异出,都是人的先天道德理性之表现。这就是徐复观先生所提出的人的心性中道德良知的独立性所在,那么它的来源和根据何在呢?
(二)“伤生若己”的元德根据
恻隐之心应于人生乃至于众生的痛苦、苦难、灾难,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它应对两种状态:一则是自然生命的危难或困境;一则是社会中的“痛苦”:基本上是对不公道、不平等、不正义的心理反应。在后者又牵涉到良知的“智德”即“是非之心”,其实孟子的“四端”、“四德”虽然“异名”却又是“同出”,即仁心,它的根脉也在于此,是故才可以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恻隐乃是四端之根。这种仁心的根基却是在一切生命的“生德”之中,这种仁德是一种宇宙的生机,牵一发而动全身,冯友兰先生谓之来自于一种“天观”,对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同情”的了解即对万物生机的认同、欣赏与“通感”:“从天之观点以观事物,则对事物有一种同情底了解。周濂溪‘绿满窗前草不除’,云:‘与自己意思一般’。程明道养鱼,时时观之曰:‘欲观万物自得意’;又有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宋儒认为此都是圣人气象。其所以是圣人气象者,因此皆是能从天之观点以观物者之气象也。”(18)这种所谓“天观”其实是从生命或生物本身出发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积极观念,所谓“与自己意思一般”也正是这个道理,即所谓“活泼泼的”也即生意盎然的意思。上面所述是一种积极的状态,反之,如果自然和社会生命受到戕害,人们也会产生感同身受的“同感”。这种“同感”、“通感”基于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生命、生意之“通”。
这种冯友兰所谓天观,在宋儒那里曰“元”、“仁”和“生意”,三者异名而同谓。明道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为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也?”(19)这种“生意”的根基不在人心外部,而是与人心联通或者说人心是其原基,任何对生意的挫伤都会使仁心也即人心发生反应,坚持格物求理的朱子甚至也曾经于此有论:
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意思。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著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逊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义礼智!(20)
仁言恻隐之端,如水之动处。盖水平静而流,则不见其动。流到滩石之地,有以触之,则其势必动,动则有可见之端。如仁之体存之于心,若爱亲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无可见。及其发而接物,有所感动,此心恻然,所以可见,如怵惕于孺子入井之类是也。(21)
元、仁为宇宙之本,“生”是它的特征表现,此之谓天命,下降为人生命,个体之“一体之仁”在心灵与躯体的整合为一则人血气流通畅旺,故“麻木”而会有“不仁”;宇宙之一体之仁为个体生命与宇宙万物的贯通为一,谓有通感,伤生若己,这是“天命之性”。人在宇宙中之灵性决定了这一点更为突出,在常人这是一种“端绪”表现,此“天地之性”人皆有之,只是因为后天“气质之性”的差异而导致或敏感、灵异或迟钝、愚拙。按照孟子只要遵循扩充的功夫,则人人可以为尧舜,明道谓之“万物一体之仁”,按阳明之说我的心根联系着世间万物,其实这也是孟子的观点,正来自于他的生命的修证和体验性认知。
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理学家的相关论述,但是又对此提出疑问。何怀宏教授在其《良心论》中曾引征朱子的论述,指出宋儒的“生生”观念并予以肯定,但是又借用清儒戴震、焦循等人的意见对朱子的严格的道德主义提出批评:“宋儒的‘生生’观念和明确的社会义务联系并不紧密。而且,由于宋明儒学中逐渐加强了自我主义的观点,不仅对如何在社会上实现普遍的‘生生’并无明确的阐述,相反,其自我定向还使他们对生命的欲望采取了一种严厉的态度。所以,清儒起而纠其流弊。”(22)这里可以看出:第一,何怀宏教授并没有在体会的层面上把握儒家关于“良知”概念的本体和完全呈现的意义,而只是停留在孟子最早提出的“四端”的“生意”端倪上,因此,对于良知内蕴的“生机”也局限于生命感性动力的层面上,而从此重要的生命、道德和天地三位一体的出发点下降滑向了流行的生态主义;第二,他也没有看到宋明儒包括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以及先秦子思、孟子之心学一系中的生命自在、活泼与道德完善相依相生的观点,这一点是与程朱理学有着迥然差异的,是他们诸人生命体证的成果。儒家心学不仅对个体生命是宽容的,而且肯定生命本体生机的旺盛与活跃,同时又指出这种发展可以在良知的完全呈现中获得最大的展开,所以,他们才有种种“仁者与万物一体”、“乐是心之本体”等等类似的论说。朱子对此有所颖悟但是的确体会不深,所以造成王阳明对朱子学的反动。阳明在儿童教育中尤其强调顺其发展“条茂畅达”等等,反对拘泥束缚、对生命的压抑,这种“真生命”的展开恰恰又是道德完善的成果,二者相辅相成,牟宗三先生将之概括为“理性的理想主义”,并归结为“觉”与“健”正是此意(23)。这个道德实践性是“於穆不已”,用阳明说就是“乐不容已”的,这正是生命的真机,也是通向万物一体的必由之路。
我们将恻隐解为“伤生若己”,实际是个体对发生于自己身外的事件的心理反应,是个体生命中之“生意”的受伤,那么外部事物又是如何感动我们的呢?因为对于一切生命来说,最一般最直接的反应是来自于外部的“切肤”之痛,即自己的身体某一部位直接受到伤害、挫痛而产生相应的生理反应,那么像上述这种“伤生若己”的“触类”式反应机理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如果是所谓“天观”,那么这种认识又是怎样得来的呢?而且这已经不是什么观念的问题,而是一种切切实实的身心状态!从前贤的叙述来看,这就是宋儒常说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体,则万物伤,我即伤;万物害,我即害;万物乐,我即乐,他们也将这种达到冯友兰所说“圣人气象”的境界称作为“大人”,这个“大人”从终极意义上已经不同于孔子时代所说的大人概念,既不是阶级概念上也不是一般的道德意义上的,而是修养至人、物同体层次上的,犹《中庸》之“至诚”、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者,这个时候的人内心之“恻隐”万物是自然的事情,而常人之良知的四端只是这样的端绪,所以因不同人会程度不一,也会因同一个人而或隐或现,大人者则是孟子所谓扩充完成者,其这样的感通最巨,阳明于《大学问》有最精辟的论述:
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24)
所谓“仁”之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一体,即是心与它们的一体,其心遍及这些人物草木瓦石,这些人、物都在其心之中,或者说天地万物都和他的心是联系着的,动这些则牵动他的心,所以就有“恻隐”和“不忍”的发生。大人、小人都是如此,小人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就其本性来说也是同样,大人者也是根于所有人都有的“先天之性”即“明德”,小人的问题只是在于没有做“明”“明德”的功夫。张载的《西铭》的思想与阳明一致,但是这一段话比较阳明更为人知,盖其集中体现了历代儒家的最高的道德精神,核心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但是就横渠“非意之也”,说明他的说法可能也是他的生命修养境界之致,或者是生命修养和道德信仰之综合之表达。而程颢对于“万物一体之仁”既有真正深切的体味又有更加深刻的阐述,而且是儒家此说之倡者:“医术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25)程明道这一比喻大概是古今最好的“一体之仁”的揭示了,麻木不仁从身体来说是气血不通,身体内部感觉中断,已不属己;而一个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如同身体内部的气血消息一样,如果认外部世界与己无关,也是“皆不属己”,这就不是“仁”了,如是,仁即是“达”:从个人身体说,气血通达;从个体与宇宙之关系说是其心达于万物,万物皆己也。一般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有一个“天人合一”的概括,佛道实际上并不尚此论甚而认为有高于此论者,其他百家只有儒家而且是儒家心学之体证庶几近之。
在万物通为一体,而人类的情感作为万物核心是最敏感的,而且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感”是最强烈的。社会的同情心、公平的愿望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道德基础,除了利益博弈的动力消极之外,积极的合作意向是人类走向整体性生存的重要基础。而在这种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共感、通感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义务即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孟子所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基于人的“四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予以了界定。万物一体只是对这种人与人之间义务关系的极端的肯定,同时给予人与人之间相互义务关系的心理根据的证明。
三、良知之“直”的“相互性”与理
关于儒家的良知学一般是从个人的德性、仁心、个体人格的道德完成的视角来审视的,其实,良知学同时也有关于人际公平、平衡和相对性的面向,这也是我们以往有所忽略的面向。康德关于人与人之间因为感性碰撞所形成的力的平衡原则,即是孔子曾经说过的“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孔子提出“以直报怨”,而不是“以怨报怨”也不是“以德报怨”。以怨抱怨是可能等利害也可能不等利害的回报,因为以怨报怨,就是仇杀,这个仇杀可能等价也很可能超过;以德报怨就是以仁爱和利他心回应冤仇;只有以直报怨,才是普通人的一种应对陌生人关系的交往方式。这个“直”就是康德“力的平衡”、就是人际的“相互性”,而这个孔子的“直”其实就是儒家良知学说的又一个层面的反映。
孔子的“直”是一种人的情感输出状态,就是当下的情感反应,所谓“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而这也就是王阳明的良知。阳明曾指出“人于寻常好恶,或亦有不真切处,惟是好好色,恶恶臭,则皆是发于真心,自求快足,会无纤假者。《大学》是就人人好恶真切易见处,指示人以好善恶恶之诚当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诚字”(26)。“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27)真诚恻怛就是孟子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只是良知的本体如果全体发用就会是完全的真诚,“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为是,非而为非,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28)。它是人在应对世事过程中的一个当下的直接的反应,此反应就是孔子的“直”。这体现的是良知的另一个侧面即通过是非之心而展现的良知在人们感性交往或利益碰撞过程中的公平性心理欲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直”,这就是人际交往的“相互性”问题,即人际交往的等利害原则,这就是正义的表现形态之一。也就是说,无论是公共理性之人际关系的义务性要求还是相互性设定其实都能在儒家的良知概念中找到它的根基,即社会正义关系的根基又本于仁,即如牟宗三所说的公心源于仁心,仁心具体面对社会事务又呈现为一种公心。所谓公心就是公共理性,它是心又是理。
牟宗三认为,仁是个体价值,义是社会价值,仁是根,义是社会之表现,建构社会公共体系源于仁而发于义:“人人心中皆有个合理不合理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正是根于‘道德的心’的。依此,‘道德的心’是普遍地存在着的,而且是随时可以点出的。这就是我们一切言论行动的起点与标准。”(29)道德心是一种对未来的企望,更主要的是一种对社会价值的评判,人类的行动须要以此作为一个衡准,人们通常所做的理性的判断都是从这里出发的,也就是人的直下的好善恶恶的心的判断:“道德的心,浅显言之,就是一种‘道德感’。经典地言之,就是一种生动活泼怵惕恻隐的仁心。”它是生动活泼的,是随时感而能发的,但是是直下的不是由物欲牵引的机巧聪明。(30)应该说,这是心性儒学的特有见识,也只有他们才能说出的道理。荀董尤其是荀子学派正视人的现实感性的诉求,即人的恶的欲望的泛滥,所以对人性的张扬采取的是压制、压抑,乃至于通过宗法制度强制克服的方法。但是,在心性儒学看来,一方面强调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要依从人的道德理性将人的道德意志完全开发出来;同时,人的社会组织的建构原则也需要依据人的道德理性自然扩展来审视:从道德理性自身的理想出发来对社会建构做出判断,这就是“义”。牟宗三着重阐发了道德仁心又如何是理性主义的。“这个仁心之所以为理性的,当从其抒发理想指导吾人之现实生活处看。仁心所抒发之每一理想皆表示一种‘应当’之命令。此应当之命令只是对已现实化了的习气(或行为)之需要克服或扭转言。”(31)这个先天的仁心一方面根于怵惕恻隐的良知,一方面力转不良习气之恶习,是扭转躯壳之念的,因此是“公的”、“正义的”,是“应当”之命令,因此也是天理、普遍性之理,是律则。虽然,在具体环境之下可能会有所不同或取舍裁决,“然无论如何,当他公心而发时,皆是客观的、普遍的。随历史发展中的特殊环境而表现理想,理想因所受之限制而成之特殊性不伤害其普遍性与客观性,此与随躯壳起念的私利的主观性不同”(32)。“又,凡公心而发的理想皆是客观的普遍的。即由此吾人亦说皆是无条件的。其为善,其为理,皆是无条件的。此无条件的必须与有条件的区别开。康德说:某一善行若只是达到某一件事的工具,便是有条件的。此时,其应当之命令所表示之理想不是公心而发,所以它不是本质上就是善的。”(33)“绝对的善,是称‘怵惕恻隐之心’而发的。由此可见的理性是理想的,由此所见的理想是理性的。由此吾人极成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理性主义。怵惕恻隐之心,同时是心,同时也就是理。此心理合一的心,就是儒家所说的‘仁’。孟子即于此言性善。王阳明于此言良知。康德于此言‘善意’。吾人如不说人性则已,如要说人性,必须从此心理合一的仁处言人的性,了解人的性。孟子就是克就这个‘性’而言善,康德亦就是克就这个性而言绝对的善意。这是随时可以指点的,也是随时可以呈现的,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34)
牟宗三在这里试图将儒家所讲的人的德性、仁心、良知扩展普遍化、客观化并称之为“理”,从此可以看出,良知之为公共理性的可能性基础。这既是儒家良知学的内在要义,同时也是使个体良知感客观化、走向社会认同的普遍的权利和义务的条件。但是,纯粹的德性、良知、仁心本身又不免带有主观性,可能时或发生,但是也可能时或消失,甚至有时候不免牵扯私欲,因此,怎样排除其中的条件性就是使之客观化、公正化的途径,形成真正的公共推理的条件,这是儒家良知学成为公共理性基础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继续探求的方向。
注释:
①[美]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再探》,时和兴译,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页。
②上引书的译者多将此翻译为“互惠”,“互惠”反映了reciprocity的积极一面,“相互性”则将其正反两面都表达出来,因此更完整确切。
③④⑤参见慈继伟:《正义的两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页及他人相关著述;第3页;第3页。
⑥⑦⑧[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3页;第26页;第34—35页。
⑨义务和权利的相关性是复杂的,不是简单对应的直线性关系,康德自己也已经注意到并予以提示;“仁爱和尊重人类权利这两者都是义务;然而前者是有条件的义务,反之后者则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的义务,那是想委身于善行的甜美的感情之中的人首先所必需充分保证绝对不可侵犯的”。[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3页。余涌教授在其著作中就道德权利的讨论也曾引证并有更多论述。参见余涌:《道德权利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及该节。
⑩这部分内容请同时参见笔者论文《正义探本》,《哲学门》第十六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11)(12)[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3页;第44页。
(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14)《孟子·公孙丑上》。
(15)(1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50页。
(17)参见慈继伟:《正义的两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18)冯友兰:《贞元六书》(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19)程颢、程颐:《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页。
(20)(21)朱熹:《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1516页;第1161页。
(22)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51—352页。
(23)参见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10年,第17—26页。
(2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下),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页。
(25)程颢、程颐:《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26)王守仁:《与黄勉之二》,《王阳明全集》(上),第195页。
(27)王守仁:《答聂文蔚》,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4页。
(28)王守仁:《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下),第969页。
(29)(30)(31)(32)(33)(34)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7页;第17页;第17页;第22页;第22页;第2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