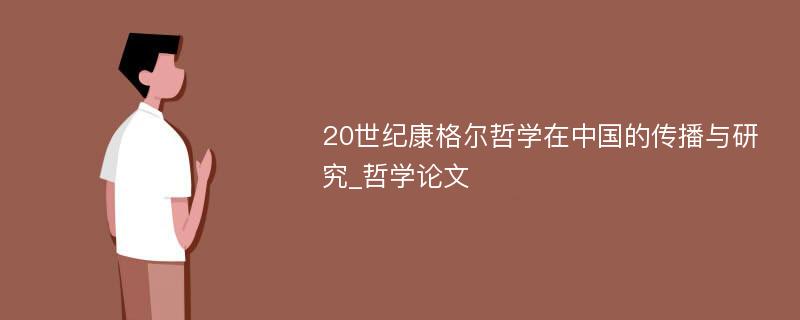
20世纪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康德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 —0460(2001)01—0049—08
一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比较有规模的传播与研究,是从戊戌变法以后开始的,但在这之前,康有为这位维新运动的著名领袖已在《诸天讲》中介绍了康德的星云假说和不可知论。据康有为说,该书写于1886年。《诸天讲》使康德、黑格尔哲学第一次进入了中国文化,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这一哲学思潮研究的开始。在以后的发展中,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启蒙介绍时期。这是康德、黑格尔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大约是戊戌变法前后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学人在认识康德、黑格尔哲学中,较早接受的是康德哲学,在康德哲学中,又是其自然哲学的思想早于其先验哲学思想被介绍。梁启超在1903年的《新民丛报》第25、26、28、46—48诸期上发表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康德生平及其思想的文章。文章已经相当完整地提到了康德的主要著作和三大批判的基本思想,对于国人完整了解康德思想,起了概览大观的重要作用。我国第一篇介绍黑格尔生平及思想的专文,是马君武留学日本时(1903年)撰写并发表在《新民丛报》第27期上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文章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在其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与康德、费希特、谢林、休谟思想的区别,以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与寻常逻辑的迥异之处,都作了大量的介绍和分析,虽然不甚准确,但基本的精神还是抓住了。此外,严复的《述黑格尔唯心论》、章太炎的《无神论》和《建立宗教论》以及蔡元培对康德哲学中科学和艺术思想的介绍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由于处在中国新文化的孕育时期,还不是新文化的生长期,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也是处于起步阶段,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认识大都是在译读西方有关研究成果中的一种“转述”。由于刚刚接触西方哲学,受中国传统观念、科学知识水平和语言翻译能力等因素的制约,“转述”中的误读现象也不少,对原著的系统研究尚未展开。
第二阶段是传播融会时期,大约是五四运动至全国解放之前,中国学者开始根据原著译解康德、黑格尔哲学,并逐步展开了对康德、黑格尔哲学体系各个部分的专门研究。这一时期我国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颐、瞿世英、张东荪、张君劢、张铭鼎、吕徵、朱光潜、周谷城、郑昕、贺麟、洪谦、周辅成、郭本道、朱谦之、胡仁源、蓝公武、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他们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上的重要推动作用在于:
第一,将康德、黑格尔哲学引入中国近代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和科研。这一时期,我国一批留学国外在康德、黑格尔哲学方面有所研究的哲学学子,如张颐、张君劢、朱光潜、郑昕、贺麟、洪谦、谢幼伟等归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陆续来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形成了在中国传播和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主体阵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颐、贺麟和郑昕。
张颐1923年回国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由于他的组织和推动,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开始进入中国高等学府,且日益被中国知识界重视。1924年和1925年,《学灯》和《晨报》副刊,以及《学艺》和《民铎》杂志,以纪念康德诞辰200周年的名义, 发表了胡嘉、张东荪、甘蛰仙、张铭鼎、吕徵、范阳等人的论文,内容几乎涉及康德哲学的所有方面,与此同时,有关的专著也纷纷问世,形成了20年代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高潮。究其原因,贺麟认为,“这情形大概是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因为康德的知识论是和科学有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的知识论。另外康德的意志自由,讲实践理性,这就必然同民主自由相关。”[1](P366)
张颐本人是黑格尔哲学专家,他的回国执教,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界当时重康德轻黑格尔的状况。他在国外留学期间写成的《黑格尔的伦理学》,是中国学者早期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成果。1931年, 当《北平晨报》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一系列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的文章时,他“阅之欣慰无似”,提笔写下《读克洛那、张君劢、瞿菊农、贺麟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论文》,其中对张君劢文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由此引发了与张君劢之间为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而展开的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张颐通过辨正张君劢的观点,客观上纠正和澄清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一些误解,由此将中国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带入了一个注重求本溯源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的发展中,贺麟的贡献尤为突出。
贺麟1931年从美国回国后也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开始了他在中国传播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事业。贺麟在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中,树立了一种“新论”而不是简单地“复述”的风气,就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观点进行有批评眼光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问题,到底是以黑格尔《哲学全书》三大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还是以《精神现象学》为全体系的导言和第一环,以《逻辑学》为全体系的中坚和第二环,以《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为第三环来看待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贺麟对后一种看法作了长期的论证,引起了中国哲学界对这一问题持续数几十年的探讨,由这一探讨进一步引发的若干问题成为后来黑格尔哲学研究深入的众多新的生长点。
郑昕是在德国这个康德、 黑格尔故乡完成研究康德哲学学业的, 1933年回国后也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历时30年。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对郑昕的教学均有难忘之深刻印象,齐良骥后来回忆道:“郑先生讲康德,满腔热诚,难能可贵,令人萦怀难忘。甚至可以说,他的态度近乎虔诚”。[2]他于1940年出版的《康德学述》, 被公认为中国学者研究康德哲学的不朽之作。郑昕研究康德哲学的功夫深刻之处,主要体现在对康德知识论的剖析、改造和提高上。
第二,开始了对康德、黑格尔哲学原著的有组织的翻译工作。贺麟于1941年组织成立并领导了“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有计划地从事西方哲学原著的译介,将20年代就开始了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工作由分散状态转为集中的有组织状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探本》,黑格尔的《逻辑大纲》和《历史哲学》等先后被译出,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专著也多有出版,为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第三,展开了康德、黑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会创新的探索。张东荪通过改造康德哲学,首创了我国现代第一个认识论体系,尽管其中有不少误解和错误,但却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走出康德”的研究态度。贺麟用中国儒家正统的“心学”观念,融会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现代精神,在40年代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新心学”,以发掘他所谓的“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中西文化共通的本体价值。牟宗三和唐君毅这两位后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早期思想的形成,也均与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有关,是试图借用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概念和方法来塑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这些创立研究学派的强烈意向,体现出这一时期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兴旺状态和浓厚的自由探讨风气。
第三阶段是建国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曲折发展时期。建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其传播和研究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对它的合理因素的吸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50年代初贺麟先后到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对大专院校师生、党刊理论工作者、部队官兵等讲授黑格尔哲学,听众之踊跃,热情之高涨,都在他的预料之外。[3]这一期间, 贺麟与冯至、郑昕、宗白华、王玖兴、汪子嵩、王太庆、方书春、陈修斋等合作,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哲学史讲演集》和《精神现象学》上卷;宗白华与韦卓民合作,翻译出版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内容涉及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大多数基本著作。随着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一批新的专业学者群体开始形成,王玖兴、张世英、姜丕之、王太庆、杨祖陶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张世英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连续推出《论黑格尔的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建国以后我国学者探索重新认识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建国之后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上的根本性变化,是指导思想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去批判地改造和利用康德、黑格尔哲学,成为研究的主流倾向。这本来是个良好的发展机遇,但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偏差,这种机遇在实践中形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康德、黑格尔哲学以一种新的形态进入了中国文化,成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康德、黑格尔哲学固有的一些人文精神底蕴被忽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单化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成为只能被改造利用的对象,其学术上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被淡化。1956年以后,随着“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形成,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一再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在“文革”中,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走入了低谷。
第四阶段是1976年至现在,这是康德、黑格尔哲学走向新的繁荣的时期。在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后,中国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重新启动并很快呈现出可喜的景象,老一代的研究者们陆续出版了自己长期思考和积累写成的专著,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走上了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上的学术探讨自由,学术研究取得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地位。80年代和90年代在大学校园兴起的国学热、人学热和西方思潮热中,北京大学黄楠森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比较研究,张世英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西方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朱德生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将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李泽厚对康德哲学主体性精神的研究、侯鸿勋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梁志学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研究、叶秀山对康德先验论的研究、王树人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基本思想的研究、薛华对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以及由贺麟、汝信开始,青年学者宋祖良和张慎等继之进行的黑格尔早期思想研究等等,不仅在国内属于一流,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国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大体沿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向进行:一是主要将它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前提,对它的研究纳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框架;二是主要将它视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对它的研究纳入到了西方哲学发展史的总体框架。在这两个方向的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总是体现为理解的一种客观背景,一种介入的话语,因而对康德、黑格尔哲学基本精神实质的任何一种挖掘,都处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交流中。众所周知的自80年代展开的主体性思想讨论就是这样,它引发于对康德哲学的重新诠释,却导致了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比较,最后又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随着这种对话的理解空间和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展,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显示出它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新的态势。
二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对异域文化的接受是一种“译读”,而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讲,任何“译读”都是一种理解,任何理解都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都要受传统赋予解释者的理解的“前结构”制约。解释者是被“嵌入”传统,按传统的方向理解文本的,但理解同时又在参与传统的进化,因为理解本身就在不断调整、补充和修正着“传统”观念,促使着传统的更新。
现代哲学解释学的看法是有合理之处的,中国人对康德、黑格尔哲学这个历史文本的研究,已经历时五代人了,第一代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马君武、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第二代以张颐、张东荪、贺麟、郑昕、张君劢、张铭鼎、郭本道、朱谦之、瞿世英、洪谦、朱光潜、杨一之、全增嘏、蓝公武、韦卓民、范寿康、吕徵、周辅成、牟宗三、沈志远、周谷诚等人为代表;第三代以王玖兴、齐良骥、张世英、姜丕之、王太庆、陈元晖、萧焜焘、杨祖陶、尹大贻、钟宇人、张澄清、李质明等为代表;第四代以汝信、李泽厚、侯鸿勋、梁志学、朱德生、叶秀山、王树人、薛华、冒从虎、朱亮、车铭洲、杨寿堪、杨文极、黄见德、李毓章等为代表;第五代的学者中,宋祖良、邓晓芒、谢遐龄、陈嘉明、韩水法、张慎、郑涌等是较突出者,每一代学者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理解都有不同的特点。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这一百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学人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认识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从国际学术范围来看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从共性的一面讲,康德、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中外学者共同面对的;从个性的一面讲,中国学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有自己的理解方式、表达方式和评价方式。这些个性的根源既是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语言特征密切相关,也是与中国近百余年来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和要求密切相联。我们是带着历史和现实所铸成的“传统”观念来认识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因而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学者的书中,总是或多或少被“中国化”了的。区别在于,上述所讲到的四个不同发展阶段中,这种解读有不同的视角。解读方式的转换,构成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传入和研究的一条基本线索。
在启蒙介绍时期,中国学人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大都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结构去“弄清楚”它们。梁启超和章太炎可谓典型。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宣称“康氏哲学大近佛学”,认为康德从内在自我意识直搜讨智慧之本源,究其性质之作用,“此论即与佛教唯识主义相印证者也”。他还以王阳明的心学比较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认为康德的伦理学视道德责任生于真我良心之自由,“实兼佛教之真如说,王阳明之良知说,而会通者也。”[4] 贺麟说:“梁启超那文章……不是客观介绍康德,而是和他所了解的佛学唯识论任意加以比较,康德在他那里,不免被佛学,王阳明良知说有所附会或曲解,可以说不是德国的康德,而是中国化了的康德。”[5](P94)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从所接受的印度佛教的立场解说康德学说,认为“康德既拔空间时间为绝无,其于神之有无,亦不欲遽定为有,存其说于纯粹理性批判矣,逮作实践理性批判,则谓自由界与天然界,范围各异。以修德之期成圣而要求来生之存在”。[6](P408)如果说在梁启超那里,已有误读康德之嫌,那么在章太炎这里,更是牵强附会了。
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方面也存在这类问题。在严复和马君武介绍黑格尔哲学的专文中,尽管依据了一些外文资料,但所用概念,多是中国传统哲学所固有,字里行间,时时让人感受到儒学的印迹。这种以中国传统思想译介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风气,说明中国学人当时的文化接受心理尚准备不充分,不明了中西两种学术思维方式的差异,离真正读懂康德、黑格尔哲学所需要的“话语转换”尚有距离。这种缺陷,在第一代学人身上是难免的。
张颐、贺麟、郑昕等一批留洋归国学人,在接受心理和话语转换上较之上一代人有一些变化。他们虽然也受过中国传统思想的教育,但却是从原著中读出来的专家,不过这种“阅读”也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的。康德、黑格尔逝世之后,在经过一个不长的过渡时期,欧美知识界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开始兴起,当时欧美一些重要大学的康德、黑格尔哲学讲坛,基本上为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所主持。这一时期到西方求学的中国学者,基本上是沿着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方向去研读康德、黑格尔哲学的。
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在理论趋向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回到康德和复兴黑格尔的口号下,通过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改造,将其中先验的或思辨的唯心主义原理加以详尽地阐发。受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影响,张颐、贺麟、郑昕等人尽管也对康德、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或主观能动性因素作了积极的评述,但一般而论,对其中的唯心主义采取了非批判的、甚至是推崇的态度。贺麟在抗战后提出理想唯心主义体系,强调引入“逻辑之心”的主体来建立一种融中国儒家思想和康德、黑格尔思想于一体的,心物不二、心理不二、体用一源、知行合一的新哲学。郑昕在《康德学述》中强调心外无理,一方面高度评价康德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上逻辑改造成为先验逻辑;另一方面又批评康德的“物自体”学说违背了先验逻辑要求,认为应该将“物自体”表示成为现象的“函数”,消除掉它作为现象背后一个不可知的绝对实在的意义。[7](P254)这个看法, 正是新康德主义对待康德哲学的一种态度,它已不单是顺着康德讲,而是“帮着”康德讲了。
新康德主义不等同于康德哲学或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也不等同于黑格尔哲学或黑格尔主义,从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来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无疑会有“成见”于其中。但是这一解读方式比较贴近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贴近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原版”,所以它在相当程度上转换了中国学人接受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心理和话语:从以前主要从中国传统哲学和佛教的角度来接受康德、黑格尔哲学,转变为通过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这个中间环节来接受康德、黑格尔哲学。这一接受心理和话语的转换,使中国哲学界开始具有了与西方近代哲学进行可理解性对话的基础,对后来中国学人的这方面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其他一些解读方式也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是重要的一种。李大钊、李达、瞿秋白、吴亮平、张心如、沈志远、艾思奇、陈唯实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对待康德、黑格尔哲学等唯心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更是鲜明地表达了对先验论和唯心辩证法的批评意见。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观点还没有被大多数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者特别是在大学任教的研究者充分了解和认识。直到全国解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逐渐取代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及其他思潮而成为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方式。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要求从根本上批判其唯心主义趋向,同时又注意吸取其辩证法等合理的因素。这种接受心理和话语的转换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学者,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但是却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初见了成效。贺麟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变化归于走出课堂,深入生活,深入实践,这是有道理的。但另外两个因素也非常重要,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本身就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二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确立,重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已成为广大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和彷徨后,开始自觉地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新的世界观,并将它运用于对过去的反思和今后的指导。从一定意义上讲,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代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者的成果,体现了他们在接受心理和话语上,从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场转换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
不过,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一开始就潜存着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主要在于: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看法缺乏全面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列宁批判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视为认识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全部基础;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的实践性意义认识不足,有用旧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唯心主义的简单化趋向,没有充分理解康德、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实质性联系与区别;第三,对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缺乏全面的认识。
这些潜在的问题,随着50年代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导人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史研究讲话精神的传入贯彻,以及在1956年以后我国社会生活中逐渐滋生的“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开始变得突出了。在宣传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片面强调政治批判,把一些本来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完全变成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消极的方面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其中首当其冲者就有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一批学者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受形势之迫不得不淡化学术而突出政治,造成了这一段时期对康德、黑格尔哲学解读方式的一种变异: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变异为从“左”的政治观点来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这一解读方式的影响涉及到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国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甚至还侵染了新的第五代学者,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事业正常发展。
然而,物极必反,“文革”把“左”倾推到极端,也把它在实践上的错误暴露无遗,这就给了人们以充分认识和纠正错误的可能性条件。在经过以思想解放运动为背景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中国学人又回到了老问题:到底应该以什么方式来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但是重新获得的相对自由的学术探讨环境为解决这些问题敞开了大门。在经过从中国传统哲学和佛教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从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以及从“左”的政治观点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之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在悄然兴起,这就是从现代或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解读康德、黑格尔哲学,它成为第五代学者的一个重要学术特点,在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谢遐龄的《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陈嘉明的《建构与范导》等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留有这种印记。
这种解读方式兴起的切入口是第三、四代学者对康德哲学主体性精神的探求。这最初是为了揭示过去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中被忽略的方面,同时也是为了对在总结我国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突现出的人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但是,在中国哲学界开始系统研究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想的时候,现代西方人已经在谈论“主体性的黄昏”。这个矛盾反映在中国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中,逐渐转化为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新的现代性批判意识。
西方人对黑格尔等哲学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从进入19世纪以后不久就开始了。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指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它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对所谓变化的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本体的追求,文艺复兴以后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思潮,强调惟有人的理性能够把握本体、与本体一致。在对这种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从不同角度超越了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实质上是要求哲学回归实践;而西方现代哲学的超越,实质上是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西方现代哲学视域中的“生活世界”是日常性的、无主体客体话语的生存经验化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理性的抽象概念可以完全把握住的,而是日常语言的对象。在这里,语言观就是世界观,每一种语言表达中都蕴含着一种世界观倾向,各种世界观的价值就在于对生活世界的信念,每一种信念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因此,对各种世界观的价值评价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存在必然的根据。这种语言—文化上的相对主义经过发展,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将近代理性主义关于主体对客体认识的确定性变为不确定性,以本体世界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多元性来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关于对世界终极本原把握的可能性信念。这种超越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特征,但是又是富于启发性的,因为它在“摧毁”、“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努力中,给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当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成为国际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视角的时候,中国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不能不受其影响,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内多元文化新格局的形成中,这种影响更是不可避免。现在中国学者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大体上承认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包括康德、黑格尔哲学在内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上是互补的,因此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话语的冲突和交流之中,过去在用中国传统哲学解释康德、黑格尔哲学时的“误读”、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解释康德、黑格尔哲学时的“偏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左”的路线占支配地位时的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康德、黑格尔哲学时的“简单化”等问题,都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得以避免。同时,在康德、黑格尔哲学被解读的过程中,它自身固有的思维方式也在起着影响作用。问题是,在这种多义的解读中如何保持理解的客观性亦即康德、黑格尔哲学时代价值的确定性,这可能是今后中国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应该加以重视的。
黑格尔逝世以后的一段时期,当西方一些哲学家将黑格尔及其哲学当作“死狗”对待时,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于历史和人类思想遗产的尊重。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康德、黑格尔哲学。
收稿日期:2000-09-01
标签:哲学论文; 康德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精神现象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实践理性批判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