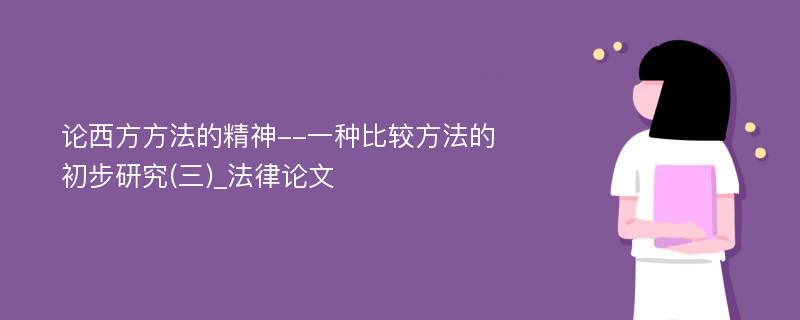
论西方法的精神 一个比较法的初步研究(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法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上所述:
1.德克萨斯州现行刑法中除了所挽救孕母生命而采取的急救程序之规定,其他漠视妊娠阶段及其相关利益的规定,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条款。
甲.对于约在妊娠期第一阶段结束前的堕胎决定及其后果,必须依据孕妇的护理医生的医疗诊断。
乙.对于第一妊娠期结束之后的阶段而言,州基于保护孕母健康的利益,可以选择与妇女健康合理相关的方式规定堕胎程序。
丙.对于分娩后胎儿可独立存活的妊娠期(注:通常是怀孕七个月后),为了保护未来生命的利益,州可以规定,甚至限定只允许为挽救孕母的生命或健康,在绝对需有合适的医学诊断的前提下堕胎。
2.州可以规定医生一词……仅指该州目前许可执业的医生,并且可以规定任何不属于规定为医生的人所做的堕胎。[70]
无庸赘说,这一判例法是多么典型地反映了在西方社会中源远流长的传统观念,即柏拉图在二千三百多年前,阐述其正义论时首先谈到的“正当”(Due)观念。 霍布斯在论证人的自然权利及其限制时依据的前提也是这一观念。孟德斯鸠的名言“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71]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至今仍然是西方人的“良好秩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的正义理念。[72]殊不见, 以上判例反复出现了如“适当的”(proper)、“合适的”(appropriate)、 “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等关键词。
判例法是法官制定法,因此,往往融立法思想与法律规则于一炉,使得人们对法律制度背后的观念性东西一目了然,成文法典或法规一般是由抽象条文所构成,非经立法思想的分析难以理解其指导性观念。但是,无论判例法,还是法典,都决不是干巴巴的规则,或条文,而是根植于一定法文化土壤之中的“有机体”。回溯古今西方法哲学史,不难看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积极性主要地在于它使人们更加精细地了解法律制度的逻辑结构,而这一学说的创始人边沁以及当代西方的新实证主义法学家,都没有排斥研究实在法背后的观念。[73]可以说,在一定文明根基上原生的社会观念是与该文明共存的。在这一文明社会中生生不息的人们以不同时代的方式,接受和培育、发展着它。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四、西方法的主要形式
制度与观念,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但是,同一观念或内容可以不同形式表现。勒内·达维德在谈及西方两大法系之间关系时,概括地说:“在很长的时期中,属罗马日尔曼法系的国家与属普通法系的国家彼此有很多共同点。两者的法都受到基督教道德的影响,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风行一时的哲学理论都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权利的概念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普通法至今还保留着非常不同于罗马日尔曼各国法的结构,但法律所起的作用增加了,两个法系所用的方法趋于接近;尤其是对于法律规定的观念,普通法系国家与罗马日尔曼法系的国家越来越趋于一致。至于在实质方面,两个法系的法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法常常是极相近的,因为这些办法都受到同样的正义观念的启示。”[74]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是:同一文明之树为什么会长出不同的法律形式——法典(code)与判例法(case law)——之果,或者说为什么两者会受到同样观念的支配?
(一)法典与判例法
法典或法典化(codification)的形式源起于古希腊和罗马法。据《雅典宪制》记载,公元前六世纪初,当时的雅典城邦发生了“梭伦改革”(Solon Reform),结果废除了前任执政官德拉古制定的绝大部分法律,制定并将新的法律刻写在可转动的白板(kyrbeis)上, 竖立在巴西勒斯(Basileus)的柱廊里。所有的雅典人均宣誓遵守法律。[75]这种法律虽不能被称为法典,但它确实是公开的成文法,是法典的雏形。无独有偶,后来在罗马史上也发生了类似事件。据《学说汇纂》记述:“根据保民官法(a tribunician statute), 君王(注:指当时统治罗马城的伊特刺斯坎人)接着被驱逐(约在公元前500年), 以前的法律统统被废除,罗马人再次开始不是依据正式的法律,而是按照不太确定的法律或习惯生活。这种状况延续了约二十年。为了结束这种状况,决定由国家权威机构任命十个人,由他们起草象希腊城邦法那样的法律,以使罗马国家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他们搜集了有关法律,写在象牙的表上,并将之竖立在演讲台上,以便使人们更清楚地感受到。国家最高权力被授予给刚才提及的官员,其职责是修改法律,并在必要时解释。一般由执政官做出的判决不能上诉。然而,他们发现了始初法律的某些不足,于是在第二年又增加了两表。所有这些法律被统称为十二表法(the statute of Twelve Tables)。”[76]可见,法典(最初的法典几乎都是被刻写在平面,或环面材料上,如古巴比伦人刻在石柱上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国先秦时所谓的“铸刑鼎”),这种西方法的最初形式具有将所制定(或编纂)的成文法予以公开(即颁布)的首要意义。由于它被刻写在书写板(tablet)上,且具有条文形式,因此“法典”与“成文法”是同义的;它被统称之为tables,或许因为它象“桌面”般,呈现在世人眼前,无任何秘密可言。法律公开,让全体人民知道,这是罗马人制定十二表法的要旨。
由法国著名罗马法学家吉拉德(Paul Frederic Girard )教授等西方学者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整理的十二表法,包括:第一表传呼、第二表审理、第三表执行、第四表家长权、第五表继承与监护、第六表所有权和占有、第七表土地和房屋(相邻关系)、第八表私犯、第九表公法、第十表宗教法、第十一表前五表的补充、第十二表后五表的补充。[77]这是一个完备的法典,尽管还没有被称为法典。真正被称为“法典”(code ,codex)的罗马法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期。 它是皇帝敕令汇编(collection of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s),如《格莱哥里亚努斯法典》(Codex Gregorianus ,A.D.294)、《赫尔摩格尼亚努斯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 ,A.D.314—324间编纂)、 《特奥多西努斯法典》(Codex Theodoinus ,A.D.438颁布)。 前两个法典属私人性质的汇编,且第二个是对第一个的补充。第三个是官方的法律汇编,并首次以皇帝名义颁布。据吉拉德的研究,codex 这个新名称“可能来源于这一事实,即, 为了替代先前在纸草纸卷轴上的书写方式, 最初的codex是用分页的纸合订而成,象合叠的刻写板(the tablets of the codies)。[78]可见,“法典”是“表”的演变形式。
与上述法典不同,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东罗马帝国尤士丁尼皇帝一度又统一东西罗马期间,尤帝主持编纂,并先后颁布实施的《尤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anus,A.D.529,五年后被《修订法典》 取代)、《尤士丁尼学说汇纂》(Digesta Justinianus,A.D.533)、 《尤士丁尼法学概论》(Institutiones Justinianus,A.D.533) 以及尤帝死后,民间编纂的《尤士丁尼新敕令》( Novellae Constitutiones Jus tinianus),主要目的是统一法制。[79]这种大规模、 有组织的法典化(codification)活动是为帝国的法制统一(unification)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典化”与“法制统一”是同义的。
与最初的法典具有公开的意义一样,肇起于十一世纪之后英国的判例法也以判例的公开(即法律报告,legal reports )为基本特征之一。最早的法律报告是
1268 年由著名的英国皇家法院法官布雷克顿(Bracton)汇编两千个判例而成的,被称为“笔记本”(NoteBook, 法官庭审的正式记录);其后是爱德华一世至亨利八世期间(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初)的所谓“年鉴”(Year Books);1513年之后出现了冠以私人姓名的法律报告,如《戴尔汇编》(Dyer's Collection)、 《普洛登报告》(Plowden Reports)、《科德报告》(Code's Reports)、《伯罗报告》(Burrow's Reports)。1865年后,由英国统一法律报告委员会出版《法律报告》(1953年改为《每周法律报告》)。[80]美国的判例法制度继承了这种形式,并沿袭至今,如联邦的判例汇编主要为《美国判例汇编》(U.S.Reports,最高法院判例汇编)、《联邦判例汇编》(Federal Reports,巡回区上诉法院判例汇编)、 《联邦补篇》(Federal Supplement,地区法院或专门初审法院的判例汇编)。没有判例的公开形式,判例法传统的延存是不可能的。
判例法始于普通法(Common Law)。普通法最初是英国皇家法院的法官通过巡回的方法处理案件而形成的。这既是英国法制统一的独特方式,又是它的结果。在现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尤其是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尽管边沁大力宣扬法典化的必要性,英国却仍然保留了判例法传统,而不象法国、德国那样为了统一法制而制定了包括民法典在内的一系列法典。本文以为,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彻底的),而在于英国的法制统一任务早已基本完成。在这意义上可以说,普通法就是统一的法(unified law)。
(二)法典与判例法的比较
作为西方法的两种主要形式,法典与判例法的产生与发展,各自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差异等原因。比如,就法制统一而言,很难设想在幅员辽阔的古罗马帝国以法官巡回审理案件的方式来实现。中世纪的英国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因而有可能通过皇家法官巡回判案来统一法制。美国联邦法制秉承了英国的巡回法院制度,并创设了多个区域性的巡回上诉法院制度,但是,建国初期,美国只有东部的十三个州,国土面积比现在小得多,因此早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时为某巡回区上诉法院的法官。另外,美国的联邦制本身为联邦法(而不是州法)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从法律的制定及其文字表现来看,法典是由立法者制定的一般性条款排列组合,判例法是由法官制定的,包括事实、法律推理以及原则或规则等具体内容。无论是法典,还是判例法,都是国家的统治者规范人们行为的手段。值得深思的是,在柏拉图时代,西方人就提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之一——统治者如何治国?人治,抑或法治?差不多同时,先秦中国的儒家和法家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意义深远的争鸣。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人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首先,人的行为以及政治社会的道德基础应是什么?柏氏的正义论和亚氏的伦理学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其次,政治社会的治理方式应是什么?柏氏和亚氏是从政体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在特定的文明条件下产生的,西方人这一政治思维角度,使得西方人与东方中国人的人治观和法治观难以相题并论,并且导致两者踏上了不同的法典化历程,前者还创造了后者未曾有过的那种判例法。
罗马人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上崇尚法治的民族。罗马法产生在共和政体的国度里。罗马共和国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罗马市民法。西塞罗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理想政体,并给国家下了如此定义:“国家是人民的事务,人民不是指以任何方式结合而成的人类团体,而是特指根据有关法律与权利的协议,并希望分享互惠的一定数量的人所组成的结合体。”[81]可见,在罗马人的国家观中,法律是多么重要。罗马法的法典形式起源于法学家的汇编传统。据《学说汇纂》记述,第一部罗马市民法汇编出自于楷称第一位罗马法学家塞斯特·帕皮里之手;罗马帝国后期出现的最初两部法典也是由法学家编纂而成;至于后来尤士丁尼的法典化结果,更是以法学家的学说汇纂为核心。罗马法实在是法学家“创造”的法。
罗马法学家的造法活动不仅表现在对现有法律的汇编,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对已有法律的解释或阐明,由此产生新的法律。罗马的法典化与后来英国的判例法传统形成过程十分相似。判例法是通过法官对已有判例的汇编或评注而形成的。判例法名符其实地是法官“创造”的法(Judge-made law)。这种法官就是法学家。 由于西方法的两种主要形式分别与教授型法学家和法官型法学家的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种活动的最主要内容分别是理论阐述和法律推理,因此都需要某种理论或推理的逻辑起点。人们常说,法典与判例法的思维差别在于演绎式与归纳式之分。但是,对判例法的具体研究,会使我们认识到:判例法的实质——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和遵循先例原则( stare docisis),恰恰反映了一种演绎的思维方式。其演绎的逻辑起点和罗马法学家的理论前提一样,归根结底,无不出自于正义的观念。
比如,牛津案的厄尔[The Earl of Oxford's Case,(1615)1.R ep.ch 1]在英国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判例梗概如下:
牛津默顿学院早已获得考文特加登(伦敦一广场名)的租约,为期72年,每年租金为9英镑。约50年后,该学院将租约转让给厄尔, 每年租金为15英镑。但是事后,学院又重占了一部分租地,理由是:伊丽莎白法禁止出售寺院和学院的土地,因此转让给厄尔的租约无效。厄尔起诉,要求剥夺学院对该土地的租用权。普通法的法官们支持学院,指出他们必须服从伊丽莎白法。厄尔提出衡平法上的请愿,要求得到救济。埃尔斯米尔勋爵予以准许,宣布学院的权利要求与所有的良知( good conscience)相抵触。 〔衡平法院〕这一判决使普通法和衡平法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并导致詹姆士一世裁定:凡遇普通法与衡平法冲突,衡平法优先。[82]
这是英国国王亲自裁定衡平法优先于普通法。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在此不必叙述。本文感兴趣的是,该判例中的衡平法理由根据是“学院的权利要求与所有的良知相抵触”。这实际上是187 5年之前,英国衡平法院奉行的最高准则,因为衡平法院的大法官被认为是“国王良心的守护人”(Keeper of the King's conscience)。[83]所谓good conscience或conscience, 实质上就是西方人通常说的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衡平法官在没有既定原则可循之时,允许根据个人对正确与错误的理解作出判决,“造就好的法官,或好的法律解释者的东西,首先是对被称为衡平法的主要自然法之正确理解:衡平法不是取决于对别人作品的阅读,而是依靠一个人自己的自然理性中的善良(goodness)和深思。这种衡平法被假定是最不受约束和最倾向于深思的东西。”[85]可见,作为判例法的一部分,衡平法是法官根据已有原则或自己内心的正义标准,进行法律推理而形成的。
判例法的生命在于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 即使在美国最高法院,遵循先例也是一个惯例,而不是例外。什么是先例(precedent s)?简单地说,先例就是判例所包含的抽象原则。这是以后处理类似问题的判决所必须遵循的,就好比法官根据法典或法规的某条款判决一样。
比如,以下一组判例都遵循同一原则,但其中微妙的变化,耐人寻味。 这些都是关于美国专利法中专利侵权等同原则( Doctrine of Equivalence,又译作等价或等量论)的判决。[86]作为一个纯粹的普通法问题,等同原则完全来自判例。1853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怀南斯诉登米德”[Winans v.Demead,56U.S(15 How),330]是这些判例中的第一个。该案涉及的是原告的专利产品——圆锥形运煤车底盘,与被告的被控产品——八角形运煤车底盘是否等同?库迪斯大法官在判例中提出:
众所周知,当某专利权人描述了某一机器,并对此提出了权利要求时,可以理解为他所要求,并且实际上为法律所保护的,不仅是他已经描述的确切形状,而且是其发明所包含的其他形状;这是一项人们熟悉的规则,即,复制原理或者甚至是所描述的操作方式,构成侵权,尽管这种复制的结果与原始的东西在形式或比例上完全不同。
为什么这一规则不能适用于本案呢?……
当形状与实质不可分时,只要看形状即可;当两者可分时,即当发明的实质可通过不同形状被复制时,法官与陪审团的职责是通过形式看实质……这正是授予专利和专利旨在保障的发明。一旦发现这种实质,便存在专利侵权。[87]
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又一次审理涉及等同原则的案件,即“格雷弗油罐制造公司诉林德航空产品公司”(Graver Tank &MFG.Co.,Inc.,et al.v.Linde Air Products Co.339 U.S.605)。该案涉及两种电子焊接合成物或焊剂,一种是获得专利的合成物,合成溶剂(溶度20),另一种是被控侵权的合成物,林肯焊剂(660)。 根据该专利的权利要求,合成溶剂是碱土金属硅酸盐和钙氟化物的结合。实际上,合成溶剂包括钙硅酸盐和镁这两种碱土金属硅酸盐。林肯焊剂的成分类似于合成溶剂的成分,除了它代之以钙硅酸盐和锰。此案的关键是:以锰(manganess)代替镁(magnesium),是否构成专利侵权?杰克逊大法官陈述了如下意见:
决定被控装置或合成物是否侵犯有效的专利权,首先必须依据权利要求的文字表述,如被指控物清楚地落入权利要求的文字表述范围内,即可确认专利侵权。诉讼到此为止。但是,法院也承认,仅此,将可能留下空子,鼓励肆无忌弹的复制者以无关紧要的和对专利表面的改变或替代(实际上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来获取规避法律禁止的复制品。挖空心思盗窃发明的人如同盗版者。盗版者可以用微不足道的变化来隐藏其盗版真面貌。原原本本地复制是愚蠢的、极少见的侵权。不制止乔装打扮的侵权,将使发明人处于文字主义的威胁中,并使实质依附形式。这将剥夺发明人的发明利益,促进隐藏而不是披露发明。披露发明正是专利制度的首要目的。
等同原则就是对这种侵权行为的反应。该原则的实质是一个人不能诈骗到专利。起源于近百年前的怀南斯诉登米德案,一直适用于本法院及下级法院,并将继续适用,只要存在适用的情况。为使这种严格的逻辑达到其应有的程度,防止盗窃发明人的利益,专利人可以根据等同原则,指控某装置的生产商,如果该装置以实质相同的方式,起实质相同的功能,达到同等结果。该原则的基点是,如两装置以等同方式做等同的工作,获得等同结果,两者就是等同的,尽管其名称、形式或形状有所不同。[88]
格雷弗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受理过任何有关等同原则的专利侵权案件。1987年,美国现在唯一受理专利侵权上诉案的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采取全体法官出庭审理的特别程序,对“佩恩澳尔特公司诉杜兰德—韦兰公司”(Pennwalt Corporation v.Durand-way - land,Inc.,833 F.2d 931)做出判决。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驳回佩恩澳尔特公司要求颁发调卷审核令的请愿,肯定了这一判决。比斯尔法官指出:
根据等同原则,如果被指控专利侵权的装置起实质相同的功能,以实质相同的方式取得与权利要求的发明相同的结果,有可能发现侵权(但不是必然)。然而,这个公司并不意味可以忽视权利要求的限制。正如本法院最近在“帕金-埃尔穆公司诉威斯丁豪思电器公司”(Perkin—Emer Corp.v.Westinghouse Elec.822 F.2d 1528 )中所说:“人们必须以权利要求为起点,并且,虽然一项‘无先驱者的’发明可以有资格获得一定的等同,但是,法院不能以适用等同原则为由,抹去权利要求中许多有意义的结构或功能性的限定,而具有这种限定的权利要求正是公众有权依赖以避免侵权的东西。……虽然等同原则旨在实施衡平法,并在衡平法所要求的时候,将发明人从死扣字眼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不允许完全修改权利要求,以致使它包括了非等同的装置,即允许权利要求扩大到包容那些远不是非实质性改变。”……[89]
以上三个判例贯穿了一个基本原则,即,根据衡平法(equity,在英美法中,这是正义、公平、公正的同义词)要求,既要保障专利权人免受“貌似不同”(colorable differences)的侵权, 又要防止将实质等同的范围扩大到完全修改权利要求的地步,以致损害了公众的权益。上述第一个判例确立了等同原则,而这一原则又是基于公平、正义的根本法律原则。作为先例,等同原则始终得到上至美国最高法院,下至巡回法院以至地区法院的遵循,成为上述第二、三个判例的逻辑起点,诚然,美国有名的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的生命不在于逻辑:它在于经验。”[90]但是,这句至理名言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判例法的精神,即,法官既要遵循先例,又不能拘泥于先例而置正义的根本要求于不顾。第三个判例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它强调了在遵循等同原则这一先例时必须根据衡平法,兼顾专利权人与公众两方面的权益。正因为如此,这个被该案少数意见斥为完全违背等同原则先例的判决,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首肯,成为目前美国关于等同原则的重要先例。
综上,由于以法典,或以判例法的法律形式分别为其主要法律渊源(这是两大法系的分野)的西方国家都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因此它们都不可能不受到正义观的支配。
五、西方法的移植
自清末民初,除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代,中国一直面临着西方法的移植(transplanting)问题,即, 如何在典型的东方文明古国建立西方式法制?从本世纪初沈家本、伍迁芳出任清朝修律大臣,制定刑律、商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乃至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继而民国的立宪及所谓六法的制定颁行,到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立法活动,中国基本上是学习西方的法典。近年来,随着国内法制的逐步完善和人们对判例法的作用日益重视,判例法的研究方兴未艾。时至今日,在“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思想指导下,立法过程中的“拿来主义”十分盛行,许多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纷纷被移植过来。本文试图论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法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法律制度;无论是西方的法典,还是判例法,归根结底都受着正义观的启示和支配。在移植西方法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忽视研究其内在的观念性东西,那么很有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移植的成功。
以公司法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4年7月1日施行)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部公司法。从形式上分析,该法与德国公司法制度相似。比如,《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共有十一章二百三十条,章目依次为:总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债券;公司财务、会计;公司合并、分立;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法律责任;附则。《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1895年5月20 日的文本,最后修改1980年7月4日,1981年1月1日施行)的六章是:公司的设立;公司与股东的法律关系;代表与管理;章程的修改;公司的解散与设立无效;最终条款。《德国股份公司法》(1965年9月6日)共有四篇:股份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联合企业;合并、财产转让、转变。其中第一篇包括:第一部分 总则;第二部分 公司的建立;第三部分 公司与股东的法律关系;第四部分 股份公司的组织法(第一章 董事会;第二章监事会;第三章 对公司影响的利用;第四章[股东]大会);第五部分 报告帐目,盈利的使用;……第八部分 公司的解散和无效声明。[9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起草时有过“先统后分,再统”的历程,即在最先草拟《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1986年1月22日)之后, 改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草案》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1987年7月24日),在最后制定时又将两者统一为《公司法》。[92]显见,中、德两国公司法典的体系基本类似。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公司组织结构采取了“四位一体”,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的模式。这与德、法、日等国的公司组织结构也是一致的。中国的公司法制度是现代西方公司制度的“移植”,这恐怕已无需论证了。
就形式或内容而言,中国主要地吸取了德、法、日等法典化国家的公司法制度。然而,尽管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公司法制度有所不同,但是其基本原则或精神是相同的。方流芳先生在“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一文中曾指出:“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是古代公司向近代公司进化的过程。”[93]作为近代,也是现代西方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如今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得到了遵循。准则主义的实质是使公司的设立完全成为民事主体(一人或数人)的一种民事行为。比如,美国《修订示范商业公司法》(Revised Modle Business Co rporation Act)第二章“公司的组建”,第2.01节“组建人”规定:“一人或多人可向州务卿递送备案所需的公司章程,以公司组建人身份行动。”[94]《德国股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至少有五位以投资换取股票的人士参加公司合同(章程)。”第二十三条(1 )规定:“章程必须是通过公证书确定。全权代表的权力需要经公证人认可。”第三十六条(1)规定:“公司应由全体创办人、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向法院申请在商业登记册中登记。”[9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法律、行政法规对设立公司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审批手续。”该条遵循的是“准则主义为主,核准主义为辅”原则。这在中国现阶段,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公司法施行以来的实践表明: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准则主义(哪怕是为辅)都没有被遵循。因为在法律上,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第六十五条)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十七条)非经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是不能登记成立的,即使是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据悉,也不是依法登记设立而无须事先得到审批。[96]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目前中国国有企业转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而所有的试点都必须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进行。试点何时能够推广?推广时能否真正地实行准则主义为主?不妨拭目以待。本文以为,我们在移植近现代西方公司法及其准则主义原则时,应注意研究和理解其内在的观念性东西。
近现代西方公司制度,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是西方社会中私有财产制度的演进形式。罗马法以公、私法分立以及私法相对发达而著称。罗马私法包括物法。《尤士丁尼法学概论》是这样区分物的种类(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things):“有些物根据自然法归属所有人,有些物归属公共所有,有些物属于社会或社团(corporation, 或译为公司),有些物不属于任何人。但是,绝大多数物依据以下所说的各种资格取得而归属于个人。”[97]物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之方式包括:先占、劳动所得、转让。保罗在《论告示》第2 卷里解释说:“‘物’(res)这个词的含义比‘财产’(Pecunia)的含义广。 物包括我们的可有物以外的那些物,而财产的含义同处于可有物状态的那些物有关。”[98]乌尔比安认为:“‘财产’(bona)这个词是自然法上的,或是市民法上的。财产,根据自然法被说成是使人幸福(即使人变得幸福)的东西,使人幸福即有用。”[99]由此看来,拥有一定的财产(按照罗马法学家的解释,财产的本意就是私人可以所有的物,即所谓“可有物”),是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必备条件。罗马人的正义观及其法律戒规——“让每个人各得其所”——与上述的财产观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就是指每个人根据自然法或市民法允许的方式,取得并拥有一定的财产,享收可有物产生的利益。
罗马法的这些精神在近代西方的自然法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将每个人生而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统统归结为“财产权”(right of property), 并将劳动视为“财产的伟大基石”。[100]为了保障这种财产权, 洛克设计了后来被孟德斯鸠完善的“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
近代西方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源起于十六世纪的“贸易共有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合股公司)。[101]这种公司制度的实质是“贸易共有人”或“合伙人”以各自投入的财产为承担风险的责任基础。如果“贸易共有人”或“合股人”没有罗马法上所说的财产以及洛克所说的财产权,这种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虽然本文在此不对西方公司制度的组织结构作历史的考察,但有一点不言而喻:股东会、董事会及经理、监事会的组织结构是三权分立的模式。这种组织结构的宗旨是保障股东的财产权,如同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旨在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兴起,上市股份公司遂成为主要的现代公司。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A.伯利在分析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的分离这一现象时,认为这说明人们已将股份这种财产所有权(股权)看作是参与公司盈利分配的权利,股票成了纯粹的分配凭证。[102]
可见,近现代西方公司制度实质上是为社会上的个人提供以自己的财产进行投资,承担相应的风险,获得相应的利益分配,这样一种“让每个人各得其所”的机会。公司的成立完全是一种民事活动,属于私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理解近现代西方公司制度包含的观念性东西,以及在公司设立上实行准则主义的原因。准则主义在现代西方各国的实行,表明这些国家对公司设立这一涉及公民财产权的民事活动,不再采取个案特许的行政手段,而是通过依照准则登记或备案的方式,以便公民能够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财产权。
问题在于,中国试图通过“移植”西方的公司制度,将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现代企业”,而对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及其所有权的行使,又难以适用类似准则主义的私法手段。如今中国施行公司法的主要目的与上述现代西方公司制度所包含的观念性东西,不可相提并论。西方的公司法制度如何通过“移植”,在中国生根开花?值得研究。推而言之,西方法在中国的“移植”,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亟待研究(已超出了本文论题)。本文的意义仅在于说明:当代中国人在研究、比较和吸取西方法的时候,应注意了解西方法的精神。
注释:
[1][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著;米健、贺卫方、 高鸿钧译:《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前言。
[2]同上,译者前言。
[3][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2页。
[4][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19页。
[5]参阅《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9月版,第88—89页。
[6]同上,第98页。
[7]同注3,导论。
[8]Baron De Montesquieu,Spirit of the Laws ( New York: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6),7.
[9][法]勒内·达维德著, 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7页。
[10]参阅,The Laws of Plato,Tanslated,with Motes and an Interpretive Essay,by Thomas .L.Pangle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及拙著:《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二章,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法哲学。
[11]Plato,The Laws,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revor J.Saunders (Penguin Books,1970),210—514。
[12]参阅,R.F.Stalley: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Laws (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1983), 以及拙文:“柏拉图《法律篇》探究”,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92年第四期。
[13]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J.Rhodes(Penguin Books,1984),45—51。关于对“梭伦改革”导致的宪制,尤其是“解负令”和阶级划分的详细分析,参阅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六章,梭伦改革与雅典的土地制度。这一部分以希腊文古典文献为基础所作的研究,可以被视为西塞罗所谓“希腊人的法律观,意指分配”这一论断的注释。
[14]Cicero,The Treaties of M.T.Cicero:On the Laws,Literally translated,chiefly by the editor,C.D.Yonge,B.A.(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876),406。
[15]同注10,100。
[16]Aristotle,The Politics.Translated by T.A.Sinclair,Revised and Re-presented by Trevor J.Saunders(Pegnuin Books,1982,),59。
[17]同注14,406。
[18]Aristotle ,Ethics,Translated by J.A.K.Thomaon (Penguin Books,1955),178。
[19]Plato ,The Republic and other Works ,Translated by B.Jowett (New York :Anchor Books,1973),13—40。
[20]The Digest of Justinian,Translated by Chacles Henry Monro ,Volume I.(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04),6-7.
[21]同注14,406。
[22]同注20,3。
[23]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Translated by J.B.Molye,Fifth edition (Oxfor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13),3.
[24]同上注,130。
[25][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丁玫译:《民法大全选择,Ⅳ.1,债契约之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59页。
[26]参阅,塔西陀《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注2:“本章开头所提到的一些史实,按年代排列如下:公元前753年,传说为罗马建城的第一年。 ……”[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448—449页:“台伯河上有一块浅滩,拉丁人和伊特剌斯坎人就在这里各处做交易。这个浅滩是罗马的发祥地。”
[27]同注23,144。
[28]Carl von Savigny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Law during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E.Cathcart,Vol.1,(Connecticut:Hyperion Press,Inc,1979),ix-x.
[29]同注23,144。
[30]同注3,第三章,伯尔曼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的背景,即5世纪至11世纪法时,对罗马法一笔带过,根本没有提及萨维尼对中世纪罗马法的研究成果。
[31]同注28。
[32]同注3,第242页。
[33]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New York:IVY Books,1991), 852.
[34]Sain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Treaties on Law ,Translated by Fathers of
theEnglishDominican Province,(Chicago: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52),205.
[35]同注33,74。
[36]同注23,130。
[37]同注25,1。
[38]同注33,872-873。
[39]同注34,208。
[40][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3页。
[41]同注14,431。
[42]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F.Kelsey,and first published in 1925 by the Carneigie Endowment ,转引自:George C.Christie ,Jurisprudence(St.Paul.Minn:West Publishing Co.,1973),154.
[43]同上注,154-155。
[44]同上注,156。
[45]同上注。
[46]引自:Joseph Modeste Sweeney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New York :The Foundation Press,Inc .,1981),2.参阅:《国际法院》,于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2页。
[47]同注42,153-154。
[48]Thomas Hobbes,Leviathan,(New York:Collier Books,1962),102.
[49]同上注,103。
[50]同注37。
[51]同注48,113。
[52]John Locke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New York:Lrvington Publishers,Inc,1979),164.
[53]Bill of Rights ,(1688)(1 Will &Mar ,Sess 2 c.2; 6 halsbury's statutes (3rd Edn.)489.
[ 54]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mendment 1 (1791).
[55]同注18,189。
[56]同注20,19。
[57]同上注,4。
[58]同上注,23。
[59]参阅:Kenneth Smith and Denis Keenan,English Law,Seventh Edition (London:pitman Books Limited,1983).
[60]Jeremy Bentham,A Comment on the Commentaries or An Introduction tothe Laws of England which is entitled Introduction to serve as a supplement to that work.载自:A Comment on the Commentaries and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edited by J.H.Burns andH.L.A.Hart (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7),边沁的《评注之评论》写作于1774— 1775年,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但他在世时没有发表该书。1928年,该书第一次面世。参阅Introduction,注4(为使中国读者了解该书出版情况。特引该注全文):"A Comment on Commentaries:A Criticism of william 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y Jeremy Bentham,Now first printed from the Authors Manuscript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ales Warrent Evreett.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
[61]边沁的《政府片论》首次发表于1776年4月18日,书的全名为:Jerem Bentham,A Fragment on Government:being an Examination of which is deliverd,on the Subject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In the introduction to Sir William Blackstone's commentaries:With a preface,in which isgiven a critique on the work at large.1823 年第 2 版(扩大版, enlarged)的书名, 除了在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之后增加了 or,A Comment on the commentaries.其他未改,近日,读龚祥瑞先生:“法与改革——读边沁与密尔:《政府论》”[载:比较法研究,第九卷第一期(1995年3月),第95页]令人费解的是:在这篇读书札记中, 竟然没有一个注解完整地标明《政府片论》的书名、出版社和版次。
[62]Jerem Bentham ,A Comment on the Commentaries and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edited by J.H.Burns and H.L.A.Hart (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7),11-13.
[63]同上注,13。
[64]同上注,483。
[65]Jerem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ation,edited by L.A.Barns and H.L.A.Hart (London:Methuan,1982),11.
[66]参阅: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67]参阅:Richard A.Posner,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68]Jerem Bentham ,Of Laws in General,cdited by H.L.A.Hart (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0),1.
[69]Webster v.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同意Roe 案关于第二个妊娠期(即分娩后胎儿可独立存活的妊娠期)的测试标准,但提醒人们注意Roe案的妊娠期标准问题:Planned Parenthood v.Casey 肯定了堕胎权,但以“不适当的负担”(undue burden)测试标准代替了妊娠期标准,方流芳博士提醒本文注意Webster案的解释,并提供了案号,在此,谨致谢忱。
[70]Roe v.Wade,410 U.S.113(1973).
[71]同注8,150。
[72]同注66。
[73]参阅拙著:《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3章,新实证主义分析法学。
[74]同注9,第27页。
[75]同注13,48。
[76]同注20,7。
[77]参阅,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附录二。
[78]Paul Frederic Girard ,A Short History of Roman law(Connecticut :Hyperion Press,Inc,1906),154.
[79]参阅,同上注。
[80]参阅,同注59。
[81]Cicero,On the Commonwealth,Translated by George Holland Sabine and Stanley Barney Smith (New York:Macmillianpublishing Company,1976),129.
[82]引自,同注59,473。
[83]参阅,Philip H.Pettit ,Equity and The Law of Trusts (London:Butteworths ,1984),4.
[84]同上注。
[85]同注48,210。
[86]参阅拙文:“美国专利侵权的等同原则”,比较法研究,第九卷,第二期(1995年6月)。
[87]Winans v.Demead ,56 U.S.330(1853)。
[88]Graver Tank &MFG.Co.V.Linde Air Products Co.,339 U.S.605(1950)。
[89]Pennwalt Corp.v.Durand-Wayland,Inc.,833 F.2d 931(Fed.Cir.1987)。
[90]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Common Law(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5.
[91]引自:卞耀武、刘鸿儒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第1039页,第1114页。
[92]参阅,同上注,卞耀武:“公司法的制定和意义”。
[93] 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第164页。
[94]引自:Selected Corporation and
Partnership Statutes,Rules,and Forms,1991 edition,edited by Lewis D,Solomon( St.Paul ,Minn:West Publishing Co.,1991),15.
[95]同注91。
[96]据本文作者参与上海日用香精厂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试点工作的经验。
[97]同注23,35。
[98][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范怀俊译:《民法大全选择.Ⅲ.物与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3-24页。
[99]同上注,第23页。
[100]同注52,29。
[101]参阅,同注93。
[102]参阅,Adolf A.Berle and Gardiner C.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revised edition,1968),及拙著:《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月第1版,第6章,公司法的经济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