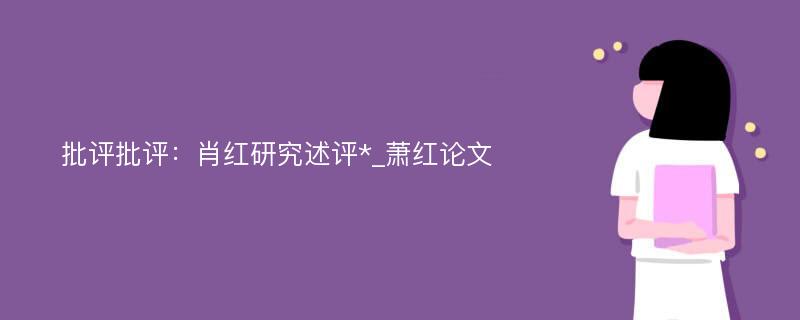
批评的批评:萧红研究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0)04—0133—07
研究一位作家就是力图全方位地接近她。在与作家无限接近的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细致地挖掘作品本身,也要深入地理解她的人生,捕捉她的心灵。作为一位作家,萧红的成名与成长离不开她生活的那个年代,但当那个年代成为历史,萧红却没有被历史遗忘。不足十年的创作历程,萧红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虽非篇篇佳构,但在20世纪80年代却重新唤起了读者的关注,她的作品内涵和文学命运也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吸引着海内外的研究者。很显然,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萧红的作品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然而必须承认,与鲁迅等大作家的沉厚和深广相比,萧红的魅力显得过于娇嫩,它不仅常常受到时代的囿限无力展示,而且需要与研究者的心灵高度契合,由此导致萧红的文学命运成为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萧红是一个极端忠实内心感受、敏感而真诚的作家。她的作品在她创作其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其后也久被冷落。时代既造就了萧红也限制了萧红。
一
萧红原名张乃莹,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随后写就《王阿嫂的死》,“一上场便获得好评”(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29.)。 早期作品与萧军的结成合集《跋涉》在哈尔滨自费出版,“轰动东北沦陷区文坛”(注:铁锋.萧红年谱[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1323.) 。当时即有文章评论,“从广漠的哈尔滨,它是一颗袭入全满的霹雷”(注: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3):218.)。 萧红最初的创作实践获得了同行和评论家的认可。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随后将多年积聚在心头对故土和乡民的印象铺展于笔下,这就是由鲁迅作序,胡风作跋的《生死场》(1935)。两位“大家”的序跋使上海文坛接受了《生死场》,也使24岁的萧红一夜成名。至今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仍是对《生死场》的权威评价,其中的字句人们耳熟能详。
在鲁迅先生那篇不足千字的序言(注:鲁迅.《生死场》序[ 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54.)中,仅有五分之一涉及到作品本身。他以相当宽容的态度赞扬作品,用词也相当谨慎。“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点明了这部作品结构上的弱点。“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肯定了它叙述与文笔上的优势。序言还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作品中“力透纸背”的是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表现。相对而言,胡风的“读后记”(注:胡风.《生死场》读后记[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的针对性则要强得多,褒扬与批评也明确得多。虽然胡风也注意到书中“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他们“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但胡风更重视书中对“愚夫愚妇们”“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的描写。胡风较鲁迅更强调小说中与抗日有关的部分,明确肯定了作品对抗日情绪和抗日行为的正面描写。同时胡风对作品的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形式的批评也相对严厉,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作者缺乏对题材的组织,使读者“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语法句法太特别了”,缺少锤炼。实际上胡风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和肯定了作品中对农民觉醒与反抗的表现,从而将《生死场》融入20世纪30年代文艺创作的主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推崇。这同时也意味着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标准衡量《生死场》,它在艺术上存在诸多缺陷,没有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表现了抗日。
虽然日后的评论家们没有忘记鲁迅先生对作品所表现“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的褒扬,但潜在的却是胡风文章的基调长期规定着对《生死场》的评价格局。因为《生死场》一度被作为萧红的代表作,所以对《生死场》的评价一度也意味着对萧红的整体评价。毫无疑问,这一评价没有突出萧红创作的独特性,整体评价也不高。
萧红的创作非常重视内心感受。但她却生活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作家虽然有自己的创作旨趣,但时代对作家却有特殊要求。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母题是“关于中国社会前途、革命道路、时代特征、阶级关系的探索,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农民等不同阶层的人们对‘道路’的选择”(注:程金城.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1900 —1949)[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84.),并且“把作品是否指明或暗示出正确的人生方向作为创作的最终目的,甚至作为衡量作品价值大小、好坏的主要依据”(注:程金城.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1900—1949)[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84.)。而紧接着爆发的抗战又导致文学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一切服从“抗日救亡”的时代呼声和普遍社会心理,使文艺顺理成章地成为宣传与鼓动的工具。虽然萧红起步之初就隶属于左翼进步团体,但这并不是源于她明确的政治主张,更多地是她与萧军、鲁迅等人的私人关系所致。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她认为,作家被迫去描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只会有害于文艺。只要善于观察和发现,抗战的题材处处皆是,“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注: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记录[J].七月,1938(7).)很显然这里我们既看得出萧红不愿因为趋同形势而放弃对自己熟悉的故土和乡民的关注,也能发现同在抗战的背景下,她选择题材的独特角度。
20世纪30年代萧红还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散文小说合集《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虽然这几部书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69.),但在批评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这显然与她的创作题材有关。
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而很少能算文学创作”(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137~138.)。 但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注:茅盾.《呼兰河传》序[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704~706.)。兼有文学家气质和文艺理论家敏锐的茅盾,准确地把握到了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艺术上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茅盾从“五四”即倡导写实的文学,至40年代已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批评家。他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而“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则无疑是造成萧红寂寞心境的原因。这时的萧红仅仅是一个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深深浸淫在“寂寞”情绪中的女作家。“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虽然茅盾的文章对《呼兰河传》不无称赞,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与思想上的严厉否定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他的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彻底否定。这也直接导致了其后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同期另有一些友人撰文怀念她,也兼及她的创作评价,如骆宾基、柳无垢、靳以等人的文章。其中石怀池写于1945年的《论萧红》(注:石怀池.论萧红[A].石怀池文学论文集[C].上海:耕耘出版社.1945.92~105.)最有代表性。 石文以一种政治评判的语调评述了萧红的一生和她的主要作品,断言萧红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斗争”的失败者。“她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融化成一个整体”,“一再陷于感情的泥沼里”。石文对萧红成名作《生死场》的评价完全承继了胡风的看法,并将其推向极端,认为它“充分地表现着一种相信人民的乐观主义气息”。但认为其后的创作是萧红无力摆脱个人情感和病痛的束缚,“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泥沼里”,“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的证明。
无疑,这里石怀池完全以当时“流行”的政治评判代替了艺术分析——这也是建国后长期统治文艺评论界的一种语调。他对《生死场》的拔高进一步加深了对《生死场》主题的误解,对《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后期作品的贬低,也同样成为一种时代的误解。也许当时很多作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为指导进行创作,但这显然不是萧红创作的指导思想。1938年夏在大后方的一次抗战文艺界座谈会上萧红明确表述过“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创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由于创作思想与时代思潮的脱节,使得萧红在解放后长期被批评界冷落,但同样也是因为这一点导致她在新时期迅速崛起,引人注目。
茅盾和石怀池的文章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注: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J].文学评论,1989(3~4).),“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题旨被简单而武断地认为是创作走下坡路,是在现实生活里无法汲取创作源泉。由于萧红于1942年、年仅31岁过早的逝世,很自然40年代的论断基本上延续下来成为这之后直至新时期评论界对萧红人生及其作品的评价思路。人们重复使用着“狭窄”、“脱离大众”、“走下坡路”等词语,评价萧红在《生死场》之后的创作,致使她后期更多的作品被误解、被忽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人们采取一种相对极端的论调情有可原。这一时期造成的许多误解也极具时代的特色。但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后以至新时期,萧红研究进展不大,对萧红的评价也没有大的改观。
作为一个作家,无论从创作题材还是创作倾向上,萧红无疑都应被文学史归入“进步作家”的行列,但作为左翼作家的萧红在解放后相当长时间里,即使在惟题材论统治文坛的情况下,也没有受到重视,只在“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群”的章节下会稍稍提及她的《生死场》。这里的重要影响因素显然是萧红对其生活道路的选择。随着日军入侵的深入,萧红与许多进步作家一起为躲避战乱辗转内地,曾与丁玲、聂绀弩等同行至临汾。当其他人准备北上延安时萧红却决定南下,同时决定与萧军彻底分手。延安是革命胜地,萧军是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萧红与两者“分手”引起了朋友的不解,也给她的进步色彩大打折扣。同时,萧红后期的写作题材虽然始终是下层民众,但因为与抗战的联系不紧密及处理题材的独特视角,使她与其他左翼作家拉开距离,对她的作品内容仅仅用“阶级”、“剥削”、“工农”、“觉醒”,等等字眼难于展开有效地讨论。这样,评论界对萧红的创作基本上形成一种共识,即《生死场》曾经有力的表现了人民的觉醒和抗日行为,大大激发了后方民众的抗日热情。《呼兰河传》则仅仅是个人寂寞情怀的写照,而对长篇《马伯乐》基本不置一词。而其中最能体现萧红进步性的无疑是《生死场》,她个人也就被简单地概括为“抗日作家”。
文学史对萧红的轻描淡写与萧红自身的价值并不相称。那些因政治原因走红的作品,当我们远离了迫切需要宣传鼓动的年代,也就很容易发现它们艺术上的粗糙。相反那些内容与政治形势结合并不紧密、在当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却做到了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作品,渐渐体现出隽永的魅力。基于这种认识,导致了新时期十年文学批评的高潮迭起。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文学研究的重点是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发掘那些因政治原因被掩蔽的文学大家身上的另一种光彩和被忽视的中、小作家。到80年代后期延续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研究者具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可以选取各自的契入点,以审美感受为基础,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成果分析作品和作家。
新时期的萧红研究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萧红研究有过一个小小的热潮,这一热潮是由东北的评论者掀起的(注:肖凤.萧红研究[A].现代文学讲演集[C].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15~231.)。它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研究文章问世,除生平考证、作品考证和怀念回忆等资料性文章,也包括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这些针对萧红作品的文章带有鲜明的“拨乱反正”的时代特色。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和“萧红生平”有关的研究。在作家研究中,生平研究也许没有作品研究重要,但对生平的了解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萧红来说,这个时期人们对她生平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她作品的兴趣。这一方面与萧红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起因于与萧红有瓜葛的许多当事人当时仍然健在。但有趣的是,生平资料的研究不仅没有带来问题的澄清,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论。他们“对于具体史料的看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注:肖凤.萧红研究[A].现代文学讲演集[C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15~231.),比如萧红的出身、生日和许多家庭背景资料。而且由于一些当事人的介入使得许多简单的问题更变得扑朔迷离。这些争论的问题和争论的声音在葛浩文(Goldblatt )的《萧红评传》里有清晰的反映。“萧红这段苦难日子(指1931年前后在哈尔滨——引者注)的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原先的小谜至今成为大谜。”(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34.)类似的“谜”在萧红的生活中还有很多。恐怕没有哪位作家的生平像仅有31岁生命的萧红这样充满疑点,纠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萧红不幸的人生实际上始终与一些卑劣的人和事有关。我们不否认这里萧红自己也要负一定责任,但当萧红去世四十多年以后,当事人却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致使一些简单的史实无法确证,却不得不让人在遗憾之余为萧红、也为文学觉得悲哀。第二,萧红很少直接言及自己的经历和感情纠葛,除散文集《商市街》外,她更是很少将这些作为创作的题材。这种“不言”的状态不仅加深了她生平的“谜”,也反映出萧红创作时选材的特殊性,她有意无意地避免把小说当作“一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工具”(注:西蒙·波伏瓦.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因为过多地纠缠于萧红身世,她与萧军、端木的感情纠葛及萧红革命道路的选择和进步性等问题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进展并不大。很显然,至此问题的关键已不是事实的真相,研究者注重的应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我们已提到美国学者葛浩文博士的著作《萧红评传》,无论就其内容的启发性还是著作的影响力而言,它都是有史以来萧红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这本书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港台出版,80年代中期在大陆印行。该著作不仅资料翔实地考证了萧红的一生,而且结合创作背景评价了萧红各时期的创作。此外,作者更着力于考察萧红作品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从而力图为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寻找合适的位置。这一努力无疑是卓有成效的。作者不仅肯定了萧红具有多方面的创作天才,肯定了她对生活敏锐的观察能力,优美简洁的文笔,对世事超乎常人的感应能力,而且澄清了关于萧红的许多误会,包括所谓“抗日作家”,包括他对《商市街》、《马伯乐》等无人问津的作品的肯定。作者在书的最后指出:“自1949年后至近几年来所写的文学史中,萧红竟被列入二流作家。她的私生活成了人们讨论的题材。”“萧红不但不能和当时中国文坛巨子……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如那些不及她才气及知名度的一批‘政治’作家。”然而作者有信心, “当许多在民国时代(1920 —1940)的作品,因受时间限制而遭读者唾弃时,而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184~185.)
1991年,哈尔滨出版社为纪念萧红诞辰80周年,出版了《萧红全集》。资料的完备无疑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同年,另一本研究专著《萧红现象》出版(注:皇甫晓涛.萧红现象[M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皇浦晓涛认为萧红的文学命运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令人困惑的诸多问题,通过对这一“萧红现象”的透视,可以把握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困惑点,诸如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反帝与反封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从而将对萧红文学命运的思考提升到了文化学的高度。如果我们认为让萧红来承担这一系列的文化困惑她还略嫌单薄的话,那么在这种对比中我们还是很清楚地能看到萧红作为一个在30年代崛起的作家,她创作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80年代初期的“萧红热”显得过于虚浮,缺少高质量的论文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支撑,“‘量’的发现并不能为这名字增添什么”(注:肖凤.萧红研究[A].现代文学讲演集[C].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15~231.)(注:赵园.论小说十家[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13~252.),“热度”消散之后,萧红研究明显降温,但陆续发表的一些著作及论文则表明萧红研究正步入健康的发展渠道。
二
新时期的萧红研究热潮虽然导致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萧红的声誉,但却很难说取得了与之相称的研究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著作和少数有分量的文章外,多数论文仍然徘徊难进,尤其没有在改变文学史对萧红的既定评价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新时期的文学研究可以说已拥有相当宽容的政治环境,摆脱了外界的羁绊并拥有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后,是什么在束缚研究的继续深入?我们认为,研究者或一时难以转变沿袭的旧思路,选取了不适宜的研究尺度,成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1.东北作家群
无疑,萧红隶属于东北作家群,且有相当一部分评论文章是将她置于这一背景下进行探讨的。东北作家群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流亡关内,以怀念故土、揭露日军侵略暴行、讴歌东北人民反击侵略的英勇斗争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们。萧军和萧红各自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为“东北作家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背景下讨论作家的作品,无疑会着重强调创作题材与抗日的联系。萧红的一夜成名与《生死场》中抗日的描写密切相关,《生死场》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然而当后来萧红能够更加从容地提笔写作,作品的内容并不与抗日紧密关联时,如果仍然坚持在“东北作家群”的背景下审视她的作品,就难免认为它们仅仅是一己情怀的悲吟,脱离了“大时代”、疏远了反抗侵略的民众,成为萧红创作“滑坡”的证据。但需要明确的是,东北作家群作为一个流派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流派和风格特色,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出生地、经历和写作题材的相似而被批评家概括为流派的。显然“东北作家群”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对探讨萧红的全部作品和整体风格显得过于狭窄,它不仅限制了对《生死场》主题意蕴的开掘,而且抹煞了萧红后期艺术更完美的作品。
2.抗战文艺
与东北作家群相似,抗战文艺是指那些以宣传抗战、反映抗战、歌颂抗战为主旨的作品。萧红写作的年代正值抗战的时代,《生死场》也是公认的最早涌现出的这一类作品的代表,正如鲁迅和胡风的序跋所评论的那样,它引导大后方的人民看到了日寇在中国东北那片沃土上的侵略暴行,这不仅大大激发了人民的抗日情绪,也给萎靡的上海文坛带去了新鲜的活力。当侵略仍在继续,当民族抗战正全面展开,曾为抗战文学开风气之先的萧红却放弃了眼前的“伟大”题材,去回忆童年,这无疑会被认为是“走下坡路”。虽然萧红也创作了《黄河》、《汾河的圆月》、《北中国》和《旷野的呼唤》等以抗日为背景的小说,但均非对抗战的正面描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种题材下萧红没有选择简单的歌颂或暴露,她更关注战乱对个体造成的精神伤害。长篇《马伯乐》则揭露了抗战中四处逃窜的知识分子的灰色行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都市里的“文明人”是否真正脱离了愚昧,改造民族灵魂的道路仍然十分艰巨。显然这与抗战文艺所提倡的昂扬格调背道而驰。这一框架下,萧红创作的价值仍然难以显现。
3.抒情小说
“抒情小说”是一个未被严格界定,但又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在小说与诗歌之间有着广阔的地带,抒情小说无疑是这一地带上一个醒目的现象。简言之,它是指那些削弱小说的叙事功能,转而加强其抒情功能,以抒发感情为主调的小说式样。因为抒情色彩在萧红的作品中非常明显,所以涉及萧红小说的“抒情性”、“情绪化”、“散文化”等方面的文章有很多。集中在“抒情小说”这一名目下的中国现代作家开列出来是长长的一串: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端木蕻良、师陀、艾芜、孙犁等,无论用哪种尺度衡量,这一长串名字的涵盖面都不算小。诸多人生理想和人格实践、创作倾向和风格特色迥异的作家被集中在“抒情小说”之下,他们之间的联系到底有多少?正如一位论者所言“抒情性,是一种太过空泛的概括,因包容过大反而弄得缺乏意义”(注:赵园.论小说十家[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13~252.)。“萧红小说并不以‘抒情性’为特征。萧红作品的情绪特征在于浸透文字的‘感情意味’”(注:赵园.论小说十家[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13~252.)。的确,当论者缺乏赵园出众的艺术感受力和良好的理论功底时,讨论萧红小说的抒情性往往演变成摘取段落,泛泛而谈。在这里有一点值得一提,我认为在萧红研究中,研究者自身能否与萧红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共鸣,决定着研究的成功与否。新时期萧红研究蜂涌而上,但研究者不注重自身与萧红内心的契合程度,从而导致许多论文言之无物,这实是“萧红热”缺乏成果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也如前文所说,萧红的魅力非常娇嫩,它的展示往往受制于许多外部条件,她不是大江大河那样的壮美,让人一触目即为之震撼,为之感染,她更像荒野中的一朵野百合,娇嫩、动人,等待被发现。
4.女性文学
当女性从这个男性统治的世界中慢慢拥有了一双自己看待世界的眼睛时,就产生了女性意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使女性获得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机会,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和女性意识的女人进行的文学创作便是女性文学。审视和分析女性文学成为女性批评,在中国它起步于新时期,使用的术语及理论框架基本借鉴于西方。
以小说描绘了一个时代妇女生活的女性作家萧红,自然成为女性批评探讨的对象。而这个看来与萧红如此贴切的概念是否能够妥善地安置她呢?我们很容易发现,甚至在一些专门讨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论文(注:钱虹.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考察[J].上海文论,1989(2);游友基.女性文学的嬗变与发展[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4(4).)中,也往往对萧红提而不论。显然这与萧红的价值并不相称。与其他女作家相比,萧红可以说卓尔不群。跟庐隐、冯沅君、谢冰莹以及后来的苏雪林、苏青等的创作相比,萧红没有将自己的经历作为创作的重点,“她没有在作品中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经历,更没有随意放纵和宣泄自我。”(注: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M].北京: 三联书店,1996.)正如前面论述过的, 因为她的过分“不言”甚至造成了她一些生活事实的混乱。虽然萧红的小说中有大量女性人物,但她们决没有梦珂、莎菲那样鲜明的性格特征,有时甚至没有名字,只是很简单地被叫做“王婆”、“李妈”,她们的作用更多是作为背景或一种女性角色,叫什么并不重要。虽然与丁玲同为左翼作家,但萧红却坚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注:王富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J].鲁迅研究月刊,1999(10).)的身份,与始终走在时代尖端的丁玲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文学命运上都形成鲜明对照。而与冰心、凌叔华、张爱玲等出身和受教育程度都较好的作家相比,仅仅中学毕业的萧红以其创作面的广泛、作品深厚的悲剧意蕴和她对笔下人物倾注的深切关怀,表现出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注: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A].萧红全集[Z].哈尔滨出版社,1991.)。即使在萧红那些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中,我们也很难说萧红关注的仅仅是女性的处境,萧红认为“人生并没有分别着男人或女人的”(注:(美)葛浩文.萧红评传 [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179.),显然她关注的重心是人的处境、弱者的处境。萧红的作品不仅没有与她的人生经历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关联,而且更不仅仅关注女性的处境,这就使得本身过于简单化、类型化的女性批评显得有点儿无能为力,对她的提而不论也就不奇怪了。
以上我们选取的四个批评角度不尽相同,有题材方面的,也有形式方面的,但无论哪一种与萧红都不尽熨帖,其实反过来也正说明评论者还没有找到适合萧红的批评尺度。正如有论者言:“萧红的作品也确实具有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风格,使你觉得难于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混到一块儿。”其实不仅仅是风格独特,这种独特性还表现在选材、切入题材的角度,主题的提炼,叙述、语言等诸多方面。正是这种难于“归类”的状况成为文学史对萧红评价的障碍,相反那些容易归类的葛浩文所谓的“政治作家”却获得了与他们创作实绩不符的荣誉,这也是其他许多极具个性化的创作在中国文坛的共同命运。多年来文学史对萧红评价过低,可以说这是一个深层的原因。而学界普遍认为萧红“学养不足”,缺乏思想的才能,是造成对萧红评价较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但通过阅读萧红的信件和后期一些杂文和散文可以发现,萧红的阅读面其实很广,对当时一些世界著名作家也有独到的看法。加之表现在作品中的对世事不同寻常的洞察,更说明她的创作靠的不仅仅是天分,萧红是真正的“大智勇者”(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74~193.)。此外,萧红虽然在后期已展露出多方面的创作才华,但过早的去世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她的创作成就。就萧红创作本身而言,她在作品中没有塑造出批评界推崇的典型人物,也减弱了其作品的影响力。而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对她私生活的过度兴趣,更妨害了对作者本人的深入探究。
萧军有诗纪念萧红:“乡心何处鹃啼血,十里山花寂寞红”。而萧红最喜用的两个笔名也是悄吟和萧红。萧者清静冷落之意,悄悄吟哦与清静冷落似乎早已暗示着她的文学命运。当世纪末人们回过头来检视这个世纪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时,萧红的《呼兰河传》成为这“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注: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揭晓[Z].当代,1999(5):202~204.),历史对待一个作家无疑是公正的。萧红,一个在大家庭中被排斥、被冷落的女孩,一个在专制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一个拥有一颗对他人痛苦极度敏感的心灵、始终热切关注故土乡民生命价值的作家,这一切构成了萧红创作的全部背景,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萧红从取材到风格特色的全部创作过程。
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讨论对萧红及其作品的看法。
标签:萧红论文; 生死场论文; 胡风论文; 文学论文; 哈尔滨生活论文; 读书论文; 马伯乐论文; 葛浩文论文; 文艺论文; 作家论文; 商市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