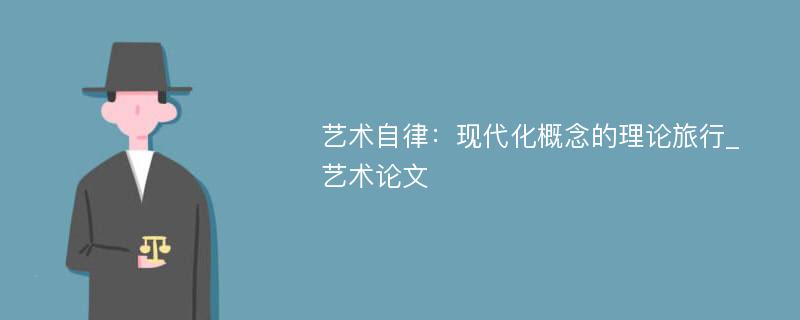
艺术自律:一个现代性概念的理论旅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概念论文,理论论文,旅行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中,艺术自律被市民社会提出并以之作为寻求文化领导权的依据,同时艺术自律又体现了现代性工程在“分解式理性”作用下各个社会实践场域建构自主性存在的诉求。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的历史理解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协商、谈判的历史,理解为各社会实践场域的合法化危机、解体、重建的历史,那么,艺术自律由诞生到分解、转型、衰落的历史,可以说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学科史”。
一、哥尼斯堡:从先验哲学到诗学天才
17世纪之前,艺术的自律性并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至高无上的神或普遍规则的逻各斯赋予了艺术和世间万物同一性秩序。只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一元论超验本体的崩溃让个体意义上的“我在”问题成为“我思”的主要内涵;全部存在都面临着由“自我”出发重新寻找合法化身份的任务。古典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曾经对知识形态作过分门别类的论述,其中诗被认为是最典范的艺术,这一艺术形式的类属性在于摹仿。诗的摹仿指向普遍的真理,因此诗表现了比有限的实在更为合乎理性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并未将艺术逐出真理殿堂,他无法想象在普遍真理之外还有需要艺术单独言说的意义。古典时代的普遍真理——神的意志、逻各斯、道、气、理等等——作为全部言说的终极意义,将艺术置于工具性或符号性存在的地位,因而没有必要去思考艺术的自律性一类的问题。在中世纪的欧洲,逻辑学、修辞学、语法学、算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这七门知识都被当成“艺术”,甚至是“自由的艺术”①。
在康德之前,曾经有两个人触及过艺术自律性的依据问题,这就是弗朗西斯·培根和查理斯·巴托。培根把人类认知区分为记忆、想象和理智,“历史涉及记忆,诗涉及想象,哲学涉及理智”②,这就从主体层面上使得诗作为艺术性活动获得了一种独立于其他认知活动的自律性。巴托则是由艺术分类学入手探讨艺术的自律性,他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关于“自由的艺术”和“机械的艺术”相互差异的观念,提出“美的艺术”的概念③。巴托将音乐、诗、绘画、雕塑、舞蹈定位为美的艺术,认为这些艺术的存在依据在于它们仅仅提供愉悦而不涉及功利。早期的西方思想家眼中,美与艺术并无牵连,比如柏拉图就肯定美而否定诗;近代思想逐渐发现了二者的关联,巴托的“美的艺术”使艺术与美有可能步入婚姻殿堂,结成门当户对的家庭。
18世纪晚期,在哥尼斯堡深居简出、思考着人类理性的康德,看出了培根的主体活动与巴托的审美愉悦之间的关联。他给艺术活动注入先验性和审美游戏的专属性内涵,从而完成了艺术作为自律性存在的合法性论证。可以这样说,艺术自立门户的第一份注册证书是1790年在哥尼斯堡由哲学家康德签发的——那一年《判断力批判》出版。
康德的批判哲学希望借助于对人的先验理性的反思和分析将真理交予个体的天性,从而解除一切独断论对知识的专制性占有权。康德运用“批判”(反思与分析)的方法来实现这一启蒙工程,即认知主体由一切自明性知识出发,反思自身理性的展开机制,分析理性活动的诸种形态和规定性。正是在理性主体的自我反思的意义上,康德为艺术的自律性存在设定了一种先验性的合法化依据。康德时代大多数学者视审美为感性认识至理性认识的中间状态,直到黑格尔仍作如是观。而康德则认为,审美判断作为先验性而独立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这一看法不仅使得康德美学超越了认识论范畴,而且提升了审美在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地位。
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支撑着艺术的自律性存在的判断力是一种与合概念性的纯粹理性、合目的性的实践理性三足鼎立的主体性先天禀赋。康德写道:“心灵的一切机能或能力可以归结为下列三种,它们不能从一个共同的基础再作进一步的引申了,这三种就是:认识机能,愉快及不愉快的情感和欲求的机能。”这里涉及“愉快及不愉快的情感”活动的主体机能便是“同样地在自身包含着一个先验原理”的判断力④。因为判断力独立于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外,所以判断力活动即审美具有自律性,它不依存于概念,也不依存于目的。通过将审美判断活动先验化并将其与人的其他先验禀赋区别开来,康德给审美判断的身份独立制定了法理原则。
继而康德展开了有关审美判断这种先验属性的各种规定性的分析,他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游戏、审美无功利性、天才论等概念界定审美活动的属性。这一系列的规定性使得艺术的生存首次获得了一块独立自主的基石,从此以后艺术就要向着自律的方向进发,甚而至于进化成为审美主义的普遍伦理,审美现代性也由此孕育出来并日趋发育成熟。审美现代性演化出纯艺术的形式美学、唯美主义的逃亡诗学、先锋派的叛逆诗学,以至于新左派的审美造反等等,把康德美学展开成为一部多声部的奏鸣曲。
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康德,在反思理性的维度上置审美于个体的先验性之中,这充分显现了主体论哲学所追求的人类解放功能。正是因为审美是人类天性的内涵之一,所以审美判断活动可以通过人类本质力量的实现而带来主体的自由。在康德之前,美或者被视为神灵光辉的普照,或者被视为物体的某种结构特征(对称、平衡等),或者被视为人的行为姿态,都不具备存在的必然性意义上的属性;只是在康德这里,审美才上升成为一种源于人类先验性并体现主体自由的本质力量。尽管“审美无功利”、“美的艺术”等并非康德首创,但是这些为艺术的自律性存在提供合法化依据的重要术语,是在康德那里超越现象描述而被提升至有关人的类本质属性的概念,所以说是康德在“天赋人权”的意义上给予了艺术自律以本体论的地位。当康德把判断力活动论证为一种人类先验属性时,艺术自然就只能是“天才”的表演了。浪漫主义的诗学天才们竭力倡导天才诗学,表达了与康德美学相通的观念,即诗是人类主体自由的体现,而诗人则是人类审美天性的集合,诗歌远离尘嚣,因为诗人天马行空。
由于康德把审美视作人类的一种本质力量,所以他以审美为艺术之自律性存在依据的论述也与前人不同。据塔达基维奇的叙述,历史上关于艺术特性的说法曾经有过“技巧的艺术”、“音乐的艺术”、“高雅的艺术”、“纪念性艺术”、“绘画的艺术”、“诗意的艺术”、“优雅的和愉悦的艺术”等等,16世纪开始出现“美的艺术”一说⑤。希腊哲人倾向于把艺术定义为一种“技艺”,文艺复兴时代的阿尔伯蒂在《论绘画》(1435)中认为画家应当集中表现美。到查里斯·巴托关于“美的艺术”的提出,艺术与审美的必然性关系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由于美尚未进入人类先验禀赋,所以康德之前有关“美的艺术”的说法都无法在本体论意义上解决艺术的自律性问题。康德写道:“正当地说来,人们只能把通过自由而产生的成品,这就是通过一意图,把他的诸行为筑基于理性之上,唤做艺术。”⑥这就是说,自由意志和自觉意识——而并非技艺、行为或感觉经验——才是艺术的本源,审美判断乃是自由和理性天然的内涵,因此艺术依据美而生成即艺术依据人类天性而出场,艺术的独立存在在康德这里所获得的美学依据具有了人类存在之本质属性提供的必然性。在后来的审美现代性的实践活动中,所有的审美救世主义、叛逆美学、抵抗诗学或造反诗学及先锋派、实验派艺术,无一不是以审美为人类自由的本真内涵而否定、反抗或超越非审美的世俗生活世界。
康德把判断力与合概念性、合目的性区分开来,以此提出了审美判断活动的无功利性、形式游戏等规定性。但康德又认为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有着密切的关联,他甚至声称美是道德的象征。“建立鉴赏的真正的入门的是道义的诸观念的演进和道德情感的培养;只有在感性和道德情感达到一致的场合,真正的鉴赏才能采取一个确定的不变的形式。”⑦康德哲学的最后目标是要解决人的自由问题,而他心目中的自由即是一种伦理意义上人类先验性的实现,因此审美鉴赏最终应当成为这种伦理情感的表现。从康德指出美与道德的密切关联开始,审美就一步一步地走近伦理,以至于后来的唯美主义、审美救世主义以及各种生存美学,都把艺术世界中的伦理原则当成至高无上的普遍伦理原则,甚至艺术化的生存方式与自由人格之间也被划上了等号。《判断力批判》出版没多久,席勒就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审美游戏可以拯救现代社会中人格分裂的病症。
二、巴黎:从天才诗学到审美伦理
1830年以后,德国哲人们用晦涩的哲学术语表达的艺术自律观念,逐渐在巴黎被诗人们改写成一出生活剧脚本,唯美主义者按此脚本编排并上演了“波西米亚式生存”喜剧。
19世纪中期,启蒙现代性影响下的现代社会初具形态。世俗化、物质主义、技术主义、都市化、职业化等等在率先实施现代性工程的国度逐步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唯美主义者登上文化舞台之前,浪漫主义就已经开始用诗学激情来对抗现代文明。从卢梭、华兹华斯等人对原始公社和自然风情的向往中可以见出,那时的欧洲正走向一种排斥诗学激情的都市文明或技术文明。浪漫主义者崇尚诗学天才,崇尚神秘意象和审美情感,他们的文本塑造了一个个依照艺术原则独往独来的旷世奇才。作为审美现代性之源头的艺术自律观念,在文学实践中的开端就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又开启了唯美主义者身体力行的审美伦理实践。而且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康德美学的文学案例,因为在浪漫主义的文化情调中已经隐约地蕴含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想法。
“为艺术而艺术”是唯美主义的口号,关于这个口号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威廉·冈特在《美的历险》一书中认为是戈蒂叶把“艺术家唯我独尊的地位和艺术家与中产阶级世界的分离”总结为“l’art pour l’art”⑧。卫姆萨特和布鲁克斯则认为是“科佩集团”的贡斯当在1804年的一则笔记中谈到席勒来访时提出“为艺术而艺术”⑨。中国学者赵灃、徐京安编的《唯美主义》一书认为是法国哲学家库辛(也译作“库赞”)在1818年提出的。1953年,约翰·威尔考克斯(John Wilcox)发表《“为艺术而艺术”的缘起》一文,认为这个口号最早的提出者是伊波利特·福图尔(Hyppolyte Fortoul)。1833年,这位批评家在《百科全书杂志》上发表《论当前的艺术》批评浪漫主义,指责“为艺术而艺术”这个令人迷惑的口号⑩。从这不同的说法中我们可以见出,在19世纪上半期,“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艺术自律论的经典表达,至少在法国和德国的艺术文化界已经十分流行。
“为艺术而艺术”是唯美主义者的职业信念。这一口号把康德美学关于先验判断力赋予艺术自律性的思想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出来,尽管那时法国文坛对德国哲学的学究气十分反感。唯美主义者对美学理论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宁愿将自己遗世独立的依据表述为“艺术”或者“艺术家”这样的名称,而排斥那些晦涩的哲学术语。唯美主义者似乎觉得表明自身的艺术家身份即足以“脱俗”,而不必再去追究那些在艺术背后支持艺术家特立独行的先验原则。所以我们看到,唯美主义者的艺术实践乃至生活实践,比康德美学更直接也更明确地张扬着艺术自律的信念。
“为艺术而艺术”对于唯美主义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所谓“纯艺术”的生产,它更意味着艺术生产者自身生活方式的艺术化。事实上唯美主义留下来的堪称伟大的作品并不多,后人津津乐道的多是他们我行我素、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作为最早举起审美现代性大旗抵抗世俗主义的文化运动,唯美主义以“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姿态表达出一种拒绝甚至抗议世俗生存规则的观念。威廉·冈特描述了戈蒂叶、惠斯勒、史文朋、罗斯金、波德莱尔、王尔德等人的生活实践,他们坚信自己是文曲星下凡,是不受人间道德约束的诗学天才:“1830年的热情此时变成了浪漫的越轨行动,它们恰逢时机,蔚然成风。巴黎的知识分子头上戴着尖顶帽,身上穿着意大利强盗的那种难看的长袍,心中积郁着对那帮奉守法度的良民的鄙视。”(11)唯美主义者把康德美学关于艺术自律的论证植入生活实践之中,使其升华为艺术家的职业伦理。当艺术天才们将自律的艺术转化成艺术家这个职业的生存伦理时,艺术活动中的自由游戏原则、想象原则、情感原则、无功利原则等等,便都成了艺术家们的生活行为,这就使得艺术从业者们可以超越乃至违背世俗生活的一般伦理规范。他们的种种惊世骇俗的言语行为并不接受世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审判,因为他们是按照审美原则生活的天才。威廉·冈特继续写道:“环境渐渐把艺术家推到了贵族式的地位上。不修边幅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仅仅是副产品,而这种生活的精神实质是:把标准定在众人之上,使之与众人分离。这种精神实质造就了异常挑剔的审美趣味。艺术家怀着对艺术门外汉的鄙视,渐渐滋长了一种情绪:他们认为,艺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琐事的分离是天经地义的。”(12)在审美现代性全面展开的20世纪,这种关于艺术与生活相互分离的信念使得艺术行业的从业者们着力于将自己的身体、言语和行为装修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奇异景观。而审美救世主义者又从这一信念中引出了审美伦理的救赎功能,并希图以此教导大众走出现代性之隐忧。
巴黎是唯美主义者进行伦理学突围的试验场,这座世界艺术之都同时也成为艺术家们以其审美伦理教化大众的演讲高台。当巴黎的审美伦理之风吹到海峡对岸的英国后,发生了这场伦理学突围的最典范案例,即审判王尔德事件。
关于1895年对王尔德同性恋行为的这场审判,其中最值得反思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审美伦理与世俗法典的冲突。王尔德与法律顾问团成员爱德华·卡森的对话,完全是两种伦理观念的交锋。当卡森意欲从《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找出作者道德败坏的踪迹时,王尔德声称:“文盲的艺术观根本就不算数,我只关心我的艺术观。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半点也不去理会。”(13)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力图用艺术家的审美伦理来论证自己有理由超越世俗道德的束缚。他自认为“我这个人象征着我们时代的艺术与文化”(14),所以他相信世俗法庭没有资格审判他这样的艺术家。
唯美主义者们所追寻的美,不仅是艺术作品的结构、意义或功能,更是艺术家的一种生存状态,或者说是艺术家们“不俗”的先验性。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而唯美主义者则用自己的生活实践将其变成道德是美的象征;与其说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还不如说他们信奉的是为艺术而人生。巴黎无愧于“世界艺术之都”的称号,艺术自律的观念在这里不仅孕育出伟大的艺术作品和新奇的艺术潮流,更是孕育出艺术场里羽化登仙般的审美伦理。这一伦理原则使得艺术家们由世俗生活世界突围,成了现实社会中不受一般道德约束的另类人物。进而他们的这种职业伦理又促进了文学场的建立,使艺术家们的生存美学有了一片自我陶醉的空间。布尔迪厄说:“艺术家群体不仅仅是创造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即艺术家生活方式的实验室和进行创作活动的基本空间。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自己构成了自己的市场……艺术家的生活本身就构成了一件艺术品。”(15)如果说独立于市场的文学场大大提升了艺术品在市场中的价值,那么,艺术家按照审美伦理来展开其生活实践则是文学场独立于市场的最好策略。
艺术自律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内涵,而审美的职业伦理化则使得艺术自律延伸至艺术家的存在属性。进入20世纪后这种审美伦理进而成为先锋派普遍奉行的生存美学,在诸如表现主义、垮掉派等艺术潮流中,审美伦理一直都是现代艺术家们实施抵抗诗学的道德依据,甚至像福柯这样的学者也由审美伦理悟出一种生存美学。“生存美学所要处理和解决的,就是自身的生存技巧,以便使自身在处理同他人的关系中,享受和鉴赏到尽可能满意的美感。福柯一生所经历的经验和实践过程,生动地体现了生存美学的原则。”(16)福柯像大多数唯美主义者一样,以主体性来创作自我这一作品,像创作艺术作品一样来安排日常生活。
三、法兰克福:从审美伦理到普遍伦理
20世纪30年代,艺术自律来到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手中,艺术自律由唯美主义的审美伦理扩张成为一种普遍伦理。尽管他们的主要著作是后来在美国写作的,但是这些学者的思想形成于法兰克福。
康德之前,英国经验主义者曾在道德意义上认定“美的精华在于文雅的动作”(17),德国理性主义者则在认识论意义上把美当成感性认识的完善。康德的先验哲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开创了“审美伦理”这一审美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唯美主义者以审美为艺术家的职业伦理,这其实限制了康德美学的“普遍人性”意义。直至法兰克福学派举起审美批判和审美救世的大旗,康德美学中所包含的普遍伦理的“解放论”功能才得以释放。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既不同于康德的“分析”式批判,也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一种以普遍伦理为价值坐标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否定性反思。他们将审美注入作为最高价值的普遍伦理,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有违这一伦理原则的种种现象,形成一种以“否定”为核心范畴的理论话语。阿多诺等人在自律的高雅艺术中提取出一种以人性自由为内涵的伦理原则,用以对照所谓“单面化”或“工具理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奴化”生存状态,呼吁人们按照审美原则进行造反以获得“解放”或“救赎”。
德国诗化哲学素来有审美救世传统。席勒设想用审美游戏克服现代人的心理分裂,尼采以艺术为生命的最高使命,海德格尔将人类的生存描述为“诗意地栖居”,这一传统也延续至法兰克福学派。德式审美救世主义比法式唯美主义更崇拜艺术自律,他们对安居于象牙塔中自娱自乐的艺术不屑一顾,而是要授予自律的艺术以创世者的爵位,希望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艺术以其终极性的价值将万千俗众救出深渊,开拓出按照艺术原则生活的美好世界。面对现代性之隐忧,唯美主义者求诸艺术的自救,而批判理论家则用艺术来普度众生。不过他们都相信在人类的世俗生活之前、之外和之上存在着一个圣洁的自由世界,即艺术的世界;人类一旦领悟了艺术世界的生存原则,便可以摆脱世俗世界的束缚而体验到真正的自由。
在康德那里,审美只是一种与认知、伦理相并列的先验性,而在阿多诺、马尔库塞手中,审美却是一种远高于人类的其他生活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原则。设定普世性价值原则,并以之为坐标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否定性认识,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思想诉求。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构想批判理论时设计了两个理论起点:一是各门具体学科对经验现象的描述,二是传统理论对普遍本质的界定。二者形成了批判理论的一个基本套路,即由普遍本质审视具体现象。虽然阿多诺拒绝一切同一性哲学关于普遍本质的预设,但事实上他只是将社会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将批判的价值坐标由形而上学转向了美学。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那里,美的艺术是人性自由的最高体现,因而也是审视和评判当代社会现实之合理性的唯一准则。马尔库塞认为:“每一真正的艺术作品,遂都是革命的,即它颠覆着知觉和知性方式,控诉着既存的社会现实,展现着自由解放的图景。”(18)阿多诺同样也是在艺术与现实的对抗性关系中设定艺术的自律性质并将自律的艺术作为超越和否定世俗社会、叩开个人自由之门的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把艺术自律从唯美主义者的职业伦理的有限性中解放出来,使之扩张成为一种具有人类解放功能的普遍伦理。自律艺术的这种普遍伦理化在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那里体现为,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艺术通过与世俗生活的对抗而唤醒人们的“否定认识论”,人们由此超越世俗生活的奴性状态从而走向自由。
法兰克福学派是艺术自律的坚定捍卫者,但是阿多诺等人的艺术自律观跟一般的艺术作品形式自足理论有很大的差别。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自律属性不等于艺术文本结构上的封闭自足,而是体现为一种与社会现实对抗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特质。这也就是说,艺术不逃离社会,而是面对社会发出否定、抗议之声,艺术就是凭借着这种“造反”的特性而彰显出它的自律性存在。阿多诺认为:“艺术的社会性主要是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的东西时才会出现。”(19)阿多诺用“新异性”概念来描述自律艺术的文本特征;这种新异性使得艺术具有反抗一切总体性或同一性的功能。伊格尔顿对此的理解是:“艺术力求某种纯粹的自律性,但是,如果没有异质性因素它将什么也不是,并且逐渐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之中。艺术既为自己同时也为社会而存在,始终既是自己同时又是其他的某种东西,批判性地从历史中疏离出来,但并不采取一个超越历史的优势点。”(20)阿多诺之所以要借异质性把艺术置于疏离历史而又拯救社会的地位上,那是因为他坚信自律的艺术能够释放出审美伦理即自由人格的光辉,在这沉沦的大地上唯有审美伦理之光将引导人类走出现代性的牢笼。
相比阿多诺,马尔库塞也许更为激进。马尔库塞强调艺术形式的独立,但这不是克莱夫·贝尔或罗杰·弗莱论述过的那种独立,而是一种反抗或革命意义上的独立。艺术形式“使作品从既存的现实中离却、分化、异在出来,它们使作品进入到它自身的现实之中:形式的王国”。跟阿多诺的“新异性”一样,马尔库塞笔下的艺术形式的独立性能够“建构出全然不同的现实”,因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唤醒了人们否定和怀疑的精神,从而体验到审美化人格的自由境界。“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是剥削主体或客体的新型的男人与妇女,将在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中,展现出人和物曾被压抑了的审美可能性视野——美学不再作为某些对象(艺术对象)的特定属性,而是作为与自由个体的感性和理性相适应的生存形式和态势。”(21)也就是说,形式自律的艺术激发的不单是关于艺术文本结构特性的经验,更是在不苟流俗中导向解放和自由。
自启蒙唤醒了现代性工程之后,政治革命、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都曾被西方知识分子当作人类解放的路径,但是随着现代性之隐忧日益蔓延继而其“自反性”日益显露,审美救世的呼声此起彼伏。艺术被美学注入了“自由的象征”内涵之后,就成为了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替代宗教的道德教化力量,人们把寻求解放的眼光投向了艺术化的生存之道。尤其是在审美现代性之体现即先锋派艺术中,艺术自律以抵抗和超越世俗社会的方式引导人们感悟心灵自由的激情。阿多诺等人从先锋派艺术中看到了审美伦理否定同一性秩序的功能以及它作为普遍伦理的救赎功能。事实上正如杰姆逊所言:“现代主义者总是希望艺术不仅仅生产出一部小说,一幅画,或是一部交响乐,他们要艺术能做一切事情。”(22)阿多诺等人偏爱现代艺术的原因就在于,以抵抗诗学见长的现代主义艺术把审美变成了生存态度,这一点正好跟法兰克福学派在审美造反中构建普遍伦理的思想诉求相互应和。
以“五月风暴”为代表的新左派造反运动,其指导性的理论就是一种审美化的伦理预设。甚至可以说,审美伦理就是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即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描述的那种身体话语的意识形态呈现。新左派的巨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审美意识形态,当然新左派最致命的弱点也在于审美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和虚无主义。
四、20世纪60年代的美利坚:审美伦理的蔓延
人们固然可以将艺术自律视为近代社会世俗化进程中贵族主义文化的自我确证,但是这一文化观念更像是市民社会兴起过程中中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诉求。艺术自律的观念在其生成进化之时就绝不仅仅涉及艺术文本的制作工艺或结构特性,它明显包含一种伦理学理想,即它设计了某种超然于所有社会实践场域之外的“艺术性”的生存方式,并以之为生存的最高价值。从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声称生活应当摹仿艺术以来,自律性的艺术就被崇拜者们当作个人自由的圭臬。尤其是康德美学给予艺术的自律性存在以先验性依据之后,面对现代性之隐忧,期盼救赎的人们在依据于审美原则而超凡脱俗的艺术里领悟到了人类解放论的意义经验。就像审美现代性张扬抵抗诗学以逃离启蒙现代性一样,艺术的自律性也让现代人看到“诗意栖居”的伦理学价值。
艺术自律给文化现代性提供了两条“自由之路”:其一是以形式主义、纯粹造型为代表的象牙塔的或逃亡者的艺术自足理论;其二是从达达派到嬉皮士运动的革命主义的或抵抗者的审美造反。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利坚,艺术自律构建的这两种审美现代性规划营造了两座“公社”——作为逃亡者的艺术家建立了纽约的格林尼治村,而作为审美造反者的嬉皮士则建立了旧金山的海特—阿西伯利自由村。
1967年,福柯在一次建筑研究学术会议上发表题为《另类空间》的演讲,提出“异托邦”概念。“异托邦”跟“乌托邦”不同,它是现实世界里的真实存在,但是它又跟乌托邦一样显示出与世隔绝的虚拟色彩(23)。异托邦常常由受到正统观念排斥的另类人群创建,它形成一个真实世界中的“虚幻空间”,因为这一空间存在的依据是被统治着真实世界的主流观念所不予认可的“他者”意识。60年代北美大地上的艺术家公社、嬉皮士公社就是典型的“异托邦”,支撑着这些公社的核心观念是不为世俗道德认可的“生存的艺术化”。这些公社里的人们向往远离尘嚣的艺术化生活,他们把这种生活方式当成投身自由空间的救赎之道。
格林尼治村是位于纽约曼哈顿南部的一片街区。由于许多诗人、戏剧家、画家居住于此,因而这里被看成一个艺术村。格林尼治村里的居民多为波西米亚生活风格的艺术家,而且这里还是“垮掉的一代”的诞生地。在这片街区里,遍布着剧院、画室、咖啡馆,不修边幅的艺术家随处可见。谈到格林尼治村,人们总是将其定位为一个超凡脱俗的艺术共和国。1916年,先锋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和约翰·斯隆登上格林尼治村的一座楼顶,宣布格林尼治村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独立的乌托镇”。美国学者萨利·贝恩斯在《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一书中关于此事的评论是:“杜尚令人起敬的里程碑式的‘占领’把政治性革命改造为文化意义上的反叛:这个事件是庆祝性的(有酒与食物)、艺术性的(有诗歌朗诵)、异国情调的(日本的灯笼)、游戏性的(玩具手枪及气球)、“左倾”的(气球毕竟是红色的)。它还发出来强烈要求建立波西米亚式自由社团的声明(‘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召唤一种替代性的文化,从资产阶级生活中独立出来(‘乌托镇’)……”(24)从那以后,格林尼治村一步步走向艺术独立性的实验室、独立艺术的博物馆以及独立艺术家们的“理想国”、艺术化生存方式的活动场。
作为一座依据艺术自律而建立起来的“异托邦”,格林尼治村承载着审美现代性的一种理想,即用审美伦理拒斥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在艺术性的伦理实践中完成审美救赎。艺术从世俗世界中独立出来之后,它负担起沉重的职责,以至于人们要以它为“法律”来缔造自由共和国。在60年代的美利坚,风起云涌的反文化运动激发了人们超越“现代性之隐忧”的渴望,而格林尼治村这座“艺术之城”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相比19世纪的唯美主义,格林尼治村带有更多先锋主义色调,因为它毕竟是与“垮掉的一代”共生的。只是随着激进主义文化运动的衰落,格林尼治村也逐渐褪去了光晕,最终让位于中产阶级的商业伦理。
嬉皮士运动的主角不是职业艺术家,但是这一运动更具“审美造反”色彩。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都典型地体现着审美现代性的特征,即叛逆性。嬉皮士运动上承“垮掉的一代”,下启新左派的“审美造反”;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一书将嬉皮士运动视为乌托邦主义的误入歧途,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标记。嬉皮士运动从“垮掉的一代”那里继承了对中产阶级生存伦理的反叛。以波西米亚式生活方式抵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生存伦理,正是自唯美主义以来审美现代性的伦理诉求。
嬉皮士运动反抗工具理性化生存伦理的方式就是感性生命力的放纵。这种放纵起源于对现代性的效率主义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又来自于现代性的另一侧面——自律艺术中所蕴涵的个人自由价值。嬉皮士们通过吸毒、性解放以及摇滚乐来对抗所谓中产阶级道德,同时他们跟追求纯粹自我的现代艺术家一样,有着一种寻找人间伊甸园的异托邦情结。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些垮掉派分子来到旧金山的海特—阿西伯利,他们在此地建立起颓废生活的根据地。几年之后,大批嬉皮士来到海特—阿西伯利寻找身体的自由,这里俨然成为一座自由之城。嬉皮士们在他们的自治公社里过着自食其力、财产公有、性关系自由、毒品泛滥的生活。一时间,北美大地上出现了多处嬉皮士公社,身体的狂欢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主题。但是当他们在纵欲、吸毒和摇滚乐中耗尽了造反的激情之后,这些公社也逐渐解体,包括海特—阿西伯利。
从唯美主义到嬉皮士,延续着一条历史的线索,那就是波西米亚式生活方式逃离或反抗布尔乔亚式生活方式。美国记者大卫·布鲁克斯写道:“布尔乔亚的主要领域是商业和市场,波西米亚则在艺术上独擅胜场;布尔乔亚崇尚物质主义、秩序规律、习俗、理性思考、自我规范和生产力;波西米亚阶级注重的则是创意、叛逆新奇、自我表达、反物质主义的生活体验……”(25)在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两种生活伦理的对立中,我们可以见出卡林内斯库描述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裂变。艺术自律来源于现代性,但是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却是对抗现代性。自律的艺术虚拟了一种自由的体验,唯美主义、嬉皮士等都想把这虚拟的自由变成现实,于是有了种种反文化的文化运动。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结合成“布波族”,其中释放的信息是:自律的艺术开始低下那高贵的身姿回到人间,审美伦理开始靠近商业伦理。到此时,艺术自律的终结也指日可待了。
五、从绝对音乐到无物象绘画:纯艺术的赋格曲
现代性工程展开不久,艺术便遭遇体制性的危机。康德美学的“无功利性”、“形式游戏”等观念,给危机中的艺术带来独立于城邦历史之外的生存合法性。康德的艺术自律论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由先验的判断力活动演化而来的审美伦理,其二是由形式游戏演化而来的艺术作品结构和意义上的自足性。如果说前者导致了从唯美主义到嬉皮士等一系列的审美造反运动,那么后一种理论则启发了有关艺术作品的文本自足性存在的观念,即形式游戏对艺术作品的统治权。
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借助天才论让艺术家跳出历史,变成天上的文曲星,同时一种关于艺术作品的非历史化和形式自律性的观念也开始流行。“为艺术而艺术”不仅是艺术家们告别历史的宣言,也是艺术作品属性、意义、结构等元素摆脱“城堡上飘扬的旗帜”的一种策略。曾经像其他社会实践场域一样接受总体性历史管辖的艺术,现在需要走出历史自立为“纯艺术”。康德之后,尽管仍有人在诸如民族精神、历史理性、意识形态等概念下界定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属性,但是关于艺术之纯粹性、自律性的论证却日益增多,探索艺术不同于一般社会实践之特性的“一般艺术学”日渐成型。面对世俗化和物质主义,19世纪开始出现“以艺术代宗教”的救世观念。既然艺术可以承担宗教的职能,它就必然具有一种超越世俗世界的本真属性和终极价值,所以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等都坚决地认定艺术属性的非历史特征,都极力推崇艺术美的纯粹性。唯美主义者们普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王尔德甚至认为:“生活模仿艺术远甚艺术模仿生活。”(26)罗斯金虽然不大同意这位学生的意见,但是罗斯金在艺术有着高于世俗社会之价值这一观点上,其实跟王尔德是相通的。
最能体现艺术品属性、意义和结构的独立性的思想诉求的,莫过于自19世纪以来在各门类艺术领域中出现的“形式自足性”理论。最早有关艺术作品形式自律的论述发生在音乐理论界。1722年,近代和声学的奠基人、法国音乐家拉莫在《和声学基本原则》中说,音乐是一门有规则的音响的艺术;后来,德国浪漫派的施莱格尔提出“绝对音乐”概念。这些看法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1854年,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中明确地宣称:“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他解释道:“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27)汉斯立克的乐音形式自律理论,体现出与浪漫主义不一样的艺术自律观。浪漫主义的天才诗学强调艺术家的主观精神的独立性而不关心作品形式自律与否,汉斯立克则认为音乐的美跟外部注入的情感无关,它来自于乐音的结构。正是这种对音响构成性的关注,导致了后来出现勋伯格的十二音序列理论。
各门艺术为寻找自身特定的独立属性而重建存在之合法化,这是19世纪晚期以来审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方面,从印象派到野兽派、立体派的造型艺术提供了典型案例。由于供养人体制的终结、照相术的应用、传统表意技法范式的僵化以及艺术场的独立,由印象派发端,西方绘画艺术开始了一段“寻找自我”的历史。从印象派对“条件色”的重视到野兽派对“二维性”的肯定,再到立体派的“纯粹造型”以及表现主义的“无物象绘画”,西方绘画由摹仿自然或服从物象走向了自我指涉或造型的自律性,这一变化的内涵也可以表述为由形式的他律转向形式的自律。现代画家们意识到,绘画被叙述性和物象统治得太久,以至于失去了自身的特性。绘画作为自律性的艺术的根本在于复归它的二维平面特性和“造型的形式”(罗杰·弗莱),如塞尚所言:“艺术是一和自然平行的和谐体。”(28)这一“和谐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平行于自然的独立禀性,就是因为它找到了形式自足的条件,即“纯粹造型”和“二维性”。格林伯格说:“‘纯粹’意味着自我定义,艺术自我批评的事业就是一种彻底的自我定义……二维空间的平面是绘画艺术唯一不与其他艺术共享的条件。因此,平面是现代绘画发展的唯一定向……”(29)以纯粹造型为基础的抽象绘画,实际上是艺术自律在绘画艺术中以“形式的自律性”来实施审美现代性工程的必然结果。
在文学领域里,形式自律的结果就是现代理论用“文本性”取代了古典时代的“诗性”概念。浪漫主义的天才诗学实际上是排斥形式自律的,它把艺术自律限定在艺术家的主观精神状态之中。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艺术自律的另一种形态,即穆卡洛夫斯基说的那种语言的“凸显”。瓦莱里曾经在“绝对音乐”的启发下提出“纯诗”概念。他把“纯诗”设想为一种绝对的诗,其特质在于“探索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效果,或者毋宁说是词语的各种联想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效果;总之,这是对由语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30)。在20世纪的语言论转向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形式主义文论完全抛弃了“摹仿”、“表现”等他律论理论话语,倡导一种超乎历史的文本自足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声称文学与城堡上飘扬的旗帜无关,“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的对比关系”(什克洛夫斯基)(31)。韦勒克对此的评论是:“俄国形式主义使艺术作品自身成为关注的中心;它尤其强调文学和生活的不同,摈弃了通常对文学的传记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解释。它以自己的术语发展了一套用于分析文学作品和研究文学史的富于创造性的方法。”(32)新批评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中把诗人的主观精神和读者的阅读感受等历史性元素从诗的意义阐释中彻底驱逐出去,让诗成了一个与历史完全隔绝的自律性存在。这一做法也许会遭遇浪漫主义者的反对,但是它在寻求艺术自律性这一点上跟浪漫主义实际上是相同的。
注释:
①③⑤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褚朔维译,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第82—84页,第22—26页。
②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④⑥⑦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16页,第148页,第205页。
⑧(11)(12)(13)威廉·冈特:《美的历险》,肖聿、凌君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0页,第2页,第5—6页,第217页。
⑨卫姆萨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颜元叔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⑩John Wilcox,"The Beginnings of L’Art pour l’Art",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II(June 1953),360-377.
(14)参见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15)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16)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17)培根:《论美》,朱光潜译,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页。
(18)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7页。
(19)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20)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21)《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8、379页。
(22)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23)参见尚杰《空间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载《同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4)萨利·贝恩斯:《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华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25)大卫·布鲁克斯:《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级的兴起》,徐子超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6)王尔德:《谎言的衰朽》,赵灃、徐京安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27)爱杜阿德·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第39、38页。
(28)瓦尔特·赫斯编《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宗白华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29)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现代派绘画》,弗兰西斯·弗兰契娜、查尔斯·哈里森编《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张坚、王晓文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30)瓦莱里:《纯诗》,丰华瞻译,伍蠡甫主编《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31)日尔蒙斯基:《论“形式化方法”问题》,托多罗夫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
(32)转引自汪正龙《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标签:艺术论文; 现代性论文; 康德论文; 阿多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旅行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唯美主义论文; 美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