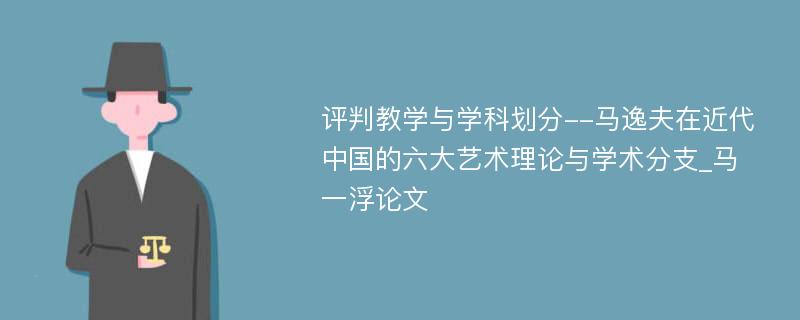
判教与分科:马一浮的六艺论与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教与论文,六艺论论文,马一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4-0065-08
六艺论是马一浮最为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由三个命题构成,即“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六艺统摄于一心”、“六艺互相统摄”,而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为核心。马一浮的六艺论甫一提出,便遭到众多质疑乃至批判。这些质疑和批判主要针对“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命题而发。马一浮在《泰和会语》中说:
今言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言语说得太广,不是径省之道。颇有朋友来相规诫,谓先儒不曾如此,今若依此说法,殊欠谨严,将有流失,亟须自己检点。[1] (P18)
此位朋友正是马一浮的好友、史学家叶左文。马一浮在答叶氏的一封书信中对此作了辩解:
浮今以六艺判群籍,实受义学影响,同于彼之判教,先儒之所未言。然寻究经传遗文,实有如是条理,非敢强为差排,私意造作。兄引朱子言,谓道有定体、教有成法,浮今所言,疑于变乱旧章。然判教实是义学家长处,世儒治经实不及其缜密。今虽用其判教之法,所言义理未敢悖于六艺。先儒复起,未必遂加恶绝。不敢自隐,故复陈之。[2] (P442)
马一浮坦承自己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是受了佛家判教思想的影响,其目的在用佛家缜密之法,寻天下学术之条理。在《复性书院讲录》中,马一浮曾以“判教与分科之别”为题,专节讨论六艺判教与学术分科的区别,并认为“有判教而无分科”。[3] (P48—52)这些都在提醒我们,马一浮之标举六艺论、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其目的即在借佛家判教思想分判天下学术,明其统类得其条理,而其潜在的对手则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大势。
罗志田先生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4] (P2)诚然,近代西学东渐,西学中的学术分科观念及学术分科体系一并传入中国,学术分科成为近代中国的学术主潮。受此影响,近代中国学者在认识和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时,往往会带着学术分科的观念,在自身传统里寻找中国固有的学术分科体系。而要寻找中国固有的学术分科体系,大概有三类传统资源是可以利用的。一是“孔门四科”之说。《论语·先进》篇说:“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人据此认为,孔门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以四科之学教授弟子。这便是“孔门四科”之说。近代学人往往以“孔门四科”作为传统学术的分类体系。比如熊十力就肯定“孔门四科”之说,并认为近代以来“义理、考据、经济、词章”的四科分类,其实正源自“孔门四科”,而后者才是“类别学术”之典要。[5] (P211—214)二是清代桐城派所大力倡导的“义理、考据、词章”之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一文中,分中外学术为科学、史学、文学三大类,很显然是受了“义理、考据、词章”三分法的影响。[6] (P403)桐城派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后来根据时代所需,又在“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加入偏于致用的“经世”一类,遂成为“义理、考据、词章、经世”的四分法。而此四分法似乎更易为近代学人所接受。熊十力曾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又说:“四科标名,虽由近代,其源实自孔门。”熊氏虽主“孔门四科”之说,反对桐城四科之目,但也承认“义理、考据、经济、词章”的四科分类乃近代“旧学家向有”的普遍性认识。[5] (P211—214)三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严格说来,四部分类是自隋唐以来的一种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① 但近代不少学人都认为四部分类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尤其是在讨论“国学”这一概念时,往往以“经史子集”作为“国学”的基本内容。黄晏妤先生经过考察发现,近代以来“正式而非随意地将中国学术分为四部的,确以各种‘国学’书籍为多”。[7]
中国传统学术重视的是博学和融通,向来不主张分科治学,既无学术分科的观念,也没有学术的分科体系。无论是“孔门四科”,还是“义理、考据、词章”(或加入“经世”),或者是“经史子集”,都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科体系,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学术分科体系根本就不存在。近代中国学人在接受了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之后,又不太情愿或还不太习惯使用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就只好返回自身的传统寻找一些似是而非的学术分类系统。这一做法看似传统和保守,其实已比较务时和趋新。因为接受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寻找中国学术的分科体系,主张将学术分而治之,这已经违背中国学术重博通的传统,趋向于西方分科治学的时代潮流。
近代学人返回自身传统寻找学术分科体系,是近代中国学术认同西方学术分科观念、接受西方学术分科体系的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派学人提倡整理国故,作为“国故”的中国传统学术经整理而分别归入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西式学科,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及学术分科的体系最终为近代中国学人所完全认同和接受。此后,中国学术便依照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分科治学、专门研究,其博学融通的传统遂成明日黄花,一去难返。②
马一浮的六艺论在1917年前后就已基本成熟,因而它首先应对的还不是胡适等新派学人直接以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割裂中国传统学术的做法,而是近代早期学人在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寻找学术分科体系的做法。他对上述三类似是而非的学术分科体系一一作了批驳。马一浮说:
分科之说,何自而起?起于误解《论语》“从我在陈”一章。记者举此十人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诸目,特别诸子才质所长言之,非谓孔门设此四科也。十子者,皆身通六艺,并为大儒,岂于六艺之外别有四科?盖约人则品核殊称,约教则宗归无异。德行、文学乃总相之名,言语、政事特别相之目。总为六艺,别则《诗》《书》,岂谓各不相通而独名一事哉?故有判教而无分科。[3] (P51)
马一浮认为,“孔门四科”之说是一种误解,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是就诸弟子才质所长而言,孔门一以六艺为教,不会在六艺之外另设四科之目。所谓“孔门四科”其实并无其事。马一浮又说:
姚姬传以义理、考据、词章并列为三,实不知类。词章岂能倍于义理?义理又岂能不用考据?[3] (P42)
马一浮认为,桐城派姚鼐以义理、考据、词章并列为三,其实是不明义类,因为三者实为一体,不可割裂。所谓“义理、考据、词章”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马一浮又说:
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照一般时贤所讲,或分为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学、史学等类,大致依四部立名。然四部之名本是一种目录,犹今图书馆之图书分类法耳。(荀勖《中经簿》本分甲、乙、丙、丁,《隋书·经籍志》始立经、史、子、集之目,至今沿用,其实不妥。今姑不具论,他日别讲。)能明学术流别者,惟《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最有义类。[1] (P6)
马一浮认为,近代学人往往将中国固有学术称之为“国学”。但“国学”一词实际上是比照“外国学术”而产生的,用佛教的说法,这便是“依他起”,严格说来,是不可用的。而讲“国学”者又往往以小学、经学、诸子学、史学等为其基本内容,也就是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分类。“国学”一词,马一浮还可以随顺时人,暂且接受;但以四部分类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分类的做法,则是他绝不能苟同的。因为“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只是一种“甲乙丙丁”式的图书分类,并不能明辨学术流别。“经史子集”不能作为中国学术的分类系统。
但在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寻找学术分科体系,对传统学术进行分类整理以使现代化,毕竟是近代早期中国的学术主潮。马一浮虽然极力反对,但也不能不受此时代潮流的影响。他也要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分类整理以使现代化,并在传统学术自身寻找固有的学术分类系统。而且,也只有真正寻找出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学术分类系统,才能一一击碎那些似是而非的中国学术分科体系,才能有力对抗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
有趣的是,同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分类整理,寻找其固有的学术分类系统,近代学人一般是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再返回自身寻找学术分科体系;马一浮却是接受佛家的判教思想,再返回自身寻找判教体系。二者具体操作不同,思路却颇为一致。佛家判教,就是对佛家各种教派教义进行分类和判别。吕瀓先生指出:“在中国佛学里,判教的说法是从南北朝以来就开展着的。经隋代到唐初,前后百余年间,著名的判教不下二十家。”[8] (P358)如此众多的判教理论,对马一浮发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他要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寻找其判教实践和判教体系。马一浮说:
或曰:天台据《法华》判四教,慈恩依《深密》、《楞伽》判三时教,贤首本《华严》判五教,然则判教之名,实始于佛氏之义学。儒家亦有之乎?答曰:实有之,且先于义学矣,后儒习而不察耳。[3] (P49)
马一浮认为,判教之名虽始自佛家,但儒家实际上也有判教,而且先于佛家。在《复性书院讲录·判教与分科之别》一节中,他大量考察《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礼记》、《春秋繁露》、《史记》、《汉书》等典籍中论述《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文字,发现在中国学术传统里,据六艺判教是真实存在,且十分普遍的情况。比如《礼记·经解》说: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马一浮认为,这一段文字显然证明了儒家据六艺判教是真实存在的。他说:“此段人法双彰,得失并举。显然是判教的实证据。”[3] (P50)又比如《庄子·天下篇》说: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马一浮说:“庄生之言与荀卿相同,言百家道之,则知治六艺者,不独儒家为然。其曰:‘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下‘判’字,尤为分晓。”[3] (P50)他认为,庄子的话表明了在中国学术传统里,治六艺之学、据六艺判教,是诸子百家共同的学术路向,情况十分普遍,不独儒家为然。依马一浮的意思,中国学术传统里的判教,就是根据《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六艺),将中国一切学术分判为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六类学术(六艺之教);反之,中国一切学术都为“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六类学术(六艺之教)统摄,也就是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六艺)统摄。很显然,中国学术传统里的判教体系,就是“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的“六艺之教”系统。马一浮说:“六艺之教,通天地、亘古今而莫能外也。”[3] (P51)这一系统,真是范围天地古今一切学术而不遗。在马一浮看来,若要认识和整理中国传统学术,只有据六艺判教、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遵循六艺之教的系统,才能明其统类、得其条理。马一浮说:
学者观于此,则知天下之书不可胜读,真是若涉大海,茫无津涯。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然弗患其无涯也,知类,斯可矣。盖知类则通,通则无碍也。何言乎知类也?语曰:群言淆乱,折衷于圣人,摄之以六艺,而其得失可知也。[3] (P26)
又说:
上来所判,言虽简略,欲使诸生于国学得一明白概念,知六艺总摄一切学术,然后可以讲求。譬如行路,须先有定向,知所向后,循而行之,乃有归趣。不然则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泛泛寻求,真是若涉大海,茫无津涯。吾见有人终身读书,博闻强记而不得要领,绝无受用,只成得一个书库,不能知类通达。如是又何益哉?[1] (P12)
马一浮认为,六艺之教的系统在中国学术的浩淼天地里,就好比行人之路标,只有循而行之,才能知类通达,得其要领,否则便会若涉大海,茫无津涯,泛泛寻求,劳而少功。
马一浮对他在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寻找到“六艺之教”的判教体系,虽然颇为自负,但从不轻易示人,直到1938年讲学浙大,才公之于世。而此时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早已经新派学人的大力鼓吹提倡,占据了中国学坛。因而马一浮公开提出据六艺判教、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标举“六艺之教”的判教体系,其针对的就不仅是早期学人在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寻找似是而非的学术分科体系的做法,更是新派学人直接以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割裂中国传统学术的做法。马一浮在浙大先讲“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接着就讲六艺“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1] (P16)前者即在证明“六艺之教”的判教体系才是中国传统学术真正固有的学术分类系统,后者则是直接对抗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割裂。难道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就是唯一的真理,就只能任由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来割裂中国的传统学术,而不能由“六艺之教”的判教体系来统摄西来一切学术?西学中的一整套学术分科观念和分科体系,都遭到马一浮的质疑和挑战。
马一浮的据六艺判教和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都是为了对中国传统学术作分类整理以使现代化,但为什么马一浮要主张判教,而反对分科,不论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寻找似是而非的学术分科体系,还是以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割裂中国传统学术。这就涉及到判教与分科背后一整套学术观念的巨大差异,也就是六艺论思想与近代学术分科精神的巨大差异。
马一浮对判教与分科的区别作了精辟的论述:
荀子曰:“圣人言虽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统是总相,类是别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举总以该别,由别以见总,知总别之不异者,乃可与言条理矣。内外本末,小大精粗,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备而不遗,通而不暌,交参互入,并摄兼收,错列则行布分明,汇合则圆融无碍,此条理之事也。(事犹言相。)若乃得其一支而遗其全体,守其一曲而昧乎大方,血脉不通,触涂成滞,畛域自限,封执随生,相绌相距,不该不遍,是丹而非素,专己而斥人,安其所习,毁所不见,是犹井蛙不知有海,夏虫不知有冰。……由前之说,则判教是已;由后之说,则分科是已。[3] (P48)
马一浮认为,判教虽然是对学术进行分类,但分类并不妨碍每一类学术之间的会合融通。如果分类是类和别,那么会通则是统和总。判教是既分类又会通,所谓统类是一、总别不异。而分科虽然也是对学术进行分类,但每一类学术之间都是畛域自限、专己斥人,而不能会合融通。分科是有分类无会通,所谓有类无统、有别无总。简言之,判教与分科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博通,后者重专门。
诚然,近代学术分科重视分科治学、专门研究,而反对中国学术的博通传统。傅斯年说:“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9] (P283)傅斯年及其“史语所”大力提倡分科治学、专门研究,正是近代学术分科精神的典范代表,并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而重视博通传统的钱穆等人,则因为与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分科精神不相合拍,所以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在外。③ 而马一浮的六艺论,主张据六艺判教、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虽然是将中国传统学术乃至西方学术分作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六类,但其六艺论又主张“六艺互相统摄”,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所代表的每一类学术之间可以会合融通,对其中任何一类学术的研究,都必须而且能够达到对“六艺之教”的整体把握。马一浮的据六艺判教,实际正维护着中国学术重博通的传统。作为“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10] (P181)的一代大儒,马一浮站在中国学术重博通的传统立场上,主张“有判教而无分科”,不是至为平常么?
对中国学术博通传统的坚守,是马一浮主张判教反对分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根本原因。当傅斯年说“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他已经注意到,中国学术里与博通传统相伴随的另一重要传统,即重视道德价值,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以造成人品为归。成中英先生指出:“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是对宇宙价值、人生价值、人类价值、社会价值深沉的肯定与体验;这种深沉的肯定与体验是基于对生命的会通得来的,也是基于对生活经验的整体反省得来的。”[11] (P230)重价值是随重博通而来的中国学术的本质。如果说重视博学融通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形式特征,那么重视道德价值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实质。正是对中国学术价值本位传统的坚守,才是马一浮主张判教反对分科的根本原因。
主张分科治学、专门研究的近代学术分科精神,在形式上强调的是“分科”和“专门”,在实质上强调的则是“治学”和“研究”。也就是说,学术分科的最终目的在研究学术,获取知识,而不在肯定和体验学术传统中所蕴涵的价值观念。比如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在形式上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纳入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强调“分科”和“专门”;在实质上则是“认为中国文化所累积的不过是一堆有待考证的材料”,“致力于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客观地’研究文史问题”,而不考虑如何“引导人们去把握存在于传统核心的精神道德的意义”。[12] (P90—91)胡适曾明确地说:“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找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体的中国文化史。不论是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13] (P143—144)客观地研究学术以获取知识,而不是主动地体认学术传统中所蕴涵的道德价值来安身立命,这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它与中国学术价值本位的传统大相径庭。中国学术重价值,主张用价值来规范知识。价值为本,知识为末;价值为先,知识为后。脱离价值、一味求知识的“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向为中国学术所不取乃至反对。马一浮反对近代学术分科,除了其形式上的“分科”和“专门”外,主要的还是因为其实质上的“为知识而知识”。马一浮说:
知识是从闻见得来的,不能无所遗;才能是从气质生就的,不能无所偏。(今所谓专家属前一类,所谓天才属后一类。)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1] (P44)
又说:
今日学者为学方法,可以为专家,不可以成通儒。……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不免失之于通,殆未足以尽学问之能事。[1] (P45—46)
马一浮认为,近代学术分科精神造就了所谓的“专家”,但专家只能从事专业研究以获取专业知识,不能体认学术传统中所蕴涵的道德价值,不能变化气质去其习染,因而也就不能成就真正的学问。
同样,马一浮主张据六艺判教,也就不仅仅是因为判教形式上的重博通,更主要的还是判教实质上能契合中国学术价值本位的传统。与近代学术分科的实质不同,马一浮的据六艺判教,其实质不在“治学”和“研究”,不在“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而在“教”,即“教化”。他根据《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将中国学术乃至西方学术分判为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六类,其“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的说法显然直接取自《礼记·经解》。因而马一浮据六艺判教的“教”,就不是佛家判教的“教”,即不是宗教的教派教义,而是《礼记·经解》意义上的“教”,即教化。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既是六类学术,又是六种教化。马一浮据六艺判教,其目的就在以六艺为代表的六类学术教化学人。马一浮说:“今举六艺以明统类乃正是始条理之事。古人成均之教,其意义亦是如此。”[1] (P21)马一浮认为,据六艺分判天下一切学术,明其统类得其条理,其意义正相当于古人的成均之教,即古代的大学教育。也就是说,据六艺判教的意义正在于象古代大学一样教化学人。而以六艺教化学人,具体说来,就是据六艺之书,讲六艺之文,明六艺之道。也就是依据《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六艺之书),研习其中所记载的文化知识(六艺之文),体认其中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六艺之道)。但是,以六艺为教,其主要目的不在获取知识,而在体证价值。因为马一浮的六艺论认为,六艺之道(道德价值)高于六艺之文(文化知识)。马一浮说“文所以显道”[3] (P22),又说“道外无文”[3] (P13)。六艺之文乃所以显发六艺之道;离开六艺之道,六艺之文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马一浮又认为“六艺统摄于一心”,六艺之道的根源就在每人各自的心性;每个人都应该而且能够体认六艺之道,以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总起来说,马一浮据六艺判教、以六艺为教,其目的就在讲明六艺之道,体认价值,造成人品。这正是近代学术分科所要打破的中国学术价值本位的传统,也是马一浮主张“有判教而无分科”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代大儒,马一浮站在中国学术重博通重价值的传统立场上,反对近代学术分科,主张据六艺判教,其主要原由即在于前者形式上重专门,实质上重知识,对中国学术传统构成严重挑战;后者形式上重博通,实质上重价值,切实遵循了中国学术的固有传统。而从马一浮“有判教而无分科”的断言,我们也就明白,马一浮之所以提出六艺论,据六艺判教、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其目的便是为了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作分类整理时,坚守中国学术重博通重价值的传统,应对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大势。但是,当现代学术分科成为普天之势,马一浮的六艺论几乎无人肯信、无人能懂,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都可谓微乎其微。然而马一浮之标举六艺论,以应对近代学术分科,坚守中国学术传统,其表现出的幽深情怀和所作的有益尝试,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激励和启发。六艺论之部分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注释:
①参阅黄晏妤《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②上面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大势,受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和黄晏妤《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两文启发颇多,特此说明并致谢。
③参阅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十一章《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