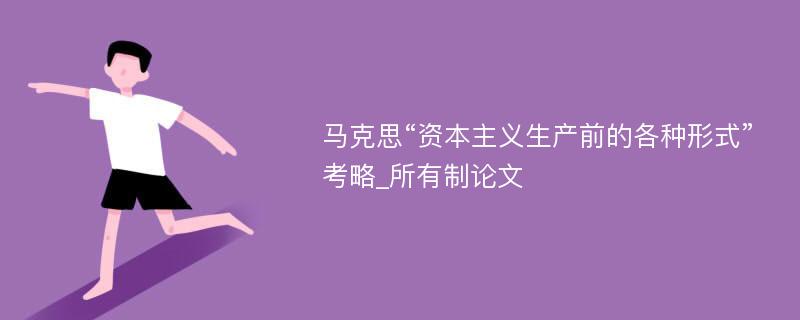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各种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此处准备考察的,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为节省篇幅起见,我们简称为《形式》。基于同样的理由,本文凡引自该文的文字,只在引文后标出它在全集第46卷(上)的页码,一律不再另作脚注,祈读者鉴谅。
(1)马克思的《形式》一文,历来被当作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经典,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和文章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最近笔者在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献之后发现,这篇一直被视为社会形态演变理论问题的文献,其主题原本是讲“资本的原始形成”(第504页)即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注:具体地讲,是研究“正在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已经成为决定的、支配整个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参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第5-6页。)而不是专讲社会形态演变的。我的理由有三:第一,文章开宗明义就谈到,他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及其演变之目的,乃是为了弄清“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第470页);第二,从文章的结构看,此文总共可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讲农业公社的起源及其各种派生和再生形式,后一部分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其特征,按逻辑显然前一部分是为后一部分服务的;第三,这篇文章虽以很大篇幅,来谈“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问题,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被列在第三章即《资本章》之下,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此文的真实意图。但这篇文章,由于在1939年和1940年以《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为题,由当时苏联马列研究所单独编辑出版,(注:最初单独发表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40年以小册子形式单独出版。К.Маркс,Формы,предществующие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Политиздат,1940.马克思著,日知译:《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读者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引导到“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上,它所阐述的资本主义起源这一主题,反而被不应有的忽视了。如果这一论点可以成立,那么过去的许多与此有关的误读或误解,以及由此引出的许多解释和发挥,可能都应重新审查。
(2)或许有人会说,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不管其主题是什么,反正文章以大量篇幅探讨了“资本主义生前的各种形式”,因此并不妨碍我们把它当作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经典来读。此说当然不无道理,因为此文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的确是涉及所有制形式或生产方式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一篇,甚至可以说是其中“绝无仅有”的一篇,因此它被人称作“稀有著作”(注:〔日〕中村哲:《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是很正确的。但由于主题不是讲“社会形态”问题,而是讲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它在写作方法上主要是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对比与分析,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文章不仅不强调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反而有时在某种程度上更强调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强调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使用价值”(第505页)的生产,而与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罕见情况,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些重要生产方式,例如东西方都存在过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在这篇著名文献中就未加详细分析,不仅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特点未加详细分析,反而很注意二者之间的某些共同之处,强调它们均“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第490页)这一点。他还指出,由于奴隶主把奴隶看作自己的“财产”,即物,而农奴在人身上被主人占有而成为“土地的附属品”(第488页),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第502页),因而实际上和此前的农村公社的各种形式一样,都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天然统一”或“原始统一”。他写道:“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第488页)。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奴隶制和农奴制是不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二者在历史上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独立存在过吗?它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3)有人不了解这一点,根据他们的误解,提出在历史上只存在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虽然存在过《形式》中所说的三种所有制形式,但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里所有制的“三种类型”,因此在资本主义之前只存在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这种意见对不对呢?笔者认为,又对又不对。说《形式》中所讲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是一种社会形态里的三种所有制类型,这一看法当然是不会错的。因为,正如马克思在《形式》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的所有制形式,原本是“以同一基本关系[即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第472-473页)。对此,他还具体解释说: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如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等等(第472页);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则“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它也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第474页);至于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虽然其特点更为突出,但它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他们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制形式”(第477页)。所以,本文的俄文版编者在出版本文时,特意在文前加了一个原文没有的小标题,称它们都是“公社的各种形式”(第470页)。原苏联学者Л.С.瓦西利耶夫等人也认为,《形式》一文中所说的三种所有制形式,是“三种主要原始公社”(注: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的所有制形式。当然,马克思划分这三种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标准,都是劳动者个人与公社土地之间的关系,因而此处所说的“公社”并非一般公社,而是专指农业公社或土地公社,它们虽然在性质上仍属于原始社会,但已是人类原始公社的最后阶段,即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了。马克思之所以要详细研究这几种所有制形式的区别和联系,其目的就是要在动态和静态中把握人类历史的走向,看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路线和程序所体现出来的多样性,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注:恩格斯认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4)但这一意见又不完全对。因为承认这三种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公社或农业公社所有制的不同类型,并不等于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只存在过一种社会形态,也不等于说马克思认为奴隶制或农奴制在人类历史上,不曾以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存在过,至少不能从作者在《形式》所作的论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众所周知,关于奴隶制和农奴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他还指出:“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恩格斯讲的,并不一定代表马克思的观点。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述的观点代不代表马克思呢?要知道此书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作品,其中每一章都是马克思亲自过目的。在此书中,他们以分工及其发展立论,讲了世界历史上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并认为它们代表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其中,第一和第三种所有制用语明确,是分别指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但第二种是否就是指“奴隶制”社会呢?笔者以为回答应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在下文讲得很清楚,说在此形式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奴隶制有了发展而且“已经充分”的社会应是指奴隶社会,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其实,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形式》一文中,马克思也以十分清晰的语言,不仅指出了奴隶制和农奴制作为生产方式存在于农业公社的事实,还讲到二者发展成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的必然性:“假如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简单的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第490-491页)请注意,“否定”在哲学上意味着质变,奴隶制和农奴制不仅成了共同体的经济基础,而且“否定”了原始的“组织”即社会结构,这不就是说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了原始社会吗?我们还发现,马克思不仅清晰地说明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必然性,还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他在《形式》的后半部分,在分别论述了“财产的各种原始形式”之后指出:“这些形式由于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制)之内而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于是属于第一种状态的一切财产形式的单纯肯定性质便丧失了,发生变化了。它们全都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因而包含着这种对自身的扬弃。”(第502页)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奴隶制产生的经济原因,是因为在财产的原始形式的演变中,融进了一种因素即“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笔者以为,这是马克思的两个重要思想,由于它采用极为抽象的哲学语言而难于为读者所理解,对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来说,是可以得到启发的。所以,在《形式》一文中,马克思只提到奴隶制和农奴制,但未对它们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展开论述,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历史上不曾作为社会形态独立存在过,《形式》本身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
(5)但承认奴隶制或农奴制作为生产方式,在经过农业公社或土地公社的过渡阶段之后,可以达到最终“否定”原有的共同体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是一回事,至于奴隶制或农奴制是否在任何国家和地方都会上升为主要生产方式而形成为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而在历史上独立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形式》一文中写道:
“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员。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一,共同体是把这些条件看作归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少。这种财产形式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土地财产、农业独占统治的地方不同,征服(其他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从另一方面说,因为在这种财产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所以奴隶制在这里并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第492-493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这段论述的重要性何在?其重要性在于,它清楚地揭示了奴隶制发展的两种倾向,即有的可能“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而有的则“不改变[部落体]本质的关系”,它要以部落体内部的财产关系的状况为转移。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奴隶制都可以发展为独立的社会形态。他虽然在这里只以亚细亚为特例(注:至于亚细亚是否形成过独立的奴隶制社会,那是一个实证问题,人们尽可以自由地去讨论,它的答案怎样,均不构成对马克思思想的否定。)来说明这种可能性,但从其行文和用语看,他并不认为只有亚细亚才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只认为“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少”,既然只是“最少”,就还有“较多”、“较少”。因此,我认为,马克思关于奴隶制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思想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应当在理论方面继续加以探索,不可轻易否定。这与前面所说的关于奴隶制发展的“必然性”并不是一回事,因而并不相悖。
(6)有些研究者,由于在《形式》一文中找不到马克思关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详细分析,于是便根据其关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的某些特点的分析,把它们演绎成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令它们分别代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究竟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内的三种所有制类型,还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三个时代?我的答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其理由已如上文所述。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是,把这三种所有制形式看作社会经济形态的三个阶段的主张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只要仔细研读一下《形式》就可发现,几种所有制形式在那里虽然是并列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其私有化的程度却有高低之分。如果以“公有制——私有制”的发展方向为线索,对三种所有制形式进行排比分类,则它们又可构成三个不同梯级:(1)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和私人占有;(2)古代的所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和个人占有;(3)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个人私有和集体所有。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离公有制最近,而第三种所有制形式则离私有制最近,从而在性质上显示出先后次序来,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仿佛这三种所有制代表了三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但不要忘记,无论其中哪一个所有制形式,都是以公有和私有并存为其特征的,因而都还是从公有到私有的过渡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它们归入三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很难的,因为任何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都必须有一种对应的生产方式占主导的地位。而《形式》对其中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的描述,都不能给我们这样的印象。
(7)应当指出,《形式》通篇以“所有制形式”立论,因此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应是“生产方式”而不会是“社会形态”。这是因为,生产力是物质内容,组成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如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是物质实体,而生产关系则是把这些物质实体联系起来的社会形式,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实体。因此,生产关系可以和生产力一起构成一个统一体即构成生产方式,但是生产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单独和上层建筑一起构成一个统一体。(注:参阅赵家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正因为如此,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经济形态,一定要通过生产关系这个中介把上层建筑与生产力连在一起才能形成,否则它就将成为一个没有物质内容的东西,因而也就无法存在;换言之,所谓“社会经济形态”,应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全部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和有机的社会结构体系,是某种生产方式在新的生产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落后的生产方式而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形成的,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鉴于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提出其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著名论断时,“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使用的就是:O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注:K.Marx,F.Engels,Werke.Band 13,Berlin,1961.P.9.)(与之对应的英译名则是economic formation of society(注:H.Selsman and others ed.,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A Reader in Marxist Social Science.New York,1980,P.52.))。不难看出,此概念的中心词是“社会形态”而不是“经济形态”,因为原文“社会形态”是一个词而不是两个词(是连写的),okonomische一词作为形容词只是用来说明名词“社会形态”的,因此其本意是指由经济所产生或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与经济密切联系的社会结构体系,直译应表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经济社会形态”。由于马克思在《形式》一文中是以“所有制形式”立论,所以他在该文中使用的也就是"form"(复数formen)(注:K.Marx,F.Engels,Werke.Band 42,Berlin,1983.P.383.)而不是"formation"。此词的英文词形与德文相同,从语言学上讲前者强调的是外貌特征(outward or visible appearance),而后者强调的是形成的过程和结果(forming or shaping)(注:《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26,427页。)其含义有重要差别。其实,关于《形式》所阐述的基本概念和内容,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已说得很清楚,他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它“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7-138页。)由于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力一起构成生产方式,因此也可以说《形式》所涉及的核心概念是“生产方式”。
(8)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形式》一文中所讲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社会形态”。关于“社会形态”,在国际学术界虽然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三形态”、“四形态”或“五形态”等说,形态的类型比较而言总是有限的。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一下《形式》便可发现,马克思在那里提到的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就不下五种。除了明文标出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外,马克思还提到“斯拉夫的”所有制形式,以及作为“派生形式”的奴隶制和农奴制,这已经超过了五种了。除了这些所有制形式之外,在《形式》一文中,马克思还提到劳动者作为“生产工具所有者”的所有制形式,并指出“同这种劳动形式相联系的是行会同业公会制度”,认为它是一种与手工劳动有关的“特殊形式”(第498-499页)。此外,马克思还注意到,只有生活资料所有权的情况,有的可能已发展到奴隶制或农奴制,但有的则可能还不能归结为奴隶制和农奴制,他们在原始共同体解体后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但还拥有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502页)还有一些人是封建主的侍从,虽然他们本人拥有土地和农奴等财产,只把个人服务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但这种统治和侍从的关系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占有关系”。所有这些,按本文所持观点,都可以构成十分不同的生产方式,但只有少数几种可形成以它们为主导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马克思在《形式》一文中所讲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社会形态;第二,比较而言,在历史上独立的“社会形态”的类型是有限的而“生产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就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一一加以对应,因为这里会因此引发出两种可能性:同一种生产方式可能有不同的社会形态与之相适应,而同一种社会形态也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生产方式。
(9)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如何区别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区分不同的“生产方式”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比较注意所有制的不同,以为它就是造成不同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但若进一步问,不同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人们在生产中所采用的“劳动形式”之不同,进而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之不同造成的。在《形式》中的一个注中,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对公共财产的这种占有方式可以发生十分不同的历史的、地域的等等变化,这要看劳动本身是由每一个私人占有者孤立地进行,还是由公社来规定或由高居于各个公社之上的统一体系来规定。”(第478页注①)这里所说的“占有方式”可以视作“所有制形式”的同义语,而“劳动本身”如何进行的问题,则可以理解为“劳动的形式”或方式。为何所有制形式要由劳动形式来决定呢?因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0页。)据考证,这里的“占有”一词,马克思是用的Aneignung,此词是从动词aneignen变来的,有攫取、占据、占取等意,表示的是一个与生产有关的过程。(注: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见《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366页。)因此,所有制形式也好,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也好,进而整个生产方式也好,仅从所有制上来观察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它们究竟采取何种劳动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言:“靠资本生活的劳动者和靠收入生活的劳动者之间的区别,同劳动的形式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区别就在这里。”(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76页。参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第12页。)
最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形式》一文原本没有小标题,现有的小标题是俄文版编者后加上去的,这些小标题因此,读者在阅读现在流行的版本的同时,适当参阅不带小标题的马克思原文译本,或许不无助益。(注:从这个角度看,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知译本,仍有参考价值。)。
标签:所有制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亚细亚论文; 农奴制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