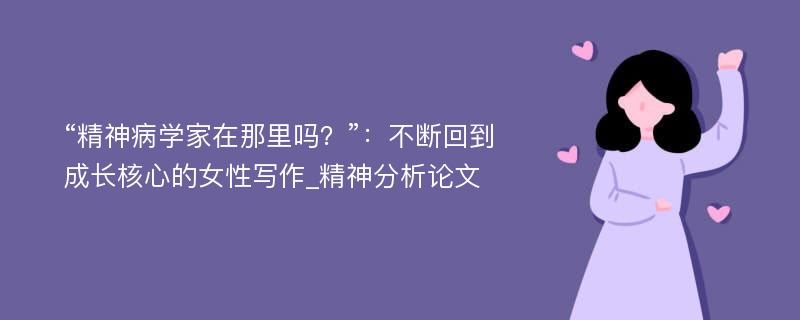
《心理医生在吗》:不断返回成长核心的女性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医生论文,核心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1-0092-05
严歌苓的小说最近五六年高密度地在国内陆续出版,已构成当代长篇创作中引人关注的现象。①
《心理医生在吗》2009年3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是严歌苓1998年的旧作《人寰》重新出版时新取的名字。《人寰》1998年在上海《小说界》第1期发表后不久,即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同年获得第二届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大奖,2000年获得第五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但评论界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专题的研究论文至今不过六七篇。如今另取新名重新出版,显示出作家自己对这部带有自传性长篇的偏爱,这个新名字更直接、通俗,也与作品内容更为贴切。
一 精神分析层面的解读
严歌苓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作家,一个工匠般的专业写作者,她一系列长篇小说《扶桑》、《雌性的草地》、《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寄居者》、《赴宴者》大都以一个女性主人公为中心,既体现出严歌苓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也体现出一个专业写作者高超的虚构才华。在这些小说中作家自己的性情、主观喜好等是严格摒弃开来的,她一丝不苟、细心而客观地投入到对女性生命传奇的勾画之中,相比之下,少数长篇像《穗子物语》、《人寰》(《心理医生在吗》)、《无出路咖啡馆》大致可以视为是基于自身体验的写作,对于真正热爱严歌苓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更让人觉得亲切。当然,《一个女人的史诗》因为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在表面的虚构和情节的编织之中蕴涵了深层属于作家自己的情怀。在严歌苓的许多短篇小说中,这种非虚构的成分更多,一些基本的体验改头换面地不时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心理医生在吗》正属于这种不断出现的严歌苓生命体验的集大成者,是阅读严歌苓所有小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严歌苓自己也特别看重这部作品,获得“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大奖”之后,严歌苓曾说:“坦白说,如果这回《人寰》没有得奖,我可能会渐渐地放弃写作了。”[1]
这也是这里对这部12年前发表的小说作出重新解读的一个坚实的理由。
目前很少几篇评论《人寰》的论文,几乎都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和评价这部作品的。对于这本小说来说,这种思路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因为它叙述的就是一个“病人”对她的心理医生的几次叙说。在“我”的叙说之中,还不断掺杂着弗洛伊德、荣格、恋父情结等名词。严歌苓也毫不讳言自己是1996年在美国向一个女心理大夫支付了三个月的诊疗费之后才心有所悟,写下这部小说的。[2]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阅读这部小说,可以简单概括就是:对恋父情结的审视。这也是目前几乎所有论文的主要论述重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郝海洪的论文,论文三个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恋父情结”、“伊底的躁动和利比多的投射”、“超我:性压抑的转移和升华”,[3]完全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之下作出的一次中规中矩的解读。
一个45岁的女子在追述她的情感历程,她这样从一个6岁的小女孩到中年半生之中对比自己大24岁的贺叔叔的爱情,到美国之后与大自己近30岁的舒茨教授的情人关系,两次这样的情感经历,当然只有恋父情结可以解释。但是,这种解读也因此完全停留在小说表层。
即使是从精神分析的层面,为论者忽略的东西,恰恰不是恋父情结中对年长男性的情感本身,而主要表现在与母亲的关系的理解上。在《心理医生在吗》之中,母亲一出场就带着某种揶揄的色彩,她对这种家庭奉献和牺牲的同时为丈夫和女儿粗暴地否定。对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有这样的理解:“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禀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4](P78)父亲不爱母亲,其实更多的是经历了父亲拨乱反正之后的情感危机的“我”的事后体认,在这里多年后被置换为少年时的潜意识。母亲不爱父亲,则更属于少女时期某种隐秘的心愿。在小说中,“我”的记忆中很少有母女关系温情的部分。我已近中年,这时父母也已离婚,在女儿眼中母亲形象是这样的:“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4](P178)对父亲那个小他20多岁的“新夫人”,“我”没有任何不恭敬的、揶揄的描绘,反而在后面被堂而皇之将名称改为“继母”。父亲如愿以偿和比自己小了很多的女性结合在一起,这个从小就有着强烈恋父情结的女子,在她心目中,值得认同的爱情也只是这种男女年龄相差极大的爱情和婚姻。在她的潜意识里,这个按常理她本应该鄙视的“后母”,可能正是她自己的心愿得以在内心中隐秘实现的替代者!父亲和年轻后母的婚姻,在“我”的内心,似乎是我对贺一骑的爱合法化的象征。即使是这一点明显关乎恋父情结的内容,在以前的专门的精神分析层面的分析中也没有得以指出。
尽管恋父情结和精神分析只是这部小说表层的东西,但是,精神分析本身,还是给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值得肯定的变化。以往的论者论及《人寰》,都没有涉及严歌苓的《屋有阁楼》、《阿曼达》和《我不是精灵》这三部短篇小说。这几部作品同样涉及年长男子和少女的“爱情”,这几部作品的存在,可以确认这种恋父情结对于严歌苓这位作家心理特质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确认《心理医生在吗》作为体现作家严歌苓核心的生命体验集大成者的重要位置。但是,这几部短篇可以视为长久的恋父情结不自觉的流露,而长篇《心理医生在吗》则是对恋父情结本身有了清晰的体认之后所做的“精神分析”,这也带来这些作品的不同。《屋有阁楼》、《阿曼达》和《我不是精灵》基本上处理为外在的事实和情节的推进,而《心理医生在吗》则一次次自愿又带着不易觉察的抵抗,沉入“我”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地方。这是精神分析带给严歌苓的小说创作积极的东西。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很多的潜意识,在45岁回首之时,已发展转换成为清晰的意识,这其实是一次不需要心理医生出场、心理医生也确实从未出场的治疗。成长的记忆与现实的纷乱纠缠着进入倾诉,回顾和倾诉本身就是自我的治疗,一位45岁的女性,她需要这一场盛大而郑重其事的倾诉的方式和姿态,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以求面对此后的人生。与其说这是治疗,不如说是整理、告别和开始。从这种意义来看,精神分析对于《心理医生在吗》这部长篇小说,也可能只是一个精致的幌子。
二 不断返回成长的细节
小说交织着讲述了两段轻重有别的爱情,一段是与大自己24岁的贺一骑贺叔叔长达近四十年,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性爱,一段只有半年,在美国与70岁的系主任舒茨教授由性开始的爱。而在小说中,我和同年龄的丈夫宋峻短暂的婚姻,缺乏必要的爱情的交代。这是人生中不正常的、却又无力自拔的爱,以致在“我”的讲述中,数次出现“自杀”这个词,可以想见这种爱情带给“我”的心灵重负。这是“我”去找心理医生的缘故。
在不多的几篇研究《人寰》的论文中,陈思和的解读别具眼光地着重于小说中贺一骑和“我”的父亲这两个男性主人公身上,从而将这部小说解读为“这毕竟是一部纠缠了几十年政治风雨,包容了难分难解的伦理因素的东方男人的精神史,让一把个人主义的小刀在上面划出了一道道口子,流出的人性汁液竟是如此的鲜活斑斓。”尽管涉及了“个人主义”、“人性汁液”这一层面,但陈思和的论述主要是在“东方男人的精神史”,偏重于小说对特殊年代政治与人性纠缠的景观,也因此,他对小说中精神分析层面的内容有所保留:“不过我不认为叙事者在叙事中一再提到弗洛伊德理论是适宜的,一个病人不应该是读了弗氏的书再去接受暗示式的自我分析。从整体解构上说,11岁的小女孩在火车上遭遇的性的感受作为全部心理治疗的病因似乎是叙事人早就安排好的结局,这就违反了被暗示的逻辑,而且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也不足以成为病因的理由。”[5]2009年,严歌苓将这部《人寰》改名为《心理医生在吗》重新出版,更加强化了精神分析这一块,看来她并不认为是不适宜的。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是一个精致的幌子,但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恰恰是严歌苓别致而出人意料的地方。那么,她的用意到底何在呢?
《心理医生在吗》中大量出现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分析大师的理论,一个病人,已经熟知精神分析的主要内涵,这种在三个月时间内向心理医生付诊疗费的事件,可能就只是徒劳,不会对她的心理困扰产生真正有实质性意义的东西。但是既然严歌苓强调自己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熟稔,而不是浅尝辄止,那么对作品的把握也还得从弗洛伊德出发。
小说共有七章,却在第一章中,就将整部小说所有的主干性事件全盘托出。6岁、11岁、18岁,这样一些关键性的记忆时段全部在45岁时的回顾中呈现出来。后面的六章只是不断返回到这些少年岁月,使得这些记忆逐渐清晰、明朗起来。小说的最后,通过那个从未露面的心理医生对我的催眠,展示出11岁在卧铺车上贺一骑对假睡中的“我”进行抚摩的场景,无疑是这种记忆逐渐清晰化所达到的一个早已存在于“我”心中的高潮。但是,正像陈思和教授所论,这种安排“违反了被暗示的逻辑”。
问题是,对弗洛伊德下过那么多功夫的严歌苓,真的那么相信催眠吗?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特别强调在治疗之中的“移情作用”,第27讲的题目就是“移情作用”,心理病人只有在对医生有可能产生移情作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最终透露内心真正的、甚至有可能被她自己所遗忘、成为潜意识的东西。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弗洛伊德不信赖被很多心理医生看重的催眠术,而催眠中恰恰有一种抑制的力量在活动着。他认为:“催眠术的疗法想要将心中隐事加以粉饰”,“因为我们已将暗示的影响追溯到移情作用,所以你们更可知催眠治疗的结果何以如此地不可靠”,[6](P364、P365)在小说里,最后的催眠之所以是一个更为精致的幌子,它让熟悉精神分析的人会想到更多一点的内容,就像那位从未出场的心理医生,一切都早已在记忆之中,而远远不是什么潜意识,只是因为它太重要、太私密,在少女的成长之中成为最核心的事件,她不愿那么轻易地将它和盘托出,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断续、隐约的叙说,谨慎而缓慢地重新走近它。她要用精神分析的外衣紧紧包裹着成长的岁月,从而得以心安理得地将每一个细节加以细细体味,回顾,确认。
由此看来,成长本身,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题。表面的精神分析,一段长长的有着强烈恋父情结的爱情,一段短暂的婚姻,这些都是成长的题中之义,这些男人们,连同父母,在更多的意义上只是因为参与了我的成长,才显得那么让“我”难以释怀。
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着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4](P120)
这是我要他明白的。或许我根本不在乎他明不明白。我希望他知道:我成长得很好。
或许我想让他知道:一份美好的成长一直擦着他的边在溜走。[4](P142)
在小说叙述推进到后半部分,这样两段关于成长的言说终于不经意间出现。对贺一骑长达三十多年不正常的爱,主要因为它是“我”成长的见证。贺一骑在我11岁时,用不能自抑的方式让我感知了性的气息,在我18岁时,则成为我青春激情的寄托,此时,在这种爱中,和所有少女的成长一样,除了幼年的记忆之外,也有那个时代塑造的整体氛围的影响,英雄式的男人,受难的男人,沉默压抑自己的男人,在18岁少女眼中闪烁着特殊的色彩。故有论者将之称之“爱慕的政治”[7]。在“我”从知青点去贺一骑劳改的瓜棚看他时,贺一骑明白:“这女孩是痴的,是不要命的。”[4](P137)从一个中年男人的眼光,他明白这个18岁少女汹涌的激情意味着什么。它不能堆积在心里,需要发泄,需要寄托,需要通过奉献来确证自身,这也是贺一骑无法呼应这种爱,因而让“我”深感失落的原因。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却压抑晦暗的爱情,这更是一个女孩平淡如水却又惊心动魄的成长。在那么晦暗、压抑的时代,严歌苓却在小说中用了“一份美好的成长”这个词语,这之中,有着深深的岁月感叹,有一种回首之时对成长和青春的充满追怀的祭奠。
三 不是创伤,而是美好的成长
这样“一份美好的成长”,它当然不会是按照精神分析来看可以确知的11岁时在卧铺车厢第一次感知成年人的性抚摩所遭受到的“创伤”。对弗洛伊德来说,丢掉催眠术才可以开始真正的精神分析,对于《心理医生在吗》来说,只有抛开小说最后在催眠术中呈现出来的11岁时遭受的“性创伤”的观念,才可以抵达它精神层面的核心部分。
严歌苓的短篇小说《屋有阁楼》中,展现的是父亲的精神迷乱,身在美国的申沐清,耳边每晚总出现隔壁女儿被洋女婿性虐待的声音,第二天却发现女儿女婿依然很亲密。最后,父亲偷偷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有这样的问话:
“你有没有想到……”医生开口道:“你对你女儿的感情……”医生改了口:“你在小的时候,是不是抚摸过她……?”[8](P152)
医生的问话,使得申沐清在自己文绉绉的一生中第一次出言粗劣:“操你妈!”父亲之所以被这样的问话触怒,在他自己是觉得过于荒唐、无聊和无礼,在心理医生可能就理解为正是神经症症候的一种。这篇写于《心理医生在吗》之前的短篇,已经出现了女孩子幼年被成人性抚摸的观念,但它展示的是其带给成年人的潜意识中深深的困扰。从这个角度来看,《心理医生在吗》中几乎在每一章都会涉及但总是隐约其辞直到最后在催眠术中才真正呈现的贺一骑对11岁“我”的抚摸,可能来源于作家严歌苓的一个心结。这里自然可以理解为逐渐呈现出来的性创伤的精神分析的结论,但是这一事件,却是“美好的成长”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小说在每一章中不断地、犹豫地接近这一个记忆的核心,只是一种强调和郑重其事。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我每每翻到小说的终章,不是震惊或愤怒,也不是出乎意料,而是会然于心地微笑起来。陈思和教授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也不足以成为病因的理由。”但是他是由此而不满意小说中精神分析的内容,却没有进一步探究作家一定要如此这样的用心。这当然不是病因,而是“我”的成长中最核心的秘密,小说在每一章中不断地加深着读者对这一未知事件的关注,最后谜底揭开小说也戛然而止,从中流露出来的决不是记忆中的积年的创伤和痛苦,而恰恰是一种强调,甚或是一种炫耀!
他一寸寸地抚摸她。他的手到之处那寸肉体便苏醒。便是蜕变。她始终在观望他的眼睛从她的形骸内窥视到他的迷恋。对所有她这个年纪,这个生命阶段的雏形女性的迷恋。不止是他个人的,他代表着他那个年龄的男性:所有没有他这份突至的幸运的同类。他粗糙的掌心如树木的剖面,刚被锯或斧剖开,带一股湿气和温暖。
他跪在那里。
她明白她父母,她的家庭同他的关系。那份恩宠和主宰,她的牺牲可能会改变一切。他毁她,她就把他毁了。她惧怕被毁,更惧怕对毁灭的向往。
我那个时候不清楚:我会以这样高昂的代价来解脱那主宰。我翻了个身,把更多部位献出来,牺牲。
他没有过限。他只是看着、欣赏着那些雏形。[4](P120)
这就是炫耀,少年时代美好的炫耀!一份如此生动的成长体验,足以使那个由父母和时代带来的屈辱和晦暗少年时代,顿然从平庸之中抽身出来,也足以使半生的记忆熠熠生辉。
小说中的恋父情结,体现为对贺一骑的情感,对舒茨教授的接受和抗拒。父亲好像是软弱的,可笑的,但是仔细品味,其中也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欣赏,一种骨子里的至爱,在上述情节中,“我”之所以不仅仅是被性骚扰,而同时是在“挑逗”,那是为了对在贺一骑阴影之中的父亲有所奉献。严歌苓还有一个令人叹服不已的短篇《冤家》,女儿即使已经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同性恋者,依然积攒着所有的零花钱给父亲买贵重的礼物,不惜冒犯一切说闲话的人,不惜牺牲母亲的生命!在严歌苓,恋父是少女的一种美好的病,无关乎父亲其人真实的品性。小说中我的恋父情结,另一方面表现为小说中“我”对于母亲始终如一的不乏揶揄甚至讽刺的叙述,母亲在有着强烈恋父情结的女儿心中,总是显得可笑的。但这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详论过女儿在一定年龄对母亲的反叛。在严歌苓这里,女儿之所以反叛母亲,那是因为女儿和母亲之间,其实血脉里、骨子里是相通的。这一次次对异常的成长经历的不断返回,这一份强烈的对于平庸的反叛,恰恰来自母亲。小说中有这样的阐释:
出身市井家庭的母亲,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他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4](P78)
这一份和母亲血脉中相通的对平庸的害怕,对于惊世骇俗的向往,恰恰成为处于成长之中年仅11岁、18岁的“我”的一种潜隐的内心追求。对于严歌苓这个不时将一些基本的生命体验融入不同作品的作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作品中得到启发。短篇小说《抢劫犯查理和我》中说:“对我来说,什么都行,就别一般化。”[9](P42)与《心理医生在吗》精神气质相通的短篇小说《我不是精灵》中,更有明确的揭示,小说中男孩郑炼点醒了“我”对于比自己大20岁的画家的激情:
正是这种不近常理的东西使你感动。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孩。一般少男少女的恋爱你是不满足的。在火车上头回见你,我就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10](P365)
在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对于“不近常理”、“惊世骇俗”事物的向往,对平庸和一般化的强烈厌恶,使得“我”即使在11岁时遭遇“性抚摩”时不致惊慌,反而在默默地挑逗,使得我要在年近45岁之时,仍然要一次次在向那个虚拟的心理医生的若断若续的诉说中,不断接近那一次“惊世骇俗”的成长体验。在小说中,和这种超越平凡的成长内涵相应的,是作家严歌苓追求的感性的、性感的写作,和贺一骑长达三十余年的情感纠葛,没有任何真正的性爱,却写得那么跌宕起伏,充满内心的紧张和触摸的质感,时时挑逗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它所达到的境界,非一般的“身体写作”所能到达和想象。
这就是《心理医生在吗》这部为严歌苓自己珍爱的长篇小说的真正内涵。它不是对于创伤的揭示,不是精神分析,不是真正的爱情或畸恋,而是回顾美好的成长,成长之中超越平凡事物、向往惊世骇俗体验的倾心。因为“我”有幸拥有这一份“美好的成长”,不平凡的成长,它在表面的焦虑之中,恰恰潜隐着不易察觉的炫耀。而作家严歌苓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成长题材的开掘之中,展现出人性的丰富复杂、深邃幽微,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注释:
①近年来,严歌苓已在中国大陆出版了《第九个寡妇》(2006年3月作家出版社)、《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年5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小姨多鹤》(2008年4月作家出版社)、《寄居者》(2009年2月新星出版社)、《赴宴者》(200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另外,严歌苓不少长篇如《扶桑》、《雌性的草地》、《人寰》、《穗子物语》、《无出路咖啡馆》等都得以在近两年在大陆重新出版.
标签:精神分析论文; 恋父情结论文; 心理医生论文; 严歌苓作品论文; 一个女人的史诗论文; 文学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