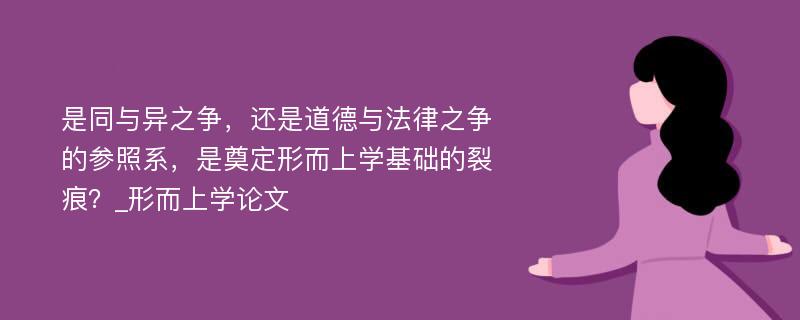
是同一与差异之争,还是其他①——评德法之争对形而上学奠基之裂隙的指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指涉论文,裂隙论文,形而上学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3—0010—09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我在写《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时,已经注意到以伽达默尔、德里达为代表的德法之争,并在此书中用“存在之辨”的一节“回避与拒绝——对Daseinsein-Gott路向的两种态度”品评了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两人的“非同一差异”(德里达叫“不对称差异”)。②
稍后(1990年),又写了《悼词与葬礼——评德法之争》,③ 当时主要根据的文本是Herta Nagl-Docekal和Helmuth Vetter编辑的德法之争文集第2卷《主体死了?》。④
十六年后,即本世纪2004年,孙周兴编译了《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出版,并在“后记”中指出:“汉语学界对此轰动一时的事件也有过一些议论,惜乎有关争论文本一直没有被完整而准确地移译成中文。”⑤
所谓“轰动一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伊始发生,一直延伸到九十年代的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启蒙理性”或“现代性”是“亟待完善”,还是“已经破产”的所谓“后现代之争”,连美国的罗蒂也卷了进来,长达十余年之久了。
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思潮总是响应热烈,然而对德法之争,除了后半段的“后现代”在文学界炒热了一阵外,哲学界呢,大概只存活在某些关注它的人的心目之中,寥落得很。不知何故?
说是对“虚无主义”的热衷吧,未必;说是对“形而上学”的眷念吧,也未必;或许是不谙深浅、不求甚解吧。
换句话说,我们自身并没有一次对“形而上学”的认真清理(也没有一次对“启蒙理性”的认真清理)。仅仅说一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主体论已经在语言哲学转向中“过时了”是不够的,即便你进一步说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不成立”或被别人“批倒了”,甚至你也“参与”其批判之中,如果你不能有起码的正当有效的防御机制,归根结底,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很快又在反虚无主义的各种理性主义意识形态中卷土重来,更强势地重新确立起新的合理性。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此两极摇摆,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家常便饭。我们也就把别人的习惯当成了正经。
在如此反反复复地摇摆习惯中,对“同一与差异:德法哲学关系”的主题讨论,又该作何期待呢?
(一)
孙周兴在“后记”中描述了一个事实:
德里达在《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的报告中,“对伽达默尔未提一字。虽然如上所述,德里达的论题还是切中要害的(实际上对伽达默尔哲学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但在场面上,他的报告仍让人觉得他无视伽达默尔这位在场者的存在。”⑥
如果撇开例如年龄性格修养类型的差异不提,甚至也不谈礼貌,仅按对话的规则看,德里达肯定有欠妥之处,伽达默尔抱怨这是一次“非对话”完全有理。但是,德里达真的不懂“对话”吗?
从“善良的愿望”看,问题不在于台面上的德里达与伽达默尔对话与否,而在于,对话本身究竟在或应该在哪个层次上交手?
既然伽达默尔自己都说哲学解释学是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的后继与发展,而且是在“艺术”、“历史”和“语言”的维度上要求解释学内在循环的普适性延伸,那么,德里达根本要追问的恰恰是作为此等解释学普适性前提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者存在的整体性如何可能?所以才有对海德格尔《尼采》解释的“专名”与“整体性”的置疑。德里达的策略是同“原因”作战(周兴指出是“釜底抽薪”),作为结果的伽达默尔解释学自然也就摆在“结果”的台面上纹丝未动。
伽达默尔是否是海德格尔的“后继与发展”,我在别的场合理论过了,这里也照样不去动弹它。顺便说一句,我对伽达默尔始终怀有最“善良的敬意”。
先接受这个事实:所谓“德法之争”,根本发生在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之中,确切地说,发生在海德格尔的文本言说与德里达的文本解释之中。
但是,海德格尔毕竟不在了,德里达的“报告”不得不把海德格尔置于“缺席审判”的地位。
德里达的述说方式包括对词语“取向立义”地使用,非常特别,连讲究对话应该在母语内进行理解与解释的伽达默尔,况且对德里达法语陈述的浪漫气度莫衷一是,再移译成中文,恐怕就难免把德里达式的浪漫变成堂吉柯德式的滑稽了。
所以,我这里的叙述整个是冒险的,与其是针对德里达,不如说是针对中文“德里达”——属不属于德里达的“专名”如“德里达们”呢?
没有回应。德里达阁下也缺席了。我对德里达同样怀有最“善良的敬意”。
有时,对话真难免某种程度的自说白话。例如,德里达同海德格尔的对话,很大程度是德里达同“德里达的海德格尔”对话,这里还要通过“德里达的尼采”做中介。
海德格尔早就提醒读者对“第二格”的魔鬼习性保持警觉。所谓“魔鬼第二格”(der/的,或底)是非常令人晕旋的语言现象。不独德语、法语,汉语亦然。
“德里达的尼采”中的“德里达的”既是“主语第二格”,又是“宾语第二格”。所谓“主语第二格”是说“尼采”仅属于“德里达的”(应写作“—底”),推到极至,它甚至完全可能是德里达的杜撰、虚构,与尼采无关。如果归根结底与尼采有关,那么,“德里达的”基本就是“宾语第二格”(应写作“—的”),即表示“尼采拥有的属性”:“尼采的属性”可以是多样的,德里达仅选择其中之一而予以强化了。在这个选择强化的意义上,“宾语第二格”中又隐含着“主语第二格”的倾向;其倾向有一个很大的区间值可供游动,依选取者即解释者的取向立义强度而定。越界的情况如虚构,太离谱了,不属此论。
德里达虽然注意到“第二格”(der)的延异性质,但好象对其魔鬼习性缺乏足够的警觉,以至偏爱做一厢情愿的解释。请看德里达对海德格尔这句话的解读:
“‘尼采’——我们用这位思想家的名字作标题,以之代表其思想的实事(Sache)”。⑦
德里达分析,所谓“思想家的名字”中的第二格表示的是“作为其思想的实事”,即作为“宾语第二格”的属性:意即“名字”仅仅用来指称专属尼采的“思想的实事”。但是,海德格尔却在往后的解释中改变了侧重点,“‘尼采’这个专名不能被看作某个个体或者签名者的专名;它是一种思想的名字,其统一性恰恰反过来赋予这个名字以意义和指称。”⑧
德里达批判的眼光在于,海德格尔的论述突出了一种倾向:作为“思想”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实体化了,它所表现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选择了尼采,并赋予“尼采”这个“专名”以意义。而不是相反,尼采“这个人”本来具有很多属性和面具,因而“思想的”只能是尼采的“宾语第二格”。现在却变成“思想底”反而做了尼采的“主语第二格”。海德格尔之所以转变其侧重点,盖因其将“思想”“逻各斯中心主义”化造成的倒果为因。
再说白一点,“尼采”作为个人的专名,应该具有唯名论倾向,换成德里达的书写理论术语:“尼采”这个书写的专名词语,其下面是无底的棋盘,因而其意义不仅是“延异”的,而且还是“播撒”的、“无限增补”的,根本就没有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或实事或意义)规定该词语的“形而上学同一性”。
这就是德里达批判海德格尔尼采解释的思想背景。“尼采”是这样的一个“专名”,它下面没有实事“整体性”和意义“同一性”,因而“尼采”就是“尼采们”——一个杂多的“延异”、“播撒”、“增补”的无限过程。与此相反,海德格尔把“尼采”变成了“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即“形而上学思想”规定了实事的整体性和意义的同一性。在德里达看来,至少不符合尼采“这个人”的事实。
结论,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说错了,反暴露了他自己才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
从德里达用于批判之前提的“德里达式规定性”看,的确如此。
但,世界并不是由“德里达式规定性”构成的,具体地说,海德格尔词语也并不一定非得按“德里达式规定性”书写或解读。德里达应该对自己的“书写”留有“例外”的余地。否则,你如何解构你自己的书写呢?须知,你的“解构”已经构成了一种“暴力”,而暴力总难免会落入“剥夺者被剥夺”的反讽境地。
(二)
俗话说,“有多少个《哈姆雷特》的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这看来很符合德里达书写词语的“无限增补说”。
但是,“有多少个《哈姆雷特》的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毕竟又是“有多少个《哈姆雷特》的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大概决不会有《哈姆雷特》的研究者把“哈姆雷特”研究成“堂吉柯德”的。“哈姆雷特们”不就是“哈姆雷特们”吗?
所以,至少在“专名”的意义上,“无限增补”颇有点像π(派)的极限无限性——再怎么无限也越不过π(派)的极限。同样道理,“尼采们”再怎么无限增补地多,归根结底还是“尼采”,即还是那个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尼采。“超人”是用“权力意志”签名的——有限摹状词签名。
其实,德里达用“签名”立论并不恰当,“签名”是“书写”的特例,只要签名是签名,不管是实指对象,还是摹状意义,有限也罢,无限也罢,“名”之极限则是规定性的,即外在的同一或整体已被“名”设定了。例如,黑格尔曾说“骆驼与铅笔”是没有同一性的,但如果由一个花果山的猴子签名为“孙悟空”,它就能把“骆驼与铅笔”同一到自己的名下。“孙悟空”不算签名吗?“哈姆雷特”为什么算?
还是针对思想或思想的书写吧。尼采的思想当然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基督教“上帝创世”的世俗化完成——一个纯粹的“白色神话”。尼采的“权力意志”多少应看作“虚无”之上的“超人”“重估价值”的“轮回”舞蹈。这个陈述有意把尼采的“五大主题”囊括了。尽管有“五大主题”,“权力意志”仍然高踞中心,而且中心到“献媚狄奥尼索斯新神”的地步。哪里有德里达说的“既没有整体又没有对立”的“毫无防卫装备”的“疯狂”?
何况尼采的新神——掌管“权力意志”的狄奥尼索斯,其“永恒轮回”恰恰是超越生死的“优先性”。而“权力意志”作为“生成性的存在”是要无限趋近作为“存在者”的“权力意志者”的——在无限趋近的颠峰意义上,“权力意志”与“权力意志者”不正好是生成着又毁坏着(“剥夺剥夺”)的差异与循环吗?即便如此,尼采还是坚持了“权力意志”的循环中心思想,否则就不是“尼采”了。
坚持“差异”的德里达,应该区分三种差异:
“同一性差异”
“非同一性差异”(“不对称差异”、“无对立差异”、“非辨证的不一致”、“近乎并置的关系”都是德里达寻找的外在特征)
“悖论式差异”
前两者是可以在内外设定为同一的,惟有第三者才是同一与差异自身的悖论,既是“同一”自身、“差异”自身,又是“同一与差异”自身(“之间”)的悖论。德里达只注意到并终止在“非同一性差异”的外在性上,妨碍了他进入哲学史上真正的“临界状态”。⑨ 所以,他迷恋自己的“解构主义”形象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极不情愿被误认为是“虚无主义者”的德里达,却一生穷于应对“虚无主义”的诘难。
(三)
上面是1981年发生的事。
1993年,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中⑩ 几乎毫不相干地又顺便把海德格尔捎带了一下。
事因起于美裔日本人福山于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如果历史真的终结了,自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自然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而最终消失了。
德里达当然不相信福山这位柯耶夫“门外弟子”的结论。在他看来,欧洲的历史“从来不曾远离俄底浦斯和哈姆雷特”。(11) 因而哈姆雷特的境遇“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已成为欧洲人的精神遗产,并被马克思用更强烈的方式——“共产主义幽灵”即“马克思的幽灵”——表达出来。福山从血缘上看,当然看不见“父亲的幽灵”,听不到这笔精神遗产游动在旷野的“弥赛亚呼唤”,所以当他以西方人自居出来宣布这个“幽灵”完结时,德里达就不得不向他讲一讲“幽灵”的历史——《马克思的幽灵们》。怎么讲,不是这里要说的,我只关注与本文相关的段落。
德里达以他特有的方式讲到哈姆雷特的言说与莎士比亚的书写:“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个名句的法文怎么译?关键是其中的“Out of joint”(“脱节”)如何在法文中表达其义?
有译成“乱了套的”,有译成“令人沮丧、萎靡不振的”,有译成“颠倒的”,有译成“声名狼藉的”,总之,德里达感慨地说:“根据这个例子,人们便可以领会到奥斯汀曾经说过的意思的必然性,辞典根本不能给出定义,只能提供例证。”(12)
不仅如此,德里达的感慨大了: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一个脱节的、错位的、断裂的时代,一个出了毛病的、走投无路、精神错乱、疯狂和没有秩序的时代。这个时代彻底乱套了、完全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自身,紊乱不堪。这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意思。由此他就为那些通常是诗与思的窥视孔打开了一个缺口,通过这一缺口,莎士比亚既俯视英语的语言系统,同时也可以用同一史无前例的手法标识出它的存在。那么,哈姆雷特是在什么时候以这种方式不仅命名了时代的脱节而且命名了历史和世界的脱节,命名了所有一切的脱节,仿佛它们是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的失调,是我们所有时代的失调?”(13)
莎士比亚“俯视英语的语言系统”造就了这样一个后果:释放出一个“语言幽灵”为的是“让记忆和翻译成为游魂”。(14)
还不仅如此,莎士比亚让哈姆雷特在生不逢时中诅咒自身,即先行地预设了哈姆雷特自己与自己脱节。“他诅咒的是自己的使命:匡扶正义,复兴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15) 包括“匡扶正义”的手段“复仇”,不得不采取“赎罪本身的赎罪”即“以恶抗恶”这一“倒霉的”形式。(16) “只有以这种本源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以罪行的这一本源的和真正幽灵般的先行存在为先决条件,才会有悲剧,才会有悲剧的本质。”(17)
所有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文学性铺垫恰恰指向并显示出历史和世界之基底的幽灵般的“脱节”(Dike)——它来自古希腊的俄底浦斯和古希伯来的约伯。(18) 不,还要早,“对于这种特殊的拓扑学,最敏感的——尽管肯定不是唯一的——场合之一在今天也许就是《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19)
(四)
海德格尔出场了。德里达说:
“海德格尔在这本书中将Dike解释为协调或和谐的连接点、毗连点、嵌合和关节,解释为Fug(理由)和Fuge(裂隙)(Die Fuge ist der Fug——这种裂隙是完全有理由的)。就其乃是以在场为基础的思考而言(als Anwesen gedacht——作为在场者的考虑(20)),Dike能以某种方式和谐地把连接点和协调结合在一起。相反,Adikia,即是分离的、断裂的、扭曲的东西,又是非正义的过错甚至愚蠢的过失中的不协调的东西。”(21)
Fug,按辞典义:“理由”。但海德格尔会按辞典义使用Fug吗?Un—Fug,岂不成了“非理由”?Die Fuge ist der Fug,如果译成“这种裂隙是完全有理由的”,海德格尔读“阿那克西曼德箴言”所听到的“在之召唤”——“裂出即是嵌入”的二重性——荡然无存了。我实在无法判断,这里的问题是来自法译文,还是来自中译文?
不过,Fug和Fuge的翻译也真是一个问题,如果要译作名词,就像现在各方表达的:Fug——“关节”之“接缝”、“嵌合”;Fuge——“关节”之“裂缝”、“裂隙”。双方根本没有差别。差别是后来引申出来的,主要是德里达的理解和解释:海德格尔要把“裂隙”“嵌合”起来“归属于统一体”,而德里达则坚持“保存裂隙打开裂隙”,以便敞开无限可能性。这个引申出来的“解释”暂且放到一边,稍后再回到这里来。先看双方相同的名词性翻译。
名词性翻译隐含着一个问题:“关节”或“关节点”,不管是接上也好(“嵌合”),裂开也好(“裂隙”),两者的行为总是针对“第三者”而言的,那“第三者”是什么?是本来的“始基”基底(——形而上学“本体论”)?它发生了裂缝,需要接起来,不接起来就要裂开成碎片,还是本来就是“裂隙”(——形而上学“虚无主义”),现在要把它连接起来,否则就会陷入深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德法之争,争的就是这个“第三者”孰谁?
还有没有另一种译法?比如,作动词译,或当动名词书写,又将如何呢?海德格尔的思维风格本来就是将“形而上学概念”还原为“动词状”的(即“动词—分词—动名词”)。如果是这样,其意义或意指所在,恰在于作为“生成”的“存在”本身之运动,属于海德格尔的这类描述已经有“存在论差异”、“显隐二重性”、“遮蔽—去蔽—解蔽”等,再加上读《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时的“嵌入—裂出”。总之,除了“存在”本身之差异运动外,没有任何“第三者”需要指涉的。而且,这个差异本身总显现在“之间”中。“之间”(Zwischen)是个非常怪异的词:它既是“关系项”的指涉——“某与某之间”,又是“关系”本身的指涉——“关系”不是辨证同一的,而是二律背反的。这“之间”,海德格尔叫做“存在论差异”,德里达叫做“非同一差异”或“不对称差异”(如前所述,极易滑向恶无限的虚无主义),我则干脆把它叫做“悖论式偶在”。
不同译法基于不同理解。我们已经进到罗陀斯地了,就在这里跳吧!
(五)
上面的引文表示,德里达其实抓住了海德格尔的思考脉络:“海德格尔在这本书中将Dike解释为嵌入,解释为Fug(嵌入)和Fuge(裂出)(Die Fuge ist det Fug——裂出即是嵌入)”。(22) 这种“裂出即是嵌入”的二重性,正是海德格尔从最古老的“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中听到的召唤,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海德格尔这个人——“人是无意指的指号”——所指向的“存在之路”。
可惜,“其实”还是一个“应然”,抓而不住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请看德里达做了怎样的评述:
海德格尔说:“Dike,aus dem sein als Anwesen gedacht,ist der fugend-fuegende Fug.Adikia,die Un-Fuge,ist der Un-Fug.”(23)
(试译:用来推想作为在场者存在的Dike,起着连接着—弥合着的嵌入作用。而Adikia,则〈意味着之间的罅隙〉即非裂出是非嵌入。)(24)
德里达解释说:
“我们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正如海德格尔一直所做的那样,实际上,为了他阐释为利益本身、被赠予的利益,亦即在协调(Versammlung,Fug)的同时能够集中或汇集的一致的可能性的东西,其实那东西就在差异或不一致(differends)的同一性中,就在一个所谓系统的合题之前——海德格尔难道就没有偏离非对称性吗?”(25)
德里达在说了“裂隙”中其实蕴涵着——“深渊似的荒芜”,那里缥缈着无可辨识的弥赛亚游魂,但毕竟是赠予着无限可能的机会与永不失去的承诺,这正是“马克思的幽灵们”延传着的西方精神遗产——之后,立即转向责备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就冒了这个险,尽管他的确保持了必要的谨慎。正如他常做的,他赋予集合以及同类的东西(Versammlung,Fuge,legein等等)以优先性,认为它们要高于我曾经在致另一个人的信中提到过的断裂,高于由关系控制并转而又控制关系的遮断物,高于其独特性——播撒于混有骨灰的绝对物的不可胜数的焦黑的碎片中——在唯一中不可能得到确证的差异。”(26)
堪称怪才的德里达偏偏在批评海德格尔时充满了常识的智慧,因而能赢得广泛的同情。例如,国内有些学者沿着德里达的解构眼光把他们的差别鲜明地定格为:海德格尔旨在弥合缝合聚合这个“裂隙”,为了存在的“整体和同一性”;而德里达则“保持裂隙、打开裂隙”,其“解构试图赠予我们以关于开端、未来、历史的别样的可能性的思想。”(27) 这就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解构在中国留下的如此面貌。由此可见一斑。
从表面上看,这是非常自然的差别:一个要合,一个要分。二值逻辑,非此即彼。德里达尚且如此,谁能跑得掉呢?
可是,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声明的“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的努力,(28) 有人注意到了吗?
用不着翻阅海德格尔的大量著作,就在德里达阅读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同一本书里,海德格尔通篇都在“指引”——“迷途指津”。
(六)
海德格尔对“箴言”考证后的译文,或者更准确地说,海德格尔按访问“存在”之“口授”的辨析所归属的“阿那克西曼德箴言”部分:
……entiang dem Brauch;gehoeren naemlich lassen sie Fug somit auch Ruch eines dem anderen(im Verwinden)des Un-Fugs.(29)
“……根据用(守护着);也就是(守护)它们听任嵌入(忍受)裂出从而一个被另一个牵引地相互拥有。”(30)
此德译文可看作海德格尔式读经将“(形而上学)概念”还原为“(初始经验)词语”的典型案例,即除了“Brauch(用)”在听召唤的“(用手)守护”意义上与人相关,被其他译家解读成的法律道德术语如“Fug(正义)”、“Un-Fug(不正义)”之类以及心理术语“Ruch(顾虑)”等,海德格尔一概还原为“存在本身的状态”(所谓“动词分词化”),如“嵌入”、“裂出”、“牵引”。
这种还原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德里达一方面严重关注海德格尔沉思所具有的穿越时空的透视所在,另一方面也毫无顾及地要做一番自己的改造。他在解释中,不仅沿用着“正义”、“惩罚”、“复仇”之类,而且还加进了“经济禁区”、“流通命运”、“市场过剩”、“贸易逆差”、“债务”、“超越压抑”、“神经官能症”这些时尚辞令,才华横溢。(31)
当然最重要的关键词是Dike,Adikia,海德格尔将前者译成der Fug(“嵌入”,孙周兴译成“嵌合”),将后者译成die Un-Fuge,ist der UnFug(“非裂出是非嵌入”,孙周兴译成“非嵌合”、“裂隙”)。
就词语翻译选择的基本意义,如前所述,德里达同海德格尔好象没有差别,换句话说,他们都发现并承认古老“箴言”中初始经验储存的作为“生成性的存在运动”。问题在于,在对海德格尔文本的通读与解释中,特别是解释取向立义,德里达做了一厢情愿的解释,差别就出现了。
我们也来读一读同样的段落,它就是关于“在场者即当下逗留”(Das Anwesende ist das Jeweilige)的思考。
“a-dikia一词首先说的是:Dike缺席不在。”人们习惯于用“正义”来翻译Dike一词,那么,adikia就是“不正义”了。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习以为常的法学—伦理的观念,“a-dikia说的就是:它运作之处,事情不对头。这意思就是说,某物出于裂隙之外(etwas ist aus den Fugen)。但这是就何而言的呢?是就始终逗留的在场者而言的。可是在在场者中,哪里有裂隙呢?何处有哪怕仅只一条裂隙(nur eine Fuge)呢?在场者如何能够是无裂隙的,即adikia,也即是出于裂隙之外的?”(32)
“a-dikia,某物出于裂隙之外”,其实就是说,“某物脱节了”或“某物裂开了”,不是说“某物从裂隙中出来了”。再由此引申出问题:这是从何说起的呢、根据什么说的呢?在在场者中怎么会有裂隙呢,在场者完整在场,哪怕仅仅只有一条裂隙,如何可能呢?注意下面一句话,看起来像说反了:“在场者如何能够是无裂隙的,即adikia,也即是出于裂隙之外的?”
Adikia,是“无裂隙”的,又即是“出于裂隙之外”的。这里好象把“出于裂隙之外”(“脱节”、“裂出”)又说成是“无裂隙”的了。我且假定孙周兴的译文至少在字面上是按德文直译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看成“自相矛盾”,而是另有所指。联系前面引文——Adikia,die Un-Fuge,ist der Un-Fug(即非裂出是非嵌入)——表明,海德格尔已把Adikia看作不是与Dike表面对立或相反的词,而是看作更根本的“关系”词,而且是前述三种关系中的第三种关系:它既是“关系项”的指涉——“某与某之间”,又是“关系”本身的指涉——“关系”不是辨证同一的,而是二律背反的。即是说Die Un-Fuge ist der Un-Fug(即非裂出是非嵌入)。总之,海德格尔把Adikia看成“之间”状态了。
由是,自然引出下面的话:
“该箴言说得明白,在场者在adikia中,也即是出于裂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者不再在场。……该箴言说的是:在场本身必然包含着裂隙连同出于裂隙的可能性。在场者乃是始终逗留者。逗留(Weile)作为进入离开(Weggang)的过渡性到达而成其本质。逗留在到来和离去之间成其本质。始终逗留者(das Je-Weilige)被嵌入这一‘之间’(Zweischen)中。这一‘之间’乃是裂隙,而逗留者一向循此裂隙从来源而来、向离开而去被嵌入其中了。逗留者的在场向前移动进入来源的‘来’(Her),并且向前移动进入离开的‘往’(Hin)之中。在场按两个方向被嵌入不在场之中。……逗留在裂隙中成其本质。”(36)
这句话很蹊跷:“在场本身必然包含着裂隙连同出于裂隙的可能性”。其中“aus den Fugen(出于裂隙)”不就是“裂隙”吗?为什么要用“连同”重复地说?除非“aus den Fugen(出于裂隙)”并不等于“die Fuge(裂隙)”,它仍带有“从裂隙出来亦即进入”的二重意味。海氏显然利用了这个短语的动词取向的动态,并没有把它固结在名词性上。这样就打开了理解下文的通路。“在场者乃是当下逗留者”的片刻状态了:
“逗留(Weile)作为进入离开(Weggang)的过渡性到达而成其本质。……这一‘之间’乃是裂隙,而逗留者一向循此裂隙从来源而来、向离开而去被嵌入其中了。逗留者的在场向前移动进入来源的‘来’(Her),并且向前移动进入离开的‘往’(Hin)之中。在场按两个方向被嵌入不在场之中”。
所以,在海德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解读里,根本说的不是把脱节的裂开的东西缝合起来恢复其整体同一性,而是发现在场者在场的存在运作是“嵌入即裂出的二重性”。说得通俗点就是,“在场者永远都处在出进之间的过渡状态”,这乃是“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der Unterschied des Seins zum Seienden)运动造成的。(34) 此“差异”根本不同于“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的关键处,它必有差异之间的“罅隙”(我命名为“悖论式偶在”)。
恕本文不再往下引证了。(35)
(七)
海德格尔在许多地方反复地强调,如此这般的“差异”,并非发生在某一个历史时刻(比如德里达陈述的“俄底浦斯时期”,或“哈姆雷特时期”,或“马克思时期”,或当代的“苏联东欧解体时期”),而是它自始至终本有的存在差异运动。(36) 德里达向福山讲述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历史正是从海德格尔那儿传承过来的,只是没有从开端根底罅隙处说得如此久远。所谓“必须在开端处保持裂缝”的思想,根本就是从海德格尔那里来的,只是没有后来德里达所做的单向开放的虚无的解释。
这里很有必要指出,海德格尔的述说方式颇带着苏格拉底遗风,即首先按正当的眼光从接受常识意见出发,如对“非正义”的“正义”整治,然后再从意见自身的可能变式中选取能带动各方的“关键词”如“脱节”,使其成为向各方过渡的生成之源,如从“脱节”中看出“裂出即嵌入”的“之间”。而且,海德格尔用的正是苏格拉底智慧之“知向而不知得”的形式指引法,不论在横向的历史开端,在垂直的生成之源,还是在当下逗留的存在者中,其“带罅隙的存在差异运动式”总会以某种方式显隐着。
说到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思之指引”的所在地。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跟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打交道,或者说在跟“遗忘存在即遗忘存在与存在者差异的形而上学史”打交道,他非常清楚尼采的命题“虚无主义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所揭示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一体性。为此竭尽心力要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也就是“临界状态”。所谓“边缘状态”——既不是选择形而上学本质主义,也不是选择虚无主义,而是寻求抗拒两极摆动的“之间”的生成性罅隙——海德格尔重读哲学史的“回归步伐”一直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赫拉克利、巴门尼德、阿那克西曼德,几乎一路都在检查形而上学奠基的“裂隙”:早期叫“存在论差异”,中期叫“显隐二重性”,后来关注“存在”运作的“遮蔽—解蔽”的显隐过程。一个如此专注而清醒的运思者,难道只是在追求“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如何接缝的“整体同一性”?
德里达之所以把边缘的临界状态简单看作“形而上学眷念”,无非是突出自己的“无底的虚无棋盘”,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进入“‘深渊似的荒芜’,那里缥缈着无可辨识的弥赛亚游魂,赠予着无限可能的机会与永不失去的承诺”。德里达为什么不想一想,他说的这些如果还要有点意义的话,那它就不可能是“深渊似的荒芜”,因为这深渊似荒芜的虚无,根本什么都不会有,连你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没有的。毕竟有了,还是“弥赛亚游魂”及其遗嘱似的承诺,已经被签名为“犹太教一神论”——为什么虚无中一定是“德里达们”知道的“微弱的弥赛亚主义”?本雅明也领受同样的签名?这真的叫“深渊似的荒芜”吗?“解构”何不再彻底一些!为什么偏偏要留一点你想要的东西?
其实,德里达并不意识他自己解释的定向极限性:“荒芜”中毕竟有“游魂”,“不可辨识”终究还是可辨识的“弥赛亚”,“无限可能的机会与永不失去的承诺”仍不外是“西方的精神遗产”,等等,界限规定得清楚得很,哪里有什么绝对“无底的虚无棋盘”?
“虚无的无限”像是“数轴式的无限”,但把“数轴”的主体“定向性”或“定数率”隐藏起来了,以至,要么在书写上恣意于“延异”、“播撒”、“无限增补”而让解构主义滑向虚无主义,要么警醒于虚无主义的辩解而滑向形而上学本体论之源的“一神论”,盖因德里达丝毫没有准备在词语运作上建立起抗拒两极摇摆的防御机制。
如此不要“临界思想”,连康德的“二律背反”都混同于黑格尔的“同一辩证法”,一看见“……根据用(守护着);也就是(守护)它们听任嵌入(忍受)裂出从而一个被另一个牵引地相互拥有”,就认为是与“保持裂隙打开裂隙”对立的、要求“相互归属于同一性整体”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想,从没反省自己乃是受制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学”所累——“非此即彼”,还名之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就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海德格尔再三提醒“逻各斯”与“逻辑学”根本不同,“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事情,即便开创者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走到今天的“逻辑学”这么远。(37) 德里达们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显示其思想上固有的“盲点”。
这是一个现代案例,表明,谱系于临界思想的存在论—偶在论,仍是一个未思的领域。
收稿日期:2007—05—20
注释:
① 本文系作者于2007年5月26日在同济大学“同一与差异:德法哲学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
② 张志扬、陈家琪:《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论语言的空间与自我的限度》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语言之辨的准备性分析”,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1页以下。
③ 张志扬:《语言空间》,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以下。
④ TOD DES SUBJEKTS?R.Oldenbourg Verlag Wien Muenchen 1987.
⑤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德法之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
⑥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德法之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⑦ 《德法之争》,第54页。
⑧ 《德法之争》,第54页,重点为引者所加。
⑨ 关于“临界的、悖论式的偶在”及其“偶在论谱系”我在别的场合有专论,此处不另。
⑩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12)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37、29—30页。
(13)(16)(18)(19)(21)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8、31、31、35、35页。
(14)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8页,稍稍变换了句型。
(15)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9页。这句话使人联想起本雅明在《历史的概念》中援引福楼拜的话:“很少有人会想到,复原迦太基是多么伤心的事。”德里达与本雅明有多少相通之处啊?请参阅萌萌《复活历史灰烬的活火——“曾经”中蕴涵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载《“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启示与理性》第三辑,萌萌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17)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31—32页。俄底浦斯的影子带上弗洛伊德的标签。
(20) 笔者按:“的”字错加,应删去。
(22)(24)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77页。
(23)(25)(26)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39、39—40、41—42页。
(27) 朱刚:《开端、裂缝与未来——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双重解读》,见《现代哲学》,2006年第4期。
(28) 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24页。
(29)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94页。
(30) 中文属我按孙译本的改译,“守护着”、“守护”字样,是我加进的义译或衬字。关于本译文的解读请参阅墨哲兰《有意指的意识与无意指的存在》,见《德意志思想评论》第二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31) 令我想起萌萌读蔻眉《拯救与复仇》分析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所做的读书笔记《记忆中“曾经”的承诺》(见《现代哲学》2006年第3期),非常有益于对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理解。
(32)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74—375页。引用的德文按原文修正。
(33)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74—375页。重点为引者所加。
(34)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6页。海氏的这个标志性短语或许应该意译成:“向存在者趋近的生成着的存在差异”。聊备一格。
(35) 详细论述请参看墨哲兰《有意指的意识与无意指的存在》,见《德意志思想评论》第二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36) 例如,海德格尔在《什么召唤思?》中用“扭身而去”、“自行隐匿”来描述自始本有的存在差异运作。Vgl.VERTRAEGE UND AUFSAETZT Pfullingen:Guenther Neske 1954.S.132—133 ff.
(37)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39页以下。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德里达论文; 尼采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读书论文; 哈姆雷特论文; 伽达默尔论文; 权力意志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