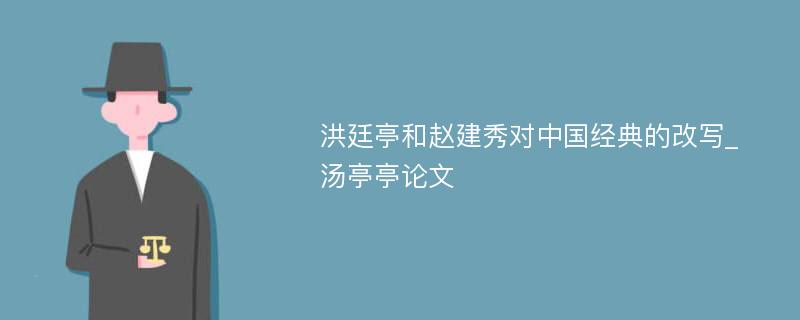
汤亭亭和赵健秀对中国经典的改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典论文,赵健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09)01-0148-04
一、引论:华裔美国文学——一种话语权力的寻求
华裔美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在寻求族裔属性和话语权力。现在被公认为华裔美国文学之祖的水仙花(Sui Sin Far,原名Edith Maude Eaton,1865-1914)在她的小说集《春郁太太》(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1912)中就表现出对美国华裔地位和东西文化冲突的强烈关注。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之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坛出现了华裔美国文学异军突起的状况。
汤亭亭(Kingston,Maxine Hong)是华裔美国文学中最知名的女性主义作家。1976年她出版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蜚声美国文坛,荣获国家图书评论奖。第二部小说《中国佬》(China Man,1980)又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界奖。在华裔美国作家中,汤亭亭是20世纪70年代后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得到了美国主流话语的肯定。她的作品不但进入美国大学文学研究的范畴,而且也编入了美国大、中学校的教材之中;《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和《希斯美国文学史》都收录了她的作品。
赵健秀(Chin,Frank)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剧本《鸡舍的中国佬》(The Chickencoop Chinaman)和《龙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被搬上了纽约的舞台,这在华裔美国作家中都是第一次。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唐老亚》(Donald Duk,1991)和《甘加丁之路》(Gunga Din Highway,1994)等。此外,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华裔美国批评家。1974年他出版了《哎呀!亚裔美国作家选集》(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这本书在美国虽然是第二本亚裔美国文学作品集,[1]但它影响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是这类选集中最突出的。1991年,其续集《大哎呀!华裔和日裔美国文学选集》(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Writers)出版再次引起巨大反响。
本文试图用“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来解读汤亭亭和赵健秀对中国经典的改写。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新历史主义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进行解读,符合华裔美国文学的关注族裔政治权力的作品特性。新历史主义的综合性文化解读,将被形式主义排除在外的文本、历史、社会和权力的关系恢复过来,并作为分析作品的核心问题。其次,新历史主义关注文学的文化背景,着力对文学进行“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文化解读。新历史主义者用通货(currency)、交易(exchange)、流通(circulation)和谈判协商(negotiation)等从经济学领域引进的术语来解释文学传统在文化之间的移植。文学创作也就可以通过拼贴(collage)、戏仿(parody)、梦幻(dreaming)等手法来实现。最后,新历史主义提出文学话语的“颠覆、含纳”理论以及“限制、能动”理论,用以解释文学话语对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对抗关系,并且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文学文本的创造性。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表现出对于双重宰制的抵抗,尤其是对于美国主流的话语霸权的一种瓦解和颠覆。
二、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与汤婷婷、赵健秀的改写主旨
“新历史主义”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话语,美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葛林伯雷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中也强调了这一复杂性。然而,可以肯定新历史主义在阐释作品时继承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潮中强调文学与文本之外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权力等之间的作用关系。其中对于历史的重新关注,使得这一思潮在阐释文本时带来了新的视野。所以当面对东西方文化遭遇的华裔美国文学之时,文学的历史性就应当受到我们的关注。
后现代的话语体系中,人们所能感觉和阅读到的就是由一个个不同文本构成的历史,所以格林布拉特说“历史不可能仅仅是文学文本的对照物或者是稳定的背景,而文学文本受保护的独立状态也应让位于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动,以及他们边界的相互渗透”。这就是新历史主义者所谓的“历史的文本性”(historicity of texts)和“文本的历史性”(textuality of history)相互交融的文学和历史的现代境遇。
面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新历史主义引进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来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后现代思想家把文本的概念泛化,德理达认为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而且“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另一方面巴赫金的诗学之中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和对话理论为“互文性”提供了依据。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互文性”理论。她在《符号学》一书中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克里斯蒂娃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在文本中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所以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而言,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没有界限,彼此不间断地流通往来。
从改写主旨上看,汤亭亭对中国经典的改写是用女性主义眼光来统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她对于中国经典的改写主要体现在代表作《女勇士》和《中国佬》之中。在《女勇士》中,她改写了中国经典《木兰辞》;《中国佬》则是她对多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进行的复杂改写。这两部作品被认为是姐妹作,前者是针对华裔女性,后者则针对华裔男性。
从东西方文学的“互文性”来解读汤亭亭的作品,她的《女勇士》是源之于中国文化中花木兰的故事。故事的基本构架来之于《木兰辞》,写女子从军杀敌,不亚于男性。作品充满了中国意象和东方色彩,故事主人公就是“花木兰”的音译“Fa Mu Lan”。此外,“长城”、“岳飞”等一系列重要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还有细微之处的“苍龙”、“白虎”、“灵芝”、“桃枝”、“金蟾”等等,这些都会对以美国文化为背景的读者构成一定阅读障碍。[2]
从互文性阅读中可以看出《女勇士》主要有下列几处与《木兰辞》有很大出入:花木兰的从军动机,父亲在其背上刻字,从军作战中遇见情人且怀孕生子,杀死皇帝。这些变化,除了从军的动机一处是原作中就已经详细描写之外,其余的变动都是汤亭亭加入的。然而,从军动机也被汤亭亭大胆地改写了。从原来的忠君爱国、抗击侵略(某种程度上也带有“夏夷之争”),变成了对于男性的报复性拯救和报仇雪恨。[3]这样的改写我们可以体味其中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和话语愿望。作者改写的目的就是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对立和女性的强大。花木兰,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对父辈说出这样的话:“我现在足够优异,可以拯救那些男孩了!”我们能够感觉到汤亭亭的文化改写就是男性的一种消亡。父亲在其背上刻字,这一情节是从“岳母刺字”的典故中来的。不过在这里被移植到了花木兰身上,其中的改变是“铭刻者由母变父,被铭刻者由子变女,铭文由忠君报国变私人怨仇。”汤亭亭把她改变为一个女性复仇者的形象。在改写中淡化甚至扭曲作品中的男性角色,强化女性角色,以求达到对女性角色和女性社会处境的重新设定。
赵健秀的改写中最突出的是其大男人主义的改写。他通过对于中国文学经典中“英雄主义”故事的重新发掘,把华裔美国男性描写成为继承了中国男性英雄主义血脉的强者所以关公、《水浒传》中的108好汉、岳飞等等都常常出现在他的小说幻想之中。有学者认为,赵健秀的文本中有“关羽情节”,他试图用传说和神话中的关羽形象来确立美国华裔男性的主体地位。他在文学选集《大哎呀!》序言中认为关公是没有任何缺陷的,是正直、清廉和复仇的化身,是一个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十分自信的战士。在《甘加丁之路》中,他在华裔儿子尤利西斯·关身上赋予这种关公气质。他改写了《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把关公的气质和尤利西斯·关的性格糅合在一起;宣称“我们就是桃园结义的三兄弟,我们是三个火枪手。”在《唐老亚》中,他也用这样的改写来凸显自己的改写策略。在旧金山的华埠之中,唐老亚一家,几年来一直做飞机模型,而且在模型上依次画上人物按照《水浒传》108好汉来命名。他们准备在元宵节时把这些飞机模型拿到天使岛(华人移民美国被囚禁于此岛)上放飞。父辈告诉他,他本性李,与黑旋风李逵同姓。可见,赵健秀的改写是对中国古代英雄的一种崇拜。总之,从“互文性”上看赵健秀改写中国经典,多从其中男性英雄主义的角度中选取材料嫁接到华裔男性身上,凸现其“男子气概”(masculinity)。
三、从新历史主义“移植说”看汤亭亭和赵健秀的改写手法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作家创作不可避免会涉及文化的移植和转换。在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一个普遍的象征体系,这个体系是由无数能激起人们的欲望、恐惧和敌意的文化符码组成。作家“能建构引人共鸣的故事,可以有效把握意象,尤其是他们对语言这一文化最伟大的集体创作非常敏感,所以他们擅长操纵这个象征系统”。在创作中,“他们从文化的一个领域抽取象征材料,将它们移至另一个领域,增大他们的感情力量,改变它们的含义,把它们和不同领域选取的材料联系起来,改变他们在更大的社会图景中的位置。”这样,文学文本成了一个多种异质文本交汇的场所,文学创作也就可以通过拼贴、戏仿、梦幻等手法来实现。由于文学所指涉的是外部世界,所吸纳的是社会价值体系,所承载的是多重文化符号,因此,文学的本质是其文化性。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移植说”。格林布拉特在他的专著《炼狱中哈姆雷特》(Hamlet in Purgatory,2001)中运用这一方法把莎士比亚多部经典和逸散的历史故事(anecdote)结合起来分析,展示出新历史主义强烈的文化分析特征。
汤亭亭的改写主要采用一种拼贴的手法,实现对中国文化的移植。首先,汤亭亭在中国经典故事之间进行拼贴,以形成不同的感情力量和含义。这一点,上文中对于花木兰的故事和岳飞的故事的拼贴可以为证。在这样的拼贴中,花木兰得到了岳飞的内在气质,使得花木兰具有“男子气概”,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艺术冲击。其次,汤亭亭引入中国式的“楔子”。《中国佬》的每一章都以一个中国经典开场,引出一个美国华裔男性故事,赋予后者以理解的张力。作品共有十八章,其中四篇来之于中国古代经典。《镜花缘》里的唐敖的故事、《聊斋志异》的鬼故事、杜子春的故事以及屈原的故事。这些故事被拼贴在同一部作品之中,作为作者描写华裔男性移民史引子。这样使得小说的结构变得非常复杂;翻开目录,这部作品把如此多的中国经典故事拼贴在同一个图版之上,给读者阅读产生极多理解的可能性,形成一个理解的大杂烩。读者很容易把中国的故事和之后叙述的“美国人”的故事联系在一起阅读产生最终理解。这种“夹心饼干式”的拼贴各类作品,使得对于中国经典的也理解出现变化,产生了阅读的张力。例如屈原的故事中把屈原的原名“平”解释为“和平之意”。这是为了让这一文化符码参与到下一章《在越南的弟弟》的解读中以达到一种“和平主义”的理解。同时,用屈原的流浪精神来改写华裔美国人在全球的流浪,体现其“世界主义”的观点。最后,汤亭亭对于中国经典的拼贴还延及不同文化的故事。《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是英国经典。而汤亭亭在改写中,对鲁滨逊的名字进行故意曲解,认为应该用广东话读成“Lo Bun Sun”;同时,拼贴了中国对于十八罗汉的解释,“‘Lo’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即‘罗汉’的‘罗’;像‘阿罗汉’,像‘菩提达摩’”而且认为鲁滨逊是中国人。这一改写是为了给中国男性移民漂流的历史提供另一种解释。
赵健秀的改写主要是用梦幻的手法。通过梦幻形成强烈的感情和含义差别,表现出一种中国英雄附体的情形,以此对主流话语中刻板形象进行强烈冲击。在《唐老亚》中,赵健秀试图重建亚裔美国被抹煞的历史,借助一个12岁男孩在春节期间对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身份认同态度的大转变,创造性地将修建美国铁路的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结合在一起,叙述一段被白人抹煞的历史。唐老亚在学校接受西式教育,白人老师认为华工长期受儒家天命的影响,习惯于观望等待,缺乏进取精神,所以在劳动竞赛中输给了爱尔兰人,而且认为美国的铁路是白人手中创造的奇迹。而且1969年铁路竣工100周年庆典中,美国交通部在这一历史性致词中也一字不提华工的贡献。而他的伯父给唐老亚看的照片所揭示出来的华人修建美国铁路的历史,却向他显示出一段被宏大叙事湮没了的历史。这样,美国白人历史和华裔美国人的逸史故事(anecdote of Asian American)出现冲突,引起了唐老亚认同的困惑。赵健秀为了解决唐老亚的疑惑,用梦境的方式改写了《水浒传》。飞机上画的一百多个英雄好汉从墙上跳下来,给他讲述水浒传中的好汉替天行道的业绩和信念。这就是赵健秀式的改写,他把华裔的英雄传统,特别是中国经典中的英雄气概赋予美国华裔。在这样的改写中,华裔重新获得了对于逸出“美国正史”的华裔历史的认同,实现对主流话语中男性刻板形象的颠覆。
以汤亭亭和赵健秀共同改写的“关公”这一中国文化符码进行分析。汤亭亭把关公视之为华裔男性的一种幻想、一种精神寄托,而这一符码是脱离在他们之外的。在《中国佬》中,她对于阿公看戏的描写是最好的例子。当美国的阿公看到关公桃园结义的时候,“阿公感到一阵暖意流入心田,仿佛他是和朋友们在一起饮酒作乐。”看到关公辅佐刘备最终建立蜀国,“阿公觉得精神振奋,大受鼓舞。他像观众席上从未有看过戏的洋鬼子们一样,大声喊着‘好’。……关公,关爷爷,他是作家、武士、演员和赌徒们的祖先。他惩恶扬善,是我们的亲人。他不是我们相隔千里的祖先,而是我们的祖父。”这些对于关公的旁白,似乎让我们感觉阿公就是关公。而事实却非如此,汤亭亭笔下的阿公是一个有暴露癖的、无能的、依靠手淫和对着大地呐喊来发泄的华裔男人。[4]汤亭亭的关公是游离于华裔男性之外的,存在于戏曲中的关公,是一种幻觉,是阿公用“手淫式”的性幻想建构起来的。而赵健秀的改写主要不是在于写过去的关公,而是不断从华裔男性身上发现这种关公的现象。赵健秀把关公的形象和华裔男性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阅读者可以从《唐老亚》中的“关”姓工头和《甘加丁之路》的儿子尤利西斯·关身上看到关公的影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从方法上看,“汤赵”对于华裔历史的书写各有不同,分别侧重于拼贴和梦幻对这一历史进行书写。汤亭亭改变文化符码的感情色彩、用中国式的“楔子”和不同文化的复杂拼贴以达到其凸显女性历史地位的目的。而赵健秀则从梦幻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改写,从梦幻和现实中巨大的情感差异表现华裔的文化心理,凸显华裔男性的英雄主义。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改写中国经典上,两位作家也运用了一些相似的后现代表现手法,如戏仿[5]等。然而,由于不同的取材角度和不同的表达策略,使得他们的改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笔者将从书写意义和话语权的角度对这一区别进行梳理,引入新历史主义关于颠覆含纳和限制能动的理论进行说明。
四、从新历史主义的“颠覆、含纳”和“限制、能动”理论看汤亭亭和赵健秀改写的影响和意义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本中的人物甚至现实中的人,都会表现出对社会某种意识形态的拒绝和抵抗,然而文本中的人物由于作家本身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无法完全摈弃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消解。前者的拒绝和抵抗以及后者的渗透和消解,所体现出的就是新历史主义著名的“颠覆”(subversion)和“含纳”(containment)理论:文学作品孕育着颠覆性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往往被权力收编,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含纳。“颠覆”赖以运行的机制往往与“含纳”属于同种模式;不少情况下,“颠覆”恰恰是权力机制留下的陷阱,它给予人们发泄的渠道,而发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被吸纳进社会的运作体系之中。即当一个人面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之时,他能够做的非常有限。更进一步,当我们试图突破或颠覆意识形态桎梏之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人的思想本身已经带上了深刻的烙印,其实我们自身已经被“含纳”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内了。所以福柯这样写道:“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力量关系领域里的策略要素或原因。在同一战略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话语;而且它们不用改变形式就可以在相互对立的战略中穿行。”
与“颠覆”、“含纳”概念相对应的是新历史主义凸现的另外一个话语理论:限制(constraint)和能动(mobility)。新历史主义者认为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作家在主流话语之外对于主流的权力话语发起的猛烈攻击。“他们置身于特定地点和特定时代能够被言说的内容的最边缘,冲击着自己文化的疆界。”如果说“颠覆”和“含纳”体现了主流权力话语对于言说者强大而且无所不在的压力,那么“限制”和“能动”则说明了言说者,特别是一流的言说者,对于主流权力话语存在着限制性和能动性。
回观华裔美国文学,从读者群上看,汤亭亭和赵健秀的读者基本是相同的。而汤亭亭的改写明显比赵健秀的改写更符合美国读者的胃口,更具有影响力。其原因可以用“颠覆”和“含纳”理论与“限制”和“能动”理论来解释。汤亭亭移植“中国故事”其目标是试图颠覆美国主流话语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同时改变华裔女性的形象。而这一颠覆的活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含纳在美国主流话语之中。汤亭亭在文化移植中,不得不更改自己作品的文类,[6]而更重要的是在话语霸权中成长的她在潜意识中还是陷入了话语权力机制留下的陷阱。
汤亭亭表现的中国文化却带有强烈的片面性,在某种程度上给美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带来不好的负面影响。由于她带有很强的女性主义色彩,所以她主要关注华裔女性群体,而忽视了华裔男性。在她对华裔男性描写的经典之作《中国佬》中,也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不论如何解读都难以逃离一个女性形象站在中国男人之后。[7]整部作品中华裔男性形象都是处于被阉割、毫无能力、永远失败的困境中的状态,这就必然引起华裔男性群体的反对。同时,这也是“含纳”的一种表现。总之,汤亭亭的“颠覆”最终还是被“含纳”在美国主流话语之中。
但从作品意义上看,赵健秀的小说却是更为成功的。赵健秀在选编亚裔文学作品选集时,就说明了他的改写目标。一方面他试图突破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对于亚裔男性或者说东方男性的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对关公的改写,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另一方面他提倡亚裔作家用笔来书写个人和族裔史,打破刻板印象。他认为:“写作即是战争。人生即是战争。兵法家曰:文字乃不祥之器。写作乃是大事。”要运用手中的笔书写自己的历史,排除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亚裔美国人的描绘;把从父母、学校、历史书、电视电影、报纸等等所描绘的亚裔美国人“太过被动、娘娘腔”的形象打碎。
赵健秀的这些文学理想在他对中国经典的改写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他致力于为华裔美国人寻找一个传统,以标榜他们在美国生活的历史性和正当性。
总之,从新历史主义“颠覆、含纳”理论以及“限制、能动”理论考察,美国华裔作家应该“置身于特定地点和特定时代能够被言说的内容的最边缘,冲击着自己文化的疆界”。而华裔作家在美国社会正是处于这种“最边缘”,赵健秀正是在这种处境下不断冲击这种文化疆域,而汤亭亭改写的冲击力却有所欠缺,虽然她的作品可能拥有更多的读者。从新历史主义限制和能够理论出发,华裔作家应该在最边缘的文化立足点中,对美国主流文化进行更激烈的冲击和批评。另一方面华裔作家应该更多采用限制和能动的策略对抗来之于西方和东方的意识形态控制,避免陷入双重含纳的境遇。
五、结论
总之,在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中解读汤亭亭和赵健秀对于中国经典的改写,可以看出他们分别从女性和男性的角度选取中国的经典文化符码进行改写。从方法上看,汤亭亭采用拼贴对中国文化进行移植,而赵健秀则用梦幻的形式来重建华裔美国人的男性气质和英雄传统。最后,从新历史主义理论纬度审视华他们对于中国经典进行的改写,我们发现文学作为一种华裔追求话语和文化权利的策略,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何种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改写能够对美国主流话语对于华裔的刻板定位产生强烈的冲击;作家改写中国经典能否带有文化冲击性;同时,这种文化冲击是否带有创新性,是否带有新历史主义文论中的那种“限制性”和“能动性”。
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家汤亭亭和赵健秀,应该能够不拘泥于其“汤赵之争”(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论战),站在华裔美国文学和文化史的高度审视其对于中国经典文化和文学的改写。在人情淡薄的后工业社会的图景下,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礼信智”已经认为是改变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途径。这些重要的中国经典题材可以,而且完全值得被改写。
标签:汤亭亭论文; 新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美国华裔论文; 美国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