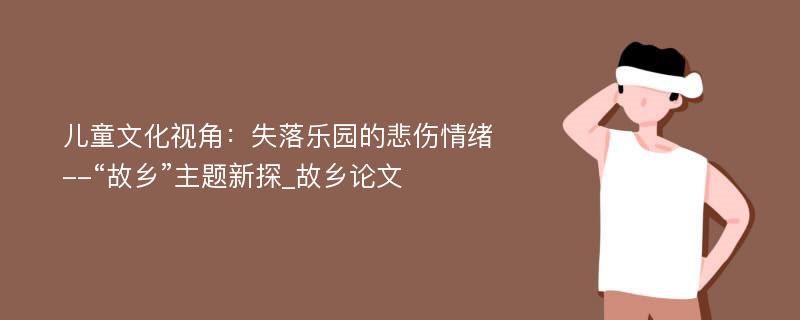
儿童文化视角:失乐园的悲凉心境——《故乡》的主题思想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凉论文,视角论文,心境论文,故乡论文,失乐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杨义曾这样阐述《故乡》的主题思想:“以时间的流逝,徐徐地展开一幅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画卷。”“小说采取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少年闰土和饱尝艰辛的中年闰土这两组镜头有机地组接起来,产生了一种连贯、呼应、对比、暗示的综合效果,深刻地显示了这位勤苦农民的悲剧命运和他灵魂中令人震栗的变化,使人惊心动魄地体味到: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把闰土磨难成一个木偶人了。”
曾有教科书的编著者在课文前作了这样的“提示”:“鲁迅于1919年12月回故乡绍兴接母亲到北京,目睹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凄苦,十分悲愤,1921年1月便以这次回家的经历为题材,写了这篇小说。小说以‘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以‘我’记忆中的故乡到现实中所见故乡发生巨大变化为基本内容,组织材料展开情节,揭示了深刻的主题思想,引起了人们对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社会根源的深深思索,激发了人们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段文字的后一句,其实就是教科书编著者以“提示”的方式,给课文归纳的主题思想。
我以为,上述观点对《故乡》的思想和情境是十分隔膜的,《故乡》的真意也并没有写故乡在物理上的变化,作品开头那段著名的描写其实是“我”的心理现实的移情的结果。“我”的心理现实是什么?那就是乐园丧失后的“悲凉”心境。《故乡》的内在结构和情节动力就是“我”对自己这代人失去的乐园的怀恋,对水生与宏儿这一代人不再失去乐园的无力而“茫远”的守护愿望。
人生的这个乐园在哪里?鲁迅以《故乡》中那个反复闪回的“神异的图画”告诉我们——人生的乐园就在童年!鲁迅在《故乡》中委委婉婉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其实就是这句话。正是这句没有说出来的话,使《故乡》蕴藉了人类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获得了征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的艺术力量。
《故乡》是一篇悲剧性作品,尽管鲁迅在小说结尾写下了点染着希望的那段名句。许多人认为,写下“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句话的鲁迅,是有着肯定而明确的信念的,但是,我觉得鲁迅是为了“听将令”而勉强写下这句话的。事实上,在小说中,“我”(还有闰土)的乐园是确凿地永远失去了,而水生和宏儿的“茫远”的“新的生活”又在哪里呢?“路”又在哪里呢?我们在“悲凉”中接过来的这个“天问”恐怕是困扰人类的永恒课题。我想,这才是鲁迅思想的深邃之处。
“我”的乐园是如何丧失的呢?
虽然鲁迅在作品中写到了使闰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的贫困生活,但生活并不处于贫困线上的“我”的“气闷”、“悲哀”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显然,鲁迅并没有像“提示”所提示的那样,把乐园的丧失仅仅归罪为经济贫困(童年为快乐而生活,成年为“谋食”而在“异地”活着)。在作品中,为“我”与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的是闰土恭敬叫出的那一声“老爷”,鲁迅以“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也说不出话”来直接突现了这一细节的重大意味。(“松松爽爽”跟着宏儿“一路出去”的水生的态度与成年闰土形成又一个对比)鲁迅后来明确地写到这是久远的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残害:“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隔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分为10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看来,从古代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等级制度也是造成乐园丧失的重要原因。但是,鲁迅在《故乡》中展示乐园丧失的原因时,理不尽之处也是明显的。鲁迅的思想存在着局限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鲁迅不是神,他不可能料到,在他所揭示的上述社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当代中国,仍然有王朔这样的作家发出“失乐园”后的叹息:“……我小时候很愉快,很多好朋友,都是一个院的。现在我一想到朋友这个词,还是觉得单指他们,虽然现在各自遭际不同,再见面也没多少话,但那份亲近感,大了以后交的朋友都赶不上。也许是小时候交的朋友印象太深了,妨碍了长大后和人的相处。我认识的很多人一聊起来都有这种感受,也不知是不是病态。总觉得像两世为人,小时候纯洁地生活过,现在活得再久也是苟延残喘。”
《故乡》的艺术魅力之一在于可以唤起我们潜藏在心底的回归童年的愿望。一部作品如果失去了唤起读者现实同感的意义,其艺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鲁迅的崇尚童心的儿童观,还给文章的表现带来了重要而明显的变化。冷峻、沉郁是鲁迅的文学风格的主要方面,但是鲁迅作品在总体冷峻的色调中,也常常透露出几抹亮色,给作品带来明朗甚至是欢快的暖色调。需要说明一句,这里所谈及的亮色,不是鲁迅自己所说的“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中的亮色,即不是“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而是鲁迅以崇尚童心的儿童观来“时时反顾”童年生活时所必然具有的结果。可以肯定地说,鲁迅文学世界的亮色与鲁迅的儿童观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我们不了解鲁迅儿童观的崇尚童心的一面,就或者容易忽略了“亮色”这一鲁迅文学世界的重要存在,或者虽然看到却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故乡》几乎通篇笼罩着悲凉昏暗的阴云,但是,唯独童年的回忆却像一缕阳光穿透阴云,给作品点染上一些明媚的色彩。《故乡》明暗色调的反差后面是一种对比:儿童时心灵的沟通——成人后心灵的隔绝。“我”与闰土童年的友谊何其纯真无邪,但30年后相见,闰土恭敬地叫出一声“老爷”,就在两人之间隔起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鲁迅与“厚障壁”这种封建的社会病相对抗而取得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却来自儿童的世界,来自童心。天真纯洁的儿童是不愿受这种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当年的迅哥儿和闰土亲密无间,他们的后辈宏儿与水生也“还是一气”。作者所真诚希望的是“有新的生活”来保护童心所体现出的美好的人际关系。
童心主义思想也有境界高下之分。鲁迅《故乡》的过人之处在于,它没有像亚流童心主义那样,将自己的心灵封闭起来,惧怕并拒绝走出童年,而是采取一种开放的、迎向生活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故乡》才可能也属于少年们。
总之,鲁迅的《故乡》是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相撞击后的产物,只有理解了鲁迅崇尚童心的儿童观,感受到《故乡》中的失乐园的心境,才能说真正把住了《故乡》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