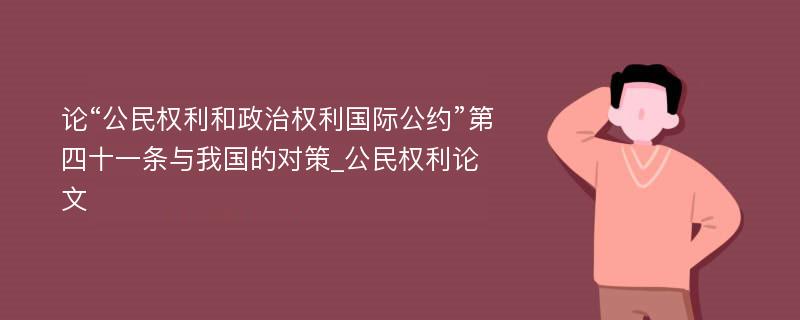
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41条及我国的应对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权利论文,政治权利论文,公约论文,应对策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1966年12月16日的第21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同时开放签字。1976年3月23日《公约》正式生效。《公约》的第41条也于1979年3月28日正式生效。截止到2001年5月18日,《公约》的缔约国已达147个(其中包括6个仅签署但仍未批准《公约》的国家),占当时联合国成员国总数(189个)的80%。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该《公约》,因此对《公约》适用问题的研究理应提上日程。
《公约》第40条至第42条规定了实施机制。第41条规定的是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即依据《公约》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议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不履行本公约义务的来文”。这条规定颇让学者担忧,如不对该条提出保留,将使我国面对众多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发难,并借此干涉我国的内政。其实,我们可不必对第41条疑虑过甚。
一、《公约》第41条的理论分析
《欧洲人权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里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规定了强制性管辖权,而《公约》里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规定的是“任择性”的管辖权,即在委员会接受并审理“来文”之前,有关缔约国都必须已经事先依据第41条第1款做出了“声明”(declaration),“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来文”。此外,只有指控国和被指控国都已经做出了“声明”,委员会才能够受理“来文”。
假设A缔约国正式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来文”,指控B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侵犯公约所保护的人权,然后人权事务委员会将按以下程序处理:
1、穷尽国内救济原则。公约第41条(1)款(C)规定:委员会对于提交给它的“来文”中所指控事项,须认定在这一事项上已按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求助于并用尽了所有现有适用的国内补救措施之后,才能处理该指控事项。但是,如果国内外补救措施被无理拖延,则无须穷尽国内救济措施,委员会即可处理有关“来文”。
2、以秘密会议形式审议来文。第二步,委员会将审议提交的“来文”,根据公约第41条第(1)款(d)规定,这个审议过程必须是以秘密会议形式进行。
3、提供斡旋以求得友好解决。《公约》第41条第1款(e)规定,委员会在解决争议过程中,应对有关缔约国“提供斡旋”,以便在尊重公约所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上求得争议事项的友好解决。在国际法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外交方法有调停、斡旋等。
公约第41条第1款(e)的措词是“斡旋”,但公约第41条第1款(f)规定,在委员会审议争议事项时,委员会有权要求有关缔约国提供任何相关信息;第41条(1)款(g)规定在“委员会审议事项时,有关缔约国有权派代表出席,并提出口头的和/或书面的说明”;第41条第1款(h)规定委员会应在收到“来文”之日起12个月内提出一项“报告”。从上述规定可见,委员会的职责不仅限于通过斡旋求得争议友好解决,而且采用了类似国内法里的听证程序制度,这使得它本身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双方谈判。这种做法似乎已超出传统国际法上斡旋定义的范围。(注:See Dr.iur·et habil·Manfred·Nowak: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Rights Commentary,N·P·Engel Publisher,1993,P599.)
4、提出报告。(1)如果委员会斡旋成功,来文指控事项得到友好解决,委员会须做出一“报告”,内容“仅限于对事实和所获解决结果作一简短陈述”。(2)如果来文指控未能最终友好解决,委员会也须做出一报告,内容“仅限于对事实作一简短陈述”。同时,审理过程中缔约国双方提出的书面说明和口头说明的记录,也应附在报告上。如果我们知道《公约》原先的草稿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30、31条对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的规定,我们就会发现,《公约》所设计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的拘束力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多么的弱。公约曾经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设的人权委员会草拟了一个草案,该草案采取了与欧洲人权公约第30、31条相似的规定。草案规定,委员会的“报告”不仅包括对事实之描述,而且还包括委员会自身对来文指控事项的看法。对事项可做出表态,这显然赋予委员会担当起调停者的角色。可惜的是,《公约》正式文本把委员会的“报告”局限于对事实之简要陈述,并采纳了“调停”这个单词,造成了委员会实际上处于既不完全是斡旋者,又不是调停者的境地,这无疑使委员会的权威性以及公约设计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之有效性大打折扣。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1966年有9个亚、非国家向联合国大会下设的第三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它们草拟的公约草案,在这份草案里,9个亚非国家很明显地想把依公约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由一个裁判机构变为一个调解机构。此外,早在1963年的一个有关《公约》实施的一般辩论会上,美国明确表示反对赋予委员会任何准司法的职能。在上述压力下,《公约》的起草者不得不做出了让步。
二、我国针对第41条可采取的策略
(一)对第41条提出保留的探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款(d)指出,保留的实质“在于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各国的保留实践表明,成员国通常是对那些认为或担心会与其国内法或国内政策相抵触的条款加以排斥或限制。但是,保留不应是毫无限制的。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条的规定,不允许做出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相符合的保留。
《公约》对保留未作任何明文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保留,也并不意味着允许对公约的任何条款加以保留。1994年《公约》的人权事务委员会曾提出了“关于批准或加入《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时提具保留,或依《公约》第41条发表声明的问题的一般性意见”。(注:See VN Document CCPR/C/21/Rev.1/Add6资料下载自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a-cepr.htm.)该意见指出,在已做出的150项保留中,一些保留排斥了规定和保障公约所载的特殊权利的责任。因此该意见强调,《公约》“未作禁止保留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允许任何保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3)条规定了有关的标准”。这一标准即:允许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合的保留。该意见指出:如果保留使得缔约国可以不履行对侵犯人权行为提供补救的保证,或者意欲逃避人权委员会的监督,那么这些保留就是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悖。由上可见,在《公约》未对保留作任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成员国提出的保留不能与《公约》目的和宗旨不符合。
据统计,截至1999年12月31日,《公约》155个缔约国中共有35个国家就《公约》条款提具了158项不同意义的保留,但没有缔约国对《公约》第41条做出过保留。(注:数据来自爱尔兰国立大学下属的“爱尔兰人权研究中心”主任Dennis.Driscoll教授2000年10月访问复旦大学时赠送的相关统计资料.)这是因为第41条规定的是《公约》的实施机制,实施机制从国际层面上讲,它的存在意味着各缔约国履行《公约》的状况与程度得到了国际机构的有效监督。而从国内层面上讲,它的存在督促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即缔约国应采取立法、司法和其它措施履行《公约》。可见实施机制是《公约》的核心之一,如果对《公约》的实施机制做出保留,应当违背了条约之目的与宗旨,而违背条约之目的与宗旨的保留是不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接受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如果对第41条提出保留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二)做出第41条规定的“声明”以及相关策略。有这样一种建议:我国在批准《公约》时,不做出第41条规定的“声明”,即不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具有审议“来文”的管辖权,这实际上是架空了《公约》设计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笔者从三方面考虑,认为这样做毫无必要。
首先,从我国加入《公约》的目的来看,我国签署并拟定国际公约,并非只是一种同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斗争的手段,而是显示了我国真诚、严肃的立场,并以此为契机,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人权法制建设,促进国内人权状态的改善。我国不应畏惧《公约》的监督机制,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需要的是更多交往和对话。西方国家借口维护人权而干涉他国内政的事件,不仅在委员会内,而且在其他场合,也可能屡屡发生。我国需要冷静应对,但不必对其疑虑过甚。
其次,公约设计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自身存在不少缺陷,这使得公约在执行时,未必如我们想象的有效,其效力主要局限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谴责。《公约》缺陷具体说来有4点:(1)第41条规定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是“任择性的”(optional),而不是“强制性的”(obligatory)。一缔约国欲指控我国违反公约,不仅需要我国做出了第41条规定的“声明”,而且该缔约国也须已经做出“声明”。所以并不是任何一个缔约国都可以运用第41条来文指控我国。截至2001年3月19日,147个《公约》缔约国中,仅有48个国家做出了第41条规定的“声明”(注:统计数据来自联合国提供的资料"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Declarationsand Reservations [As of 19 March 2001],资料下载自http://www.unhchr.ch/html/menu3.),其中包括一些和我国保持较好外交关系的国家,如俄联邦,北朝鲜,刚果等。但是,这也包括美国(1992年),丹麦(1976年),英国(1976年)这类经常在人权问题上向我国发难的国家。可是,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之严重以及持枪犯罪数量之令人惊讶,世界有目共睹,这难道不是违反公约所规定的保护人权的义务?我国同样也可以利用第41条向美国“发难”,以促进《公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2)委员会在审议来文的过程中负有“发现事实”(fact-finding)之责任。但是,这种对事实之发现的手段仅仅限于有关缔约国应委员会的要求提供有关“情报”,以及缔约国派代表出席委员会的审议,提出口头或书面的说明。委员会仅限于从上述材料中发现事实,而无权亲自从事调查。公约这样规定避免了委员会可能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这样的规定是我国乐意接受的。(3)由于亚非9国以及美国的原因,公约规定无论被指控之事项是否得到“友好解决”,委员会根本不可能在其“报告”中对事件做出实质性评价,更不用说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了。委员会根本不具备司法裁判的功能,委员会报告的拘束力较弱,对于违反公约的行为,委员会也不能提供有效制裁。
最后,从国际实践层面来看,各缔约国大多极为勉强地愿意利用第41条设计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根据《公约》第49条之规定,在第35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3个月后生效。待到《公约》生效时,已是1976年3月,距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整整过去了10年。《公约》第41条第2款规定必须有10个缔约国做出“声明”,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来文之后,第41条才生效。直到1979年3月才有第10个缔约国做出了“声明”,《公约》第41条才由此生效。
联合国截至2001年3月19日的统计数据显示,147年《公约》缔约国中,仅有48个国家做出了第41条规定的“声明”。(注:参阅朱晓青:“《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机制”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5页.)虽然除了德国、西班牙、瑞士3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声明”都是“永久性的”,但令人惊讶的是至笔者写本文时止,上述48个国家迄今没有一国启动过这一程序。有了争端,各国似乎更乐意诉诸于政治交涉、外交手段,而不愿意“对簿公堂”。因为这种指控方式被看作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因而在国际关系中“不可为”。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我国将来批准公约时,不应该对第41条做出保留;并且可以考虑做出第41条规定的“声明”,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来文。
标签:公民权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