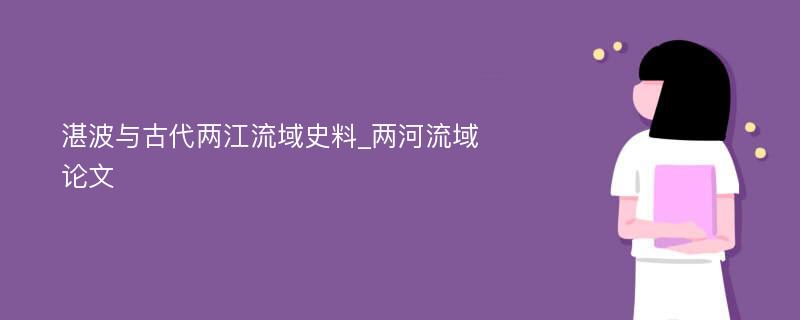
脏卜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史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流域论文,古代论文,两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代,人们出于对神明的崇拜,希冀能够时时得到神的指导而发明了占卜术。牲羊之脏卜(Extispicy )是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发明的一种独特的占卜方式。脏卜由卜师通过观察牲羊内脏各器官的大小、颜色、位置、形态及附着在脏器上的各种征象推测所占之事吉凶。人们通过这种占卜方式达到解惑、祈福、预知未来的目的。这种技术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的叙利亚地区和小亚细亚地区广泛使用,甚至远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发现了铜制的肝脏模型。古代两河流域的脏卜文献中所记载的问卜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起国家大事、军事征伐、宗教祭祀,下至起居、疾病、贸易等等,事事问卜。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占卜文献为数众多,在小亚细亚,卜辞文献占所发现文献总数的1/10强。在两河流域,仅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792 —前1595年)(注:本文中古代两河流域各时代及统治者年代,除注明者外,均采用J.欧斯的年代分期,见其《巴比伦》(J.Oates,Babylon ),伦敦1979年版,第199—202页所附之年表。)的占卜文献就有88篇近2700条兆辞,其中88%为脏卜兆辞。亚述帝国(公元前745—前609年)国王阿述尔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前627年)更是把所能搜集到的文献都收入到尼尼微的国家图书馆中,其中包括不计其数的脏卜文献。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末的一百年间,研究者们致力于整理、研究这些浩繁卷帙,释读并发表了几十种文献汇编,并基本提供了一幅包括其起源、发展、选拔、培训、任命卜师,脏卜技术术语、规则、步骤等脏卜技术的全景图。但是,学者们对于兆辞中所涉及的丰富的古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记录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研究者寥若晨星(注:包括L.金:《关于巴比伦早期国王的年代记》( L.W. King, Chronicles Concerning Early Babylonian Kings),伦敦1907年版;E.维德纳:《巴比伦兆辞文献中的历史史料》( E.F.Weidner,Historisches Material in der Babylonischen Omina—Literature), 《古代东方学会杂志》(Mitteilungen der altoriental isches Gesellschaft),1929年第4期,第266页以下;H.圭德博克:《巴比伦人和赫梯人的历史文献和史学传统》(H.G.Güterbock,Die historische Tradition
und ihre literarische Gestaltungen bei Babylonien
und Hethitern),《亚述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1934年第42期, 第1—91页;A.奥本海姆:《楔形文字兆辞文献》(A.I.Oppenheim,Zur keilschriftlichen Omenliterature),《东方》(Orientalia),1936 年第5期,第199—228页;等等。)。本文将在概述脏卜技术在古代两河流域发展的历史,它在周边地区的传播,以及脏卜技术的规则等方方面面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脏卜文献对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史学研究价值,希望引起学者们对脏卜文献的重视,收到补充历史、认证历史的效果。
一
脏卜是两河流域居民最早使用的一种占卜方式。最初是南部地区,即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居民发明并将之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中。早在公元前4 千年代,西帕尔(Sippar
)半人半神的王埃麦努兰凯 (Enmeduranki)就曾经宣称自己由“沙马什(Samas)和阿达德(Adad)处习得脏卜之术,并传之臣民”(注:W.兰博特:《埃麦努兰凯其事》(W.G.Lambert,Enmeduranki and Related Matters),《楔形文字研究杂志》1967年第21 期,第132页。)。古巴比伦时期是脏卜技术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古巴比伦的国王们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对外商业贸易往来关系的迅速恢复和加强,这种技术先后传到叙利亚地区各个国家。在马瑞(Mari )、阿拉拉(Alalakh)等地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在马瑞发现了最早(约公元前1900年)的有文字记载的脏器模型(注:M.如顿:《马瑞发现的2个泥制肝脏模型》( M. Rutten,Trente— deux Modeles de foies en argile provenant de Tell— Hariri ( Mari ), 《亚述学及东方考古学杂志》( Revued'assyriologie et d'arch éologie orientale)1938年第35期,第36页以下。),大量信件中也涉及到这种占卜活动。根据马瑞文献(注:J.杜杭:《马瑞皇家档案》(J.—M.Durand,Archives royales de Mari)第26 卷,巴黎1985年版。),我们可以确定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脏卜活动在公元前18世纪已经被应用于社会生活。古巴比伦的卜师将观察到的各个内脏器官的兆象以及前人对这些兆象的解释归纳结集,形成了最早的脏卜手册,共36节,每节记录一种内脏器官的各种兆象。
古巴比伦王朝亡后,加喜特人(the Kassites)和亚述人继承和发展了巴比伦尼亚地区流行的脏卜技术。中亚述时期(约公元前1192—前745年)(注:此年代据G.胡:《古代伊拉克》(G.Roux,Ancient Iraq),伦敦1980年版。)的国王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
Tiglath— pileser Ⅰ,公元前1115—前1077年)与南部的伊新(Isin )第二王朝(公元前 1158—1027 年)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Nebuchadnezzar,公元前1126—前1105年)几乎同时各自编撰了新的脏卜手册,其主要内容仍然延续了古巴比伦时期脏卜手册的主要内容。亚述帝国时期,星占术是帝国国王们推崇备至的占卜技术,但是脏卜术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在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发现的图书馆中,发现了大量的脏卜文献,其中包括这个时期重新整理的脏卜手册。
约公元前14世纪脏卜技术传入小亚细亚赫梯国家(约公元前1650—前1200年),赫梯人对脏卜术的学习似乎应该来自两个途径,一个是由两河流域直接学来的;一个是通过占据着叙利亚及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胡利安人那里学来的。赫梯人对外来的脏卜技术没有全盘吸收。首先,赫梯人简化了繁杂的两河流域的脏卜术语系统,改变两河流域同一种脏器形态用几个甚至十几个动词、形容词甚至比喻的方式表达的办法,而只选用一词,最多两词表达即可。另外,赫梯人没有沿用两河流域的一次脏卜活动要观测牲羊所有的内脏器官的做法,每个问题只选几个器官进行观察。
两河流域脏卜术的影响似乎不止于此。对曾经居住在今意大利地区的古代埃特鲁斯坎人(the Etruscans)的研究表明, 埃特鲁斯坎人所使用的占卜技术中也有用牲羊的内脏占卜的方式。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铜制的脏器模型与两河流域的陶土的脏器模型如出一辙(注:I.斯达:《有关卜师的仪式》(I.Starr,The Rituals of the Diviner), 《两河流域文库》(Bibliotheca Mesopotamica)1983年第12卷,第2 页注6 。另见 J.达罗斯:《赫梯人和埃特鲁斯坎人》 (J. de Roos,Anatolia and the Etruscans),《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97年第12期,第37—43页。)。虽然无法确定它们之间有何确切关系、联系途径如何,但可以肯定,二者之间必有某种关联,而从时间上看,两河流域的脏卜术应为埃特鲁斯坎人脏卜术的祖先。
二
在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脏卜文献共有四种格式:脏器模型上的记辞、兆辞、脏卜报告及小亚细亚的脏卜卜辞。脏器模型上的记辞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脏卜活动的记录形式。早期的记辞仅具有报告和记录脏卜结果的功能,后来兼具有教授新卜师的功能。
古巴比伦王朝后期,脏卜报告取代了脏器模型的报告和记录功能,其教授新卜师的功能则为兆辞记录所取代。古代两河流域历代卜师不断收集整理各个器官的兆象及各种征象,结集成册,作为后代卜师的参考手册。脏卜报告是记录实际的脏卜活动的报告。除在古代两河流域本土发现的大量脏卜报告外,在叙利亚地区的马瑞书信中,也有一些记录脏卜活动的书信,当属脏卜报告一类。此外,小亚细亚的脏卜卜辞记录的是卜师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观察的记录,也应归属脏卜报告一类。
在实际的脏卜活动中,卜师首先挑选脏卜用的牲羊,经过净化仪式,献于神前,请求神的认可。祭祀后的牲羊仰放在卜师面前,卜师站在牲羊上方,沿中线剖开牲羊外皮。卜师将由肝脏开始,依顺时针顺序观察牲羊的内脏各器官。肝脏是最主要的观察对象。卜师将牲羊的肝脏分为若干区间,每个区间都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如“驻地”、“路途”、“强权”、“平安”等等。其他脏器,包括胆、肺、心脏、肾和肠等。肺是除肝脏之外,最为古代两河流域的卜师所关注的脏器之一,如肝脏一样,肺的各个区间划分明确,兆象记录众多。但是,在小亚细亚,虽然在赫梯国家首都哈图萨(Hattusa)发现的阿卡德文兆辞文献中, 也有有关肺脏的兆象记录,这个内脏器官却不为赫梯的脏卜卜师所关注。在脏卜卜辞中没有任何对肺脏的观察记录。此外,在各个内脏器官上出现的一些征象也为卜师所关注,如颜色的深浅、是否有孔洞、是否有黏着物等等。在脏卜技术规则中,若两个不好的征象同时出现,对我方为吉兆,对敌方为凶兆。此外,若卜师在自己的位置无法观察到应当观察的内脏器官,为凶兆。若脏器位置、形状、数目或颜色不符合常规,也为凶兆。脏器上的各种征象代表不同含义,如脏器上出现孔洞,代表死亡,征伐失败;若出现“武器”,代表战争等等。
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占卜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古代两河流域,人们比较关注现世的幸福,和预测将来的吉凶祸福,因此绝大多数的脏卜活动集中在祈福和预测未来上,如祈求风调雨顺、繁衍子嗣、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或者占王位是否稳固、征伐之结果、贸易之利益等等。太阳神沙马什是古代两河流域的正义之神,他同时也是脏卜过程中神之裁判会的主神。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对于神是崇拜和信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神是正义和公正的。而在古代小亚细亚人的心目中,神是易变的。若人对神的供奉得当,则神颜大悦。赫梯人问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惑:为什么王获病,房屋倒塌,征伐失败等等。赫梯人将一切灾难和挫折的发生归结于神颜震怒。赫梯脏卜文献中,大多数的问题集中在占问哪一个神或哪一组神震怒,原因是什么。
三
追溯过去是古代两河流域、叙利亚地区、小亚细亚地区居民特别是王室的传统。两河流域历朝历代的国王都命人编撰前人的王表、年代记、颂诗等,其目的一方面是颂扬祖先的功绩,另一方面是向世人证明自身荣登王位的合法性和血统的纯正。在小亚细亚,赫梯国王颁布诏书从宣颂历代祖先的名号和尊号开始;与邻国或属国签订条约时,也以记述祖先的赫赫战功和追溯与签约国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开始。由于研究两河流域、叙利亚、小亚细亚地区的历史依赖于考古发掘的成果,而考古发现又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但是,由于编写目的不同,各种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也有所不同。与其他文献相比,脏卜文献以及其他各类占卜文献应具有更加真实的特性。
首先,占卜活动起源于人们寻求超世俗的神灵对人间事务的兆示,人通过各种方式达到解惑、祈福、预知未来的目的。因此,卜师编撰文献,记录兆辞的目的在于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祝福或警示,弄虚作假就失去了兆辞存在的意义。何况兆象随时改变,也就没有篡改的必要了。相反,其他文献,如王表,如前所述,其编撰目的是宣扬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因此其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苏美尔王表》(注:T.雅各布森:《苏美尔王表》(T.Jacobsen,The Sumerian King List ), 芝加哥1939年版。)中记载的早王朝的某些国王, 他们的统治年代可长达几百几千年,显然是不可信的。《亚述王表》中将古亚述王国的开国之君沙姆什·阿达得一世(Samsi—AdadⅠ ,约公元前1813—前1781年)及其祖先附会为亚述人,而隐瞒他们“野蛮人”的本质(注:范科尔斯坦:《两河流域的历史方法论》( J.J. Finkelstein, MesopotamianHistoriography),《美国哲学学会通讯》(Proceeding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63年第107期,第469页注32。),其目的当然是证明整个亚述王国祖先血统的纯正和高贵。赫梯国王图塔利亚四世( Tuthaliya
Ⅳ,公元前1250—前1220年)是哈图西里三世(Hattusili Ⅲ,公元前1275—前1250年)的继承者,而哈图西里三世是篡夺其侄乌尔黑·泰素普(Urhi—Teshup)的王位而登基的。在图塔利亚四世时期的各类文献中,为了显示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他绝口不提乌尔黑·泰素普的国王身份。而在赫梯卜辞文献中,他忧心忡忡地反复占问自己的王位是否巩固,是否会有篡位者(注:《博卡茨科依出土的楔形文字文书》(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oi,ⅩⅤⅢ36,以下简称KUB), 第11—21行。参见R.比尔:《赫梯卜辞:问题和答案》(R.Beal,Hittite Oracles:Question and Answers), 《古代世界的巫术和占卜》( Magic and Divina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伯克利1994年版,第16页;Th.冯丹候:《赫梯继位卜辞和图塔利亚四世的登基典礼》(Theovan denHout,Hethitische Thronbesteigungsorakel und die Inauguration Tudhalijas Ⅳ),《亚述学杂志》1991年第81期,第279 页以下。)。显然,在占卜活动中,他对先人篡位者的身份耿耿于怀,也并不隐瞒。总而言之,由于占卜文献编撰的目的是祝福或警告,是针对占卜委托人——大多是国王的个人行为,因而较其他以宣传为目的的文献更可信,更具有史料研究的价值。
其次,与其他文献相比,占卜文献,特别是早期的脏卜文献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两河流域早期脏器模型上的记辞多记录真实的历史事件,因此又称“历史记辞”。这些脏器模型制作时间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其中记载的事件多为前朝阿卡德王朝(公元前2334—前2154年)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113—前2004年)的历史事件,如“若……纳拉姆·辛(Naram —Sin ,公元前2254—前2218 年)捣毁阿皮萨尔 (Apisal)城的城墙,将其居民掠为俘虏”(注:YOS 10 24第9行。),这一事件指阿卡德王纳拉姆·辛发动的一次战争;“若……王朝的混乱时期”(注:TCL 61反面第23行。),这段混乱时期约发生在公元前2198—前2195年;“若我们起义反抗伊比·辛(Ibbi—Sin )的统治,肝脏将出现如此情形”(注:RA35,第42页第7 条。)。伊比·辛是乌尔第三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他的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2027—前2003年。其间时差为100—200年。而我们目前所发现的有关两河流域早期历史的《苏美尔王表》和《亚述王表》多完成于古巴比伦时期以后,甚至是亚述帝国后期, 其时差达500年以上。
再次,占卜文献的编撰人比其他各类文献的编撰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占卜文献的编撰人同时也是卜师。他们的义务是为其委托人将要做或已经做的事情提供参考和给予解释,并将结果如实地记录下来。卜师也是国王或各级官员的参谋,帮助他们进行决策。因此,在脏卜文献中,卜师从不讳言王的短处和过失,“王将携款私逃”,“某人将弑君为王”,“王将死于征途”,“国家将遭遇瘟疫”等凶兆的记录充斥各个时期的脏卜文献中。在赫梯占卜卜辞中,卜师也常常告诫国王在某些方面的疏漏,“雷神庙供奉不及时”,“有不洁之人闯入神庙大殿”等。
最后,作为占卜活动委托人的国王或各级官员,甚至是平民对占卜记录的态度与对待其他文献的态度不同。占卜活动的结果是决定委托人行止的依据,其目的是防患于未然。而国王签署的诏书、公告或下令编撰的王表、年代记是有其政治目的的,隐恶扬善也是政治活动的需要。亚述帝国的国王辛那赫里布和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二世(Mursili Ⅱ,公元前1330—前1295年)在占卜活动中公然占问他们的父王死于非命的原因。而在各个时期其他文献中,国王暴死总是被极力掩饰和回避的话题。
四
事实上,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脏卜文献也确实起到了认证史实、补充历史的作用。两河流域早期脏卜文献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涉及从早王朝苏美尔时代到乌尔第三王朝时的多位国王和统治者。如吉尔伽美什,他是两河流域著名的吉尔伽美什神话的主人公。长期以来,研究者们都认为他是传说中半人半神的英雄,而不是历史人物。虽然也有人认为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苦于没有证据。在脏卜卜辞中,他以人的身份出现,没有神的标志,认证了他是一个历史人物,并且在当时无敌于天下(注:YOS 10 42 Ⅰ第2—3行。)。梯瑞卡(Tirika)是阿卡德王朝灭亡时入侵两河流域的古提人(the Gutians )的首领。当时乌鲁克(Uruk)的统治者乌图·海嘎尔(Utu—hegal)曾宣称他打败并俘虏了梯瑞卡。脏卜文献认证了梯瑞卡的存在并战败这一历史事实,还进一步证明他战败被俘后被处死(注:YOS 10 9 第31—32 行。)。脏卜文献中关于乌尔第三王朝第二王淑尔吉(Shulgi,公元前2094—前2047年)征服塔帕·达拉赫(Tapa— Darah)的记载补充了其他文献中关于淑尔吉在位第26、27、33年和第45年对外战争的对手不知为何人的缺漏。第45年,由于征服了他最后一个对手塔帕·达拉赫,淑尔吉加冕为“四方之王”。此外,早期脏卜文献还在不同程度上认证和补充了乌尔第三王朝其他国王和伊新第一王朝统治时期的历史事实(注:格策:《古巴比伦兆辞文献的历史典故》(A.Goetze,Historical Allusions in Old Babylonian Omen Texts),《楔形文字研究杂志》(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1947年第1期,第260—263页。)。
两河流域早期脏卜文献最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在于它对阿卡德王朝历史的认证和补充。脏卜文献中涉及阿卡德王朝的五位国王:萨尔贡一世(Sargon Ⅰ,公元前2334—前2279年)、瑞姆什(Rimush, 公元前2278—前2270年)、玛尼什图苏(Manistusu,公元前2269—前2255 年)、纳拉姆·辛和萨尔卡力萨瑞(Sarkalisarri,公元前2217—前2193年)。它首先认证了研究者们通过文献研究和考古发现得出的阿卡德王朝五位国王的名号。脏卜文献中所记载(注:努盖浩:《论巴比伦脏卜文献的历史地位》(J.Nougayrol,Note sur la Place des Présages Historiques dans I'Extispicine Babylonienne), 《高校古史研究年鉴:宗教科学版》(Annuaire Ecole Practique des Hautes Etudes,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1944—1945年,第5—41页。)的萨尔贡一世发动的西部战争(第61条)、平叛战争(第68条)、攻克卡匝鲁(Kazallu,第69条)、打败埃兰人(the Elamites,第77条)、攻克马尔哈西(Marhasi,第54 条)等与研究者们根据其他文献和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相符。关于纳拉姆·辛,一般认为,萨尔贡一世是阿卡德王朝的开国之君,纳拉姆·辛则使阿卡德王朝达到鼎盛。但是由于纳拉姆·辛居功自傲,自称为神而得罪了上天,上天降罪于阿卡德,导致王朝衰亡,纳拉姆·辛是个不祥之人。但是脏卜卜辞中所有涉及纳拉姆·辛的兆辞都是吉兆。这就对前面的结论提出质疑:纳拉姆·辛是建功者还是毁灭者?事实上,纳拉姆·辛是个反传统者。他为了抬高自己的保护神纳那( Nana )的地位, 意欲在都城阿卡德—恩利尔神 (Enlil )之城,建立纳那的神庙。他两次通过脏卜询问恩利尔神的意见,但两次遭到拒绝。纳拉姆·辛最终选择了大逆不道的做法,他竟然毁坏了恩利尔的神庙,占用恩利尔神的土地,使用恩利尔神庙的砖建造纳那的神庙(注:《诅咒阿卡德》,文见L.乔治:《两河流域脏卜的道德规范和思辩哲学的探索》( L. George,Mesopotamian Extispicy:Explorations in Ethics and Metaphysics), 《加拿大两河流域研究会简报》(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Mesopotamian Studies Bulletin), 1990年第19期,第20页。)。纳拉姆·辛对神的蔑视可谓彻底,是因为他把自己提高到了神的位置,自称为神,接受其臣民的供奉。两河流域的后人视此行为为大逆不道之举,而将阿卡德的覆亡归之于此举。我们都清楚,某一个人对神的不敬不能导致一个王朝的毁灭。而他对敬神重卜的传统的反对却可以导致后人对他的诋毁。实际上,是纳拉姆·辛的人格特性决定了历史上将他视为毁灭者的评价。纳拉姆·辛虽然不重视脏卜的结果,但是卜师仍然记录了他的诸多功绩,有关他的兆辞也都是吉兆,与建功立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关。在卜辞中,他仍然是建功者。根据脏卜文献,阿卡德王朝的衰亡似乎始于纳拉姆·辛的继承者,因为有关纳拉姆·辛的继承者的兆辞都是凶兆,或死于非命,或国家遭受灾难等。总之,脏卜文献中对阿卡德王朝历史的解释一方面认证了萨尔贡一世的不世之功,同时也补充了对纳拉姆·辛历史评价中的某些不足。
古代两河流域后期的脏卜文献反复使用前期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再反映真实的人和事,而引申为一种象征意义。当某一位国王占出征之事时,他可能得到这样一条兆辞:“纳拉姆·辛的阿皮萨尔之战”。这预示着在即将进行的一场攻坚战中,他将采用当年纳拉姆·辛攻克阿皮萨尔城时采用的战术,并取得同样重大的胜利。他将攻城掠地,俘获敌酋。具有引申意义的还包括:“萨尔贡的武器”,意为国王将发动的战争的规模与当年萨尔贡一世所发动的战争规模一样大。“布尔辛(Bur—Sin,公元前1985—前1874年)之死”,意为与伊新第一王朝国王布尔辛一样将死于噬咬“毒鞋”等等。由于流传下来的这些具有引申意义的兆辞多有验辞证明同类事件反复发生,因此这类卜辞可以补充卜辞记录时所处历史时期的某些细节。
此外,两河流域的脏卜文献提供了一些在历史文献中无法发现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如两河流域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关于起义、叛乱的记录很少。而脏卜文献中,类似记载很多,涉及叛乱者的身份:宫中的仆役、宫廷卫士、奴隶、边防军人、仆从国等等;涉及叛乱者的目的:争夺王位、独立或自立为王等;涉及叛乱结果:弑君自立、国王平叛等。同时,脏卜文献中关于军事活动的记录也有很多。国王发动战争的目的、起兵的原因、出征时间、战略战术、后勤保障、战争结果、战俘处置、战利品分配等等军事征伐的各个方面在脏卜文献中都有所反映。仅攻城技术一项,文献中就记载了诸如使用攻城棰捣毁城墙、打开缺口、使用攻城梯等几种方式。关于日常生活,文献中记录的都是两河流域居民所关心的事情,如农业的丰产歉收、天气和气候的变化、商业贸易的时机和利润、法庭诉讼等等。可以说,两河流域的脏卜文献提供了有关这个地区古代社会的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
脏卜活动是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最久远、技术最完备、应用范围最广泛、传播领域最广阔的占卜方式之一。脏卜完备的、庞大的技术体系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对自然的深刻认识。脏卜技术在周边地区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证明古代两河流域和周边地区的频繁交往。而脏卜文献所具备的史料价值,其真实性和时效性也是其他文献所不具备的。其中丰富的反映古代两河流域日常社会生活场景的记录,更是其他以国王和王室活动为中心的文献材料所欠缺的。脏卜文献在认证和补充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此外,作为一种占卜活动方式的记录,古代两河流域的脏卜文献还反映出当时居民对于神的观念、对于神人关系的态度,对于历史的态度等等,这些还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