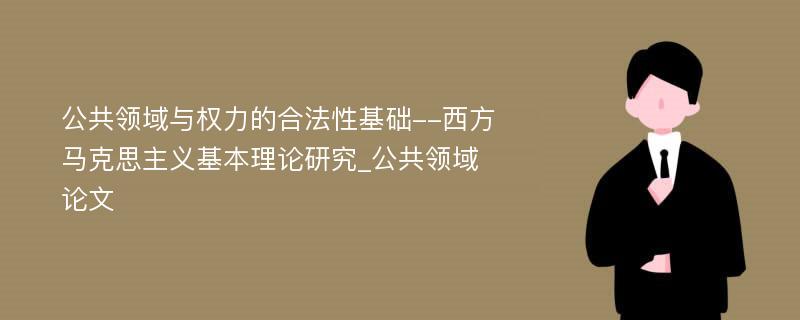
公共领域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论文,理论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权力论文,合法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6-0045-08
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和理论突破性质的是公共领域理论的兴起。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意识得以形成的领域,直接对西方议会制民主提出了挑战。它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了一种民主的新形式,因而在和谐社会和世界公正的建设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西方社会的普遍异化或物化现象,即资本的原则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而所有人都成为追逐资本和金钱的工具。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种新的现象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那就是经济与政治的结盟。也就是说,国家本应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维护公共利益,然而在资本的诱惑和逼迫下,国家却完全站到了资本的立场上,与公众的生活世界相对立。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一旦联盟,其结果都是公众生活的边缘化。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压力下,生活世界普遍殖民化。为了对抗这种双重异化,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整个社会可以简略地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最底层是公众的生活世界,中间一层是社会的经济系统,最上层是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一旦结成联盟,并按金钱和权力的原则进行统治,生活世界就必然被殖民化,生活世界团结、共生的生活原则就被资本、强力原则就所取代。真正的权力应该来自生活世界的公众认可,公众权力被边缘化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源。哈贝马斯认为,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结成一体,从而用金钱原则和权力原则统治世界。
法西斯主义是国家与资本主义联盟,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而行资本主义之实,因而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判。正如霍克海默所说:“整体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或国家社会主义乃是独裁主义国家最一般的表现形式。”①由于国家政权与资本连成一体,因而“一切形式的独裁主义国家都是压抑性的”②。弗罗姆认为,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残酷地压迫人民”,“不管它如何乔装打扮,它的既定目的就是使个人屈从于外在的目标,并且削弱真正的个性发展”。③马尔库塞也认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④,即政治与经济连成一体,国家成为最大的资本家,而人民则一无所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声中,哈贝马斯不仅发现了极权主义即经济、政治联盟所造成的人类个体的异化,而且发现了它所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即人类的生存基础——社会一体化的瓦解:
在现代国家中……我们发现这样一种见解,即通过价值和规范获得、又由国家权威保护的社会一体化,在原则上可以被系统一体化所取代,即被规范性社会结构(或机制)的潜在功能所取代。⑤也就是被系统的金钱原则和权力原则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通过传统的议会民主的方式,已不能从内部改变系统的运行原则:
将经济和国家机器视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为领域。这些领域再不能以民主的方式,也就是说,以一种政治整合的方式从内部加以改变,而同时不损害其整体特征和功能。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证实了这一点。⑥也就是说,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完全可以被资本所控制,即使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强权一旦形成,传统的民主方法也很难改变它的极权趋势。因此,“应当在社会整合的不同资源之间,而不是国家权力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力量均衡关系”⑦。这种新的力量均衡关系就是生活世界与公共领域的联盟,即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力量——交往生产力,以制衡系统的权力扩张,使生活世界的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联盟的“目的不再是‘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统治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这样,我们就告别了实践哲学中异化和有客观本质力量的观念。合理化过程转向激进民主,其目标是,在社会整合的种种力量之间达成新的均衡,以求在面对金钱和行政权力这两种‘暴力’时,使团结这一社会整合力量——‘交往的生产力’——得以贯彻,从而使以使用价值为转移的生活世界的要求得以满足”⑧。在这里,哈贝马斯改良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民主方式不是议会式的,而是全体公众的民主参与。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和系统遵循两种不同的活动或运行范式,生活世界遵循的是交往范式,其目的是在实践理性指导下通过民主对话增强社会同一性,使社会获得谅解、和谐与共生。系统遵循的是生产范式,其目的是追求金钱增值和权力最大化,因而一切人和物都不过是实现财富和权力的工具。两种范式对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离开了生产范式,社会生活就没有基础,但是离开了交往范式,生产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因此,片面强化某一范式,而弱化另一范式,都会带来社会生活的不协调。
就生活世界而言,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张。……如果我们把社会系统理解为生活世界,就会忽略控制问题;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为系统,就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现实性虽然得到公认,但往往是虚拟的有效性要求是实际存在的。⑨
因此,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都很重要,问题在于把它们联系起来。⑩
这样,哈贝马斯就从理论上确立了生活世界的哲学地位,并把生活世界与系统的矛盾看作当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系统范式排挤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范式,颠倒了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主从关系,因此要恢复生活世界的主导地位,“关键是要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形成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11)。这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就是公共领域。也就是说,生活世界静默无声,必须通过公共领域把生活世界的要求表达出来,以形成某种合力,才能影响政治和经济,恢复它应有的主导地位。
何为公共领域?
什么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12)因此,公共领域简略地讲就是公共意见得以形成的领域。
个人和家庭是生活世界的主体,生活世界作为私人生活领域,并不直接产生政治要求,但是当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受到某种威胁而影响其存在和发展时,它们的意见往往需要通过公共领域即各种公民自发的民间组织表达出来并进而影响政治,这些民间组织形式多样,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等”(13)。正是这些非政府、非经济的民间组织,不断地反映着生活世界的民间要求,从而不断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政治取向,在客观上也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公共领域是人们表达公共要求的领域,它在客观上构成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中间环节。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权力本质上起源于公共领域,因而支持、培育还是压抑、反对公共领域将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试金石。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作用机制曾作过非常清晰的说明:
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门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之区别于例如文学的公共领域)。(14)因此,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它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领域,是所有公民平等对话的领域,是所有公民自由地表达并公开形成他们意见的领域,也是依靠传媒表达意见的领域。作为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公共领域是形成政治意见的领域,因此,对于一个民主的国家来讲,它是形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根源。
公众意见纷繁复杂,互相冲突,只有经过对话、讨论、分析、批判,真正的公众意见才能形成,所以哈贝马斯说:“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15)因此,公共性是以公共舆论、公共批判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公共讨论、公共批判,公共性才真正代表公民的共识。
公众最初只是私人生活的代表,只有在他参与国家事务和公众普遍利益问题讨论的时候,他才真正成为公众。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哪里有‘国家事务’的交流,哪里具有批判意识的‘普通人’的公众也就成为‘市民’公众。”(16)因而,公众就是参与国家事务和公共问题讨论的公民。
公众参与国家事务和公众公共事务的讨论是公众真正的政治权利,因为真正的国家权力在公众的政治权利得到执行和维护的地方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公众应当“享有参与政治、参加选举的权利,并有权依据理性原则对统治者的权力与活动,进行公开评论、批评和监督”(17)。这是社会民主的基石,是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力,也是防止政治腐败、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尤其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联盟反对封建神权的斗争中。
在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民族和领土主权国家形成了,于是,封建制度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之下,王室贵族统治阶层才能够把交际场所——尽管所有的礼节在当时已高度个性化——改造成为“上层社会”的活动领域。(18)这个领域就是早期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在18世纪虽然还十分不稳定,但已相当清晰可辨。最终集中在封建君王宫廷当中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同时也具有典型意义,它已经是正在从国家当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内部的一个禁区。严格来讲,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分”(19)。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局限在于它的不彻底性,即“只有有产者可以组成一个‘公众’,才能用立法手段来保护现存财产秩序的基础;只有他们的私人利益才会自动地汇聚成一个以维护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为目标的共同利益”(20)。公共领域在当时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而开放性原则应该是公共领域的最基本原则。他说: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因此,称得上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主体的公众是把他们的领域看作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他们认为在原则上一切人都属于这一领域。(21)因此,公共领域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领域,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集中体现。
公共领域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对外形成政治共识;另一方面,对内对公众也达到启蒙的效果,即“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22)。公共领域越是开放,它的影响面就越大,它的力量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原则上反对一切外在强制。正是公共领域的开放性、自觉性和非压抑性,才有可能使公共领域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在公共领域中,各种社团代表着不同的兴趣爱好和利益,那么如何才能形成统一的公共意见呢?哈贝马斯寄于重大希望的是各级政党和组织,并把政党和组织内的民主看作公共权力的真正代表。
只有内部实行民主的政党和组织才是批判的公共性的载体,而这些政党和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在我看来是仍具有再生能力的公共交往的真正枢纽。这一结论是从组织社会的特征中得出的。在一个多中心的公共领域中,争取消极大众的支持,旨在一同或面对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来争取使权力和利益达到均衡。(23)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新概念,即政党和组织内的公共领域,亦即只有在政党和组织内实行充分民主,具有公共领域平台和公共领域精神的政党和组织,才能真正成为公共权力的核心和代表,而政党和组织内的公共领域,才是公共交往的真正枢纽。这就把政党和组织分成两类,一类是体现真正民主精神,并贯彻民主精神,其目的在于推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团结和发展。而另一类,则是把政党和组织仅仅作为谋取政治权力的工具,把党员和组织成员仅仅当作政治工具的策略性组织,它的指导原则不是以社会同一性为核心的交往理性,而是以谋取权力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因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实际上是一个以话语民主为核心的、各个政党和组织都充分贯彻公共领域精神的立体公共领域网络。他希望这个网络制度化,以对抗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显然,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思考是深入的。
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哈贝马斯在面对政治、经济的双重权力要重视公共领域建设?原因可能有许多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哈贝马斯在政治暴力之外发现了更加重要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的真正根源就在公共领域之中。1970年,汉娜·阿伦特的《暴力论》在纽约出版,哈贝马斯受到极大的启发,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阿伦特的交往权力概念。
阿伦特在《暴力论》中认为,政治权力有两种,一种是暴力,另一种才是真正的权力。
权力不仅相当于人的行动能力,而且相当于人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从来不是个人的财产;它属于集团所有,并且只有当集团保持聚合的时候,它才继续存在下去。当我们说某人是“有权的”,实际上说的是他被一定数量的人们授权给他以他们的名义行事。(24)因此,权力不是自封的,而是集团中的人授权的,阿伦特实际上揭示了权力的根源。
权力的基本表现不在于支配别人的意志,而是在那旨在达成协议的交往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意志。因此可以如此理解:“权力”和“强力”只是标明行使政治统治的两个不同方面。“权力”意味着为集体目标动员起来的被统治者的一致赞同,也就是他们对于政治领导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而“强力”则意味着对于各种强制手段和办法的支配。(25)也就是说,强力的基础是暴力或霸权,而权力的基础则是人民的支持。哈贝马斯对阿伦特的观点表示极大的赞赏,认为“这个思想实际上已经启发了一种制度论的权力概念的产生”(26)。哈贝马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可能就是这种制度化的公众权力的形成。
哈贝马斯认为,阿伦特的权力概念本质上就是起源于人们交往中产生的共同信念,这种非强制的、非功利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才是权力的真正根源。这个权力实际上指的是公共权力,即管理公众的权力,它必须以公众的支持为前提。而“强力”,例如资本的强力,可以看作是一种私人权力,是资本所有人支配别人的权力。因而,公共权力不能起源于强力,只能起源于公众。“交往中产生的共同信念的权力起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人是为了达成协议,而主要不是为了各自个人的成功。”这种“为了共同行动而在一起协商的人所达成的协议——‘大家公开同意的一种意见’”,本质上是“在自由交往中产生的达成一致的力量”,“以期非强制地建立起主体间的相互关系”。(27)
阿伦特从国家制度的根源上指出:“正是人民的支持才能使权力变成一个国家的制度……所有的政治制度是权力的具体化和物质化,一旦人民的活生生的权力停止对它们的支持,它们马上就会僵死和腐朽。”(28)因而,暴力(或强力)离开了真正的权力就寸步难行,“没有一个政治领导能平安无虞地用强力来代替权力;它只有从未遭损坏的公共领域那里获得权力”(29)。因此,公共领域建设就成为政治权力建设的根本。哈贝马斯所说的“关键是要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形成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公共领域建设,以抵制金钱和权力向生活世界侵入。所以,在论文中哈贝马斯间接地指出:“公共政治领域也曾被有些人看作即使不是权力的产生者至少也是权力的合法性的产生者。”(30)强力来自政治、经济的霸权,而权力则来自人民的支持,公共领域则是人民意志的表达领域,它是权力产生的根本源泉。哈贝马斯试图把国家制度建立在以公共领域为前提的合法性基础之上。所谓交往理论,实质上就是如何在公共领域中产生合法权力的理论。由于“交往”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文化领域的学术交流都可以称为交往,但哈贝马斯主要强调的是以社会同一性为核心的公共领域中的平等交往,他关注的是合法性权力的基础。
理论上讲,公共领域是所有人的交往领域,但人们又是按照不同的兴趣和需要参加不同的交往组织,阿伦特对政治团体的作用非常重视,认为它是产生合法政治权力的基础:“谁要是对政治团体开始予以破坏,继而加以扼杀的话,那么它就会失去权力并变得虚弱无力。”(31)权力来自公共领域,权力也必须维护公共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确保政治团体的公共性活动,只有在民主基础上的政治团体才是更高一级的权力合法性来源。
阿伦特对权力的重新定义,深刻揭示了公共权力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哈贝马斯非常赞同,并进一步指出:“只有当没有被歪曲的交往组织存在于其中的时间内,公共政治领域才能产生出合法的权力。”(32)破坏公共领域本质上也就是破坏公共权力,而公共领域它是以交往组织为前提的。
假若有一种政治制度对公民不予信任并使他们互相隔绝,切断意见的公开交流,那它就要退化为一种基于暴力之上的统治。它破坏了人们交往的组织,而权力恰恰只能在这种交往的组织中产生。(33)哈贝马斯的意图十分明显,即要确保公共领域成为合法权力的基础,关键是要确保交往组织的政治合法性。专制主义的本质就是破坏公共领域,用强力控制社会。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如果一种政权“说它是一种暴政的话,那么它只表现为消灭公共领域的交往活动”(34)。因此,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组织结构上的差别,而在于是否“消灭公共领域的交往活动”。阿伦特在《极权统治的基本原则和起源》中对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批判:
警察国家一方面破坏公共政治活动,中断人们之间仍然保持着的一切关系;另一方面它又要求那些已被完全孤立并彼此隔绝的人们能够从事政治行动(当然,这并非真正的政治行动)……极权主义统治并不在于剥夺人们的活动能力,毋宁说,在于它无情地强使人们成为极权主义统治的全部行动与罪恶的帮凶。(35)显然,极权主义的本质一方面在破坏人们的公共交往,另一方面又强迫人民赞成极权。
强调交往范式,加强公共领域建设,本质上就是加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设。哈贝马斯所说的激进民主,其真实含义也在这里。也就是说,面对极权主义统治,人民有权“撤回对于已经失去合法性的机构的服从”,“并把交往权力的产生赋予制度上的永久性”。(36)这也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说阿伦特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启发了一种制度论的权力概念的产生”(37)的原因,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交往权力的产生。
阿伦特有一句名言:“权力产生于一起行动着的人们之中,而消失于他们的瓦解之时。”(38)政治权力的本质是人民授权,权力的根源在民间。“假若有人以为光凭他居于一种能阻止别人实现他们利益的地位,就能产生出合法的权力,那完全是糊涂观念。合法的权力只有在那些自由交往中形成共同信念的人们中才能产生。”(39)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是产生共同信念的前提,也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根源。并且,权力也不能产生于精神垄断,“按照阿伦特的看法,借助于精神上的限制、说服、操纵等办法所能产生的东西,只是增加强力,而不是增加政治制度中的权力。……权力只能从自由交往的组织中产生;不能‘从上面’产生出来的”(40)。一切操纵意识形态的做法从根本上讲都是反民主的。最后,哈贝马斯也否定了一切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阿伦特正确地极力主张争夺政治权力的战略竞争既不能产生出也不能保持住那些权力得以在其中巩固的制度。政治制度得以生存并非通过强力而是通过公认。”(41)也就是说,一切政治权力的真正基础在民心和民意,在人民的拥护,而不取决于争夺政治权力的战略竞争。
在这里,哈贝马斯实际上把人的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另一种是以功利为目的的战略行为。“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例如,冲突、竞争、通常意义上的战略行为——统统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行为的衍生物。”(42)这样,以语言为中介,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构成真正的权力基础。那么,如何才能通过话语共识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呢?哈贝马斯认为:
话语共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们必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但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起来的规则,还必须为所有人遵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行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在这里,话语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起决定性作用。(43)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一切思考,其目的就在于奠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一切离开了政治合法性的,以财富、强权为目的的行为最终只能导致社会均衡的破坏,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人民分裂和社会同一性的缺失。交往行为高于工具行为,交往权力高于金钱、政治暴力,交往范式高于生产范式,交往理性高于工具理性,这就是哈贝马斯的结论。尤其在现代社会,“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务渗入到公共的领域,政治演化为行政机关,个人统治被官僚政治的措施所代替,法律演变为政令”(44)。因此,要解决现代性问题,必须强调交往理性和交往范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即在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之间确认和强化公共领域这一不可忽视的层面。这一层面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基础,只有通过加强这一层面,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所体现的交往理性不仅是处理国内问题的重要原则,而且也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他说:
我仍然坚持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我认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45)
理想还是空想?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面对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他从根基处展开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他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理论功绩是提出了生活世界与系统的矛盾,即“把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作为自己的指南”(46)。这一对当代问题切入的角度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整个现代社会说到底依然是资本统治的世界,资本的原则是财富、金钱,并且它在发展过程中不会顾及穷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相反还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当政治与经济同流合污,其结果必然是生活世界的普遍异化、殖民化。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矛盾与冲突的理论,从而最明快简洁地将现代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剥现在世人面前。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其目的是在经济与政治之外树立起一个新的标杆,作为衡量政治与经济的最高原则。而公共领域理论的目的则是确认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根源,并“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
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作为生活世界私人领域的代表出现在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合法性权力的真正源泉。只要维护、培育、发展公共领域,就会产生一种与系统金钱、权力原则相抗衡的新的社会力量——一种以社会团结、社会同一性为最高原则的“交往生产力”,这种交往生产力本质上就是合法性权力的真正基础。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平等性、普遍性、真诚性原则,试图使公共领域真正成为反映民意、形成共识的领域;提出了培育公共领域是民主社会的本质特征,而消灭公共领域是专制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公共领域的建设中,哈贝马斯特别重视政党和社团组织的作用,因为真正的“权力恰恰只能在这种交往的组织中产生”,并认为“只有内部实行民主的政党和组织才是批判的公共性的载体,而这些政党和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在我看来是仍具有再生能力的公共交往的真正枢纽”。(47)这就对公共领域的建设提出了一条完整的思路。哈贝马斯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构想不可谓不精细,然而仔细想来,又带有浓厚的空想性质。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哈贝马斯对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保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统治体制”的前提下,“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试图通过对话,通过精神或文化的力量解决当代最尖锐的物质冲突和政治冲突,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面对的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以及握有强权并为资本服务的统治者,这些人怎么可能坐下来与你平等地对话。“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48)要资本家放弃这些权力是不可能的。
从本质上分析,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是改良主义的,哈贝马斯对资本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而又要求资本能放弃资本的权力,维护社会同一性,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在哈贝马斯眼里,资本不仅合法,而且为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性:
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它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解决了问题。它为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不再来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根植于社会劳动的基础。……这样,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治统治就能“从下”而不是“自上”(借助于传统的文化)得以合法化。(49)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以公平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维护了私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以及把群众的忠诚同这种经营方式结合在一起”。(50)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都过时了,必须要用交往理论来代替,因而从哲学角度讲,哈贝马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谓交往理论,实际上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51)。其结果也就必然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同一。因为这种平等对话,结果只能是实力的较量,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它所直接体现……是社会力量的对比,即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统治。”(52)即使真正的公共权力来自公共领域,来自公众的支持,但是暴力却来自资本和政治的霸权,这种霸权能不干预公共权力的形成吗?思想离开了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哈贝马斯希望资本放弃资本的权力而追求社会同一性,这在现实中如何才有可能呢?
争取社会同一性的斗争,不能仅停留在形式上平等的对话,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斗争的结果。只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并互相配合,社会同一性才能真正通过制度和价值而被巩固起来。离开了经济与政治上反对资本霸权的斗争,人民大众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同一性呢?
注释:
①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第97、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③[德]弗罗姆:《逃避自由》,第354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④[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⑤[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86页,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
⑥⑦⑧[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⑨[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前言,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⑩[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7页。
(1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407页,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2)(14)(1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第125、125、41页,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3)(1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9、124页。
(17)欧力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第296页,重庆出版社,1997。
(18)(19)(20)(21)(22)(2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0、10、5、94、46、18页。
(24)(28)[德]汉娜·阿伦特:《暴力论》,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第156、159页,朱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5)(26)(27)(29)(30)[德]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第156—157、156—157、158、161、161页。
(31)[德]汉娜·阿伦特:《人类的情况》,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第162页。
(32)(33)(34)(35)(36)(37)(38)(39)(40)(41)[德]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第161—162、163、163、163、164、156—157、165、170—171、172、170页。
(42)[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页。
(43)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载《外国文学批评》,2000(1)。
(44)《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第167页。
(45)《哈贝马斯访谈录》,参见《哈贝马斯传》,第2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46)[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400页。
(4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9)(50)(5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见《二十世纪经典哲学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423、428、4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1)《哈贝马斯访谈录》,参见《哈贝马斯传》,第2页。
标签:公共领域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权力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阿伦特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