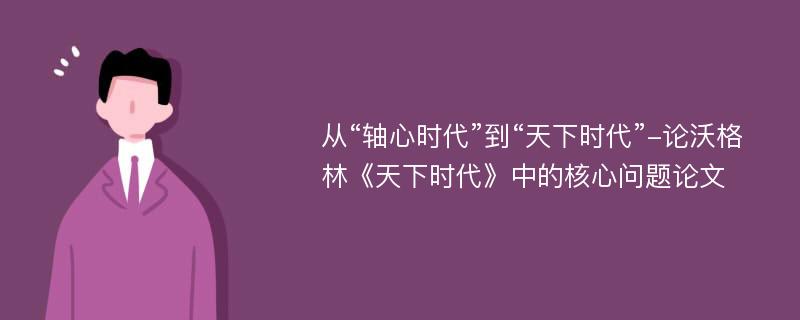
从“轴心时代”到“天下时代”
——论沃格林《天下时代》中的核心问题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18世纪初以来,欧洲的思想家开始面对和思考“中国精神”,典范人物可从莱布尼茨、黑格尔、韦伯一直数到沃格林。其中,沃格林算得上20世纪思考得最深的历史哲学家。他从世界政治史和政治观念史的双重角度思考人类的诸种“秩序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用“天下时代”概念取代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在地理上和历史时间上,“天下时代”指西方从波斯帝国到罗马帝国的帝国更替,与此平行的是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崛起,西方和东方平行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天下意识”。“天下时代”还有形而上学的普遍含义,即寓指这个世界的恒在性质:世界因群体或政治单位之间的冲突永远充满暴力、不幸和灾变。“天下意识”意味着对天下征服的精神反应:人类政治体之多样性及其冲突这件事困扰着我们,同样困扰过早期天下的帝国时代。无论在帝国式的政治体还是希腊城邦或以色列式的政治体那里,关于政治体起源的思辨都与历史之域相关。这意味着政治秩序的思考受到历史之域的限制,史学带有神话时间与溯源式叙事的基本形式。宇宙论式的帝国秩序紧紧包裹着人类的观念,以色列的存在经验才让人类的观念突破了帝国式的宇宙秩序。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因此在于:存在的飞跃没有像西方那样彻底打破宇宙论秩序。
关键词: 沃格林;灵知主义;“轴心时代”;“天下时代”;天下意识;政治秩序;“居间”伦理
从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纪事书中可以看到,致力于认识邻人的秉性是一个政治体成熟的标志之一。自18世纪欧洲思想家知悉中国以来,认真下功夫研究过中国文明的欧洲大思想家 (而非汉学家)屈指可数:从莱布尼兹(1646~1716)、黑格尔(1770~1831)、韦伯(1864~1920)数下来,恐怕就得直接数到沃格林(1901~1985)了。
欧洲的汉学家很多,但他们未必对欧洲文明的历史命运有自觉的承担意识。换言之,欧洲的思想大家关注中国文明,为的是更好地肩负起传承欧洲文明的历史使命。有人会说,欧洲的思想大家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远不如汉学家。但我们更应该说,他们理解中国文明时的问题意识远比汉学家深切,从而也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毕竟,我们迄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
沃格林自觉肩负起传承欧洲文明的历史使命体现于他用上了自己整个后半生的智识心力与灵知主义缠斗。但要认识这一点,我们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首先,沃格林的探究基于大量思想史文献,他亲自阅读过这些文献,要判定他的论断是否恰切,我们就得阅读他读过的那些原始文献。
第二,沃格林至少三次调整自己的思考视角,修改自己的基本观点。换言之,沃格林探究灵知主义的过程,同时是认识自己的过程。一个热爱智慧者在哲学探究过程中若不是同时在澄清对自己的灵魂的自我认识,就算不上真正的热爱智慧。
第三,沃格林针对西方历史上的灵知主义展开的现象学分析具有相当艰深的思辨品质,它基于对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的批判性改造[1](P90-94)。在《论意识理论》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关键性句子:
最终,我们与一个超越了的意识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以对它的对象性的知晓这一神秘[相联系];现象学尚未照亮这一关系,却只是“从外部”描述过它。[2](P52)
传统德育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单一、枯燥,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感,让教师产生倦怠心理,师生都只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理,只要将任务完成就可以,德育教育效果不理想。新型教学模式——微课的实施,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方式,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微课教学模式引入德育教育中,可以有效地激发高职学生的兴趣,培养德育素养,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论意识理论》以下面这句话结束对“意识哲学”的沉思:
如今我们看到的“政治观念史稿”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不过是因为沃格林把此前的材料用来构筑“秩序与历史”系列的前三卷[4]。按原定构想,这个系列的后三卷分别名为 《帝国与基督教》(中世纪)、《新教的世纪》(近代)和《西方文明的危机》(现代)。可见,“秩序与历史” 系列起初仍然带有思想史特征。
如果我们没有跟随沃格林进入他曾深入过的灵知心性现象学思辨的纵深,那么,我们断乎不能理解他在自己的探究历程中获得的灵魂觉悟。
一方面,酒店业行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行业,普通员工入职都是从基层做起,所以人员录用的门槛较低,从社会招聘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人员的录用门槛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饭店业复杂的工作氛围,工作氛围的复杂性造成员工跳槽思想变得正常和随意化;另一方面,酒店行业大都有面临经营的季节性,淡旺季的经营差别也致命整个饭店行业的员工需求弹性较大,有一些酒店不得不根据淡旺季的员工需求量来安排员工的人数,人员的经常变动也会增加员工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感,影响到从事饭店业的人。
一、灵知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嬗变
搞清灵知主义及其与西方文明历史嬗变的关系,并非沃格林在年轻时就有的哲学抱负,尽管他很早就对思想史上的“灵知”现象和与此相关的政治宗教问题产生了兴趣。按沃格林自己的说法,早在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思想界,“灵知主义从古代到现代的连续性”问题就已经成为话题,绝非他的发明。而直到写作《新政治科学》(1952)和《科学、政治和灵知主义》(1959),他才专注于灵知主义与现代现象的关联[1](P86)。我们知道,沃格林这时已经50 岁出头,在此之前,他的学术关注点一直游移不定。
1940年代初,移民美国的沃格林接受了一份稿约:写一部大学教科书《政治观念史》。受韦伯和斯宾格勒影响,青年沃格林把人类各大文明的历史比较视为首要的时代问题,毕竟,这也是18世纪以来形成的欧洲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因此,在写作教科书《政治观念史》时,沃格林注入了自己对西方政治观念历史嬗变的独特理解和问题意识。
5年之后,《政治观念史》已经接近收尾,沃格林猛然意识到,即便卷帙浩繁,陈述政治观念的历史也无法澄清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沃格林还意识到,“观念史这个概念乃是对实在的一种意识形态扭曲”,毕竟,“并没有什么观念,唯有表达直接经验的符号”[1](P83)。
不仅如此,如果说世界历史有一条线性发展模式的史观是荒谬的,那么,政治观念的历史有一条线性发展模式的史观同样荒谬。要深入探究历史上的政治观念,就必须与历史中具体的政制嬗变联系起来。
沃格林毅然撇下长达4 000 多页的《政治观念史》成稿,开始撰写多卷本“秩序与历史”系列,以探究人类文明的“历史意识”。当然,沃格林并不认为,写作《政治观念史》是白费功夫,毕竟他由此熟悉了思想史上的大量原始材料[1](P98-103)。
实际上,沃格林终生都没有离弃“观念史”。毋宁说,他逐渐意识到,必须先澄清“观念”赖以形成的意识结构本身,才能把“观念史”的问题看透。但要搞清人的意识结构,就非得对意识现象本身作深入的现象学分析不可[2](前揭,P450-451,P454-474,P484-494)。
自我论界域的基础主体性,作为胡塞尔哲学不容商榷的最后通牒,是精神层面虚无主义的症候,它作为反动虽仍有其功绩,但也仅此而已。[2](P63)
“秩序与历史”系列有一个总的导言,但不在第一卷,而在第二卷,即《城邦的世界》的导言“人与历史”[5]。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秩序与历史”系列的写作抱负与挽救欧洲历史哲学的“没落”有关。
二、“轴心文明论”与西方文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雅斯贝尔斯(1883~1969)出版了《历史的起源和目的》(1949),被学界视为继《西方的没落》之后最重要的比较历史哲学论著。雅斯贝尔斯力图论证,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世界上三个地区的文明政治单位不约而同地共同建立起了一个人类世界理解自身的精神框架。直到今天,“轴心文明论”仍然是一些人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观念范式。在沃格林看来,真正的“历史哲学”问题涉及有关“存在真理” 的理解及其高下之争,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把人类文明形态放在一起搅和,无视人类各大文明单位在政治生存上的差异,以为可以通过“发现共同人性”的理念来消弭人类各文明传统的理念冲突,无异于让“历史哲学问题”彻底消失[5](P88,P90)。因此不难理解,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很快就让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论”遭遇灭顶之灾,强调文明差异的“非轴心文明论”或否定元典的“零度思维”甚至“非文明论”迅速成为学界主流。
学术思考和研究离不开某种观念范式,如今的中国学界与欧美学界相似,显得是在“轴心文明论”与“非轴心文明论”两极之间摆荡。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有必要了解沃格林的思考。毕竟,沃格林尖锐地批评雅斯贝尔斯的话用在后现代的“零度思维”身上同样合适:尊重各大文明的“存在真理”是一回事,“堕落为一种宽容,无视在追求真理和眼界方面存在的档次差异”是另一回事[5](P91)。如果真正的“历史哲学问题”在于各文明政体对“存在真理”的理解及其高下之争,那么,历史哲学就必须在意识层面展开关于“存在真理”的争辩。
沃格林心怀忧虑地感觉到,“随着历史地平线的扩展,存在中的飞跃的多样性和应对性问题再度尖锐起来”,“理论状况相当混乱”。因为,有目共睹的是,急剧增长的实证史学知识“冲垮”了西方传统的精神观念,作为对存在危机的反应,“对历史的灵知式思辨甚嚣尘上”[5](导言 P52)。像当年的汤因比(1889~1975)一样,如今的全球史学(global history)极大地增加了“研究文明的数目”,但不等于展现了“人类历史的问题”。沃格林的思考值得关注,不仅因为他致力于从比较哲学角度考察世界政治史上各大文明单位对“存在真理”(truth of being)的理解,毋宁说,他所关注的“智识秩序”(intellectual order) 的历史问题是我们当今值得关注的首要问题。
我吓得不轻,跳下树就要走。眼睛一瞥,发现纸团上有字,什么字却辨认不出来,心想,我何不把纸团取下来瞧瞧?
这里出现了沃格林的历史哲学独有的两个术语,值得特别注意。所谓“存在中的飞跃”(leaps in being,又译“跃入存在”)即对存在的理解,由于这种理解无异于个体灵魂接近实在的终极奥秘的向上飞升意识,沃格林也称之为 “神显事件”(the theophanic events)。显然,这种对存在的理解仅仅体现在各文明政治体中的极少数思想人物身上,而这些智识头脑无一例外地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处境,因此,“存在中的飞跃”也就自然呈现为所谓的“历史意识”。
“秩序与历史”致力于考查各文明政治体中极少数智性超迈之士的“历史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关于“历史意识”的精神现象学。因此,在沃格林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远比一个世纪之后的斯宾格勒(1880~1936)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高明。毕竟,黑格尔关于“存在真理”的理解不仅更精深,而且对“智性和精神秩序”的历史问题给出了富有哲学深度的解释[5](导言 P85)。
由于有自觉的韦伯式的文明比较意识,沃格林看到,黑格尔关于意识的经验“源于作为存在本质的主体的经验”,这与印度“《奥义书》的思辨”别无二致。这种与宇宙同一的最高意识或者说“超个人和超世的现实的一致性”,实质上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神秘主义”意识,比如犹太教神秘主义的所谓“喀巴拉”学说[5](导言 P86)①。
1.3 口腔黏膜炎分级标准[12] 参照WHO抗癌药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分级标准,将口腔溃疡分为0~3度,0度:无任何口腔不适;I度:口腔黏膜干燥、潮红、变薄,未有破损,进食时可有轻触痛;Ⅱ度:局部口腔黏膜有轻微破损、脱皮,破损灶不超过3个,范围不超过3 mm ×3 mm,进食时伴有明显疼痛;Ⅲ度:口腔黏膜多处溃烂、出血,伴有剧烈疼痛,且范围超过3 mm×3 mm,不能进食。
由于这种向上飞升的意识把智性的灵魂带到了超出自然宇宙的天外,“神秘主义”意识堪称最高的存在意识。在沃格林看来,保罗—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式的存在理解同样带有这种神秘主义取向。黑格尔“把启示的逻各斯化约为哲学的逻各斯,进而将哲学逻各斯化约为意识的辩证法”,其实是在模仿基督教的启示真理[5](P85)。
此前一直被诟病的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一方面反映了金融业偏重于体系内空转、陶醉于“钱生钱”的金融游戏、忽略了对社会客观金融需求的照顾;另一方面也表明实体经济面临困境,这显然也不利于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向上飞升的灵知意识尽管能把智性的灵魂带到超出自然宇宙的天外,却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智性灵魂脚下的历史实在。在1950年代的反思中,沃格林越来越确信自己的如下感觉没错:超出天外的神秘意识回头看待历史的实在过程时,难免严重扭曲现世中的实在。
沃格林在《天下时代》的“导言”中已经深入阐述了“意识的畸变”,若将这个“导言”与“秩序与历史”前三卷的“导言”(即《城邦的世界》中的“人与历史”)加以比较,我们就能清楚看到,沃格林的思想转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的灵知式思辨”的反思愈来愈哲学思辨化,更确切地说愈来愈现象学化,更少受思想史框架束缚。1965年,沃格林在德国政治学协会做了题为“何为政治实在”的学术报告,其中“对根基的意识” 一节能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他要谈论的是“政治实在”[2](P393-440)。
在以赛亚的预言里,我们碰到一件怪事,以赛亚告诫犹大国王,不要依赖耶路撒冷的防御和他的军队的力量,而是要依赖自己对耶和华的信仰。如果国王有真诚的信仰,上帝就会做余下的事情,在敌人中间降下瘟疫或恐慌,该城的危险就会化为乌有。国王具有足够的常识,未听从先知的建议,而是依赖防御和军备。而先知仍然认为,实在的结构会因信仰行为而产生有效的变化。[1](P88)
与灵知意识对立的是“常识”,因此,沃格林称扭曲“常识”的灵知意识为“变形启示录”(metastatic apocalypse)式的经验意识。由于黑格尔置身于启蒙后的欧洲历史处境,在沃格林看来,他的历史哲学因携带灵知意识而有“严重缺陷”:虽然印度的神秘经验与黑格尔的绝对意识或“新教内在论的确正好背道而驰”,但“都惊人地产生了类似的历史后果”。具体而言,晚期《奥义书》走向了无神论救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经黑格尔左派走向了马克思的无神论,“这些无神论后果使灵知式思辨(gnostic speculation)的非历史特征更加暴露无遗”。因为,
①晴雯冷笑道“这一遭半遭儿的算不得什么,过了后儿还得听呵!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第二十七回)
灵知是一种囿于神话形式的思辨运动,而现代灵知,如黑格尔式的诸同一性(the Hegelian identifications)所显示的那样,乃是从分殊大步退回到前历史的神话之浑然一体(the pre- historic compactness of the myth)。[……]当有限的思辨(finite speculation)让自己拥有了历史意义,哲学和基督教就给毁掉了,历史的生存也走向了没落。(译文略有改动)[5](P87)
这段说法的要点是:虽然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理都基于向上飞升的意识或拒绝此世的意识(即所谓“超世”意识),毕竟没有彻底抛弃实在及其过程(所谓的“历史”),而是将其涵括在出世意识之中。与此不同,灵知意识是彻底的超世意识(“非政治”意识),以为个体的“有限思辨”可以超升为非宇宙式的“无限思辨”。
现代灵知意识的怪异之处在于,凭靠彻底的超世意识构造的神话转而积极入世地,人为打造灵知式的实在及其历史,沃格林称之为“有限的思辨让自己拥有了历史意义”。这样一来,古人的超越意识同时具有的节制和审慎品质就被抛弃了,由此催生出各种扭曲实在的政治行动。因此,对沃格林来说,把灵知主义与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理的抵牾视为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历史关系,无异于无视西方精神意识历史地经历过一场“智思情势”(noetic situation)”的古今之变这一思想史事实[2](P62,P438)。
可以看到,虽然“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考察的仅是希腊化时期之前的“存在的飞跃”,反思“对历史的灵知式思辨”(gnostic speculation on history)已经成为沃格林的“历史意识”精神现象学的核心问题。
时隔17年之后,《天下时代》让我们看到,沃格林对神秘灵知的反思有了明显的新突破:“居间”(metaxy)和“畸变”(deformation)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足以证明,沃格林对作为“存在的飞跃”的历史意识的理解发生了决定性转变。
在《城邦的世界》中,“居间”一词仅出现过一次,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出现过3 次,在《天下时代》 中出现的地方,仅索引就有近一页篇幅[3](P490-491)[2](P9)。至于“畸变”一词,我们在“秩序与历史”前三卷的索引中一次也见不到,而在《天下时代》中,按索引的指引至少涉及10 多页篇幅,而实际上索引并未穷尽所有出现过这个语词的地方。
“畸变”是沃格林发明的概念,它指“意识的畸变”(a de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从而是一个现象学概念。沃格林喜欢自造术语,这不是一种哲学自恋癖,毋宁说,为了更准确地描述“神性显现的人性构成的经验”,他不得不自造术语[1](P88)。
按沃格林的用法,所谓“畸变的心灵”(deformed mind)指智性灵魂“直面实在之奥秘”时的“自我显现式的造反”(egophanic revolt),与“神性显现的人性构成的经验”相对,从而“遮蔽了古典和基督教的意识结构中的神显”[1](P87)。由于 “神性显现式的”经验与“自我显现式的”经验都是理智天分很高的极少数人(文明政治体的智识头脑)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直面实在之奥秘”时的经验,辨识两者的差异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段话显然直接指向“逃离”世间的灵知意识,或者说让保罗的启示录式的“逃离诉求”面临柏拉图的挑战。因为,沃格林紧接着就说,“启示录式的想象通过摆弄意义的奥秘而威胁到意识的均衡。”随后,沃格林就提到保罗“通过变形想象而进行歪曲的可能性”,其逃离诉求的根本理由是:
如果说“实在之奥秘”始终是“一”,那么,各文明政治体的智识头脑对“实在之奥秘”的理解或者说“存在中的飞跃”就是“一”的分殊化意识。这听起来有点儿像宋代理学家所说的“理一分殊”,但沃格林关注并深入思考的问题并非是这种分殊化意识对“实在之奥秘”的不同理解,而是“意识的畸变”作为 “灵魂病理学中的现象”(the phenomena that in psychopathology)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表现及其与实在过程(政治史)的历史关系。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智性灵魂“直面实在之奥秘”的经验本来是一种超越性经验,这种经验使得个体灵魂沐浴在神性的光照之中,但它也容易“畸变”为“自我显现式的造反”,即自以为自己的超越意识就是神性光照本身。由于这种“自我显现式的造反”意识说到底基于偶然的个体性情,我们要辨识自己的灵魂是否偶然撞上了“意识的畸变”绝非易事,除非我们的灵魂有真正的自我反省的意愿。
在宗教经验中,尤其是在强调“属灵”意识的宗教经验中,超越性意识最容易发生“畸变”而又不自知。这意味着,“自我显现式的”超越性意识固然也是灵魂品质很高的极少数人的意识,但它扭曲了人的在世状态,以至于必然败坏人“直面实在之奥秘”时的经验,因此沃格林称之为“属灵病理学的畸变”(Pneumopathological deformation)[3](P351)[2](译注 3)。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以为,只要是在颂扬灵知式的“超越意识”就没问题,或者就一定是好事情。
“畸变的心灵”或“自我显现式的”超越性意识现象,见于所有文明意识高度发达的政治单位,从而堪称普遍的人性现象。在《天下秩序》题为“普遍人性”的第七章结尾时,沃格林带总结意味地写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历经民主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具体形态的演变取决于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变化,取决于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但是,无论是党领导的哪个阶段、哪个形态的统一战线,都致力于构建保证中心任务实现的共同体。统一战线所构建共同体为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体现了阶段性和长期性、局部性和整体性的统一。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的纵向逻辑与统一战线的性质演变方向一致,经历从阶级联盟的共同体到政治联盟的共同体的发展。
直面实在之奥秘,意味着生活在信仰中,它是所望之事的实质,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这些终末论意义上的为人所期盼却未曾得见的“事物”,被以变形的方式畸变为 (metastatically deformed) 一种终末论标志(它被赋予将在“历史”中为人所期盼和得见之物),并且这种作为终末论事物的实质和证据的“信仰”,被相应地畸变为一种黑格尔式、马克思式或孔德式的“科学体系”(它那唤启性的魔法意欲“在历史中”实现那些期盼),在这个时候,疑问就能得到比它在人类历史中曾经经历过的更加充分的分[殊]化,但奥秘将被摧毁。对奥秘的摧毁体现在围绕各种“答案”的当代教条之争中。[3](P441)
在自传性“反思”中沃格林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沃格林生前未来得及出版的《求索秩序》(计划中的“秩序与历史”第五卷)更为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居间”和“畸变”这两个语词——我们还得加上柏拉图这个人物,仍然是甚至更是关键词[6]。
三、“天下时代”与成熟之人及其自由
《天下时代》共 7 章,位居中间的 3 章(第 3 至5 章)围绕“逃离[此世]”主题就灵知主义的核心问题展开了精彩的现象学辩难。与其说《天下时代》作为“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是前三卷的延续,不如说它完整替换了“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进入灵知主义诞生的历史时刻直凑单微,与“灵知传统”创始人的灵魂展开面对面的哲学辩驳。
灵知主义诞生于世界历史的第一个 “天下时代”,这个时代的现实特征是帝国之间的“征服”,而所谓“征服”的另一面含义则是世上的生灵涂炭。换言之,作为“逃离”世间的超升意识,“灵知”意识并非没有退出世界的现实因由。按照灵知人的观点,此世的自然性质或本相从根本上讲是恒在的恶,而恒在的战争状态就是其具体体现。据说,由于命运女神才最终掌管着战争的胜负,对任何政治体来说,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分,只有命好或命不好的际遇。
沃格林笔下的“天下时代”这个语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指“从波斯帝国的兴起开始,延续到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历史时期,也就是从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到以保罗—马克安为标志的灵知主义诞生的时期[3](P182-186)。另一方面,“天下时代”还有形而上学的普遍含义,它寓指此世的恒在品质:现世因群体或政治单位之间的冲突永远充满暴力、不幸和灾变。正是基于此世的这种恒在品质,“逃离” 世间的终末意识主张 “反宇宙的蔑视此世”(contemptus mundi)伦理才有了正当理由:
本次大会对当下“三农”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宿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光华指出,第八届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对政产学研推一体化、校企合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搭建起政产学研推进一步沟通平台,凝练智慧,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沃格林让希腊哲人提出的“居间”伦理与这种“逃离”伦理针锋相对。“居间”概念不是沃格林的发明,而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发明。在沃格林看来,“居间”是希腊哲人伦理的符号,或者说哲人面对此世本相的伦理态度,称为哲人的历史意识也行。换言之,在《天下时代》中,沃格林不仅用“居间”和“逃离”来表征两种截然不同的灵魂飞升意识,而且让“居间”伦理据理反驳“逃离”伦理。
高中物理所涵盖的领域有光、热、力、声、电这几方面内容,所学的内容比较抽象却都和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教师可以通过生活当中的经验,提高学生高中物理的学习能力.将生活存在的现象与高中物理理论相结合,丰富了学生高中物理知识.
在第1 章“历史创生论”中,沃格林阐发了具有形而上学含义的“居间”概念,并将其视为古希腊哲人的在世经验突破宇宙论神话的标志[3](P126-143)。在接下来的第2 章“天下时代”中,沃格林让我们看到,时代的灾变如何带来“精神层面的天下”意识:在这里,保罗、摩尼和穆罕穆德依次先后出场[3](P205-219)。
随后的第3 章题为“历史过程”,这个术语在沃格林笔下也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指通常所谓的现实历史或人类生活的经历,不用说,“历史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种种暴力、不幸和灾变。另一方面,这个术语又带有沃格林所赋予的独特含义,即各文明政治单位的智识头脑求索根基之真理的内在意识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面对现世中的暴力、不幸、灾变时的伦理态度。
下面这段说法出自《何为政治实在》,它清楚表达了这一含义:
历史不是一个由各种无关紧要的对象性材料[形成]的场域,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随意的标准来从中进行拣择,以便构建某种历史“图景”。毋宁说,历史由意识所建构;这样一来,何者在历史层面紧要或不紧要,由意识之逻各斯来决定。尤其重要的是要提到,历史在其中建构其自身的时间,并不对应外部世界的时间(在世界的时间这里,人的生命及其身体基础留下了其痕迹),而是对应着对根基之渴爱与求索这个内在于意识的维度。[2](P415,比较P408-409,P445)
所谓“对象性材料[形成]的场域”相当于如今实证史学占据的领域,沃格林断然否认这个领域的“材料”堪称“历史”,尽管他随后说的“外部世界的时间”为实证史学的领域留出了地盘。
在1956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沃格林更为简洁也更为明晰的表达:
该算法的硬件实现采用的是Xilinx ML507评估板板载xc5vlx110t型号FPGA[9]。FPGA的功能由具体配置逻辑决定,且提供丰富的IP核资源供参考[10]。系统包括DDR2控制器、捕获模块、相关模块、双口RAM、算法模块以及时钟模块,其结构如图3 所示。
历史是人类psychē[灵魂]的展开;历史书写是通过史学家的灵魂来重构这一展开。[2](编者导言P19)
由此可以理解,在沃格林笔下,所谓“历史过程”更多指“意识过程”,即超越性意识与实在的关系意识。题为“历史过程”的第3 章第1 节即题为“实在过程”,这一节又分三小节,沃格林将古希腊自然哲人的代表阿那克西曼德摆在中间位置,以突显自然哲人对“实在过程”的理解。他特别提到,自然哲学的出现“得益于古希腊城邦毗邻亚洲各帝国的便利位置,伊奥尼亚人拥有大量机会去体验天下时代的暴力”[3](P254)。
言下之意,古希腊哲人并非不知道此世的恒在品质是恶。随后,沃格林以高度概括的笔法从柏拉图谈到康德、怀特海、海德格尔,由此引出了对“理智性意识领域”的历史的现象学分析[3](P255-258)。严肃而又富有哲学旨趣的问题来了:在沃格林看来,一个纯粹的智识头脑应该如何与尘世保持距离?
虽然“居间”概念的要义来自伊奥尼亚哲人的生存经验,即人置身于此世与超世之间,人既渴望出离又深深爱恋着这个“之间”(In-Between),但对这个概念最为精彩也最为透辟的阐发见于柏拉图的《会饮》[3](P267-269)。在阐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居间”论之后,沃格林突然插入了世界史家布克哈特(1818~1897)在19世纪末所表达的极度悲观主义的历史意识或“非政治人”的伦理态度[3](P276-280)。我们应该知道,沃格林在“政治观念史稿”卷一 “导言”提到的“非政治的”政治哲学传统,并非出自他自己的思想史洞见,而是来自布克哈特②。
保罗因在该进程中看不到任何意义而深感绝望,同时又对由那些终末事件带来的有意义的终结而深怀希望。[3](P404)
这印证了笔者的阅读感觉:沃格林的“天下时代”概念具有形而上学式的普遍历史含义。这意味着,从古至今乃至不可预见的将来,无论文明多么“进步”,“天下”处境都让人极度悲观绝望,总会不断有人萌生宁可做“厌政治的异乡人”(the apolitical strangers)的念头。
结束对布克哈特式的“非政治人”气质的论述时,沃格林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智性“成熟之人”(spoudaios/mature man)的德性问题:
成熟之人的各种德性虽然为人性提供了标准,但没有被期望成为人民群众(Plethos)中每个人的德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甚至试探性地为不同的基本类型提出多样化的伦理标准。如今,由各种生存类型及其各自的问题构成的这片广袤领域,已然为一种启示录式的幻梦遮蔽:只有一种“道德”,它适用于一个由全都平等的人构成的共同体。[3](P281)
所谓“启示录式的幻梦”指的正是灵知意识,这意味着,在沃格林看来,布克哈特对现世的极度悲观情绪和与生俱来的厌政治心性,对热爱智慧者来说,是检验热爱智慧的德性是否成熟的试金石。换言之,“非政治”的伦理态度或“逃离”意识,不过是灵魂的理智德性尚不成熟的表征。
沃格林特别提到,“保罗不是一个哲人”,而是为“向他现身的基督而工作的传教士”[3](P335)。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懂得,要指望世上所有人的灵魂都在理智德性方面变得成熟断无可能,因此,必须为不同天性的灵魂设立不同的伦理规矩。他们没有想到,帝国的更迭或世间的恶使得“一种启示录式的幻梦”在战乱频仍的地中海周边迅速蔓延。
沃格林紧接着就说:
这个幻梦表征着一种严重的生存畸变(deformation of existence),而它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带来了以下后果:在伦理上,这个幻梦是当代个体无序与社会无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理智上,对那些梦想家来说,“大众并未按照启示录的要求行事”这一事实持续令他们感到诧异。有这样一种“灵魂学”,它幻想着某种内在于世界的“灵魂”(psyche),从而使那些有关参与式实在的问题隐而不彰;这种“灵魂学”进一步加剧了由启示录式的说教对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造成的损害。[3](P281)
本文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遵循问题产生发展的特定环境进行思考分析,结合高中《文化生活》课堂中出现的问题,紧密联系高中政治课教学,深入挖掘分析现有教学环境和条件下所出现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紧紧抓住教师和学校的作用,提出相应具体可行的措施,以期更好地落实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并完善教学方法,从而能够在日后对高中阶段《文化生活》的教学产生积极影响。
取参考文献[7]中的模型试验参数:挡土墙高度H=1.0 m,砂土容重 γ=15.6 KN/m3,填土内摩擦角 φ=34.2°,墙土外摩擦角 δ=2φ/3=22.8°,土体达到被动极限平衡状态挡土墙所需要的平动位移量Sc/H=8.5%。为比较分析,取RT位移模式墙底的最大位移S1与墙高H之比 S1/H=5.5%(情况1,即 S1/Sc=0.65)和 S1/H=11.6%(情况 2,即 S1/Sc=1.36)进行计算。
在《天下时代》接下来题为“征服与逃离”的第4 章中,沃格林对柏拉图作品中的“居间”意识展开了深入的现象学辨析,所涉意识哲学层面的义理极为抽象,行文也颇为艰涩。笔者觉得,要读懂这一章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其中第3 节“意识的均衡”[3](P319-331)。尽管如此,有一点清楚无误,无需特别的思辨脑筋也看得明白:柏拉图已经预见到,启示录式的“逃离”灵知对各种类型的灵魂来说都是一种心灵的危险。
The mean crystallite size of the line broadening of the(101) plane wa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Scherrer formula[17],
因此,沃格林在结束这一章时说:
柏拉图充分了解人的精神均衡的不稳定性和出现精神紊乱(nosos)的可能性,因而他在踏足这类问题出没之处时,总是如履薄冰。[3](P328)
沃格林关于灵知主义及其与西方政治史之关系的最终看法,见于“秩序与历史”的第4 卷《天下时代》(1974)[3]。该书与“秩序与历史”的第3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1957)相隔足有17年之久,出版时沃格林已经是70岁出头的老翁。《天下时代》开篇第一句即宣称,此书“背离了我曾经为‘秩序与历史’设定的计划”。如英文版编者所说,读者“不难想象,此言一出举座皆惊”[3](P3)。到了这把年纪,沃格林还在修正自己,并未故步自封,可见他颇为自觉地以古希腊贤人梭伦为榜样:“吾老来为学逾勤”。
紧接第4 章之后的第5 章题为“保罗的复活者意象”,我们能够感觉到,仅仅这个标题就极富挑战性。沃格林开篇就说:
柏拉图将神显事件与对宇宙的经验保持在均衡中。他并未容许狂热的期盼歪曲人的境况。……就社会而言,理智性秩序的各种范式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但它们并不会终结于心灵理智性程度较低的大众的斗争;就历史而言,人们并不指望对结盟民族的洞见能阻止历史走上神国之路。总而言之,柏拉图并未容许神显事件发展成启示录式的“充满整个世界的大山”。[3](P332)
在沃格林看来,“神性显现式的”经验体现为智性灵魂蒙受神的引领,进而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在世状态,“自我显现式的”经验则体现为智性灵魂自居为神的视力本身,以为自己的智性即神的智性,并凭靠这种自称属灵的理智构想重整乾坤的计划,如果可能的话就付诸行动。由于这种实践行动必然扭曲实在本身,沃格林称之为“畸变行为”(deforming action)。
我们的身体将从日渐衰亡的名义束缚中获得自由(或救赎),进入神之子民所得享的自由和荣耀。[3](P332-333)
这种自由观引导世人“逃离”世间,堪称启示录式的消极自由,它显然有别于苏格拉底—柏拉图所理解的热爱智慧者或成熟之人的“自由”。笔者不禁想起,苏格拉底临终前对热爱智识的年轻人语重心长地说:
这种男人会热切追求涉及学习的快乐,用灵魂自身的装饰而非用不相干的装饰来安顿灵魂,亦即用节制、正义、勇敢、自由和真实来安顿灵魂——就这样等待去往冥府的旅程:一旦自己的命份召唤就启程。(《斐多》114e4-115a3)
苏格拉底的这段临终教诲让我们看到,“安顿灵魂”的德性首先是政治德性(节制、正义、勇敢),并用“自由和真实”取代了通常的“智慧和虔敬”德性。显然,如此“保持洁净”不可能会是启示录式的消极自由;相反,要求普遍洁净的启示录式的消极自由倒可能会反转为彻底变革世间的积极自由诉求。
“保罗的复活者意象”一章中有个小节题为“真理与历史”,其中的一段话让笔者读起来触目惊心:
革命的杀戮将会诱发“嗜血欲”;从这种嗜血欲中,“人”将会作为“超人”出现,进入“自由王国”。来自这种嗜血欲的魔法,是保罗关于复活者意象的承诺的意识形态等价物。[3](P349)
沃格林把“嗜血欲”算到意识形态式的杀戮头上,明显过于简单化。他熟悉世界政治史,他当然知道,“嗜血欲”体现在形形色色的杀戮之中,而非仅有“革命的杀戮”才体现了“嗜血欲”。圣巴托洛缪(La Saint-Barthelémey)屠杀、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都算不上“革命的杀戮”,却不能说没有让人看到世间的“嗜血欲”。
尽管如此,我们能够理解,沃格林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式的杀戮,因此,他把意识形态式的“恋尸癖”与保罗的“逃离”灵知及其属灵愿景联系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甚至惊怵。由此可以理解,恰恰在“保罗的复活者意象”一章中,沃格林凭靠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居间”伦理进一步辨识了“历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y)与“历史中的意义”(the meaning in history)的差异,绝非偶然。
所谓“历史的意义”是现代欧洲历史哲学的枢纽概念,在沃格林看来,这个堪称灾难性的概念恰恰来自保罗的“逃离”灵知。换言之,如此灵知诉求颠覆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居间”伦理,才会让17世纪以来的欧洲哲人逐步构建起“历史的意义”神话:“保罗能以历史的意义(a meaning of history)来取代古典的历史中的意义(the classic meaning in history)”,因为他“将伦理学和政治学贬谪至历史的边缘地带,这种历史已被缩减为通往变形的逃离”[3](P354-355)。沃格林并没有忘记提到,古希腊的“非政治” 哲人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芝诺来雅典后,经过长时间考虑,他加入了已经与城邦彻底决裂的犬儒学派”[2](P62)。
实现“历史的意义”是欧洲现代历史哲学的诉求,这意味着,欧洲现代哲人身上携带着保罗式的灵知诉求。寻求“历史的意义”表征着哲人德性的品质畸变,其具体体现即染上了启示录式的“逃离”伦理品质。用沃格林的术语来讲,这叫做“生存的自我显现式畸变”(egophanic deformations of existence),其结果是产生出一种“想象出来的历史”(imaginary history),正是这种“历史”使得“人类的大屠杀”(the mass murder of human beings)成了有意义的行为。因此,说到底,欧洲的现代历史哲学是哲人德性品质畸变的结果[3](P358)。
沃格林得出结论说,种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哲学不过是“畸变模式(the mode of deformation)下的保罗式神话的种种变体”:“现代的反叛很大程度上是其所反叛的‘基督教’的发展结果。”人们只能将这种现代反叛理解为对那些“被启示给耶稣和使徒们”的“神显事件的畸变”(the deformation of the theophanic events),否则,种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哲学将无法理解[3](P367)。毕竟,“自18世纪中期以来,以‘历史哲学’名目出现的那类阐释”,并非是“对历史及其秩序的智性阐释”,毋宁说,它们不过是“对意识形态社会场域的自我阐释行动”[2](P483,比较P488-489)。
沃格林把形形色色的灵知视为精神疾病,而这种疾病看似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是“对生存的各种迷恋性畸变”。沃格林提醒我们,如果仅仅看到灵知人的“逃离诉求”是一种精神性的走出实在牢笼的灵魂超越,却看不到这种超升式的“逃离”意识本质上很可能是一种对现世的迷恋,看不到超越宇宙的向上“逃离”意识一旦遭到否弃(近代欧洲的反基督教取向),这种迷恋现世的心性必然会以一种看似属灵的激进形式表达出来[7],那么,我们对历史中的灵魂畸变的认识就不仅太过简单,也太过肤浅。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针对“逃离诉求”的灵魂畸变,沃格林为何特别强调“成熟之人”的德性。在识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政治正义”的表述时,沃格林具体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成熟之人”即“明智者”(phronimos)的德性[2](P157-164)。在这里我们看到,沃格林事先让“成熟之人”概念明确针对当今时代的“灵知分子”: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伦理学既不是一系列道学原理,也不是像我们时代某些生存论的灵知分子(existentialist gnostics)所做的那样,让生存逃离此世的牵缠 (complexities of the world),并将其收缩进[时刻]准备的张力状态或某种终末期待中,而是各自具体情势下行动的实在性之中的生存真理。[2](P154)
这意味着,“成熟之人”的德性最终体现为在历史的具体生存处境中践行正确的言行。“成熟之人”这个语词已经有多种中文译法,不同译法体现了对这个语词的不同理解。按古希腊原文,在笔者看来,仍然应该译作“高尚之人”。如沃格林在这里的解释:
spoudaios 是成熟的人,他希求真正值得希求之物,并正确地(rightly)判断一切事物。所有人都希求好[东西],但他们对何为真正的好[东西]的判断,却受到享乐的蔽晦。在既定的人群中,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找出何为真正的好[事物],结果会是:有多少不同品质的人受访,就有多少不同答案(《尼各马可伦理学》1113a32),因为,每种品质都认为它所希求的是好[事物]。
我们应当求教于spoudaios:这种人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能看到“各种具体事物中的真”,因为,他仿佛就是这些具体事物的标准与尺度(《尼各马可伦理学》1113a34),这是我们那些“经验论”社会科学家们应当注意的一个方法原理。[2](P157)
可见,虽然沃格林用了“成熟”来理解spoudaios,但我们应该说:所谓“成熟”意味着智性正确地追求“高尚”并践行高尚的正确。否则,一个人无论智性或超越意识有多高,都谈不上生存德性方面的成熟。
四、畸变的心灵与消极自由意识
《天下时代》位居中间的3 章(“历史过程”—“征服与逃离”—“保罗的复活者意象”)呈现了沃格林反思古今启示录式的灵知主义的最后成果。在这场意识现象学式的辩驳中,柏拉图 (公元前 427~前 347)与保罗(公元 3~67)虽然相隔 3 个世纪,却成了一对决斗角色。显然,这场对决更多具有现象学思辨性质,尽管它仍然发生在思想史的框架中。
因此,在“征服与逃离”一章结尾时,沃格林宣称:
我已经考察过天下时代里的灵知主义运动的一些方面,它将神性实在分割为一个真正神性的超越和一个由精灵塑造结构的世界。这些早期的运动试图通过将居间的各极分割成作为实体的此世和超越,从而逃离居间;而现代的启示录式灵知主义运动,则试图通过将超越转化成此世而取消居间。[3](P331)
笔者难免好奇:沃格林的思考在什么时候取得了这一决定性的新进展?
在沃格林自己出版的文集《记忆》中,有一篇长文题为 “时间中的永恒存在”[2](P351-389)。看得出来,这篇文章是《天下时代》的缩写版,首次刊发时间在1964年。看来,沃格林的新觉悟发生在他年届60 岁的时候。坦率地说,笔者未读《天下时代》之前时读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读完《天下时代》再重读这篇长文,笔者不禁为沃格林的苦涩而又艰辛的思考深深感动。
文章标题就意味深长:“永恒”与流变的时间相对,严格来讲,也只有在流变的时间中,“永恒”才显出其意义。同样,善与恶相对,美与丑相对,正义与不义相对,高尚与低俗相对,严格来讲,正是在充满恶和永远都不会完美的现世之中,善、美、正义、高尚才显得出其意义,而且弥足珍贵。
不难设想,若非某些心性坚韧的心智在此世中肯定和坚守善、美、正义和高尚,这样的对立断无可能。换言之,能否在此世中肯定和坚守伟大的政治品质,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心智偶然具有的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尤其是坚韧德性。毕竟,即便心性很高,也难免因恐惧恶、丑、不义和低俗而产生“逃离”此世(逃离政治)的想象。
由此可以理解,沃格林为何会越来越关切“哲思着的人”(philosophizing human being)或 Noetiker[智思人]的德性品质[2](P403)。保罗不是智思人,而是“属灵人”(Pneumatiker),追随保罗的马克安不仅不是智思人,而且是“属灵人”中的异类,即parekbasis[偏离]属灵意识的“灵知人”(Gnostiker)。无论怎样“偏离”,就非智识性心性而言,马克安与保罗属于同类。
沃格林看到,智思人参与终极奥秘的方式与神话式或灵知式的参与方式有德性品质上的差异,更明确地说,“在达成自我理解的明澈性方面”,神话思维式的意识和属灵人或灵知人的意识都不如智思人[2](P406-407)。在参与神性的意识经验方面,属灵人尤其灵知人不可能凭靠智识反省自己,因为,非智识性意识不可能成为这种意识本身的“批判工具”。属灵人和灵知人特别喜欢说“灵语”,用沃格林的说法,即过分信赖不受“理性掌控”(rational control)的“迷醉性语言”(obsessive language),就是欠缺智识性意识的体现[2](P453)。
“灵语”不仅体现为属灵人或灵知人的自我迷醉,而且特别能让周围的人迷醉,因为“灵语”具有打动心灵的修辞力量。对热爱智慧者来说,蔑视非智识性的参与终极奥秘的意识方式,不仅徒劳而且没有意义。毕竟,“属灵人”或“灵知人”是一种人的心性类型,而非智识性地参与终极奥秘的意识方式自有其无可辩驳的道理。毋宁说,热爱智慧者必须当心自己变成了“属灵人”或“灵知人”,同时也得警惕“属灵人”或“灵知人”冒充智思人,仿佛灵知还得到了智识的担保。
沃格林让柏拉图与保罗较劲,以便搞清各式参与终极奥秘的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仅仅因为自近代以来,诸多欧洲哲人都成了保罗—马克安的信徒。在尼采看来,这种现象堪称哲人族的咄咄怪事。在还不到30 岁时写下的 《论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就警觉到智思人变成灵知人会给热爱智慧[哲学]带来致命危害:
世界进程的开端和终点,从意识的最初惊异到被抛回虚无,连同我们这一代为世界进程而精确规定的任务,这一切都出自如此智慧地发明出来的无意识者的灵感之泉,在启示录的光芒中闪耀,一切都模仿得如此具有欺骗性,如此实在、如此认真,就好像这是认真的哲学,而不只是开玩笑的哲学。[8]
正因为如此,在病倒之前,尼采终于忍不住写下了叱骂灵知式智思人的《敌基督者》,尽管他叱骂得让人觉得过分,而且让人误以为他是在叱骂基督教③。
沃格林是智思人而非属灵人或灵知人,他关切参与终极奥秘的意识的意向性结构问题,其实是对自己的灵魂安危的关切:哲人应该如何面对实在及其历史过程。他在“时间中的永恒存在”一文开篇就说:
历史这部未完成的戏剧并不像某个 “事物”那样摆在那里,人们可以对其本质作出各种陈述;而且,哲人并不作为一个观察者站在这个非物对面,而是通过他的哲思,成为这部戏剧 (他想就这戏剧说点什么) 中的一个演员。[2](P351)
看来,沃格林的真正思想对手不是保罗或马克安一类教士,而是那类“非政治的哲人”。可是,沃格林并没有直接与这种所谓的伊壁鸠鲁传统展开交锋,令人费解。尽管如此,如已经看到的那样,沃格林对古今灵知主义的哲学批判最终凭靠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把《天下时代》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放在一起对观,我们就不难看到,两书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并不完全相同。
发表 《时间中的永恒存在》 之后的第二年(1965),沃格林在德国政治学协会发表了题为“何为政治实在”的学术报告,随后就将报告扩写到一本小书的篇幅(中译本接近 100 页)[2](P393-494),不仅预示了“秩序与历史”第4 卷的“天下”观论题[2](P480),而且预示了“秩序与历史”第 5 卷《求索秩序》的论题[2](P458)。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献堪称理解沃格林政治哲学的关键文本。
虽然题为“何为政治实在”,沃格林谈论的实际上是作为意识的“实在”。至于这种“实在”为何是“政治实在”,我们得看沃格林自己怎么说。
沃格林认为,人对实在的“参与”意识本身是一种“实在”,但这种“实在”有别于那个作为终极奥秘的“实在”。因为,终极奥秘的实在是“恒常的”,而人的意识作为“参与”终极奥秘的实在则受体验之“在场”(presence)制约。由于这种实在并不恒常,而且是可变的,沃格林把这种实在称为“历史”。
沃格林强调恒常的实在和可变的实在的区分,是因为他深切感到,灵知人的心性喜欢混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实在:“实在的恒常性可能因为它被体验到的可变性而被遗忘”,反之亦然,实在的可变性可能因为实在的恒常性而被遗忘[2](P426)。
基于两种“实在”的区分,沃格林致力于进一步辨识具有可变性的实在,即人对恒常的终极实在的参与意识。这种“殊显性体验”有两种基本样式,即“智思的或属灵的”(noetic or pneumatic)样式。无论哪一种参与意识,都会让“经受该体验的个人感到自己转化成了一个新人”,进而产生出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个成为新人的“转化过程”本身会作为意识的实在变成“实在的某种结构性材料”,并“被外推至将来”,由此产生出 “各种变形信仰”(metastatic faith),这就是“政治的实在”:
[人类在]世界时间中的无尽进步的渐进主义观念;旧世界的浩劫以及它——通过神圣干预——向新世界变形的各种启示录式异象(apocalyptic vision);[认为]改天换地 [变形](metastasis) 可通过人类行动来操控的各种革命观念,等等。[2](P426)
在参与之域(realm of participation)内,作为参与意识的实在具有可变性,但终极实在本身却始终保持着恒常不变。因此,“变形信仰”的最终结局难免是这种参与意识自己都无法承受的灵魂幻灭。
在沃格林列举的种种幻灭心绪中,有一种尤其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即“信仰者们从死不变改的世界(stubbornly unchanging world)退却”[2](P427),因为,这让我们想到灵知论的“逃离”。在这里,沃格林详细考察了作为“意识”的“参与”(metalēpsis),这个概念与作为“意识”的“居间”概念可以相互说明。
智性意识是一种显亮:在这种显亮中,对实在之思(thinking about reality)寻获其语言,同时又通过这种语言层面的表达将自身与实在关涉起来。这是一种新被体验到的、人朝向其根基的张力;不过,这种张力所激发的热情,以及对关于神性根基之知识的欲求(在这种张力中,此种欲求以一个无可抗拒的“在! ”[esti]闪现出来),模糊了不少有待区分的东西——尤其是参与本身、参与之诸端点这两类实在之间的那个边界。[2](P428,比较 P442-443)
接下来,沃格林就说到“畸变意识”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来,“人的参与纯属某种自发行动”,这种“意识朝向客体的意向性本身并不会导致各种错误的实在图景”。但是,由于这种参与实在的行为(意识)“拥有某种自由维度”,又难免导致各种错误的实在图景。
在这一维度中会出现一些失当现象——比如神话创制式的自由、艺术性创造、灵知式思辨和炼金术式思辨、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各种私己世界观、各种意识形态体系的构建。[2](P430)
这里提到六种因人的参与意识“拥有某种自由维度” 而形成的 “错误的实在图景”(或 “变形信仰”),它们都可归入“丧失实在”一类。与我们眼下关切的问题相关,如下两种“错误的实在图景”最值得注意:“灵知式思辨”和“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各种私己世界观”(private worldviews)。
由于“错误的实在图景”是因为人的参与意识“拥有某种自由维度”,前者可称为灵知式的自由意识,后者则是通常所说的伯林式的消极自由意识。我们值得意识到,这两种自由意识是并列关系,而非同一关系,但这种关系既可能转化为对立关系,也可能转化为同盟关系。
沃格林将这两种“自由意识”并列,乃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心性品质:
仅在自己的努力中倾注平平常常的兴味[关切](interest),或获得部分成果就浅尝辄止,或把谬误当成真理来接受,或拒绝努力甚至反抗这种努力——同时还不失为一个参与着的人,并且也拥有其作为人的意识。[2](P430)
这段描述无异于刻画了“消极自由”的所谓“消极”含义,尤其是“拒绝努力甚至反抗这种努力”这一说法。倘若如此,我们值得看沃格林如何进一步辨识这种“消极”的自由意识的意向性特征:
这一洞见能使我们对“实在之丧失”这一问题作更精确的表述:除却我们体验的实在之外,别无其它实在。如果一个人拒绝生活在朝向根基的生存张力中——或者说,如果他对根基发起反抗(亦即:拒绝参与到实在中,并由此拒绝体验他作为人的这种本己实在,那么,他并未因此而改变“世界”,毋宁说,他失去了与实在的接触,并在个人层面蒙受着丧失实在内容[这种病态]。
然而,由于他仍然不失为人,而且他的意识也继续在实在形式层面起着作用,那么,为了替自己的生存和在世上的行动找到秩序方向,他会制造出一些替代图景。……“实在之丧失”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与此相关的个人,其生存秩序中发生灵魂病理学意义上的混乱;而且,如果生活在“次级实在”中这种现象在社会层面变得具有主导性,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层面的严重秩序动荡 (这个我们就太熟悉了)。[2](P434)
沃格林对这种“自由维度”[意识]的论析,对我们把握如下问题有很大帮助:灵知式的“自由意识”如何从“拒绝”和“反抗”的生存意识中产生出来?沃格林以加缪(1913~1960)的《西西弗神话》(1942)和《反抗者》(1951)所表达的情绪为例,形象而又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自由意识”形成的三个阶段,让我们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他说,《西西弗神话》表达了这种“自由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即认定此世的生活荒谬透顶,恶无处不在,而且浸透到此世的骨髓。在《反抗者》中,这种“自由意识”上升到第二阶段,即否弃所有关于此世的“正典”学说:
他[反抗者]既认识到,生存意义的不确定性必须作为生存的重担得到承当,也力求让生存张力远离各种教条论的替代真理(Ersatzwahrheiten)——无论是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或意识形态的。[2](P435)
随后,这种“自由意识”的“沉思性演进”(Progressus)上升到第三阶段,即“获取创造的自由”或“反抗者”的消极自由。沃格林引用了《反抗者》中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一点:
[由于反抗者]对于个人自由不抱希望,却在梦想整个人类的某种怪异的自由;他们拒绝孤单的死亡,还把某种集体的大苦痛称为“不朽”。他们不再相信现存的东西,不再相信世界和活着的人;欧罗巴的秘密就是,她不再热爱生活。[2](P435)
沃格林力图让我们体会到,这种 “反抗者”的“自由意识”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摧毁了意识的生存张力,并由此摧毁人本身的秩序中心”[2](P439)。沃格林说这是“欧罗巴的秘密”,而非中国的秘密。这让我们应该意识到,若我们掉以轻心,对现代西方的自由意识不加辨识,“欧罗巴的秘密”迟早会成为中国的秘密。
接下来,沃格林进一步考察这种自由意识的参与行为如何“偏离到了灵知主义”。简单来讲,这种“偏离”体现为某个“具体个体的单独意识”(discrete consciousness of concrete individuals)自以为是地 “硬要试图去超越我们朝向根基的超越本身”,“以越过对实在的视景性知识的方式占有实在”,并自以为获得了对超逾“世界”的“星际”的真实洞见[2](P447-448)④。
换言之,这种灵知式的自由意识把自己等同于“星际意识”,忘记了一个智识性的常识:
意识乃是这样一个实在之域:在其中,神性实在与属人的实在彼此参与,却不合二为一,如此,意识便得以意向性方式关涉那些参与着的实在。[2](P448)
灵知意识不仅是一种“理性化程度较低”的意识[2](P456),它还以为自己是一种超迈的神秘意识,或者说以为自己的意识只要在参与神性实在就已经与神性实在合二为一了。这种“合一”意识固然具有“神秘论”(mysticism)意识的根本特征,在沃格林看来,它与真正的“神秘论”意识并非是一回事。为了澄清“神秘论”的含混,沃格林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论述这一问题[2](P467-474,比较 P29)。
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有“意识形态的时代”之称,沃格林的《何为政治实在》正是针对这一时代的意识混乱而作:所谓“政治实在”即一种政治性的参与实在的意识[2](P394-397,比较 P444)。沃格林相信,如果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迷宫,就必须回到人类的参与实在的意识诞生的开端,搞清这种“对根基之意识”的体验结构本身[2](P398-440)。
我只需简短指出我们时代的各色争吵:各色教条论的拥趸们彼此指责对方的 “真理”是非真理,却丝毫不去注意推动性体验(motivating experiences),甚至对体验问题连听都没听说过。[2](P449,比较 P461-462)
澄清“对根基之意识”的体验结构本身,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天下型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原初的“对根基之意识”的体验变成了“各种学派的教条论哲学”,以至于当“智思”在历史的实在过程中重新苏醒时,必然会反抗种种教条论哲学。沃格林相信,“直到现代,这种教条式的标立与对立游戏,都还仍然是西方文明对秩序之自我理解的主导性形式。”[2](P454-456)
反教条论哲学是现代哲学的开端:培根的洞穴偶像说即著名的例子,而培根和笛卡尔恰恰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视为洞穴偶像。因此,17世纪时,始于笛卡尔的思想反动“用来抹煞传统的这种彻底性是再彻底不过了”[2](P62)。然而,问题在于:
怀疑论、启蒙、以及实证论对旧式教条论所发起的反抗,固然再次让注意力转到体验(为了表达这些体验,秩序真理的各种象征才被创造)上来,却并未导致智思得到决定性的更新。紧随教条论神学而来的,是教条论的形而上学,再之后呢,便是同样教条论的意识形态。[……]在今日,智性阐释不像古典哲学智思那样处于与神话和智术对立中,而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情势之中;这个情势的最大标志就是ratio 对各式教条论的抗争,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型教条论。[2](P456)
沃格林最终相信,要走出现代意识形态的迷宫,而非出于合理的“反抗”意识而不断增加“意识形态型教条论”的数目,只有回到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因为,区分“历史场域”中各色灵魂类型的意识,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伟大贡献。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对沃格林来说,灵知人与柏拉图笔下的所谓daimonios anēr[精灵人]仅仅是貌合神离。谁不懂得这种区分,就表明他在智性思考方面的努力还不够彻底,或不愿付出艰辛的智性努力。
如果说《时间中的永恒存在》让笔者深切感受到,沃格林所关切的那类灵魂并不多,而这类灵魂则未必个个都热爱学识,即便热爱学识也未必会自觉地意识到有必要反思自己的灵魂德性[2](P366),那么,《何为政治实在》则让笔者感到,沃格林对西方意识危机的反思并非不可争辩,无可争辩的仅是:热爱智慧首先得反思自己的灵魂意识。
五、沃格林对中国“天下”的观察及其问题
在《天下时代》中,沃格林用整整一章篇幅谈到了中国汉代的“天下意识”。他在书中明确说到,“天下时代”因此得名的世界史现象是:由于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帝国更迭以及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秦汉王朝的帝国扩张,“天下”进入了帝国冲突的时代。
到了约公元前二世纪,我们不再处于部落社会或小城市国家的世界,而是处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延伸的天下帝国的世界。[3](P128)
从地理上讲,“天下时代” 从波斯帝国开始伸展,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紧随其后。但是,远东的中华帝国在当时虽然已经出现“天下意识”,却并没有在地理上与西方的“天下”连成一片。因此,在人类世界的第一个“天下时代”,实际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天下观”或“天下意识”。这意味着,“天下时代”出现了“天下意识”的“多样性和平行性问题”(the question of multiple and parallel)。
沃格林用“存在中的飞跃/跃入存在”这个他发明出来的哲学术语指人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它体现为某个政治体中极少数优异的智慧者的精神意识或者说“代表性意识”。所谓“天下意识”的“多样性和平行性问题” 指在帝国更迭的 “天下时代”,人类的“跃入存在”的意识面临“多样”甚至“平行”的代表性意识。比如说,荷马是希腊人的代表性意识,摩西是犹太人的代表性意识,孔子是中国人的代表性意识。
但“天下时代”更多意味着天下的征服,而且成了随后的世界历史的一个根本推动力。因此,思考“天下时代”应该更多关注史书,即关注一个政治体如何通过修史来塑造自身,而非像雅斯贝尔斯那样仅仅专注佛陀、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的精神意识。从“天下时代”的修史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秩序的建立始终面临毁灭性扩张所带来的无序威胁,为了克服这种威胁,就需要虚构出一个凭靠神话建立起来的秩序,以便正在建立的帝国秩序获得正当性证明。
沃格林把希罗多德、珀律比俄斯与“中国的第一代史学家司马谈和司马迁”相提并论。无论在帝国式的政治体还是希腊城邦或以色列人的流亡政治体那里,关于政治体起源的思辨都与“历史之域”(realm of history)相关。古代的史书无不带有神话时间和溯源式叙事的形式,这意味着政治秩序的思考无不受到历史之域的限制。
沃格林不仅要用“天下时代”取代“轴心时代”的问题意识,他还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不应该是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假设,而应该是“天下意识”。因为,当罗马人把波斯人和亚历山大治下的希腊人纳入囊中后,形成了一个“多文明的帝国”,而这个帝国解体之后,各民族政治体马上开始新一轮冲突,“文明”难以继续成为基本单元。为了把“文明”概念打造成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单元,汤因比不得不从帝国秩序出发来建构文明单元。
沃格林主张,世界政治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是精神迸发、帝国建构和修史这三者的关系。沃格林对汤因比的世界史研究范式产生质疑,来自他学习中国文明形成的历史:
在“天下帝国”中达到顶点的“文明”,在帝国扩张前并不存在。显然有一种类似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的东西,即从古典的周时期进入汉和后汉帝国的连续性。但是,从帝国的苦难历程中出现的中国文明,显然不是公元前8世纪进入帝国的部落社会的聚集体,而从希腊和罗马帝国扩张而出现的希腊罗马社会,显然也不是柏拉图的雅典或早期共和国的罗马。文明社会不是历史的终极单元,而是极为不令人快乐的、血腥的历史过程的产物。[1](P85)
出版《秩序与历史》前3 卷后,沃格林改变自己的写作计划的直接原因,其实并非是受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的刺激。他回忆说,1945年至1950年的5年对他来说 “如果不说是瘫痪期的话”,也得“概括为彷徨期”,因为他撞上了中国这个世界史范例。
我发现了问题所在,却无力令人满意地以智慧去洞察它们。我的工作并未止步。我不得不继续挖掘材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视野变得更宽了,因为中国已经变成时髦的话题,考虑到我的语言能力,系里决定选取我来教中国政治。这就让我投身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由于不理解中国的经典就很难谈论当代中国的观念,我开始学习中文,学到足以理解经典的字义,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经典。这种知识对于理解中国思想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今天仍然有帮助。[1](P84)
很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945)之时沃格林才开始关注中国,因为这场战争让中国成了西方的“时髦话题”。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西方学界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由于“八国联军”轻松洗劫北京城以及中国建立民国后长期处于内战状态,西方的政治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在“走投无路挣扎求生存” 的处境中会凭靠自身的搏斗获得解放。中国成为“时髦话题”,仅仅因为这个国体既古老又幅员辽阔,地缘政治位置也十分重要。
对沃格林来说,毕竟“人类之种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这样一件事困扰着我们,同样困扰过早期天下的帝国和后来的正统帝国的创建者”[1](P86)。这话清楚表明,沃格林探究古代的“天下时代”是出于现代的“天下时代”给他带来的精神困惑。在沃格林看来,20世纪的世界大战即便不能说它证明了西方文明的耻辱,至少也可以说它证明了西方“历史形式”的血腥和混乱。20世纪的两次欧洲大战连在一起刚好 30年(1914~1945),这让西方的史学家想起三百年前的德意志30年战争(1618~1648)。决定性的差异之一在于:20世纪的欧洲30年战争演变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战争,亚洲被拖入了欧洲生存的“历史形式”,而这一形式的突出表征是连绵不断的战争。
对中国学人来说,“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是,现代西方的生存模式传入了亚洲社会。在沃格林的大历史眼光看来,这一世界历史的基本趋势的结果是:要么亚洲民族因“走投无路挣扎求生存”最终接受西方秩序,“要么是西方的历史形式的毁灭”[5](P91)。所谓 “西方的历史形式”(Western historical form) 这个看似普通的表达式其实相当抽象,显然是个哲学术语,不容易理解。简单来讲,在沃格林看来,亚洲文明传统没有“历史”,因为,亚洲人的世界观念被紧紧包裹在 “宇宙论的秩序”(the cosmological order)中,没有像以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那样,突破宇宙论秩序进到一种历史的生存形式。
这并非是说,亚洲的文明政治单位(以波斯、中国和印度为代表)没有自己的实际历史,因为所谓“历史”首先指政治体的生存经历。毋宁说,西方文明政治单位对“历史之域”的理解与波斯、中国和印度文明在亘古不变的“宇宙论”秩序之下来看待自己的生存大相径庭。
希腊人生活在分散的城邦状态,长期没有能够形成一统化的帝国,犹太人甚至流离失所,虽然是一个政治体却没有自己的“国土”。分散的城邦状态难免内战不断,流离失所显然是因为自己的邻人过于强横。这无异于说,西方文明对自己的生存形式的理解不得不突破亘古不变的宇宙论秩序,是由于自身的实际政治处境所迫。
但是,自17世纪欧洲出现“科学革命”以来,接替希腊人和犹太人成为西方文明代表的欧洲日耳曼人凭靠科学技术支撑的军事和商业力量征服了亚洲,于是就有了亚洲民族因“走投无路挣扎求生存”被迫接受西方秩序这一历史结果。接受西方秩序意味着,不是从亘古不变的“宇宙”而是从变动不居的“历史”来看待生存秩序,这就有了“秩序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用沃格林自己的话来说,“秩序与历史的哲学是一个西方的符号”(a Western symbolism)。因此,雅斯贝尔斯用“轴心文明论”引导人们思考,值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5](P92)。
对于中国学人来说,同样值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的问题来了:的确,中华民族由于“走投无路挣扎求生存”最终接受了西方秩序,但我们必须因此而抛弃亘古不变的“宇宙论”秩序观吗?从“历史”来看待生存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结果又怎样呢?
沃格林看到,历史哲学有一个出自本能的习惯,即力图找出人类历史上可识别的结构,然后转变成一种教条,而帝国的解体总是让历史哲学的这一本能习惯遭遇挫折。罗马共和国已经具有帝国扩张的欲望,她使得这个城邦共和国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疆界,先把意大利部落社会组织进邦联,随后就开始征服不属于意大利种族单元的其他人民。罗马帝国秩序一旦解体,地中海周边的种族—文化随即释放出多样性。因此,在沃格林看来,一个涵盖多民族—文化的帝国秩序总是难以为继。
沃格林没有意识到,中华帝国的历史秩序成了他的世界史惯例的例外。但是,我们自己却应该充分意识到,西方世界一直不断在想方设法从世界史上抹去这个例外。
沃格林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的后三卷(《帝国与基督教》《新教的世纪》和《西方文明的危机》)要考察的正是“欧洲的历史形式”的形成史,这个研究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他留下的“政治观念史稿”(后人编为1~8 卷) 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他的历史考察的基本线索:从希腊化时代到“危机与人的启示”时代⑤。
不妨把天下时代说成是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时期:从这个时期,出现了新型社会,在其中,帝国征服的冲动这个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开始变得具有效力。当一个罗马帝国破碎,进入一个拜占庭帝国之际,或者一个西方拉丁帝国破碎,进入近东和北非的新兴扩张性伊斯兰帝国之际,还要依然声称希腊罗马文明在延续那就是在胡扯。已经兴起的,是基于新的移民运动、文化接收和扩张的新型社会单元,这些单元采取了在天下时期创造的帝国形式,但现在吸收了“把教义化的精神迸发作为他们的政治神学”这一正当化方式。天下的帝国和它们的灾难被继之以正统帝国——不论是在孔教中国或在印度教的印度,还是在伊斯兰帝国,在东方希腊正教或西方拉丁正统帝国。这些新型帝国文明——作为文明社会,它们根本不能被等同于天下的帝国所统治的社会——在整体上得到延续,直到在所谓的现代时期中出现新的灾难和断裂的浪潮。[1](P86)
“新的灾难和断裂”指基督教欧洲在16世纪重新发现异教古代,同时出现了自然科学革命,人的意识突破了基督教帝国确立的正统。换言之,现代的“天下时代”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意识中断了所有传统帝国的正统。由于这个“现代”的世界意识如今已经蜕变为一种正统,即所谓“进步论”或“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人对政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理解面临重重危机:“零度思维”或“非文明论”不过是这种危机的必然结果。倘若如此,现代西方新帝国的崛起将中国秩序同化为西方的历史生存形式给我们带来的是无法回避的政治史学问题:中国的历史崛起,是否会给世界秩序引入新的历史秩序。
眼下美伊之间的军事对峙应该让我们想到两千年前的希波战争,如一位美国的世界史学家所说:在巴格达执勤的美军如今守卫的其实是当年波斯帝国的边界。强势的波斯帝国军队入侵希腊半岛,未料被弱势的希腊人击败。如今,强势的美帝国军队兵临波斯湾威慑古老的波斯土地,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一现实至少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天下时代”仍然有某种同一性和延续性。
注:
①参见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②参见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M].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1-182;比较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M].楚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57-168.关于布克哈特“非政治”的个性气质,参见70-73;148-152.
③尼采.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M].吴增定,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比较洛维特/沃格林等.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M].刘小枫编,吴增定,田立年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④关于“星际”概念的产生,参见雷比瑟.自然科学史与玫瑰[M].朱亚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44-68.
⑤参见埃里克·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1-8 卷)[M].刘小枫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19.
参考文献:
[1](美)埃里克·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M].段保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2](美)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M].朱成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美)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M].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4](美)埃里克·沃格林.政治观念史(卷一):希腊化、罗马、早期基督教[M].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5](美)埃里克·沃格林.城邦的世界[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6](美)埃里克·沃格林.求索秩序[M].徐志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7](美)迈克尔·沃尔泽.清教徒的革命:关于激进政治起源的一项研究[M].王东兴,张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德)尼采.尼采全集(第一卷)[M].杨恒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30(译文略有改动)
From “Axial Age” to “Ecumenic Age”: on Core Issues in Eric Voegelin’s The Ecumenic Age
LIU Xiao-feng
(College of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European thinkers began to face and think about the “Chinese spirit”,and the prominent figures include Leibniz,Hegel,Weber and Voegelin.Voegelin can be counted as one of the most thoughtful historical philosophers of the 20th century.He though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der and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and replaced Jaspers’ “Axis Age” with the concept of “Ecumenic Age”.Geographically and historically,“Ecumenic Age” refers to changes from Persian Empire to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In Parallel with this is the rise of Chinese Empire in the Far East.The West and the East developed two different “world concept” in parallel.“Ecumenic Age” also has a universal meaning of metaphysics,which refers to the perpetual nature of the world:the world is always full of violence,misfortune and disaster due to conflicts between groups or political units.The “world concept” reveals a spiritual response to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The diversity and conflict of human polities has troubled us as much as they did for the early empires in human history.Whether in polities of empires or Greek city-states or Israelite polities,all speculations about the origin of polities are related to the field of history.This means that thinking of political order is limit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has the basic form of mythological time and traceable narration.The cosmological imperial order encapsulates human ideas,and it is Israel’s existence that allows human ideas to break through the imperial cosmic order.Therefore,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s that the leap of existence does not completely break the cosmological order as the West did.
Key words: Voegelin; Gnosticism; “Axial Age”; “Ecumenic Age”; world concept; political order; in-between ethics
中图分类号: G 04;B 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9)05-0013-17
收稿日期: 2019-09-10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公职人员的人文思想训练与政治素养关系研究”(GJ2016AW06)
作者简介: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研究。
【责任编辑:来小乔】
标签:沃格林论文; 灵知主义论文; “轴心时代”论文; “天下时代”论文; 天下意识论文; 政治秩序论文; “居间”伦理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