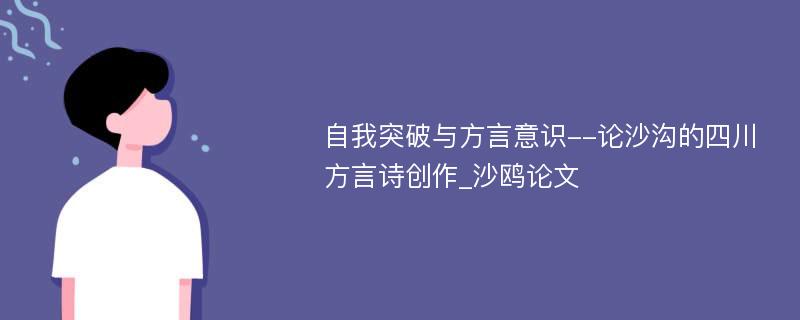
自我突围与方言自觉——论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沙鸥论文,自觉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2)04-0090-05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重庆诗坛,有一位诗风独特、影响甚著的本地方言诗人——沙鸥。当时他不论是编辑诗歌刊物,还是发表诗作出版诗集,都在诗坛上显得相当活跃。以其诗作成集情况而言,他共有个人诗集5部问世,除《百丑图》是杂有方言性的讽刺诗集外,其余4部全部是纯粹的四川方言诗集①。——这在新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诗人执著于家乡四川方言的诗歌创作,贯穿了整个40年代。本文以他3本四川方言诗集为主,尝试分析沙鸥是如何通过抓住四川方言入诗来寻找自己作诗的特色与声音的。站在整个现代方言入诗的流变潮流中,审视沙鸥自足性地把握与呈现方言诗这一事件,我们又如何评估他抒情的方式、手法,诗人的创作目的与原则,以及这一潮流的意义。
40年代的农家青年沙鸥,在家境贫寒以及旧学与新学都无多少家学的背景下,能迅速走上诗坛并以方言诗引起轰动、称著一时,这一过程本身并不容易。总体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起了关键作用。首先,一个人的出生背景与成长经历,往往影响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与价值取向。从沙鸥的大致经历来看,这一点首当其冲。沙鸥原名王世达(沙鸥之名系1940年发表诗作时所用笔名,来自杜甫律诗《旅夜书怀》诗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后主要以此笔名存世。为论述方便,下文统称沙鸥),1922年4月出生于重庆巴县蹇家桥一户穷苦家庭。父亲为当地一中医,不幸六岁丧父,哥哥王世均长兄作父,在生活、读书、工作等方面对沙鸥帮助甚大,特别在沙鸥因受一爱好诗歌、文艺的同学引领与激励下学会涂抹并发表第一首诗以后,王世均赞赏有加,不仅继续在经济上慷慨相助,而且带他走进了他在重庆小有名气与作为资源的编辑、作家等朋友圈子,为沙鸥走上诗坛做了较好的客观铺垫。
其次,时为青年小伙子的沙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有鲜明突出的特征。他在高中读书时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死读书的小屋中卷了出来”,“诗歌成了武器”,即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或编墙报、写宣传诗、上街游行、参加当时带有“反抗性”的文艺界活动;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接受党组织指派的农村调查工作等等,并以当时高中生的身份,在16岁时加入了共产党。正因如此,他所具有的思想上的苦闷与愤激、对时局的牢骚与指责都甚于同龄人,办诗歌刊物结社与文朋诗友的胆量与热情也甚于同龄人。巧合的是,沙鸥开始把从笔尖流贯出的新诗作为投枪射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时,这一姿态与立场也恰好和素有党的喉舌之称的《新华日报》合拍。沙鸥的四川方言诗,最初几乎全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以“失名”的笔名发表。这一类诗大多在主题、立意上尖锐揭露国统区农村的黑暗与残败。当时《新华日报》副刊编辑们十分重视具有这一价值立场的诗作与诗人,如刘白羽、何其芳自延安带着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目的来重庆后,敏锐地像伯乐一样培植了四川方言诗这一株幼苗。编辑们与沙鸥建立了密切而互信的编读关系,如及时而又大量的通信、发稿等等。以国统区农村为对象、题材的四川方言诗,正是因特殊的题材、主题与语言,与党的宣传方面的意识形态背景一拍即合,导致了四川方言诗被迅速推上强势传媒渠道,轻松地走出四川而面向全国辐射开去。
更重要的是,沙鸥选择四川方言诗为自己的创作新路标,与他在起步后经过长期的徘徊而勇于自我突围相关。这方面的经历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从“艾味”到“川味”。“艾味”指的是“艾青味”,“川味”指的是“四川方言味”;换言之,即由模仿艾青“转型”到用四川农民的语言(方言)来写农民的苦难生活,并获得成功。沙鸥最先写诗从模仿起步,对艾青的作品达到爱不释手的地步,艾青诗的语言、想象、感情基调、自由诗体形式都潜移默化地吸引、影响了他。“他成了‘艾青迷’,常常朗诵艾青的一些名句,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他早期发表的诗,也带有‘艾味’。”[1]这里举一首诗为证,如艾青有一首诗叫《愿春天早点来》(1944年艾青还在桂林出版《愿春天早点来》的诗集),沙鸥也有一首效仿之作,不说抒情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就是连标题都几乎一样②。但模仿艾青并不容易,只能在表面词句上往返,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超越。诗人自己感觉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特色”,没有“自己的个性”[2]91。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写什么,怎样写,不来一个突围显然深入不下去,但又向何处突围,突破口在哪里呢?这些相互牵连的问题因没有及时、有力地得到解决而极大地困扰着青年诗人沙鸥。后来机会终于来了,诗人是这样描述与回忆的:
一九四四年的暑假,我去离重庆不远的马王坪农村舅父家里。这年和第二年的寒假,又去了万县白羊坪的山区农村。农民的穷苦生活和悲惨命运,把我带到一个全新的题材的天地。我开始用四川农民的语言来写农民的苦难。我一方面深入了解当地佃农和贫农的生活,一方面把写的诗念给他们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写的有短的抒情诗和小叙事诗,有的也受到四川及西南民歌的影响。
这些诗最初是在《新华日报》发表,并引起广泛注意。四川方言诗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从写自己的空虚与苦闷,变为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苦难,对我写诗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我突破了自己的禁锢。我很快觉察到,不仅这个新的天地有写不尽的题材,自己的诗风也变化了。[2]92
正因这一次突围,沙鸥在新诗的创作、发表、影响,乃至个人风格的形成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又显著的变化。四川农村题材与四川方言的结合,便是沙鸥紧紧抓牢的两个基点。40年代中期与后期,均是这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河改道式巨变,才被迫放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在《新华日报》及重庆当地进步文学期刊与报纸刊载以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与异乎寻常的关注,结果因《新华日报》等的肯定与赞赏而得到大面积的扶持与倡导,于是“在沙鸥的带动与影响下,一批更年轻的四川诗人也写起四川方言诗来。一时间掀起了四川方言诗的热潮。沙鸥——方言诗;方言诗——沙鸥,几乎成为同义词”[1]。
整个过程大致如此,但沙鸥到底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他在国统区农村访贫问苦时,主要从学习农民的语言着手,这似乎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体现。后来沙鸥在关于理论资源与武器的回忆时,连接上了这一点,他认定方言诗“是一个大众化的问题”,“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应从学习群众的言语开始……方言诗正是用群众的语言,使诗歌从知识分子的手中,还给广大的群众、与群众取得结合的开始”[3]。和群众结合的最好方式是向农民学习,把他们的生活诗意性地记载下来。沙鸥先后搜集当地许多农民方言,一句一条记在笔记本上,四川方言丰富、生动而又形象的特质,让诗人感觉到它是一个抒情达意的好工具。尽管沙鸥在贫寒农家长大,童年时也偶有失学、缺衣少食之虞,但相比之下毕竟缺乏川东农村如此苦大仇深的人生体验。在川东农村与当地佃农、贫农打交道时,他们的悲惨命运与非人遭遇,特别是与当地农民密切相关的极其繁重的征租、送粮,草菅人命式的抽丁、拉夫,尖锐对峙的阶级冲突、贫富分化,诸如此类,把诗人带到了另一世界。
沙鸥选择用四川农民的语言来写国统区黑暗残败之农村,在突围与执著中开辟了前人没有开垦过的领地,下面从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分别论述。
这批四川方言诗,从主题、题材上看是从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写大后方农村、农民的现实生活,其中虽然不乏充满活泼、欢快等亮色的诗作,但主要的是以呈现灰色、暗淡、悲惨的生活与遭遇为基调的。这是沙鸥作为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诗歌下乡”后得到的收获,在新诗史上并不多见。国统区的旧农村,农民们生活在僻远的乡下,他们面朝黄土汗流满面、遇水而居、看天吃饭,有自己生活的圈子与习惯,这一切在沙鸥方言诗中有所体现。除纯粹描摹山乡晨雾村景的一二首诗外,题材范围有以下几方面:或是偏向于反映农忙、抢收、砍柴、烧饭、看牛等日常农事,或是以青年男女恋爱、进城拉车谋生、祈神算命、上茶馆请人解决家庭纠纷为素材,同时也不忘把笔伸向过年过节赶场等节庆时村民上街贸易购销农产品、吃烂牛肉汤锅、聚众赌钱、上坟许愿等带有民俗性质的生活细节。这类以反映普通农家日常琐事为主的方言诗占总数的二成左右,它们呈现着农家的生活情趣、乡土气息,其中虽然不乏艰辛的画面,但基本上保持了在大自然、农村面前的宁静、安详与欢快的基调。
沙鸥3本方言诗集中涉及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悲苦与困厄,给读者以民生维艰、唏嘘长叹之慨。其中有因借债度日以助农事或做垮庄稼而陷入困顿的《茶馆里》、《空屋》、《除夕》、《讨饭》、《生活》,有因雨雪失度、过多而导致农作物歉收的《雨》、《麦苗》,也有因人畜得病死亡而陷入绝境的《化雪夜》、《死》、《猪》、《死牛》、《岩洞》、《那人》,还有因家境清寒失学而陷入迷茫的《保国民校》、《上学》……正应了“天灾人祸、祸不单行”那句老话,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在赤贫线下挣扎的农民生活,显然不能以“悲惨”两字来全部归纳。
如果说上面所举的天灾人祸还只是活得异常艰难、极其不易的话,那么残酷的阶级压榨更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如地主老爷在荒年对佃农的加租退佃、奸淫民妇、残害农人之举,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意而悍然发起内战导致的大量“捕抓”壮丁等政府行为,这些非自然因素把水深火热中的大后方农村,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地狱。加之执行政策的乡公所、保甲长等机构或个人,或无所顾忌徇私舞弊,或颠倒黑白公报私仇,导演了多少无助农家家破人亡的悲剧。这一部分在整体方言诗中占多数,具有数量多、分量重、体验深刻、控诉性最强等特点。地主对佃农敲骨吸髓式的残酷榨取,在贫农们中也差不了多少,所有的一点土地、家产,也在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与冲突中丧失干净。地主、老爷、保甲长相互勾结、横行乡里,他们动辄以加租退佃相威胁,时时以巧取豪夺相迫害,如《逼债上吊》写的是郭华堂过年前因还不了账而上吊自杀,《债》写的是张老汉因打赌免债而亲手拿刀杀死三岁的亲生娃,《是谁逼死了他们》述说的是佃农李家因庄稼做垮而被逼租只好全家自杀,《池塘》一诗里烈士家属刘幺嫂因交不起乡丁催交的粮谷而投水自尽……穷人走投无路时,除了冒险去剪谷穗、偷腊肉,去当强盗、拦路抢劫之外,就只有投水、上吊、吃毒药自尽这一条老路,他们都是以不正常死亡来尖锐地揭露、抨击社会黑暗的冷酷,来昭示、警告世道人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主、统治阶级的生活却又是那么荒淫、无聊、空虚。如以财主生活为题材的《陈大老爷》一诗,内容细节便是陈大老爷一边云吞雾吐吃云土不断,一边在妻妾成群中每顿大鱼大肉,养得简直像肥猪似的;他一边随性收租、加租、发行高利贷,横行乡里而暴富,一边又狡诈、刻薄且以假哭穷著名。又如对比富人与穷人过年的《火炮》,有钱人买到临时参议员头衔而炫耀乡里的《临时参议员》,相互倾轧夺权之事的《乡长》,揭露兄弟通奸丑事的《大户的子女》,父子两辈轮流偷着去烟馆抽鸦片的《父与子》……均从各个方面典型地反映了剥削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侧面。至于以“政府名义”收取钱财、搜刮民脂民膏的更是无奇不有:如乱抓壮丁而陷人于难的有《保长》,私吞壮丁安家费、乱派捐税、欺凌孤儿寡母的有《安家费》、《孤儿》、《不敷费》(即乡公所办公费不够开支而征收的一种捐税)、《又在拉人了》、《瞎子》、《声音》等。还有具体细化到与壮丁相关的诗,这一类诗大概有近30首,涉及与日军作战即打国战时的征夫与打内战时的征夫两种,其中以后一类为主。诗中写的是农人不愿打内战,以免成为被活活拖死的冤大头等事,他们躲避抓夫的方式及造成的后果形形色色,如宣传自己人搞不得、不要去冤枉替死的(《教我从那说起——哭内战阵亡“国军”》、《场上》),自己刺瞎眼睛、砍伤手脚想因致残而躲避壮丁的(《他自己宰错了手》、《一个老故事》、《母子遭殃》),在新婚之日自杀身亡的(《这里的日子莫有亮》)……诸如此类,曲折地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写出了大后方农民的人心向背。尤为可贵而又令人欣喜的是,除了那些或自残或投水或自尽的悲剧外,诗作还尝试性地写出了农民的反抗、奋起与斗争。除了《饿》一首写一家人铤而走险、拦路抢劫等系盲目行为之外,以下诸篇都晃动着向压迫者生死抗争的身影:如《火把》、《空屋》中写农民上山当土匪夜抢地主家产的故事;《这里的日子莫有亮》中新娘在新婚丈夫上吊后拿刀杀死了直接元凶李保长,最后自己也一死了之;《寒夜难挨的日子》写佃农刘老幺因妻子被保长强奸后而和两个孩子自尽,他愤而用刀杀死保长以报家仇。这批方言诗,诗风纯朴,笔触细腻,给人印象也特别深,正如时人评论所说“写得最动人的有农民与牛的关系”,“拉壮丁的悲剧,也写得最动人”[4]。
上面分析了沙鸥用“四川农民语言来写农村、农民的生活与遭遇”的一个方面,即农村农民的生活与遭遇,下面来看“四川农民的语言”这一方面。四川农民的语言即四川方言,在沙鸥的笔下得到了大量而灵活的运用与表现。他当时搜集川东地区的许多农民方言,包括口语、谚语、俗语,还包括四川民歌等语料。他还把写好的方言诗念给会讲四川话的朋友听,念给当地农民听,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是求得音节上的顺口,以“听得懂”为上;二是争取妇孺皆知,在题材与语言上都与农人打成一片。因为农民95%不识字,听是第一位的,看倒是属于第二的[5]。
他的诗作“以客观描写为主,语言口语化,并以方言入诗,有意识地探索诗歌的大众化”[6]150;叙事诗创作上“以方言俚语入诗,叙事带有说唱文学的特点”[6]130。他的方言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里尝试着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一是方言词汇、表达法;二是以一种四川方言句式来予以剖析;三是比喻、拟人所体现的特色。
方言词汇往往是方言最为醒目的标签,在沙鸥四川方言诗中,这一部分川语中特有的词汇比比皆是。从人称方面来看,称呼一家的男主人为“老板”(地主则称老爷;另外生僻词汇在随后括号内注明普通话中有类似意思的词汇),女人则为××嫂、娘子,小孩子则是细人、娃娃、细娃、奶毛头。排行最小的冠以“幺”字,如诗中出现的幺麻子、幺娃子、幺嫂子、赵老幺、陈幺爷。以“头、子”作为名词后缀的构词法,如茶馆头、提兜头、田头、心里头、外头、城头、奶毛头(婴儿)、后头(后来)、门外头、屋头、肚子头、月黑头、缝缝头、院子头、老辈子屋头、坟头;李胖子、小毛子、黑娃子、小婆子(姨太太)、名子(姓名)、鸡子、空位子、苍蝇子、谷草烟子(烟雾)。将词素重叠构成名词,如兜兜(袋子)、土堆堆(土坟)、坪坪上、白壳壳(秕谷)。另外除了朗个办、朗个活、脑壳、啥子、笑扯扯的、阴惨惨的、摆龙门阵、莫得、晓不得、怕不要、硬是、包谷、门角角、脚杆、缩起手等外,还随处可见以下方言词汇:箩兜(箩筐)、小耗子、害人死的、转个弯(转身)、年辰、天老爷、二指姆(食指)、落坡、牯牛、精精灵灵的(聪明、伶俐)、阴惨惨的、堰塘(池塘)、括毒(刻薄)、皱皱(皱纹)、上坡(上山做事)、颈项(脖子)、打抖抖、光脚板、看眼(看一下)、破朽朽的(破烂)、几向(几间)、闹热(热闹)、跑脱(跑掉)、歇房(卧室)、挞谷、开斗、想法子、大太阳天、仗火(战争)、眼睛水(眼泪)、乡头、刀头(敬神的猪肉)、心子(心脏,良心)、死人子、刷粉亮(天刚亮、黎明时)、犯娃子(小偷)、今朝子(今日)、老鸡婆(老母鸡)、告化子(乞丐)、捞柴、宵夜、蚂蚁子……总而言之,沙鸥的方言诗,几乎不避原生态的方言语汇,只要是四川农村百姓会说能说和正在说的,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统统大胆地植入诗行之间。
另外一层便是一些四川方言中带有地域性的句子与习惯说法,在他的诗中也相当集中,例如:
(1)莫气我,你娘是吃眼睛水过日子。(《上学》)
(2)乡公所是把言语拿顺了的,/若县府派人来,送路费的就在这地点。(《烟馆》)
(3)横顺是一个干人,出不起钱的。(《不敷费》)
(4)像逃荒一般又忙又乱,/小娃儿也拿起括子和扫把,/把胡豆和麦子装进箩兜里。(《晒坝》)
(5)在山坡坡的小路上,/女人梳个光光头在前走,/男的提个送情兜兜跟在后头。(《拜年》)
从(1)到(5)所引的诗句来看,一是都不乏上述所及的四川方言语汇,像“莫、眼睛水”、“言语、拿顺了的”、“横顺、干人”、“小娃儿、括子、箩兜”、“山坡坡、光光头”之类便是,这些词语基本上属于方言特征词,但因四川方言属于官话子系统,一般根据上下文可以推测、揣摩其意义,没有理解上的障碍。在这基础上,上面的每一句诗,都是口语性的,相当贴近嘴唇上流动的原生态话语状态。它写的是农民、农村的生活,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等也都是农民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朴素纯净、无奈粗野的格调,浸润在乡土人情的勾勒与描摹中。另外,他的诗中还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句法,例如:
(6)就指望这些菜呀!/把一家人的命从饿死中捞起。(《偷菜》)
(7)这场,赌摊有八处了,/像蚂蚁子搬蛆一样的挤起。(《赌摊》)
(8)吃一碗,板凳一空下又有人坐起。(《汤锅》)
(9)刀一幌,过路人的荷包便伸进老二的手,/常常有遭杀死的人在路边摆起。(《夜路》)
(10)他哭横了心一下冲出了房门,/他是向堰塘摸起去,/他用眼睛水淋着田坎。(《是谁逼死了他们》)
(11)雪风把大门都封起(《村庄》)
(12)清鼻子在胡子上吊起(《冬日》)
(13)那晓得自己人一下又搞起(《教我从那说起》)
这里仅集中引用了带“起”的四川方言特殊语法,重庆方言(当时属于四川)中,用在谓词后的口语常用字“起”,在方言语法中被划为语气词、助词,它有以下四种作用:表示动作、性状处于某种状态或动作正在进行,如例(7)(8);表示动作的完成和趋向,如例(11)(13);表示动作、性状的延续,如例(9)(12);可以连接述语和补语,如例(10)。这些方言性质的表达法,在普通话中没有类似丰富的说法与含义,其内部结构和表现形式与普通话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如表示动作、性状正在进行的“起”,大致相当于北京话的动态助词“着”,但也不尽然;又如普通话的复合趋向动词系统中,“起来”没有“起去”跟它配对,四川话中有“起来”也有“起去”,如“V起来”、“V起去”以及更复杂的“V起XY”句式③。总之,其间的微妙之处,是其余方言区民众难以察觉出来而四川民众又习焉不察的。
沙鸥方言诗,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层面,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与方言意味。如比喻的本体与喻体之间的想像方式与联系点,如拟人、夸张的对象性因素,都是西南农村较为常见的,符合底层百姓具体化、形象化、日常化的理解与表达习惯。它与农村的现实生活存在对应关系,如“风从门缝里伸进手来”(《灯》),“王大爷说这期银子紧,/弄钱像莫得灯笼赶夜路一样不容易”(《茶馆里》),“太阳红得不打一个阴,/田坎上有挑谷的去晒坝了”(《收割》),“风吹在脸上像刀刀在刮”(《一个老故事》),“像磨盘背在背上”(《债》),“像躲煞一样躲壮丁”(《望太平》),“是不是玉皇娘娘打泼了胭脂粉,/你看,半边天都红了”(《火烧天》),“像甩梭子”、“像洄水沱的水”(《赶场天》),等等。这些举不胜举的诗句,或拟人,或譬喻,都是农村习见的生活事象,思维跳跃的幅度不大,抽象的强度也较弱,理解起来是相当容易、亲切的,虽然少了几分含蓄。
下面再看三首这一方面的完整短诗:
大牯牛滚水回来了,/它的尾巴把太阳扫落土了。//外婆坐在门前的竹凳上,/一只手搓麻线,/一只手还抓谷头喂鸡子。//蚊虫嗡嗡地朝起王来,/隔壁的幺嫂子又在喊宵夜了。
(《黄昏》)
有凶人用枪把子打门,/用绳子捆走年轻人。//有人用刀剁甲长,/有的用扁担砍死乡丁。//夜晚又回到一年前的老样子,/连狗也得不到安宁。
(《夜》)
一间黑屋点起灯,/屋头有做庄稼的,有兵有甲长。//不晓得是那一个一刀剁在甲长背上,/刀一弯,刀尖断在肉头了,/甲长一声怪叫,像杀条牛,/乱滚在地上闭起眼睛喊娘老子。//杀人的遭捆起了,/做庄稼的还是遭捆起手,/乡公所的兵问甲长朗个做,/甲长已人世不醒的痛昏过去了……
(《甲长》)
这里所引用的三首诗,不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思想内容上,都是粗略一看便知是写西南农村生活的,除第一首看不出具体的时代语境外,后面两首明显有“王保长传奇”一类的时代信息,因都是写保甲长的事,与战争、农村势力等方面便有勾连。第一首带有农村牧歌的味道,类似于西方写实派《拾穗者》式的油画,诗人截取农家生活的黄昏一角,来呈现乡村祥和、安静的生活。后面两首显然打破了这种宁静与祥和,荡漾着暴力反抗反动当局的血腥气息,有人物、有画面,也有情节,诗人“我”隐在画面后面,似乎没有情感的宣泄,但在叙述、描绘的心理节拍中似乎可以听到不满与愤恨的声音。这几首诗,在语言思维上也非常通俗,不论是字词还是句子,它几乎没有多少深奥难懂的,取譬浅显,但弥漫着一种农民式的情绪。在形式上看也难以划分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它们或是恬静的乡曲,或是素描中的写意,或是故事中的述说,都在短小的篇幅中寄托了某种客观性的人性关怀。另外,整体上排列均较为整齐,带有民间歌谣、时调、小曲等特点,即使是叙事,情节也没有多少曲折、波澜,看上去浅,但一琢磨,意味还是深长隽永的,其中的四川方言味也相当浓厚。
总而言之,方言诗集《农村的歌》、《化雪夜》、《林桂清》实际几乎指向同一个主题,即是四川农村一曲无声的悲歌。诗人沙鸥用四川农民活生生的自己的语言,撇开“欢”与“合”来典型书写他们的“悲”与“离”,带有控诉、代言的色彩。
深入民间、直面惨淡的人生,体察民情、为民生多艰代言,在这一点上,沙鸥在接续传统时完成了一次自我突围,这是他以自己的母语方言作为突破口所带来的。其全局意义在于,这既是他自我风格、特色形成的关键所在,也是新诗与方言这一领域如何结合的一次积极尝试。
①除本人没有查阅到的《烧村》外,其余三本分别是《农村的歌》(春草社1945年出版)、《化雪夜》(春草社1946年出版)、《林桂清》(春草社1947年出版)。
②沙鸥的《愿春天早些来》,见《文学》第2卷第2期。
③参见喻遂生《重庆方言的“倒”和“起”》,《方言》1990年3期;参见张一舟等《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98-4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