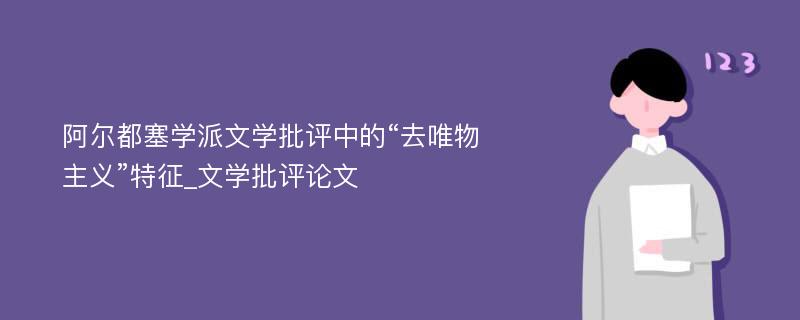
阿尔都塞学派文艺批评的“去唯物主义”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唯物主义论文,学派论文,阿尔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和卢卡奇一样,阿尔都塞主要精力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上;与卢卡奇不同的是,阿尔都塞“只是个哲学家”,①除了三篇直接论述艺术的论文②之外,几乎没有在这个领域内充分地展开,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的“新异的”阐释工作使得“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这个经典的文学问题获得了一个有可能被重新界定的基础,并且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几乎都是在阿尔都塞划定的问题性当中展开的。
一、阿尔都塞的基本命题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总体”和社会“结构总体”对立起来,并认为对“社会总体”的“科学认识”只能在发现“意识形态”“脱节”的症状之中形成。阿尔都塞的这种理论使得“意识形态”成了批判的焦点,“意识形态批评”也成为了文学理论科学性的总主题。因而,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当中,“意识形态”概念处于其理论的核心之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做了哪些方面的发挥呢?
首先,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中,“意识形态”是一种超结构的“体系”——“意识形态活动依附于一整套宗教的、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哲学的表象或信仰,以自发的或非自发的,自觉的或无意识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表象涉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与社会;涉及人们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社会、社会秩序、他人和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包括经济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③因而,阿尔都塞是将意识形态分别放在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方面去考察,把“意识形态”描述为一整套结构松散的表象体系。似乎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层面,虽然“归根到底”被经济基础决定,但是其功能却是以扩散性和流动性渗透于其他实践层面,以歪曲的方式表现或掩盖社会真实矛盾,起到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其次,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中,“意识形态”是一种总体性的结构。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物质实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倒置的反映。阿尔都塞深化了这一论点,认为这种“倒置”的反映有其物质基础,是通过一系列物质组织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意识形态具有其物质性。他强调指出,人类主体的理念仅存在于他的行为之中;这些行为依次进入实践;这些实践“在意识形态的物质实在”中,如在教堂、学校或政治团体中,“受到物质仪式的支配”。④这种支配实践的意识形态物质仪式和组织,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阿尔都塞这里,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比强调客体更为重要,甚至使意识形态的物质性颠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的社会决定因素问题的探讨。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这意味着,人的意识可以解释为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或团体在这些关系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的产物。阿尔都塞把这种决定因素颠倒了过来。他坚持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并不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产生的,而是“意识形态物质组织”对人们发生作用的结果。意识形态不是由阶级地位决定的意识的纯粹反映,而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生产形式,生产出人类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为补充“生产力的再生产”和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而发挥作用。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再生产并不单单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至少又包括下面两个必要条件,“1、生产力再生产;2、生产关系再生产”。⑥就“生产力再生产”而言,仅仅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劳动力的衣食住行)并不足以进行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有效的劳动力必须是合格的,必须拥有劳动技能,像学校和技术培训组织这样的意识形态物质机构,在传授给就学者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技能的同时,还使他们变得有“教养”,或学会服从“规范”,根据他们可能承担的“地位”的不同,将他们生产为合格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并因而也生产出这些就学者(被规训者)对既有生产关系的认同、默许、服从。其实,这里的“生产力再生产”也包含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容。全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履行的任务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学校、家庭、宗教组织、文学艺术通过制造“服从”的“主体”,维持既有生产关系再生产。
再次,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中,意识形态具有“主体建构”功能。一切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的范畴起作用,通过一系列仪式和日常组织方式,通过“质询”、“传唤”(interpellation)而使个体成为具体主体。⑦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偏重于“意识形态生产”的“客观”方面和“物质性”方面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方面,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心理的“被建构”特征。阿尔都塞更多地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引入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个体成为“具体主体”的过程,类似于拉康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向“象征界”的认同过程:个体要成为自我必须进入社会,把社会当作承认自己的对象,并经过投射和反射成为具体主体,既而主体同社会主体相互认同识别,具体主体间相互识别,主体确认自我认识,具体主体从而被“编入”社会秩序当中。这是一整套复杂的心理的认识、认同或误认过程。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就是“个体”通过“别人的”、“他者的”,也就是“社会”的“眼光”看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因而意识形态总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⑧
最终,要认识“意识形态”总体的运作,必须依靠“症状阅读”的批判(批评)方法。“意识形态”理论和“症状阅读”方法是一个整体,没有“意识形态”理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泛化”,“症状阅读”也无从谈起,“症状阅读”也只有针对通过多层次“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真相”的文本才有效。这个理论整体在20世纪60、70年代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的“生长点”,阿尔都塞用“结构的因果性”和“知识(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使对马克思的理解更换了理论场地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次“发展”的契机,不再用与批判对象共享的意识形态来进行批判(类似于“批判的批判”),而是开始了对现代性意识形态本身的外部批判工作,即“症状阅读”(类似于马克思“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正是阿尔都塞为“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要旨。阿尔都塞使意识形态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人靠意识形态生活,靠意识形态化了的知识或知识化了的意识形态去从事认识,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意识形态为人提供了唯一的“现实”,但由于这意识形态的“症状性”——它的各种形式总是“移置”着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和理论(知识)实践所构成的社会整体中的矛盾——它的形式在“勾销”问题性的同时以其形式内部的固有“错位”(décalages)暴露出它自己的“本性”。从过度决定的理论出发,无论是政治文本,哲学文本还是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所有物质性的表达方式都受到外部现实的限制:在“最终”意义上的经济生产由于其“非主体的”社会凝结作用(同时也是限制作用)在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中“曲折地”再生产自身的再生产条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转向了“批判”,这是一种新批判(“无尽的批判”):为占统治地位的、作为“政治无意识”存在的意识形态确立其界限,揭示它的“问题性”。
二、“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实践
文学理论“批评化”、“批判化”,在20世纪最后30年当中彻底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原有的那种“经济—历史”分析模式,而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合流从而激发了“文化研究”的兴起。在这个时期英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和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受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他们也在把阿尔都塞的理论运用于具体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源于“语言学转向”的“阿尔都塞转向”,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开始。而使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文艺批评的这些批评家可以称为广义的“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家。他们的实践可以说表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倾向。
第一,“文学批评权力的扩张”。在“意识形态”理论和“症状阅读”构成的理论整体中,“意识形态”概念越宽泛,“症状阅读”式的批评的权力就越大。这种“理论扩容”,随着阿尔都塞学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英美文学批评界影响的扩大而愈演愈烈。将阿尔都塞学说植入英国文学批评的“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就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扩充到十六种之多。⑨因此,“‘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就具有了非常宽泛的功用意义,而且所有这些意义都不完全相容”,⑩但其最核心的内涵是“话语和信仰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联结的方式”,(11)“‘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所具有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我具体地是指那些与社会权力的维护和再生产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模式”,(12)是为社会个体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植根于信仰的深层结构之中。意识形态的载体则是“文学”。这里的“文学”已经不是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文学”,而是指一切“话语形式”,“是表示社会中有价值的写作的总和:哲学、历史、杂文、书信以及诗歌等等”。(13)“文学”,作为以“症状阅读”为基本方法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因而包括了一切口头或文本言语行为,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也涵盖了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等一般文化文本形态。这样一来,虽则“文学”恢复了它语源学上的原意,但是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对象的“文学”却不复存在了。文学批评不再是针对“作品”、“创作”、“作家”的研究,“文学研究的是能指的问题”,(14)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成了“话语”或者“文本”——“文学批评没有确切的所指,但它如果想要的话,却可以把注意力或多或少转向任何一种作品”。(15)正如最早将“症状阅读”理论在“文学批评”中体系化的马舍雷所说的那样,文学文本和任何理论文本只是占统治地位的那种话语的“不同层面”罢了:“情况看上去似乎是,文学的任务就是表达哲学中的哲学要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文学通过形式的自由运用,通过它各种各样任意而随意的表达方式,而与真理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从本质上讲是批判性的:它与某种间离效果(Verfremdunseffeke)的产物是一样的,当文学是其自身诸种话语的反映之时,它的间离性总是在这种反映之中引入内在的距离。正是这一距离才使得文学不可能成为自身封闭的和自在的思想体系。也可以这么说,文学就是哲学的‘三毛钱歌剧’”。(16)因而,在“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看来,“文学”文本话语和理论文本话语是相同的、互补的,表述着同一种“意识形态真相”。因此,随着“文学”范畴抹消,“批评的权力”也随之而扩大。批评可以针对无差别的“文本”本身,而不是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文学文本”、“理论文本”等等。文学理论同样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之场”,只有对文学文本进行“症状阅读”才能找出特定文本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复杂关系,揭示文本话语是如何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并以何种方式建构“主体”的。
第二,“文学的消失”。正是理论的这种“建构功能”,使得“文学批评”必须让位于“文学批评的批评”。传统文学理论通过“建构”一系列“正典”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并因而建构着文学理论的“主题”,也即主体(subject)。在这种“建构论”之下,“文学”不复是一个匀质的、具有明确内涵的确定性存在,而是“理论”的话语不断地重新划分“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之间的界限。有些作品之所以被某个时代排除在文学作品之外,而在另一个时代被奉为“经典”,全赖于社会决定的理论话语配置的变化,“莎士比亚作品不是伸手可及的伟大作品,其所以成为伟大作品是由于文学构成认定如此。这并不是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伟大,也不是说这只是因为人们对他看法不同,而是因为如果离开了处理作品的社会和体制形式,就没有‘真正’伟大的或‘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可言”。(17)“批评”因而必须以“文学理论的批评为前提”,才能最终发现“文学”的内在构成和理据。然而,在“症状阅读权力”支配之下的“文学理论”宣布“文学”消失之后,“文学理论”实际上也就消失了。没有对象的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宣布文学只是话语造成的“幻觉”,其结果必然是:“承认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幻觉……所以说它是一种幻觉,这首先意味着文学理论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支,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把它同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与社会的思想充分地区别开来的单一性和特殊性;其次,它还意味着,它希望把自己区分出来——紧紧抓住一个叫做文学的对象——这是打错了算盘。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企图发掘出来的那个对象(指文学理论),结果恰恰被我们所埋葬。”(18)“文学理论”不再存在,只有“理论”得以延续;“文学批评”不再存在,只有“批评”得以延续。“批评”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伊格尔顿毫不讳言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和女权主义的文学理论”,作为“身份政治”(阶级身份和性别身份)的斗争工具,在文学“意识形态”斗争之场中,比任何一种从属于高等教育里文学院系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有价值。(19)
第三,“历史的文本化”。“一切都是话语”,在“症状阅读”的这个前提下,历史本身也被表述为“归根到底”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一系列被“过度决定”的“话语变迁”。阿尔都塞批评学派的美国学院代表杰姆逊所说的“永远历史化”,(20)就是指通过对当下作为“话语”体系的历史情境的“症状阅读”,理解历史本身,描绘测绘文学文类风格的“历史的谱系”,(21)或者说对当下作为“文本的历史”进行“认识的测绘”。在这一点上,杰姆逊的文化批评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评中的有机延续。他们都认为谁也不能为历史发展提供一个预言性的直线性图式,历史发展本身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是,特定历史条件内的社会发展变动是有其界限的,该界限的决定性因素“最终”是经济实践状况,也就是说,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是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美学的、文化的实践包括在内)、理论实践及经济实践结构性“过度决定”的产物。这种对历史的理解,绝不作对未来的预言——只用阿尔都塞主义的“意识形态”症状阅读的方式去划分迄今为止的社会运动规律及相应的文化现象。
三、症结所在:“双重去唯物主义化”
“阿尔都塞学派”紧紧抓住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总体性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理解”,并生产出一套有关“意识形态整体”、“结构因果性”的批评话语。正是因为这种“再理解”或者“再阐释”,使得“我们反观阿尔都塞的著作时,可以发现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迥异的马克思主义”。(22)这种理论取消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无疑曲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总体理论模型,使“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成了移置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场所,开启了“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话语斗争”取代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本身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趋向。
由于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文学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式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他的理论使得“文学”也显出了特殊的重要性。既然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他的文艺观上一则表现为取消作家的独立性:作家只是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一个承担者,一个当事人,他只是“社会无意识”自我表达的一种工具,可以说,福柯所说的“作家死了”就是阿尔都塞这种观点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版本;一则表现为消解文学相对于批评的独立性:文学和一般文学阅读、艺术和艺术欣赏是意识形态自发性的实践,是批评分析的科学实践的对象,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症状文本,有待于批评家把其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用科学的语言表述出来,揭示症状的症结所在。尽管阿尔都塞所确立的这种取消作家、读者在“意识形态”中的独立性的文艺观更强调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在历史“意识形态”中的复杂作用,但无疑也通过将“意识形态”总体化,而扩大了“批评”的权力,并使得“批评”总体化了。这一点在阿尔都塞之后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杰姆逊那里表现得十分突出,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意识形态总体化”、“批评权力扩大化”的趋势,也在后来“文学”边界的“消失”,“文学理论”边界的“消失”这一理论现象当中体现得很明显。因此,我们只得说,阿尔都塞批评学派呼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科学性”的动机是对的,但并不成功。以下我们就从其理论本质和理论效果上来说明这一点。
1、对“现实”的“去唯物主义化”:颠倒一。如果我们也用“症状阅读”的方法,通过仔细阅读阿尔都塞学派批评理论文本中的“疏漏”、“脱节”、“缺环”、“错位”的方式,来解析它借以确立自己全部批评理论体系的最关键概念的话,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理论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去唯物主义”(23)过程和它的“去唯物主义”本质。当然,这个“最关键”的概念就是“意识形态”。
在很多场合,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们混淆“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区分。他们有时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使用的是该词的原意,强调该词所指与现实之间的严格区别,在强调区别的同时,他们都能使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与现实实际相对而言的“虚假意识”和“幻想”,是与现实偏离的“错误意识”,而且这种幻想、错误意识是一种能够“自圆其说”并因而能为社会主体提供行动合理化基础的“体系”。例如,阿尔都塞的典型定义:“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24)“在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主宰着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的体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关系”。(25)
伊格尔顿也在许多地方这样使用此概念:“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是由相对连贯的一系列‘话语’、价值信念、表象和信仰构成的,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某些物质性的社会机器之上,并与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相关,把个体与他们社会条件之间的经验关系反映为有关‘现实’的错误表象系统,正是这种‘现实’再生产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26)但是,与这种提法相反的说法,也经常出现。如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第一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当中,伊格尔顿在《批评和意识形态》之中,就阐述了这样一种提法:“意识形态”建构并再生产了“现实”,甚至就可以等同于“现实”。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区分了“经验现实”和类似于“物自体”的“实在现实”,并认为人们不可能直接体验经验现实,而只能通过“认识”来把握“现实”。又因为“认识”只有在发生“认识论断裂”的情况下才产生科学,所以“认识”的常态就是“意识形态”。这样一来,一方面“实在现实”不可把握,另一方面“认识体系”(也就是“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就是建构经验现实的全部“工具”,那么,就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公式:意识形态=认识体系=现实,(27)因此阿尔都塞宣布“意识形态”作为“现实”的“永恒性”。“意识形态既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历史的寄生赘瘤。它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只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必要性,才能去影响意识形态,并把它改造成为用以审慎地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工具”。(28)伊格尔顿则说得更明确:意识形态“生产并建构着现实”。(29)
如果可以称这种偷换概念为“颠倒”的话,那么它的确切含义就是指,“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转换,表明了对“现实”的“意识化”。在马克思明确自己的社会总体性的本质在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地方,阿尔都塞学派却以非唯物主义论断,改造了这种社会总体性的本质内核。
2、对“意识形态”的“物质化”:颠倒二。如果只完成了第一步颠倒,那不过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做法。阿尔都塞学派要为他的这种做法辩护,就必须使这一套学说找到“唯物主义”基础。因此出现了第二层的混淆和颠倒。
一方面,阿尔都塞学派正确地使用着“意识形态”概念的“观念体系”含义,并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真正的剥削关系、剥削为主导的社会关系必然需要某种“思想体系”的存在来掩盖这种剥削关系(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在这里,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起源,即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着剥削,并制造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履行的职能是掩盖剥削关系。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解释相关的则是这样一个命题: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一旦工人认识到剥削的存在,他们就会努力改变并砸碎剥削关系,此时,意识形态就不再能够履行其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职能了。
但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阿尔都塞学派放弃了“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含义,而代之以一系列“体制”(institution)的“物质实践”的含义,“因为他(社会个体)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30)在阿尔都塞的表述中,“意识形态”甚至不是“从”这些机器(即物质性的社会仪式)里“产生”出来的,而就是那类作为“指号”系统的社会仪式的“能指”本身,社会个体在一次又一次地践行弥撒、划十字、凝视、握手、写作、阅读等物质性社会仪式的过程中,被“意识形态”所俘获。连阿尔都塞本人也承认,就“意识形态”概念而言,原有的“观念”意涵消失了,取代这种意涵的则是“行为”、“实践”、“仪式”、“意识形态机器”等更为“宽泛”的“物质性”体系。(31)
显而易见,阿尔都塞在这里所说的“物质性”,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语境,而是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正如索绪尔所提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第一原则或首要真理”所表明的那样,语言系统的意指功能是通过“物质性”的声音现象和所指之间的强制性(任意性)关系来起作用的。整体语言的个体使用者,正是通过对这种以物质性语音现象为纽带的强制性意指体系的使用,或者说,通过进入这一强制性意指体系,而不断地认同、加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联,并在此体系中进行意义的交流的。(32)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符号系统物质性”基本规定性,能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物质性”当中一一找到对应。归根到底,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物质性”,首先表现为作为“物质基础”的语音与它所意指的对象之间关系的“强制性”。阿尔都塞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物质性”也首先表现为表面“中性”的社会文本与它的所指之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尽管这种“强制性”的理据来源于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过度决定”的社会实践。其次,正如索绪尔所说的在意指活动中,物质的听觉印象与它所唤起的“概念”是同一的整体一样,(33)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和同一性,这种“自足”的、作为物质机构系统的“机器”在运作过程中,把“主体”的角色分配给处于该系统不同层面的个体。可以看到,在伊格尔顿那里,“意识形态物质性”和“语言物质性”之间的等号被划得更加武断,他直接断定“语言”就是“意识形态”,“语言归根到底无非是政治语言”,(34)因为二者在“物质性”上,在“唯物主义”的“基础”意义上具有同一性,“语言首先是心理的、物质的现实,同时也是物质生产力的一部分”。(35)
尽管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语言实践观认为,语言不仅是纯粹意义上的“物质的”,即“震动着的空气层”,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实践的”,它“为别人存在并且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6)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在马克思“总体性”思想框架之内,物质实践的范畴要广泛得多,显然包括一切生产活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物质载体之间界限的混淆,实际上是为了对他们的理论工作提供“唯物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基础。
至此,我们看到,通过第一个“颠倒”,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给出了一个等式:意识形态=认识体系=现实,进而又通过理论上的第二个“颠倒”——即把“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体系的意涵翻转为作为物质机构体系的颠倒,又给等式中的“现实”加上了“物质现实”的“唯物主义规定性”。可以说,阿尔都塞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去唯物主义化”,并不是通过抽掉“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的方式来完成的,恰恰相反,却是以对“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范畴的片面化理解的方式完成的,是通过“唯物主义化”的方式来完成的。
这种“双重的去唯物主义化”的理论效果也是明显的。首先,它是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阿尔都塞主义能“理所当然地”摒弃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践方式,以文本的“同一性”为基础,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转入其他符号系统的批评(即话语批判),把“意识形态介入”和“话语政治介入”当作自己的理论任务。其次,用物质性的“意识形态总体性”取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经典模式,从而在理论上越来越“方便”地将“斗争”移置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最后,在实际的理论效果上,阿尔都塞主义为自己制造了难以勾销的一个困难: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阿尔都塞的理论一开始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诉求,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科学;然而,这个正确的论断却在其“意识形态总体性”的理论构造和理论语境之中,丧失了其“正确性”,因为如果“物质基础”仅仅被有限地界定为文学文本、一般文本、理论、日常生活等“话语文本”,阶级斗争也就因其真正对象的丧失而变成马克思恩格斯曾讥讽过的“词语对词语”的斗争了。
注释:
①③Louis Althuser: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ed.and trans.Gregory Elliot,London:Verso1990,p.i,23。
②这三篇论文是《小剧场,贝尔多拉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一封论艺术的信——答达斯普尔》和《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
④⑥⑦⑧(24)(25)(30)(31)路易·阿尔都塞《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59、321、361、352、352、355、359、35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⑩Terry Eagleton:Ideology:an Introduction,London,Verso,1991,P.1-2,1。
(11)(12)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0、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3)(14)(15)(17)(18)(19)特里·伊格尔顿著、刘峰等译《文学原理引论》第14、236、236、235、239、237-23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16)Pierre Macherey:The Object of Literature,trans.David Mace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33-234。
(20)Mark Cueeie: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9。
(21)在史学领域,历史的“话语研究”,是从曾受教于阿尔都塞的米歇尔·福柯开始的。他的《疯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性经验史》今天已成为了历史“知识型”研究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经典。继福柯之后,美国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也把话语分析同历史研究联系起来,在其《元史学》之中,明确指出,历史观念只是一系列具有意识形态本质的语法结构和修辞方式。史学界对历史的这种“文本化”,本身就使当代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文学批评领域”,同样,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也无法摆脱历史文本化的这种影响,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参看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彭刚校《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2)Postmodern Mater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t theory:Eassys in the Althusser Tradition [M],Antonio Callari and David F.Rnccio ed.Hanover NH: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Press,p.1。
(23)此处借用英国学者列昂纳德·杰克森的术语“demateridisation”。他在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整体之后,得出结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讲,就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去唯物主义化过程,见Leonard Jackson,The Dematerialiation of Karl Marx:Literature and Marxist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4。在本文作者看来,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学派兴起之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界某种程度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的“滥用”基础上,才真正造成了彻底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去唯物主义”。不可否认的是,阿尔都塞尽管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但对“意识形态”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的再阐释本身存在着“脱节”、“混淆”,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们的“滥用”、“去唯物主义”提供了理论条件。然而值得强调指出的是,阿尔都塞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在哲学史的研究中重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潜流”的概念,对“唯物主义”概念做了斯宾诺莎主义的再阐释。相关著作可参看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Later Writings,1978-1987,trans.and ed.G.M.Goshgarian,Verso,2006。
《再思理论:也谈当代文学理论及其批判》的两位作者明确地指出过“阿尔都塞批评学派”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混淆,本文作者的这个思路无疑受惠于这个批判文本,见“Althusserian Marxism”,in Richard Freadman Seumas Miller,Re- thinking Theory: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an Alternative Accou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26)(29)(34)(35)Terry Eagleton:Critciism and Ideology,London:New Left Books,1976,p.54,69,54,540
(27)参看[法]路易·阿尔都塞著,李其庆、冯文光译《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第一章《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当中,雄心勃勃地试图像《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那样为自己确立一个认识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现实”和“经验现实”之间的区分和“认识型生产理论”(即知识生产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认识论”相断裂的“科学”,在断裂之后,这种科学在政治实践中就成为新的“认识型”,通过意识形态功能“锻造”、“召唤”“无产阶级”,并规约“无产阶级”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现实”的体验。总之,就这个层面而言,“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观念体系的“常态”,是人们集体体验现实的“环境”,因此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中明确表示,他不能确定共产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是否会消失。
(28)路易·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第20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2)(33)索绪尔著、屠友样译《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第83-87、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标签:文学批评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物质决定意识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社会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