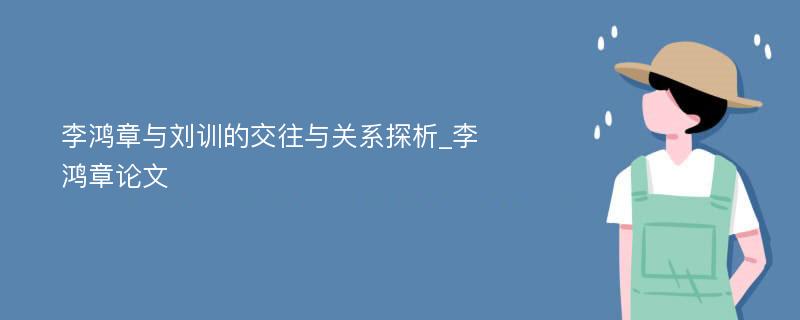
李鸿章与刘郇膏之交往及关系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李鸿章论文,刘郇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2-0083-05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泉),安徽合肥人。刘郇膏(1821-1867),字松岩,祖先由山西洪洞县迁居河南太康县,遂为太康人(注:贾熟村:《刘郇膏传》,载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下),黄山书社1995年版。)。李鸿章比刘郇膏小2岁。道光二十七年(1847),两人同为该年丁未科进士,于是双方有了“同年”之谊。丁未会试后,李鸿章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咸丰三年(1853)随工部侍郎、安徽旌德人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底(1859年初)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后受命组建淮军,赴援江苏;刘郇膏则以即用知县分发江苏,历署娄县、嘉定县,有政声,补青浦知县,咸丰八年调任上海知县,咸丰十一年(1861)冬,因率团练死守上海,保全有功,加道衔,以知府用,升海防同知(注:《清史稿》40册,第12351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两江总督曾国藩推荐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担任援苏主帅。同治元年(1862)三月十日,李鸿章率领首批淮军驶抵上海。二十五日,李鸿章致书曾国藩,谈及沪中情形及对刘郇膏的任用,称“沪中人才多染习气,惟刘郇膏朴实爱民,吴仲宣(指吴棠)来信亦力赞之。已令其随营整顿兵勇,练习防剿。但吏才欠精核,可胜臬司外道之任”(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357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二十七日,清廷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以刘郇膏署理江苏按察使,上谕并称“刘郇膏深得民心,迭经中外保奏,并著曾国藩、李鸿章察看,如该员于军务可期得力,则李鸿章往镇江后,所有上海军务即可责成该员接办。倘该员不能驾驭楚军,即著该署抚另简得力之员管带”(注:《李鸿章全集·奏稿》(一),第40页。)。二十九日,李鸿章复函吴棠,称“刘松岩太守诚悫廉正,为沪才之冠,但不善理财。委以沪事,尚恐力不能举”(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359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四月二日,李鸿章函告曾国藩,拟委刘郇膏总理淮军营务处:“刘守郇膏笃诚可爱,拟委令总理营务。渠于薛公务营皆熟,到处民情爱戴,经理一番,将来鸿章出江,可托其照应一路。”淮军营务处设立于安庆组军之初,入沪后以至整个平吴时期,一直随李鸿章行动。其主要职能是协助主帅参赞军务,办理文牍,并协调各部之间以及军队与地方间各种关系。刘郇膏因在上海等地任职多年,循声卓著,深得民心,且与前苏抚薛焕在沪招募各营较熟,易于联络,是故李鸿章有此任命,以备自己将来赴镇江之后,由刘郇膏负责上海防务。
四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到三月二十七日谕旨。次日上书曾国藩,信中对刘颇为倚重,“刘松岩奉旨署苏臬,兼办鸿章营务,各事皆能帮同经理。惟其手无亲兵,不能骑马,尚须徐徐练习。渠颇以沪事自任,二三月后或可替手。”(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362页。)十八日,李鸿章上《初到上海复陈防剿事宜折》,指出松沪水陆各军人数虽众,但军纪不严,必须挑选淘汰、择换将领,束以楚军规制,训练整顿须数月方有头绪,“署臬司刘郇膏朴实廉正,深得民心,现委办臣军营务,藉资练习,亦须数月后察看能否接办。”(注:《李鸿章全集·奏稿》(一),第41页。)并表示此举用意在于让刘郇膏多加历练,因为在曾幕中见曾国藩选将练兵,亦不求旦夕之速效。二十日,曾国藩复函,对李鸿章的安排表示同意,“阁下自带五千人东征西剿,留刘松岩驻沪,留湘淮二三营交刘统辖训练。薛部亦可酌调数营回沪,改用楚师营制营规,并交松岩训练。数月之后,阁下带三四千人赴镇,松岩留沪,此其张本矣。”(注:《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715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
因清廷裁撤各省团练大臣,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奉召还京,江南团练事宜移交李鸿章接办。李因莅任不久,于各路情形不太熟悉,前线战事又紧,于四月二十九日附片奏请由刘郇膏负责上海附近一带地方团练事宜,所有庞钟璐移交过来的团练捐款及文案卷宗,统交刘郇膏接收。五月二日,李鸿章致书曾国藩,论及刘郇膏之升迁及短处,称“刘松岩质朴谨厚,不独不能打仗,即节度诸将亦难合宜。去年上海县,今年即作统帅,熟人熟地其谁服之?况才亦短绌,鸿章若不管沪事,委之松岩,是实害松岩并弃地矣”(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363页。)。此段议论亦是实情,由于淮军基本继承了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即所谓“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注:王定安:《湘军记》,第338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安徽团练的血缘地域特征在淮军中十分明显,刘郇膏以“外人”居中调度,难以妥帖。况上海华洋杂处,富庶之区,湘淮军饷需所系,李鸿章希望由一位深谙洋务、善应变之人来坐镇(注:据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记载,李鸿章赴沪前与曾国藩相商,“上海洋商萃集,江苏司道必须通达外情、明知政事者方克胜任。”见该书第20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1年版。)。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此亦似为李鸿章不愿离沪赴镇的开脱之辞。针对李鸿章的议论,曾国藩在二十四日给刘郇膏的复信中,劝其勤加整顿营务,“阁下以召杜良材办理营务,拊循体恤,易得士心。惟兵勇狃于积习,整顿亦颇不易。……江南大营及苏浙各防向来略于训练,人情恶劳就逸,颓放之后便难振作。今当力与更始,庶几旌旗变色,壁垒一新。”(注:《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805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
六月十四日,李鸿章致书曾国藩,谈论前往镇江之难处,“如须赴镇,留潘(鼎新)、刘(铭传)各营守浦东,令华尔守松江,刘松岩带数营守沪,若无大股贼至,原可敷衍。惟各营与松岩多不浃洽,皆欲随鸿章西行,骤易统将,本是难事。”(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368页。)二十六日,曾国函复函:“松岩守沪,与各营既不浃洽,一与大旆相离,必不相安。或饬令三弟(指李鹤章)专管沪中营务,而以松岩专管松沪民事,或较妥洽。”(注:《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893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曾国藩当时希望在李鸿章移驻镇江后,由李鹤章来主持上海的局面,以固饷源。李鸿章出于避嫌,以“三舍弟从军志定,畏人多言,不肯独当一面,似难强之”为由婉拒。不过他还是听从了曾国藩让刘郇膏多管松沪民事的建议。六月底浦东金山卫城克复后,李鸿章派刘郇膏前往该地会商守将潘鼎新,查勘城东海塘及河道形势,兴工浚修,为稳守计。闰八月二十八日,在与庞钟璐的通信中,李鸿章还称赞刘郇膏,“沪中吏治近稍谨饬,只是可用之才多,可靠之人少。而刘郇膏实心爱民,长于察吏。”(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388页。)
九月初,因李秀成率太平军围攻金陵外围曾国荃部湘军甚急,曾国藩请李鸿章派淮军骨干程学启赴援助剿。因程学启进兵嘉兴,势难撤回,李鸿章内心也不愿放行,他另抽调吴煦、杨坊督带常胜军往援,并借机削吴煦之权。时吴煦身兼两职:署理江苏布政使、苏松太道,掌控关税开销与沪饷出入。十三日,李鸿章将此安排函告曾国藩,并称吴煦去后,拟令黄芳代理苏松太道,刘郇膏兼代苏藩司。十九日,李鸿章不待曾之复函(次日始发出),就会列曾衔上“擢用刘郇膏黄芳片”(注:《李鸿章奏稿》(未刊),上海图书馆收藏。),与《程学启不能赴援金陵片》一起,随《逆贼围攻四江口折》呈上。片中称吴煦已奉命督带常胜军赴援金陵,该员兼理司道两缺,关系至要,自应派员接代,以重职守,“查有署臬司刘郇膏,质朴廉勤,讲求吏治,堪以委令暂行兼理苏藩司篆务。”二十七日,李鸿章函告曾国藩,已安排接替,并称“刘松岩兼理藩篆,如办理裕如,似勿更张;若竭蹶不胜,再请筹调”(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394页。)。常胜军赴援金陵之议虽因白齐文索饷闹事而作罢,但相关的人事更替却照常进行。李鸿章对此举甚为得意,十月二十五日《上曾相》中称:“吴公(煦)卸去两篆,刘(郇膏)、黄(芳)才虽较短,而无丝毫欺蒙,沪中吏治渐有返朴还醇之象。”(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401页。)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湘淮军饷事最终把持在他自己的亲信班底手中。
刘郇膏兼理苏州布政使后,于十一月初在上海与布路斯国公使列斐士继续商谈天津条约换约事宜,后又与苏松粮道郭嵩焘、署苏松太道黄芳设局筹办京米,以充仓储。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颁布谕旨,命通商大臣薛焕调京使用,著李鸿章暂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督同刘郇膏、黄芳等悉心经理。刘郇膏自兼理藩篆、署理臬司后,事务较繁,难以顾及淮军营务。李鸿章另委苏州府知府李铭皖、候选道潘曾玮接办,郭嵩焘随营襄助,并于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二日上奏,称刘郇膏“办理营务,小心勤恳,军民辑睦,著有微劳”,现在江苏按察使一缺尚无人实任,刘郇膏署任一年,始终奋勉,请求朝廷实授刘郇膏江苏按察使一职。廷旨允准。
三月初十日,因刘郇膏请求于兼理藩司与臬司两职中辞去一差,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考虑到刘“才实未足久兼繁剧”,商量接替人选。后因万启琛出任苏州藩司,“派员署臬即作罢论”。
江苏为朝廷财赋之区,仓庾根本,湘淮军饷糈所系,而江苏一省赋额尤重,特别是苏州、松江、太仓二府一州,比他省多出数倍。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向朝廷上《分路规取苏州折》陈奏进取苏州方略的同时,还呈上了由曾李联衔、冯桂芬捉笔的《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奏请在江苏推行赋税改革。在后一奏折的起草过程中,吴云、冯桂芬、刘郇膏等当事者在赋税裁减率问题及奏折中是否应写进裁减浮收和大小户均赋问题上意见不一(注: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对此曾作详论述。她认为刘的提案,是从中央征税的一名官吏的立场出发,吴云的提案始终着眼于与其它地区间定额的公平。吴、刘两者体现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和确保地方利益这样两个相互抵触的原则,而冯桂芬的提案介于两者之间。同治初年的江苏减赋改革,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进行的,李与冯等苏州士绅之间的合作是为了确保地方的财富和军饷来源。但在冯与刘之间,李也势处两难,一方面是司署具体主持,一方面又要官绅和衷共济。但在1865年6月间江苏籍京官殷兆镛、王宪成弹劾李鸿章事件发生后,李与苏州士绅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因而具体负责这一改革的刘郇膏的意见在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治年间李鸿章与江苏省的赋税改革》,载《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安徽人》,黄山书社1994年版。)。刘郇膏提议削减苏、松、太二府一州原定额的二成,削减常、镇二府原定额的一成;并认为要将州县浮收一并裁尽并非易事,此次上奏的主旨是减赋,故反对将裁减浮收与大小户均赋之事与此并提。冯桂芬则主张将最近十年间的实征额作一合算,取其平均值为新定额,并“欲减赋与裁浮收并举”。最后,李鸿章综合各方面意见,决定以冯桂芬的方案为基础,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来减赋,并把裁减浮收一项也写入奏折,但详细内容留待以后设局筹议。
七月十一日,李鸿章自沪启行,前往吴江、苏州、昆山、常熟、江阴各路查勘形势,督筹调度。考虑到此次出巡时间较长,临行前,李鸿章作出部署:军务及地方紧要事件由行营办理,有关洋务交涉由署海关道黄芳就近商办,江苏巡抚衙门日行公事及上海地面弹压防守事宜由兼理藩司刘郇膏暂代主持。如有重大事件,仍须待回沪后裁夺。嗣因正任苏州藩司万启琛仍在皖营,而松属各州县准备择完善之区开征新漕,必须拣员接署苏州布政使一职。李鸿章认为刘郇膏久任江苏州县,熟悉漕粮情形,勤廉朴实,关心民瘼,故于十月初四日上“刘郇膏署理江苏藩司片”,奏请将刘郇膏由兼理苏藩司改为署理苏藩司,以便督同地方官核明科则,察看各处秋成分数,酌量征收新漕。此外,综核各军支放粮饷及一切公务较繁,其本任臬司篆务则由苏松粮储道郭柏荫署理。
十月十一日夜,因苏州战事紧急,李鸿章自上海前往苏州前线,督同程学启、李朝斌、戈登等筹划调度,所有巡抚衙门日行事件,委署苏藩司刘郇膏代拆代行。二十五日,苏州克复。二十九日,李鸿章移驻苏州,因上海地方紧要,奏留署藩司刘郇膏在沪经理筹饷征漕各事,会同署苏松粮道薛书堂督办捐厘总局,并会督营弁弹压防守地方。13天后,曾国藩复函刘郇膏,称赞他与李鸿章齐心协力,在后路筹画饷需劳苦功高:“苏垣克复,欣慰同之。上年少荃中丞统淮扬一旅之师赴沪渎一隅之地,与阁下及诸君子经营兵事,筹画饷需,甫阅半年,竟成伟绩”,阁下“早著循身,民望久孚,帝心简在。沪上饷源所系……悉赖荩筹,兼权并计,其劳勚可想而知”(注:《曾国藩全集·书信》(六),第4161页。)。
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附录寄谕,询及苏州克复后李鸿章能否在苏城驻守、居中调度,抑或亲赴无锡、常州督剿?上海一隅为华洋交涉要地,饷源所系,刘郇膏等日后能否办理裕如?是否应酌留武职大员在沪驻扎弹压?著李鸿章悉心筹划,以期周密。十七日,李鸿章致书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谈及刘郇膏与冯桂芬在减赋续稿上有分歧与沪上乏人接替:“移驻苏垣,沪上根本所系,苦乏替人。昨奉廷旨垂询,茫无以应。”(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446页。)不过,在二十八日李鸿章上《移驻苏州兼筹上海片》中,仍委刘郇膏负责沪上,“上海饷源,为臣军命脉所系,自臣赴苏后,各司道循照旧章办理,静谧如常。署藩司刘郇膏久任上海厅县,民情爱戴,堪资坐镇。现在筹饷征漕各事,亦须在沪经理。臣本留有记名总兵郑海鳌护军营淮勇五百人扎营沪城南门外,即令刘郇膏等会督营弁弹压防守。”(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482页。)不久,因江宁布政使乔松年升任皖抚,苏州布政使万启琛接任江宁藩司,刘郇膏、郭柏荫升任苏州藩司、苏臬司。接任后,刘郇膏疏浚吴淞江以通运道,议定新漕海运章程及漕余折耗章程,历年州县浮收、绅士包揽之弊无不杜绝(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486页。)。
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九日,因江苏全境渐次肃清,劝捐抚恤、资遣难民、赈济灾民、招集流亡等善后事宜亟需筹办,李鸿章奏苏州布政使应即回驻省城,并饬刘郇膏将上海经手事件料理周妥,即日驰往苏州,办理省城善后局务,抚绥地方。由于藩司衙门被毁,拟暂就民房居住,以资办公。九月初三日,李鸿章上“优叙刘郇膏郭柏荫片”,奏请奖励刘郇膏,“臣上年冬间督军进攻苏州,其时嘉兴各属均未克复,所有上海后路防务交苏藩司刘郇膏筹办,镇静周密,地方赖以晏然。前敌各军粮饷军火,亦由该藩司随时筹济无误,藉得迅速奏功”,请将苏州布政使刘郇膏交部从优议叙,并赏给三代二品封典。十一日,上谕允准(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488页。)。
同治四年(1865)四月,因僧格林沁败亡曹州,清廷极度恐慌,京师戒严。二十七日,清廷诏命曾国藩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以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二十九日寄谕命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刘郇膏护理江苏巡抚。五月初四日,李鸿章奉到署理江督之上谕,同日函告曾国藩,因奉命暂署江督,江苏省内事宜暂由刘郇膏经理,“仍是一鼻孔出气,兵饷或不致掣肘”(注:《李鸿章全集·奏稿》(一),第196页。),另拟派郭柏荫署理苏州布政使,王大经署臬司。初六日,上《署理总督筹办大概情形折》,称“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印。此间善后如浚河、兴学、抚恤、劝农及常镇招垦荒田、上海通商洋务,均次第办有端绪。藩司刘郇膏接护抚篆,情形熟悉,地方一切可无贻误”。二十日,李鸿章自苏州起程,途次专员将抚篆交刘郇膏接收。二十二日,李鸿章至金陵接两江总督关防,刘郇膏也在苏州接苏抚篆印视事。
因江苏籍京官礼部侍郎殷兆镛(吴江县籍)、内阁给事中王宪成(常熟县籍)上奏弹劾李鸿章在江苏境内遍设厘卡,加设租捐,横征暴敛,恃功朘民,一向以“清廉”自持、早在以知县分发江苏时就曾对神明誓不苟取一文的刘郇膏,深感“官斯土者,何以自白于天下?”闰五月十七日,李鸿章写信安慰刘郇膏说:“其(指殷兆镛)所陈厘捐一疏,捏造名目,殊为可恶。至厘卡之密东南数省略同,少见多怪,不识时务。……尊论官斯土者何以自白于天下,其咎与怨皆鸿章一人任之,诸公尽可以自白。总之,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又何不可自白、不可共白耶?”(注:《刘郇膏神道碑》,《续碑传集》卷30,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六月十七日,李鸿章致函刘郇膏,再论此事,并表心迹:“鄙人兵饷兼筹,事体轻重略有权衡,或未俟去任而先议裁卡,又值巨绅谤侮之时,未免稍涉支离。敝疏复陈,聊表心迹,以觇上意之从违为进退耳。……折内不累及司道一语,怨固独任,谤亦独受,惟赖执事(指刘郇膏)与远堂(指郭柏荫)、子奉(指陈庆长)、蔗农(指蒯德标)诸君随时确查弊端,就近整顿,以匡弟所不逮。”(注:《李鸿章奏稿》(未刊)。)针对朝廷内外皆言裁并厘卡,七月十一日,李鸿章复函刘郇膏,主张派委明练老成之员周历各处,咨访考察,然后集议,并称“弟与阁下共处危难数年,于兹断无不可共谅之隐。从事各员有偏见未化者,委曲开导,以求一是”(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491页。)。
九月,因张宗禹部捻军在河南南阳一带活动频繁,河南防军极不得力,初六日,清廷发出上谕,拟派李鸿章督带杨鼎勋等军赴豫,驰往河洛防剿,兼顾山西、陕西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署江宁藩司李宗羲、两淮盐运使丁日昌递署漕运总督、江苏巡抚,并饬曾国藩与吴棠、李鸿章彼此函商后复奏。对于朝廷以丁日昌取代刘郇膏接任苏抚的打算,李鸿章既赞同,又有疑虑。十四日,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松岩护抚以来,兵饷尚未掣肘,远久必难如常。雨生(丁日昌字雨生)洋务既熟,与敝军息息相关,朝廷自有深意。惟资望过浅,松岩闻之当先引退,司道以下,亦难翕服”(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495页。);另一方面,一旦自己视师河洛,则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其“满腹牢骚,用人行政或多变局”。在此信中,李鸿章还提出三种人事方案供曾参考:以李瀚章(时任湖南巡抚,李鸿章长兄)为苏抚兼通商大臣,丁日昌为苏州藩司;或以李瀚章署江督,丁日昌为苏抚兼办通商;或以刘郇膏署漕运总督,李宗羲留任江宁藩司。
曾国藩在接到廷寄的当天,就感到朝廷措置太突然,“竟日为之不怡”。他认为李宗羲、丁日昌虽各有所长,但资格太浅,骤升督抚,物望未浮,难以胜任,关键是两江系湘淮军用武力打下来的最可靠的后方饷地,“李(鸿章)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217页。),此缺岂能轻易为旁人所夺?因此,他不待同吴、李商量,便于十九日径自回奏,表示强烈反对。李鸿章在明了曾国藩的基本态度后,也于十月初八日复奏,历陈兵势难远分、饷源难专恃、军火难接济,表示殊难前往。奏人,上谕以此事“毋庸置议”(注: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一,第14页,申报馆光绪三年印行。),事遂寝。
清廷九月初六日的廷谕并非密寄,消息传开后,果如李鸿章所料,刘郇膏以老母患病思乡为由,具折恳请开缺回籍终养。十月初六日,刘郇膏写信给李鸿章,准备告老还乡。初八日,李鸿章即复函劝慰挽留,叙同年之谊,剖析事情原委,信末仍以淮军粮饷军火相托。在李之《朋僚函稿》中为数不多的与刘郇膏的信函往来中,此信最有人情味:“台端忠厚恳笃,实心办公,不独弟共事数年知之最深,即阖省僚属、军民亦莫不同声依恋也。九月初六日寄谕,弟奉到后,因恐大局未甚稳妥,秘存数日,但缄商爵相(指曾国藩)妥酌复奏。嗣见爵相咨抄疏稿,漕帅并将前奉廷寄咨行,又恐外间传闻异词,故补咨尊处、俾释众感。今阁下陈情万一奉准,苏局艰难谁与搘撑?念之心悸。……弟西行终不获免,惟粮饷军火根本在吴,仍赖老同年始终维持,是所感企。年伯母上寿康强,定占勿药,幸多方劝慰之。目前征漕吃紧,断不可稍有松劲。吾辈在官一日,当尽一日之心。州县有不率教者,务祈秉公严办,岂有救令不行之事。弟亦将去官,且离苏较远,此事实难兼顾,愿我兄勿稍推诿。”(注:《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五),第2497页。)
对于刘郇膏陈请开缺之折,朝廷也未批准,而是温旨慰留:刘郇膏之母既经迎养在署,即可随时随地加以照顾,且护理江苏巡抚责任綦重,毋庸开缺回籍。同治五年(1866)四月初三日,刘母病故,刘郇膏在护理苏抚任内丁忧,例应回籍守制。他致书李鸿章,请据情代奏,并将巡抚衙门事件札委署苏州布政使郭柏荫代为处理。初六日,李鸿章上“江苏巡抚接护折”,因刘郇膏丁忧,奏请以郭柏荫补授苏州布政使并护理江苏巡抚。十二日,廷谕允准。
刘郇膏护柩回籍,因积劳和哀痛触发旧疾,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死于太康(注:另有一说:刘郇膏因同乡同族求贷者不满所欲,众怨逼之,上吊自杀。见《大平天国史料丛刊简辑》(二),第14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此时,李鸿章已继曾国藩出任钦差大臣,北上督师镇压捻军起义。同治六年(1867)五月十八日,李鸿章上“刘郇膏请恤片”(注:《李鸿章奏稿》(未刊)。),陈叙刘之劳绩及对自己的帮助,请朝廷从优议恤。此片大意为:该故员由进士历任江苏嘉定、青浦、上海等县,治行卓然。同治元年,鸿章率师至沪,刘郇膏于海防同知内奉特旨擢任署臬司,所至舆情爱戴,鸿章即令其总理营务。其时军情复杂,沪上三面受围,李秀成、谭绍光等以数十万之众迭次扑犯,鸿章孤军初集,屡频于危,汰旧募新,增兵簿饷,筹商计画,实得其助。鸿章每视师前敌,直至苏州克复,上海后路一切事宜均赖刘郇膏处理。及刘擢任藩司,正赶上恩旨议减苏松等属粮赋,刘郇膏折衷群议,研精覃思,勾稽考核,务期平允,年余始定,民间尤感颂之,而该故员心力亦交瘁矣。该故员厚重刚方,秉性笃孝,撑持艰险,实为僚属中不可多得。请将护理江苏巡抚、苏州布政使刘郇膏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从优议恤,以昭荩勋。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刘郇膏著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从优议恤。”后赠右都御史,上海建专祠,祀苏州名宦。
李鸿章率淮军入沪不久即署理江苏巡抚,集领兵、筹饷两项权力于一身。在淮军独立进行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次恶战,守住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他便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改变“江苏吏治,多趋浮伪巧滑一路”(注:《李鸿章全集·奏稿》(一),第51页。)的现状,在人事上,李鸿章罢免了以吴煦、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起用了一批务实肯干的官员,逐步组建自己的亲信班底。刘郇膏是其同年,又在上海等地任职数年,熟悉情形,故亦被罗致,委以重用,成为李鸿章早期关系网中重要的一员。在此后的数年里,尽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通信中曾抱怨刘郇膏才识短绌,缺乏洋务、应变之才,但由于刘郇膏为人“诚悫廉正”、实心任事、“无丝毫欺蒙”,与自己“一鼻孔出气”,在为湘淮军筹措饷糈、处置上海后路一切事宜方面甚为出力,给予李鸿章较大帮助,故两人间也始终能维持一种互相支持与合作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