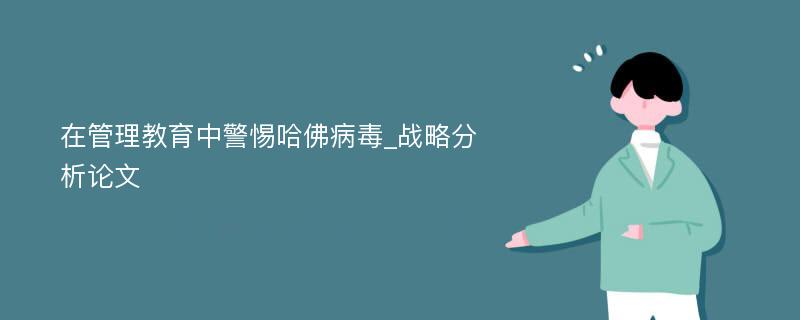
警惕管理教育中的哈佛型病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佛论文,病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学界的学术研究和企业单位的用人实践都发现,很多MBA学员夸夸其谈却眼高手低,长于分析但不善人事,重个人发展却轻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其实与被奉为管理教育最重要工具的“哈佛案例”的内容直接有关。由于案例教学在MBA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哈佛案例和其他院校模仿开发的“哈佛型案例”所隐含的思维模式误区,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导致MBA学员畸形发展的一种病毒。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管理院校近年来开发的本土案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感染了这种“哈佛型病毒”。
案例教学与思维模式
高层管理的最大困难往往不在于如何解决问题,而在于如何正确地定义问题——难的不是处方,而是诊断。面对千头万绪的世界,最关键的管理问题往往不是“应该怎么办”(What to do?),而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What is going on?)。从这一角度来说,管理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分析技巧的传授,而是思维模式的开发。
案例教学在这方面的作用特别重要。哈佛商学院是这样介绍案例教学法的:“每个案例都是一个真实商业情境的描述……所提供的情境对大多数企业都具有代表性。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而且是一种管理哲学。”通过对大量企业管理实际案例的学习,学员不但会学到处理商业世界问题的方法、工具,而且会逐步形成自己观察思考商业世界问题的基本框架和行为理念。但是,案例中的实践并不是实践活动本身,而是经过提炼的“报告文学”。案例作者的视野、偏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案例素材的筛选剪裁,作者的盲点、色差会直接或间接地在案例中表现出来。因此,MBA教学案例所反映的“商业情景”是否能真实地再现企业管理的实际,就成为案例教学是否有效的关键。如果管理案例是一种“哈哈镜”,反映的是扭曲的现实,案例教育就可能误导学员形成错误的思维模式。
那么,管理学教育中使用最多的MBA教学案例所反映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实际?学完了MBA课程中的几百个案例之后,MBA学生将会潜移默化地建立起什么样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模式?
由于在管理教学中发行量最大、使用最多的是哈佛案例,哈佛案例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就成为管理教育学界必须研究的问题。
哈佛型案例的五大误区
2003年,美国管理教育杂志发表了两位美国学者Swiercz和Ross,对哈佛商学院1987至1988年间销量最高的30个案例的分析。由于企业组织及其所处社会的复杂性,案例的真实性就在于全方位地反映管理实践,尽可能充分地体现问题的方方面面。这两位学者用企业管理活动的四种基本维度(经济理性的、人性情感的、权力政治的、精神文化的),对哈佛案例反映现实生活的全面性、真实性作了细致的定量分析。他们发现哈佛案例的整体框架几乎完全是经济理性的。大多数案例将企业简单地描述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工具,忽略企业的社会性和组织成员的人性面,忽视心理契约、非正式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忽视企业是不同利益集团联盟的政治现实,忽视企业人的精神层面需要。同时,哈佛案例通常围绕高级经理展开,以高级经理人的视角为惟一视角,基层员工在案例中或者被完全忽视,或者是以要解决的“问题”的面目出现,而总裁、董事长则几乎永远以正面人物的身份出现。我与我的合作者王佳茜(2004)、林淑(2005)所作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缺陷的存在。
根据我本人在国外商学院任教十几年的观察,国外商学院所采用的哈佛商学院案例和其他院校模仿开发的哈佛型案例,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这些案例的内容大概可以这样概括:选材是企业的战略决策,主角是企业高层,而决策则来自于数据分析。在这种“哈佛型”案例的背后,隐含着许多错误的思维模式。择其要者,大约可以归纳为五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理性偏向”。也就是片面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方面,而忽略管理中同样重要的非理性(人性的、政治的、精神的)因素的作用。“理性偏向”片面地把企业看成是管理者手中的一种工具,关注的主要是所有者、经理人如何控制企业。其实,企业一旦形成,就是一种有生命、有知觉、有意识的社会细胞,其运行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并不完全受控于其所有者或行政首长。在企业活动的实际运行中,非正式组织往往是正式组织的基础,心理合同可能比法律合同更重要,而决策过程的象征性意义有时候可能比决策结果本身更关键。
第二个误区是“战略至上”。大多数教学案例把企业的问题简单地看作战略决策的制订问题,片面强调战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好像制订战略是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实际上,战略是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必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经常制订战略的企业一定不是好企业。改善企业管理绩效最主要的问题,绝大多数时候不在于战略制订,而在于组织建设,这是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
有“战略至上”偏向的案例往往把战略问题描绘成董事会、总裁室的拍板问题,好像战略问题是独立于企业日常业务、独立于细节之外的。其实,做企业就像写小说,故事好编,难的是细节。一个优秀企业就像一部世界名著,她的深刻、她的精彩、她的风格,体现在每一个细节的丰富、细腻和准确上。麦当劳的战略,就是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连锁店,一年365天的每一天,做好服务每一个顾客的每一个细节。那种认为只要选对了战略,其他都可以委托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这就好比是说,只要有了一个出色的“构思”,就可以委托他人写出世界名著;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相反,战略制订却是可以委托的,可以找咨询公司来做;惟独组织建设必须亲历亲为,因为这里要改变的,是管理者自身的行为。
第三个误区是管理教学案例的“总裁中心”、“高管中心”偏向。几乎所有的哈佛型案例的中心人物、观察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企业的高管或者总裁。员工和中下层管理人员或者根本不出现,或者是以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面目出现在案例中。总裁、高管则被塑造成主宰宇宙的英雄人物。MBA教学案例几乎从来不讨论最高管理团队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权力斗争,以及高管人员尤其是行政首长的个人缺陷、代理人行为问题。企业管理的挑战,或者被写成外部环境的问题,或者是内部协调的问题,或者是考核激励的问题,但却几乎从来不是最高管理团队的问题。这就给MBA学员一种错误的假象,似乎管理者要做好工作,只需要做好工作本身,而不必涉及“公司政治”问题。但是,企业的问题,归根结底都与其最高管理团队的问题有关。不懂得“对上管理”的管理者,不可能是有效的管理者。
第四个误区是“分析决策”的偏向。大多数案例以某个高管正在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管理问题而一个人冥思苦索的场景开头,然后,案例正文介绍相关的各方面的情况数字,最后要求读者通过数据分析,比较不同的方案的利弊,提出一个行动方案。这种案例隐含的思维模式是,管理的关键是决策,决策的方法是分析,而分析的目标是优化。这里至少有三重错误。
其一,管理的关键未必是决策。很多哈佛型案例过分强调管理者的“决策者”作用,忽视了管理者作为不同意见、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调人”的角色。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大多数管理问题的难点不在于问题的分析决策,而在于怎样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寻求共识。“分析决策”的偏向忽略了管理活动的社会性本质。
其二,决策的方法未必是分析。“分析决策”的偏向片面突出分析的作用,片面强调“先思考,再行动”,忽视管理者的实干家角色,忽视了“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的重要。实际上,大多数管理方案产生在实地解决问题的摸索过程之中,而不是在此之前。“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之所以比精心策划出来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更成功,原因也在这里。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可以理解为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人“分析”出来的。
其三,分析的目标未必是优化。很多教学案例往往孤立地分析问题,就营销谈营销,就财务谈财务,割裂焦点问题与其他各种管理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追求单一问题的最优解。其实,绝大多数管理者都身兼多职,角色冲突是管理世界最普遍的现实。管理者在解决问题时不可能不面对各种各样的历史包袱,不可能不受到政治、法律、人事的社会限制。营销决策中可能有法律问题,财务分析可能涉及人事安排,实际工作中不得不兼顾各方面。所谓管理,就是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妥协解,而不是单一问题的最优化。
第五个误区是“价值中立”的偏向。西方管理模式片面强调MBA教育的工具性和科学性,几乎避口不谈管理教育的价值观取向。绝大多数管理案例以价值中立的面目出现,就业务问题讨论业务问题,似乎不含任何价值偏向。但是,案例的选材(什么问题值得研究)和观察角度(从谁的角度来看问题),本身就体现了鲜明的价值观。大多数案例有意无意地美化和神化老总,漠视和歧视员工,把企业的管理问题描写为被管理者的问题,而不是管理者本人的问题。同时,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通过对“交易成本”、“代理人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使得不道德行为合法化。机会主义行为不再是一种道德问题,仅仅是企业的“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由于这种误区,导致西方MBA教育中普遍忽视学员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教育。研究发现,MBA学员的社会责任感明显低于公共管理硕士(MPA)学员,而他们的个人中心主义(egoism)则明显高于其他专业学员。
当然,造成部分MBA学员“夸夸其谈、眼高手低,长于分析、不善人事,重个人发展、轻社会责任”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不能完全归咎于案例内容的偏差。但是,上述思维模式误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指出哈佛和哈佛型案例的这些误区并不是要否定案例教学方法,更不是要否定哈佛在开创和推广案例教学法上的巨大贡献。一位我很尊敬的香港学者说,案例研究的重要性之于管理教育,就好像尸体解剖之于医学教育。这一点我非常赞成。本文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案例教学方法是否真正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取决于教学案例的质量,取决于它们所反映的“商业情景”是否能真实地再现企业管理的实际。如果我们解剖的是木偶、洋娃娃,那是不可能培养出好医生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