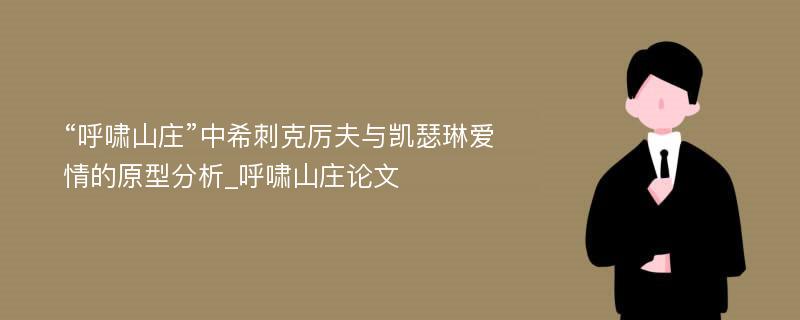
对《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的原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山庄论文,凯瑟琳论文,斯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其两位姊妹相比,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的作品很少,只有一本小说和一些诗歌,但正是她唯一的小说《呼啸山庄》,掀起了一百多年后一阵阵研究艾米莉·勃朗特的热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艾米莉引起了东西方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
由于作者及其作品都有许多难解的谜,长时间以来人们视艾米莉·勃朗特为现代文学中的“思芬克斯”。为了解谜,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其作品,从而得到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因而往往是旧谜刚解,新谜又出,解谜热潮永无休止,这种现象,充分显示了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永不凋谢的艺术魅力。
伟大的艺术作品所揭示的真谛往往不止一个,人们总能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诠释。《呼啸山庄》正是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本文运用一种较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原型批评(Archetypal Criticism)来研究《呼啸山庄》中男女主人公的爱,希望能借此解开《呼啸山庄》中一些长期困惑人们的谜。
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生死之爱
在《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吸引着读者的视线,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相互表现出的深沉,激烈而狂热的情感超出了任何世俗的爱情,正如喜尔达·斯皮尔所言:“他们的爱有着伟大的精神特质,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浪漫的爱”[①]。
希斯克利夫是凯瑟琳的父亲恩肖先生“捡”回来的孩子,虽然家里其他人都恨他,疏远他,凯瑟琳却从一开始就喜欢他,亲近他。他们从小就朝夕相处,连女管家纳莉都说,“她(凯瑟琳)跟希斯克利夫好得不得了,我们能想出的对她的最大的惩罚就是不许她跟他在一块儿。可是为了他,她比我们哪一个都受到更多的责骂。”[②]
恩肖夫妇死后,凯瑟琳的哥哥亨德莱成为家庭的统治者,他把希斯克利夫看成篡夺他父亲的爱心,侵占他的特权的人,要把他贬到他原来的位置——流浪儿和下等人的位置。于是他剥夺了希斯克利夫受教育的权利,强迫他到田间劳动;命令他像下人一样叫凯瑟琳“小姐”,并且不准他们一起玩。而凯瑟琳不顾哥哥的万般责难,依然与希斯克利夫站在一起:她教给他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一有空就跟希斯克利夫溜到草原上尽情地玩。纳莉说,“他们(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最大的乐趣就是两人一块儿一大早就奔到荒原上玩一整天,至于事后的惩罚变得无非是让他们好笑的事罢了。副牧师尽可以任意规定凯瑟琳背诵多少章《圣经》,约瑟夫尽可以把希斯克利夫抽打到自己的胳膊都酸痛了;可是只要两个人聚到一块儿,他们便立刻把什么都忘了……”[③]。就这样,在共同反对亨德莱的过程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情感的纽带越系越紧,直到最后的不可分离。而这种连结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他们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直到一切的变故发生之后,彼此才发现了与对方的不可分离。
这就是凯瑟琳在答应富有英俊的林敦的求婚之后却只感到一片空落落的原因。对她,对希斯克利夫而言,画眉山庄永远是一个异己的世界,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天堂。这一点,从凯瑟琳对纳莉的表白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只是想说,天堂不像是我的家,我哭碎了心,闹着要回到人间来,惹得天使们大怒,把我摔下来,直掉到荒原的中心,呼啸山庄的高顶上,我就在那儿快乐地哭醒了……”[④]
这个表白也从一方面说明了婚后的凯瑟琳郁郁寡欢的原因:离开了希斯克利夫,离开了荒原和呼啸山庄,凯瑟琳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在画眉山庄那样一个异己的世界里,她感到的只是失落和空虚。她曾幻想通过嫁给林顿这样有钱有地位的人去帮助希斯克利夫摆脱亨德莱的统治,使他也成为人上人,可结果却令人心碎:希斯克利夫的出走带走了她的欢乐之源;远离荒原和呼啸山庄使她迷失了自我。
离开凯瑟琳,希斯克利夫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从呼啸山庄出走时,他是想从此不再见凯瑟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但经年的分离不仅没有淡化他对凯瑟琳的思念与渴求,反而不断加深了这种思念。如同一个灵魂的两半,失去另一半,他们就再也找不到完整的自己。
为了不再迷失,为了与自己灵魂的另一半重聚,希斯克利夫不得不重回呼啸山庄,重新回到他与凯瑟琳共有的世界里。一见面,他们就马上“完全沉醉在共同的快乐里,再感不到什么窘迫了”[⑤]。一个灵魂的两半,终于又得到暂时的重聚,他们融化进了彼此的快乐之中,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但以林敦为代表的世俗的社会道德却容不下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超越一切的灵魂之恋。所有的人,包括管家纳莉在内,都把他们的相互吸引看作是“可耻的”,违背伦理的事,从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林敦——凯瑟琳世俗的丈夫,逼迫凯瑟琳在他与希斯克利夫之间作出选择,这个要求无异于要分离凯瑟琳的灵魂与肉体。其实,凯瑟琳早就有了自己的选择:林敦是世俗的丈夫,希斯克利夫却是灵魂之恋。但林敦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一点的。他的逼迫把凯瑟琳推入了绝望之境,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凯瑟琳选择了死亡,以此来达到身体和灵魂的彻底自由,重回呼啸山庄和荒原的世界——她与希斯克利夫的世界。
把死作为解放自己唯一出路的凯瑟琳在面临死亡之时没有丝毫的恐惧。她唯一惧怕的是死亡会隔断她与希斯克利夫的结合,她对希斯克利夫说“我但愿我能一直揪住你……直到我们两个都死了为止!我可不管你受着什么样的罪……为什么你就不该受罪呢。我是在受罪呀!你会把我忘掉了吗?将来我埋在泥土里之后,你还是会快乐吗……”[⑥]“我再不会得到安息的了……我并不要你忍受比我还大的痛苦……我只愿我俩永不分离……”[⑦]
而希斯克利夫也面临着同样的恐惧,他一句安慰的话也没给凯瑟琳:“……贫贱、耻辱、死亡不管上帝还是恶魔能怎样折磨人,可别想把我们俩拆开!……我并没有弄碎你的心——是你自己把心弄碎了:揉碎了你的心,把我的心也揉碎了。我是强壮一些,因此格外地苦!我想活下去吗?这叫什么生活呢?当你——啊,天哪——难道你愿意活着吗,当你的灵魂已进了坟墓?”[⑧]
事实正是如此,凯瑟琳死后,希斯克利夫成了一个灵魂不全的人,一股破坏一切、摧毁一切的复仇的力量。没有了凯瑟琳的世界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完全的陌生者”,一个“黑洞”。
坚信凯瑟琳的灵魂(自己灵魂的另一半)还没有安息,还在荒原上等待着,呼唤着自己,希斯克利夫努力破坏曾经阻碍他们结合的一切,从呼啸山庄到画眉山庄到山庄的下一代,试图通过摧毁一切给他们最终的灵魂结合找一个安静的居所。从这一点上看,希对第二代的“复仇”其实不是有意而为,而是一种直觉的行动,一种追求灵魂完整的途径。
整整十八年,凯瑟琳不散的阴魂折磨着,呼唤着希斯克利夫,日日夜夜,从没间断。直到一天,希斯克利夫挖开了凯瑟琳的棺木,看到她正在消逝却依然是她的面容时,这种折磨才宣告结束:“我(希斯克利夫)平静下来了,我梦见我靠着那个长眠者(凯瑟琳)睡我最后的一觉。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的冰冷的脸贴着她的脸。”[⑨]
看到凯瑟琳安然躺在地下,希斯克利夫一下明白了自己十八年来痛苦挣扎的根源——没有跟自己灵魂的另一半真正地结合。他知道了自己的归宿是与凯瑟琳躺在墓穴中,从肉体到灵魂彻彻底底地融为一体,只有这样,他,以及凯瑟琳飘荡的孤魂才可以得到安宁。
一旦决定要离开那个世俗的世界,希斯克利夫放弃了“复仇”,放弃了一切,并且开始绝食,同凯瑟琳一样,他自愿地选择了死亡来解放自己的躯体和灵魂。他整日情绪亢亩,夜夜激动地在荒原上行走。他告诉纳莉:“我灵魂的快乐,杀了我的肉体……但灵魂自身并没有得到满足。”[⑩]
为了满足灵魂的快乐,在四天绝食之后,希斯克利夫愉快地踏上了他的死亡之旅,他死在小时候与凯瑟琳一起睡过的橡木床里,眼睛里显出一种“可怕的,活人似的狂喜的凝视”(11),这暗示他已实现了毕生的渴求——与自己灵魂的另一半终于重新结合在一起。
在普通人看来,选择死亡来达到最终的结合并不是成功的结合,由此他们把《呼啸山庄》看作一出大悲剧,但在艾米莉看来,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这个观点在她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明确,比如在《死亡》、《我的灵魂毫不怯懦》等诗中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在她看来,死亡如同一场酣睡;生活像一次让人疲惫的长途旅行,它最终的目的地是一片宁静之乡——死亡。更重要的是,死亡是艾米莉眼中永恒的先驱,达到死亡便达到了永恒,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
在《呼啸山庄》中,通过收实教堂的司事,希斯克利夫最终得以与凯瑟琳一起躺在荒原下的墓穴中;恩肖与林敦的第二代人也搬出了呼啸山庄,把荒原和呼啸山庄留给了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小说末尾牧童的话及故事叙述者都给了我们这样的暗示: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终于成功地获得了他们生生死死拼搏的东西——完整的、永恒的结合。
从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最终结合中,我们可以看出艾米莉对理想之爱的理解——一个灵魂的两半超越世俗、社会道德,甚至死亡的限制,最终合二为一,归于完整。
追求完整——爱的原型的再现
作为一个生活在荒原上的乡下姑娘,艾米莉并没有什么经历或经验。她历来被看作一个“隐居者”,而且据考证既没有爱上过任何人,也没有被任何人爱过。是什么使她得以写出英国文学中最伟大、深沉而炽烈的爱情呢?其创作灵感来自哪里?我们可以从希腊神话原型中找到答案。
在希腊神话中,最初的始原人是圆形的,“它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脑袋,一个脖子上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其他的身体部件也是这样成双的”(12)。他们可以像现代人这样行走,想跑快时就像不倒翁一样在地上滚。他们力大无穷,非常骄傲,甚至雄心勃勃地向众神发动了进攻,要与众神一试高低。众神被激怒了,商议惩治始原人类,是宙斯找到了惩治的办法:“我把他们劈为两半,一方面使他们更弱小,一方面有更多人为我们服务。”(13)于是始原人都被劈成了两半,被劈以后,始原人的一半总是寻觅着从前与自己连成一体的另一半,当碰着自己的另一半时,他们就拥抱在一起,怎么也不分开,不吃不喝直到死去……
对于这个神话,柏拉图作了如下的诠释:“爱植根于人类的古老由此可见一斑,它带领我们重返始原的状态。努力合二为一,愈合人的裂痕。因此,每个人都只是整体的一半,而且总是追寻着自己的另一半”(14)。
由此,柏拉图认为:“这种原始的追求完整和合二为一的欲望和过程就是爱。爱是人类对自身完整的始原状态的回忆,是一半渴求与另一半合为一体,回到其初始的完整状态的欲望。
两千年后,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赋予这个老观念以新的生命力,认为这种追求一体和完整的欲望和过程是一个爱的原型模式,是人类漫长发展历史中宝贵的精神产品之一。它沉淀在每一个正常人的无意识之中,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中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反复的重现。实际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都是人类文学描述爱的主题最基本的形式。
在《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就是对这个爱的原型的最好重现。
原型批评的另一代表人物诺思罗普·佛赖伊认为:一定的原型在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文化中重现时会有不同程度的“置换变形”(displacement)(15);每个原型的变形随着具体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以及再现这个原型的艺术家的禀赋和特质的不同而不同。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把《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看作始原人的变体,分别代表始原人被劈开的两半;而亨德莱、约瑟夫、林敦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力量则可以被看作是宙斯的变体。
跟始原人一样,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原本共有一个灵魂,一个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的灵魂。正如大卫·塞西尔所言,他们是“风暴的孩子”(16),在蛮荒、原始的荒原上,过着狂野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共有的特质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注定了他们永远像始原人一样不可分离。他们灵魂的同一性在彼此的表白中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凯瑟琳说,“他比我更是我自己”,“我就是希斯克利夫!”(17);希斯克利夫也发自内心地呼喊,“我不能离开的我的生命而活着!我不能没有灵魂而活着!”(18)
跟始原人一样,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有着骄傲的灵魂和惊人的勇气:他们轻视亨德莱的家庭专制,瞧不起亨德莱与其妻子平庸的爱情;他们嘲笑约瑟夫对亨德莱的愚忠和对上帝的盲目崇拜;他们不相信祈祷并且对进入天堂毫无兴趣……一句话,他们蔑视所有的权威、宗教以及世俗的一切,他们对当时的世俗及道德发起了挑战,不顾人为的万般阻挠,生生死死地追求原本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然而,不管凯瑟琳多么坚定地宣称:“无论我们的灵魂是由什么制成的,他的(希斯克利夫的)和我的一模一样!”(19),亨德莱、约瑟夫、林敦及他们所代表的世俗道德绝不承认他们的同一性;虽然希斯克利夫也是恩肖家中的一员,但亨德莱从来没把他当自己人,就连约瑟夫和纳莉也想方设法地阻挠他们的结合。这样,他们在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硬生生地设下了一道鸿沟。
这条鸿沟由于林敦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深。林敦一家在看到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第一眼就在他们之间立下了一条分界线:同是闯入画眉山庄的野孩子,凯瑟琳被礼貌地请进门去,待若上宾,而希斯克利夫却被粗暴地赶了出去。原因在于凯瑟琳是“绅士的女儿,一个小姐”,而希斯克利夫是“一个吉普赛人,一个流浪汉”,“一个坏孩子,不配进入体面的家庭”(20)。
第三者插足的林敦显得满怀自信,因为在他世俗的眼光里,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看,他与凯瑟琳才是匹配的一对,而希斯克利夫是一个外人,一个不自量力的入侵者。在亨德莱及家人的帮助下,他成功地让凯瑟琳成了自己的妻子。结婚以后,他世俗的虚荣及自私心容不下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灵魂之恋,他强迫凯瑟琳在他与希斯克利夫之间作出选择,实质上是想迫使凯瑟琳舍弃希斯克利夫。正是这个自私的意图导致了凯瑟琳的死亡,以及希斯克利夫在之后的十八年中所受的折磨。
因此,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跟宙斯劈开的始原人一样,被亨德莱、林敦及他们代表的世俗道德硬生生地劈开了。他们重复着被劈后的始原人所进行的抗争:不顾外力的阻挠和世俗的限制,终其一生去争取永恒的结合。最后,像始原人劈开的两半重新变为一体一样,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一个灵魂的两半,终于完成了他们的毕生的追求,在死亡之中真正地合二为一,实现了他们在俗世所不能实现的愿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找到了《呼啸山庄》几百年来震憾着人们的原因了:它涉及到了一个超越作者意识界限,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建立在原型的基础上的。通过再现这个爱的原型,艾米莉道出了“千万人的声音”,激发出人类无意识中埋藏很深的重回自身完整的始原状态的欲望。这就是我们总能从艾米莉的爱情故事中找到共鸣的原因,这也正是《呼啸山庄》具有永恒不朽的艺术魔力的源泉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之前,已有不少评论家认识到了艾米莉作品中超越本人意识界限、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主题(universal theme):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曾在《普通读者》里面说:“艾米莉的创作是受到了某种更加普遍的概念(general conoeptions)的启示,促使她创作的动力,不是她自己的灾难或伤痛,而是她对陷入巨大混乱的世界产生的一种内心力量……”(21);而大卫·塞西尔在《艾米莉与呼啸山庄》一文中则说得更明白一些:“跟布莱克一样,艾米莉关心的是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影响的生命始原的样子……她是在宇宙的天幕上来审视人类的”(22);除此之外,许多评论家也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与此相同的观点。
不管这些评论家用了什么不同的字眼,中心只有一个——《呼啸山庄》具有超出个人意识的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东西。而这个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东西是荣格所说的“原型”(prototype)。
通过原型分析,我们终于解开了艾米莉创作《呼啸山庄》之谜,也找到了她的作品与整个人类文学的联系。
促成艾米莉·勃朗特进行这个伟大创造的还有两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一)蛮荒原始的生活环境以及她隔绝尘世的生活;(二)艾米莉敏感的心灵及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
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一文中,荣格强调了一定原型的再现与特定的神话环境再现的关系:
“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环境就会有多少原型。无数次的重复已经把那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心理构造之中,这种刻画是以概念的形式而非内容的形式进行的。当与一个特定的原型相应的环境再现时,原型就会活动起来,不由自主的情形就出现了,像一股本能的驱动力,不顾一切理性和人为的意志,不断往前冲……”(23)
由此可见,环境在原型的再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艾米莉的创造也证明了这一点。她短暂的一生几乎都在荒原上度过,住在约克郡(Yorkshire)北部的一个边远山村(Haworth),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那里没有工业文明带去的喧嚣,有的只是宁静和蛮荒。而正是这蛮荒、原始的环境帮助艾米莉完成了《呼啸山庄》这样伟大的创造——艾米莉所居住的山庄及四周的荒原其实就是小说环境的原型。
从原始的生活环境帮助艾米莉再现原型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原型在古老、原始的环境中更容易找到其回声。这正像人们通常所经历的——某些原始的遗迹或一个古老、边远的山村通常会激发起心中埋藏很深的、很伟大、很古老的情感。
如果我们把艾米莉蛮荒的生活环境看作一个原型的情境,那《呼啸山庄》的伟大创造就是在情理之中而不是一个谜了。下面一段荣格的论述,可以为其作一个完美的注释:
“每当这一种神话的情境(原型的情境)出现之际,总伴随着特别的情感强度,就好像我们心中以前从未发出过声响的琴弦被拨动,或者有如我们从未察觉的力量顿然勃发。原始意象(原型)寻求自身表现的斗争之所以如此艰巨,是由于我们总得不断对付个体的、非典型情境。这样看来,当原型的情境发生之时,我们会突然体验到一种异常的释放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所操纵。这时我们已不再是个人,而是全体,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个体的人并不能完全运用他的力量,除非他受到我们称为理想的某种集体表象的赞助,它能释放出为我们的自觉意志所望尘莫及的所有隐匿着的本能力量……
“一个原型的影响力无论是采取直接体验的形式还是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之所以激动我们是因为它发出了比我们自己强烈得多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他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慢长夜的亲切的力量。”(24)
这就是伟大艺术的奥秘,这也是《呼啸山庄》成功的奥秘。创造过程,就我们所能理解的来说,包含着对某一原始意象的无意识的激活,以及将该意象精雕细刻地铸造到整个作品中去。通过给它赋以形式的努力,艺术家将它转译成了现存的语言,并因此而使我们找到了回返最深邃的生命源头的途径。艺术家以不倦的努力回溯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这恰恰为现代的畸形化和片面化提供了最好的补偿。艺术家把握这些意象,把它们从无意识的深渊中发掘出来,赋以意识的价值,并经过转化使之能为他的同代人的心灵所理解和接受。艾米莉·勃朗特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通过不倦的努力,她成功地用语言表达出了自己所把握到的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赋之以意识的价值,并为当世和后世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原型(原始意象)虽然埋藏在每个人的无意识中,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把它发掘出来。这极少数就是那些伟大的艺术家,而艾米莉正是其中的一个。一颗愚钝的心灵连理解别人在想什么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发掘深藏在无意识中的东西了。因此,那些能够发掘出原型的人必须有一颗敏锐、善感的心灵和有深刻思想的大脑。而且重新表述一个原型更要求有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创造性,只有这样,原型才能以能够被人们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从《呼啸山庄》中爱的原型的再现中,我们看到了艾米莉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特质。
从评论家托马斯·A·沃尔格对艾米莉的生平介绍中,我们知道了勃朗特家的孩子“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博览全书并且喜欢摹仿所读的东西”(25);读艾米莉的(Gondal)诗歌及抒情诗,我们无不为其奇特丰富的想象力所打动;夏洛蒂·勃朗特也曾高度赞扬过艾米莉的出色想象力:“她的想象力充满了无比的力量,使她得以创造出希斯克利夫、凯瑟琳这样的人物”(26)。这一切都印证了我们提出的论断:艾米莉罕见的丰富想象力在她再现爱的原型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原型只是一种概念,一种形式,它需要内容去充实,如何充实则取决于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艾米莉得天独厚的禀赋和特质帮助她完成了这一创造性的劳动。
通过比较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与爱的原型,我们发现他们之间深沉、强烈而狂热的爱是人类爱的原型的再现;所以《呼啸山庄》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和艾米莉个人天才的结晶。更明确地说,艾米莉在《呼啸山庄》的成功既归因于集体无意识也归因于她敏感的心灵,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创造性。另外,原始、蛮荒的生活环境在她伟大的创造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别的批评家一再批评艾米莉远离19世纪英国文学主流,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孤军奋战的作家的时候,从本文中我们看出了它与人类文学传统和人类文明的密切关系。这一研究结果得益于原型批评。原型批评摆脱了一般文学的“近视”,在宏观文化背景中,从仪式和原型的“远视”中找到了“解码”的奥秘。
《呼啸山庄》与人类文学最传统的部分——神话的紧密联系是以前的评论家几乎没有看到的,通过原型批评,我们看清了这一点。同许多伟大的文学家一样,艾米莉也是我们人类文学传统伟大的继承人之一,她并没有背弃人类文学的主流,也绝不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甚至带着鬼魅气息的作家。
注释:
[①] Hilda Spr."Themes and Issues",MacmillanMaster Guides WutheringHeights by Emily Bronte.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5,p.37.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7)(18)(!9)(20)Emily Bronte.Wuthering Heights:An Authoritative Text and Essays in Criticism Ed.William M.Sale.Jr.W.W.Norton & Company Inc,USA,p.43,p.46,p.72,p.85,p.135,p.136,p.229,p.262,p.289,p.74,p.141,p.73,p.57.
(12)(13)(14) Plato."The Two Symoposium Myth",The Myth ofplato.Trans.J.A.Stewart.Intro G.R.Levy.London.Centaur Press LTD,1960,p.359,p.360,p.361.
(15) Northrope Frye "the Archetype of Literature",20th CenturyLiterature Criticism.Ed.David Londge.Longman Group Limited,LongmanHouse,UK,1957,p.422.
(16)(22) David Cecil."Emily Bronte and Wuthering Heights".Early Victorian Noverlists.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35,p.148,p.153.
(21) Virginia Woolf.The Common Reader.Harcout Brace and WorldInc,1925,p.158.
(23) C.G.Jung."Archetypes of the Unconscious",The CollectedWorks of C.G.Jung.(vol.9).Ed.Herbert Read.Trans.Hall.R.F.C.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59,p.158.
(24) C.G.Jung."On the Relation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Ed.Thomas Volger.New Jersey:Prentice HallInc,1971,p.817.
(25) J.H.Miller."Wuthering Heights,Repetiton and the Uncanny",Emily Bronte:Wuthering Heights Ed.Thomas Volger.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68,p.174.
(26) Charlotte Bronte."Biographical Notice of Ellis and ActonBell",Wuthering Heights:An Authoritative Text & Eassay in Criticism.Ed.William M.Norton & Company Inc,USA,1963,p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