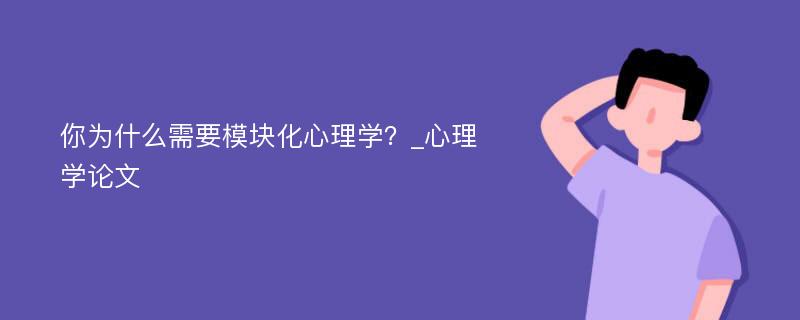
为什么需要模块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模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06-0083-06
模块心理学(Modular Psychology or Psychology of Modularity)是继福多1983年《心理模块性》(Modularity of Mind)出版以后引起心理学研究者关注的理论思潮。福多的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围绕心理模块性的讨论。20多年来,讨论的议题从最开始的“心理是否应该是模块性的?”演化为“心理模块性的意义是什么?”“心理模块的构成标准是什么?”从讨论议题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虽然关于心理模块性的意义尚存在争论,但是关于心理模块性的观念已基本形成共识。于是有学者提出,应该明确“模块心理学”的概念并提出模块心理学的建构纲领,以此促进心理模块性研究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的规范[1]。
“模块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被提出,需要拥有自己独立的基本假设、概念网络以及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具有自己区别于他种学科的论证基础,这是学科研究的基本哲学假设或逻辑前提。那么,在基本预设的层面上,模块心理学和其它心理学流派有什么区别?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曾经盛行过多种理论流派,而当今的模块心理学和其它的理论流派有什么关联,是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的改良还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架构呢?模块心理学是否具备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呢?所有这些疑问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模块心理学?本文将通过对模块心理学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前提的解析,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阐述模块心理学的理论意义。
一、心理模块性的充分性证据
经验研究为“模块性心理性”提供了充分性论证的证据。
首先是来自言语机能研究提供的证据。
Remez,Rubin,Pisoni,Carrell等人1981年在Science发表文章Speech perception without traditional speech cues,他们通过向被试呈现一些人工合成的语音,要求被试进行记录。结果发现,被试的语音知觉不会受到被试关于“信号特性的信念”等因素的影响;被试的“语音知觉并没有采用传统语音学所界定的那些片段性的语音信息”。因此,他们提出可能存在称为“语言知觉模块”的独立机制。[2]
1990年,Mattingley和Liberman进一步根据言语知觉和听知觉的区别,提出“言语知觉涉及一个特异性的模块或认知处理器,其功能独立于其他模块”[3](P.463)。有关言语知觉的研究发现,“处于两个音素之间的言语刺激可以典型地归类为一个音素或另一个音素,从而产生一个区分边界(它比物理刺激本身所保证的更为清楚;参见Miller和Eilmas,1995的文献综述)”[3](P.462),这被称为“类别语音知觉”模块。例如,日语不区分发音[l]和[r],对于日本被试来说,这两个音属于同一个类别,听者也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
反对意见则指出,在Remez等人的研究中,被试的期待会渗透其语音识别,因此关于语言模块的假设是不成立的[3](P.463)。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语音知觉对期望的依赖并不足以否认语言模块的存在。因为Remez等人的研究为模块性假设提供的是充分性证据,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期望渗透也是一种充分证据。也就是说,研究结论显示,存在语音知觉模块的可能,同时也没有排除期望渗透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因为期望渗透可以理解为对某种模块的激活水平的影响。模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体[4],其内部的执行过程不受外在信息渗透的影响,但是模块本身作为一个机制,它的运作同样有赖于其它条件的激发或抑制。
针对类别语音知觉模块,反对意见认为,已有的证据并不一定意味着言语加工的更早阶段也进行类别加工。要获得人早期言语知觉的证据就需要考察新生婴儿对语音刺激的反应。对婴儿行为的研究受技术的限制,难于获得直接的反应,但是诸如“习惯化-去习惯化”技术可以提供间接的支持证据。[5]1986年,Mehler等人用吮吸习惯化技术考察了初生婴儿对语音刺激的反应,发现,出生12小时的婴儿能够区分与语言有关的刺激和其它非语言听觉刺激。[6](P.33)Ramus等人还发现,初生婴儿能够区分丹麦语和日语,但是将两种语音刺激颠倒顺序播放时,婴儿就不能区分了。这说明初生的婴儿已经具备了专门用来识别正常语言的知觉机制。[7]
来自对拼写和阅读有困难患者的考察也提供了存在语言模块的证据。Patterson以及Hanley和Kay曾经报告,有的患者的拼写错误是由于运用音形规则时出了问题;而另一些患者能正确拼写却不能正确阅读。[8]于是Weekes和Coltheart提出大脑中存在两个拼写字典,其中一个负责阅读(视觉输入词典),而另一个负责拼写(词形输出词典)。[9]总之,来自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为模块化心理机制的假设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证据。
其次,来自思维领域的研究也为心理模块化提供了证据。
Cosmides关于条件推理任务的研究为推理这样的复杂思维活动的模块性提供了证据。Cosmides运用“四卡片任务”实验方法,但是将推理描述为包含内容中社会交换信息的形式。结果发现,虽然两种推理任务在逻辑上是等价的,但是在进行纯粹的条件推理时,大多数大学生会犯错误;当进行包含社会信息的推理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犯错误。Cosmides于是推论,人具有一套专门从事社会交换推理的机制,她进一步推论,这种机制是人类祖先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进化而来的一种专门化的本能机制,她称之为“骗子侦察模块”。一旦推理内容与社会交换相关,骗子侦察模块就会被激活,既快又准确地形成推理结论,因此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推理任务中不会犯错误;但是在从事纯粹的形式化推理时,这个推理模块不会被激活,所以人们的推理就会犯错误。[10]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种专门化的社会交换任务推理能力具有跨文化一致性[11]。
此外,专门化的机制还在归纳推理[12]、数量认知[13]、信念推理[14]等任务中被发现。还有学者指出,视错觉也是由于心理加工机制的模块性导致的[15](P.52)。在视错觉现象中,即使当事人被告知真实的情况,视错觉依然存在。这说明导致这种认知偏差的机制不受意识干预,具有自己“强制性”的信息加工特征,而这正是心理模块的构成标准之一。
总而言之,来自实证研究的结论为心理模块性假说提供了充分性证据,依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论,除了已经考察过的内容外,更多的心理机制也有可能是模块性的,心理模块性特征是人的心理机制组织的固有形式。这个推论的确立还需要经过心理模块性的必要性论证,即,我们必须有理由断定心理机制必然、或只能是模块性的。
二、心理模块性的必要性论证
关于心理模块性的必然性论证即是要证明:如果否认心理机制的模块性,并且遵循规范的理论推演,必然会导致有矛盾的结论;因此,我们只能接受、或必然要接受心理模块性假说。本文接下来将采用理论推演的方式论证心理模块的必然性。
如果我们否认心理机制是按照模块形式存在的,就是承认心理是一个均质、统一的整体机制。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均质、统一的心理观是否必然导致有矛盾的结果。
首先,均质统一心理观必然遭遇执行方式的矛盾。如果心理机制是一个均质的统一体,那么它的运行就应该遵循一个统一的法则。与之对应的是,心理机制必须针对不同的情景做出有差异的反应。一个统一的法则如何应对多变的情景呢?是否存在一个完美到可以应对所有情景的法则呢?
早期的逻辑学家相信,逻辑规则就是对人的思维特征的合理描述,于是,按照逻辑规则进行思考一定能解决人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随着心理学对人类思维的了解逐步深入,这样的猜想被放弃了。现有逻辑规则对思维特征的描述很有限,人有大量思维形式是在逻辑之外的。那么是否因为现有的逻辑体系不够完善,不能描述人的全部思维特征呢?第一,从人类认识历程来看,在人的认识范畴内不存在能够描述对象的全部特征的“完善的规则”。第二,如果被描述的对象本身包含了不两立的矛盾特征,那么任何一个法则都不能够描述对象的全部特征。有研究发现,归纳推理任务中,当情景条件不同时,人进行推论所依据的信息有可能是对立的,例如,在“获利”条件下的推理所依据的信息在“避害”条件下则被忽略[16]。
因此,在心理是均质统一体的前提下,心理机制为了能够应对各种情景要求,必须要准备多种应对法则。如果心理机制是统一的,但是其运行法则是多样性的,这就导致一个新的命题:心理机制和机制的运行法则是分离的。这种分离进而引发一个问题:决定人的行为的是心理机制还是反应法则?如果反应法则是决定行为的关键,那么心理机制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心理机制和反应法则的分离还会衍生出一个问题:既然心理机制需要在面临不同情景时选择某种适合的反应法则,那么是谁在做这种决定呢?在心理机制中是否存在一个作这种决定的“小人”呢?这个“小人”又受谁的支配?他的“头脑中”是否又有一个“小小人”呢?这样的追问必然陷入“小人问题”的漩涡[17]。如此看来,从执行方式的角度分析,均质统一体的心智观是行不通的。
其次,从身心关系的角度来看,均质统一心智观也会面临矛盾。如果心理机制是一个均质的统一体,而人的生理机制却是非均质、有差异的结构,关于两者的差异性界定必然产生两个问题:第一,由于将心理和生理界定为两种不同的形态,言外之意就是两者是可分离的两种存在,那么在生理之外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第二,如果心理和生理是分离的两种机制,那么这两种机制是如何在同一个身体内协调运作的呢,它们通过什么媒介实现互动呢?
这两个诘问都可以追述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笛卡尔将心理与生理分离,提出生理等同于机器,其运行遵循物理学原则;心理则是非广延性的存在,需要由专门的心理学来考察。笛卡尔的二元论积极促进了心理学的诞生,至今依然在规划着心理学的学科建构。将心理与生理分离,并将心理界定为某种非广延性的存在,这在心理学与科学研究之间设置了障碍。心理学为了争取科学的地位,采取了各种将心理“还原”为物理运动的做法。例如,通过“心理物理学”在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而将两者统一起来;精神分析理论则将心灵世界类比于物理世界,按照物理世界的格局建构心灵的结构,并用能量转化与守恒法则来约束心灵的活动;行为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否定心理的做法,用行为的物理学特征取代关于心理的描述。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解决身心分离带来的困惑,须知,心理物理学在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本身也是一个心理过程,也就是说这种对应本身只是一种臆想;而精神分析按照物理学的格局平行地建构了一门心理学,并没有说明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正因如此,精神分析遭遇到针对其科学性的质疑;行为主义因为否认心理的存在而建构了符合科学要求的理论,却遭遇到不是心理学的批判。
认知主义力图避免先前理论的困难,用符号运算来描述心理,这就是当代认知科学的计算机隐喻特征[18](P.85)。计算机隐喻面临的诘问是:众所周知,计算机有硬件和软件之分,那么心理应该类比于硬件还是软件呢?如果将心理类比于软件而生理类比于硬件,那么又会产生新的疑问:心理这个软件是如何在生理硬件上运行的呢?须知,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的匹配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实现的,这是否意味着人的心理和身体匹配也需要某种超越人心智的更高级意志的控制呢?这样的追问会将讨论引向科学之外的领域,这显然不是科学心理学希望的目标。
如果说计算机隐喻仅仅是一种功能性隐喻,即,心理如计算机一样执行特定功能以达成目标,这也会引起质疑:在功能执行的意义上心理能等同于计算机吗?塞尔用著名的“中文屋论证”批驳了计算机隐喻。塞尔指出,虽然从功能的实现来看,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对输入做出恰当的输出反应,但是所不同的是,在符号运算或网络联结之外,心理还能够把握“意义”,这是心理与计算机根本的差异。人是根据输入的意义做出意义输出反应,而计算机不能了解输入和输出的意义,它不过是按照编定的程序运行而已[19](P.25)。如果人也像计算机一样按照既定程序做出反应,那么,人心理所依据的这个程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总之,无论是在结构的意义上还是功能的意义上,计算机隐喻都不是对心理的成功描述。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概念[20],旨在摆脱早先认知主义的理论困难,强调认知的“具身性”、“情景性”和“系统动力性”特征[21],即,在身心统一的前提下、在情景特殊性的范围内来考察心理。可以说,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本质就是对早先认知理论的均质统一心理观的否定。
综上所述,以均质统一心理观为出发点必然推导出了矛盾的结论,而以均质统一心理观为基本预设建构的理论也遭遇到不可逾越的理论困难,因此,关于心理的描述必然要采取模块性心理观。
三、为什么需要模块心理学
前文的论证说明,心理的模块性特征既有其充分性也有必要性。但是,即使心理模块性已经得到认可,依然会有疑问:我们为什么需要专门的模块心理学,而不是用现有的心理学理论来描述心理的模块性呢?
第一,心理模块性特征决定了对它的理论描述必须以身心统一论为基本预设。
自从笛卡尔以后,身心统一论就在科学领域内消失了。如前文所述,身心分离的预设使得心理学理论处境尴尬,因此,到了21世纪初第二代认知科学开始倡导“重回人的心智”,因为认知是“具身性的”,具身性就是体验性。“认知是具身的,就是说认知源于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依此观点,认知依赖于主体和各种经验,这些经验出自具有特殊的知觉和运动能力的身体,而这些能力不可分离地相连在一起,共同形成一个记忆、情绪、语言和生命的其它方面在其中编织在一起的机体(matrix)”[21]。需要说明的是,第二代认知科学提出认知具身性犹如精神分析提出潜意识、行为主义提出刺激-反应模式、第一代认知主义提出信息加工模式一样,是对“心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之后全部理论建构的基础。因此,所谓“第二代”认知科学相对第一代认知科学而言,不仅仅是理论的改良,而是在理论建构的前提层面上的更新。第二代认知科学是否会以心理模块性作为其理论建构的依据尚未可知,但是它对认知具身性的强调已经给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心理学到了需要转换传统的身心关系视角的时候了。
第二,对心理模块的理论描述需要对功能与结构的关系做出不同于传统的理解。
心理与身体可以被看做是功能与结构两种形式的存在。身体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因为结构是具有广延性的,具有时空的确定性,所以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心理作为功能性存在,体现为一个过程、一种关系,不具备广延性和时空确定性,因而不能成为传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传统自然科学只研究离散的时空量,而过程、关系等连续性的概念只有在20世纪下半叶,当“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复杂系统论”[22](P.13)等新兴科学出现以后方进入科学家的研究视野。因此,在传统科学理念下建构的科学心理学缺乏对功能或心理重视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作为科学的心理学只能考察结构,而为了言说心理,它只能选择用结构来界定功能。例如,精神分析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的结构来说明其中的能量运行关系;行为主义用刺激-反应联结来取代对心理的考察;认知主义用信息加工机制的结构特征来界定其输出。于是,在身心分离的预设下,用结构来界定功能的策略似乎顺理成章地被确定下来,作为结构的身体是逻辑上的先,而作为功能的心理被定义为逻辑的后。在这种关系下,寻求心理向生理的“还原”就成为自然的研究取向。在关于心理模块性的描述中,这种取向提供了一个极有诱惑力的入口,却最终导致没有出路的困境。例如,福多作为心理模块性思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第一个提出心理模块的构成标准,其中包括“有固定的神经结构”[15](P.93)。可见,福多实际上是在用结构的意义来定义心理模块。福多继承了加尔的垂直官能假说,他正是将垂直官能定义为心理模块,并将心理模块和脑的结构对应。这个选择让福多无法进一步解释各种模块性的结构如何组成完整的心理,他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将分离的亚结构组织起来成为整体,所以不得不承认“中枢系统”是非模块性的。使得福多的模块性思想失去意义[23]。对心理模块的结构性定义导致了福多自相矛盾的命题。
心理模块性的特征需要功能与结构的逻辑顺序被颠倒过来,以功能作为逻辑的先决定了结构的意义。平克曾经对这种关系进行论证。他将心理模块定义为一种功能体,其核心构成标准是功能的特殊性,而非在结构上作专门的限制。这种模块不是像一个个独立的筹码,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其构成更像是机体的组织,比如上皮细胞,可以出现在多种不同的器官中,并且和身体的其它部位有广泛的联络。而一些领域特殊性的思维或情绪也可能作为元素而结合成为各种不同的功能体[24]。也就是说,心理模块的意义在于实现某种特殊的功能,而不一定需要有固定的结构与之对应,只有当实现功能有所要求时,特定的结构才成为必要。因此,是功能作为逻辑先在决定了结构,而不是相反。
强调心理模块的功能意义还有一个理论价值,就是可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心理模块的起源问题。[25]乔姆斯基也是一个心理模块理论的早期倡导者,但是他将心理模块定义为一种结构,这使得他只能用突变来解释心理模块的起源[26];而后来的进化心理学家将心理模块定义为功能体,自然选择就成为心理模块之所以形成的理由。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是机体的功能,而非直接作用于机体结构[27](P.83)。
第三,模块心理学是以“协同学”、“耗散结构论”、“复杂系统论”等新兴科学为理论基础的。
如同福多在心理模块的整合问题上的困难一样,模块心理学也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各个相对独立的心理模块如何能够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心理机制?因为心理模块是功能体,所以模块的组织就是功能的组合。按照心理模块的定义,每一个成为模块的功能都遵循自身独立的运行法则,在运行过程中不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这样的模块如何能够组织成为整体的心理呢?“协同学”、“耗散结构论”、“复杂系统论”等新兴科学为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一个现象: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在不断有能量、物质或信息输入的条件下,会发生自组织效应,原来各个局部的无序运动会在一瞬间跃变为有序运动。这种自组织现象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乃至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不断得到印证[28](P.126)。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的心理机制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遵循同样的规律,在不断有外在输入的条件下,各个独立的局部功能会自组织而形成一个有序整体。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兴科学都是从整体的视角来把握系统的功能,其理论特征契合了模块心理学的建构需求。
四、小结
从现有的证据看来,心理机制的模块性是“应当的”、同时也是“必须的”特征。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之所以忽略这一点,是因为其身心分离的研究立场、以及以结构定义功能的研究策略不能适应描述心理模块性的需求。经过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基于传统研究立场和研究策略,心理学遭遇到的理论困难预示了在基本预设层面上的理论变革。
如此看来,模块心理学并不是将心理模块性思想渗透已有的心理学理论,而是要在身心关系、功能与结构关系等基本预设的层面上对已有理论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这种理论改造已经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经典自然科学领域开始了,诸如“协同学”、“复杂系统论”等新兴科学的出现就是这种理论改造的标志。正是在这些新兴科学的理论支持下,模块心理学方能够建立一种全新理论架构,用以言说心理与环境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