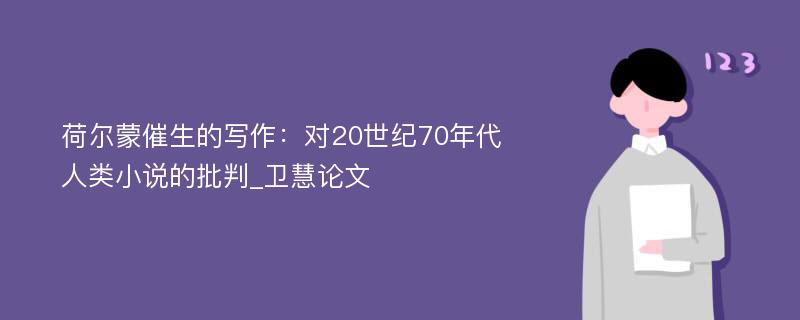
激素催生的写作——“七十年代人”小说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素论文,代人论文,七十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2-0022-04
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在1998年冲出地面并走向前台,成为媒体的新宠,给在沉寂中焦虑如焚的文坛带来一阵躁动,他们以集群性姿态粉墨登场,曲折地表明了他们作为个体的稚嫩与脆弱。媒体对他们的钟爱绝不由衷,而是在追新逐异法则驱遣下的别无选择的选择。在这种意义上,七十年代出生的与作者的亮相是一种假面狂欢,媒体的揠苗长迫使他们沦为一种依附物,文学的独立空间在这种步步为营的蚕食中崩解。以创造为精髓的文学一旦涌入机械复制的轨道,其悠长的韵味被放逐成了风中飞絮,空洞的残骸在殚精竭虑的粉饰中幻化成美妙的陷阱。他们的写作演绎的是一出有声有色的空城计,令人怅惘的是,他们只不过是身不由己的演员,表面上挥洒自如,实际上战战兢兢,被垂帘听政的媒体所操纵。因此,我坚持认为,七十年代人的写作是激素催生的写作,缺乏自然生长的精神间隙,没有原汁原味的文学创造的芳香、色泽和饱满度。
黑夜情景以其光怪陆离的魅惑吸引了七十年代人的笔触。卫慧和棉棉的多数作品以黑夜为主题意象,黑夜不再仅仅是框定故事的特殊时段,其象征意蕴为作品笼罩上暧昧的氛围,奔突于其中的生命在昏昧的光线中敞亮灵魂的黑暗状态:“黑暗是我的家,黑夜是我的温床”(卫慧《黑夜温柔》)。酒吧和迪厅作为一种存在空间,在昏晕的光芒和缭绕的烟雾中蒸腾起颓废的、感官的体味,其间的人群陷入了尼采所言的“酒神状态的迷狂”:“它对人生日常界限和规则的毁坏,其间,包含着一种恍惚的成分,个人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淹没在其中了。这样,一条忘川隔开了日常的现实和酒神的现实。可是,一旦日常的现实重新进入意识,就会令人生厌;一种弃志禁欲的心情便油然而生。……由于他们的行动丝毫改变不了事物的永恒本质,他们就觉得,指望他们来重整分崩离析的世界,乃是可笑的或可耻的”。[1]P28七十年代人正是陷入了这种尴尬,他们痛恨“日常生活就是毫无诗意的繁琐”(卫慧《像卫慧一样疯狂》),当他们的颠狂放纵在冲决庄严的规矩和解开天性中最凶猛的野兽的缰绳时,拯救的梦想愈走愈远。他们在作品中总是按捺不住汹涌的倾诉欲,把叙事者的主动性剥夺得一干二净,急不可耐地自我表白:“我对自己说我要用最无聊的方式操现在操未来。我有我的方式。……有人喜欢把青春和幸福混为一谈,那天我却把青春和失控混为一谈,我觉着我的青春是一场残酷的青春”(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对我们来说青春仅仅意味是一段虚度的光阴,是一个在路边莫名等待的岁月,一个在夜晚幻想加手淫的年代。……我的全部青春就是生活在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中”(丁天《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他们的青春是黑色青春,但他们的文字只不过如温柔而矫情的指头在黑色的皮肤上滑动、抚摩、搔痒。因而,他们无法直刺黑夜的心脏。面对着都市庞然背影的沉重压迫,他们无法容忍自己向荒谬虚无的下坠,于是,他们把写作视为“从生活中抽身而出来的技术”(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面对生命的荒谬,我们唯一的合理姿态就是神采飞扬”(卫慧《神采飞扬》)。这是一种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言的“夜梦”状态:“夜里的梦不属于我们。它不是我们的财富。夜里的梦是劫持者,最令人困惑的劫持者:它劫持我们的存在。夜,夜没有历史。夜与夜之间互不相连”。[2]P182被夜梦所囚禁的七十年代人是失去了梦想的人,因为“作夜梦者是失去自我之影子,……梦想是一种梦景依稀的活动,其中继续存在一线意识的微光。梦想的人在梦想中在场”。[2]P189老尼采阴鸷而敏锐地说:“时间在黑暗中比在光明中是更沉重的负担”![1]P268此话极为贴切地击中了我们的文化语境的要害。
七十年代人的故事常常落入羁囚与奔逃的模式,即津津乐道“在房间”和“在路上”的状态。酒吧、迪厅和卧室在他们笔下成了贬值的符号,其中剩余的象征意蕴被掠夺性地榨干。“我也说不太清楚,房间是一种逼近人生内核的象征,与外部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对立,很多故事是在房间里发生的因此而具备另类气质那是与逻辑和秩序无关的一种状态。……现在我经常去另外的城市旅游,我再也不能长久地呆在房间里我的生活永远在路上了”(卫慧《甜蜜蜜》)。这段话在某种程序上涵纳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的审美旨趣。尽管他们的作品以膨胀的信息企图实现意义的增殖,但这种表层的混乱和复义恰恰是对内在的空洞欲盖弥彰。丁天的《门》、卫慧的《爱人的房间》、金仁顺的《玻璃咖啡馆》、戴来的《要么进来,要么出去》、棉棉的《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等作品在标题中就显豁地点明了要义,而其余作品大多也画地为牢,跳不出窠臼。城市化的空间扩张和信息化的资讯爆炸在改善人们的生存质量的同时,也将导致人类走向社会隔离,堵塞社会交往的精神渠道,以麻醉的方式将人类改塑成封闭性生存的鼹鼠,窃夺人类最宝贵的天赋,强迫人们放弃原来所有的一系列生活方式。但七十年代人的批判神经似乎已经被这种幽闭所窒息,房间成了钝化自我的精神牢笼。于是,他们只好在“进来”与“出去”的二元并置的选择中恶性循环,或此或彼的逻辑使围困感和流浪感在撕扯中不但没有相互抵消,反而相互催酵,精神的自主性就在这种强迫性重复状态中弥散殆尽。第一部“垮掉的一代”派小说《在路上》的作者凯鲁艾克说过一句话:“第一个念头总是最好的念头。”相反,将陈词滥调视为时尚的结果是话语的通货膨胀,思想只剩下僵硬的外壳,成为浮光掠影,这种虚假的浮华使七十年代人的言说成为一种可怕的缄默:“说出来的话语都是谎言”。传统的鲜活的语言丧失了生机,格式化的言说方式使作者自以为在思维和创造,实际上却只不过是在模仿那些熟视无睹的成规。
在作品中搜索父亲形象的强弱似乎已经成了当前批评家的一种例行公事,不少批评家为七十年代人作品中怯弱或遁逸的父亲感到振奋,但这种莫名惊诧只不过是削足适履的后遗症。卫慧的《艾夏》中的主人公在父性缺席的环境中成长,她的父亲“从她一下地就逃之夭夭了”,只有邮局送来的神出鬼没的汇款单维系着脆弱的父女之情,“艾夏从心底最深处憎恨着那个叫艾仲国的男人。关于她生活中的所有不幸和错乱,该让他来承担。”《像卫慧一样疯狂》则出现了一个“女里女气”的继父,“他那双呆滞的、闪着磷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主人公毫不掩饰对他的鄙夷不屑:“这个成为我新任父亲的男人,他永远也成不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父亲。”《黑夜温柔》中温亮和舒昕的父亲都被妻子遗弃,显得黯淡无光。棉棉《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中的父亲冷漠自私,“我失去了一个孩子对父亲所有的信任”。周洁茹《熄灯做伴》中的父亲“烦恼、怯弱、担心、怨恨”。丁天《葬》中的父亲迷信、专断,常常向亲人喷射“没来由的愤怒”。但是,七十年代人对父亲的逃离和反抗中,同时隐蔽着寻找父亲和顺从父亲的情节线索,构成二重组合的矛盾结构。艾夏对父亲“充满了恨意和莫名其妙的期盼”,并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能够拯救一个自小就等待父亲的女孩”,“于是有人推测,少女艾夏只身流浪四方,去寻找她父亲或寻找她父亲留下的线索了”。周洁茹的《淹城故事》中有这样的反诘:“怎么能够怨恨自己的父亲呢?”丁天的《一种疾病》中的主人公想以退学挑战“一向惧怕”的父亲的权威,但父亲深谙世味的劝解使他无奈地膺服,在“死捱”中度日如年,首尾呼应的逃离与顺从构成了寻找父亲的循环结构。在棉棉的《九个目标的欲望》和《啦啦啦》中,父亲在女儿陷入绝境时总是适时出现,以自责和宽慰抚平女儿心头的创痛。七十年代人对父性的暧昧姿态意味深长,与其说他们是在反抗,毋宁说他们是心怀怨恨,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怨恨是依赖的反面:当一个人给出了一切,他总觉得收到的回报还不足够”[3]。面对炎凉的世态和竞争日益残酷的生存状态,深重的被弃感和孤独感催萌对温馨的庇护的无限神往。他们对父性的怯弱的嘲讽,回旋着对可供依傍的铁肩的呼唤:“我天生敏感,但不智慧;我天生反叛,但坚强。……我们的人生是虚弱的”(棉棉《啦啦啦》)。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与苦难荒诞的黑色年岁擦肩而过,崇高神话的崩塌使他们轻信地阻断了超拔的精神维度,物欲漩流的席卷使他们与现世生活一拍即合。周洁茹在《飞》中喃喃自语:“我父母爸妈就生了我一个孩子,我们生下来就是太阳,热热闹闹。”这种洋洋自得在《熄灯做伴》中却又一扫而光:“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像姐妹那样亲密无间地去爱别人,每个人都不相干,我们彼此都是皮肉隔离的个体,我们互相漠视,在必要的时候才互相需要和互相仇视,但是那样的接触也是异常短暂的。”无处栖居的空落将安全感粉碎成尘,精神越荒芜,无可名状的欲望膨胀就越剧烈。他们饥不择食地向躯体的空壳灌注替代物,但结果却是使精神和肉体同时沦入被奴役状态。他们企图用酗酒、吸毒、性宣泄来点燃疯狂的激情,但这种对身体的自虐式鞭打事实上渍灭了真正的激情,与之接踵而至的是沉重的挫败感,自己成了自己的奴隶,这种向束缚宣战的盲目的激烈恰恰是一种新型的桎梏。棉棉在《我是个坏男人或生日快乐》中有这样的表达:“我必须做这种不去爱上却有稳定男朋友的练习。”爱欲的萎缩使灵魂成为一种布满暗缝的容器,不管如何填充,它都处于始终的倾空状态。《饲养在城市的我们》的叙述者的喟叹沉积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哀痛:“自由了,自由到了明天以后任何一天我都没有具体的安排和打算。……昨天已过去,无法改变。明天不可预知。今天没事可做”。这样的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表面上它将个体从群体的重轭中解救出来,事实上它以一种精神塑料封闭了个体,使之处于无可反抗的束缚状态,泯灭为多余的数字。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整个个体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不能为个人实现提供基础,而人同时又失去了那些给他以安全的联系,那么,这一脱节现象就会使自由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那时,自由就会变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4]。七十年代人的姿态与“垮掉的一代”不无形似,但后者的反抗掀开了美国当时社会百般掩抑的腐烂的脏腑,而前者的申述仅仅作为中国当下社会的脚注而存在。他们机械地说“不”,内心却又无限痴迷现世的享受甚至堕落,他们缺乏一种“走向未知”的勇气,价值标向在撒娇和赌气的沼泽中湮灭。“或许我对于生活对于爱情时时有一种既挑剔又妥协的矛盾立场,对于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人物感到厌烦透顶,却又时不时有着关于追求美和真的痴心妄想,这两种极端混在一起就组成一种叫眩晕的东西”(卫慧《神采飞扬》)。在眩晕中一切痛苦、困惑和矛盾都成为编织精神摇床的丝缕,亦此亦彼的恍惚逃避了选择,带来一种随风飘荡的解脱感。米兰·昆德拉说:“晕眩,就是沉醉在自己的软弱中。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但又不想反抗它,而是任其下去。人因自己的软弱而沉迷,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所有人面前瘫倒在大街上,希望脚踏在地上,在比地还要低的地方”[5]。深具反讽色彩的是,七十年代人逃避命运的行为反而有助于实现命运的安排。
七十年代人的作品备受指责的是其经验的匮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结撰模式又过分地依赖有限的经验,表现出“非虚构化”的自然主义倾向。沿着新写实作家和晚生代作家驾轻就熟的辙印,对世俗生活与生俱来的亲和使七十年代人表现出对想象力的先天的隔膜,无法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他的双脚在地上行走,他的脑袋在腾云驾雾。”没有想象力作为点化剂,有限的经验在叙述中要么呈现为壅塞的板结状态,要么被稀释成寡淡的疏离状态。由于情绪的失控,这股漫漶的水流并不能有机地溶解那些杂凑的经验,水乳交融的状态就只能是一种空想。经验叙事和情绪文本之间出现了一条相当明晰的相互隔离的裂缝,其间的空洞使作品的“意味”无处容身。在某种意义上,情绪的烟笼雾罩是对经验匮乏和想象贫困的掩饰。棉棉在《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中迷茫地质询:“我写不好作品是因为我总是控制不了我的激动可我为什么总是那么激动呢?”但其失败不在于无法成功地调用克制性叙述,这种自责还折射出中国作家根深蒂固的成见,即注重再现本体世界而忽略表现象征世界,亦即坚信生活的博大精深与主观世界的渺小肤浅,畸重生活而畸轻想象。小说中的情绪流露并没有违犯规则,也无需刻意追求表现对象的毕肖,想象与经验绝非势不两立,关键是主客体必须相互契合,能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而《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借祖咒的口说出的“艺术就是东捅捅西蹭蹭添点乱才好重要的是创作者本身得时刻保持兴高采烈的状态”,这句话或许可以视为作者的一种自我慰藉和自我开脱。
叙事的奇迹化是七十年代人的文体策略,这种故作惊人的姿态既表露出对自身体验的疑虑,处心积虑地将它改塑得面目全非,也是对大众趣味的曲意逢迎。但声色犬马的经验堆积、狂放不羁的语言喷射和顾影自怜的暴露叙述很快就唤醒接受主体的厌倦和逆反心理。为了追加刺激强度,七十年代人只好沿着猎奇的轨道愈走愈远。他们的故事常常脱胎于市井传言与晚报新闻,叙述套路隐隐闪现出侦探小说和通俗小说的印痕。迄今为止,丁天和金仁顺是七十年代人中感觉最为敏锐并最具有穿透力的写作者,他们对于成长的荒诞和生存的困境保持着一种感性的警惕和冷峻的审察。遗憾的是,丁天的《幼儿园》、《数学课》、《死因不明》、《一种疾病》、《你想穿红马甲吗?》等极具批判意味的作品大多是“听别人讲或看来的故事”,对社会资讯的过分依赖在叙述中掺杂进一种小心翼翼的隔膜。《阳关三叠》的三复的穿插性叙述结构尽管不无新意,但寄生于武侠传奇的外壳中的故事并没冲出传统的陷阱。金仁顺的《五月六日》、《好日子》、《玻璃咖啡馆》、《鲜花盛开》和《冷气流》较好地控制了情绪的节奏,在平静的语流中缓缓绽放青春的明媚亮丽,同时层层剥笋地显现阻遏成长的黑色内核,把环境的诡谲和人性的幽暗不动声色地彰显出来,但她过分地偏爱陡转的效果,结尾的出人意料在带来震惊的同时也驱散了逐渐凝集的叙述张力。
也许是深切地感受到第一人称叙事的自叙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了保持与叙事对象的必要距离,七十年代人除了调用第三人称叙事外,还经常让叙事者与作者进行性别反串,如丁天的《蕾》中的“我”是女性,卫慧的《硬汉不跳舞》、《甜蜜蜜》和《黑夜温柔》的叙事者与主人公则是男性,金仁顺的《四封来信和一篇来稿》还采用了书信体,而周洁茹的《肉香》则在作品后面附上“一个陈旧故事的备注”作为补叙。但繁复叙事技巧的运用并不能遮掩资源枯竭的苍白和焦虑。七十年代人在崭露头角时便浮显出自我重复的迹象,丁天的《流》以《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的一个人物刘军为主角,细节与情节的重复无可避免。赵波的《萍水相逢》和《异地之恋》叙写的都是一对邂逅的陌生男女之间发生的勾引与抗拒的故事。棉棉的《啦啦啦》、《黑烟袅袅》和《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讲述的都是“我”和“赛宁”的大同小异的故事,而且后者和《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的最末一节一字不差。她在《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中真诚地袒露自己的痛苦:“我把我仅有的那点故事都变成小说了,其实我向来反对女作家写真人真事,但是写作确实没有赐予我虚构生活的权利。我费尽心思在我的故事里寻找感觉,毁灭性地找,企图化腐朽为神奇。”写作在这个年代成为在各种压力的夹缝中艰难绵续的挣扎,但七十年代人的首要障碍和超越目标只能是他们自己。
七十年代人中不少为没有体制保障的自由撰搞人,这种承受着巨大压力把自己变成“一个坐在家里靠写字吃饭的人”(戴来《要么进来,要么出去》)的胆识,蕴蓄着一种抗拒平庸的精神诉求,中国文学的未来或许正由这些自由的灵魂浇铸而成。但文学史绝对不以年龄和姿态作为价值座标,因为两者都是暂时的、可疑的甚至是荒唐的刻度,只有作品质量才能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的兴衰浮沉。七十年代人只有冲破诱惑和压力的围堵,才能为新世纪的文学敞亮一种崭新的期待和惊喜。
[收稿日期]2001-0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