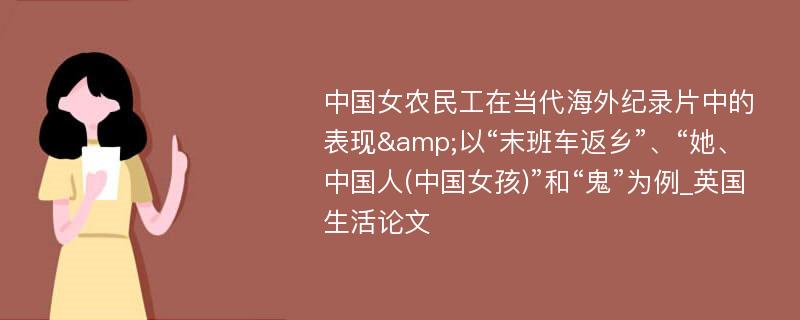
中国女性农民工在海外当代纪录电影中的呈现与表达——以“LAST TRAIN HOME(归途列车)”、“SHE,A CHINESE(中国姑娘)”、“GHOSTS(鬼佬)”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归途论文,为例论文,农民工论文,列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灰姑娘”的想象与“父权”的抗争
(一)“灰姑娘”式的农民工想象
“LAST TRAIN HOME(归途列车)”中的张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农民工夫妇张昌华和陈素琴的第二代外出打工妹;“SHE,A CHINESE(中国姑娘)”中的李梅是一个重庆农村姑娘,厌倦了单调的乡村生活,成为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中国非法滞留英国的打工妹;“GHOSTS(鬼佬)”中的艾琴是一个年轻的从福建农村偷渡到英国的非法劳工妹。张琴、李梅、艾琴她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来自偏远的农村,贫穷、落后,其父母思想保守甚至愚昧而无知。她们成长在中国农村低微而贫贱的农民工家庭中。这些来自当代中国底层世界的青年女性,或为贫困生活所累,或为外在世界所诱惑,女性的苦难与底层女性生活的艰难困苦密切相连,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年女性的个人经验与“灰姑娘”式农民工的想象。“灰姑娘”带有浓厚的女性主义的特点:倔强独立、自尊自爱、敢爱敢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灰姑娘”式农民工的想象“把注意力集中在亲身经历上,这种亲身经历常常是以自白的方式表达的”。①
(二)“家”中“父权”与“他者”的抗争
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由平等和睦两性关系的母系制社会到父权成为道德伦理唯一立法者与主宰力量的父权社会,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②。在家中,“中国女子,有三从之义,故终身其身无自主之一日。云最亲之男子,则其初之从父,其后之从子”③。由此,有人说,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丧失了主导话语权,造成了年青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自我压抑和扭曲。张琴、李梅、艾琴在家中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很难与家人进行言语的交流沟通,更多的是沉默和沉思。如果说,父权主宰下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奴役女性的话,那么在“家”中女性一旦丧失“自我主体”的身份认同,就成为传统社会中的父权制与父权思想的“他者”。因为在人们普遍的意识里,“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④。所以说,一旦女性被物化成男性眼中的“他者”,就再也“不是作为尘世间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的抽象概念——不是作为赞美之物,而是作为分析之物——不是作为爱的对象,而是作为那种虽说杂乱无章但却是最为深奥的沉思之主题”。⑤
事实上,三部电影中女主角的父亲在家中的角色似乎并非如我们所期待,他们在家庭成员发生冲突之时要么缄默,要么缺场,要么袖手旁观。如影片中李梅的父亲“吵啥子嘛,女儿大了”、艾琴的父亲在家中几乎没有说过话。影片中塑造的这些父亲的形象,要么是乡村务农的农民,如艾琴的父亲;要么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如张琴的父亲;要么是城乡间的废品收集者,如李梅的父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教育程度低,不善言辞。当然,女主角很难在家庭生活中找到父爱的痕迹,父亲在她们心目中很难成为慈爱的象征,更多的似乎是内心深处与父亲日益增长的疏离感。故而,有人认为,压抑性因素的存在成为了女性生存自由的障碍,同时也成为其反抗父权的导火线和突破口,这些因素可能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女性自身对规范的主动屈从。由此,家庭生活中时常会出现有所抗争、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女性,其所扮演的是反抗或颠覆父权权威的理想女性角色,她们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拥抱女性他者的身份,以自欺的态度来审视自己,而是试图从失语的状态中开始解脱出来。她们与之对抗并试图颠覆的是父权思想和权力,以此来摆脱“他者”处境,恢复真正自主的自我身份,如性格鲜明独特的张琴对父亲张昌华充满了反叛与叛逆“老子”的粗口,李梅与艾琴的离家进城打工并没有与父亲进行任何的言语交流和意见征询,而是以她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父权权威进行坚决抵抗,她们已不再是逆来顺受、默默忍受屈辱的弱者,不再是缺乏自我意识的懦弱女性,也不再是父权制度束缚下的牺牲品,而是敢于挑战父权意志、对抗父权话语的当代青年女性。
对传统意义上父权话语与意志进行颠覆,表明父权权威不再是“家庭”的中心,“权威的统治者是睡在床榻上的母亲。这是一个无父的国界”⑥。将父权作为孱弱的角色从家庭话语权中心放逐到边缘位置,父权不再占有家长权威地位。女性家长甚至取代父权权威,如李梅的妈妈要求李梅相亲而遭到拒绝时,扇李梅耳光道“你必须去见”。此时,母女之间诚挚的天然亲情,不再是抵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女儿心中的母亲已不再是“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⑦。又如,陈素琴对女儿张琴教训道“不管怎么样不能说老子”。其实,母亲陈素琴的“插嘴是权利和支配的表现。插嘴的人获得了交谈的控制权,而这正是一种人际间的权力”⑧。又如,艾琴出国前与回国机场迎接等重要时刻出现的都是艾琴母亲的身影。这些母亲扮演的都是家中强悍女性家长角色。
不过,与其说这些强悍的女性家长角色填补了父权话语与意志缺席产生的空缺,代替了传统社会中父权意志承担的功能,倒不如说这些女性家长在父权桎梏中含辛茹苦地过着家庭女仆的生活,她们从小就在礼教规范的熏陶中成长,很容易把这种奴隶教条视为天经地义。比如李梅的妈妈对丈夫大声叫嚷道“你还是管一下”。她代替了自己的丈夫,成为“家”中的领导者,直接决定着女儿的婚姻和命运。陈素琴对女儿张琴训斥道“你怎么这样对你爸爸说话”。此时,“母亲已经成为父权论述的代言人,她的任务,就是要把‘女性’这个符号(以及所附加的负面特质)教导给她的女儿。在无意识的心理中,每一个女性主义者都变成了一个‘女儿’,要反抗父权的压制,同时要排斥母亲。虽然女儿总是渴望着父母亲,但是,女儿对母亲有双重的不满:一来不满于她无法提供独立于父权体系以外的身份认同;二来则怨恨她无法保护女儿免遭父权的伤害,却又不断地训练女儿进入正统社会制度”⑨。
二、挣脱“夫权”走出家庭自我主体性的寻求
(一)挣脱“夫权”,婚姻与性爱的分离
灰姑娘在一夜之间光彩照人获得王子爱恋,最终飞上枝头变成金凤凰,嫁入豪门追求人生的幸福与完满。对此,有人说,“夫权”是“展示女性命运的映衬之物”。因为“现代的独立家庭是建立在对妻子进行公开或者隐蔽的奴役之上的……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阶级,妻子则代表着无产阶级”。⑩故而,可能的情况是,“女人一生的使命是用眼泪和痛苦为代价,用极度的努力来矫正自己的身体和行为,从而取悦于男人”。(11)“两性的对应等级,即两性等级制度,首先在家庭生活引起了她的注意”(12)。当女性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时,势必会依赖于他人,这自然就会依赖于自己的丈夫——一个男人。传统家庭的女性或以父亲,或以丈夫,或以子女为主体、以自身为客体,缺乏自我的主体性,她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男性带来生理快乐以及为他们传宗接代,她们的价值似乎只有在对男性对象的付出和牺牲的时候才会呈现。女人之所以“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雌性’这个词出于男人之口时,有种侮辱性的含义……‘雌性’这个词之所以是贬义的,并不是因为它突出了女人的动物性,而是因为它把她束缚在她的性别中”。(13)
值得玩味的是,三部电影中的灰姑娘们,绝没有想把自己的后半生绑定在一个男人身上,丈夫和婚姻不再是她们未来幸福的唯一,她们的未来更多是属于她们自己。或许出于这样的原因,“作品里不再写恋爱了,但凡主角,都是独身,即使有幸成婚了,就让一个(远)去……总而言之,取消了家庭生活,夫妻感情,作品中的中国人都成了……没有什么个人生活情趣的圣僧高尼”。(14)如陈素琴最后决定离开广州的丈夫张昌华回家照顾上学的儿子;李梅选择离开了年老无力的英国丈夫退休教师亨特;艾琴因丈夫跟另一个女人好上了,她带着两岁的儿子自己过活。丈夫要给儿子生活费,她说她不要。既然已经不在一起了,那就不要他的钱。看得出,影片中的女性已不再是作为男性生理上的泄欲工具,不再是一味满足男性的生理欲望与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对待无情感的婚姻,虽未采取激烈的反抗行为,但也并未就此主动丧失自我而甘当丈夫的附属品。
其实,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与探索,有时婚姻并非是源自爱情,甚至对女性而言,“我从没提过恋情,也绝没想到过爱”。(15)或许,女性眼中的男性只不过是“他们是要抢着钓我的渔夫”。(16)对待性爱,影片中的女性忽而主动热烈自由张扬忽而又含蓄收敛克制的个性,完全是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来把握性爱的主动权。如李梅对强哥提出性爱要求的拒绝,对待“大钉”、拉希德的主动热烈;艾琴对包工头林老板的断然拒绝,对打工仔小李的收敛与含蓄;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张琴一味地在克制,并没有描述带有生物本能的情欲。如果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那么也可以说,女人的爱情也未必是女人整个生命的存在。在爱情中,女性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没有一味地表现出依恋和顺从而成为其附庸和奴隶。她们抗争过,她们企求得到真正的爱,她们是在以自己感性的方式酣畅淋漓地生活。“SHE,A CHINESE(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将女性的一切现实注入了银屏:爱情、性欲、强奸、怀孕、妓女等与女性有关的各个元素都呈现出来,将这些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所有可能都变为故事情节,一切看来都是自然而然,并没有让观众觉得厌恶、下流或是变态。在故事的开篇,李梅是个对爱情充满向往的青春少女,对在外打工闯荡大城市的青年强哥存有羡慕与幻想。面对文化局照相馆小高的提亲,李梅开始是坚决反对的。在经历了被卡车司机强奸事件之后,与黑社会打手“大钉”“在那张挂历下,李梅感觉到爱情”却是异常的短暂。即便是因经济压迫而沦落红尘,李梅也没有将情爱连同性欲作为商品搭售,而是坚守自己的人格和自尊。当“大钉”拿出三百元现金时,李梅的反应是发自内心的气愤,着实与“大钉”打斗了一番。然而,迫于英国生活的种种窘况,李梅嫁给了英国退休教师亨特,因为无法从英国丈夫亨特身上获得渴望的情爱,又把得到爱情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个餐馆送外卖的印度穆斯林拉希德身上,并与拉希德偷情。李梅又把这个印度男人拉希德视为能将自己从寂寞和绝望的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希望。然而这个印度男人依然令李梅失望,最终,李梅抛弃了拉希德。她并没有将自己的生存价值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渴望攀附某一个男人从而获得安逸的生活与美好的情爱,并没有迷失自己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
(二)“大女人”之梦,自我主体性的寻求
正如恩格斯所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7)对当代中国青年女性而言,与其接受“家”中必须“从夫”这条不幸婚姻枷锁的束缚,还“不如到黑暗的社会里做一盏明灯”(18)。因为“要求进步的思想和春光一样,绝不是铁门所关得住”(19)的。更何况,女性意识顿悟的构建过程,从来都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无论是李梅,张琴,还是艾琴,作为一名女性,她们都是勇敢的当代中国青年女性的代表。她们善良、正义、独立、勇敢、顽强,努力完成着自己的使命,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她们已经不是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妇女了。或许她们未必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她们知道,“在这样变化纷纭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幸福和生命之道,是掌握在你(女性)手中,而不是在(男权)你的父亲、丈夫、家庭手中”(20)。或许只有怀着“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21)的理想,才能冲出家庭的束缚,摆脱作为男权的附属品,勇敢地自我拯救,才有机会获得独立的主体人格,同男性一样走出家庭,加入到农民工浩浩荡荡的打工行列,踏上社会公共生活领地,走入国家的历史洪流中,在社会各个领域里施展自己的才华,以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此时,她们把追求和男性平等职业竞争作为自我主体性寻求,作为以人的自觉来审视自身存在、证明自己生存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尺。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妇女生活的社会使她们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是在传统观念的决裂中证实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二是在男女角色的冲突中证明自己作为女人的意义。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面,她们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消耗。”(22)即便是受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规范,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这种规范必定会受到女性自身行为的冲击,尽管存在着自身条件、抗争力度、反抗姿态等方面的差异,但一旦女性意识觉醒后,必然会开始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确证,关注自我本体性的建构。当张琴与父亲张昌华厮打时,面对摄像机大声地吼道:“你们不是要记录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也许这不再是危言耸听,“女性的文本必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像火山般暴烈,一旦写成它就引起旧性质外壳的大动荡,那外壳就是男性投资的载体,别无他路可走,假如她不是一个她,就没有她的位置,假如她是她的话,那就是为了粉碎一切,为了击碎惯例的框架,为了炸毁法律,为了用笑声打碎那‘真理’。”(23)
当女性开始追求独立、张扬自我,从默默忍受的状况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其不屈不挠坚韧执拗的性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特有的感性、人性色彩的智慧力量等,无不见证着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优长之处。“其实每一个女性都面对着很多困扰,我也同样有。你要问到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选择女强人,也不会选择小女人,我要做的是大女人。大女人的意思是,不需要用权力来感知自我的价值,也不需要依附别人来获得快乐。”(24)无论是艾琴那句“像我这样的年纪,不能再这样过下去。我要想办法出去,多挣一点钱。”还是李梅与张琴,她们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是肯定的,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独立自主地自己作出判断,显然她们被刻画成了当代中国新女性的形象,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角色都颠覆了男权社会所定义的所谓理想女性,从而刻画出了具有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观的形象。
三、都市中迷茫的张望
(一)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漂泊
随着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加快,背井离乡打工成为中国社会现实。“GHOSTS(鬼佬)”讲述了艾琴从福建乡村偷渡到英国打工的故事;“SHE,A CHINESE(中国姑娘)”讲述了重庆姑娘李梅从乡村走向超级城市漂泊打工的故事;“LAST TRAIN HOME(归途列车)”是对张琴退学离开四川乡村到广州服装厂、深圳夜总会打工的讲述。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都市,不再是一个以传统家庭道德伦理来规约人们行为的地方,而是一个放纵个性、迷失本性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为了追求一己之私欲而任意践踏各种伦理准则,似乎只有拥有权力和财富,才算是城市的主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行动者对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为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25)当然人们还注意到,城市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从事的往往是短期性的工作,不可避免地经常性失业。由于没有任何失业补助,农民工一旦失业,日常生活就会出现危机,而只能依靠亲友、老乡借钱度日。可以说,正是这种残酷的生存状态中所带有的情绪和个性而让女性更加关注现实的层面。如李梅与英国丈夫亨特的结合,不过是打工所需的信用卡与教堂婚姻的捆绑;艾琴那句“我这样的年纪,不能再这样过下去。我要想办法出去,多挣一点钱”;期待赚更多钱的张琴离开了广州服装厂,只身到深圳夜总会去做女招待。事实上,城市除了贫富悬殊、道德沦丧之外,更多的是打工者自我主体身份的失落。如面对英国肉厂同事每周240英镑的工资,而自己每周才100英镑,艾琴很难理解英国同事那句“You are from China.Different”;李梅在学校做解剖学人体模特领取酬劳时更难理解伦敦人反复强调的“Bank Card”的意义。对此,她们无奈地旁观,陷入女性自我主体身份失落后内心的那份无限迷茫。她们在失落中寻找、在寻找中失落,又在失落中困惑迷茫。当困惑无法缓释释放时就成了精神危机的表现,种种危机不断呈现,过去的一切不断支离破碎。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身份问题的提出总是在与异质文化的交往中浮现出意识层面的:一种是共时横向文化交往中产生的异质感,另一种是在异质文化影响下经历史转型所产生的文化缺失感及危机感。一般说来,认同欲望的产生总是与某种缺失或丧失感相联系的”。(26)如果说,在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浪潮中,城乡二元体制和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模式,日益扩大了各阶层之间的鸿沟,导致城乡文化的隔阂,那么,“对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之所以比较普遍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城乡分离的劳动就业市场等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加之绝大多数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网’之外,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27)
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没有城镇户口就意味着不能平等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权益,不堪工作压力重负的城市边缘群体,为求得基本温饱的生存状态而在经济困境中疲于奔命。这如同19世纪西方文学传统中女性的形象,妇女既是都市现代性的寓言,也是它的转喻(metonymies)。她们体现了城市的诱惑、不稳定、匿名及晦暗不明,这些特征时常是通过将女性的面孔、身体与都市的灯火交错并置。(28)身份卑微、经济贫瘠、社会歧视,为生计所迫而挣扎于社会最底层、在生存重压之下奋力拼搏,以期过上短暂“安稳”生活的愿望,还是一次次被社会现实无情地打碎了。如,张琴在广州服装厂打工刚刚适应却遭遇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李梅在重庆成衣厂刚刚立足就遭到了厂方的开除,在“爱的发廊”做坐台小姐刚刚稳定,又遇到身为黑社会杀手的男友大钉;艾琴刚刚适应了肉厂的工作,住处就遭到警察的查封而被房东赶走,搬到海边挖蚶刚刚安定,又遇到了英国流氓的骚扰。对影片中的青年女性而言,“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29)失去“安稳”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在精神梦幻与文化交汇口的一次次徘徊,城乡二元对立的两套价值体系导致了城乡夹缝中生存的残酷性,使得她们既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回报,也无精神的慰藉和文化身份的认同,而成为文明道路上的精神漂泊者,接着而来的是对漫无目的漂泊的焦虑和恐惧。
(二)“梦里家园”孤立无援的人生困境
现实社会将“女人定义为由男性创造、从他们身上产生、为他们服务的人。她们是男性大脑、肋骨和聪明才智的产物”。(30)与此同时,“工作场所、法律、经济、知识以及文化等具有权力和权威性的层面被视为男性当然的领域;而家庭、炉灶边和孩子等私人范畴被认为是最适于妇女的领域。”(31)作为众多女性的代表,她们在命运、个性和时代所造成的困境中奔突,在孤苦无依的城市中颠沛流离地找寻满足生存之需的谋生新路。如艾琴偷渡到英国后,在肉厂做过非法劳工,在农场打过短工拔葱,到海边挖蚶;李梅在重庆成衣厂做过缝纫工,在“爱的发廊”做过坐台小姐,当她逃离旅行团滞留伦敦期间在学校当过解剖学人体模特,在中国餐馆门前扮成大熊猫招揽顾客,在按摩诊所打过工;张琴退学后在广州服装厂做过缝纫工,到深圳的夜总会做过女招待。逆境和困顿中的生活,反映出了她们的个人命运与时代、与社会大环境的冲突,她们为了获取一份安稳的生活而苦苦挣扎,与男性周旋,与同性相争,她们自己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处处碰壁、遍体鳞伤而备受生活的压力和摧残,即便这样,“她们忍受着这一切的不幸,仍然挣扎的生活着,却始终摆脱不了社会最底层的命运”。表面看来,“在观众同情的好人身上,尤其是在无依无靠饱尝痛苦的女主角身上,情节性加浓、戏剧性加强,要观众对女主角同情程度深、共鸣程度高,那女主角就需要吃尽苦头”。(32)细辨之下却不然,因为,“要被人看成女人,就必须具备大家所公认的女性气质”。(33)实际上,“包裹着女性身体的服装,其实无处不体现着男性的文化思路”(34)。基于这样的思路,就“意味着她们要无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为她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体面的服从”。(35)理所当然的是,她们常常被降格为男人的客体而存在,常常扮演着男权社会为她们规定的或期待的角色,而她们自身的主体性权益被否定、被遮蔽。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自身的自我压抑,使女性成了无私、无我的纯粹客体,成了“为符号服务,以忠诚、耐心和绝对沉默表达自己的符号”(36),或许“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女性正是在这种包裹中‘失踪了’——失去了自我”。
现实社会并不是大女人梦想的“梦里家园”。生活中充满了磨难和不幸,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黑暗,绝不会放过这些正当妙龄的女性。女性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恶劣的社会环境一点点地剥掉这些青年女性身上的美德,将她们的性格扭曲变形。面对残酷的生存状态,即便是受到侮辱和损害,也要戴着假面具强颜欢笑,处处压抑自己,掩饰自己的悲哀和软弱。如艾琴常常在厕所里大哭,哭完了还得振作精神继续去打工。有时候她打越洋电话回家,无非就那几句,“妈,我在这挺好的”、“我钱寄回去了,收到没有?”“钱还得差不多了吧?”“妈,让宝宝听电话”,电话中儿子哭闹叫嚷着分明没理会,艾琴还是自顾自对着电话跟儿子对话“宝宝你要乖啊,妈妈很爱你的”、“你为什么又跟同学打架了呢?你想不想妈妈啊?妈妈给你唱歌听:世上只有妈妈好……”可以说,女性的悲剧“是‘病态社会’中‘病态的人’的悲剧,因此,其悲剧根源也主要在于‘病态社会’和‘病态的人’两个方面”。(37)毋庸讳言的是,男权社会国民的劣根性及对女性能量潜能的探索,更多的是对底层和下半身的思考。(38)特别是在充满了性和暴力男性权力符号的社会环境。如,“SHE,A CHINESE(中国姑娘)”中“爱的发廊”、黑社会杀手大钉;“GHOSTS(鬼佬)”中包工头林老板的性暗示,肉厂上班住处与挖蚶海滩上英国流氓的野蛮暴力;“LAST TRAIN HOME(归途列车)”中夜总会的放纵狂欢,回乡村老家过年时张昌华、张琴父女的对打。这何尝不是对当代青年女性底层贫苦生活的无助和绝望,何尝不是对她们孤立无援的人生处境、坎坷与波折的个人命运的困惑和无奈呢?
(三)孤独的“忧郁”基调
在个人奋斗过程中,女性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和苦闷,当“为了要个人独立地生活,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身心交瘁为止后”(39),女性“一生的名誉和爱情,几乎都是为职业所牺牲”(40);当女性处于被摧残和压迫的边缘而日益焦虑变得歇斯底里时,无论是执著于对女性的悲观主义论调,还是牵强于影片效果统一论而执蓍于女性的虚无主义观点,其实都强调了女性的陪衬地位和附属意义。“男性常说女性只关心自己的小世界而不关心宏大的历史社会,但是,我们又凭什么断言人的内心世界就比外在世界小呢?”(41)当黑夜里内心的苦痛变得无限孤寂时,似乎唯有堕落才是唯一的出路,还有什么比精神心灵的彻底绝望更孤独、更痛苦的呢?李梅在重庆成衣厂做缝纫工被开除后,孤立无援的她只得到“爱的发廊”做坐台小姐;张琴在广州服装厂遭遇金融危机后,只身闯荡深圳的夜总会。如果说,“美是诗的唯一正统的领域……那么,忧郁是所有诗的情调中最正宗的”,(42)那么,影片流露出了一个女性心灵上的痛苦与孤独、悲愤与不平,表现出了女性对被尊重和被爱抚的那种独有心态的渴求,“这种渴求受到不自然压抑的苦涩;或深沉地体现了女性在社会生存情境中别有艰辛的心理体验等等,一种用女性特殊感受和评价标准来发现自己在现实生存情境中的处境与地位的自觉的女性意识”(43)。也就是说,从效果论来看,为了实现其特殊的美学目标,影片中的女性角色没有任何实体存在的意义,她们只是为了表现其作品所谓的“忧郁”基调,以达到叙述者情感跳跃,从而成为引起观众心灵震撼的工具和手段罢了。
四、“男性他者”精神家园的无奈回归
(一)无法走出男权藩篱的“男性他者”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作为“男性他者”被建构,男权观念依然占据着社会统治地位,女性在观念、权益和生活方式上均处于他者地位,处于男权中心的统治之下,双方的关系也是建立在绝对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在某种程度上,男权的强势无法仅仅通过解构的方式来完成,也无法将女性从“男性他者”无处不在的目光中剥离,更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的视角理性看待女性的行为。了解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一旦女性的自身主体性权益被否定,她们为何会心甘情愿地去扮演男权社会为她们规定的角色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立场,更是一种策略。可以说,出于维护男性中心文化之需,将女性置于他者地位,是影片必然要面对的语境。如,“SHE,A CHINESE(中国姑娘)”中工厂会场布置的庄严、厂长宣读开除李梅决定时,如同作报告般的做作和强势;“LAST TRAIN HOME(归途列车)”中父亲张昌华因言语之怒殴打女儿张琴时,母亲与外婆在一旁围观和言语上的指责,无疑成了父权与夫权的帮凶;“GHOSTS(鬼佬)”中英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寻衅滋事的男流氓。
事实上,“一旦男人声称自己是主体和自由的存在,他者的概念——特别是妇女作为他者的概念就产生了”。(44)这里的他者,“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全体余数,而这个我则从这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45)。由此,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女性只是被排除在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她们建构的不是自我主体,而是男性主体;她们认同的不是自我价值,而是认同了男权社会赋予她们的“他者”地位和角色身份。人们无形中形成一种审美的思维定势,就连女性自己,也在按着男性社会的标准规范矫正自己的言行。甚至许多获得经济独立人格、实现了自己社会价值的女性,仍然在乎男性目光的审视和来自男性社会的评判。
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权意识形态中的观念和价值实质上已经溶解到女性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即使男性的主体性被消解甚至被完全剥离,男权意识仍旧存在于所有女性的深层意识之中,替代男性掌握着话语权的女性不过是男性行使权力的工具罢了,女性依旧是男权文化和体制压迫下的奴隶。此时,男权意识形态不再直接压迫女性,而是通过女性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来抑制和扭曲。换言之,对于社会强加于女性的这种规范的认同才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当女性将社会约定俗成的戒律转化为自身意愿时,女性便成了自己命运悲剧的制造者。
事实上,此时处于控制地位的是主观的非我(The Subjective Other),只是由于投射作用才显得好像是某个他人在进行的操控或牵制。(46)换个更简便的说法,“当女人们想要体验激情时,社会提供给她们的就是浪漫。当女人试图想象与人交往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美好前景就是男性和性交。当女人们幻想着成功和权威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方法就是去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当女人们幻想着性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表现只是去直接的挑逗和满足男人,而把大多数的表现都视为禁忌。当女人们打算独身时,社会几乎就不会提供关于这方面的诱人前景。女人的真正完美总是表现为社会的、家庭的和性感的。”(47)诚然,“在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与文明之中都充满了女性的表象和关于女性的话语,但女性的真身与话语却成为一个永远的‘在场缺席者’。”而这又何尝不是“被千百年来以男性文化为核心的内容所浸泡、修剪、润色”。(48)的呢?
(二)从“社会女人”重返“家园女人”,“家”与精神家园的无奈回归
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面前,女性往往是软弱、无力的,无法与强大的男权世界相抗衡,这些女性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男权势力的压抑和歧视,当怀揣“大女人”梦想的强者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因难以适应当下社会现实而走向绝望的境地时,对那些性格懦弱、依赖性强、独立能力较差者而言,又该如何面对、怎样生存呢?在社会现实无情挤压和打击下,那些怀有“大女人”梦想的社会女性的理想追求、美好人性和虚荣人生,几经挣扎、几经较量,但终究被逼上绝境而遭到毁灭。李梅刚刚找到真爱享受幸福时,男友“大钉”却被杀身亡了;张琴与同伴在海滩上挖蚶遭受英国流氓的群殴后,深夜挖蚶的那些同伴却又在海水涨潮中全部遇难了。男权社会不再是物质和生活中的伊甸园,男权意识形态赋予的规定性角色使女性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自我价值、自我身份的追问。因为自我对女性而言,“‘首先’是在与他人无涉的情形下存在着,然后它也还能‘共’他人同在”。(49)真实的情况是,每当她们抗争得越强硬、挣扎得越激烈,遭受的打击就越惨烈、所陷落的不幸就越深刻。女性在呈现个体鲜明性格特征的同时,更强调了女性对性别等级现状的清醒认知,对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理性审视。这或可以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50)正如赞美诗中所唱:“唉,你诚然是时代的牺牲者,但是你不要忘了悲哀有更大的意义呵。”(51)
“家”,成为女性的归宿、生活的现实和世俗的命运,成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而无法得以解脱的真实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性的历史就是一部陷入家庭的历史,女性成长的每一步都与“家”息息相关。可能的情况是,女性在生理和客观经济条件制约下更容易被拘泥于家庭的环境之下。故而,女性角色和女性气质总是围绕着家庭这个主题来规定,并根据家庭职能的关系来命名和诠释女性。现实的情况是,“家”带给女性的感觉常常是破损压抑的。如,李梅的妈妈始终在家忙于家务活,当女儿倔强地拒绝上门提亲时,母亲的粗暴犀利逼人,没有话语权的父亲只是静坐在地上。李梅与英国丈夫亨特的不幸婚姻,与印度人拉希德婚外偷情而独自承担酿下的苦果;张琴在乡村老家与外婆、弟弟相依为命,又在家中与父亲张昌华发生了暴力冲突;“GHOSTS(鬼佬)”开篇从艾琴偷渡到英国,对家的依恋,到最后回家与亲人的团聚。总的说来,她们的反应并非始终是沉默失语的,在经历了作为男性附庸的痛楚之后,她们内心潜藏的“家园女人”真正的自我终于走到前台,实现了“家园女人”主体意识的复苏。对于来自男权中心的压迫,她们采取的是与之抗争的方式和态度,虽然并没有获得一方能使她们自由独立的新天地,但毕竟她们具有了女性自我意识和反抗男权的社会意识,表现出了女性的对立与反抗精神。影片在叙述女性反抗时那种对面临困境的清醒认识和对自由独立追求的执著,给人带来一种心灵上的强烈震撼,但略为遗憾的是,她们最终并没有走出一条可行的女性抗争之路。虽然反抗的结果并不理想,值得欣慰的是,她们都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现了对女性生存和发展的自觉意识。
“家”,又构成精神家园的隐喻,是女性获得理想归宿的寓言形态,女性形象的塑造就是在不断地憧憬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实现的。在对“家”的抵抗和憧憬中,反思并审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的历史因袭和现实困境,虽然那些无法得到安抚的灵魂,仍将继续回归到“家”中,以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事实上,当把“家”从伦理意义的“家庭”上升到具有彼岸价值和人文理想的“家园”时,以当代中国青年女性为题材的纪录片电影,寻求的就是一曲精神家园的旋律。换而言之,就是以一个没有家园的流浪者,从“父权制”的“娘家”与“夫权制”的“婆家”勇敢走出来,寻找自我的精神家园的过程。只有通过追寻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改变作为男权他者的身份和地位,获得真正的主体性,以真正实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注释:
①[英]沃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③严复:《法意按语》,王木式编:《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55页。
④[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⑤曹明伦:《怪异故事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38-39页。
⑥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
⑦冰心:《繁星·一五九》,转引自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⑧[美]詹尼特·希伯雷·海德:《人类一半的体验》,威斯康辛: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3页。
⑨陈儒修:《女儿的仪式:爱恨交加的母女关系》,转引自游惠贞编:《女性与影像:女性电影的多角度阅读》,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237-246页。
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页。
(11)[美]苏珊·布朗米勒:《女性特质》,徐飚、朱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75页。
(1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4)丁玲:《丁玲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15)曹明伦:《怪异故事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16)庐隐:《或人的悲哀》,转引自钱虹编:《庐隐选集》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
(1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1页。
(18)郑培为、刘桂清:《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94-95页。
(19)欧阳予倩:《电影半路出家记》,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第42页。
(20)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21)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转引自钱虹编:《庐隐选集》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22)远婴:《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转引自胡克、张卫、胡智锋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23)[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24)王路:《杨澜要当“大女人”一不做女强人二不做小女人》,《潇湘晨报》2007年1月31日。
(25)[法]布迪厄、[美]华德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孟、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26)张宁:《文化认同的多面性》,转引自周宪主编:《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7)陆益龙:《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28)Mary Ann Doane,“ Film and the Masquerade,Theorizing the Female Spectator,” Sceen,vol.23,no.3-4(September-October,1982),pp.74-88.
(29)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转引自刘勇选编:《流言》,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30)S.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12.
(31)谭兢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237页。
(32)程步高:《影坛忆旧》,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3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4)张爱玲:《流言》,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3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674页。
(36)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37)朱勇:《对〈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命运的深度探析》,《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32页。
(38)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216页。
(3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40)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41)郭小橹:《电影理论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42)[美]爱伦·坡:《创作的哲学》,转引自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43)任仲伦:《新时期电影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
(4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4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7-138页。
(46)[美]艾森卓:《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杨广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47)[加]安·芭·斯尼陶:《大众市场的罗曼斯:女人的色情文学是不同的》,转引自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66页。
(48)罗婷:《伍尔夫在中国文坛的接受与影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92页。
(49)[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9页。
(50)[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51)庐隐:《时代的牺牲者》,转引自钱虹编:《庐隐选集》(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