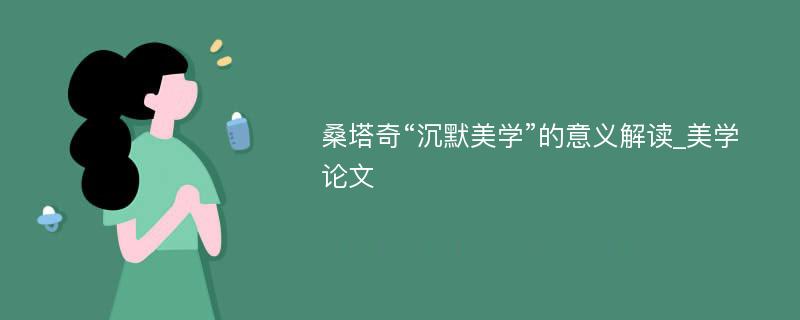
桑塔格“沉默美学”的意义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沉默论文,意义论文,桑塔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4-0070-06
艺术如何表现自身的问题一直是西方文论的主要争论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一直到18、19世纪重形式的唯美主义,都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摇摆不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相继推出了心理时间说和精神分析学,对文学的表现形式产生了革命性的震动,当时风靡欧洲一时的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流派都与上述两种学说有紧密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弗氏的潜意识学说是为了深挖文本的潜在意义,但超现实主义作家却只接受了他的潜意识理论,认为世间一切都是荒诞不可知和无意义的,唯有用“自动写作”的手法表现主体内心感受和意识流才是艺术的真实。这一派思潮犹如一匹奔腾不羁的野马,冲破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的认识论模式,也充当了后来法国“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流派的先导。
从形式主义美学的层面来看,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则受“新批评”的影响较大,这一流派几乎统霸了美国批评界,融入大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之中。与同一时期欧陆文学流派相比,新批评强调的是文本结构的独立性,摈除一切文本之外的干扰,理性地分析和建构文学的“文学性”,试图区别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文本的质差。这种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追求“陌生化”原则一样,其割裂社会历史与文本联系的作法必然导致狭隘的死胡同,在寻求普适存在的“文学性”原理的同时与历史的演变形成悖论,无怪乎后期新批评庶几成了融各种观点为一体的大杂烩,如芝加哥派的代表人物韦恩·布斯(Wayne Booth)便信奉多元论,坚持形式主义的实用批评的同时,也允许“外在的批评形式”,将意图和作者联系起来,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帮助读者去认识和理解小说[1](pp.597~598)。20世纪60年代,苏珊·桑塔格率先将瓦尔特·本雅明、罗兰·巴特等文艺理论家及萨罗特、阿尔托等作家的先锋派思想和著作介绍到美国文坛[2](p.689),然而她最突出的特点是承袭了法国“新小说”派注重形式美的一脉,于1964年发表《反对阐述》一文,对精神分析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期新批评从庸俗社会学角度解读文本意义的手法发起猛烈抨击。显然,她所继承的是卡津提出的美国两大文学批评传统中的一支,即爱伦·坡和亨利·詹姆斯所代表的注重风格和技巧的传统。她鼓吹文学的“性感”(erotics),认为性感的形式才能提高读者的感性(sensibility)体验能力。她的反对阐释理论轰动一时,从形式本体论的角度为60年代左右兴起的美国后现代文学铺垫了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的文学表现出种种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苦闷荒诞、孤独迷惘、信仰恶化。文本内容成为碎片,在风格和技巧上则随心所欲,不信任任何现成的艺术形式、体裁、原则和一切权力结构,把小说完全当成一种纯粹个人独特内心感受和表现另类风格的游戏场所。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沉默美学”,它在后现代性的语境下对文本意义进行了颠覆和消解。然而从积极方面看,它或许又是从艺术本体的层面上对意义进行重构的一种尝试。
一、沉默美学的内容意义
1967年,桑塔格发表了《沉默美学》一文①,进一步“阐释”她的形式美学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她认为艺术的目标最终将受到限制;艺术本身是制造神秘的形式,但将忍受一系列打破神秘化的危机。古老的艺术目标会遭到攻击,被取代,因为人们陈旧的意识在改变,从中显示出桑塔格与俄国形式主义仍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后者在谈到文学类别的嬗变时,就将其归咎于形式神秘感或陌生感的消失,这种仅从语言结构层面构建文学性的做法是把社会演变因素彻底排斥在外的。桑塔格把艺术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来表达人们的意识,第二阶段则与人们心灵和“自我疏离”(self- estrangement)的能力联系起来。“艺术不再被理解为作为表达的意识,因此可以隐含地伸张自身。艺术不是意识本身,而是它的抗体,从意识的本身演变而来”[3](p.4)。这时艺术家所追求的目标无论从情感和道德角度都已失去了意义,能让他满足的不再是通过艺术找到一个声音,而是沉默。作为终止意义的沉默指向终极情绪,沉默是艺术家形而上世界的最后姿态,使他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因为当代艺术对神秘和创新的不懈追求,必然要导致交流中断的沉默。艺术家追求完美的标准越高,对自己艺术表现的质问就越无穷尽,在这种状况下,诚如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勒内·夏尔(Rene Char)所言:“栖在问题灌木丛中的鸟儿是没有心情歌唱的。”[3](p.7)
我们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沉默”的含义,其实艺术家依旧在言说,只是以一种观众听不到的方式进行着。当代艺术的沉默表现为“无意义”,或看不到听不见,对观者构成直接的冒犯。其让观者颇感沮丧和不悦的品质构成了理想沉默的一部分。沉默不等于不再生产作品,“因为作品与观众的隔阂不能永久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新更难作品的干预,艺术家的超越变成了媚俗和合法化”[3](p.7)。德国剧作家、诗人克莱斯特(Heinrich Wihelm von Klaist)为“隐型戏剧”(invisible theater)创作的戏剧就曾遭到歌德的指责,然而最终其丑陋、不和谐和无意义的形式变却得“美丽”起来,由前卫而嬗变为平庸。所以桑塔格认为艺术的历史就是不断成功的超越。[3](p.8)艺术家不可能把观众完全废除,艺术是一种精英行动,必然要预设广大观众的存在,只是艺术中的沉默有时走得过远,或以自虐的形态出现,如荷尔德林和阿尔托就是以牺牲理性为代价来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意识疆界的。总体来讲,沉默美学关注的是艺术制作,是关于现代时期艺术作品自身内部的局限性。当代的艺术具有一种反艺术的冲动,即对艺术概念的反叛。艺术家“企图让艺术去做我们的文化在传统上艺术从没有承担过的任务——如超越或消灭自身,乃至担负起宗教或精神的功能”[4](p.7)。
在桑塔格看来,艺术家既然不可能从真实意义上保持沉默,那么其沉默的“话语”就是追求与以往不同的行为。沉默、空白和简约的理念都是为了让观者能以更直接的感性体验去看视和倾听艺术真谛。法国超现实主义主将之一布勒东称这种艺术为“彻底边缘化”(full margin),即艺术家只填补艺术空间的边缘,中心留下空白;它也被称作“贫穷绘画”、“贫血艺术”,其宗旨均是凸现艺术形式美而提高欣赏主体的体验。桑塔格认为艺术技巧或是艺术史其实就是引起别人注意的历史,即为我们的环境“命名”的过程,通过“对有限的事物的筛选而让人们留意到有意义的、带来愉悦的和复杂的审美客体”[3](p.13)。正如王尔德曾说过的,居住在英国伦敦的人们一直看不到大雾,直到19世纪一些诗人和艺术家教他们如何去欣赏;同样,电影艺术发明之前,人们面部的多样性和微妙表情是很少被注意到的。艺术愈是被“沉默”过滤,表现得愈简练,注意力就愈能超越诸多庞杂选择的痛苦,深化审美质量,否则审美体验将易于扭曲。无独有偶,中国老子哲学追求天人合一和艺术形式本体论的美学思想与桑塔格的沉默美学颇有相似之处。美的最高境界其实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隐隐于市”,这种审美过程中的“沉默”和“无言”是对宇宙万物生命体验的诉求,是摆脱了俗世一切羁绊的高层次超脱。
语言是艺术的媒体,它一方面具有抽象的特质,但同时又是最不纯洁和因反复使用而被“污染”的,它负载着历史的重负。尼采说:“我们生活在比较的时代,可以对过去从未被证实过的东西加以证实。”所以艺术家陷入两难之地:要么使用自己的语言,要么使用已被驯服的负载历史积累的语言。这意味着他若不是以取悦和屈服的姿态,奉献给读者他们已知的东西,就是对读者大不敬,给他们不知道的,“而为了弥补不光彩的成为历史奴仆的状况,艺术家便以一种反历史,因而是异化的艺术来升华自己的梦想”[3](p.15)。“沉默”的艺术于是就构成这种愿景式的反历史状况的一种手法。
桑塔格的沉默美学以牺牲艺术内容为代价而诉求于艺术形式的本体,这种将内容和形式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违背的。她主张人在欣赏艺术时就像观赏风景,不必深究其意义,并期望艺术家以精英式的“沉默”先锋艺术形式俯瞰并影响普罗众生。她的观点在上世纪60年代针对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们的麻木状态起到了警醒和启迪作用,然而其完全摈弃内容的超验和虚无思想在艺术阐释和审美中却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抽空了“意义”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二、沉默美学在作品中的呈现
在《沉默美学》一文中,桑塔格提出当代艺术已变成了“精神事业”(spiritual project)的比喻,而“每一个时代都要为自己重新创造‘精神’事业”[3](p.3)。她指出作为美学冲动的艺术是超越痛苦的存在以及冲突的主要途径。但艺术是人类的产品,是物质实体,“而正是这一认识驱使一些艺术家走向沉默,从而他们能从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中解脱出来”[5](p.86)。其悖论是,她发现他们不情愿“交流”,但恰好通过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定义空间之后而构成了与艺术本体交流的方式。
沉默可采取多种形式:自杀(如德国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克莱斯特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死作为艺术的替身,或完成了“反艺术”)、对世间的拒斥、疯癫以及受到检查制度的惩罚等。桑塔格认为沉默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能起到将艺术作品置于中央位置及达到更加感性的效果。
文章论述了沉默是如何呈现自身的;一个沉默的人是非透明的,拒绝阐释,或拒绝引诱他人去阐释沉默。瑞典戏剧和电影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执导的影片《人格》(Persona)便是“沉默美学”的绝好样板。它的焦点围绕着演员伊丽莎白和护士阿尔玛的关系展开,前者在整个影片中几乎缄默不言,后者则因伊丽莎白的沉默而几近发疯,想方设法要让她开口说话。沉默状态不仅存在于女演员身上,也构成整个影片的生成方式,致使观众因意义的不在场而感到失落。[6](pp.133~134)桑塔格认为倘若影片表现出任何主题的话,那就是“意识淹没了瓦解人格的恐怖”[6](p.142)。这一瓦解在言说和沉默之间的争夺中展开,作为言说的语言代表暴力,即对他者的暴力侵犯,然而在关系以及叙述中占支配地位的却是沉默。护士的镇定终于瓦解,随之而来的就是语言和自我身份的坍塌,用桑塔格的话来说,便是“女演员用她的沉默创造了一个虚无,护士通过言说掉了进去——瓦解了自身”[6](p.144)。
女演员和护士的关系就是艺术作品和阐释的关系。对封闭性阐释不可能奏效的强调显然就是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一文中所关注的问题,即“女演员或艺术作品拒绝意义的指涉”[7](p.51)。伯格曼所要表达的不可阐释的沉默正是桑塔格所说的“非透明性”,是如何“引诱精神迷惘(spiritual vertigo)”[3](p.17)的思想。艺术作品像一幅提供了各种象征性符号的大屏幕,意义和欲望展现其上,然而却发现它们缺乏支撑,无从阐释。桑塔格认为沉默并非仅仅表现了艺术的无以言表性,而是投射出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陌生化(defamiliarisation),它暗示阐释的崩溃可以通过颠覆幻觉上的自我安全感而表现出潜意识的恐怖和兴奋的形式。我们在这类艺术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是“理性依赖于非理性、自我依赖于非我(nonself)以及语言依赖于沉默的必要”[7](p.51)。
桑塔格自己编导的影片《卡尔兄弟》(Brother Carl)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人格》的模仿[5](p.17),虽说该影片和她编导的另一部《食人二重唱》(Duet for Cannivals)触及到了多种解读的主题,如“疯狂(真正的和想象的)、统治、利用、心理残酷”[8](p.26),甚至还有女权主义,但其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则是对“沉默美学”的注脚。影片采用现代手法,故事中角色使用的语言呈现出反常规倾向,能指链条不断地翻滚不仅消解了所指的出场,也消解了意义的指向性,制造出多重解读的空间。《卡尔兄弟》中的主角受到过他导师的伤害,从此便沉默寡言,人们既不知道他受伤害的原因,也无从知晓他当下的内心世界感受,整个影片就是在这种摆脱了语言的“历史意识”的情景下展开和演绎的,直到终结。
桑塔格显然希望通过这部影片(其实也包括《食人二重唱》及她的长篇小说《恩人》和《死亡套件》),来实践她的“反语言”及“彻底经验”(total experience)的理论。
桑塔格认为语言是艺术创作中充当中介表达的具有特权的隐喻。一方面,言说与形象相比是非物质化媒体,也是超越个别事物的人类活动,因为“所有言辞都是抽象体,只是粗略地依靠或指涉具体的事物”[3](p.14)。另一方面,在所有用来完成艺术作品的材料中,语言又是最不纯净,污染最多,消耗最厉害的。这一语言的双重性构成了当今令人不愉悦的艺术状况。过去欧洲思想的光辉成就却使今日的艺术陷入泥沼;两百年以来,意识已从自身的解放、带给人类福音的启蒙变成了一个令人不能承受的自我意识的包袱。“一个艺术家写一个词(或创造一个形象,或做一个姿态),如果不让他联想到曾经已被别人创作过,几乎已成为不可能”[3](p.14)。为此,桑塔格在《沉默美学》一文中引用尼采的话说:“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享受,以不同的方式受难:我们本能的活动就是与在数量上从未听说过的事物进行比较。”[3](p.15)其实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个存在,然而在今天使用语言的艺术方面,这却成了一个令人倍感疲惫的大问题,因为我们“经验着的语言是被腐化的,被历史的积累压得透不过气来”[3](p.15)。面对这种局面,艺术家必须应对两种意义及其意义关系的潜在的敌视对手:第一种是他自己的意义(或无意义),第二种是一系列二级意义,它们将“滞碍、伤害及污染他的语言”[3](p.15)。因此,艺术家便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取悦于观众,给他们已知的东西,要么冒犯他们,给他们未知的。当代艺术就是在传达着由这种“历史意识”造成的异化,而反历史和非异化的艺术便是“沉默”。
按照桑塔格的解释,沉默隐喻将艺术作品看作风景,风景无须观者对其有任何理解,对其赋予任何意义、忧虑或同情心;相反,它要求的是观者的不在场,无须他为风景添加任何东西,即观赏主体的消失。我们从《人格》和《卡尔兄弟》中便可感受到这种消解主体的策略:“茫然、简约、个性解构和反逻辑,原则上说,观者甚至无法将自己的思想介入。”[3](p.16)美国实验派作曲家凯奇在论述沉默美学时一语中的:“一旦一个人开始倾听,他不可能思想。”[3](p.16)他的反音乐便建构在环绕音响(ambient sounds)的理念之上,表演时什么也不做,让观者体察大宇宙的冥冥之音,用他的话说,“根本没有沉默这么一说。世间永远发生着什么在制造出音响”[5](p.196)。他甚至描绘说,即便他呆在一个无声的大厅里照样能听到两样东西:他的心跳和他脑袋里血液流淌的声音。杜尚的美术“现成品”也同样是对任何即定的艺术标准的反动,它们没有话语,没有主题甚至于没有形式。而英国诗人济慈也从积极的方面看视沉默的非透明性,把希腊瓮的“沉默”看成精神养料的焦点:“未听过”的旋律才能永恒,而灌入“感性耳朵”的音乐将会腐烂。在济慈那里,沉默是与捕捉永恒(“悠慢的时间”)等同起来的。他在诗中又接着说:“沉默的形体呵,你象是‘永恒’/使人超越思想……”[9](p.229)由于时间和历史是特定、有形思想的媒介,永恒的沉默便为思想的超越铺设了道路,达到“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境界。
桑塔格在《沉默美学》和她的诸多作品中倡导的是“彻底关注”的原则,即给予的越少(非语言),对事物的关注质量就会越高,越少有污染,越能使主体全神贯注。“欣赏贫乏艺术(impoverished art),得到沉默的净化,我们就能开始超越选择注意力的烦恼,这种选择必然导致经验的扭曲。理想的是,一个人应能够对所有事情都给予关注”[3](p.13)。她在这里进一步延伸了反对阐释的观点,因为被全面经验添满的空间便意味着不让任何思想(阐释)进入。一个沉默的人对他者就是非透明的;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为阐释他的沉默开辟了无穷的可能性,也为把话语赋予他的沉默开辟了无穷的可能性,这才是艺术作品的真谛所在。《人格》中女演员的沉默不仅可以理解为她的拒斥道德、追求纯真的姿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权利的手段,一种施虐狂、摆布和抗衡护士伙伴的一种不可违抗的力量,而后者却背负着讲话的包袱,不能自拔,这象征着沉默对语言及语言所承载的历史及道德意识的胜利,象征着艺术本体自身的张扬。桑塔格认为沉默的魅力在于希望到达智性和文化的清白(clean slate),“所预见的是……艺术家从自身中的解放,艺术从具体作品中的解放,艺术从历史中的解放,精神从物质中的解放,以及思想从其认知和智性局限中的解放”[3](p.18)。
桑塔格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象论理论作为她沉默美学的哲学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语言与世界在逻辑上同构和逻辑结构不可能用语言描述,而只能自身显示出来的两个命题。桑塔格所关注的是其第二个命题,即语言与世界共同的逻辑结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原因在于,它被限定自身不能被描述,而只能自身显示。维特根斯坦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0](p.235)他要求对不能用语言谈论的事情保持沉默(但断定该“事情”的存在),因而对有意义(可说的)和无意义(不可说的)的句子作了区分。[11](p.399)在此基础上,桑塔格则认为语言除了可以达到“启蒙、解惑、混淆、歌颂、影响、敌视、满足、震动和活跃”等促成行动的功能外,“有些话语,无论是口头或书写,自身就是行动的表现……但话语也能沉默……没有沉默的一极,整个语言体系将坍塌”[3](p.19)。批评除了判断某个艺术家是怎样,或不是怎样之外,还可采用沉默的手法使思想关闭,而这种沉默式的关闭是使一切“敞开”的途径。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桑塔格的美学思想与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后工业及消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她指出技术的复制、资讯的迅速传递和无所不入,印刷语言及影象的蔓延(新闻和艺术品),政治、广告和娱乐领域中公共语言质量的下降,都使生存在当今大众文化社会的人所操作的语言贬值。[3](pp.20~21)桑塔格为了救治大众的麻木神经,使艺术达到本雅明所提出的“惊颤效果”,从而承担起对工业化无视人性的批判,便借助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领域的存在,试图将艺术形式推到本体的高度,让人们获得审美感受以摆脱非人化。然而如前所论,她在消解一切意义的同时,不免暴露出了十分明显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在遇到用语言逻辑和理性思维无法了解的神秘艺术现象时,常常求助于非理性的体验、直觉乃至不可言说的“沉默”。
收稿日期:2010-01-22
注释:
① 收入《激进的意志风格》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