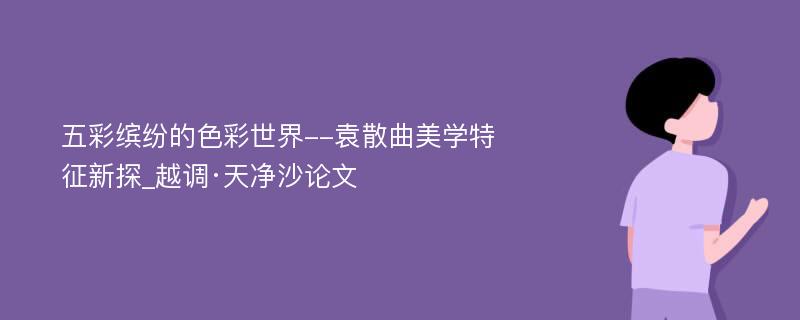
绚丽多姿的色彩世界——元散曲审美特征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曲论文,绚丽多姿论文,特征论文,色彩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曲,和唐诗、宋词同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作为元曲重要组成部分的散曲,堪称古代诗歌艺苑中的奇葩,其瑰丽夺目的艺术光辉,无不有赖于色彩的点染,无一不是绚丽多姿的色彩世界的艺术创构。
色彩进入艺术的殿堂,当与绘画艺术的诞生同步。史前人类在创造图腾艺术时,就已经懂得使用颜料了。最为生动的考古证据,便是图腾圣物“丘林加”上的赭色颜料,它们极其生动地标志着原始人以生命化的自然色彩,赋予图腾物以自然美的形态。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着色,是绘画艺术的主要手段,也是文学艺术的必要手段。元散曲的艺术魅力之一,正在于散曲家们以精湛的艺术画笔,铺陈色彩,借色传情,赋予色彩以生命,以情感化了的色彩,揭示了人事景物的情姿神采,将色彩融于意境创造,寄寓内心情绪和审美意趣。因此,元散曲中丰富的色彩世界,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审美的新领域。发掘、探索色彩世界的审美特征,无疑是研究元散曲艺术价值的重要视角。
情浓采丽:元散曲的审美特征
文学作品中的色彩世界,是大千世界绚丽多姿的色彩世界的艺术反映。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对色彩的描绘,在《诗经》《楚辞》中已很发达。《文心雕龙·情采》曰:“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彩是也……”当时五色的概念,指青黄赤白黑。刘勰对色彩的理想是“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也就是崇尚古代礼服上的黑白相间或青黑相间的图案式的、简单典雅的色彩,要是再加上大红或紫色,他认为太艳丽,便评之为“淫巧”。因此,魏晋以前,文学作品中的色彩描绘都较单纯。到了唐代,色彩的点染出现鲜明的倾向,唐诗中色彩浓艳的作品不少。如杜甫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王维:“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中》)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宋代诗词,受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启发,很重视色彩的点染,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一枝红杏出墙来”、“绿肥红瘦”等,都是通过色彩的凝滞,来达到状形达意的效果。元代的画风直接受到南宋画院浓笔重彩的影响,并不时地渗透到诗歌领域,从而形成元代诗歌色彩运用的特色。可见,注意色彩的运用,选择有色彩的字眼入诗,使诗歌增强鲜明的色彩感,使之有声有色,已成为古典诗歌的传统。
元代散曲作家尤其注重色彩的运用,情浓采丽,是元散曲的主要审美特征。无论是本色派还是文采派的作品,无论是汉族诗人还是蒙古、色目诗人的吟咏,亦无论是自然景色还是人物肖象的描绘,都以其色彩的鲜明、浓丽,色调的明朗、和谐,使人耳目一新。
本色派和文采派,是元散曲的两大艺术风格。所谓本色派,大致从金末(约1234年)至大德以前(1307年)的数十年,散曲刚从民间的“俗谣俚曲”进入诗坛,又受到外来民族音乐和艺术的影响,所以在风格上富于民间文学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饱含着北方民歌中直率爽朗的精神和质朴自然的情致,粗犷,有“蛤蜊”风味。代表诗人有元好问、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贯云石等。所谓文采派,大约指大德以后至元亡(1368年),创作中心从大都转到临安,作品风格趋向雅正典丽,文采华美,词藻绮丽,代表者有马致远、乔吉、张可久、徐再思等。其实,这只是大体划分。通观全元散曲,常常不同风格并存,即便是同一作家,他们也不拘一格,尽态极妍,蔚为奇采。本色派的作品,清新、自然、质朴,但并非不重文采,其色彩的运用同样五光十色、浓艳明丽。如元好问,这位十三世纪的文坛领袖和文学大家,其散曲《骤雨打新荷》,被誉为元散曲的开路先锋,也可以说奠定了元散曲浓艳色彩的基调:
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琼珠乱撒,打遍新荷。
作者用浓笔着色,铺写池塘水阁的一片绿阴,然后,在万绿丛中,点几朵鲜红如罗的石榴花,令人顿觉其景照眼欲明。色彩的搭配恰到好处,如果是半红半绿,往往给人以平庸俗气的感觉;万绿丛中几点红,则显得艳而不俗,色调清新,给人以美感的愉悦。以本色当行著称的曲家关汉卿,他的不少散曲,亦是情浓采丽,声色并茂。如《双调·碧玉箫》中的秋景:“秋景堪题,红叶满山溪;松径偏宜,黄菊绕东篱。”开篇一连四句,展现出秋山景色的壮丽:火红的枫叶、金黄的菊花、苍劲的青松、清澈的山溪,色彩鲜艳明丽,超尘拔俗。
白朴的散曲,多写男女情爱、自然风光和隐逸生活,意境和谐,色彩清丽。如《越调·天净沙》写春、夏、秋、冬的四支小令,构成了一组四季风景图。在他的笔下,春天是“啼莺舞燕”,“流水飞红”;夏天是“纱厨藤簟”“罗扇轻缣”;秋天是“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冬天是“雪里水滨”“淡烟衰草孤村”。四季的景物、色彩均不同,尤以秋景色彩最为鲜明。作者给山、水、草、叶、花分别涂上青、绿、白、红、黄的颜色,把各种色彩巧妙地调合在一起,将一片秋色点缀得如此灿烂、绮丽。如果单看“青山绿水”,夏天似乎还没有去远;单看“白草红叶黄花”则完全是深秋之景色,色调未免衰飒。白、红、黄之色间杂、映衬,背景是青绿色,显得分外艳丽、生机勃勃。
文采派的散曲家对色彩运用的重视更不待言,他们的散曲犹如一幅幅彩色的画卷,洗人眼目,令人愉悦。马致远被誉为元代散曲中的第一大家,其散曲风格飘逸脱俗,以富有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著称。他的《越调·天净沙·秋思》和《双调·夜行船·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前者在色调上极善映衬,如“夕阳西下”和“枯藤老树昏鸦”,一面是落日余辉的明亮,一面是深秋晚景的暗淡;一面是落日给枯藤老树昏鸦抹上一层淡金,一面是枯藤老树昏鸦又减弱了落日的余辉。作者把明暗这一对矛盾的色调,统一于深秋晚景的画图之中,一明一暗,相反相成,既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又增强了画面所表达的感情色彩。后者《秋思》套曲,明代文学批评家王世贞在《曲藻》里品评说:“元人称为第一。”这主要是从音韵的角度加以肯定。其实,套曲的“妙境”除音韵外,还体现在画面的美感之中,以“黄”“紫”“红”“白(霜)”的色彩悦人耳目,怡人心境,引人入胜。这些色彩词同特有景物(秋露、秋霜、美酒)的和谐组合,不仅表达了诗人特有的清高品格,而且还把我们带进了元代林下雅士所歌咏的清秋妙境之中,让我们随诗人“摘花”、“分蟹”、“煮酒”的时候,想象出一幅幅诸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惯耐江湖十月霜”、“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优美画卷。
乔吉、张可久的散曲以清丽典雅著称。乔吉散曲中的色彩词,颇为鲜艳。如“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秋江傍晚,江头眺望,红的枫林,绿的山峦,有如一道道胭脂和翡翠砌成的屏障。色彩多么怡人眼目。再如:“红梨叶染胭脂,吹起霞绡,绊住霜枝。”《双调·折桂令·秋思》)写送别场景:“殷勤红叶诗,冷淡黄花市。清江天水笺,白雁云烟字。”用红叶,黄花,清江,白雁构成一片天高气清的秋色图景,寄寓着诗人依依惜别的情思。张可久是元代专写散曲的作家,其语言华丽典雅,色彩词的运用几乎每篇可见,而且极其浓艳。如《双调·折桂令·次韵》:“翠树啼鹃,青天旅雁,白雪盟鸥。”“绿满江南,红褪春愁。”绿树与杜鹃,蓝天与大雁,碧水与白鸥,一片翠绿中又揉进花的红色,几种色彩交相辉映,尤如一幅刚画就的水彩画。
少数民族诗人具有绿色草原文化的特有气质和民族精神,尤喜用明快、鲜艳、浓烈的色彩词。如畏吾儿作家贯云石,最具代表性的色泽明丽浓艳的散曲要数《中吕·粉蝶儿·西湖十景》,在他笔下,“青霭霭山抹柔蓝,碧澄澄水泛金波。”“绿依依杨柳千株,红馥馥芙渠万朵。”“娇滴滴粉黛相连,颤巍巍翠云万朵。”“叠叠层楼画阁,簇簇奇花异果。远远的绿莎菌,茸茸的芳草坡。”他尽情挥洒生花妙笔,将西湖的景致表现得酣畅淋漓。此外如勃罗御史、阿鲁威、刘庭信、薛昂夫、兰楚芳、萨都剌等人的散曲,无不以情浓采丽著称。
元散曲作家不仅用浓墨重彩描绘自然景物,而且还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如杨果《越调·小桃红》“采莲湖上棹船回,风约湘裙翠”。一位风姿绰约身着翠绿裙儿的少妇,形象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张可久《仙吕·锦橙梅》,描写一位歌妓容颜体态的魅力,风韵楚楚动人,以至使诗人惊艳倾倒,为之销魂。“红馥馥的脸衬霞,黑髭髭的鬓堆鸦。”“颤巍巍的插着翠花,宽绰绰的穿着轻纱。”花朵般红艳的脸蛋象映衬着彩霞一样光彩照人,乌黑秀美的鬓发上珠翠首饰颤巍巍的摇动,淡雅的轻纱宽松地披在身上,真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张鸣善《中吕·普天乐·遇美》:“海棠娇,梨花嫩,春妆成美脸,玉捻就精神,柳眉颦翡翠弯,香脸腻胭脂晕,款步香尘双鸳印,立东风一朵巫云。”曲中描绘了一位少女的绝世姿容,如海棠般的鲜艳,梨花般的柔弱,脸庞如绚烂春色,肌肤如晶莹的玉石,弯弯的眉,淡淡的胭脂,轻盈的步态,高耸的发髻,犹如巫山一段云。难怪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赞道:“张鸣善之词如彩凤刷羽。藻思富赡,烂若春葩;郁郁焰焰,光彩万丈,可以为羽仪词林者也,诚一代之作手,宜为前列。”此外,如庾天锡的《双调·雁儿落过得胜令》中以色彩塑造隐士风姿;乔吉《中吕·山坡羊·寓兴》中“白,也是眼;青,也是眼。”用黑、白二色寓意世态炎凉,表明诗人对世俗的蔑视。
由上可见,情浓采丽,是元散曲的审美特征。如果散曲失去了这一审美特征,也就失去了文采,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感人的艺术魅力,正如一朵花失去了芳香和神韵,其审美价值就值得怀疑了。元散曲丰富的色彩世界,构成了散曲的血气、精神、风貌、脉搏。赤橙黄绿青蓝紫,是通过文字熠熠闪射出来的光芒,是一种神奇的光彩和气息,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审美情结:两种色彩世界的联结点
大自然是色彩的宝库。但是,“文学作品中的色彩世界是作家创造的,这和自然界的色彩不一样。除了形态上和色彩的丰富性上存在着差异之外,主要是文学作品中的色彩具有作家审美的和情感上的意义。”(刘烜《文艺创造心理学》第304页)这就是说,作家笔下的色彩,不是直陈自然环境的颜色,而是通过对色彩的选择,特别是通过具体描绘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展示其主观心灵的色彩世界。因此,自然界的色彩世界要进入元散曲的艺术领域,就必须通过创作主体的审美情结,作为两种色彩世界的联结点,使色彩成为寄寓作家某种理性思考和情感内容的一种符号。作家用这种色彩符号,来形象地比附、暗示某种有形的事物或无形的、抽象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之产生相应的审美趣味和感情效果。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借色寄情的着色艺术。歌德就将色彩划分为积极的色彩(红、红紫)和消极的色彩(蓝、红蓝)。积极的色彩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有生命力的和努力进取的态度”,消极的色彩,也可以说是被动的色彩,“适合表现那种不安的,温柔的和向往的情绪”。当然,判定色彩能引起人怎样的情感反应,还与审美主体本身的状况有关。元散曲中,审美主体的情感世界与色彩画面的情感间的关系则是通过象征、比喻、错位等审美情结来实现的。
色彩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有的比较固定,约定俗成,有的则是适应特定的情境而临时产生的,并不固定,它常常随作者思想感情的不同而不同。在元散曲中,诗人常用色彩来揭示或增强主观的感情色彩。同样是红色,“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一写悲,一写喜。同样是写秋的《越调·天净沙》,马致远用灰暗的色调表现了一种萧条、寂寞、悲凉的情景;而白朴由于在最后两句用了“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将前面的寂寞、迷朦的秋色一变而为鲜明、灿烂的秋景,在情感上,似乎惆怅失落得到了某种安慰和补偿。可见,不同心境的人对于同一景物色彩有不同的感受。这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色彩的象征意义,无论是较固定的,还是非固定的,实际上都是将色彩以实变虚,化实为虚的一种艺术运用。其艺术作用在于引导读者透过五彩斑斓的色彩意象,去联想、想象、寻觅、发掘色彩所含而不露的意义宝藏,创造含蓄、隽永、意味无穷的艺术表达效果。元散曲中常用红叶、黄花、夕阳、昏鸦等色彩极浓的意象来表现文人士大夫隐逸自适的怀抱、啸傲江湖的逸兴、怀才不遇的牢骚、壮志难酬的失落。而徐再思的《中吕·普天乐·西山夕照》却用同样的色彩,表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之情,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晚云收,夕阳挂,一川枫叶,两岸芦花。鸥鹭栖,中羊下。万顷波光
天图画,水晶宫冷浸红霞。凝烟暮景,转晕老树,背影昏鸦。散曲中,暮云渐收,残阳斜挂,红色的枫叶,白色的芦花,黄、黑、白色的牛羊,五光十色的霞光倒映水中,就连老树、昏鸦也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色,它们不再是孤寂、凄凉意义的象征,而是一种美化了的意象。作者的情感、思绪、心境就孕含在这色彩浓烈的景物之中。再如刘秉忠的《南吕·干荷叶》:“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写秋风中荷叶的憔悴之状,夜来的一场浓霜使本已由翠绿变为深青的荷叶,更由深青转为枯黄。联系全曲,其象征意义是丰富、复杂的。“黄色明度高,光辉四射,最能刺人眼睛。它能使人产生兴奋、明朗、希望的感受。淡黄色使人觉得和平与温柔,深黄色使人感觉庄严高贵。”(刘烜《文艺创造心理学》第306页)但在这首散曲中,黄色却象征一种衰败、憔悴。就人生而言,其所象征的是青春之不再,年华之易逝;就世事而言,其所象征的是江南之残破,繁华之消歇。这些色彩的象征意义,都是由实而来,化实为虚,以客观的物质色彩,来揭示主观的感情色彩,从而获取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效果。
色彩或带色彩的物象还具有比喻的意义,这种比喻,可以使诗更具形象性和感染力,表达更为丰富的情感和思想,收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如张可久《南吕·一枝花·湖上归》中所创造的清幽淡远的艺术境界,“花如人面红,山似佛头青。春色围屏,翠冷松云径,嫣然眉黛横。”用“人面红”喻花,比喻用得极为活脱。佛头青,佛陀之发被称为“绀发螺髻”,绀为青中带赤的颜色,螺旋发型称作“青螺髻”。这两句既写出花、山的颜色,又写出鲜花、山形的秀美和精神。后三句用碧绿的屏风比喻西湖四周的山,用松云径喻隐居的环境,隐含了李白的诗句:“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然后又进一步用美人的眉黛喻山的远景。这样,本应产生热烈气氛的色彩词,便和谐地融入了清幽淡远的意境中,暗喻诗人鄙薄世俗,寄情山水的高洁情趣。再如他的小令《越调·天净沙·鲁卿庵中》:“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红叶山斋小小。”暗喻友人隐居环境之幽静,品格之高洁。青苍的云彩,清澈的秋水,贴切喻示隐者古朴、悠然、明净的心怀。红叶掩映的小小山房,更显其雅致。既创造了优美的意境,又流露出诗人对友人的赞美和敬慕,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另外,元散曲在描绘人物形象时,常常把人的美物化为大自然的美丽景色,色彩词在其中的作用亦不言而喻。如前面提到的张鸣善的《中吕·普天乐·遇美》用海棠花的娇艳、梨花的白嫩、玉石的晶莹反复比喻、渲染少女的美艳。关汉卿的名作《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摇四壁翡翠浓阴,射万瓦琉璃色浅。”用珠帘的光彩夺目、流彩溢金暗喻一代名优朱帘秀出台亮相时的光彩照人的姿容。此外,散曲中出现最多的还是被点染了鲜亮色彩的一些物象,如“青山”“白云”“黄花”“红叶”、“苍松”“翠竹”“清溪”“新月”等等。这些物象所构成的是一个极澄极静的世界,是远离闹市、官场的世外桃源,它不是“红尘”外的仙境,也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观,而是元代社会文人士子心灵中的圣所、理想中的“隐士”精神世界的外化,它表现的是一种淡泊名利、超然绝世的人生态度。
色彩与主体的情感一致,互相映衬,利用色彩的不同性格,引起人们不同情感反应,这在元散曲中有大量的表现。然而,为了更好地显示自己的感情,散曲家们往往运用错位的手法,使色彩与主体的情感相背离,构成情感与客体的反衬,达到“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艺术效果。如杨果《越调·小桃红》,是一支写少妇忆远的抒情小曲,曲中表现女主人公盼君不归、望穿秋水、美人迟暮、满腹闲愁的意绪,却偏用艳丽的色彩来描绘,“风约湘裙翠”,习习的晚风吹着她翠绿的裙儿,一个绰约多姿的少妇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最后以景结情,以物喻人,在物我对比、情景交融中,情味更深,韵致更佳。“晚凉多少,红鸳白鹭,何处不双飞。”艳丽的画面,鸟的双飞,反衬女子的孤独寂寞,言虽尽而意无穷。有时,诗人又用两种相反的色彩、景观来反衬,表面看来似乎极不协调,其实达到了情和景的高度统一,妙合无垠,也即是“含蓄不露,意到即止”的传达手法。如张可久的《双调·清江引·秋怀》便是运用色彩的浓淡、明暗,反衬人物内心的悲欢、苦乐。“红叶天”、“黄花地”,是显色,是大景,是用浓墨重彩涂成,这大的背景,是客观外在的自然环境;雨中芭蕉、梦里的秋雨,是隐色、小景,是主观感觉的投影。显色、大景是用来以衬人物心理的,而隐色、小景,才是人物的真情实感,才是阴沉、灰暗的人生的写照。
和谐鲜丽:创造色彩世界的美学原则
色彩能唤起人的审美愉悦。但实际生活中的色彩,并不是单纯的,大都是不同颜色配合而成的复杂的有机构成。文艺作品中,若干色彩词的杂乱拼凑、堆积,并不能产生美感。色彩的生命,在于既要多样,又要有秩序。散曲的色彩世界之所以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正是因为散曲作家把握住了色彩组合的美学规律,遵循色彩世界的美学原则,使几种色彩有机地配合在一起,通过不同颜色之间的关系构成一定的节奏感。
首先,诗人通过色彩词语的准确选择运用,构成时空的变幻、流动。在这里,时空的变换与生命情感的流动都借色彩描绘来实现。元散曲中写春、夏、秋、冬四季组诗的作品颇多。总体来看,诗人对季节的观察和感觉是细致深切的,对大自然的景物和色彩在四季中的变化是敏感过人的,对季节特征的把握与表现是准确传神的。而且诗人在景物、色彩的描写中有着情感的寄托,甚至还有某种人生的哲理隐含其中。关汉卿的《双调·大德歌》“春”“夏”“秋”“冬”四首,实是四季情歌,写一位少妇从春盼到夏,从秋盼到冬的离别之苦,对爱情的忠贞执着。通篇以景喻少妇的心理状态,春天的绿柳杨花,子规啼叫,乳燕成双;夏天红艳的石榴花,成荫的绿杨,既标明时间的流逝,又反衬少妇苦涩的心境。秋景和冬景的萧瑟,又从正面衬托出少妇孤独、寂寞和凄苦的内心世界,词的色彩亦变成暗绿的芭蕉和灰白色的雪。白朴《越调·天净沙》中,青色与红色标志春,浓绿色标志夏,绿、白、红黄的混合标志秋,白色、枯黄色标志冬。贯云石《正宫·小梁州》分别为西湖四季画出四帧精致生动、韵昧清醇的水彩画,体现出西湖四季各自的魅力。西湖之春,“春风花草”,“桃红柳绿”,骢马暂系,水鸟息羽;西湖之夏,“画船绿柳”,“佳人才子”,“一钩新月”,“十里芰荷”;西湖之秋,“芙蓉映水”,黄菊盛开,秋风阵阵,金桂飘香;西湖之冬,“彤云密布”,“凛冽寒风”,大雪纷飞,粉装素裹。这既是对四季时空推移的描绘,又体现出在同一场景上四时行乐的鲜明区别。无论是写春夏的暖色调,还是写秋冬的冷色调,都把读者引入了一种境界,都展示了诗人淡泊名利,飘然出世的心胸。畏吾儿诗人贯云石游戏人生,啸傲江湖,诗酒风流,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自然地融进景物色彩之中,融进时空意识之中。元散曲作家用色彩的符号,表达了特有的时空意识见解,即是用色彩来创造艺术空间,用色彩标志时空的变换,用色彩表达情感的动态过程,即生命流动的过程。
其次,元散曲作家特别重视色彩搭配以建构色彩世界的形式美,即衬托性着色艺术。在艺术作品中,选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色彩,分为宾主,在统一的艺术布局下配置各色的不同比例,使之产生相互映衬、以宾托主的审美效果——这种衬托性着色艺术,关键是要看作者选色配彩是正适当,是否正确把握色与色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究各种色彩有没有协调统一于一个总色调之中,相互映衬,突出主色调,从而达到以此衬彼、化平庸为神奇的艺术效力。元散曲中色彩的运用搭配,往往遵循了这一美学原则。如关汉卿的名篇《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是以青绿色为主色调,从近处看,苍松如盖,竹海如云,繁多的草药,满坡的茶丛,一片郁郁葱葱;从远处看,山色青如千叠翡翠,江水碧似万顷玻璃,到处是清溪、绿水,整个杭州都掩映于这碧云翠霭之中。诗人又用“花蹊”、玉带似的盐场、清波之上的大小画船、万绿丛中的建筑物“飞阁流丹”,衬托出秀丽江南的葱茏之色;画船和建筑物,又造成一种运动感和立体感,给画面以盎然的生机。诗人把姹紫嫣红的花蹊、白色的盐场、彩色的画船、红色的飞檐等几种事物的色彩都统一于青绿色这一主色调之中,使人感到色彩清新而丰富,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再如元代著名画家倪瓒的小令《越调·小桃红》的景物描绘,运用的也是这种衬托性着色艺术。“一江秋水澹寒烟,水影明如练,眼底离愁数行雁。雪晴天,绿萍红蓼参差见。吴歌荡浆,一声哀怨,惊起白鸥眠。”作者用画家的眼、诗人的笔描绘出一幅美丽的秋江图,充分显示了他画家兼诗人的高超艺术造诣。小令中,“江”是诗人描绘的主要对象,“秋水”,点明季节,并限定了整幅图画的色彩和景物特点。“水影明如练”,是整幅画的主色调。“雪晴天”,指明朗的晴天,“雪”,雪白,形容词。在明朗的晴天,江边红红绿绿的水草辉人眼目。这里,“雪晴天”“绿萍红蓼”都是对白练似的秋水起衬托作用的,更显得秋水的清澈、明净,色彩斑斓的水草,还给这幅秋江图增添了明远、清丽的特点。元散曲家在运用衬托性着色艺术中,都非常讲究宾、主色彩搭配组合的相对比例。因为宾、主色彩的比例恰当,衬托才能不落俗套。比如张可久《越调·天净沙·鲁卿庵中》便是以绿衬红。“青苔古木萧萧,苍水秋云迢迢”,是写远景,是隐者所居的幽深的大环境,色调是大片的青苍、浓绿。在这样的背景色彩中,出现“红叶山斋小小”,这种巧妙的色彩搭配,是以大面积青绿色为宾,面积小红叶山斋为主,收到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妙,给人以优雅、冷艳的美感。
第三,利用色彩的对比造成读者强烈的审美直观效果。色彩的衬托主要是以此衬彼,如清代邹一桂所言:“举一色为主,而他色附之。”而色彩的对比则是相互生发,相得益彰,使双方的色彩效果在对照中更显鲜艳、强烈、分明。元散曲的艺术魅力,亦得力于对比着色艺术的巧妙运用。这种对比着色艺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相近的一组色彩互相对比,使之互相烘托,相辅而相成;有的是差别较大的一些色彩互相对比,使之构成鲜明的对照,相反而相成。如白朴的《双调·沉醉东风·渔夫》,他首先为“渔夫”设计了一个优雅的环境,“黄芦岸白萍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诗人精心选取了“黄”“白”“绿”“红”四种色彩,渲染他精心选择的四种景物,这四种色彩的景物相映成趣,五彩缤纷,绚丽多姿,构成一幅美丽的水乡风光。这便是“渔夫”的活动场所。“渔夫”实是隐士的化身。白朴幼年经历了蒙古灭金的变故,家人失散,跟随他父亲的朋友元好问逃出汴京,受到元好问的教养。他对元统治者异常反感,终生不仕,却仍找不到一片避世的净土。因此,他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渔夫”身上。四种色彩互相映衬,色彩鲜明,意境开阔,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抒发了诗人恬淡闲适的心境。赵善庆《中吕·普天乐·江头秋行》,同样写秋江景物,就与白朴大异其趣。赵善庆是用“黄”“绿”两种色彩的对比,加一个“添”字,一个“淡”字,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季节的更替,以及农家秋收的喜悦。“黄添篱落,绿淡汀洲”。农家院落里,篱笆上,黄澄澄的稻谷堆积起来,而河上汀洲,芳草已渐枯,大地显出了“黄添绿淡”的变化。这是一组相近的色彩,互相映衬点染,使秋色不至于萧瑟惨淡。元散曲中写秋景,常用“黄花”“红叶”“青山”“绿水”组成画面,这也是运用色彩对比映衬的原理,使各种颜色互相搭配,更显出各自的特色,来创造绚丽多彩的艺术境界。另外,两种反差较大的色彩对比运用,在元散曲中例子就更多了。如庾天锡《双调·雁儿落过得胜令》中写隐士的风姿,“以他绿鬓斑,歌枕白石烂。回头红日晚,满目青山矸。”绿鬓斑与红日晚,白石烂与青山矸互相映照,色彩对比鲜明,一位志趣高洁、与青山白石为伴的隐士形象,如在目前。此外,散曲中常看到一些反差较大的色彩词相对比,如“白鸥”和“红鸳”、“白花”和“红树”、“白发”和“黄花”、“白练”和“青淀”、“白眼”和“青眼”等等。还有不少散曲则用色调的明暗相对比。这样使散曲更富有诗情画意,景物描绘更富层次感和色阶明暗对比的空间立体感,使散曲的气韵更加生动,更加和谐。
元散曲中的色彩世界,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审美新领域,也是认识元散曲的地位、价值的一个重要角度。过去学术界对此课题少有人探究。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抛出引玉之砖,希望引起海内外同仁的注意,以期有助于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